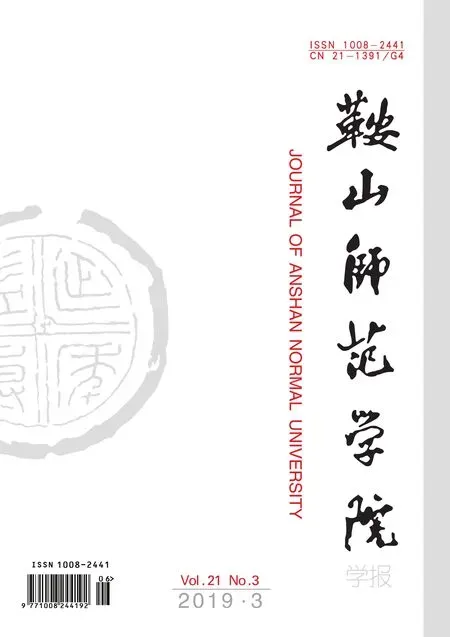叛逆背后的爱
——莫里森小说《秀拉》的姐妹情谊解读
徐 闽
(福州大学 至诚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托妮·莫里森是当代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她凭借《宠儿》和《所罗门之歌》分别获得198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和199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莫里森创作了以《所罗门之歌》为代表的长篇小说十部及大量文学评论文章,为黑人文学创作做出杰出贡献。莫里森的作品主题深刻,人物立体,她将小说视角聚焦于黑人文化,通过对黑人言语、窘迫生活、两性关系及精神世界的描写,“力拨迷雾向人们揭示人间之正道、生活之真谛”[1]。《秀拉》是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在《秀拉》中,她将秀拉塑造成了一位离经叛道,成年后与黑人社区格格不入,突破传统道德底线,极具颠覆色彩的黑人女性,秀拉和好姐妹奈尔一同成长,姐妹俩性格差异悬殊,童年时代开始的姐妹情谊伴随彼此,成年后,秀拉的叛逆和奈尔的顺从给两姐妹带来了全然不同的人生结局。“《秀拉》这本书的思想是我最钟爱的,但是写法也是独一份儿”[2]。这是笔者一心想要探究该部作品艺术魅力的原因。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秀拉》进行了研究,Novak从小说主题,结构及叙事角度来分析《秀拉》中的创伤书写,指出在延续非裔文化的情境下哀悼创伤历史[3]。Nigro对秀拉和奈尔的成长历程及女性友谊进行了描述,认为莫里森给读者讲述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悲伤故事,让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小说中的“底部”黑人社区,体会他们的愁苦[4]。Reddy建议应将小说中渗透式存在的死亡主题,文化历史背景的叙述,双主人公成长历程到后期分离及小说按年代叙述的写作结构结合起来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抓住小说的主题。此外,他还将《秀拉》当成一本战争小说来分析[5]。国内研究方面,蒋欣欣从“母辈认同”“女孩认同”“自我认同”和“精神认同”四个方面分析秀拉的自我建构过程[6]。魏颖超运用赞赏和批判的传统剖析法分析秀拉叛逆的人物形象[7]。刘君涛从《秀拉》在结构上的镜像式对称角度探讨小说的人物组合和叙事风格[8]。大多数研究是从《秀拉》的叙事风格角度分析秀拉的叛逆之旅及对自我的追求,鲜有作者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重要内容姐妹情谊角度来解读小说。因此,笔者将着重解读这部小说中秀拉和奈尔的姐妹情谊及隐藏其背后的作者真实意图。
一、姐妹情谊——自我救赎的基石
法国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在其社会学著作《第二性》中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等方面分析了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真实处境以及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她认为,由于父权制度和女性“内在性”,女性的“他者”地位和自身的社会处境息息相关。这种社会结构和“内在性”导致了女性主体性的缺失。因此,她呼吁女性自身意识发生改变,实现自我救赎。美国女权主义者、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贝尔·胡克斯在其著作《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提出“姐妹情谊”这一政治术语,她强调:“在共同的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联合其他的妇女。这是女权运动应当支持的,这样的联合方式也是姐妹情谊的本质所在[9]。”对于黑人女性而言,姐妹情谊建立是一种重要的自我救赎体验,一种建构黑人女性主体性的方式。胡克斯盛赞莫里森的小说《秀拉》,她认为小说展现了黑人女性为建构自我、实现自我救赎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而莫里森自己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当我创作《秀拉》时,我知道我要写一部关于善与恶,关于友谊的书[10]。”姐妹情谊伴随着秀拉和奈尔从少女时代到成年时期,从亲密无间到背叛、迷惘,这一主线贯穿小说始终,小说最后奈尔思考秀拉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开放式结尾引导读者反思秀拉在自我救赎、自我认同道路上的“善”与“恶”。
二、童年时期——姐妹情谊的建立
秀拉和奈尔少女时代姐妹情谊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环境,二是家庭生活。莫里森对小说中社会环境的描写主要通过人物外貌、对话、行为、精神状态等体现。故事起源于秀拉童年时期白人间的一则笑话,白人农场主许诺在黑奴帮他干完一件难办的活儿后给他一块土地。最后,白人农场主给了黑奴山顶上的一块土地,黑奴不解,认为土地在山顶,而山谷的土地才是低地。白人农场主解释道:“从我们这里看是高的,可是当上帝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低地了。所以我们才这么叫它。那是天堂之底——有着最好的土地[11]”。黑奴得到了山顶上的一块土地,而住在谷地的白人拥有富饶而肥沃的土地。结果,对于黑奴来说,“在那里耕种真能让人累折了腰,那里水土流失严重,种子都会被冲掉,而冬天寒风又呼啸不已[11]。”这种赤裸裸的欺骗残忍地将黑人和白人隔离开来,在黑人心中蒙上重重的阴影。黑人夏德拉克在战争中被炸伤,战场上亲眼目睹同伴的死亡,回到黑人“底部”社区始终无法从战争的阴影中抽离,得了狂躁症,终身处于惊吓之中。好不容易从令他恐惧的医院逃出,却被当成流浪汉被警察带进监狱。他迷惘、痛苦,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语言、身份,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他创立“国家自杀日”期望摆脱自己的恐惧,希望“底部”所有对死亡有恐惧的人在“国家自杀日”这天释放自己的恐惧,得到自由。秀拉和奈尔在夏德拉克摇着的牛铃声中,在他的吼声中,在他疯癫的行为下度过童年时期。夏德拉克疯疯癫癫、毫无理智的行为无疑给处于童年时期单纯的孩子内心也蒙上了阴影,孩子们似乎懵懂地知道黑人的窘困,地位的低下。慢慢地,“底部”的很多孩子习惯了夏德拉克的荒唐行为,而自杀日也悄无声息地融入居民的生活中。看似麻木而毫无希望的“底部”谁曾想会是秀拉和奈尔姐妹情谊产生的摇篮。秀拉的家粗犷而朴实,祖母伊娃在丈夫波依离开后含辛茹苦养大三个孩子,但却在最宠爱的小儿子应征入伍回来后烧死了他。秀拉的父亲在她三岁时离世,母亲在父亲离世后便钟情于男人,秀拉从小就看着自己的母亲和不同的男人,慢慢地,也觉得性是稀松平常、给人带来愉悦的事了。奈尔的父亲威利是名海员,常年在外,母亲海伦娜骄傲不可一世,她的家整洁而压抑,即使不喜欢但也没更好的解决办法。直到她遇到秀拉,在对方身上找到了惬意和舒畅,因为“只有和秀拉在一起时,她的这种性格才能自由驰骋[11]。”“黑人女性们聚在一起,相互寻求关爱及支持性谈话,这只有另一位黑人女性能做到[12]。”对于童年时期的黑人女孩,他们同样需要依靠彼此,也只有依靠彼此来自我界定。十二岁的秀拉和奈尔会一起围观斗殴,一起研究柏油娃娃酒瓶上的标签,一起研究男人。她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对方能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快乐和痛苦。秀拉和奈尔的童年姐妹情谊还体现在对自我的认同上。秀拉在放学路上,用割伤自己指尖的方式保护自己和奈尔,吓跑了欺辱她们的白人小男孩,勇敢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友谊成为女性自我定义的手段,在这种关系中厘清自我身份,也反映了自我最基本的层面[13]。”奈尔在1920年随自己的母亲海伦娜到南方看望病危的外祖母时,由于母亲上错了车,在被白人列车员质问后向对方露出挑逗的微笑。奈尔心中莫名升起一股仇恨,当她看到同车厢的几位黑人士兵对她母亲露出阴沉沉的目光时,这股仇恨更转化成了羞耻,她下定决心这辈子不会让任何男人用这样的眼光看着她。回来后,奈尔意识到“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们的女儿。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我[11]。”她的心中积聚着力量,既快乐又恐惧。快乐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和母亲的不同,和“底部”大多数黑人女性的不同,在种族歧视下,她的自我意识开始萌芽,恐惧是因为她还是个小女孩,她从小在母亲营造的严厉而压抑的氛围下长大,她不知道这种意识是对是错,是善是恶,她害怕,但她内心渴望自我得到认同,成为伟大的女性,和母亲不一样的黑人女性。奥德烈·罗尔蒂说,“对于黑人女性来说,假如我们不定义自己,我们就会被别人定义——对别人有益,却对我们有害[14]。”秀拉在一生义无反顾地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奈尔成为唯一能和她的精神世界交流的人,是她的精神同盟。童年时期秀拉和奈尔姐妹情谊的建立是以双方的精神契合为基础的,但不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性格特点为后期秀拉对奈尔的背叛,积极追寻自我以及奈尔成为性别主义牺牲品打下基础。
三、成年时期——姐妹情谊的转变
成年时期秀拉和奈尔的姐妹情谊经历了“爱、背叛、爱”三个阶段,奈尔新婚时期和秀拉十年后刚回到“底部”社区时,她和秀拉依然是彼此眼中最美好的朋友。然而,随后秀拉的背叛成了奈尔心中永久的痛,她无法释怀,甚至无法原谅,直到秀拉死后,当奈尔再度遇上夏德拉克,一番谈话勾起一段回忆,她才意识到自己对秀拉是爱,这份情谊没有改变。
(一)少女时代延续的爱
结婚是成年的标志。1927年,奈尔和裘德在“底部”举行了地道的婚礼,奈尔全心全意爱着裘德,认为和裘德在一起的感情甚至比与秀拉的友情更为重要。这时的秀拉仍将奈尔视为最亲密的伙伴,他比奈尔还激动,在奈尔的婚礼上丝毫不马虎,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秀拉、奈尔和在场的所有人快乐无比地享受着婚礼的美好。此时的奈尔感受幸福,只有秀拉才能给她自由感,只有秀拉能看透她的心思,也只有秀拉才能将她从苛刻而压抑的家庭中抽离出来。她们亲如姐妹,“对她们俩其中一个的赞美就是对另一个的褒奖,而对一个人不逊也就是对另一个的挑衅[11]。”秀拉在奈尔的新婚之夜离开了“底部”,直到十年之后,她们才再次重逢。
十年后,秀拉回到了知更鸟成灾的“底部”。知更鸟本是善良、和谐的象征,但数量过多则会带来灾难,在《圣经》中,上帝有时会引发自然灾害作为对罪的审判,秀拉就像是上帝的使者,这为她将给“底部”带来的改变做好铺垫。秀拉在某个下午来到了奈尔的家,这时的奈尔按照黑人社区传统模式生活着,结婚,生子,照顾家庭。“带有性别歧视的思想意识告诉妇女们,作为妇女就是做一名受害者[9]。”奈尔已经习惯了白人甚至黑人男性的歧视,她只是接受眼前的一切。她期盼着能和回到“底部”的秀拉聊聊双方这十年来的所见所闻。秀拉讲述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奈尔倾诉了家庭之乐,她们回忆童年,说说笑话,奈尔已经很久没有开怀大笑过了,她觉得只有秀拉让她快乐,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更文雅。
(二)回归后噬心的背叛
奈尔毫无保留地爱着裘德,相夫教子,爱情战胜了她和秀拉的姐妹情谊,她无法想象秀拉会和自己的丈夫有染。秀拉遇见了裘德,因为狂野的笑容和古怪地看问题方式,裘德觉得这个女人很有趣。他们偷情的一幕被奈尔撞见,奈尔崩溃了。十年来,她的生活只有裘德和孩子,她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而秀拉的所为打破了一切的美好,这让活在婚姻这张“蜘蛛网”中的奈尔无所适从,更多的是撕心裂肺的疼痛。遇到这样的事,没有人出来为她拿主意了,因为少女时代,出主意的总是秀拉,而现在裘德正是因为秀拉才离开她的,她憎恨、惧怕、大脑一团乱麻,她领会到别的女人口中“再也不去看其他男人”[11]的意思。性别歧视让妇女成为广大男性的性客体[9]。秀拉就像是戴剑复仇的勇士,而这把剑就是——性。此时的奈尔不知道的是被这把利剑所伤害的不只是她,还有“底部”的其他居民。秀拉的主体意识已然觉醒,她是来复仇的。在去奈尔家之前,秀拉先去看望了外祖母,她憎恨伊娃亲手烧死了李子,她憎恨“底部”女性要做一个好女孩、好妻子的传统,她说:“在你有时间扑灭它之前,我会把这镇子和所有东西撕成两半[11]。”她想亲手点燃叛逆之火,她想奋战到底。奈尔是秀拉十年后选择重回“底部”的原因,她想找到自己的精神同盟,这个对她方方面面全盘接受的好姐妹。但是,她发现奈尔也成了“底部”麻木的黑人女性中的一员,那个曾经在镜子前说“我不是奈尔。我就是我。我[11]。”的奈尔在婚姻现实面前放弃了和秀拉曾经共同的认知,秀拉感到震惊和伤心。“我们必须定义自我关系,我们需要一场女权运动来结束性压迫[9]。”秀拉用“性”这个工具来反抗,她对成立家庭、成为贤妻良母毫无兴趣,她认为女性只会成为男人的附属,就如裘德对待奈尔,她不愿在婚姻的漩涡中挣扎,更不愿用自己的一辈子来支撑一个男人,甚至是一个歧视你的男人。她要的是自我,和同伴共同建立的自我。她想“打破对性别歧视的依附,改变女性的意识[9]。”而奈尔只会在来看望秀拉时说“你是个女人,还是个黑种女人。你不能像个男人一样行事。你不能摆出一副独立的架势[11]。”强烈的自我意识让秀拉以最激进且“底部”黑人社区无法接受的方式来解构社区的法规,挑战男权统治,将它们撕成两半。奈尔对秀拉的恨不仅因为秀拉背叛了她,还因为秀拉和裘德有染后马上抛弃了他,奈尔爱而不得、秀拉得而不惜都让奈尔始终无法面对。秀拉和“底部”的大多数有妇之夫都发生了关系,但无一例外,全部都在发生关系后直接将男人们抛开,“男性惧怕妇女性别角色的转换,他们用暴力来展现自己的愤怒[15]。”居民区的人们直接给秀拉定了罪,她是一朵“恶之花”,同时也摧毁了奈尔的世界。秀拉背离传统,拒绝忠贞,对父权制度进行有力颠覆。秀拉和奈尔姐妹情谊的背后是她不妥协,追求独立的“男子气”。
(三)叛逆背后幡然醒悟的爱
奈尔来探望生病的秀拉,事先准备好措辞,让自己看起来就像是个善良的女人看望一个孤独的病人,她告诉自己这是出于同情,并非友谊。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看见秀拉,这个摧残她的身体、摧毁她精神世界的女人躺在伊娃的屋子里,连起身的力气也没有。秀拉交给奈尔抓药的差事,奈尔欣然应允。她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奈尔认为秀拉应该循规蹈矩,做黑人女性该做的事,秀拉不以为然,童年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生活,尤其在她失手杀害了玩伴小鸡且知道自己的母亲并不喜欢她后,她与母辈的认同产生了分裂。她认为“底部”社区所有的黑人女性都在等死罢了,但“区别在于她们是像树桩一样等死。而我,我像一株红杉那样倒下”。“我的孤独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独却是别人的。一种二手的孤独”。[11]秀拉在孤独中死去。很多“底部”黑人也在本应给他们带来希望的开掘隧道工程中丧生。二十多年后,奈尔来到养老院看望年迈的伊娃,伊娃指责当年是奈尔害死了小鸡,奈尔辩解,伊娃的一句“太像了。你们俩。你们从来没有什么区别[11]。”让奈尔陷入了沉思,她回忆起了那个秀拉失手害死小鸡的夏天,回忆起是她打电话给医院拉走秀拉的尸体,她也是唯一参加秀拉葬礼的黑人。她心情沉重,但似乎曾经如乱麻的大脑慢慢清晰起来。她在回程路上遇见了夏德拉克,夏德拉克就像是串起往事珠子的穿线人,奈尔大声痛哭,“我一直,一直,以为我想念的是裘德。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女孩”[11]。奈尔意识到了秀拉才是她的灵魂,她理解了秀拉。这份姐妹情谊中的同性之爱是“一种爱的完美典范,它越过了种族、性别和阶级的障碍,抛开家庭,社区的束缚,是最纯洁的爱[16]。”悲剧的背后是认同,是爱。
四、结语
姐妹情谊是《秀拉》的主线,通过秀拉和奈尔从童年时代到成年时期的姐妹情谊,刻画了一个反抗男权制度下妇女性别角色的人物。莫里森塑造秀拉的意义在于用秀拉叛逆行为唤醒黑人社区,促进黑人女性的觉醒,奈尔的觉醒则是莫里森对整个黑人女性群体身份认同寄予的希望所在。童年时代曾和秀拉一起追寻自我的奈尔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悲哀,自我意识再次觉醒,她成为黑人女性自我救赎的后继者。“黑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要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自我,必须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才能有真正的生活[1]。”莫里森以姐妹关系为主线,对秀拉和奈尔两个角色的塑造,开放式的小说结尾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愉悦,而非失望的凄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