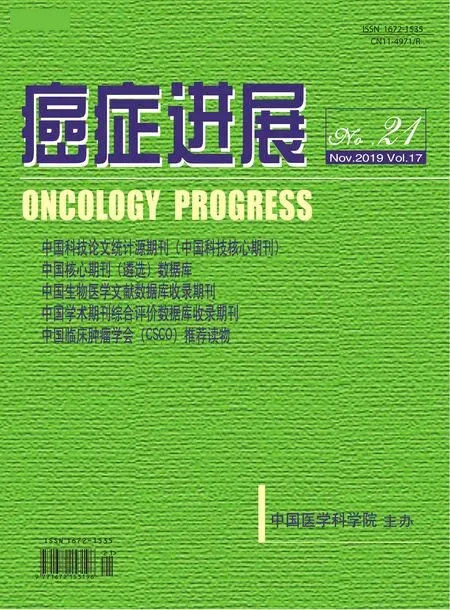双重打击淋巴瘤的研究进展△
王岭,潘云,高波
1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0
2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云南 大理 671000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是一种由多基因共同作用的遗传性疾病,MYC、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 cell lymphoma/leukemia-2,Bcl-2)和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6(B cell lymphoma/leukemia-6,Bcl-6)基因易位是最常见的基因学异常改变。研究发现,15%的DLBCL患者中可见MYC基因易位,超过30%的DLBCL患者中可见Bcl-2基因易位,约33%的DLBCL患者中可见Bcl-6基因易位[1]。在2016年版世界卫生组织(WHO)淋巴瘤分类标准[2]中,将双重打击淋巴瘤(double-hit lymphoma,DHL)正式归类为高级别B细胞淋巴瘤(high grade B-cell lymphoma,HGBL),并将其定义为一类伴有MYC或Bcl-2基因易位的侵袭性淋巴瘤。严格地说,“双重打击”是指MYC基因与另外一个基因同时发生易位,通常为MYC和Bcl-2基因发生易位,也可为MYC和Bcl-6基因易位[3],而MYC、Bcl-2和Bcl-6三个基因同时易位的DLBCL被称为三重打击淋巴瘤(triple-hit lymphoma,THL)。部分原发性纵隔/胸腺大B细胞淋巴瘤(large B-cell lymphoma,LBCL)属于DHL[4]。DHL患者常具有高侵袭性,对现有的一线化疗方案利妥昔单抗联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R-CHOP)不敏感,生存时间短(中位生存期为0.2~1.5年)[5]。近年来,DHL的检出率不断上升,深入对DHL的认识有助于指导DHL的临床治疗和预后判断。本文对DHL的生物学特点、诊断、预后及治疗等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DHL 的分子生物学特点
MYC基因是较早发现的一组癌基因,是转录因子家族的重要成员,编码细胞核内磷酸化蛋白质,通过参与调控基因组部分基因的转录,从而影响细胞的增殖、分化、转录和凋亡等正常生命活动[6]。染色体易位、序列调控和启动子区域的突变及拷贝数增加等均可使MYC基因异常表达,致使MYC蛋白的表达上调,最终导致细胞过度增殖[7-8],因此,活化的MYC与肿瘤的形成密切相关。MYC与免疫球蛋白重链(immunoglobulin heavy chain,IGH)基因易位是MYC蛋白过度表达的最常见诱因,IG启动子结构异常可导致信使RNA水平和MYC蛋白的表达水平增加。
MYC基因异常表达可促进肿瘤的发生。MYC基因在Burkitt淋巴瘤(Burkitt lymphoma,BL)、DLBCL等多种淋巴瘤中异常表达。MYC与IGH基因易位是BL的特征性分子遗传学改变,8q24染色体与14q32染色体易位是MYC基因驱动BL的淋巴瘤原型[5,9]。MYC基因易位对BL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Bcl-2是与凋亡相关的原癌基因,最初是从滤泡性淋巴瘤细胞染色体14和18的异位断裂点(14;18)上分裂出来的,在滤泡性淋巴瘤中最常见的染色体易位位点是t(14;18)(q32;q21),该易位导致Bcl-2与IGH基因融合,使Bcl-2基因异常表达。Bcl-2基因是抗凋亡基因,位于18q21染色体上,编码促存活蛋白,可抑制肿瘤细胞凋亡。氧化应激、基因组紊乱及含BH3结构域的蛋白的表达均可诱导Bcl-2基因异常表达[10]。在恶性淋巴瘤中,Bcl-2与MYC基因及其他原癌基因协同作用可促进淋巴细胞的增殖[11]。Bcl-2蛋白的过表达可通过调控线粒体的通透性抑制细胞色素C的释放,从而延长肿瘤细胞的存活时间,发挥抗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染色体易位和基因扩增均可导致Bcl-2过表达。MYC与IGH基因的易位在BCL中的发生率较高,其中,MYC与Bcl-2基因的t(14;18)(q32;q21)易位较为常见,该易位可导致Bcl-2高表达。在大部分滤泡性淋巴瘤患者中可见Bcl-2基因易位,在少部分DLBCL患者中可见Bcl-2基因t(14;18)易位[12]。
Bcl-6基因属于抗细胞凋亡的原癌基因,位于染色体3q27上,其编码的锌指蛋白在生发中心的形成及细胞活性的维持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正常B淋巴细胞中,Bcl-6基因可促进淋巴细胞的分化,抑制生发中心的形成,在生发中心B细胞来源(germinal center B-cell like,GCB)和具有GCB表型的淋巴瘤中高表达[13]。Bcl-6可抑制P53、MYC、Bcl-2蛋白的活性。另外,Bcl-6基因是淋巴系统功能的重要调节因子,可影响正常淋巴细胞的分化和生发中心结构的形成,从而参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14]。MYC和Bcl-6基因易位型DHL是指Bcl-6基因发生易位后,Bcl-6蛋白的抗凋亡能力下降,变异后的Bcl-6失去了对MYC突变的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肿瘤细胞过度增殖,但MYC和Bcl-6基因易位不影响DHL患者的预后[15-16]。Basso等[17]研究发现,部分DLBCL患者发生了Bcl-6基因易位。
MYC和Bcl-2基因易位型DHL是B细胞在生发中心形成时,暴露于高水平的、活化诱导的胞嘧啶脱氨酶,使MYC和IG基因发生染色体易位,最终产生肿瘤细胞。据统计,MYC和Bcl-2基因易位型DHL在DLBCL中的发生率为0~8%;约65%的DHL发生MYC和Bcl-2易位,约14%的DHL发生MYC和Bcl-6易位;MYC、Bcl-2和Bcl-6同时易位的DHL比例为21%[1]。MYC基因的过表达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Bcl-2基因的过表达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二者同时表达异常可使DHL患者出现一系列具有高度侵袭性的临床表现,影响预后[18]。
2 DHL 的临床特征及诊断方法
DHL的发病年龄较晚,多见于男性,儿童和青少年的发病率较低[19],常表现为肝、脾、纵隔淋巴结肿大,胸腔积液,咳嗽,胸痛等症状;病变常累及淋巴结外组织,受累部位以骨髓、外周血、中枢神经系统多见,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是正常值上限的3~4倍,国际预后指数(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常提示为高中危或高危,Ann Arbor分期较晚[20]。Škunca等[21]研究发现,约82%的DHL患者的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70%的DHL患者的病变累及淋巴结外组织,其中,腹部脏器更易受累。Snuderl等[22]选取了20例DHL和40例DLBCL患者进行研究,结果发现DHL患者的血清LDH水平为727 U/L,明显高于DLBCL患者的366 U/L;DHL患者的骨髓受累比例为59%,明显高于DLBCL患者的23%。Oki等[23]研究发现,84%的DHL患者的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65%的DHL患者为男性,69%的DHL患者的血清LDH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升高。Petrich等[24]对311例DH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发现,67%的DHL患者为男性,81%的DHL患者的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76%的DHL患者的血清LDH水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高,60%的DHL患者的淋巴结外部位受累,41%的DHL患者存在骨髓侵犯,7%的DHL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受累。
DHL在细胞形态学上无特殊特点,其形态学和遗传学特征常介于DLBCL和BCL之间,无法分类[23]。DHL的细胞学形态主要包括以下3种:①DLBCL型,即MYC和Bcl-6基因易位型DHL,肿瘤细胞大,细胞质边缘窄,泡状核。②BCLU型,即MYC和Bcl-2基因易位型DHL,肿瘤细胞中等大小,细胞质少,细胞核呈圆形,呈多态性。③MYC和Bcl-2基因易位型母细胞性BCL,此种淋巴瘤由滤泡性淋巴瘤转化而来,肿瘤细胞小至中等大小,大爆炸样外观,细胞核分散存在。有研究发现,约有21%的滤泡性淋巴瘤转化为DHL[18]。
Li等[25]选取了13例MYC/Bcl-6基因易位型DHL患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1例患者出现了淋巴结外部位受累,其中,9例患者的淋巴结外受累部位达两个或两个以上,淋巴结外受累部位主要包括骨髓、中枢神经系统、胃肠道(胃、小肠或结肠)、肝脏、脾、卵巢、鼻咽、皮肤和软组织。接受脑脊液检查的6例淋巴结外部位受累患者中,3例患者出现淋巴结阳性;11例淋巴结外部位受累的患者中,9例(82%)患者的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10例IPI评价指标信息完整的患者中,8例患者的IPI提示为高中危和高危。
DHL的早期诊断直接影响着患者的病情风险评估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目前,检测MYC、Bcl-2和Bcl-6基因异常的方法主要有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immunohistochemistry,IHC)技术。FISH是诊断DHL的金标准,若检测出MYC、Bcl-2和Bcl-6等基因的易位,即可诊断为DHL。FISH的检测标本无需新鲜组织,可以是福尔马林固定的石蜡包埋组织或悬浮细胞,具有高度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对判断疾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3]。断裂探针和融合探针均可用于MYC基因的FISH检测,其中,断裂探针的灵敏度强,且与IHC检测MYC蛋白的表达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而融合探针可弥补断裂探针检测易遗漏的不足。因此,Carabet等[26]建议,有条件的实验室应对新诊断的DLBCL患者进行MYC断裂探针检测,若MYC为阴性,再进行MYC融合探针检测,并检测MYC阳性的DLBCL患者Bcl-2和Bcl-6基因是否出现易位。由于DHL的发病率较低,且FISH的操作相对复杂,检测价格昂贵,检测时间较长,在资源贫乏的地区,对全部DLBCL患者进行FISH常规检测是不现实的,既不经济,又耗时耗力,因此,FISH在DHL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有限,病理学家和肿瘤学家正在探索确诊DHL的最佳检测方案。
Miyaoka等[27]提出,对DLBCL患者进行FISH检测之前需进行IHC筛查,影响IHC筛查结果的因素较多,检测MYC、Bcl-2和Bcl-6基因表达的最佳阈值的研究尚在进行中,IHC单独作为DHL的诊断方法尚缺乏足够的研究支持,尚不能够以IHC代替FISH对DHL进行诊断。但是,由于IHC检测方法的价格较低,IHC常用于检测MYC、Bcl-2和Bcl-6蛋白的表达情况,成为DHL初筛的检测手段,目前较为公认的阈值是免疫组织化学MYC≥40%、Bcl-2≥70%,此阈值仍需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加以验证。Horn等[28]分析了336例DLBCL患者DLBCL组织中MYC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发现,当MYC≥40%时,IHC结果显示,DLBCL患者DLBCL组织中MYC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51%。Cheah等[29]建议对MYC进行IHC检测时,使用较低阈值(30%)与FISH检测结果相比较以进行判读,从而降低假阴性率。Oki等[23]认为,尽管87%的DHL患者IPI>1,预后不良,但在不易对MYC进行IHC检测的医疗机构中,对具有GCB表型且IPI>1的DLBCL患者而言,FISH仍是比较合理的检测方法。因此,当前DHL的诊断技术仍主要是FISH。
DHL的免疫表型往往为生发中心来源,无特异性的组织细胞形态。应结合DHL患者的临床特征、病理组织形态和免疫表型进行DHL的初筛,然后再使用FISH技术进行诊断。Snuderl等[22]研究发现,20例DHL患者均呈Bcl-2阳性且Ki-67增殖指数为80%~95%,并建议对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存在淋巴结结外部位或中枢神经系统受累患者以及Ki-67增殖指数>80%的非特指型成年DLBCL患者和由低级别滤泡性淋巴瘤转化而来的HGBL等患者进行FISH检测。目前,尚无标准的DHL诊断方案,因此,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筛查流程对DHL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3 DHL 的治疗及预后
大部分DHL患者在接受传统R-CHOP方案治疗后病情会出现恶化。Green等[30]对193例DLBCL患者采用R-CHOP方案进行了治疗;193例DLBCL患者中,6%的DLBCL患者确诊为DHL,中位生存期仅为13个月,而非DHL的DLBCL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可达95个月。高强度的化疗对于发生MYC基因易位的BL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对DHL应采用高强度化疗的方案。Snuderl等[22]研究结果显示,311例DHL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分别为10.9个月和21.9个月,其中,接受强化一线免疫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21.6个月,明显长于接受传统R-CHOP方案治疗的患者的7.8个月(P<0.01),但总生存期无差异。
临床推出了旨在降低DHL患者复发风险的自体干细胞移植战略,其首要指标为DHL患者获得完全缓解。然而,Landsburg等[31]对159例DH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患者的3年无复发生存率和总生存率分别为80%和87%。采用R-CHOP,环磷酰胺、依托泊苷、强的松、长春新碱、多柔比星(DA-EPOCH)方案、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表柔比星/地塞米松与甲氨蝶呤/阿糖胞苷交替使用(R-hyperCVAD)方案和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多柔比星、氨甲蝶呤与异环磷酰胺、依托泊苷、阿糖胞苷交替使用(R-CODOX-M/IVAC)方案治疗后,DHL患者的3年无复发生存率有所不同,分别为56%、88%、87%和91%,其中,R-CHOP方案的治疗效果最差。但是,治疗后,DHL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无明显差异,分别为77%、87%、90%、100%。因此,对化疗后获得完全缓解的DHL患者是否进行自体干细胞移植仍待证实。
由于明确了基因改变在DHL发生、发展中的作用,靶向药物可能会是未来治疗DHL的一线用药。目前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Bcl-2和MYC基因的靶向治疗方面。关于MYC和Bcl-2抑制剂靶向治疗、Bcl-6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靶向治疗方面的研究正在陆续开展。
针对MYC基因易位和MYC蛋白高表达的新型药物可单独使用,也可联合使用。MYC抑制剂包括双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和组蛋白脱乙酰酶抑制剂、极光激酶抑制剂及免疫调节剂苯二胺,可减轻临床前DHL模型的症状,但有效性仍待研究。Cinar等[32]对DHL和THL细胞进行体外实验,结果发现,Bcl-2抑制剂ABT-199以及MYC抑制剂10058-F4、JQ-1均可抑制DHL和THL细胞的生长。有研究表明,Bcl-2抑制剂ABT-263可增加发生t(14;18)和t(8;14)易位的BCL细胞对传统化疗药物的敏感性[33];MYC抑制剂Max-UMax与E3泛素连接酶融合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34]。新型DHL靶向药物或靶向药物联合传统药物有助于提高DHL的疗效。鉴于DHL的总体预后不佳,关于DHL的最佳治疗策略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前,DHL的临床性质尚无法确定。影响DHL预后的因素尚未统一,基因表达是否异常、肿瘤侵袭性的高低、年龄、化疗方案均可能与DHL患者的预后有关。有研究认为,存在MYC和IG基因易位的DHL患者预后较差[35-36]。李俊波[37]研究发现,LDH水平高、2个或2个以上的淋巴结外部位受累、骨髓受累、中枢神经系统受侵、IPI评分>2分均可能与DHL患者的不良预后有关。Oki等[23]研究发现,体力状态、骨髓是否受累直接影响DHL患者的预后。Petrich等[24]研究发现,LDH水平高、中枢神经系统受累、Ann Arbor分期为Ⅲ~Ⅳ期和白细胞计数增多均是DHL患者总生存期的危险因素。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DHL是一种在基因水平发生MYC和Bcl-2或Bcl-6基因易位的高侵袭性BCL,发病年龄大,Ann Arbor分期晚,IPI高,常见淋巴结外部位受累,患者预后差。与DLBCL不同,DHL尚无公认的国际诊疗标准。临床可采用常规IHC对DHL患者进行初筛,依据DHL患者的临床特征、病理组织形态及免疫表型,再通过FISH技术诊断DHL。传统的R-CHOP方案疗效不佳,强化BL治疗是目前治疗DHL的推荐方案,为了使DHL患者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靶向治疗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靶向治疗对DHL患者预后的影响及DHL的最佳治疗方案仍需未来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