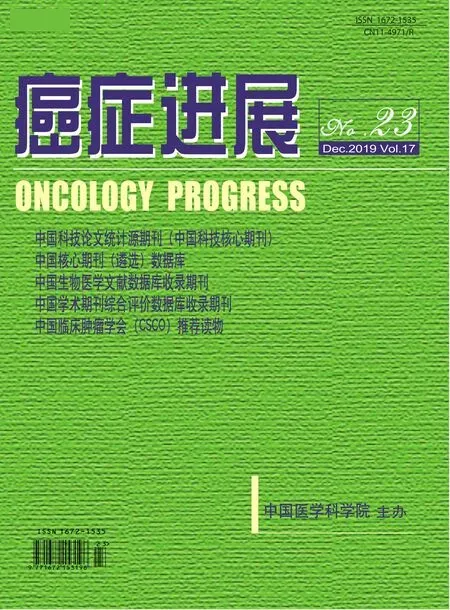系统性炎症指标对胰腺癌预后的价值研究
徐雪君,周天朔,李志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哈尔滨 150000
胰腺癌的预后极差,且缺乏有效的预后评估手段。胰腺癌是中国肿瘤死亡的第六大原因[1]。胰腺癌的预后极差且病死率极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为多数胰腺癌患者初诊时便已处于晚期,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药物治疗方案是临床治疗晚期胰腺癌的重要手段之一。尽管近几十年来对胰腺癌治疗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截至目前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仅约为6个月,5年生存率低于5%[2]。目前,通过肿瘤大小、组织学分级、组织学分型及年龄等临床特征判断胰腺癌患者预后情况的作用有限,而且往往无法准确地对每位患者进行高低危分层[3]。相关研究表明,炎症反应是肿瘤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恶性肿瘤的肿瘤细胞增殖、血管生成、转移及化疗耐药等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4]。因而,通过测量外周血细胞计数反映系统炎症反应,并由此判断胰腺癌患者的预后,为临床医师制订更为针对性的治疗策略提供一定参考。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l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值(lymphocyte to monocyte ratio,LMR)、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ystemic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I)等均与胰腺癌的预后有关,本文就上述指标与胰腺癌预后的关系作一综述。
1 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the modified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mGPS)与胰腺癌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the Glasgow prognostic score,GPS)是基于肿瘤炎症反应的预后标志物,由血清C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浓度和白蛋白浓度组成,能够反映宿主的全身炎症反应[5]。它最初是在一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中发现,结合血清CRP升高和白蛋白降低来评估预后。后来,由于一些研究未能显示低蛋白血症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因此通过强调CRP升高变为改良格拉斯哥预后评分(mGPS)。根据mGPS评分,如果CPR正常(<10 mg/L),无论白蛋白水平如何,mGPS评分为0;mGPS评分为1分时,表示CRP升高(>10 mg/L);mGPS评分为2分时,表示CRP升高并伴有低白蛋白。
已有研究证实,mGPS与包括胰腺癌在内的多种肿瘤患者的预后有关,是一种有效的系统性炎症标志物[6]。国际胰腺外科研究组的共识已经确认了肿瘤相关全身炎症反应与胰腺癌患者生存期的关联性,并建议所有考虑行胰腺癌切除手术的患者,应先行mGPS评分或检测NLR[7]。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在胰腺导管细胞癌患者中,随访期间死亡组患者的中位CRP为4.9 mg/L,明显高于随访期间生存组患者的1.9 mg/L(P<0.01),提示CRP水平越高,患者的生存时间越短[8]。Martin等[9]回顾性分析了mGPS对晚期胰腺癌患者预后评估的意义,结果发现,mGPS评分低的晚期胰腺癌患者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明显长于mGPS评分高的患者。Ikuta等[10]对37例晚期无法切除的胰腺癌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mGPS评分为2分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media survival time,MST)为1.7个月,明显短于mGPS评分为0~1分患者的6.3个月。Salmiheimo等[8]回顾性研究显示,术前CRP水平升高与胰腺癌术后患者预后较差有关,并且是胰腺癌术后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随着mGPS评分的升高,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明显缩短。上述研究表明,mGPS可以作为胰腺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炎症指标,且与胰腺癌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根据mGPS评分可对胰腺癌患者预后做出预判,有效分层患者并制订不同的治疗计划。
2 NLR、PLR与胰腺癌
全身性炎症反应可以通过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进而导致胰腺癌的进展。NLR和PLR作为炎症指标,其数值增加能够反映宿主的免疫状态。研究显示,在其他肿瘤中发现,NLR、PLR水平升高提示更短的生存期[11-13]。虽然,已有研究证实,NLR和PLR可以作为胰腺癌患者预后的预测指标[14],但是,高NLR值、高PLR值与胰腺癌患者预后不良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
中性粒细胞聚集可以促进微环境中肿瘤的进展和转移,而且其还可以通过分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血管生成素-1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而上述细胞因子也与肿瘤的血管生成有关[15]。因此,中性粒细胞数升高为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提供了有利条件,可能导致患者的复发和低生存率。血小板是细胞因子的重要来源,尤其是转化生长因子-β及VEGF,该类因子可以通过促进新血管生成,进而促进肿瘤进展。通过血小板和淋巴细胞的结合,PLR还被认为是乳腺癌、卵巢癌和结直肠癌的敏感标志物和预后因素。然而,与NLR相比,PLR在胰腺癌预后评估方面不如NLR敏感。Cheng等[16]比较晚期胰腺癌患者NLR、PLR的研究显示,仅NLR与肝转移相关,而PLR与肝转移无关;化疗后PLR值的变化与治疗反应和总生存率无关。相关研究表明,NLR比PLR更能预测胰腺癌患者的预后;已发生远处转移胰腺癌患者的NLR值明显高于未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且NLR是胰腺癌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的独立预测因素,化疗后NLR值升高的患者预后更差,提示NLR不仅具有诊断价值,而且能够为胰腺癌的预后提供信息[15];而且接受根治性切除的胰腺癌患者NLR水平升高也与预后不良相关[17-19]。
3 LMR与胰腺癌
LMR是一种与炎症和免疫有关的生物标志物,通过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水平的变化及宿主对肿瘤的免疫反应,抑制肿瘤细胞的侵袭、迁移及血管生成[20]。一项纳入了57例接受放化疗的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的研究,对LMR在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前、期间和之后的预后意义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放化疗结束时LMR>0.32的相对变化和放化疗期间的绝对单核细胞计数与局部晚期胰腺癌患者的OS和PFS有关[21]。另一项关于胰腺癌根治术前LMR对胰腺癌预后意义的研究显示,外周血LMR≥2.86的胰腺癌患者的术后OS明显长于外周血LMR<2.86的患者[22]。上述研究提示,LMR在胰腺癌预后预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4 SIII与胰腺癌
SIII作为NLR和PLR的结合可以全面反映宿主免疫和炎症的平衡状态,已被证实是肝细胞癌、肺癌、胃癌、肾癌和前列腺癌的有效预后指标[22]。SIII作为胰腺癌患者术前生物标志物检查的重要性已经被证实,当胆红素水平<200 mmol/L时,SIII是可行手术切除的胰腺癌患者生存和复发的独立预测因素,SIII高的患者预后较差[23]。而一项关于胰腺癌切除术后患者的研究显示,术前SIII是胰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术前SIII升高的患者可能受益于抗炎和/或抗免疫治疗[24]。SIII作为评估新辅助化疗反应的预测标志物的相关研究也有报道。新辅助治疗后的SIII为胰腺癌切除术后患者总体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25],新辅助化疗后,SIII>900与胰腺癌患者OS较短有关(P=0.050),SIII≤900和SIII>900的胰腺癌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27.50、20.03个月。一项纳入419例晚期胰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无论糖类抗原19-9是否正常,治疗前SIII均是晚期胰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高SIII与胰腺癌患者较短的OS有关(P=0.002)[26]。上述研究显示,针对糖类抗原19-9水平正常的胰腺癌患者,SIII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预后预测指标。
5 小结与展望
目前,临床针对胰腺癌的早诊预警、治疗和预后判断方面均缺乏有效的手段。mGPS评分、NLR已被证实与胰腺癌患者的OS呈负相关,SIII、LMR已被证实与胰腺癌患者的OS呈正相关,并且NLR较PLR能够更好地预测胰腺癌患者的预后。此外,对于无法切除的转移性胰腺癌患者,炎症标志物可用于预测患者的化疗效果及监测患者的疾病进展情况。炎症指标是独立的、强有力的预后因素,与临床特征联合可能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并且,全身炎症指标可以通过常规血液检测出,成本低廉,因而可以帮助临床医师更好、更便捷地预测患者预后,对患者进行有效危险分层,从而有助于临床制订合理的系统治疗策略。
关于炎症指标目前仍存在一些缺点:对于炎症指标的最佳界定值仍没有统一的标准;炎症指标易受患者自身情况的影响,如感染、化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但炎症指标作为预后判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并初步显现其意义。炎症指标较其他检查更为安全、低廉且临床易获得。随着肿瘤细胞的增殖,其产生和释放的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血常规标志物的检测应该是动态、规律、结合临床的。
综上所述,炎症指标在胰腺癌预后判断和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方面潜力巨大。但目前由于还没有特定成熟的治疗方法或干预措施可以改变炎症反应和调节免疫反应,所以针对合适的患者群体,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设计,探索该领域的前景。我们也期待通过这些研究去筛选新的治疗模式或预后预测模型来优化胰腺癌新辅助、辅助或姑息治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