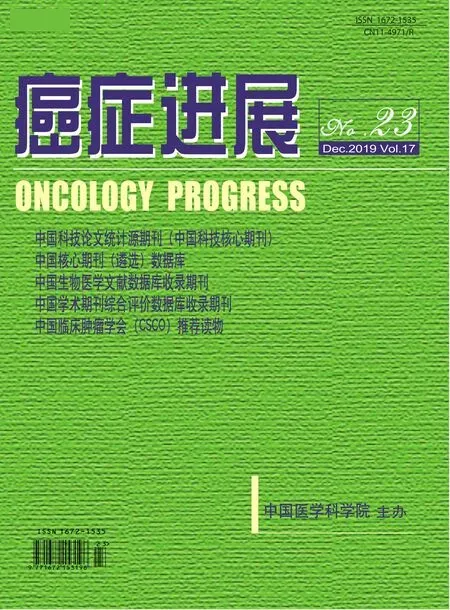肿瘤微环境的理论及治疗进展
邹子骅综述,李峻岭审校
国家癌症中心/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北京 100021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最早由Ioannides和Whiteside[1]提出,其定义为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局部生物环境,可为肿瘤细胞的生长提供支架和屏障,产生免疫豁免区域,从而为肿瘤的发生、发展提供“温床”。随着对TME研究的深入,肿瘤学界越来越重视TME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归纳起来,TME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重要作用[2]:①为肿瘤提供生长环境;②可削弱抗肿瘤药物的作用;③局部免疫应答呈免疫抑制状态,辅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监视。鉴于TME的重要地位,TME在未来的科学研究领域和肿瘤治疗领域中具有巨大价值。本文介绍TME的组成成分,并对TME的各组分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TME相关的治疗进展进行概述。
1 TME 的构成及各组分的作用
TME由细胞成分、物理组分和生化组分构成。细胞成分又称为基质细胞,主要包括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免疫细胞。物理组分指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生化组分主要包括细胞因子、黏附分子、生长因子、氧气和pH[3]。
1.1 氧气、pH 和内皮细胞
在肿瘤早期增殖阶段,由于肿瘤生长部位的局部供血速度短于肿瘤细胞增殖的速度,肿瘤处于乏氧的环境。乏氧环境可诱导肿瘤细胞释放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inducible factor-1,HIF-1)[4]。HIF-1可促使肿瘤细胞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血管生成因子从而启动肿瘤血管形成的过程。肿瘤血管形成与生理状态下的血管形成并不相同。生理状态下,血管旁支持细胞如周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分泌的血管生成素-1(angiopoietin-1,Ang-1)可与内皮细胞特异性酪氨酸激酶受体-2(tyrosine kinase with immunoglobulin-like and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homology domain,Tie-2)结合,从而调节内皮细胞之间、内皮细胞与血管外膜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血管成熟,并维持血管正常的有序结构。但肿瘤细胞分泌血管生成素-2(angiopoietin-2,Ang-2),它可与Ang-1竞争性结合Tie-2,而Ang-2与Tie-2的结合并不能引起后续信号通路的正常激活[5-6],因此,肿瘤新生血管具有结构排列紊乱、血管壁不完整、血管壁不连续的特点[7],从而进一步加重局部乏氧状态,并严重影响抗肿瘤药物的投递。在乏氧状态下,肿瘤细胞的主要代谢形式为糖酵解,糖酵解产生的乳酸等酸性物质可通过氢离子的形式被肿瘤细胞的质子泵排出细胞内,可进一步加重TME的局部酸化状态,而这种酸性条件并不利于免疫杀伤细胞的存活[8]。由此,免疫杀伤细胞在乏氧、酸化的环境下无法充分发挥其活性。此外,HIF-1还可启动P糖蛋白(P-glycoprotein,P-gp)耐药基因的转录,促使肿瘤细胞外排抗肿瘤药物而降低细胞内的药物浓度。
1.2 成纤维细胞和ECM
TME中的成纤维细胞又称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CAF)。一方面,CAF可分泌胶原、纤连蛋白、弹性蛋白,构成ECM,为肿瘤细胞的生长提供支架和屏障(屏障可理解为ECM形成的高间质压力影响抗肿瘤药物的投递以及免疫杀伤细胞的聚集,削弱药物和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攻击)[9];另一方面,CAF分泌生长因子或细胞因子[10],如肝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HGF)、VEG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从而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加重局部免疫抑制状态或降低肿瘤细胞对药物的敏感性。CAF在肿瘤耐药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CAF产生的HGF可激活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ion protein kinase,MAPK)/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信号通路,而这种旁路的激活可导致肿瘤细胞对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致癌同源体 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BRAF)抑制剂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抑制剂的敏感性降低[11];如化疗或放疗引起的CAF相关的DNA损伤,可促使CAF进入衰老的状态,在此种衰老的状态下,CAF可分泌大量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从而诱导肿瘤细胞启动抗肿瘤细胞凋亡通路及DNA修复,从而增强肿瘤对放化疗的抵抗[12]。
1.3 免疫抑制细胞和其他免疫抑制机制
TME中存在大量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可进一步划分为与肿瘤杀伤相关的免疫杀伤细胞和与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相关的免疫抑制细胞。免疫抑制细胞主要包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MDSC)和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TAM可分为经典活化的M1型和选择性活化的M2型巨噬细胞两种极化类型,其中,M1型巨噬细胞可促进肿瘤抗原的呈递,而M2型巨噬细胞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TGF-β等免疫炎症介质从而抑制免疫杀伤细胞的活性[13-14]。MDSC包括不成熟的树突细胞、不成熟的粒细胞和不成熟的巨噬细胞,它们通过分泌精氨酸酶-1从而降解精氨酸为鸟氨酸和尿素,而精氨酸是T细胞完成细胞周期所必须的化学物质,因此,MDSC可通过阻止细胞周期的完成从而抑制T细胞的活性[15-16]。Treg同样也在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其可通过分泌 TGF-β、白细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从而抑制免疫杀伤细胞的活性,另一方面其可下调树突细胞共刺激分子的表达从而减少效应T细胞的激活[17-18]。TME中除了免疫抑制细胞参与局部免疫抑制状态的形成外,其他信号分子或蛋白亦可参与肿瘤逃避免疫监视的过程。程序性死亡受体 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CD1,也称PD-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1(programmed cell death 1 ligand 1,PDCD1LG1,也称 PD-L1)信号通路在正常情况下是机体维持外周免疫耐受的重要机制,但在肿瘤内部,免疫炎症介质可诱导肿瘤细胞上调PD-L1的表达从而帮助肿瘤逃避免疫杀伤细胞的攻击[19-20]。此外,肿瘤细胞在遭受免疫系统攻击时可释放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IDO可使TME处于色氨酸“饥饿”的状态,从而促使色氨酸依赖的T细胞合成停滞于G1期,另外,色氨酸的代谢产物犬尿酸亦可对T细胞产生毒性杀伤作用[21-22]。由此可见,IDO的释放与局部免疫炎症信号有关,是一种继发的免疫负向调节机制。
1.4 外泌体
在肿瘤内部,外泌体是肿瘤细胞释放的一种功能性双层膜结构,可携带蛋白、细胞因子、生长因子、微小RNA(microRNA,miRNA)等物质,不需要其他细胞表达相应受体即可完成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因此,其在肿瘤细胞与TME的通讯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3-25]。外泌体的生物学作用与其携带的信号分子密切相关。外泌体通过向肿瘤周围的正常细胞传递增殖信号从而诱导其发生恶性转化。外泌体亦可降低肿瘤细胞间连接分子的表达,使肿瘤细胞的黏附能力减弱和侵袭能力增强[23-25]。同时,外泌体亦可通过携带生长因子或免疫炎症介质从而参与肿瘤新生血管生成、重塑ECM、抑制免疫杀伤细胞活性等多个肿瘤生物学过程[23-25]。此外,肿瘤也可通过外泌体将抗肿瘤药物排出细胞外。但由于外泌体在正常细胞之间也扮演着“通讯信使”的角色,因此,目前针对肿瘤相关外泌体的治疗仍存在难度[23-25]。
2 针对TME的治疗
2.1 针对乏氧、酸化状态及肿瘤血管正常化的治疗
肿瘤局部乏氧状态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而杂乱无序的新生血管结构进一步加重了肿瘤局部的乏氧状态,造成恶性循环,而乏氧、酸性的环境不利于抗肿瘤药物和免疫杀伤细胞发挥作用。而抗肿瘤血管生成药物可辅助修剪、正常化肿瘤血管,改善肿瘤血流灌注和局部乏氧的情况,从而促进抗肿瘤药物的投递和免疫杀伤细胞的活性。目前,临床上的抗血管生成药物主要包括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VEGFR)的单克隆抗体(如贝伐珠单抗、雷莫芦单抗)、VEGFR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呋喹替尼、阿帕替尼)和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瑞戈非尼、索拉非尼、帕唑帕尼)。这些抗血管生成药物已在肺癌、消化道肿瘤、肾癌、软组织肉瘤等多种恶性肿瘤中得到广泛应用[26],但目前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临床应用仍面临很大挑战,如抗血管生成药物耐药、抗血管生成药物的不良反应以及抗血管生成药物在其他肿瘤中的应用均是临床上棘手的问题,未来还有待肿瘤学界进一步研究。除正常化肿瘤血管外,肿瘤学家正尝试采用更直接的方法改善TME乏氧、酸化的状态,如二甲双胍可通过降少肿瘤细胞的耗氧,改善肿瘤细胞供氧与耗氧的平衡,从而达到减少HIF-1释放的目的[27];质子泵抑制剂、碳酸酐酶抑制剂可通过减少TME中氢离子的生成从而改善TME的酸化状态[28-29]。但这些药物目前仅在动物模型中表现出一定的效用,未来仍需临床试验进行验证。
2.2 改善局部免疫抑制状态的治疗
肿瘤局部免疫抑制状态是肿瘤逃避机体免疫监视的根本原因。因此,通过改善肿瘤局部免疫抑制状态从而增加机体免疫系统对肿瘤的识别和杀伤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随着人们对肿瘤免疫抑制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免疫治疗已成为人类治疗肿瘤的重要手段。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checkpoint inhibitor,ICI)在肿瘤的免疫治疗中应用最广泛,随着PD-1单抗/PD-L1单抗等的问世,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目前,ICI已获批应用于恶性黑色素瘤、肺癌、胃癌、霍奇金淋巴瘤、肾癌、泌尿上皮恶性肿瘤等多种恶性肿瘤[19-20]。另外,针对TAM、MDSC的治疗亦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前景。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CSF1)通过与 TAM 或MDSC表面的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受体(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1 receptor,CSF1R)结合,可招募TAM和MDSC至肿瘤区域,因此,阻断CSF1/CSF1R通路亦可改善肿瘤局部的免疫抑制状态[30-31]。目前,CSF1R抑制剂Pexidartinib已经获批应用于腱鞘巨细胞瘤(其发病机制:滑膜细胞存在CSF1染色体易位,造成CSF1持续过量表达,从而招募过多巨噬细胞导致组织增生)的治疗。Pexidartinib治疗其他实体肿瘤的临床研究也正在进行中(NCT01525602,Ⅰ期)。
需要注意的是,肿瘤局部免疫抑制状态的形成需要多种免疫抑制细胞及信号分子、蛋白的参与,因此,仅针对某一环节进行阻断并不能充分改善肿瘤局部的免疫抑制状态,但从目前的研究进展看,单纯地将不同的治疗方法相叠加并不一定能得到1+1>2的效果。ECHO-301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此项Ⅲ期临床研究比较了IDO抑制剂Epacadostat联合Pembrolizumab(联合治疗组)与单药Pembrolizumab(单药组)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疗效,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较单药组未能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32]。但是,近年来,ICI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为肿瘤微环境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方向。多项研究发现,VEGF可从不同水平参与肿瘤免疫调节:①VEGF促进内皮细胞表达Fas与其配体Fas-L结合,激活细胞凋亡通路,从而导致CD8+T细胞凋亡;②抑制抗原呈递细胞的成熟;③抑制效应T细胞的成熟,促进Treg细胞的分化与增殖;④促进MDSC的招募[33-36]。因此,抗血管生成治疗联合ICI在改善肿瘤局部免疫抑制状态方面有协同作用。而这一协同作用在IMpower 150研究中得到了有利印证,化疗+抗血管生成治疗+ICI方案可使肝转移的晚期非鳞状NSCLC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肝脏是免疫豁免器官,因此,肝脏转移瘤不易诱导机体产生免疫应答,肝转移是免疫单抗治疗恶性肿瘤的不良预后因素。而在IMpower 150研究中ICI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在肝转移患者的疗效[37]证明从多水平改善肿瘤局部免疫抑制状态可显著提高机体对肿瘤的免疫应答。因此,肿瘤复杂的免疫抑制机制使免疫治疗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更好地通过免疫疗法联合多种抗肿瘤药物改善肿瘤的免疫抑制状态并抓住肿瘤免疫抑制的核心机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2.3 针对ECM和CAF 的治疗
CAF分泌胶原、纤连蛋白、弹性蛋白等构成ECM,而ECM形成的高间质压影响抗肿瘤药物的投递和免疫杀伤细胞的聚集,削弱药物和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攻击,因此,针对CAF和ECM的治疗可有效破坏肿瘤的生长支架和屏障,有利于抗肿瘤药物和免疫杀伤细胞发挥作用[9]。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s activation protein,FAP)是CAF表达的特异性标志物,不表达于正常组织的成纤维细胞,因此,理论上,针对FAP的靶向治疗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38],但很遗憾针对FAP的单克隆抗体Sibrotuzumab在Ⅰ、Ⅱ期临床研究中并未取得很好的结果。而目前针对ECM的治疗,较有应用前景的药物是聚乙二醇化的重组人透明质酸酶(PEGylated recombinant human hyaluronidase,PEGPH20)。PEGPH20可减少肿瘤周围组织中透明质酸的含量而降低间质压力。一项Ⅱ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PEGPH20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和吉西他滨可使晚期胰腺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为6个月,而透明质酸高表达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可达9.2个月[39]。胰腺癌组织以高间质压为特点,严重影响抗肿瘤药物的投递,因此,透明质酸酶的作用迫切需要在后续的临床研究中得到确认。当然,在关注如何降低间质压而促进抗肿瘤药物的投递时,也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肿瘤细胞也有可能利用低间质压环境完成侵袭和转移的过程。由此,肿瘤学界也尝试从增加组织屏障这一方面抑制肿瘤侵袭和转移的过程。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在肿瘤的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主要由肿瘤细胞分泌,但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TME中的间质细胞亦可分泌MMP,MMP可水解胶原蛋白、蛋白多糖等大部分ECM,使肿瘤的天然屏障发生改变,导致肿瘤向周围组织浸润和转移[40]。因此,曾有学者研发MMP抑制剂,但很遗憾多种MMP抑制剂在针对软组织肉瘤、乳腺癌等多种实体肿瘤中并未展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因此,基于CAF和ECM复杂的生物学机制,目前临床上尚未有针对性的治疗手段。
3 小结与展望
TME参与肿瘤的生长、侵袭、转移、新血管生成、免疫逃逸、肿瘤药物耐药等多个重要生物学过程。但目前针对TME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TME各组成成分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未来如何从多个层面改善TME和把握TME的核心机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同时,目前大部分针对TME的研究还处于体外细胞实验及早期动物实验阶段,仍需更多的活体实验或临床试验证明其机制理论的准确性,更关键的是,即使人们可以进一步阐释TME的机制,针对TME药物的研发同样也很困难,因为目前尚不能建立与体内TME相似的实验模型,因此,建立与体内TME相似程度极高的模型尤其是可以模拟TME各组分功能的模型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