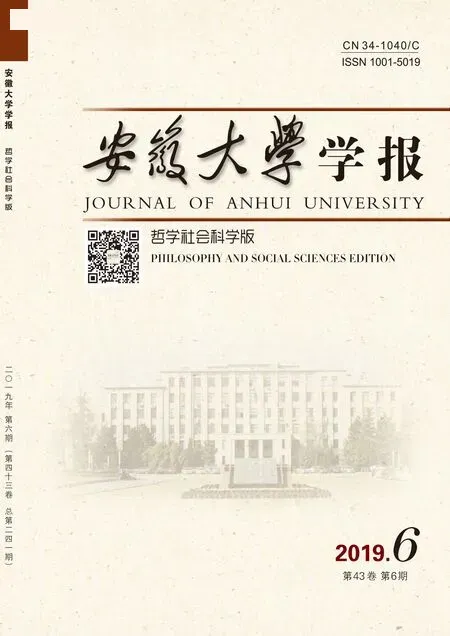当代欲望主体的哲学处境
——拉康与萨特学说中的自我、主体与他者
卢 毅
自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问世以来,经过康德关于“我思”的先验演绎,再到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自我”,西方哲学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不仅将“自我”(ego)想当然地等同于“主体”(subject),而且通过逐步区分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最终在胡塞尔那里见证了作为最严格意义上的主体的先验自我对于一切经验活动的奠基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语境下,对自我作为主体的“明见性”深表怀疑的萨特与拉康,分别从现象学与精神分析的进路出发,对自我的本质与起源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批判性反思,揭示出自我相对于主体的异化地位与对象身份,并且不约而同地指出真正的主体乃是基于某种“存在之缺失”的欲望主体,尽管萨特将欲望主体视为意识之虚无与自由本性的体现,而拉康眼中的欲望主体则是语言能指介入人类世界并将其结构化的产物。此外,二人均受到科耶夫(Kojève)对黑格尔学说阐释的影响,都将欲望和他者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不同于萨特将他者视为妨碍主体欲望与自由之完全实现而需要加以克服的外在因素,拉康在欲望主体与他者之间设想了一种可能的内在超越关系,而主体恰能借此实现某种尽管相对但却独特的自由。最终,与作为“异化主体”的自我以及作为“另一主体”的他者“共在”,实际上构成了当代欲望主体生存论意义上的基本处境,而作为构成这一哲学处境的主要环节,拉康与萨特学说中的自我、主体与他者也就将成为本文考察的对象。
一、针对自我的两种批判及其语境
20世纪50—60年代,拉康高举“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对弗洛伊德过世后以精神分析正统自居的“自我心理学”(egopsychology)展开了猛烈批判,其矛头直指作为该学派核心概念的“自我”(ego/moi)。拉康认为自我心理学由于片面强调“自我”的自主性,因此偏离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das Unbewußte)之重要性的一贯坚持,并且将精神分析这一原本卓越的实践降格为“美国式生活”的经营(1)Cf. Jacques Lacan, Subversion du sujet et dialectique du désir, Écrits, Paris: Seuil, 1966, pp. 808-809.。不过,若要追本溯源,可以发现精神分析界对于自我的关注其实并非始于以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等人为代表的自我心理学派,而是恰恰源于弗洛伊德本人晚年的学说。
弗洛伊德在创立精神分析之初的二十年里专注于揭示无意识的表现形态(梦、过失行为、诙谐、神经症症状等)与运作机制(凝缩、移置等),并致力于让人们承认无意识对人类个体与群体活动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而随着精神分析的发展和深入,一方面对于无意识的探索不断遭到来自无意识内部的抵抗(Widerstand),另一方面被压抑在无意识中的内容又以“强迫重复”(Wiederholungszwang)的方式不断呈现自身。弗洛伊德到了晚年越发重视这种存在于无意识内部的抵抗与重复之间的张力关系,并认为它有别于自己早年所探讨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外在的对立和冲突关系。弗洛伊德晚年著名的《超越快乐原则》便是这一转变的标志,他在该文中明确表示:“倘若我们不是将意识与无意识对立起来,而是将凝聚的自我(zusammenhängende Ich)与被压抑者(Verdrängte)对立起来,我们就避免了含混不清。自我本身肯定有很多方面是无意识的,确切地说就是人们可称为自我之核心的东西肯定是无意识的,它只有一小部分与‘前意识’(Vorbewußt)的名称相符。……被分析者(Analysierten)的抵抗源于他们的自我,于是我们马上就理解强迫重复要归于无意识的被压抑者。直到与之针锋相对的治疗工作使压抑松懈之前,被分析者的抵抗很可能不会表现出来”(2)Sigmund Freud, 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 Gesammelte Werke Band XIII, London: Imago, 1940, S. 17-18.。在晚年的弗洛伊德看来,相比于意识或前意识的外在施压,其核心同样是无意识的自我,才是使得无意识中被压抑的内容——这些内容往往与性和死亡有关,弗洛伊德将它们归于作为冲动(Trieb)发源地的“它”(das Es)无法被回忆起来而只能以强迫重复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内在抵抗之源(3)此处涉及弗洛伊德早年构想的“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精神结构模型即所谓“第一区位论”(erste Topik)与其晚年提出的“它(das Es)—自我(das Ich)—超我(dasÜber-Ich)”的精神结构模型即所谓“第二区位论”(zweite Topik)之间的差异。在早期“第一区位论”的框架下,弗洛伊德更多地将自我置于“意识—前意识”水平,并且往往是从“意识—前意识”对于无意识内容的审查(Zensur)以及反向投注(Gegenbesetzung)的角度来论述压抑(Vgl. Sigmund Freud, Metapsychologische Ergänzung zur Traumlehre, Gesammelte Werke Band X, London: Imago, 1946, S. 416)。而在后期“第二区位论”的框架下,弗洛伊德则强调不同系统在无意识层面的冲突或者说无意识内部的张力对于压抑的构成作用,包括本文所提到的自我在无意识层面对于“它”所包含的内容的压抑。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自我对于“它”的压抑还可以是出于外部的现实要求以及出于作为文明道德之内在化的“超我”的理想要求,而这些要求同样可能在无意识层面发挥作用,例如作为良知的超我对自我的支配就可能表现为“无意识的罪恶感”(unbewußtes Schuldgefühl)。Vgl. Sigmund Freud, Das Ich und das Es, Gesammelte Werke Band XIII, London: Imago, 1940, S. 263.。不仅如此,弗洛伊德的以上表述还传递了这样一层重要信息,即源于自我的抵抗往往是在精神分析治疗使得压抑开始松懈也就是治疗接近成功时产生的,这就意味着自我的抵抗成了阻挠被分析者了解其自身的真相或真理以及阻碍精神分析治疗取得成效的最后屏障。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晚年对于抵抗的分析以及对于自我的关注,其目的并非是像后来的自我心理学那样确立自我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而恰恰是为了揭示自我及其抵抗与精神分析真正关心的无意识、压抑以及重复等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为推进和深化精神分析治疗乃至最终化解自我的抵抗做好理论上的准备。
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的。自我心理学只在表面上看到弗洛伊德晚年对于自我的关注,却未能深切领会这种关注背后的真正用意。不过,这种误会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承接自西方思想传统对“自我”这一概念本身的误解。当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我思”之“(自)我”似乎不仅成了意识、理性与明晰性的代名词,而且也成了人的整个精神和心理活动与生俱来的当然主宰。然而,笛卡尔所发现乃至发明的这种自我,在经历了休谟彻底经验论立场的解构以及康德对理性心理学谬误推理的批判之后,其在哲学领域作为一种实体式主体的地位便开始受到质疑和动摇,而随着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自我也逐渐实现了从实体性主体向功能性主体的转型。待精神分析创立之后,弗洛伊德则先是通过将自恋(Narzißmus)即力比多投注于自我的状态视为后天精神活动的产物(4)Vgl. Sigmund Freud, 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 Gesammelte Werke Band X, London: Imago, 1946, S. 142.,再通过将自我明确界定为身体表面(在精神层面)的投射或映像(5)Vgl. Sigmund Freud, Das Ich und das Es, Gesammelte Werke Band XIII, London: Imago, 1940, S. 253.,由此开启了对于自我之起源与本质的进一步深入考察。实际上,从独特的视角深化并丰富对于自我的理解,可以说恰恰构成了精神分析对理论界的一大贡献。作为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真正的集大成者,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同样是以他本人在20世纪30—40年代对自我的批判性研究为基础的。值得一提的是,拉康不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关于自我的思考,而且巧妙地借鉴了法国心理学家亨利·瓦隆(Henri Wallon)关于儿童如何形成自己身体概念的心理学实验,最终构建起他关于“镜子阶段”(stade du miroir)的著名理论。
在1949年发表的《对于正如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向我们揭示的“我”的功能具有形成作用的镜子阶段》(以下简称《镜子阶段》)这篇著名论文中,拉康通过系统阐述其“镜子阶段”理论,深刻揭示了自我的他者本质与他性起源。依据瓦隆心理学实验的结果,拉康认为婴儿在诞生之初还处在一种身体感相对破碎的状态,尚未形成一种完整而稳定的自身感,当然也就没有“自我”的概念以及“自我”与“非我”的区分。到了6—18个月的时候,婴儿便能够凭借发育已相对完善的视觉系统捕捉到自身在镜中的完整形象(Gestalt)并将其认作自己的形象,从而预先获得当时发展相对迟滞的身体运动机能尚不能提供的自身感。换言之,此时尚未切实拥有自身统合感的婴儿,正是通过想象地认同其在镜中的完整形象而建立起具有想象统一性的“自我”。如此一来,自我非但不是与生俱来或向来属己的,甚至它的出现竟是将镜像这一本质上与本人相异的他者——拉康称之为“小写他者”(autre)误认为“我”的结果。正如诗人兰波所言:“我是一个他者”(Je est un autre)。
在拉康看来,这种将(小写)他者误认为自我的举动,尽管让婴儿获得了一种想象的身份或同一性(identité),却也使其从此进入了某种异化状态,并且导致被其镜像所捕获的自我从此便带有误认(méconnaissance)的功能(6)Cf. Jacques Lacan, Position de l’inconscient, crits, p. 832.。因此,拉康认为这种想象的认同或误认之举,不仅揭示了弗洛伊德通过“自恋”概念所描绘的力比多的动力学——自恋意味着将力比多即性冲动投注于自身的形象,而且也揭示了人类世界的一种存在论结构,而他本人则将这种结构纳入了他关于“妄想狂式知识”(connaissance paranoïaque)的反思中(7)Cf. Jacques Lacan, Le stade du miroir comme formateur de la fonction du Je: telle qu’elle nous est révélée dans l’expérience psychanalytique, crits, p. 94.,即将基于自我的一切认识都归结为人类受到想象的迷惑而不免产生的误认或妄识。
从上述这番对自我的批判性考察出发,拉康对自我心理学的抨击显然是有的放矢:自我并非如自我心理学所宣称的那样是自主的,而恰恰在本质上是某种异己的、异化的被构成物;人类心理问题的根源也不会像自我心理学所认为的那样是自我不够强大或对现实缺乏适应性,而恰恰是自我太过强大所导致的对于被压抑的无意识真相的遮蔽,以及这种遮蔽所引发的强迫重复及其致病作用。在拉康看来,自我作为想象认同的产物,其本质上是一个形象化的对象,而将其视为自明、自主、自由的主体显然是一种误认。相对于真正的主体即无意识主体(sujet inconscient)而言,自我完全处在一种异化的位置上,可被称为一种“异化的主体”。值得指出的是,拉康对自我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对自我之异化与对象化身份的定位,一方面不可否认地受到了弗洛伊德思想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则也可能受到了萨特相关研究的间接启发(8)拉康的女婿兼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ian Miller)甚至直言萨特关于反思前的意识的研究是拉康对“自我”概念进行批判的基础,并且表示拉康是凭借萨特而将精神分析从“自我”的监狱中解放出来(Cf. Miller, L’orientation lacanienne, L’expérience du réel dans la cure analytique, leçon du 17 mars 1999, inédit)。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细节确实值得注意。拉康的《镜子阶段》一文虽然宣读于1949年在苏黎世举办的第16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并发表于同年的《法国精神分析杂志》(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但该文的初稿实际上至少在13年前就已经完成,因为拉康于1936年在马里安巴德举办的第14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就做了题为《看镜子阶段》(The Looking-glass Phase)的报告,却由于发言超时被大会主席恩斯特·琼斯(Ernst Jones)禁言而愤然离场,因此这篇报告只留有摘要被会议文集收录。而萨特的《自我的超越性》首次发表的时间也是在1936年,更为巧合的是它当时就发表在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主编、拉康以合作者身份参与编辑的《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上。若非纯属巧合,且考虑到《自我的超越性》于1934年便已完成,那么尽管两人的研究进路各有不同,似乎仍有理由怀疑拉康对自我的探究以及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萨特相关研究的启发。。
在《自我的超越性》中,萨特通过批判前人对于自我的种种错误定位,尤其通过驳斥认为自我居于意识内部等流行观点,意图确立自我外在于意识的超越性地位。从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出发,萨特认为(反思前的)意识本身清空了一切实体性的内容(9)萨特在同一时期完成的《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一文中写道:“意识没有‘内部’;它不外乎它自身的外部,而正是这种绝对的逃离,这种对成为实体的拒绝将其构成为一种意识”。Cf. Jean-Paul Sartre, Une idée fondamenta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de Husserl: intentionnalité, Situations philosophiques, Paris: Gallimard, 1990, p. 10.,因此是纯粹的、透明的、空虚的,从而与将意识或思维视为精神实体的笛卡尔式传统立场拉开了距离。与此同时,萨特批判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仍不够彻底,“在观察到自我是意识的综合和超越的产物(《逻辑研究》)之后,他在《观念》中又回到了先验的‘我’的古典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先验的‘我’在每种意识背后,是这些意识的必要结构”(10)Jean-Paul Sartre,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aris: Vrin, 1992, p. 20.。换言之,萨特认为胡塞尔意识现象学的不彻底性体现在其仍保留了先验自我作为意识之构成来源与统一性的保障(11)在利科看来,“清除了自在甚至自我,完全外在于自我的萨特式的意识是通过一种超级还原而彻底化的胡塞尔式的意识”。Cf. Paul Ricoeur, l’éco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Vrins, 2004, p. 166.。根据萨特本人的观点,意识的统一性并非是由先验自我所保证,而是被本身就由意向活动构造出来的对象所构成(12)Cf. Jean-Paul Sartre,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aris: Vrin, 1992, p. 32.,因此究其根本“是意识自己把自己统一起来”。如此一来,萨特表示:“现象学的意识概念使‘我’(Je)的进行统一和个体化的作用完全没了用处。相反,恰恰是意识使‘我’的统一和个性成为可能。先验的我因此没有存在的理由。此外,这个多余的‘我’是有害的。倘若它存在的话,它就会让意识抽离自身,它会使其分裂,它会作为一把不透明的刀滑进每个意识当中。先验的我便是意识的死亡”。由此可见,萨特一方面表示没有理由像胡塞尔那样预设某种先验的“我”(Je)作为意识的源头,因为这对于思考意识的统一性而言是无用的和多余的,另一方面认为即便存在某种“(自)我”(moi),它在根本上也只能是意识之超越活动的产物,而“如果‘我’不以与世界相同的名义成为一个相关的存在者即成为意识的一个对象的话,那么现象学的一切成果就会毁于一旦”(13)Jean-Paul Sartre,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 22, p. 23, p. 26.。
通过上述引文不难看出,在以意识为中心而将自我边缘化的同时,萨特也确立了自我作为对象的地位,具体而言便是将自我视为与反思前意识的纯粹自发性相对的反思意识的自身对象化。不仅如此,在将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意义上的“我思”之“(自)我”贬为对象的同时,萨特实际上又确立了一种新的“我思”即“反思前的我思”(cogito préréflexif)或者说“非反思意识”(conscience irréfléchie),它与下文将要阐述的萨特式的欲望主体实际上可被视为同一种存在即“自为存在”的两个不同面向。对于萨特依靠现象学还原所达到的反思之前的“我思”这一新的哲学起点,国内学者张能为教授表示:“一方面,‘我思’作为意识的深层结构是一种自发的、虚无的自由意识,必然地能够在一个遗忘人的世界上重新确立人的尊严;另一方面,哲学史已经证明,任何以分开的作为实体存在的主体或客体任意一方去统一两者,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而‘我思’的优势就在于它既不作为实体的客体存在,也不作为人格化的构造主体而显现,相反,是主客未分的原始统一体。这样,就避免了重蹈传统唯心论和实在论之辙。由于以这种‘我思’作为起点,萨特哲学就显示出不同于其他哲学的独有特征”(14)张能为:《论萨特伦理学的评价维度问题》,《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按照《自我的超越性》法语单行本编者朋(Sylvie Le Bon)的理解,萨特通过这个文本旨在表明“自我既非形式地亦非物质地存在于意识之中:它在外面,在世界之中;它是一种在世存在,正如他人的自我一样”。的确,萨特在《自我的超越性》中赋予自我的乃是一种在根本上超越于意识之外的、在世界中存在的对象身份。不仅如此,萨特还进一步区分了精神(psychique)与意识,认为“精神是反思意识的超越对象,也是被称为心理学的这门科学的对象。自我向反思显现为实现着精神之持续综合的一种超越对象。自我属于精神一方”(15)Jean-Paul Sartre, La transcendance de l’ego, p. 13, pp. 54-55.。
现在不妨对萨特与拉康关于“自我”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稍做总结。首先,萨特从关注意识的现象学立场出发,将自我归入有别于意识领域的精神领域,并将其视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拉康后来则是从关注无意识的精神分析立场出发,批判自我心理学误将心理学研究的自我作为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可见二人的研究进路异中有同:尽管二人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但都将自我视为心理学的对象,并且都通过强调各自所属学科(现象学、精神分析)与心理学的差异而将自我边缘化了。其次,二人的研究内容则可谓同中有异:尽管萨特在《自我的超越性》以及拉康在《镜子阶段》中都将自我视为被构成的对象而非自主的主体,而且都认为自我涉及自反性(réflexivité),不过自反性在各自理论中的表现方式与实现路径却有所不同。在萨特那里,自我是通过被反思、被对象化的意识表现出来的,是意向性构造活动的产物,是通过“思”实现的自反性,因此可以说仍处于笛卡尔—胡塞尔的“我思”语境中(16)不过,正如马迎辉正确指出的那样:“与胡塞尔相比,萨特的极端之处在于,他认为只有在对象化意识所带来的反思中才会出现‘我’,而在此瞬间,纯粹意识就已经死亡了”。参见马迎辉《萨特论意向性与自我的建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在拉康那里,自我则是借助被反映、被对象化的身体形象构成的,是力比多投注活动的产物,是通过“看”和想象实现的自反性,因此可被认为处于比朗(Biran)的“我能”(弗洛伊德的“我欲”亦可被归入其中)语境中,并且似乎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更具亲缘性。最后,尽管二人都对自我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但其各自的研究目的毕竟有所不同,正如法国学者克洛蒂勒德·雷吉勒所言:“萨特之所以揭示自我的对象身份,是为了相对于意识的存在或其存在的虚无而贬低自我;拉康揭露自我的想象惰性,是为了贬低自我,不过是相对于无意识的存在本身,而他将无意识界定为一种非实体性的主体,一种言语的、纯粹符号性的主体”(17)Clotilde Leguil, Sartre avec Lacan, Paris: Navarin/Le Champ freudien, 2012, p. 85.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萨特对自我与意识进行区分,是为了将意识纯粹化,以便重建胡塞尔意义上的意向性;拉康区分自我与主体,则是为了将无意识纯粹化,以便重建弗洛伊德意义上被压抑的意谓(Cf. Clotilde Leguil, Sartre avec Lacan, p. 87)。。不过,尽管存在上述差异,二人对于自我之本质与起源的探索却不约而同地导向了对一种“真正主体”的揭示(18)当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涉及的理论体系不同,对于“两种主体”之区分的讨论自然会呈现出相应的差异,因此无论是考察康德或胡塞尔对于经验自我与先验自我的划分,还是探讨萨特或拉康对于自我(异化主体)与主体(欲望主体)的区分,都应当置身于具体的理论语境并结合相应文本展开细致分析,切忌断章取义或脱离相关语境进行笼统比较。另一方面,也不该片面强调某种学说自身的独特性乃至封闭性,而应当尝试将其置于思想史的宏观视域下来把握它的来龙去脉,通过揭示不同理论体系之间可能具有的内在关联,来更好地评定相关学说的学理贡献与学术地位。本文一方面紧扣相关一手文献与具体语境,另一方面不忘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相关问题加以观照,正是为了在可靠的文本依据之上尽可能呈现萨特与拉康对于“两种主体”乃至“三种主体”(作为“异化主体”的自我、作为“欲望主体”的主体以及作为“另一主体”的他者)之辨析的思想史意义。。他们都认为,真正的人类主体应当是一种欲望主体,而某种意义上的“存在的缺失”,既可以说是欲望主体之主体性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欲望主体之欲望的源头。
二、欲望主体的两种形态及其处境
在《自我的超越性》中区分了自我与意识之后,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进一步将意识界定为与“自在存在”(l’être en-soi)相对的“自为存在”(l’être pour-soi),并且将欲望视为自为存在的基本模式。作为自为存在即意识的基本样态,欲望的典型特征就是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既体现为欲望超出自身的内在性而朝向外在对象,也体现为欲望对其对象及其自身的否定。如此一来,萨特用来界定自为存在或者说“人的实存”(réalité-humaine)的“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19)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aris: Gallimard, 1943, p. 93.,就具体表现为欲望的不可满足性。在萨特看来,自为存在的本性是虚无,是自在存在意义上的“存在的缺失”(manque d’être),而这种缺失并非对某物的欲望,其作为“存在的欲望”不断纠缠着自为存在,使得后者尽管无法达到自在自为(en-soi-pour-soi)即上帝的完满存在,却始终不满足于任何具体的对象,而是不断否定和超越自身及其对象,从而体现了作为自为存在的人所特有而作为自在存在的物所缺乏的自由。
如果说在《自我的超越性》之后,自我在萨特的理论中只能占据对象的位置,那么与包括自我在内的各种意识对象相对而言的主体,便只能是《存在与虚无》中所描述的自为存在。通过上文的梳理不难发现,自为存在正是以某种意义上的存在之缺失为基础的欲望主体。这种欲望主体是有意识的,可以自由地对其将来进行筹划,也可以自由地选择实现其筹划的方式,而无论是自由筹划还是自由选择,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自由欲望。同样,正因为这种欲望主体是有意识的和自由的,同时又被认为是从虚无中被抛入世界的,而非任何外在于或先于他的原因的结果,所以他势必将对其自身负起全部的责任。当然,对于萨特式的欲望主体而言,绝对的自由似乎更多的是理论上的,现实中的自由却总是处境化的,因而是相对的。例如,一名囚犯或许有在狱中自杀的自由,但却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尽管如此,依然可以说是他本人自由地选择了犯罪才葬送了自己的自由,而他或许又是在某个甚至完全“迫不得已”的处境中选择了犯罪。然而,无论其处境有多么迫不得已,在萨特看来,欲望主体或是还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或是其自由地导致了其不自由和无可选择的处境,因此无论如何他都要为自己的举动及其背后的欲望全权负责。这种需要为其欲望及其行动绝对负责的主体,显然是一种伦理主体。
无独有偶,同样是通过对自我的批判性考察,拉康也旨在确立一种真正具有主体性和伦理地位的欲望主体。在他看来,当时的精神分析存在这样一种趋势,“通过对正确选择——它决定在言语中接待的是哪个主体,进行一种颠倒,对症状具有构成作用的(constituant)主体被视为如人们所言在质料方面被构成的(constitué),而在抵抗中被构成的自我则成了分析师从此要将其作为具有构成作用的机构来召唤的主体”(20)Jacques Lacan, Variantes de la cure-type, Écrits, pp. 334-335.。将实际上作为被构成对象的自我误认为具有构成作用的主体,进而在精神分析治疗中错误地依赖甚至强化实际上会因其抵抗而使治疗陷入僵局的自我(21)Cf. Jacques Lacan, 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 en psychanalyse, Écrits, p. 250, note 1.,这正是拉康强烈批判的自我心理学之弊病所在。因此,明确区分自我与真正的主体即无意识主体(22)关于拉康理论中的自我与无意识主体的区分,雷吉勒有一段精要的表述:“将作为言说主体的无意识主体与想象的自我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是言说的主体指向作为欲望的存在本身,而自我只不过是一个沉默的形象,它让人们遗忘了语言所造成的存在的缺失”。Cf. Clotilde Leguil, Usages lacaniens de l’ontologie, La Cause Du Désir, vol. 81, no. 2 (2012), pp. 121-129.,不仅可以避免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中的种种混淆,而且更有助于为精神分析临床实践找到正确的方向与着力点。
然而,尽管在精神分析最常处理的神经症症状方面具有构成作用,但与萨特式的主体从虚无中被抛入世不同,拉康式的主体完全是在经验世界中被构造出来的,并且其构造同语言的介入密不可分。在拉康看来,母亲相对于婴儿的缺席,或者说婴儿与母亲的分离,打破了原本完满的母婴一体的共生关系,并且使得婴儿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从此成了一种相对之前的完满状态而言有缺失的存在。与母亲的分离所造成的缺失,一方面成了任何存在者都无法填补的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成了语言介入的条件和契机。正是因为母亲的离开和缺席,婴儿才会因其生理性的“需要”(besoin)呼唤母亲到场,才会逐渐通过言语的“请求”(demande)来准确表达其需要。在此过程中,语言介入了婴儿的世界,并且将这个世界结构化和符号化了,同时也造就了一个随着能指链的滑动而飘忽不定的“欲望主体”(sujet du désir)。
与萨特式的欲望主体相似,拉康式的欲望主体同样源于某种“存在的缺失”(manqueêtre),因此其欲望在根源上同样可被视为对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完满状态的欲望,而显然任何具体的对象都无法满足这一欲望,因此必然导致欲望不断从一个能指(即一个符号化的对象)滑向另一个能指——而这正是拉康对“换喻”(métonymie)的界定,因此他称“欲望是存在之缺失的换喻”(23)Jacques Lacan, La direction dans la cure et les principe de son pouvoir, Écrits, p. 623. 在雷吉勒看来,“拉康之所以如此强调欲望的存在论意义,也就是强调欲望与对某个特殊对象的欲望无关这一事实……是为了阐明作为无意识欲望之表述的弗洛伊德式的无意识本身,而无意识欲望后来由于后弗洛伊德主义者们关注自我以及对象关系(relation d’objet)之故而被抹除了。……在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中,对萨特式的‘存在的欲望’的这种重拾,使拉康得以阐明弗洛伊德的发现”。Cf. Clotilde Leguil, Usages lacaniens de l’ontologie. La Cause Du Désir, vol. 81, no. 2 (2012), pp. 121-129.。另一方面,与萨特式的欲望主体不同,拉康式的欲望主体既不属于意识领域,亦非绝对自由,而是在像一门语言那样被结构化的无意识中生成,并且受制于“象征—符号性的大写他者”(Autre symbolique)的法则。更进一步说,不同于萨特式的欲望主体从虚无中被抛入世界的无根性,拉康式的欲望主体是有根的,尽管其存在之根同时也是其异化之根。
在拉康的语境下,一个婴儿的降生还不能被等同为一个欲望主体的诞生,因为在人类个体身上,语言的发生、欲望的产生和主体的诞生,这三者可以说是同步的。婴儿在尚未学会说话的阶段,起初可以像动物那样通过肢体动作或哭喊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生理性的“需要”,而当他不得不开始学着通过言语来表达其需要时,他就有了“请求”。此时,语言的异化作用首先就体现在使其婴儿所请求的必然多于他所需要的,而拉康正是将请求比需要所多出的那一部分界定为“欲望”。除此之外,语言的异化作用还体现在,其对人类世界的符号化与结构化作用虽然为能言、能思、能欲的人类主体奠定了基础,却也使得主体(sujet)在各方面都受制于(assujetti)语言这个“大写他者”,从而丧失了萨特意义上的自由。如此一来,正是由于语言的介入,才从生理性的需要衍生出了符号性的欲望,也才有了一个追随无意识的能指链苦苦寻觅其欲望对象而不得的欲望主体。
可见,拉康非常强调语言在构成欲望主体及其世界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尽管这种构成作用不免会带有异化效果。而由于划分了自在与自为,并认为后者即欲望主体从虚无而来且在根本上无异于虚无,因此在萨特的学说中,对语言之于欲望、主体乃至人类世界之构成作用的这种拉康式的强调则付之阙如。不过,尽管自为被萨特等同于虚无或非存在(non-être),但这种虚无或非存在毕竟只有从逻辑上在先并且奠定它的(自在)存在那里才能取得具体成效(24)Cf. 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50.。因此,严格说来非存在的自为只能拥有一种“借来的存在”,“它是从存在那里获得其存在的。……只有在存在的表面才有非存在”(25)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51.。与之相反,(自在)存在却是充实而自足的,不需要虚无就能被设想(26)Cf. Jean-Paul Sartre, L’être et le néant, p. 51.。由此可见,萨特式的欲望主体其实并没有乍看起来那样自由且孤独,而是同拉康式的欲望主体一样,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他者”的问题。
三、面对他者的两种姿态及其困境
在欲望的问题上,拉康与萨特可以说都受到了科耶夫对黑格尔学说阐释的影响,因此不约而同地将欲望和他者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在科耶夫看来,欲望的性质在根本上是通过其欲望的对象而得到界定的,因此一个欲望如果仅仅满足于像食物这样的自然对象,那么它就将保持为一种自然的、动物性的欲望,而只有当它以一个非自然的对象即另一个人的意识或欲望为对象时,它才成了真正人性的欲望(27)参见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姜志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7页。。就此而言,人性的欲望必然指向他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指向他人的欲望,甚至可以说人的欲望在本质上就是他人的欲望,因为人欲望他人的欲望,以他人的欲望为自己的欲望。科耶夫对动物欲望与人性欲望的区分以及对人性欲望的基本界定显然被拉康所继承,只不过拉康以生理性的需要与符号性的欲望取代了科耶夫对于两种欲望的区分,以凸显二者之间存在的质的差异,并且进一步将人的欲望界定为“他者的欲望”,而从“他人”到“他者”的转变显然淡化了科耶夫学说的人类学色彩,同时使得这一界定具有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下,“他者”可以被赋予想象的(imaginaire)、象征—符号的(symbolique)与实在的(réel)三个维度,而“欲望是他者的欲望”则可以从这三个维度分别获得解读,但需要注意的是,当拉康宣称“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时,“他者”所意指的往往是符号性的(大写)他者,因此我们需要首先从这个角度来把握拉康的思想。上文已经谈到,拉康式的欲望主体是大写他者的语言能指运作的产物,因此其生成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异化的历史。具体而言,婴儿为了在这个已然被语言符号化和结构化的世界中正常生存下去,不得不放弃其前语言或非语言的存在状态,不得不进入语言并服从这位大写他者的法则。这种委曲求全虽然为其赢得了主体的名分,但这一主体性却因为主体受制于他者的状态而无异于名存实亡,因此拉康将主体化的这第一个环节或操作称为“异化”(aliénation)。这种异化虽然有其负面效果,但对于“正常”主体的生成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代价,因为倘若不经受语言的异化,人类个体要么只能沦为“异类”(例如自闭症患者或某些类型的精神病患者),要么甚至性命难保。处于异化状态的个体虽然受制于他者,却依然可以凭借其仅剩的一点自由来尝试实现与大写他者的某种“分离”(séparation)——拉康称之为主体化的第二个操作,尝试在大写他者之外寻找可为其存在奠基的东西,以便摆脱这种异化状态。在拉康看来,与大写他者分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先前已被语言能指划杠的主体($)进入与其欲望对象(a)的无意识幻想关系($◇a)的过程,而“通过这条途径,主体在其作为无意识而涌现的丧失中实现了自身”(28)Jacques Lacan, Position de l’inconscient, Écrits, p. 843.。尽管主体此时已经找回了一点存在,已经能够作为无意识主体而在对其欲望对象的幻想中涌现,但要真正扬弃异化并完全实现其主体身份,还需要进一步的分离即“穿越幻想”(traversée du fantasme),需要经历主体化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环节,而这最后一个环节同时也被拉康视为精神分析治疗的终点。通过穿越幻想,主体虽然还是在被大写他者所符号化和结构化的这个世界中思维、言说和欲望的主体,但此时他已经不再将大写他者或幻想对象作为其存在的直接基础,而是通过一种自由的、无条件的、能够真正确立其伦理主体地位的揽责行动,通过将语言能指和欲望对象的“他性”主体化,将原本由它们所造成的外因内在化,将原本的他律状态自律化,来实现对他者的一种内在超越,同时实现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自由。
尽管不像在拉康理论中那样直接和明显,但萨特式的欲望主体的确也面临着他者的问题。萨特从黑格尔那里借来了“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这对术语,却没有真正接受黑格尔认为二者实则同出于一并且最终同归于一的一元论思想,而是坚持自在与自为、存在与虚无之间的分裂与对立,这可以说是继承了科耶夫将动物与人类、自然与历史截然相分的“二元存在论”(29)Cf. Vincent Descombes, Le même et l’autre, Paris: Munuit, 1979, p. 64.。然而,作为欲望主体的自为尽管被描述为从虚无中被抛入世,但在他被抛入世之前,自在存在的世界作为偶然性(contingence)或事实性(facticité)毕竟已经存在,并且实际上构成了他的处境(situation)。就此而言,自为从一开始就并非是完全自立和自由的(30)瓦萨罗通过研究指出,萨特的戏剧和传记作品“通过将自由呈现为与事实性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必然折损了自由之开创性的特征”。Cf. Sara Vassallo, La liberté l’épreuve de l’Autre symbolique dans le thétre de Sartr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231, no. 1 (2005), pp. 61-83. 她在另一处甚至还表示:“唯有一个能指贯穿了[萨特的]哲学与传记这两类文本:自我奠基的无能”。Cf. Sara Vassallo, Du texte philosophique au texte littéraire. D’un double sujet del’énonciation chez Sartre, Rue Descartes, vol. 47, no. 1 (2005), pp. 19-30.。不仅在理论和逻辑上虚无奠基于存在,而且在实践中主体也处处要面对他者。因此,尽管如法国学者萨拉·瓦萨罗正确指出的那样,萨特在论述的顺序上与拉康相反,不是像拉康那样先强调与他者的异化关系再描述主体通过分离实现其存在,而是先设想一个从无中凭空而来的自为存在再考虑与他者的相遇(31)Cf. Sara Vassallo, Sartre et Lacan, Paris: L’Harmattant, 2003, p. 237.,但二人理论的基本设定却并无实质性的不同,都预设了他者相对于主体的某种在先性。不同的只是萨特对于他者的态度,即认为他者(无论是自为且为他存在的他人,还是自在存在的他物)在本质上构成了主体实现其自我奠基、体现其绝对自由的外在障碍。这样一来,自为的欲望作为存在的欲望,虽然以自在自为的神性地位作为其纯粹理想化的终极目标,但为自由扫清障碍而去征服他者却是其可能部分实现的阶段性目标(32)“根据萨特,欲望通过其肉身化寻求对作为自由主体性的他人(autrui)的不可能的占有。换言之,在欲望中,主体试图征服他人的自由”。Cf. Philippe Cabestan, Sartre et la psychanalyse: cécité ou perspicacité? , Cités, vol. 22, no. 2(2005), pp. 99-110.。但无论是作为自在还是自为的他者,在萨特看来终究是一种无法被彻底消除的外部力量,而“正是因为存在他者,《存在与虚无》中的自因(cause de soi)便是不可能的或者想象的”(33)Sara Vassallo, Sartre et Lacan, p. 241. 瓦萨罗在另一处对此观点稍做了展开:“如果说萨特的主体想要自我奠基或成为自因,而这个欲望一开始就被视为不可能的,那是因为主体的缺陷存在于他自己的外部,存在于任何行动都无法排除的一种他性中”。Cf. Sara Vassallo, La liberté l’épreuve de l’Autre symbolique dans le thétre de Sartre,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231, no. 1(2005), pp. 61-83.,作为欲望的人终归只能如萨特所言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就此而言,即便不说“他者即是地狱”(l’enfer, c’est les autres),至少也可以说他者将自为逐出了想象中绝对自由的天国。
值得深思的是,面对他者的上述两种理论态度实际上有其各自的困境。一方面,萨特将他者视为自为实现其自由与欲望之路上需加以克服的外在障碍,这似乎又陷入了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为了得到承认而与其副本展开殊死搏斗的僵局中,而这种想象的甚至是镜像式的敌对关系正是拉康曾大加调侃并加以批判的。尽管萨特晚年在《辩证理性批判》中通过引入“融合群体”(groupe en fusion)等概念来试图淡化和弱化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由于萨特依然坚持自为的无根性,强调自为的独立与自由,因此他者终究难免被视为是一种从外部包围自为的异化因素。可见,“异化在萨特那里是按照外在性(他者)/内在性(意识)的对立来思考的。自为仅仅从外部被破坏,萨特说它在外面,在外在性的虚无中‘自我奠基’”,他者的存在却被认为破坏了自为从纯粹的虚无中完全自由地凭空创造自己、奠定自己的伟大计划——正如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计划一般。因此,在萨特那里,他者始终难以摆脱负面的理论形象,始终难以洗脱随时可能沦为地狱的嫌疑。另一方面,拉康将他者设想为主体形成的条件和基础,而“主体在大写他者能指中的登录赋予了接受这一点的主体在符号秩序中的一个位置,而这将使得被设想为主体最初欲望的从无中自我奠基的欲望(这是萨特的情况)变得无用”(34)Sara Vassallo, Sartre et Lacan, p. 222, p. 227.。拉康式的欲望主体虽然不再追求萨特式自为的那种绝对意义上的、无中生有式的自我奠基,但作为异化的扬弃,与他者的分离依然意味着其对欲望与存在的自我担当。然而,尽管拉康对主体异化的扬弃之路做了精心构想和详尽阐述,但由于他所做的将主体划杠以及将他者大写等非人格化处理,使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主体具体该如何行动才能实现分离、穿越幻想并完成对他者的内在超越,便依然是一个需要澄清并有待解决的问题。
四、结 语
通过对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套欲望学说进行梳理,当代欲望主体的基本哲学处境得以被初步勾勒:相对于通过自反性活动并且根本上是作为对象被构成的自我及其表面性而言,当代的欲望主体通常处于某种有待揭示的被遮蔽状态,其奠基于存在的缺失之上,并且被设想为应当为其自身在存在论层面的这种根本缺失亦即欲望负责的伦理主体(35)通过下面这番简要说明,或将有助于澄清萨特和拉康语境下的欲望主体和伦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伦理主体可被视为欲望主体的一个维度,当然也可以说是欲望主体最重要、最核心的维度,但欲望主体并非只有这一个向度,而是同时具有认知主体、审美主体等不同向度,或者说伦理、认知与审美等都是在根本上由欲望所维系的主体呈现出来的不同面向。;与此同时,这种欲望主体的伦理性还体现在其与他者的关系中,或者说体现在其面对他者的态度上,尽管无论是萨特所憧憬的对于他者的外在克服,还是拉康所构想的对于他者的内在超越,似乎都由于缺乏对他者本身的伦理关怀而暴露出了某种值得反思的理论缺陷。不过,上述缺陷虽然揭示了当代欲望主体可能面临的伦理难题——如何顾全对于自身的伦理责任以及对于他者的伦理责任,但同时也呼吁着新的思想资源的投入以及更多相关研究的推进。无论是列维纳斯所阐发的对于他者的无限伦理责任,还是约纳斯所设想的在技术时代保存一切生命的责任律令,这些思想上的努力或许都将有助于化解这一困境。
——拉康对《孟子》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