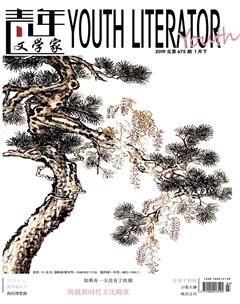西汉《诗经》学视域下“《诗》无达诂”说的内涵初探
摘 要:西汉董仲舒的“《诗》无达诂”说在后世引起了多元的经学和文学阐发、演变。它本指西汉当时学者根据各自所持的思想和需求阐释《诗》,以实现经世致用,并没有固定的辞义解释。本着“从变而易,一以奉天”的原则,“《诗》无达诂”最终体现了“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并归属于汉代经学阐释为主的《诗》学发展。
关键词:《诗》无达诂;董仲舒;经学;《诗》学
作者简介:张玥(1995-),女,满族,北京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二年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3-0-02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吸收百家思想,创立了适应大一统国家建设的新儒学。《汉书·董仲舒传》“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强调其他学说不能和儒学处于同样高的发展地位和态势,以儒学为主、百家为辅,对原始儒家更新改制。兼容变革思想作为董仲舒的总体学术精神,对“《诗》无达诂”说的生成有重要意义。
一、“不任其辞”的经学阐释思想
在兼容变革思想统摄下,董仲舒独创了“名号”“辞指”“经权常变”等与“《诗》无达诂”相关联的具体理论。
1.名号论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②儒者要重视辞文表述,洞悉孔子的微言的大义。“名号”是以语言的形式对事物进行概括、分辨;它被抬到治理天下的高度,由圣人依据天意制定,具有判定是非进而规整世界的功能。
原则是“《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③对于“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一事,楚君行动有礼、晋君相反,因此即使按照写作惯例楚国作为夷狄国君不被称爵位,《春秋》记叙时根据“礼”的标准变通了语言规则,“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从变而移”要求根据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变化,灵活解释《春秋》的意味。这为引《诗》来阐释《春秋》、表达政治文化诉求奠定了基础,可看做后面“《诗》无达诂”的伏笔。
2.辞指论
具体到言意关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竹林》篇提出“辞不能及,皆在于指”“见其指者,不任其辞”。根据清代苏舆疏释,“指,即孟子之所谓义”“任,用也,旨有出于辞之外者”。由文字所表达的意义,指向文字所不能表达的意义;在重视表露于外的意思的基础上,理解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由表及里,追求“言外之意”。这种《春秋》意义观和理解观是“《诗》无达诂话”话语生成的理论环境。
3.“经权常变”论
《春秋繁露·玉英》曰:“《春秋》有经礼,有变礼。为如安性平心者,经礼也。至有余性,虽不安于心,虽不平于道,无以易之,此变礼也……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④常变关系,乃一般与特殊、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对‘权的严格框限实质是就是对‘经的至上地位的尊重”⑤;将经权意识直接落实到经学解释的意义观上,就是常辞与变辞,常义与变义。根据苏舆的注疏,常变皆要因时因地而运用,不可拘执一端而不化。
总之,董仲舒在《春秋》探微、史实索引、和引《诗》推衍等阐释行为中始终求“变”,实现了儒学释义,客观上促进了“《诗》无达诂”命题的孕育和生成。
二、历史语境中的 “《诗》无达诂”内涵
“《诗》无达诂”最早明确见于《春秋繁露·精华》篇:
难晋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曰:“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⑥
根据《说文》《尔雅》,“诂”可训为“古”和“故”,引申为解释和理解。刘向《说苑》称引时“达”作“通” , “通”与“达”都是明白、通晓之意, 可以互训。[1]“《诗》无达诂”即《诗》没有通达晓畅的确定含义,辞文蕴含着可探寻的意境空间。就董氏主观意图来说,“诂”还包括史實和义理的推衍。“所闻”二字证明“《诗》无达诂”并非原创;而作为一种引起人们重视的理论,从董仲舒始。
它其实是董仲舒对西汉初至武帝阶段《诗》学发展现状的描述和总结。西汉武帝之前,《诗》学发展呈多样化格局和形态,:不仅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四家诗)各有其面貌和师承系统, 在篇章字句的解释方面“文字或异,训义固殊”⑦;就是同一家诗之中也有学术的分野。基于不同学术背景的诗学流派也形成了对《诗》的不同阐释观念,正可谓“《诗》无达诂”。然而董仲舒的所指不止于此,“《诗》无达诂”与后面两部经典都要“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人”字,后代学者普遍认为应为“天”字,即天道、天意。解《诗》“使学者有所统一”,遵循“天”的统一哲学原理,以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建设需要。这里“经”成为了阐释的“可以然之域”,阐释的根本在“经”而不在《诗》。
更深层次上,“《诗》无达诂”说有两层含义。(一)根据“经”与“权”,“常”与“变”的辩证关系,阐释者要突破经典文本的文字界限,“借古喻今”,赋予经典新的理解。(二)相比于《春秋繁露·竹林》,“从变”纳入了“从义”“一以奉人”的原则中。“义”指六艺大义。徐复观说:“仲舒无达辞、无通辞之言……是他要突破文字的藩篱, 以达到其借古喻今, 由史以言天的目的。”[2]将对历史、时代的认识统摄在天的哲学精神下, 以天道来言人事, 体现出“天不变, 道亦不变”的绝对权威和意志。
董仲舒用《诗》、引《诗》时也运用“《诗》无达诂”原理。例如 “采封采菲,无以下体(《邺风·谷风》)”句:《竹林》篇用“取其一美,不尽其失”的兴喻之意,采叶喻取其美,不采下体喻不记其失;旨在赞扬子反具有对百姓的仁爱体恤之心,即使背叛了国家。《度制》篇取其字面意,采封菲之菜仅采其叶即可,不要将根茎一起采去,此乃遗民以利。
面对不同语境和事项,借用《诗》的经典权威性来为天道政治儒学立名,似乎只有“《诗》无达诂”才能为相互矛盾的微言大义阐发提供合理性。
三、“《诗》无达诂”与《詩》学史
(一)“《诗》无达诂”的历史渊源与背景
“《诗》无达诂”说并非董仲舒始创,可溯源至先秦的政治文化现实。《诗》的产生与流传方式包括周代王官采诗和列国献诗,例如“雅”和“颂”这类王权贵族的宫廷礼乐和祭祀用歌,赋予《诗》为王者观风教、为后人垂范的先王政典功用。章学诚说:“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3]
《诗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威地位可以说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后渐渐确立。“而‘礼乐作为周代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整体,对整个周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文化生活的形成均有着根本上的影响。”[4]因此《诗》是涵盖制度、仪式、文化的综合典籍。春秋至战国先后发展出“赋诗”“引诗”活动,继承《诗》的经典权威性并深化主观维度,称为“赋诗断章”,明确记载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是春秋时代《诗经》阐释的普遍原则。
可见,从产生起,《诗经》就被赋予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含义;其经典性和道德教化意味逐渐酝酿,促成了汉代《诗经》道德化政治化的思考习惯和审美形态。
根据西汉的学术文化现实,百家并进的环境消失,儒家在巩固君权至尊和避免暴政的矛盾境遇中繁衍生存,生发出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等真理性认知。四家诗以“经”解《诗》甚至以《诗》为谏书,将政教阐释落到最实处。因此,毛湛侯说,“汉代是《诗》经学化的时代”。
(二)《诗》学史视域下的“《诗》无达诂”评价与思考
“《诗》无达诂”说体现了董仲舒对《诗》的功能观念。《春秋繁露·玉杯》曰: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⑧
此外,《史记·太史公自序》转述董仲舒的关于《诗》的论述有“《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北肚雌雄,故长于风”“《诗》以达意”。《诗》有“长于质”和“长于风”两特点。“长于质”继承春秋时代“诗言志”的传统,其内涵包括作诗言志和赋诗言志。“长于风”继承儒家“《诗》以载道”思想,指《诗》的道德教化作用。对于“诗”无达诂与“从变从义,一以奉人” 的六艺致用原则,变是对“引譬连类”的认可和肯定;“一以奉人”的义又是对“《诗》以载道”的发扬,“道”就是每个用《诗》人心目中的真理正道。
董仲舒“《诗》无达诂”说可以看成是阐释型“用诗”行为,归属于“以经解《诗》、以用解《诗》、以谏解《诗》、以礼解《诗》和以美刺解《诗》”[4]。按照现代文学审美标准,这是理解与阐释的局限性,但也是理解与阐释的历史性,更是西汉特定历史境遇中《诗》学发展的真实性。这种先入为主的政教美刺的说《诗》理念和模式在中国诗学史上一直绵延不绝。“《诗》无达诂”说与所属的汉代《诗》学经学化一道为《诗》学史贡献了一段以政治教化归旨释《诗》的学者阐释历史,进而在中国传统诗学领域衍生了更宽泛多元的意义。
注释:
①(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2523页。
②(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84页。
③(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46页。
④(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74-75页。
⑤李有光:《中国诗学多元解释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⑥(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94-95页。
⑦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序.续修四库全书总76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1163页。
⑧(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35-36页。
参考文献:
[1][4]毛宣国. “《诗》无达诂”解[J].中国文学研究. 2007(01).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卷[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文史通义·易教上》[M].中华书局,1985,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