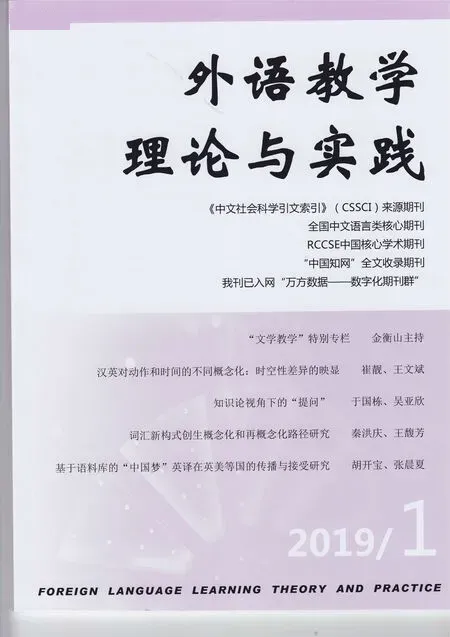汉英对动作和时间的不同概念化:时空性差异的映显*
北京外国语大学 崔 靓 王文斌
提 要: 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概念化理论,对比汉英对动作和时间的不同概念化方式。主要发现有二: 一是汉语对部分动作的概念化具有双向可逆特征,而英语却表现出单向不可逆特征;二是汉语对时间的表征具有二维空间性,而英语对其则呈一维线序特征。本文提出,汉英在这两方面存在区别的深层缘由,或许与二者的时空性思维差异有关。
1. 引言
意义即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认知语言学的一项重要假设。概念化作为一种复杂的认知加工和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Langacker,1987: 5;Evans & Green,2006: 157等),既含涉概念形成的体验过程和认知方法,也蕴含该过程的结果(王寅,2006: 298),其本质是一种动态的(dynamic)主观化活动(subjectification)(Langacker,1999: 297,361)。而人作为认知主体,在其中自然具有关键的主体性作用。因此,面对相同的概念化内容(the object of conceptualization),因文化经验和认知视角不同,各民族的概念化方式往往会产生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化结果,并体现于语义内容和句法表达等诸多方面(戴浩一,2002;蒋绍愚,2014等)。例如:
(1) a. 他租了我一间房。
b. He rented me a room.(租给: 他租给了我一间房。)
c. He rented a room from me.(租用: 他从我这里租了一间房。)
(2) a. 小明想死观众了。=b.观众想死小明了。
c. Xiaoming misses the audience so much.
d. The audience miss Xiaoming so much.
(3) a. 前/上半夜 后/下半夜
b. before midnight after midnight

概而言之,汉英在一些动词的语义和时间表达上具有明显差异,而这一语言表征上的区别,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汉英对动作和时间不同概念化的结果。对此,本文将在下文论述。
2. 汉英的时空性差异
以往的研究中,王文斌(2013a,2013b)以汉英的不同思维模式为基点,力图考究两种语言在诸多层面的差异性表现(于善志、王文斌,2014;何清强、王文斌,2015;王文斌、崔靓,2016;王文斌、何清强,2016;王文斌、于善志,2016等),提出并证明了“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而英语具有时间性特质”的观点。如在句构层面体现于汉语不受时制束缚,在整体语义的统摄下,铺排大小表义单位,具有块状性、离散性和可逆性特点,而时制对于英语句法则具强制性,以动词的形态变化为载体,复杂句以主句动词时制为轴榖,形成前呼后拥的时制链;语篇层面展陈于汉语的思维方式和衔接机制均具块状性和离散性,而英语则借助显性关联词,从而呈现出勾连性和延续性的特征。
综上可知,空间立体结构在汉语诸多层面皆具鲜明的同构性,是汉语三维空间(spatially three-dimensional)特质在语言中的映显,是汉民族多维思维模式的体现;而线性结构(linearization)是英语词法、句法乃至语篇的共享属性,是英语单维时间特质(the one-dimensional nature of time)在语言层面的展现(Comrie,1985/2005: 15),也是英民族一维线序思维的反映。
本文聚焦于汉英部分动词和时间的表达,发现汉英对有些动作和时间表现出不同的概念化方式,这或许是两种语言时空性差异的又一佐证。因此,本文拟立足概念化这一视角,对比汉英部分动词和时间的不同表征现实,以期揭示其差异的深层缘由。
3. 汉英对部分传递动作的不同概念化: 双向可逆特征和单向不可逆特征
动作的传递往往蕴含着一定的方向性,一般体现于动词语义,或作用于特定的句式表达中。因此,有些汉英传递动词在“方向性”的表征差异,或许可看作英汉民族对传递动作的不同概念化。鉴于此,本文拟从两个视角: 双宾句“A↔B”与“A→B”,详见本文3.1;以及可逆句“A→B = B←A”与“A→B ≠B←A”,详见本文3.2,对比分析汉英对部分传递动作概念化方式的差异。
3.1 汉语动词概念化的“A↔B”与英语动词概念化的“A→B”
一般来讲,双宾动词包孕“传递”义,是一类典型的意涵方向的动词。汉语对这类动词的概念化往往呈现出双向可逆的特点,即物体的位移传递方向既可从左到右,也可从右到左,而这一双向过程[注]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汉语所有涉及物体位移传递的动词均具“左右双向”的语义特征,诸如“送他一本书”、“抢他五元钱”等,其动作的传递方向就是单一、明确的,但为何汉语动词存在较为普遍的双向性用法,而英语却仅能表现出单向性,此乃本文的关注焦点。下文3.2中的可逆句同样如此,并非汉语所有的句式均可逆,在此探讨的重点是为何汉语存在如此习见的可逆句式,而对英语却不成立。均被识解为同一种动作或行为,用同一动词表示,可抽象为“A↔B”;而英语的概念化方式则展现出单向不可逆的特征,即物体的位移方向是单一、明确的,不同的方向需要明分细辨,往往借助不同的动词分别表示,可抽象为“A→B”。传递动作的这一概念化差异在汉英动词的语义内容和语法结构上均有体现,下文拟在3.1.1和3.1.2具体阐释。
3.1.1 汉语“A↔B”与英语“A→B”在动词语义中的体现
长期以来,学界(朱德熙,1979;古川裕,1997;卢建,2003;张斌,2010/2015;等)注意到,汉语中表达物体传递的有些动词,本身就蕴含着“双向性”这一语义特征,传递的物体既可从主语向右移至间接宾语,也可从间接宾语向左移至主语。这类动词往往被称为“兼向动词”或“予夺不明动词”,可形式化为“A↔B”。例如:
(4) 我借了他三万块钱。
(5) 我上了他一节课。
(6) 张三赁了李四一个柜台。
不难看出,以上动词均表现出物体的双向传递过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4)中的“借”本身即包含“借进”和“借出”两个相反义项,故其双宾句同样蕴涵两义:“我从他那里借了三万块钱”和“我借给他三万块钱”,译成英语则应分别处理为“I borrowed 30,000 yuan from him.”和“I lent him 30,000 yuan.”。可见,汉语将方向相反的动作用同一动词“借”表示,而英语却分别表达为“borrow”和“lend”,以区分物体不同的传递方向。例(5)亦然,根据《汉英大词典》(第三版),汉语“上课”所涵盖的两个义项,在英语需借助两个不同的表达:“attend class”(学生听课)和“conduct a class”(教师讲课)。例(6)同样如此。其实,汉语这类现象自古有之。试看:
(7) 沽: a. 买(buy),如“沽酒”。
b. 卖(sell),如“待价而沽”。
(8) 假: a. 借入(borrow),如“久假不归”。(《孟子·尽心下》)
b. 借出(lend),如“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成公二年》)
(9) 受: a. 接受(receive),如“权辞让不受”。(《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b. 给予(give),如“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从(7)(8)(9)可知,古汉语也常将相反方向的传递动作概念化为同一动词,其动作的双向特征已固化于动词语义中。而英语的动词概念化方式往往是单向的,对不同方向进行严格区别。这一表征差异表面上与动词的词汇语义特征有关,但其背后的深层缘由或是汉英两种语言对动作的不同概念化。上述仅是这一现象的一个侧面,下文拟谈另一侧面: 汉英部分双宾结构的概念化差异。
3.1.2 汉语“A↔B”与英语“A→B”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
一般而言,汉英双宾句均可形式化为“S+V+O1+O2”,但两者在具体使用中却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句法意义和适用范围: 汉语既有表示移动物体自左至右的句法结构,也有自右至左的,即双向可逆形式“A↔B”;而英语通常仅表现出物体单一右向的移动特点(马庆株,2002: 271;石毓智,2004;张建理,2006;何晓炜,2009等),即单向不可逆形式“A→B”。
既然语法结构和词汇成分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而词汇成分往往代表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总结,因此语法结构也可看作人类一般认知经验的反映(张伯江,2016: 101-9),即句式意义与词汇语义具有共同的来源(徐盛桓,2001),均系汉英对动作不同概念化的结果。
3.1.2.1 汉语“A↔B”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
经上文分析,“借、租、赁”等动词本身即具双向语义特征,但除此之外,本文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双宾句,其双向语义特征并非来自动词本身,而是由所在的双宾结构赋予,即该结构“对进入的语言成分进行了压制和修改”(张建理,2006: 33)。例如:
(10) 我倒了你一杯咖啡。
(11) 他切了我一块蛋糕。
(12) 她捧了我两捧瓜子。
不难看出,以上动词本不含涉明显方向,但进入双宾结构后,却表现出双向语义特征。现以(10)为例,“倒”的方向本不明确,但在双宾句中却既可从左向右理解为“我给你倒了一杯咖啡”,也可相反解读为从右向左“我从你那里倒了一杯咖啡”,译成英语分别是“I poured you a cup of coffee.”和“I had a cup of coffee from you.”。由此可见,汉语的同一传递动词若对应英语,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编码,并且该双向语义特征显然来自其所在的语法结构的压制,而这一双向赋义能力则与句式本身蕴涵的双向义有关。试看:
(13) a. 我送了他一支笔。
b. 我拿了他一支笔。
(14) a. 我递了他一本书。
b. 我偷了他一本书。
两例a中的动词“送”和“递”,均表示物体从主语向右移至间接宾语,而b中“拿”和“偷”的传递方向,则为从间接宾语向左移至主语,两类方向相反的传递行为在汉语双宾句中均较为贴切,其原因即在于汉语双宾结构的双向可逆特征,使得相反方向的传递动词可直接进入句子,无需做出改变。
一言以蔽之,汉语双宾句式的双向语义特征为如(10)至(12)中自身方向不明的动词接受句式方向压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如(13)和(14)中自身方向明确的左、右向动词进入句子,并保持原来方向不变奠定了基础。本文认为,这一语法现象与汉语概念化方式的双向空间性特征有关,对此,本文将在下文再做析述。
3.1.2.2 英语“A→B”在语法结构中的体现
Langacker(1991: 327-9)指出英语双宾句一般表现为“来源→终点”(source-target path);Goldberg(1995: 32-4)将其概括为“施事主语成功地致使一个客体转移给接受者”,包含“给予”这一基本语义;徐盛桓(2001: 82-3)也将其视为“实施者S通过V的行为和V展开的某种方式让N1领有N2,可简称为给予”。由此可见,英语双宾句仅蕴含 “给予”义,表现为物体自左至右的单向位移过程。例如:
(15) I gave Mary a book.
(16) I baked them a cake.
(17) Tom stole Mary a book.
总体来看,以上三句均包蕴英语双宾结构的 “给予”义,表示物体右向的传递过程,但细看则发现其分属三种不同的类型: 首先,(15)“give”为第一类: 动词本身即蕴涵“给予”义,与双宾句的物体位移方向相同,因而无需变动直接入句,此类动词还包括hand、bring、offer等;(16)“bake”属第二类: 动词本不具备“给予”义,徐盛桓(同上)将其分为“现实地蕴含给予义”和“潜在地蕴含”两种类型,但本文在此统一视为“动词本不包含给予义,由双宾句式赋予”,如wish、cook、pour等均可划入这一行列;而(17)为第三种: 动词本身表示的物体传递方向朝左,进入双宾句后传递方向发生反转,由此引起了句义的改变,具体来看:
(18)a. I stole a book.
b. I bought a pen.
(19) a. I stole him a book.
b. I bought him a pen.
(18)“steal”与“buy”原本蕴含“取得”义,即主语“I”获得某物,表示物体向左位移至主语位置,但在双宾句(19)中,虽然动作的发出者仍为主语“I”,但物体的最终传递方向却是从主语向右移至间接宾语“him”,继而表达了“给予”义:“我给他偷了一本书”(I stole a book for him.)和“我给他买了一支笔”(I bought a pen for him.),双宾结构使得物体的位移方向发生了反转。[注]不同于“借”类动词所表示的“借进”和“借出”的动作发出者发生了调换,第三种类动词“买、偷”动作均由主语发出,但本文在此暂不对动词的内部语义差异进行探讨,而是整体聚焦于物体在这些动作的作用下发生位移传递的方向。由此可知,英语左向动词,进入双宾结构,或比照(19)反转物体位移方向,并伴随句义的改变,或直接借助介宾短语明示其动作所指方向,表述为“I stole a book from him.”。
综上可知,方向不明确的动词进入汉语双宾结构时,往往被赋双向性,这源于双宾句式本身所蕴涵的双向语义特征,而英语的双宾结构对动词只能进行从左到右的单向压制,或许同样与句式本身的单向线序特征有关。
质言之,传递动词所表现的语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该民族对相关动作的概念化方式。因此,汉语部分传递动词的双向可逆特征“A↔B”,即方向不同的传递动作用同一动词表示,以及英语的单向不可逆特征“A→B”,即相反的位移方向需借助不同动词以示区分。石毓智(2006: 135-42)曾将这一语法现象解读为汉英动词矢量语义特征的差异,即汉语对动作行为的矢量特征不敏感,使得动词的矢量方向一般不具体化,而英语则是对动作矢量特征非常敏感的语言,因此英语动词的矢量方向往往是确定的。不过,本文认为,石毓智虽然为汉英双宾句不同的语法表现提供了新的解读视角,但似乎依然处于描写层面,尚未对汉英动词矢量特征差异的深层缘由做进一步的挖掘。本文在此认为,汉英民族这一表征差异,其背后隐匿的是二者不同的时空性思维偏好。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哲学将天地空间视为一个整体,睽重六合(上下、东西、南北)所体现的、为空间所特有的对称性和可逆性(刘文英,2000: 136)。鉴于此,汉语在空间性思维的影响下,往往倾向于诉诸空间视阈编码事物,对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进行空间化表征,从多维视角识解动作行为,从而影响了这一行为既可此方向,也可彼方向,还可发生逆转,呈现出双向可逆的空间性特征。而在西方,时间被视为一种无限进展的绵延,以一维性为前提,前后相承,连续出现,不可逆转,任何两部分也不得重叠(洛克,1983: 170-73)。因此,英语作为西方语言之一,在时间一维线序思维的统摄下,常对行为或动作的发展、变化进行时间编码,一个动作常常只能对应一个特定的时间节点,因而须对动作的方向进行严格区分,条分缕析,不得含糊,从而表现出单向不可逆的时间性特征。
3.2 汉语动词概念化的“A→B=B←A”与英语动词概念化的“A→B≠B←A”
上文立足双宾结构“A↔B”与“A→B”视角具体验视了汉英部分传递动词的概念化差异,本节拟从可逆句“A→B = B←A”和“A→B ≠ B←A”角度进一步探究汉英传递行为的另一区别。
汉语“两面性动词”这一概念滥觞于丁声树等(1961/2009: 37):“有的动词是两面性的,主语跟宾语可以互换,意思上没有大差别”,这类句式往往称为“可逆句”或“双向动词施事宾语句”(翁义明,2014)。例如:
(20) 一个大饼夹一根油条=一根油条夹一个大饼
(21) 三四个人盖一条被子=一条被子盖三四个人
(22) 火车通西藏=西藏通火车
(23) 人参泡酒=酒泡人参
据此,马汉麟(1993: 22-4)反驳到,(20)中动词“夹”和(21)的“盖”不能等量齐观,“夹”或者可与“炒、拌、加”等视为两面性,前后成分易位不产生意思变化,但“盖”的意义却有所区别,因此不宜算作两面性动词。陈平(2017: 6-9)与其看法类同,指出不仅(21)如此,(22)中的动词在主宾互换后语义的同一性也大大降低,不再是同一动词,转而从语义角色的施受性特征对(23)这类句式进行了阐释;[注]诚然,主宾语互换后,难免会引起语义或语用上的差别,但句子的基本命题不变,这恐怕是事实。因此本文认为,举凡“前后成分易位而客观事实基本不变”的动词,均是两面性动词,这类句式也一并视为“可逆句”。沈家煊(2015: 239-43)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扩展,他指出主宾语的对立实质上是施受事的对立,以上例句主宾互换但施受关系不变,说明句中施受对立关系原本就是模糊的,而模糊的原因正在于句中动词的动作义已削弱,失去了原有的支配能力和方向性,施受关系的中和使得句式可逆。持相似观点的其他学者(张旺熹,1999;陈昌来,2000: 200;陆俭明,2004;张斌,2010/2015: 612-8;等)也纷纷表示动词“非动态性”的语义特征是这一语法现象的关键。
概言之,学界倾向于将这类句式可逆的管钥归于动词动作义或方向性的削弱或丧失。然而,本文认为,可逆句中动词的动作义或方向性虽在表面上看似模糊,但实质上动作的方向性并未削弱,其中潜藏的深层机制或许仍与汉语对传递行为的概念化方式有关。尽管石毓智(2006: 286)曾富有见地地表述过“转换式之间存在动作方向性的改变”,但动作的方向具体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为何改变?在相应情况下英语为何不能改变动词方向以实现句式的互逆?他对此尚未陈述。经研究,本文发现,可逆句式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供用关系,而供用关系又往往意蕴位移传递行为,结合上文汉英对部分传递动作的概念化差异,可为可逆句这类语法现象的进一步究问提供新思路。对此,本文拟在下文阐述。
3.2.1 供用类可逆句
(20)(21)这类句式一般表示“某些物品、器具、食物、材料等可以供多少消费者、使用者、占有者消费、使用或占有”(张斌,2010/2015: 612-8),是语法学界发现较早且用力最勤的一类可逆句(鹿荣、齐沪扬,2010),常被称为“供用句”。研究发现,供用句中的动词往往蕴含“给予”义,或“动作+给予”的复合(任鹰,1999),因而这类句式可进一步解读为“供用者以某种方式给予供用对象某供用物”(李敏,1998)。但需指出的是,其中的供用者往往具有语义隐含性,一般不外显,并且也不一定发生了实际的位移行动。本文拟对这类供用关系采取宽泛的解读,认为凡是可以通过隐喻或转喻等方式看作“某存在物以某种方式供给某人或某物使用”的句式,均算作供用句(鹿荣、齐沪扬,2010)。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便可从“供用物位移传递行为”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可逆句,即主语位置上的供用物A,在供用者的动作下向供用对象B作位移传递,动词表示供用的具体方式,宾语位置的供用对象B是该传递行为的终点,因此,供用句a所表示的位移过程可形式化为“A→B”。试看以下例句:
(24) a. 一锅饭吃十个人=b. 十个人吃一锅饭
(25) a. 一张桌子坐五个小孩=b. 五个小孩坐一张桌子
由上可知,供用句(24a)可看作供用物A“一锅饭”由供用者给予供用对象B“十个人”吃,虽供用者没有出现,但其中内蕴的传递过程为A“一锅饭”向右位移至B“十个人”,即“A→B”。供用句(25a)也可作类似的理解: 供用物A“一张桌子”给予供用对象B“五个小孩”坐,虽然桌子可能未必发生实际的位移行为,但可从隐喻角度看作是桌子向右移动至终点“五个小孩”,形式化为“A→B”。
但学界对其可逆关系式b,即“B←A”,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主宾易位后原句式的表义重点发生了改变,由“供给”义变成了“分配”或“益得”义,也有学者如陆俭明(2004: 414)认为这类句式实际是“表容纳性的数量结构对应式”,不论颠倒与否,均表示“容纳量—容纳方式—被容纳量”的语义关系。其实,不难看出,学界意见相左的主因在于,主宾语的颠倒引起了解读视角的变化,原本位于句末的“供用对象”B移至句首成为话题,继而引发了对句义的不同理解。不过,且不论原动词的语义内容是否变化,如果单从“句中蕴含的位移传递行为”来看,其实质并未改变,仍表示“供用物”A在动作作用下发生位移至“供用对象”B,其区别仅在于b句的位移终点提至句首,使得物体传递方向发生了逆转,但归根结底仍是同一传递行为的双向演绎。
结合前文的分析,汉语空间性的思维方式使其对部分传递动作的概念化呈现出双向可逆的特征,传递方向的逆转并不改变位移本质,因而这类句式可在动词形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发生互逆,形式化为“A→B = B←A”。因此,如果说供用句是给予物向右传递的话,那么,其可逆对应式发生的只是方向的反转。如(24)中供用句a表示物体“一锅饭”向右传递给“十个人”吃,而其可逆关系式b仍表示“一锅饭”向“十个人”作位移行动,只是表示的方向朝左。因此,汉语空间性思维的双向可逆特征使这一可逆表达式依然成立,且与原句表义基本一致。
至此,我们回到本节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相比于汉语,我们在此需要追问为何英语不会发生如此互逆?试看例(24),在此记作(26):
(26) a. 一锅饭吃十个人。
a’. *A pot of rice eats ten people.
b. 十个人吃一锅饭。
b’.Ten people eat a pot of rice.
显然,(26)中b可英译为b’“Ten people eat a pot of rice.”,而其可逆式a’“*A pot of rice eats ten people.”却不合语法。由上文分析,既然这类句式本质上为方向相反的同一传递动作,将给予物‘a pot of rice’移至给予对象‘ten people’这一基本事实未曾改变,那么,为何方向逆转使得英语表达不再成立?本文仍将其根由归于英语对传递动作的单向概念化方式,方向的逆转需要视为不同的行为,借助不同的表达,因此,不做任何改变直接主宾易位,并不适用于英语。鉴于“方向性”作为传递动作的基本属性之一,往往蕴涵于动词语义中,因而英语一般采用动词的形态变化“BE+动词过去分词”予以明示,表述为“A pot of rice is provided for ten people.”。
3.2.2 广义的供用类可逆句
虽然学界对供用句的涵盖范围尚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但我们已在上文指出,本文对供用句采取比较宽泛的标准,因此,对以下例句我们同样可以做此类分析:
(27) a. 纸糊窗子=b. 窗子糊纸
(28) a. 火车通山村=b. 山村通火车
(27a)可隐喻性地看作通过供用者的施力行为把A“纸”供给B“窗子”使用,表示“纸”向终点“窗子”作位移运动,其中区别在于a句移动的方向朝右,即“A→B”,而b为向左“B←A”,实质上是同一位移行为的双向过程,因而汉语概念化方式的双向可逆性使得主宾语互换后仍表达同样的意思,基本不影响原命题。其实,陈平(2017: 8)曾从另一视角印证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这类句式中,一个名词性成分为工具,如“纸”,而另一成分却不仅是动作对象,也可看作工具通过动作所抵达的地点,动作“糊”的结果是“纸”成为“窗子”的一部分,说的也是这一位移运动。然而,对比英译却发现,(27a)需先补齐动作发出者,即上文提到的具有语义隐含性的供用者,表述为“He pasted a sheet of paper onto the window.”,而(27b)则需将“纸”作为工具的语义角色展现出来:“The window was pasted with a sheet of paper.”。由此可见,汉语这类互逆句式在英语中很难直接实现,因为英语的动作方向往往是明确的,其方向的灵活性远不及汉语,而这也源于英语单向不可逆的动词概念化方式。 同样,(28)也可隐喻地理解为“火车”通过位移行为抵达了“山村”这一地点,汉语a和b两种方式均蕴含此意,但英语则需要分别表示为a“The train passes through the mountain village”和b“The mountain village has a train station”。
概言之,本节论及的内容与3.1均为汉英对部分传递动作的不同概念化在语言层面的投射。汉语往往将方向相反的传递动作概念化为同一种行为,用相同的动词表示,从而展现出双向可逆的特征“A↔B”,而供用句同样意蕴位移过程,并且传递方向的逆转并不改变其位移的本质,因此该句式可在动词形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发生互逆,即“A→B = B←A”,此或许为汉语空间双向思维的佐证。而英语对同类动作的传递方向常作严格的区辨,其概念化具有单向不可逆的特点“A→B”,因而并未形成相应的互逆表达,即“A→B ≠B←A”。据此,对于方向相反的动作,英语或采用不同的动词分别表示,如3.1,或借助动词的形态变化以示区分,如3.2,此皆英语时间单向思维的一个映显。
4. 汉英对时间的不同概念化: 二维空间特征和一维线序特征
总体来看,汉英民族的时间认知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二者皆采用直线型(linear)模式,视时间为单向前进、不可逆转的直线,有别于循环型(cyclic)和螺旋型(spiral)两种模式(转引自Yu,1996: 86)。此外,时间是抽象的,无法直接感知和描述,因而两者均借助空间方位隐喻表征时间,体现了汉英民族共同的体验和认知基础。
然而,尽管二者在认知模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但其差异性也颇为明显,时间的线序单向性,并不代表其识解方式也必须采用单维视角。因此,若将时间概念化方式用X和Y两个坐标轴分别标识,代表水平横向维度和垂直纵向维度,则不难发现,汉语的加工模式同时牵涉X和Y两个方向轴,具有二维空间特征,而英语则仅限于X轴,即主要以水平维度识解时间,具有一维线序特征。汉英民族时间概念化的这一差异已得到国外一些心理实验的证实(Boroditsky,2001;Fuhrmanetal.,2011等)。
4.1 汉语时间概念化的二维空间特征
“前”和“后”均为水平维度的空间方位词,将其用于时间隐喻是汉民族用X轴加工时间的典型表现。例如:
(29)以前 从前 前天 前年 前世 前汉 前程
以后 往后 后天 后年 后世 后汉 后路
前人植树后人乘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不觉前贤畏后生
而“上”和“下”乃垂直维度的方位词,但在时间表征中也相当习见。例如:
(30) 上半叶 上周一 上一代 上个世纪上辈子 上古
下半叶 下周一 下一代 下个世纪 下辈子 五代以下
由此可知,Y轴同样是汉民族识解时间的基本方式之一。《说文解字》中“上”和“下”的释义为: 高者为“上”,底者为“下”。由此,我们或许可做这样的延伸: 举凡能在Y轴表示位置高低(或上下)的词素,如头/尾,头/底,高/低等,均可用来喻指时间,如年头/年尾,月头/月底,高寿/低龄等(张建理、丁展平,2003: 33)。
不仅如此,汉语的时间概念化不仅X、Y两轴均涉,而且彼此互通自然。史佩信(2004: 10)有言,古人把时间想像为一根垂直的轴线,箭头向上,因而“前”又是“上”,“后”又是“下”。我们的观察可得到《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的佐证:“上”作为空间方位词,明确标有“次序或时间在前”这一义项。因此,汉语时间表达常将“上、前、先”归为一类,相互替换。例如:
(31) 上/前半天 上/前半夜 上午=前晌
上/前/先辈 正如上文/前文/先前提到 三十岁上下/左右
此外,X轴与Y轴不仅可以如(31)彼此替代,再往前走一步,汉语时间表征中两轴交叉混合,并置共现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试看:
(32)前天上午后天下午上世纪前叶下半场后二十分钟
上回说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可见,汉语倾向于从多维视角识解时间,将其视为空间中的实体,具有长、宽、高的特征,因而诸多描述物体形貌的词语,如高低、大小等,均可用以表征时间,相当适宜。例如:

大前年 大龄 大礼拜 大尽 大年 小晌午 小青年 小字辈 小憩
一家大小 二十大几的人 七十大寿
此外,汉语中的其他空间词汇,也常被用来表征时间。如“万寿无疆”中,“无疆”原指空间延伸没有界限,此处却指寿命长久;“分寸”本是空间长短单位,却另有“分阴”、“寸阴”等表时间短促的说法(刘文英,2000: 135)。
4.2 英语时间概念化的一维线序特征
学界(Boroditsky,2001;徐丹,2008;Fuhrmanetal.,2011等)普遍认为,英语的时间认知模式一般以水平X轴为主。试看:
(34)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 am looking ahead to Christmas.
The past is behind us.
Look back to the days of one’s childhood.
而垂直维度的方位词,如up、down等,在英语中鲜有表达,即便有,也常以固定搭配的形式出现(刘丽虹、张积家,2009)。例如:
(35) up to now
to pass sth.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custom has been carried down from the fifteenth century.
不难发现,基于Y轴进行时间加工,英语的普遍性和能产度皆远不及汉语,或许垂直视角的概念化方式并不符合英民族的思维习惯,自然,面对汉语众多来自纵向维度的时间表征,英语往往编码如下:
(36) 上半年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下半年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上次 last time
下次 next time
上半夜 before midnight
下半夜 after midnight
显然,英语将Y轴的“上”和“下”均作了水平化处理,表述为X轴的“first、last、before”和“second、next、after”等。可见,英民族的时间概念化具有明显的单维线序特征,倾向于从水平维度加工,似乎并未形成垂直方位的投射(Lakoff,1993;Alverson,1994等)。而英语的这一特征在构词层面也有体现,如表时间的词缀“fore-”意为before, 如foretell、forewarn等,“post-”意为after,如post-war、post-modern等, “pre-”意为before/in advance,如pre-war、pre-19th century等, “re-”意为back/ again,如recycle、recall等(夸克等,1985/1989: 2133),此均系水平维度的词汇表征。[注]英民族的时间认知方式是以水平维度为主的,从垂直维度表征时间可谓屈指可数,仅有ascendant、descendant等少数词项(张建理、丁展平,2003)。
至此,汉英民族的时间识解差异已清晰地展现于我们眼前。汉语的时间概念化方式既有X轴的水平视角,也有Y轴的垂直视角,或X和Y两坐标轴彼此替代,交叉共现,具有明显的二维空间特征;而英语的时间概念化方式仅限于水平维度的X轴,展现出显著的一维线序特征。
5. 结语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其表征形式的根源在于思维。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概念化理论,对比汉英对部分传递动作和时间的不同概念化方式,发现汉语动词概念化在许多情况下具有双向可逆性,以及时间概念化体现出二维空间特征,而英语动词概念化通常仅具单向不可逆性,以及时间概念化呈现出一维线序特征,这或许为汉英时空性思维差异的又一力证。正如Nisbett(2003: 89-96)所述,东方人常以广角镜头(a wide-angle lens)审度世界,而西方多以隧道视角(tunnel vision)。而空间多维之于广镜,时间单维之于隧道的根性差异,与本文观点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