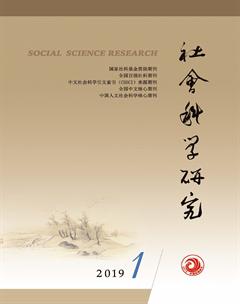赋文体渊源再论
〔摘要〕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賦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关键词〕 赋;辞;宋玉;文体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1-0185-08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言谓:“楚之骚,汉之赋……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以楚骚汉赋而言,楚国孕育产生了屈原的楚辞,汉代的大一统政治和地理催生了汉赋。佛教传入后登堂入室进入文人视野,遂在音韵基础上促进了格律诗的繁荣。宋有词,元有曲,明清小说大盛,五四后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影响至今。我们欲考镜源流,探赜索隐,需将特定文学置于产生其特定范式的时代语境,方能剥离现象,得其真源。欲探寻作为文学文体的“赋”产生的来龙去脉,需先界定“赋”文体的本质特性。刘勰说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2〕,实已捕捉到汉赋的本质特征,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应专指学界所谓“汉大赋”或“体物散体赋”,而与汉代文学中的其他体裁诸如拟骚之作、《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模拟屈辞之作以及四言咏物小赋皆有本质不同,今人不可不察焉。因而,本文所讨论的赋体,实专指有汉一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典范之汉大赋。
一、从文字学考察“赋”的含义是探寻赋体渊源的前提
学界关于赋体渊源的不同看法,多源于对“赋”这一文字字义的不同认识。梳理“赋”文字含义的历史变迁,探察后代借用古“赋”字命名新文体这一汉字文化现象,是认识赋体渊源的关键。
1.“赋”字的本义是赋税。“赋”为“贝”与“武”的结合。《说文》谓:“赋,敛也。从贝武声。”〔3〕其实不然,构造“赋”字的两个部件在“赋”的原始本义中皆有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形声组合,而应纳入会意字更能体察其原初意象。《说文》谓“古者货贝而宝龟”〔4〕,贝币曾为上古货物流通的交流媒介,至秦方废贝行钱,此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多有印证。“武”乃“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5〕上古部落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外来族群的侵扰,自然会在部落内产生劳动分工,一部分勇猛之人会剥离生产劳作,而专事保卫部落的人身财产安全,此即为武士阶层的产生。武士阶层一旦专门化、职业化,那么就需要其他一线劳作阶层的奉养,因而从劳作阶层抽取赋税的制度由此而产生。由此,“赋”字的本义即是,为了部落的安全,为了部落不受外来战争的掠夺,必然要从原来全体从事劳作的部落群体中分离出一部分能保家卫国的武士阶层,为这些武士阶层提供的财物奉养即是最早的“赋”义,此正如孟子所谓“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天下通则。
先秦典籍中,使用“赋”字本义处尚多。《尚书·禹贡》言“赋”最伙,这可能与《禹贡》重点记九州物产与贡赋相关。《禹贡》载:“禹别九州……冀州……厥赋惟上上错……兖州……厥赋贞……青州……厥赋中上……徐州……厥赋中中……扬州……厥赋下上错……荆州……厥赋上下……豫州……厥赋错上中……梁州……厥赋下中三错……雍州……厥赋中下……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6〕《禹贡》即使用了12处“赋”,其意义皆为“赋”最早的原初本义赋税。根据“赋”字字源的探析,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的说法似为可信。
《周礼》言“赋”极多,基本为赋之本义。《天官·大宰》载“以八则治都鄙……五曰赋贡……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7〕此正是“赋”原初赋税之本义,《大宰》此记太宰“九赋”职责,《天官·小宰》再次提到“九赋”:“小宰之职……执邦之九贡九赋”〔8〕,此皆是“赋”之本义。“九赋”说明了早期赋税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为赋税的地域范围,只要在统治阶层势力范围内,皆可征赋。一为赋税的税种类别,都市商贸、山泽物产,统治阶层皆可抽取赋税用于治理邦国。对于“九赋”的功用,《天官·大府》解释得更为详赡:“大府掌九贡、九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馀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9〕《地官·大司徒》“以敛财赋”〔10〕更明白揭示了“赋”的原初语义。此外,《天官·职内》《天官·职岁》《地官·小司徒》《地官·载师》《地官·县师》《地官·遂人》《地官·遂师》《地官·委人》《地官·羽人》《地官·掌葛》《夏官·大司马》皆有类似“贡赋”“赋贡”“赋税”“野赋”“财赋”“邦赋”的记载,兹不赘。
此外,《今本竹书纪年》卷下载“宣王……复田赋”〔11〕以及“幽王……初增赋”〔12〕,《左传·隐公四年》载“君为主,敝邑以赋”〔13〕,《左传·僖公二七年》载“《夏书》曰:‘赋纳以言”〔14〕,《春秋公羊传》卷二八哀公一二年载“十有二年,春,用田赋”〔15〕,《春秋谷梁传》卷六庄公二九年载“民勤于财,则贡赋少”〔16〕,《春秋谷梁传》卷二〇哀公一二年载“十有二年,春,用田赋”〔17〕,《论语·公冶长》载“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18〕,《孟子·离娄上》载“孟子曰:求也我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19〕,诸多先秦典籍中所载之“赋”皆为赋税之本义。
2.“赋”由本义贡赋、赋税衍化出铺陈政教的政治功能。“赋”因何衍化出铺陈之义,于史难征。笔者推测,在上古缴纳赋税的时候,纳贡者应按统治者要求将其财货一一铺陈以方便官方点数收纳。
《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和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20〕此段文字历来为治赋者所重视。不少学者在引用这段关于言赋的文字时,往往不顾前后语境,从而导致断章取义。郑玄谓:“教,教瞽矇也。”〔21〕太师为掌管宫廷祭祀大礼的音乐总管,他所掌管的治乐者多为瞽矇,瞽曚即盲人。瞽矇从六个方面受太师的政教,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和方式总称为“六诗”。郑玄注释其中“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22〕依据郑玄的注解,太师教导瞽矇在祭祀时要学会用六种不同的歌诗方式来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或引古以喻今,或直陈今之善恶,或婉曲类比以谏今,或以譬喻赞美今之所得,或树今之典范以为后世法则,或大声颂扬今之广德,此即为“教六诗”的本义。由此可知,在《周礼》时代,作为政治意识或话语意义表达形态的六诗之“赋”与汉代所形成的汉大赋文学体裁在概念本质上相去甚远,我们如果非要将两者硬性黏合在一起,免不了比附之嫌。在此,我们有必要顺带论述并还原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昔者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23〕一语的历史语境。后世学者多认为班固所谓赋为古诗之流的意思是赋来源于《诗经》的传统,此似没有全局观照班固此言的前后语境,班固说得再清楚不过,周成王、周康王继承文王、武王业绩,成就西周最为强盛的成康盛世,然而成康以后,瞽矇们祭祀所用的“六诗”之“赋”“颂”行为遂告停歇,再也没有复兴之机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言“赋者,古诗之流”,正是完全依从《周礼》太师“教六诗”的古义,其着眼于赋的政教社会功能这一先在之义,强调的是用语言声音铺陈展示君王政教善恶的行为方式,而非关“诗三百”的《诗经》,非关文体源流的考辨,而是着眼于赋的政教社会功能,今人不可不察焉。
《诗·大雅·烝民》载:“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24〕郑玄谓:“赋,布也……王之政教使群臣施布之。”〔25〕此处“赋”为动词功能,就是后世所说的布告天下的意思,布告天下的本质是要原原本本地将天子的英明决策直接让天下人周知。《烝民》另外一章也说到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郑玄谓:“以布政于畿外,天下诸侯于是莫不发应。”〔26〕此处“赋”一如前引“明命使赋”,皆是作为王之喉舌的仲山甫将王命布告四方,实行政教功能。
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所谓“敷布其义谓之赋”〔27〕的看法,即是从“赋”铺陈之义的角度认识汉赋的。
3.赋由铺陈之义再引申为诵读、朗诵。赋税之“赋”,衍化为铺陈之义,是因为贡赋者所贡之物什需一一鋪陈以备“劳心者”具数清点。“劳心者”在清点物什过程中,需大声诵读具陈的物品和数量,以便归类入库储存,此或为“赋”义再次引申为诵读的历史语境。
《左传》用此“赋”义极伙。《隐公四年》“卫人所为赋《硕人》也”〔28〕,《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为之赋《清人》”〔29〕,《僖公二四年》“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30〕,《文公四年》“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公赋《嘉乐》……为赋《湛露》及《彤弓》”〔31〕,《文公十三年》“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32〕,《成公八年》“公享之,赋《韩奕》之五章……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33〕,《襄公九年》“宣子赋《摽有梅》……武子赋《角弓》……武子赋《彤弓》”〔34〕,《襄公一四年》“赋《青蝇》而退……穆子赋《瓠有苦叶》”〔35〕等等,皆为其例,其数量甚多,兹不具录,大致计来,有78处之多。
从《左传》的记载看,此“赋”已经是动词,所“赋”之内容大多是《诗》里的篇章,此即为春秋时期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的“赋诗言志”传统。由此可知,“赋”在先秦引申为诵读义时,更多强调的是将已有的诗篇用适当的语气语调陈述出来,即原原本本地再现已有作品,此与铺陈之义极有关联,将诗篇用语言铺陈出来,即为吟诵。《楚辞·招魂》有“人有所极,同心赋些”句,东汉王逸注谓:“赋,诵也。”〔36〕“赋”从原初赋税之义流衍为大声吟诵,表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则有着内在的逻辑演变轨迹。汉赋体物写貌的本质特征正是源于“赋”义由铺陈而引申出的诵读含义。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谓:“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37〕,班固对汉赋的认识亦正是基于“赋”义在春秋时代衍化出来的诵读之义,春秋时代“赋诗言志”即是在正式场合选择恰当的《诗》篇大声朗诵以为自己代言的行为,此种行为不需要配乐进行,仅以声音的形式呈现于众人之前以言心志。那个时代士阶层中的大夫是否合格称职,即以是否具备这一才能作为评判标准之一,也即是大夫是否能熟读且能背诵《诗》,并还要能在正式场合恰切地“赋诗言志”。由此可知,此“赋”义与汉代之文学体式汉大赋似乎还有一段长路,由“诵读、朗诵”引申发展为文体之赋,即由动词之“赋”的诵读朗诵行为过渡到作为名词的“赋体”尚有一定距离和逻辑过程。
二、认识辞、赋不同本质是探讨赋体源流的基础
要探寻“赋”作为一种全新的文体是如何起源产生的,仅仅对“赋”进行文献文字的溯源工作并不能揭示其历史本源。当然,以传统的荀子、宋玉、枚乘等所谓实际赋体创作来进行赋体的源流考镜似乎也并不能真正触及赋体产生的本源。文学的问题常常不能仅停留在文学自身所谓的发展规律上,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是时代复杂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价值观、审美观以及语言发展规律等综合因素的合力。一种文体的发展往往是凭借于外力的刺激才促成其现实的演变。此一现象在文化史中尤为突出,没有佛教的传入,道教的产生几乎不太可能,没有“五四”前后西方思想文化的译介,20世纪中国文化的转型几乎也很难想象。
我们先从辞、赋之本质不同谈起。以文体论,《楚辞》所收作品大体为诗,多以言志抒情为主,关注点并不在铺陈叙事,而在抒发内在心灵的情绪性灵,其书写的向度是内求诸己,将自己内心主观的喜怒哀乐呈现给读者。早期大赋虽间有诗之韵语格调,但就总体而论更接近于散文,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要创作目的,其关注重点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如果以绘画为喻,《楚辞》特别是屈原的作品极似写意水墨,而汉赋更接近西方油画描摹状物的写实之风。
两千多年来,同屈原作品的真伪与篇数一样,屈原作品命名亦是纠缠不清,“屈骚”“屈赋”抑或“屈辞”,学者们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为能更好厘清辞、赋作为文体的不同特征,笔者在《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中主张屈原的作品宜以“辞”称名。〔38〕辞、赋当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辞之登峰造极即屈原其作,这似乎也是《楚辞》成书之初编辑者以“辞”为名的初衷所在,而且,流传至今刘向《楚辞》一书所收作品似乎也是按照上述标准进行采编。
真正让赋成为一代之新型文学范式的当属汉代典型的汉大赋。诸如汉初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等所谓“骚体赋”只不过是以“赋”名篇的“辞”体,贾谊诸家借宋玉“赋”名表达的完全是屈“辞”的牢愁情思,这或许即是后世学者辞、赋不分或辞、赋并称的真正渊源。虽然贾谊谪居长沙期间将楚地文宗屈原的地方作品推向中原,并使其成为天下文学,但其时指称屈原其作尚没有专门定型称名为“辞”。作品先行,理论滞后,这是文学现象的普遍规律。屈原诸作虽皆不以“辞”称名,但内在感情基调与行文风格却是基本一致的。宋玉除了模拟屈原诗作,于屈辞之外还创制新体并借用战国惯用的“赋诗言志”“登高能赋”之“赋”称以名篇,此即《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由于屈原本人并没有固定一个特定的名称来称代自己的作品,这也就无意间造成后世辞、赋混称的乱局。当有了屈原和宋玉不同风格的作品,加之汉初两类文体皆有大量拟作的出现,人们才开始主观意识到两者的差异,进而在理论上进行总结区分,此即刘向《楚辭》成书之由。刘向编辑《楚辞》,标准甚为分明,所收作品除屈原诸作外,宋玉只收《九辨》《招魂》,而《高唐》《神女》以赋名篇之文,概莫收录。汉人篇什亦仅收模拟楚辞之作。不仅刘向,司马迁也已意识到这两种文体的内在不同。但后世多认为辞、赋混称始自司马迁,其实这源于人们对司马迁《史记》的误读,认真清理《史记》的原始文本以及原始含义,对认识辞、赋两种文体的本质至关重要。
我们先看《史记》涉及辞、赋的不同记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行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屈原贾生列传》)〔39〕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贾生列传》)〔40〕
贾生……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屈原贾生列传》)〔41〕
贾生……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屈原贾生列传》)〔42〕
司马相如……会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列传》)〔43〕
《屈原贾生列传》所记“乃作怀沙之赋”,其“赋”义与前引《左传》大量“赋诗言志”之“赋”同,乃为诵读,吟诵之义,非关汉代文学体裁汉赋的特指。上引三条材料中的“其辞曰”中的“辞”,也不是《楚辞》中文学体裁的特指,而是文辞之辞。司马迁真正涉及辞、赋文学体裁的论述只有“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以及“会景帝不好辞赋”两处记载。这两条材料说得十分明确,“辞”与“赋”在司马迁的意识中似乎已有主观的区分,汉景帝不喜欢楚地的“辞”以及当朝的“赋”,遂致使以擅长写汉大赋的司马相如没有用武之地。司马迁正是体察到了屈原所作与后来继踵者宋玉、唐勒、景差所作颇有本质不同,所以司马迁才将屈原的作品以“辞”称名,而将后来宋玉诸家的作品以“赋”为名,从而将屈宋诸作进行了文体上的简单区分,这一点《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44〕的记载亦可为佐证,表明司马迁将屈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离骚》是以“辞”称名的。由此,我们认为司马迁对他所处时代出现的两种不同文学体裁“辞”与“赋”已有所认识。
但是,东汉初年班固却完全以“赋”称“辞”。《汉书》归屈原作品为“屈原赋二十五篇”。班固这样认识辞、赋,自有其时代原因,他身处赋体大盛的汉赋时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班固还没有以文学的视角主观意识到二者的根本区别,以致“辞”“赋”不分或以“赋”称“辞”。班固开此先河,直接造成后世楚辞学者在屈原作品命名问题上的混乱,诸如楚辞研究大家汤炳正《屈赋新探》、姜亮夫《屈原赋今译》等皆以“赋”称屈原辞作。屈原作品诸如《离骚》“就重华而陈辞”、《抽思》“结微情以陈辞”、《抽思》“兹历情以陈辞”、《抽思》“敖朕辞而不听”、《思美人》“因归鸟而致辞”、《惜往日》“听馋人之虚辞”、《惜往日》“不毕辞而赴渊”、《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等皆大量使用“辞”来行文,这或许也是《楚辞》命名的启发,即使刘向编选的《楚辞》文学选集明显以“辞”指称屈作以及后继扬波者的仿作,更有文艺理论家如刘勰以《辨骚》《诠赋》这样十分彰明的区分来作“辞”“赋”“划境”之论,但后世学者还是囿于《汉书》传统和习惯喜用“屈赋”来命名屈原作品,人为造成辞、赋两种文学体裁的混淆和杂乱。
清代学者对此问题已多有认识,如徐焕龙《屈辞洗髓》、陈本礼《屈辞精义》,此外,今人金开诚《屈原辞研究》、黄凤显《屈辞体研究》,皆是“辞”“赋”划境之论,“辞”“赋”分途应为学术发展的未来方向。费振刚《辞与赋》更有明确的认识:“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先出现的。辞,即楚辞,汉代人用以称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创作。赋,作为文体,初步形成于战国,而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专称。”〔45〕
自班固《离骚序》“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46〕的论断后,王逸《楚辞章句序》“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47〕、刘勰《诠赋》“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48〕、刘熙载《赋概》“骚为赋之祖”〔49〕等皆着眼辞、赋两体的紧密渊源,然而,指认汉赋源于《楚辞》似并不能揭示辞、赋本质不同以及汉赋文体的真正来源。以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学者身处庐山,其时尚离屈原不远,加之汉代作家大多“辞”“赋”两体兼擅,而且“辞”“赋”创作者又往往无意识混用“辞”“赋”两种名称,故而产生这种混乱,当属情有可原。但是,自刘向、萧统之后,尤至今日,若仍以“赋”称“辞”,或以“辞”称“赋”,似颇不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分门别类,因而,认识“辞”“赋”两种文体的本质不同,不仅有助于“辞”“赋”研究的专精深入,更能从历史语境中探寻认清赋体文学的源流线索。
三、还原文本是探索赋体渊源的关键
研究文学文献,回归文本、还原文本无疑是最符合历史真实也是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后世研究者的看法、认识只能是研究环节的重要参证,并不能作为唯一定论,探讨赋体起源亦应作如是观。赋体起源说法众多,我们试对这些说法进行文本对比探析。
1.汉赋源于《诗经》。此种说法起始于后世对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的误读,正论前述已明,此不重复。由此误读引起的这一看法影响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古代至当代的汉赋研究史,今人坚持者颇多。诸如简宗梧认为赋“是诗的别支……诗的延续……叙事描写的诗”〔50〕,迟文浚认为赋是“中国诗史上不容忽视的一章”〔51〕,徐宗文也有相似看法。〔52〕回归文本,考察《诗》与汉赋原始文本的文字记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汉赋先叙主客问答,然后再引出繁富的铺陈描摹,明显带有故事情节性敷陈特征,而汉赋的这种类似小说人物、情节、环境的写法在《诗》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其次,《诗》多数为重复短章,通过变换个别字词来反复咏叹。而汉赋不采用重章复沓式的行文模式,每句皆用新语新词,极力追求语词的丰赡。再者,《诗》在描写事物时往往是将镜头聚焦在某点,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只是变换主角的简单动作来反复描写同一场景。而汉赋采用的是推移镜头视角对不同景物做不同维度的细致描写,如《上林赋》“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荡荡乎八川分流……于是乎崇山矗矗……于是乎周览泛观……于是乎离宫别馆……于是乎卢橘夏熟……于是乎玄猿素雌……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于是乎乘舆弭节……于是乎游戏懈怠……于是乎酒中乐酣……于是历吉日以斋戒”〔53〕等描绘,完全是从不同活动主题进行细致的场景摹画,每一个画面皆用不同的语汇表达不同的内容。此外,《诗》基本为四言,整齐划一,而汉赋完全是散文的写法,并不局限于四言句式。由此而论,将赋的起源与《诗》生硬附和,从深入文本的角度考察,难免牵强。
2.汉赋源于荀子《赋篇》。《赋篇》分礼、知、云、蚕、箴等五个部分,后有四言《佹诗》。细读文本,五个部分其实是高级的文字游戏,即所谓谜语。《赋篇》虽也采用君臣问答的形式来设谜与猜谜,但这种问答完全没有汉赋中主客设问的情节情景性。《赋篇》言五物虽亦有铺陈描写,但离汉赋铺采摛文的极致夸张尚有较大差别。《赋篇》隐设五物虽亦从不同侧面进行描摹,但都是围绕某一物进行的多方描写,目的是让猜谜者尽量能猜出谜底。而汉赋的描摹是穷尽式的博物观览,将同类事物铺排置放于同一个画面,让人产生繁富宏丽的视觉震撼。由此,仅从语言文字角度说汉赋与《赋篇》有内在紧密的联系,似乎与文本事实并不相符。但是,荀子此作何以名为《赋篇》呢?虽然《汉书·艺文志》记有“孙卿赋十篇”,但我们不能就此据信荀子的十篇赋作就是与汉赋相同的作品,因为《汉书·艺文志》同样也说“屈原赋二十五篇”。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前面所引《左传》大量有关“赋诗言志”的记载,不难看出,在战国时代,称引《诗》篇或者自作适合情景的诗作来表明心意,已是当时的时代风尚。荀子此赋与《左传》中的描述情形大体无异,即是说《赋篇》之文,实近前代出使应对之诗而远敷陈写物之赋。
3.从文本内容考察,汉赋既不源于《诗》,也不源于荀子《赋篇》。事实上,就文体独特的语言风格而论,汉赋更多接受了战国纵横家的游说辞风。章太炎《文学说例》即认为苏秦、张仪之纵横辞风与汉赋有着承继渊源,实为汉赋之先导:“纵横出自行人……秦、代、仪、轸之辞,所以异于《子虚》《大人》者,亦有韵无韵云尔。”〔54〕刘师培《论文杂记》亦有类似看法:“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行人之术,流为纵横家……西汉诗赋,其见于《汉志》者,如陆贾、严助之流,并以辩论见称,受命出使……是诗赋虽别为一略,不与纵横同科,而考作者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职……欲考诗赋之流别者,盖溯源于纵横家哉。”〔55〕《战国策》中记载颇多。《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56〕《秦策》此处描写秦国的地理形势,从四方反复叙写,其铺排夸饰的手法就极似汉大赋惯常的描写技巧了,类似的描写在《秦策·谓魏冉曰楚破秦》《秦策·范雎至秦》《秦策·顷襄王二十年》《齊策·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齐策·苏秦说齐闵王》《楚策·江乙说于安陵君》《楚策·苏秦为赵合纵说楚威王》《赵策·苏秦从燕之始合纵》《燕策·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中皆有体现。特别是《楚策·庄辛谓楚襄王》,其主客问答、文风与枚乘《七发》已极为相似。
4.赋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直接渊源得益于宋玉的写作实践和创新。《文选》载有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此四赋从文章形制结构以及饰言状物等写作手法方面,皆与汉代流行的汉大赋相同。赋之为独立的体制,学者们认同颇多。郭绍虞《<汉赋之史的研究>序》明确提出赋于诗、文外独立为一文体:“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无论从形式或性质方面视之,它总是文学中的两栖类。”〔57〕王力、褚斌杰、高光复、曹道衡等皆认同赋是一种特有的文学现象。费振刚也认为“战国时代与赋有关系的两个作家……一个是宋玉。”〔58〕《风赋》曰:“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59〕《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其结构布局与描写手法皆与《风赋》相同。宋玉赋文设主客问答,此正是汉赋承袭的写作手法,此写法与屈原的抒写心灵创作完全不同,而是设立一个简单的故事场景展开对某一事物的夸张性描摹,此为宋玉在屈原“屈辞”基础上的文学再创造,屈原与宋玉生活在同一时代,一前一后,宋玉对屈原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可见屈宋历来并称并不是虚言。宋玉要为楚王言说风有雄雌的不同种类之别,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情志,暗含喻世之意。“宋玉对曰”后面对风的具体描写与汉大赋中体物手法也一脉相承,只不过汉大赋更加铺张扬厉、更加细致周全,从而在篇幅上更加宏丽。由是可知,宋玉将其作以“赋”这一全新的文体名称命名正是借用上文所讨论的“赋”义在战国时代的普遍延伸义项“赋诗言志”,也就是《汉志》所谓“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实际场景,从而形成了战国末期楚国文坛上“屈辞宋赋”的双峰并峙局面,由屈原和宋玉开创的“辞”“赋”两种文体并行而下,泽荫中国文坛两千余年。
四、结语
我们探寻了“赋”义的历史演变,从最原始的赋税、贡赋之义逐渐衍化出铺陈政教的政治功能,再由铺陈之义引申为诵读、朗诵。《周礼》“六诗”之“赋”、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以及刘熙《释名》“敷布其义谓之赋”的论断皆是着眼于“赋”义铺陈政教的衍化义,但此与汉代文学体裁之汉赋尚有差异。王逸“赋,诵也”以及班固《汉志》“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论断皆是着眼于“赋”义诵读的引申义,但此与汉代文学范式之汉赋亦不可同日而语。
辞、赋并称自汉至今皆混乱异常,厘清并界定这两种不同文体,无疑可以真正洞察辞、赋两种文学体裁各自不同的表现手法以及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先有屈原大量抒写性灵的创作实践,虽然屈原并没有以“辞”命名自己的作品,但汉人司马迁、刘向、王逸等皆从理论上对屈原作品进行了总体概括,并借用屈原作品中常使用的“辞”来命名屈作以及后来的仿作。刘勰《辨骚》《诠赋》之分,萧统《文选》赋、骚分列,皆已清楚看到屈辞与汉赋的巨大差异。辞、赋分途,应为秦汉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费振刚《辞与赋》一文已有深入探讨。
楚辞本质是诗,汉赋总体为散文,文体自有不同。楚辞重在抒发内在情感,汉赋重在描写外在事物,一为内求于心,一为外摹于物,其表现手法甚有差异。辞、赋既有如此差别,在考察赋体渊源时,我们就不能张冠李戴,将产生辞体的来源比附于赋体之上。还原文本,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无疑将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可信的探求途径。若言汉赋源于《诗經》、荀子《赋篇》、《楚辞》,皆不能很好解释汉赋文本的独特个性。也有主张汉赋多源说以求全面折中之论的。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60〕万光治师《汉赋通论》认为四言赋“直承荀况《礼》、《知》等赋和《佹诗》”〔61〕,骚体赋“所祖述的,乃是屈原的楚辞体作品”〔62〕,散体赋是“随着南北文化交汇而崛起的一种综合性文体,它汲取了先秦各文体之所长”。〔63〕龚克昌《汉赋研究》一书《汉赋探源》详细探讨了汉赋的多种来源,认为汉赋来源于《诗经》、楚辞、倡优、纵横家等几个方面。〔64〕多源说顾及先秦文学多种样式,以继承而论,汉赋吸收了先秦多方面文学成就当毋庸置疑。但是,作为一种新型文体的出现,应有某种直接动因的促成以及天才作家的首倡其风。纵横家铺排的文风与汉赋铺张扬厉的繁富最有直接姻缘,当然,宋玉在屈辞之外的赋篇创制实为汉赋最为直接的文体源头,《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设主客问答的文学手法正为汉赋承袭的风神骨架。楚地同一时代的两大文学天才屈原和宋玉,一前一后,各擅辞、赋,形成双峰并峙,光耀古今。屈原以生花妙笔书写缠绵痴狂千回百转的内心愁烦怨曲,由此开中国心灵文学之先河,为后世各体文学所祖述,此为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之巅峰。宋玉于屈辞之外,辞、赋并作。他吸收纵横家言,另制新体,以人物情景对答的新颖手法如气贯长虹般携裹繁词富语织成宏丽文章,宋玉的赋作实践,正式确立了赋这一文体的形成,开汉赋繁荣之源。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
〔2〕〔48〕周振甫.文学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81,80.
〔3〕〔4〕〔5〕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31,129,266.
〔6〕尚书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6-153.
〔7〕〔8〕〔9〕〔10〕〔20〕〔21〕〔22〕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46-647,653,677-678,704,795-796,796,796.
〔11〕〔12〕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M〕.济南:齐鲁书社,2010:97,102.
〔13〕〔14〕〔28〕〔29〕〔30〕〔31〕〔32〕〔33〕〔34〕〔35〕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725,1822,1724,1788,1816,1840,1853,1905,1940,1956.
〔15〕春秋公羊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351.
〔16〕〔17〕春秋谷梁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388,2450.
〔18〕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473.
〔19〕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721.
〔23〕〔59〕萧统,编.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21,190-191.
〔24〕〔25〕〔26〕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68,568,568.
〔27〕刘熙.释名〔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99.
〔36〕〔47〕王逸.楚辞章句〔M〕.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213,49.
〔3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55-1756.
〔38〕汤洪.屈辞域外地名与外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16:8.
〔39〕〔40〕〔41〕〔42〕〔43〕〔4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86,2491,2492,2496,2999,3314.
〔45〕〔58〕费振刚.辞与赋〔J〕.文史知识,1984(12).
〔46〕班固.离骚序〔M〕//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50.
〔49〕王气中.艺概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255.
〔50〕简宗梧.汉赋史论〔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120-143.
〔51〕迟文浚,等.历代赋辞典〔K〕.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1216.
〔52〕徐宗文.试论古诗之流——赋〔J〕.安徽大学学报,1986(2).
〔53〕司马相如.上林赋〔M〕//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3016-3041.
〔54〕章太炎.文学说例〔M〕//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7.
〔55〕刘师培.论文杂记〔M〕.北平:朴社出版社,1928:121.
〔56〕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8.
〔57〕郭绍虞.序〔M〕//陶秋英.汉赋之史的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9:1.
〔60〕王重民.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16.
〔61〕〔62〕〔63〕万光治.汉赋通论〔M〕.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61,70-71,82.
〔64〕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196-213.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