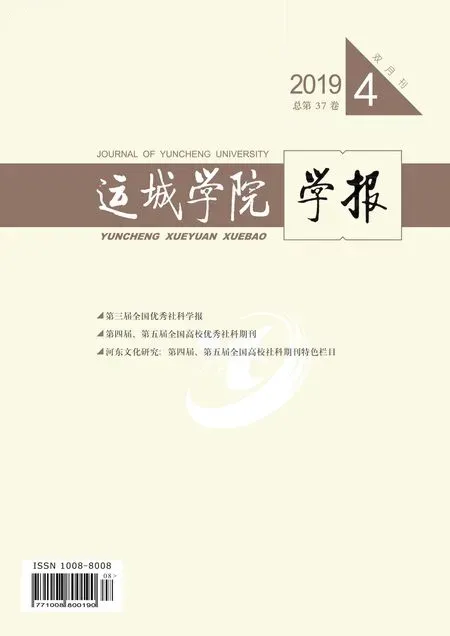严复中西学新格义论的思想内蕴
牛 秋 实
(玉林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格义”一词来源于梁慧皎《高僧传·竺法雅传》:“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1]152具体说来,就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外来]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习的中国[固有的]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外来]印度的学说[的一种方法]”[2]283-284。
中国文化经历了很多重大的变革:第一次重大的变革是佛教进入中国,中国自动地吸收佛学,以达至对于中国文化的融合和改造。第二次重大的变化乃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西学术的融合与汇通。对于第二次中国文化在强力入侵之下被动的吸收与改造,中国文化希望吸收西学以达到复兴的过程中,严译著作的地位和贡献,王国维在1904年所写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是最为中肯的评论:
“‘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3]
王国维把《天演论》比之汉末译出的《四十二章经》,就某一意义上来说是很富于启示意义的。他把在第二波中国文化的新变革中严复的地位与第一波文化融合外来佛教的意义相比。足见严复在新的文化变革中的启蒙家的地位。而在新的文化启蒙中,严复采用了类似中国儒学与佛学的格义之法进行中西文化新的格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
严复在中西文化的对比和比较中,常用这种格义法来阐述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先是从政治、法律入手,然后着眼于学术、宗教、民风,最后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夫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4]466通过格义之法,他总结中国与西国的最大区别:“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同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4]3
在对西学的格义中,严复内心不断遭受价值观的重创和重新弥合。在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过程中,赫胥黎对宇宙的仇恨深深地刺伤了严复的宗教观。从严复利用中学阐释西学的过程中,他不仅被佛教深深吸引,而且还被《老子》《庄子》的神秘核心“道”,甚至印度吠檀多不二论派所深深吸引。和李约瑟的看法不同,严复不认为道教的神秘核心与印度宗教的神秘核心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严复也不赞成批驳道教的神秘成分。道教、佛教、甚至宋明儒教中的神秘成份,在严复心中与斯宾塞的“不可知”微妙地结合起来了。正如《老子》或《易传》中的“万物”世界来自“无”或“玄之又玄”的“道”那样,斯宾塞的复杂的、异质的、有组织的世界来自“不可知”。斯宾塞坚持认为的终极实在不可知和人类推理或人类语言绝对不能说明终极实在,并不能削弱严复对于终极的信仰。从严复以中学对西学的格义中,“一方面,面向富强,面向力本论的信条、活力、维护自我权利、竞争和发挥全部的人类能力;而另一方面,仍然面向神秘主义,在神秘主义中为人生的痛苦寻找安慰,这种神秘主义竭力否认整个感觉到的世界及其全部成果的重要性,对于严复来说,整个进化过程背后的‘不可知’,也就是他躲避人生风暴的最重避难所。”[5]96也许,在严复面对中学和西学的紧张中,因为对中国未来的关注,使得他保持着或许经历西学的冲击和融合之后,中学能有忧虑之下存在的持久性和发展的想象空间。
在对斯宾塞的格义中,严复的理念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一开始对西方近代文明持赞美态度。用他对中国历史上黄金三代的格义之法的看法,“三代之治不过是一种虚构的宗教迷信”。对比之下,他认为西方近代文明称不上“郅治极盛”。不仅如此,他甚至认为近代西方不仅算不上“郅治极盛”,而且与之“相背而驰,去之滋远也”。[6]27
严复在《庄子评语》中有一段妙文,比较中西宗教之形象进行分析。他在《庄子·齐物论》“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一段上的批语是:“世人之说幽冥,宗教之言上帝,大抵皆随其成心而师之之说也。曰福善祸淫而不容,事偶尔赦罪宥眚;中国之想像,则衮冕而圭璋;西人之为容,则袒裸而傅翼。凡此者,皆随其成心以为之说。至其真实,则皆无据。”如此批判宗教,深入浅出。何谓“成心而师之”,他解释说:“言其术成于己,而与物不谋,故曰师心。”[4]1107人不是神创造的,而神的形象却是人根据自身形象而创造出的,然后又加以膜拜。道教早期不供奉神像,因为神是变幻无穷的,至高无上的,无从见到其真容,图画出来反而世俗化,但为了便于民众的祭拜以及有利于道教的传播,才借鉴佛教的做法,道教也供奉图像或塑像,宋代以后普遍流行。它的形象是身着帝王礼服,头戴前后悬垂珠串的长方形礼冠,手执玉杯环,正襟危坐,庄严肃穆。而西天天使的形象,则是稚态童男,坦胸露体,背负双翅,飘然欲飞。严复从心理起源上批判了宗教。[7]109
严复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体会到中国国民性质的优越性,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并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中国之国民性质,根源盛大,岂可厚诬。……其国民性质所受成于先圣先王数千年之陶溶渐渍者,有以为之基也。须知四万万黄人,要为天壤一大物,故其始动也,其为进必缓,至于成行,乃不可御。”[4]324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久常新,为人类历史所罕见,乃炎黄子孙的骄傲,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成为奠固酋邦的巨大力量。对此,严复结合国命之兴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且吾民治智德力,经四千年之治化,虽至今日,其短日彰,不可为讳。顾使深而求之,其中实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随摧斫而不可灭者。夫其众如此,其地势如此,其民财又如此,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陈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4]933-934“储能”一词乃严复在译述中通过格义之法所创造,意即深藏的无穷力量。这个结论是在格义中西学术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和体会,反映了严复高度的爱国主义及对中国民族未来的坚定信心,他预言二十世纪以后,中国将与美国并驾齐驱于国际舞台,“故二十稘以往,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4]894
二
正因为接受了西方的知识系统,他才始终强调中国古书中隐藏的道理必须通过现代西学才能得以证明。我们不能把责任推到他的头上。但在清末而言,这正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贡献。为什么他评点的《老子》会得到夏曾佑、陈三立等人那样击节称赏呢?那当然是因为他的“评点”处处用西方的哲学、历史、宗教,甚至科学来阐明《老子》的现代意义。[8]117例如严复在《天演论》之导演十三中说:“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盖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严复用中学中之说法进行了一番格义,“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吾窃谓此语,必古先哲人所已发,孟坚之识,尚未足以与此也。”[9]39
晚清对西学的格义是知识分子的常态,但围绕着中学与西学之间衡量短长,各自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梁启超是晚清的知识大家,曾著有《西学书目表》阐述读西学的心得。严复就曾批评梁启超对中学和西学书籍的读法有许多附会的地方。他批评梁启超主张民主是西洋固有的东西。这种议论方法与他对言语的观念以及对翻译的观念,即表面上看去虽是类似的词语,其中各蕴藏着不同文化所固有的世界观。
文化的本质实际上在历史的进化中就已经决定了,这是严复对比中西历史所做出的结论。“共产党人以帝国主义的出现为理由解释了这个问题。他们说,要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禁锢了中国的进化力,中国早就通过历史进化的正常阶段了。严复不是这样来解释的,他哀叹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生存竞争导致的正常结果,中国无能力参与这一竞争,必须根据它自己作为一个有机体是衰败和虚弱的才能得到解释。在道德判断方面,他不愿接受西方的浮士德力本论。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为何迄今不适应生存竞争?‘哉!吾中国之社会也。’这是他的《社会通铨》译者序的开篇第一句。”[5]164严复的独特识见使得他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看法觉得非常肤浅。
虽然,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民主政治的地步,但它毕竟具有强大的邦联国家的许多因素。所以严复对满清新政抱有强烈的希望。他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才能强盛。
严复的希望都寄托在晚清新政的努力上。严复认为革命并不是中国的出路。严复认为中国当时首先需要的是建成强大的“军事”国家,所有的公民在“军事”国家里将只为国尽忠。但满足本身的某些蒙昧主义因素和某些革命者的煽动,却为复活一种分裂倒退的部族思想积俗铺平了道路。[5]169
三
不能把严复的思想截然地划分为“中国传统”和“近代西方”两种话语系统。因为在他译著的《穆勒名学》中严复已经兼容穆勒与老子思想的痕迹。事实上,严复为《老子》作评语,并不意味着严复对这些年里构成自己哲学的基本前提有所偏离。如果说严复为赫胥黎、穆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所加的按语里包含着对老庄的赞美,那么《老子》所作的评语毫不含糊地证实了严复完全信奉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思想。
事实上,正是由于严复对老子学说的热情,促使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决定翻译达尔文、孟德斯鸠和斯宾塞的著作。严复最初的动机是要通过“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以拯救敏子字还敢,即面对他本人以为的近代西方思想的话语优势,来拯救他自己和国人的自豪感。他在老子中找到了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老子历来是反对儒教的。
在严复看来,中国思想的核心都在于老子的思想。因为老子思想是中国思想永恒的基础。他用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来支持穆勒的逻辑学。老子的“小国寡民”不正是孟德斯鸠的城邦式民主吗?
在严复看来,老庄最富特色的道教思想,正是对整个人类事业的抛弃,而且首先抛弃的可以说正是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严复在评语中说:“老子哲学与近世哲学异道所在,不可不留意也。今夫质之趋文,纯之入杂,由乾坤而驯至于未济,亦自然之势也。老子还淳返朴之义,独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质而强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文而返之使质,老氏之术非也。何则?虽前后二者之为术不同,而违其自然,拂道纪,则一而已矣。故今日之始,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不可期而至。”老子不愿意相信人类的能力可以通过自然选择的严峻考验,他更向往宁静的“母亲”,这种想象几乎使人想起弗洛伊德的退回到子宫的说法。[10]190
严复的翻译是一种全新的格义之法,他熟练地将中学与西学熔为一炉,带有典型的严译著作的本质特点。
对于西学中对中学隔靴搔痒式的评论,严复往往不以为然。例如晚清盛行一时的环境决定论,如在中国,南北诸省的勤惰情况恰与孟德斯鸠的看法“若相反者”。至于孟德斯鸠诬称中国的天时地利使其商民欺妄饰伪之俗“为大地诸种之尤”,严复愤然痛斥其说乃妄言而“非笃论”。他指出:中国的天时地利适中而至美,中国的商民“信义卓著,白敫然不欺”。往往在他国契约券符所为之而不足者,在中国则“片言相诺而有余”。[10]403他也承认中国之民确实存在“各恤其己私”的缺点,但不能归咎于天时地利,实乃“控制教化使然,于天地无可归狱也”。可见,严复在这里所论,已不仅仅是学理的探讨,多少羼入了些民族感情。不过严复的学问便得到了吴汝纶的击节赞赏。
吴汝纶是晚清声望最高的桐城派古文大家,他说《天演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这才会引起不知西学为何物的士大夫竞读其书。严译畅行不仅得力于他对英语的熟练掌握,更在于他采用格义之法,又熟练地掌握了桐城派古文,所以在两种渊雅的语言之间游刃有余。当时读者胡适的话最可作证:
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
胡适的取名便来自于“适者生存”。胡适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学界对严译著作的崇拜程度。
严复认为,“群学之难,因时而见者,彼以世运为天开,而风会为成于名世。又谓天常生一代之才,以主一时之世局,得之者治,失之斯衰,问天下之治否,观君相之所为。自彼言之,无所谓天演者矣。独其人于格物既明之后,生学深造之余,知两间所呈,皆因果相生,无偶然忽至之一境,则知群者有生之大物,其形体性情,官神消息,一切皆演于自然。常始于至微,终至至巨。故考一时之政制风俗,必上溯千载,下观百世,而后能得其真。则知时之于群,为义大矣。”[9]192
“群学”即西方的社会学,严复以中国之熟语译著西方艰深之社会学著作。通过研究严复的格义著作,在中国文化领域里严复最为信奉的,可能依然是老庄的神秘主义特性。1916年底,他在给弟子熊纯如的信中说《庄子》甚至比《老子》更明确地论证了万物世界里的相对性、短暂性。也许在严复的世界中,中国的富强则是他更为关注的。
当年严复将科举的废除的意义强调得十分重要。与废除科举密切相关的是一批趋新之人“去经典化”的努力。但是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说,严复以新格义之法来沟通中学和西学,其经典的意义必不能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