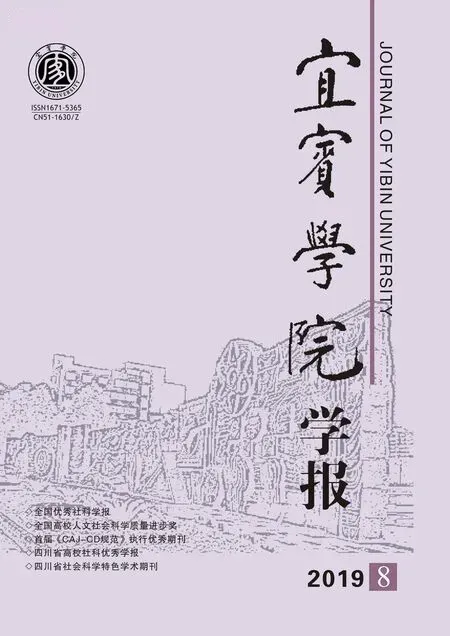钱穆与唐君毅
陈 勇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在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之际,一些学人离开大陆,南走香港,在“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上兴学育才,弘扬中国文化。在这一批南来学人中,钱穆、唐君毅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本文主要叙述钱、唐二人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期的交往及其文化理想。
一、 创办新亚书院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17岁考入北京大学,对梁漱溟执弟子礼。19岁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师从方东美、宗白华、熊十力等人。抗战时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出版有《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年)、《人生之体验》(1944年)等著作,在哲学界已崭露头角。贺麟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对唐氏“富于诗意”的唯心论哲学有极高的评价,称其著作“为中国唯心论哲学的发展,增加了一股新力量”。[1]49
抗战时期,钱穆与唐君毅虽然都在西南后方,但似乎没有什么交往。从现有的材料看,两人的直接交往始于他们任教无锡江南大学之时。
江南大学在无锡太湖之滨,是无锡巨商荣家斥资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唐君毅与好友牟宗三、许思园同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牟、许二人系由唐推荐而来。1947年秋,中大哲学系人事纠纷日趋激烈,系内要解除牟、许两位的教授职务,出于对朋友道义上的支持,唐与牟、许二人共进退,应江南大学之聘任教授,兼任学校教务长。此时钱穆也应江大之聘,任文学院院长。大约这年年底,钱穆正式到校任职,这是钱、唐二人论交之始。
钱成名在唐之前,在二人论交之时,唐在学界名声已著,两人同为江大的中坚力量,交往较密,多次同游太湖,荡漾湖中,畅谈学术。钱穆当时撰有《湖上闲思录》一书,唐君毅也写成了《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著作。1948年夏,唐君毅应好友程兆熊的邀请,到信江农学院讲学。该学校设在江西铅山鹅湖书院内,是当年朱陆讲学聚会之地,历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就发生在这里。程氏有意恢复鹅湖书院,让唐君毅来筹备此事。唐君毅对程氏的想法深表赞同。早在抗战期间,唐君毅就认识到书院教育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办学方式,故与程氏相约,先由农院附设鹅湖书院,然后逐渐改为由鹅湖书院附设农院,致力于书院的恢复工作。两人的想法也得到了钱穆的大力支持。钱氏认为中国现代的教育制度深受欧美的影响太支离破碎,他向往宋明以来的书院制度,以及书院制度下的人格教育,所以他极力支持程、唐二人的做法,希望将来再来一个新的“鹅湖之会”,不料由于时局的变化太快,这一愿望终成泡影。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形势急转直下。钱穆在给唐君毅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对时局的看法,流露出焦虑不安的心情。2月,钱穆收到了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的一封信,邀请他和唐君毅赴广州讲学,为期3月。王淑陶是唐君毅旧友,于是钱赴唐处商量南下之事。经过反复商量、考虑之后,两人决定联袂南下。
4月4日,钱穆与唐君毅一道乘火车由无锡前往上海,7日乘金刚轮赴粤,11日到达广州,受聘于华侨大学。华侨大学创办于香港,后来迁到广州。钱、唐二人在广州停留近二月,在此期间,他们见到了张其昀、熊十力、杨树达、陈寅恪等南来学人,同时通过政界出身的徐复观接触了不少国民党党政要人。①1949年6月,因时局动荡,华侨大学迁回香港,校址设在沙田大围铜锣湾。钱、唐二人于6月7日夜乘船抵港。入港后,钱穆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入港之前,他在广州街头遇见了老友张其昀,张氏从杭州来,告诉钱穆,拟去香港办一学校,暂定名为“亚洲文法学院”,以研究文法两科学术,培养具有通识而擅专长的人才为宗旨,已约谢幼伟、崔书琴等三人,亦邀请钱氏加入。钱穆接受了邀请,与已抵达香港的谢幼伟、崔书琴共同筹办学校。在筹办过程中,张其昀得蒋介石电召赴台,发起人之一吴文晖中途退出,谢幼伟应印尼某报馆之聘任总主笔离去,崔书琴因是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随时准备入台,因此,几位发起人实际上只剩下了钱穆一人。由于人少力薄,孤掌难鸣,钱穆邀请与自己同来香港的唐君毅和《民主评论》的主编、经济学家张丕介两人一道参与学校的筹建。10月10日,亚洲文商学院在香港九龙佐顿道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楼上举行开学典礼,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教师有唐君毅、张丕介、罗梦珊、程兆熊等人。亚洲文商学院存在了约半年时间,1950年3月,学校得到来自上海的建筑商人王岳峰的资助,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租得三间教室,作为新校舍,正式改名为新亚书院,由钱穆任校长,唐君毅任教务长,张丕介任总务长。
余英时在一篇谈新亚书院创办的文章中说:“1949年新亚书院的创建是历史的偶然,但同时也涵蕴了一种潜在的必然。所谓历史的偶然是指当时创校人物志同道合,而恰好在乱离流浪之中同时凑泊在香港,再加上种种人事因缘的巧合,因此才有亚洲文商学院——新亚前身——的成立。”[2]唐君毅也多次讲新亚书院的创办是一个“偶然的无中生有”,这一批来自天南地北、最初并不彼此相识的学人,“只因中国政治上之一大变局,偶然同聚在香港,遂有此新亚书院的创办。”所谓偶然中蕴含着潜在的必然,是指这一批南来的学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担当意识,他们原本在大陆从事教育工作,素有承传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宏愿,他们来到了这块“近百年来既属中国而又不算中国的土地”,以香港作为保存、传播和复兴中国文化的基地,希望能把中国文化在这块殖民地上灵根自植。诚如钱穆在给老师吕思勉的信中所言,他要效仿明末朱舜水流遇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之举,“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事实上,新亚创办人心目中“新亚”一词即“新亚洲”之意,即“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唐君毅曾言:
树立“绩效”观念,以预算执行效果和效率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既强调绩效目标订立的效率,也强调绩效成果考核的效果,创建既强调“过程”又重视“结果”的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思想和组织文化。在此基础上将总体战略目标细化分解成部门/项目战略目标,根据目标要求对预算执行各环节的工作设定量化指标和权重系数,在此基础上编制“项目工作战略计划”和“部门工作战略计划”,充分考虑完成目标所需要的程序、技术、人力资源、资金、信息等各类资源,以及完成这些目标的潜在风险和阻碍因素,确定绩效预算的程序、目标、主体、内容和方法,设计预算绩效考评制度的框架体系。
“新亚”二字即新亚洲……亚洲是世界最大的一洲,他比欧洲有更古老的文化。有古老至四五千年之绵续不断之中国与印度,同时是世界最伟大之宗教——耶、回、婆罗门、佛等——之策源地,他在人类文化史中,原远较欧洲居于更前进的地位。然而此二三百年来,他却成为欧洲最大的殖民地之所在……此二三百年亚洲的地位之降落,亚洲人应负责任。中国之百年来之积弱,中国人应负责任。古老的亚洲,古老的中国,必须新生。我们相信只有当最古老的亚洲、最古老的中国获得新生,中国得救,亚洲得救,而后世界人类才真能得救。[3]407-408
在新亚书院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钱穆与唐君毅等创办人同甘共苦,情谊笃深。当时,钱穆主持校政,并兼任文史系主任、新亚研究所所长,讲授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为筹集经费时常奔波于香港与台湾之间。唐君毅主持哲学系,并兼任教务长,讲授哲学概论等课程,彼此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以人文理想精神自励并感染同仁和学生,为学校的发展殚精竭虑。钱穆称“同事间真志同道合者,实亦惟君毅一人而已。”[4]352这是两人在新亚共事时情谊深厚的真实写照。
在授课之余,钱、唐诸人还结伴出游,或散步石澳海边,或游西林寺,或漫步太平山顶。当年与他们同游的徐复观在《太平山上的漫步漫想》中有如下这样一段回忆:
当时经常走在一起的有钱宾四、张丕介和唐君毅诸位先生。钱先生当时是五十多岁,我和张先生是四十多岁,唐先生大概刚挂上四十的边缘。钱先生一向是游兴很高,而且是善于谈天的人;他谈的是半学术、半生活,偶而也掺杂一点感慨和笑话,真是使人听来娓娓不倦。唐先生一开口便有哲学气味,我和丕介当时对学问有虔诚的谦虚,对钱、唐两位先生,是由衷的钦佩,所以对唐先生的哲学漫谈,也听得津津有味。[5]192
居港办学时期,钱、唐二人也笔耕不辍。钱穆的著述主要转向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研究和阐释,出版有《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民族与文化》等10余部著作,唐君毅则由1940年代对人生哲学的研究转向对中国人文精神的探寻,写有《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等重要著作。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唐君毅对钱穆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成果多有采撷、吸收。
1954年7月30日(农历六月初九),是钱穆60寿辰,新亚书院和《民主评论》《人生》杂志联合出版祝寿专辑,以表彰钱穆在学术和教育上的贡献,唐君毅不仅表示支持,还专门写下《钱宾四先生还历纪念》一文,称“钱先生最初为学是治古文辞,后乃及于中国学术之各方面。钱先生之知名于中国学术界,在其早年有《刘向歆父子年谱》与《先秦诸子系年》二书。其著作最重要之阶段,为其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国史大纲》之一时期。钱先生只身来港后,其时之著作则尤重于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文化灵魂所在之学术思想之说明。中国之社会政治问题解决,不能袭取他人已成之方案,而同时注意及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融通等问题,承认中国未来之文化当另有一新面目。斯其胸量之所及,又非其旧作之所能限者矣。”文章最后一段阐述了纪念钱氏六十寿辰的意义,读来更是意味深长:
要而言之,六十年之中国迄在内忧外患之中,而钱先生一生之学问,实与时代之忧患,如比辞而俱行。六十年之中国,亦产生不少的学人。然时代之变太快了,我们看,多少老师宿儒,其治学只承清学之遗风,而不能再进一步。多少新进留学生,只是取西方之一家一派之学说之长来评论整个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问题;又多少中国夙擅辞章之士,竟甘心于入日本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又多少学人治学,除了满足个人之学问兴趣外,竟忘了他自己是在自古未有之忧患时代的中国人,忘了他之治学与著述,直接间接,皆当对时代有所负责;又多少人真知道所谓对时代负责,并非只是随时代风势转,而只是先承担时代的问题,乃退而求在学术上卓然足以自立,而有以矫正时代风势之偏弊!我们从这些问题上想,只使我们生无穷的慨叹。诚然,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我们亦绝无悲观之理。但是由这些问题,却更使我们现在不能不纪念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三十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之钱先生。此固非只为一人祝寿之意而已。[6]
二、 新亚文化讲座与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迁入桂林街后,来访的学人增多,限于学校规模和经费,无法一一聘请,在钱穆、唐君毅的倡议下,学校面向社会开办学术文化讲座,邀请在港的文化名流和著名学者主讲。新亚文化讲座每周末晚上7至9时在桂林街校舍的四楼大教室举行,可容纳百人左右。每至周末,无论是寒暑风雨,校外来听者常常满座,留宿校内的新亚学生只好环立于旁,挤立墙角而听。讲座由唐君毅具体负责实施。钱穆在《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序》中说:
新亚书院之始创,艰窘达于极度,同人心力无所展布,乃于日常授课之余,周末之夜,特设文化讲座。除同人主讲外,并邀在港学者参加,以社会人士为听讲对象,而新亚学生亦参列焉。其时,新亚校舍在桂林街,隘巷秽濁,楼梯窄而黝,盘旋而上,每不得踏足处,讲室设座,无凭无靠,危坐不能容百席,而寒暑风雨,听者常满,新亚学生仅能环立于旁,并有每讲必至,历数年不缺席者……唐君毅先生长新亚教务,始终主其事,匪唐先生不能有此讲座。[7]3-4
新亚文化学术讲座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5年初止,举办139次,共讲122个专题,内容遍及新旧文学、中西哲学、史学、经学、宗教思想、中国传统艺术、绘画、诗歌、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中钱穆主讲“中国史学之精神”“孔子与春秋”“老庄与易庸”“孔孟与程朱”“王阳明学派流变”等21次,唐君毅主讲“儒家精神在思想界之地位”“人文主义的发展”“康德哲学精神”“辩证法之类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等16次,成为讲座的核心力量。唐君毅在谈到开办讲座的宗旨时言:
忆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始办,即蒙社会人士之赞助。初意并非纯为学院式之讲会,而在启迪听众对对中国文化问题、世界学术之一般认识,及人类前途之关心。于四五年中,凡举行百三十九次,所讲内容,虽颇涉及专门学术,然始终不同于学院式之论文报告……就诸讲题之范围之广,与讲者包括儒、佛、耶、回诸教人士、及各专门之学者而论,则可见当时诸参加讲会之人士,其目光所注,意趣所存,乃在人类文化之全面。[7]5
讲座后经孙鼎宸整理,形成《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一书。孙氏在回顾整理此书的过程时说:
笔者在乱离中,深受此讲座之教益,得略识中国文化之特质与中西文化交流之重要,而新亚精神之感召,更启迪余治学之兴趣。文山有路,学海无涯,遂视讲座为传习学术文化之灯塔。当是时香港英国文化委员会、青年会、孔圣堂、学海书楼各处,亦有学术讲座之事,但多未能按期举行,只有新亚文化讲座,四年来,除寒暑假期外,每星期日晚,一贯的均如期举行,济济多士,相聚一堂,当时讲学风范,真是令人神往。[8]
钱、唐二人“全幅精神,注于新亚”,共同确立和奠定了新亚的文化理想和教育理想,这种文化教育理想后来被概括成为“新亚精神”,即在忧患时代中建立起来的为中国文化续命的担当精神。曾做过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在纪念新亚创校三十周年时曾声情并茂这样一番演讲:
新亚不是一间普通的学校,她是一间有崇高的教育理想与文化意识的学 府。新亚是由一批具有忧患意识的“流亡”学人,在忧患的时代中建立起来的。忧患意识不止是由当时风雨交集的困乏而来,而毋宁是由一种要对中国和人类文化加以承载的责任感而来……当年新亚的创办人钱宾四、唐君毅和张丕介诸先生,以及社会上先进如王岳峰、赵冰先生等,凭着一股豪迈沉毅的心情,一种为文化学术不计劳困和钱财的决心,冲决种种困难,卒于在香港这个殖民地树立了一个以宋代书院为格局之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形象。由于新亚先驱者的艰卓努力,新亚的教育理想终于渐在香港形成气候,并且受到海内外友人和团体,如雅礼协会等的重视和支持。事实上,新亚成长的历史,就是她的理想越来越受到更多人欣赏接受的历史。[9]166-167
这里所说的“新亚的理想”,实际上是指创办人钱、唐诸人承继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的创校宗旨。徐复观曾撰文称新亚是靠钱穆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的理想,张丕介先生的顽强精神而支持的,他们有一个讲学的理想,有一个对中国现状,从文化上加以反省的自觉,有一个要使中国文化从三百年的冤屈中获得它正常地位的悲愿,才能有新亚书院的出现。“可以这样断定,香港之有一点中国文化气氛,有少数中国人愿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做中国学问,是从新亚书院开始的。”[10]21确如徐氏所言,新亚书院创办人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海外的志业宏愿在后来得到了实现,向为商业社会、文化空气淡薄而被人们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经过钱穆、唐君毅这一批南来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变成了一个弘扬儒学、传承中国文化的重镇,新亚书院成了港台新儒家的大本营和发源地。
三、 分歧与疏离
作为新亚书院的院长,钱穆无疑是学校最具有号召性的人物,是新亚的核心力量。当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新进人员日渐增多,办学条件不断改善之时,也出现了对钱穆的不满之声。唐君毅出面说道:“不是钱先生的大名,便没有新亚书院,所以大家还是要维护他。”[11]176唐氏之言,既维护了新亚的团结,同时也表达了对老友的信任和尊敬。
当然,钱、唐二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分歧。这种分歧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表现得愈来愈明显。比如,在对待儒家思想,尤其是对《中庸》《易传》的理解上,两人就有不同的看法。钱穆不赞同纯粹从心性之学的立场去诠释《中庸》,主张把儒学置放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互为竞流,多元并立的思想情境中去分析,其对《中庸》所进行的“天人合一”之宇宙论的诠释建构,是以道家进路显出其对儒家思想补偏的一面。他在致徐复观的信中说,“弟宗主在孟子、阳明,然信阳明而知重朱子,尊孟子而又爱庄周”,因为“晦庵(朱熹)可以救王学之弊,庄子可以补孟子之偏”,认为《中庸》《易传》即“采用庄老来补孔孟之偏”。[4]354所以他撰《中庸新义》一文,即以《庄子》来解释《中庸》。在《中庸》的成书年代问题上,唐君毅持论与钱穆大体相近,认为“其成书极可能在孟荀后”,但不同于钱穆以文献考证为立基的进路,在论证《中庸》晚出的问题上,唐君毅选择是义理阐释的路径。钱穆是以道家自然的宇宙论去立论,是史学家“通天人之际”的讲法,结合具体考证理据去讲。而唐君毅是基于儒家心性内在超越的道德本体之“心”,直承理学上的心性义理概念求其思想内涵之发挥。[12]他在致徐复观的信中说,“钱先生之思想自其《三百年学术史》看便知其素同情即情欲即性理一路之清人之思想,此对彼影响至深。彼喜自然主义、喜进化论、行为主义。由以此论德性,亦一向如此。彼有历史慧解,生活上喜道家,故在历史上善观变。但其思想实自来不是《孟子》《中庸》至宋明理学之心学道学一路……今其论中庸文释‘诚’与‘不睹不闻’,都从外面看,此确违《中庸》意。”[13]98
再如,1958年元旦,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的长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以下简称《宣言》)。这篇洋洋洒洒4万字的长文,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生命、伦理道德、宗教精神、心性之学、科学民主、中国历史文化长久的原因及其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港台新儒家思想的总纲,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不少学者视为海外新儒学形成的标志。《宣言》初稿由唐君毅起草,在发表时邀请钱穆同署,钱以签发《宣言》容易成为有形的学术壁垒,形成“门户”偏见,不利于学术的发展而加以婉拒。他在致学生余英时的信中说:“年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联名作《中国文化宣言书》,要穆联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张君,此函曾刊载香港之《再生》。穆向不喜此等作法,恐在学术界引起无谓之壁垒。”[4]414-415钱穆拒署《宣言》,表明港台新儒家内部在复兴儒学的路径上存在着重大分歧。1950年代后期,钱穆与第二代新儒家的关系由密转疏,是导致他拒签《宣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拒签《宣言》之举又使彼此间感情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自《宣言》发表后,钱穆与第二代新儒家唐、徐、牟诸人关系渐行渐远,乃至最终分道扬镳,这对于港台新儒学复兴运动而言,当是一件憾事。
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处理上,钱、唐二人也存在着分歧。比如,在新亚书院是否加入中文大学的问题上,钱穆力主加入中大,使学生的毕业资格能得到香港政府的承认。唐君毅在这一问题上则有所保留。他在《新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讲辞中说:“照我的意见,如今日之新亚尚未加入中文大学,我亦可以赞成不加入;但今已加入再退出,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多困难的。不退出,当然有所获得,亦必有所牺牲。”[9]164-165
事实上,在新亚加入中大之前,钱、唐二人已经意识到新亚先前的许多办学理念会因加入而受损,其文化理想不容易得到维持。所以当新亚加入中大后,二人力主推行联邦制,以保持新亚书院的办学特色和固有风格。
1964年7月,钱穆在办学理念上与中文大学当局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愤而辞院长之职。辞职后的钱穆又未能回到他亲手创办的新亚研究所,只得闲居沙田,于是钱、唐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1966年11月17日,钱穆在致学生的信中说:“新亚研究所×、×两君竞欲作大师,竞相拉拢研究生,必欲出其门下为快。故以前所中诸生亦相戒不敢来沙田。怪事如此,聊以相闻。穆亦籍此杜门,惟目睹青年有为之士,如此窒塞其前进之途,则于心不能无憾耳。”[4]4501967年钱穆离港赴台定居前,唐君毅曾与他见面二次,“晤面时初几无话可谈”。[13]155从“同事间真志同道合者,实亦惟君毅一人而已”,到“晤面时初几无话可谈”,钱、唐间过去那种患难相共、亲密无间的关系至此不复存在。唐君毅曾在致友人书信中言道:“以超越眼光看彼(指钱)在此十七年之所为,与弟等在此十七年之所为,皆是一悲剧也。”[13]155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推行行政改制,以中央统筹的集权制取代过去的联邦制,违背了新亚书院加入的初衷。唐君毅承认从经济的立场着眼,“似乎统一为一大学更经济”,但他的根本立场与中文大学当局和改制工作小组的意见又截然不同。当年6月17日,唐君毅在“新亚道别会”的演讲中沉痛地指出:
我认为中文大学三间学院之联邦制度,必须真正维持,不容破坏。此乃依三院之教育原各有其特色,如崇基学院是基督教大学,着重宗教性的教育,并透过教会,而有更多之国际性的关系。联合书院办了许多适合地方需要的学系,如公共行政系和电脑系。新亚书院自开办以来,就是求多继承一些中国大陆文化的传统而更求发展。这三院各有特色之事实,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中大学院之间各有特色,便必需肯定联合制度,以便各保持其特色……如果中文大学的联邦制度不能保持,我们的新亚精神不能保持,或大家只知有国际与香港,而不知有中国,则我们将连此痛苦亦不能有,而我们的生命只有化为麻木无生命的国际游魂,或单纯的香港顺民。这才真正成了一绝对的痛苦。[9]162-164
为了维护“中国人的立场”,维护新亚书院的创校精神和文化理想,唐君毅奋起抗争,与中文大学当局的矛盾激化。当年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唐君毅等人同意新亚加入中大,实以各书院在行政教学上各自独立、推行联邦制为联合组建的基础。而中文大学改制的结果是以集权制取代联合制,这恐怕是他们所无法认同的。尽管这时的钱穆早已离开香港,抗议改制的主角已是唐君毅。为了争取更多的新亚学人的理解和支持,唐君毅也曾去台北素书楼拜访钱穆,在唐氏的《日记》中,不乏上午参加中大改制会议,下午离港赴台,第二天去素书楼拜访钱穆的记载。唐君毅去台北拜见钱穆,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去叙旧,而是争取仍为新亚校董钱穆的支持。然而唐君毅等少数新亚学人的抗争毕竟势单力薄,无力扭转中文大学当局的决定而陷入困窘。正如徐复观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新亚是靠钱穆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的理想,张丕介先生的顽强精神而支撑着。如今钱先生撤走了,张先生去世了,唐先生陷于孤军奋斗,更为吃力了。”
1974年,唐君毅怀着极不愉快、极不甘心的心情从中文大学退休。1976年12月22日,香港立法局三读通过“新富尔敦报告书”,一元化的集权制取代了过去联邦制的大学组合制度,新亚书院九位坚持创校精神的校董(李祖法、沈亦珍、吴俊升、刘汉栋、郭正达、钱宾四、唐君毅、徐季良、任国荣)在唐君毅的带领下集体辞职以示抗议,成为香港高等教育史上最具震撼性的学术冲突。②“辞职声明”称:“联合制终被废弃,改为单一集权制……同人等过去惨淡经营新亚书院以及参加创设与发展中文大学所抱之教育理想无法实现……是非功罪,并以诉诸香港之社会良知与将来之历史评判”。[14]唐君毅在致《明报》月刊的信中直斥香港政府“背信食言”,“香港政府先以联合制度之名义,邀约新亚崇基参加中文大学之创办,而终于背信食言,改为实际上之统一制,是犯了道德上的罪过。”[15]其沉痛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当年钱穆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辞去新亚书院院长之时,曾亲眼目睹书院在困苦中诞生、在忧患中成长的徐复观写下一篇《悼念新亚书院》的文章,称“香港中文大学的成立,可能不是新亚书院的发展,而实际上是新亚书院的没落;钱穆先生的辞职,正是此一没落的象征。新亚书院之所以为新亚书院,有它创立时的一段精神。这一段精神没落了,新亚书院实质上便等于不存在了。”[11]176在新亚创办人唐君毅等人看来,联邦制的取消就意味着新亚的死亡,任何形式的改变都是对原来新亚精神的背叛。而在改制的主持者,唐君毅、钱穆的学生余英时等人看来,新亚加入中大,以及由书院制而联邦制而集权制,并不意味着“新亚精神”的丧失,恰恰相反,是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和更新,新亚“硬体”的每一步发展也就是新亚原始精神“软件”的每一次“变异”(或“异化”),而这种“变异”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必然,中大改制不过是使新亚维护中国文化的理想和精神转换了一种形式而已。诚如余氏在《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所言:“新亚精神只是更新了,但没有消失;新亚的原始宗旨也只是扩大了,而没有变质。”[2]
结语
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新亚书院从原来的私立专上学院,变为附属公立大学的成员书院,已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教育机构,其自主空间较以前大大减少。新亚初创时期的精神和办学宗旨在大学制度下渐渐消失,这是当年钱穆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早期的新亚书院近于宋明书院,宋明书院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大学则是从西方文化系统中移植过来的。早期的新亚书院的确发挥了宋明书院的长处,创办人钱穆、唐君毅诸人对学生而言同时发挥了“经师”而兼“人师”的作用。但是新亚并入中大,由过去传统的宋明书院式学校逐渐转变为“现代大学”时,原始的新亚精神在新的条件下必然会慢慢减弱,书院的文化理想与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冲突也就愈趋激烈,中大改制风波就是显例。现代大学的架构来自西方,它是否可涵摄传统书院所孕育的基本精神?传统书院如何与来自西方的现代大学制度相融合,在转变为现代大学时如何保留传统书院自身的特征和人文理想,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的确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注释:
① 据《唐君毅日记》载,1949年4月28日:“徐复观请吃饭,与钱先生同入城,晤见国民党中上级人物数人”。5月15日:“今日星期。阎锡山及国民党等要人来一帖,约我与钱先生入城茶会,看见三党人不少,然气象罕足观者。”《唐君毅先生全集》卷27《日记》(上),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31、32页。
② 在目前已公布的文本材料中,均是言新亚九位校董集体辞职,这自然包括钱穆在内。中大改制工作小组主席余英时也持相同意见,他在《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在新亚书院发展的历程中“有几个清楚的记里碑,1954年雅礼援助是第一个,1963年中文大学的成立是第二个,1973年新亚迁入中文大学现址是第三个,1977年中文大学改制完成,包括钱、唐两先生在内的新亚旧董事集体辞职,则是最后一个。”但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后来透露内情,当年九位校董发表辞职声明一事,钱先生事先并不知道,也未在辞职文件上签名。此又为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