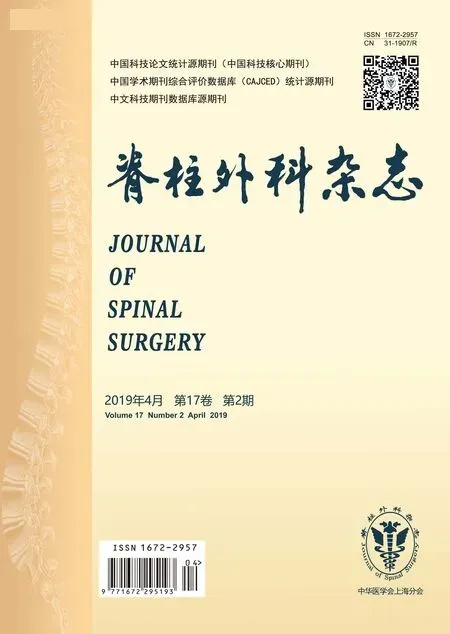强直性脊柱炎合并脊柱骨折的手术治疗研究进展
刘 齐,阎崇楠,王 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脊柱外科,沈阳 110004
强直性脊柱炎(AS)是一种常见的累及中轴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固有的病理特征导致骨质疏松和脊柱生物力学性能下降,使脊柱逐渐硬化、出现后凸畸形,影响脊柱整体的平衡和灵活性,晚期脊柱多节段融合后像一个长臂杠杆,轻微外力即可导致脊柱骨折和神经损伤[1],这也使得AS合并脊柱骨折患者的治疗与其他骨折不尽相同。由于骨质疏松和脊柱融合,AS患者椎体骨折发生率高出健康人群4倍[2],且多为经椎间隙的三柱骨折,同时至少10%的患者存在多处骨折[3-4];骨折好发于相对固定的胸腰椎和活动度较大的颈椎,最常出现在C6,7[5];此类患者出现神经损伤的概率是健康人群的11倍[6-7],且81%最初神经功能正常的患者会出现继发性神经损伤[6]。AS合并脊柱骨折患者死亡率高达6.6%[3]。对于AS合并脊柱骨折,由于早期条件有限和认识不足,临床上多主张非手术治疗;但不稳定的AS合并脊柱骨折,非手术治疗常出现骨折不愈合和继发性神经损伤,且长时间卧床易引起褥疮、坠积性肺炎和静脉血栓等并发症[8-9]。近年报道显示,AS合并脊柱骨折手术治疗在稳定脊柱、改善神经功能等方面较非手术治疗优势明显[4],对于不稳定的AS合并脊柱骨折、合并脊髓损伤、存在骨块或血肿等造成神经压迫且可以耐受手术的患者,均建议手术治疗。手术可使脊柱获得及时稳定,改善脊髓损伤节段的外环境,促进残存脊髓功能的恢复,还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继发性脊髓损伤,为早期离床活动和康复训练提供保障。本文就近年AS合并脊柱骨折的手术治疗相关研究作如下综述。
1 重视AS合并脊柱骨折的早期诊断
AS合并脊柱骨折易漏诊而延误治疗,单纯依靠X线片诊断的漏诊率高达59.4%[10],而晚期的特征性Andersson病损则易误诊为脊柱结核[11]。具有明确外伤史的AS患者会主动就医,但仅受轻微外力的AS患者,由于长期忍受炎性疼痛,早期骨折易被掩盖,直到骨折进展、疼痛加重或出现神经症状才就诊,而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严重后果[12-13]。Gilard等[13]报道了手术治疗的7例AS合并颈椎骨折患者,受伤来院检查时神经功能Frankel分级E级4例,D级3例;从受伤到确诊入院平均12.9 d,期间出现神经功能障碍加重5例(3例E级进展为D级和B级,2例D级进展为A级和C级);从确诊到手术经历约15.7 h,期间又有2例D级进展为C级和B级。早期诊断是保护脊髓神经功能的第一步,AS患者突发或体位改变时颈腰背部疼痛加重,以及受到轻微外力后疼痛加重,均应假定发生骨折,直到确定排除,同时预防性的保护十分必要[14]。使用支具和转运时必须要考虑到患者的脊柱曲线,不可将AS合并脊柱骨折当成普通的脊柱骨折,以避免医源性损伤。在患者清醒状态下,所有被动的体位变化,务必反复确认患者的主观感受。进行全面的影像学检查(X线片、高分辨率薄层CT和MRI)有助于AS合并脊柱骨折的早期诊断,CT可以清晰地显示骨折的情况,MRI在显示脊髓损伤、椎间盘和肌肉韧带损伤、血肿、骨折新旧和隐匿性骨折方面更具优势[15-16]。
2 手术治疗
2.1 AS并颈椎骨折
前路固定融合术具有减压彻底、融合率高和组织损伤小等优点,适用于前柱损伤较重、骨质较好、后方韧带复合体完整且无明显脱位的患者,可针对骨折位置进行椎间盘切除或椎体次全切除后植骨融合,固定范围应包括骨折节段上下各1 ~ 2个椎体[17-18]。Guo等[17]报道10例AS并颈椎骨折患者行单纯前路内固定融合术治疗,术后配合颈托固定,9例患者骨折愈合,神经功能Frankel分级平均改善1级,疗效满意。许鹏等[19]报道9例AS并颈椎骨折患者,其中行单纯前路手术5例,患者术后神经功能均获得改善,骨折均愈合。值得注意的是,单纯前路内固定融合术有内固定失效的风险[20-21]。由于早期对该病认识不足,单纯前路内固定术被应用于后方韧带复合体损伤和后柱不稳的患者,强直的颈椎屈曲时钉板无法承受后柱的张力而出现内固定松动失效;同时,严重颈椎后凸畸形患者前路视野显露困难,不适用此术式。笔者认为,基于文献中AS并颈椎骨折前路手术的成功经验,仅前柱损伤、后方韧带复合体完整同时无明显脱位的患者,可采用单纯前路固定融合术治疗,固定骨折节段上下各1 ~ 2个椎体,术后辅以颈托保护,即可取得良好的手术疗效。
后路内固定融合术固定强度较前路更为可靠,适用于前方无需减压且前柱支撑尚可的AS并颈椎骨折患者。近期的研究对颈椎后路长节段固定融合意见比较一致,固定范围应跨越骨折端上下各2 ~ 3个节段,术者可根据需要选择侧块螺钉或椎弓根螺钉[22-24]。李伟伟等[24]手术治疗21例AS并颈椎骨折患者,其中16例行后路固定融合术,5例行前后联合入路手术,术后脊髓神经功能改善,随访期间脊髓神经功能进一步改善且骨折愈合,作者认为颈后路内固定融合术可明显缓解患者症状,有效恢复颈椎序列,明显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后路内固定融合术适用于前柱轴向承载功能良好(椎体压缩<1/4,滑脱<Ⅰ度)的AS并颈椎骨折患者。
前后联合入路内固定融合术适用于AS并颈椎骨折严重脱位不稳的患者,同时对于存在严重骨质疏松、前后方均需减压或颈椎有明显后凸畸形的患者,前后联合入路可同时稳定前柱和后柱,融合范围更大,生物力学强度更高,减压更为彻底[20,22-23]。Ma等[18]报道了10例采用前后联合入路内固定融合术治疗的AS并颈椎骨折患者,术后效果良好,骨折均愈合。Yang等[25]对12例AS并下颈椎骨折脱位患者行一期前后联合入路内固定融合术,术后平均3.09个月骨折愈合,未出现螺钉松动和折断,证明了此术式的良好稳定性,术后早期离床护理方便,仅颈托保护即可。He等[26]报道了12例AS并颈椎骨折患者,均在伤后3 d内采用一期前后路联合手术,所有脱位均解剖复位,随访显示患者神经功能状况均得到改善,其中9例神经功能恢复至正常,术后3个月骨折融合率为66.7%,6个月时为100%,无严重并发症或死亡发生。Xiang等[27]回顾性分析了11例AS并颈椎骨折患者行一期前后路联合内固定的治疗经验,术后平均随访25个月,平均4.5个月骨折愈合,术中无置钉损伤,术后也没有内固定松动断裂、骨不连或其他并发症发生,作者认为前后路联合内固定治疗AS并颈椎骨折是可行的。尽管前后联合入路手术固定效果更为确切,但也存在手术时间长、创伤较大和出血量多的缺点,对患者心肺功能有一定要求,术中需要密切观察,一旦出现生命体征不稳无法耐受一期手术者,应果断改为二期手术。
对于AS并颈椎骨折来说,手术入路和手术方式需要根据骨折的部位和类型决定,同时也要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只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选择合适的内固定方式都能获得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AS患者脊柱解剖标志改变,关节突增生融合,后路置钉定位标志模糊,手术难度较大,为避免椎动脉和脊髓损伤,术中操作务必谨慎轻柔。值得一提的是,AS并颈椎骨折偶有骨折尖端反复摩擦引起食管瘘的情况发生[28-29],如果骨碎片压在食管上,CT显示骨折部位周围有气体阴影,则应怀疑食管破裂穿孔,若术中发现食管破裂,用生理盐水和双氧水反复冲洗后使用可吸收缝线缝合,前路切口一期不闭合,每天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再视情况闭合。
2.2 AS并胸腰椎骨折
由于胸腰椎前方有大血管和神经,多选择后路长节段内固定融合术,固定跨越伤椎上下各2 ~ 3个节段,对于前柱损伤严重患者也可行前后联合入路手术[30-33]。李仁虎等[32]报道了182例AS并胸腰椎骨折患者行单纯后路椎弓根螺钉内固定的治疗经验,术后平均随访31个月,骨折愈合和脊髓功能恢复良好,无内固定松动和断裂,作者认为,在伤椎上下各固定2个椎体,必要时行扩大内固定术,可获得坚固内固定。Lu等[30]报道了25例AS并胸腰椎骨折患者,6例早期行后路手术,术后骨折愈合,神经功能改善;8例骨折漏诊导致全部形成假关节且4例出现进行性神经功能障碍;11例行非手术治疗仅3例骨折愈合,8例出现假关节;因此,作者建议AS并胸腰椎骨折应早诊断、早手术以预防神经系统并发症。张文生等[33]报道了11例AS并胸腰椎骨折行前路椎管减压植骨、前后联合入路固定的成功经验,术后患者骨折愈合情况良好。后路长节段固定治疗AS并胸腰椎骨折疗效确切,但开放手术、长时间麻醉和大量出血对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AS患者来说手术风险较大,应持谨慎态度。
AS合并脊柱骨折手术的并发症主要有螺钉松动、切口感染、脑脊液漏、尿路感染、肺部感染等,其中肺部感染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18]。近年来,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和内固定器械的发展,微创术式被用于治疗高龄、基础疾病较多的AS并脊柱骨折患者,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34-37]。Moussallem等[34]对比了经皮置钉和开放手术治疗AS并胸腰椎骨折,结果显示,平均手术时间、出血量、输血量、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率,经皮置钉均优于开放手术,且优势明显。Kruger等[35]报道了一组高龄AS并胸腰椎Chance骨折患者采用经皮置钉治疗的成功经验,10例患者平均年龄81.5岁,出院时所有患者均可不拄拐下床行走,末次随访时骨折均愈合;4例患者存在持续背痛,1例因无法忍受在术后9个月时取出内固定。作者认为微创术式能够取得满意的疗效,且最大限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微创治疗AS并胸腰椎骨折损伤小、出血少、住院时间短、并发症少,特别适合高龄并基础疾病的患者。但微创手术也存在学习曲线陡峭、手术视野和操作空间小等缺点。直视下进钉因AS患者脊柱解剖标志改变而变得棘手,微创置钉就更具挑战,而且并非所有AS并脊柱骨折都可以行微创手术,若考虑同时行截骨矫形改善脊柱平衡,微创手术也较难实施。
近期也有使用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治疗AS并胸腰椎骨折的报道[38-39]。陈磊等[38]对1例前柱轻微压缩后柱无损伤的AS并胸腰椎骨折患者行PKP治疗,患者术后背痛明显缓解,可正常下床活动。田庆华等[39]回顾性分析4例采用经皮骨水泥融合术治疗的AS伴假关节形成的邻近椎体应力骨折患者,所有患者术后疼痛明显缓解,作者认为此术式适应证为无神经症状、无需手术减压,止痛制动等非手术治疗无效的伴有假关节形成的脊柱A1或B型骨折。对于早期发现的AS并脊柱轻微骨折,PKP可以明显改善骨折引起的疼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但此术式治疗AS并胸腰椎骨折争议较大,临床报道较少,骨水泥的力学强度能否承担三柱骨折的应力仍需进一步研究。
AS并胸腰椎骨折的治疗方式除了后路、前后联合入路、微创术式,亦有在固定骨折同时进行截骨矫形改善后凸畸形的报道[40-42]。由于AS自身的病理特点,AS并胸腰椎骨折后路手术时,单纯依靠器械达到完全复位的可能性很小,在保证螺钉可靠的前提下尽可能复位、减压充分、大量植骨即可;手术的根本目的是稳定脊柱和神经减压,以利于骨折愈合和神经功能改善,若患者可以耐受,也可适当恢复脊柱序列改善后凸畸形。AS并胸腰椎骨折的治疗可以类似长干骨骨折的偏心固定,应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固定长度和置钉技术以获得足够的生物力学强度,同时考虑到椎体可能骨质疏松,为了获得足够的固定强度,需设计长节段固定以防止螺钉应力过大折断,使用骨水泥加强螺钉、增加把持力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43]。目前微创术式和应用骨水泥的治疗方式尚缺乏大量临床证据支持,具体疗效还有待研究。随着精准、微创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或许将来此类术式会成为早期AS合并胸腰椎骨折的常规术式。若AS患者因为轻微外力出现背部疼痛加重而及时就医,得到早期及时诊断,此时可能仅为裂纹骨折,应用此类术式即可获得良好效果,避免出现三柱骨折再行长节段内固定,大大减少患者病痛、提高生活质量。
3 总结和展望
AS常伴随骨质疏松和脊柱生物力学的改变,致使脊柱易发骨折,但其又不同于一般的脊柱骨折,在治疗上仍存在一定挑战。AS合并脊柱骨折常累及三柱、异常不稳,所有治疗都应以保护脊髓功能为前提,无论是麻醉、翻身还是术中操作,均须高度重视。术前需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及身体条件,多学科共同制订个性化手术方案。麻醉对于AS合并脊柱骨折患者也是一大挑战,不稳定的颈椎骨折是常规后仰喉镜插管的绝对禁忌证[44],目前文献报道,推荐选用纤维支气管镜下清醒状态经鼻气管插管或喉罩引导下插管[24,45]。很多AS并脊柱骨折患者伤后会出现保护性的强迫体位,该体位下患者脊髓损伤多不会加重,麻醉应在此体位下进行。笔者建议在术中预先进行减压和临时固定,使用术中唤醒技术或神经电生理监测确保不损伤神经功能,借助手术床的曲折功能进行骨折复位。术后密切观察神经功能,因为骨质疏松的骨折断端容易渗血形成血肿压迫,一旦术后出现进行性神经功能损伤,应及时进行手术减压。
目前对于不稳定的AS合并脊柱骨折,除不耐受手术者均推荐积极采取手术治疗。疑似AS并脊柱损伤患者的处理需极为谨慎,及时确诊并给于合适体位的固定和妥善转运,制定和实施个性化治疗方案,将会很大程度上保留和改善患者神经功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能以更小的创伤和更少的固定节段获得足够的力学强度是脊柱外科医师未来努力的方向,且由于AS合并脊柱骨折患者基础疾病较多,怎样在保证手术效果的前提下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是将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