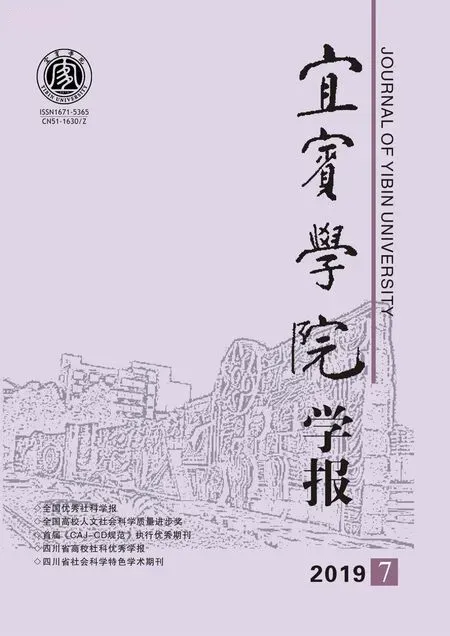由同情到和解
——裘山山小说论
陈广通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作为女性作家,裘山山没陈染、林白、海男甚至铁凝、王安忆有那么强烈的性别立场,其作品传达的并不是单一的女性经验,而往往具有人生普遍意义。在流派频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她或可被看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裘山山的创作起始正值寻根、先锋崛起之时,并与新写实、新历史主义潮流相伴随,但她并没有被归结到其中的某一流派名下,即使是女性主义似乎也与她关系不大。她不具有潮流认证的代表性,但也恰恰说明了其创作的个人性。“新时期”以来,批判精神渗透到各个文学潮流中,似乎只有质疑才能表现出作家的写作深度与思想高度。出身军旅的裘山山并没有介入到当代文坛的“战斗”序列,而是从对于生命的关怀出发,保持着自我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片同情。但与导向反抗的契诃夫、鲁迅式的同情有异,她在想象与假设中完成了与现实生活的和解,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许在她心里,放低个人姿态才能拥有整个世界。对众生的同情和与世界的和解促成了裘山山的创作艺术形态,突出表现于舒徐、平缓的叙述节奏上,可以将之看成其主体性格的流露,更加确证的是其艺术经验的老到。
一、温情之光照耀下的日常生活之美
裘山山的创作取材有点像“新写实小说”,都是来源于日常现实中的琐碎生活,即使那些与“主旋律”接近的作品(例如《我在天堂等你》之属)也是以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为切入点。但是“新写实小说”中的生活一片狼藉,人物落魄不堪,他们的性格也大都随着生活的进行被雕刻得支离破碎。裘山山笔下的人物却多有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他们身上生命之光熠熠闪亮,往往是一个小事件、一件小物品就能表现出作者对于美丽人生的希冀。
《一条毛毯的阅历》并不是作者的阅历,初看起来像是要通过一条毛毯来概括一段历史,但是人物的经历与毛毯的关系并不是很大,毛毯只是一个旁观者。结尾才发现作者并没有历史演义的雄心,她只是将现实中不知所踪的毛毯的去处做了一个“温情脉脉的猜想和假设”,在这个“猜想和假设”里,吴向英成为烈士永垂青史,“对面那个人”得到原宥,吴念英有了归宿。《何处入梦》里的艾红被一条裙子点燃了生命之火,即使在黑暗里她也能感受到裙上散发出的阳光气息。《激情交叉的黄昏》更能体现寂寞中的人对于美好人生的渴求,落魄诗人南国收到的信件让他浮想联翩,凌小凡因为一次邀约产生了过往爱情的回忆。《等待星期六》里一份没有报酬的心理咨询工作就能让李素产生出回报社会的满足感……“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1]46裘山山虽然少用那些细到极处的微末意象——比如墙上的某处斑点、人物的隐秘动作之类,但也往往能在生活无关痛痒的事实里发掘出蕴藏于其底部的幸福可能性。与“新写实小说”的“零度叙述”稍有不同,裘山山对其笔下的人物倾注了满满的同情。她说:“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的小说过于温情,用评论家的话说,不够狠,不够深,但在埋怨自己的同时,我也明白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就是我,我的小说就是我对生活的认知,我对生活的猜想,而不是别的作家。所以它只能那样”。[2]683她由独立的对于“生活的认知”走向对于美好现实的独断“猜想”,以微温的同情照亮笔下的芸芸众生,在创作主体与艺术对象之间产生了交互的认同。
从表面上看,《脚背》写的是两个生活阶层的冲突,但冲突双方同样是现实社会中的普通人,发生的车碾脚面的摩擦也不是什么大事件。虽然在事件解决的过程中有猜疑、有算计,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算是很和谐,严立成夫妇并没有盛气凌人,“小个子男人”也没有狮子大开口。在叙述的进程中,作者不仅给予了地位低下一方以同情,同时也表现出对于相对富足者的理解。偶有讥嘲笔调,但是并不尖锐,仅有的批判色彩已经被双重温情厚厚掩盖。这一掩盖有着不彻底的嫌疑,似乎她的同情并不是那么纯粹,作者好像将自己置于一个优越的观察位置,如“五四”文化巨人一样俯视着笔下的大众。但是,我们不能说她“‘对他人悲剧的感同身受’源于‘拿自身优越的位置和受苦受难者做交换’”。[1]124虽然我们能够看出裘山山也是在刻意努力、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但是对于生活的艰难处自有其铭心刻骨的体验。即使将《脚背》作为一篇喜剧作品来看,作者的主人公们也显然不是比她更“坏”的人,近似的生活经验(无论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使作者与人物走到了一起,同情也就显现不出矫揉造作。
或许会有人质疑:作家怎么可能对小人物有着共同的生活经验?我们不要忽略一个作家创作的初始来源——童年记忆。童年时期的经历是文艺创作资源的重中之重,汪曾祺认为“小说是回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都努力打捞着童年记忆,并将它作为思想观念的生发点。许多外国作家也努力运用童年记忆来切入叙述,比如普鲁斯特、高尔基、乔治·艾略特等。乔治·艾略特的童年回忆发生论甚至对废名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决定性作用。[3]79如此看来,裘山山对于上述质疑的回应也就顺理成章:“关于这点,很多朋友和读者都想不明白,觉得我对小人物的关注,与我的身份不符。一个作家关注什么,并不等于一定要熟悉什么,而是缘于情感上的贴近。也许,根源来自父母吧,我小时候曾经过过苦日子的,对贫困日子还是有体验和感受的”[4]。
裘山山对于童年经历的开掘最明显的要算《春草开花》,此中更能显示出作者与人物之间的经验关系。裘山山在散文《小钱大快乐》里说到自己十二岁时打牛草卖钱的事,“过完秤人家把钱递给我时,我不好意思数,一把捏住就塞进口袋里,然后边走边悄悄用指头去捏”。《春草开花》里的春草通过卖自己的头发有了人生的第一笔收入,拿到钱之后“她的手紧紧攥成一团,手心里是两张毛票和三枚硬币,还有一些汗。那个女人递给她时她没敢看,一把就攥住了。到底是多少,她也不清楚”。人生的第一笔收入使她们心中同样涌动着暖流,同样紧张与欣喜交杂并陈。不同的只是二者收入稍有差距,用以买来的第一件物品稍有不同——一个买的是西瓜,另一个买的是米糕。关于存款,关于存款的花销方式,特别是《小钱大快乐》里母亲带“我”买新衣服时“政府”对于“民间”钱财的“征用”,与春草的经历何其吻合!当然,裘山山在回忆起自己有关财富的过往时,流露出的是一丝丝欣悦,吃尽生活苦头的春草则对钱有着纯稚天真的寄托。二者胸心似有差别,但我们不能说春草是个唯利是图者,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每一个独立个体的权力。作者对于春草的同情自不必说,它有着人生经验形成的基础,对这个基础进行改造、开掘是作家理应完成的任务。《春草开花》虽有冲突,但多半是为生活形式所迫,而且并不是那么剧烈,生活的琐碎消解掉了剑拔弩张的态势。春草虽然命苦,却也遇到了不少好人:孙经理、张阿姐、娄大哥……那个在半夜里买她茶叶蛋的警察虽然语气生硬,但也在客观上缓解了她的困境。这显然不是批判的笔调,只能看作是作者在同情的关照下,对于笔下人物命运的真挚祝祷。
在裘山山的意识里生活是美好的,人性是美丽的。她的作品里少有丑恶现象,也少有绝对意义上的“坏人”,虽然也有对于生活困境的展现,但她似乎一直都“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保持了看到美好事物的能力”。[5]但是,生活并不一定如表象呈现中的那样美好,“看到”什么,很可能与个体对于人生的信念有关。从信念出发对现实做出单方面的判断,是一种有着心理预设的幻想,虽然大部分读者都“接受并认同”她“对生活温情脉脉的猜想和假设”[2]683,然而在一般情形下,它往往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说自欺欺人可能严重了一些)。作家之所以有着对笔下人物微温的同情,除了主体的悲悯情怀外,一定有人物的遭遇并不称心如意时,因为平凡的美好之下潜藏着命定的危机。当危机崭露,人又无可奈何,为了寻求生命与生活的平衡,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主动和解。
二、无奈中的和解
在作品中表现生活之美和对于人性善的坚信者并不在少数,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将危机作为一种潜在的动向压抑于美好生活与人性的底层,对于人与世界之间矛盾的解决方式往往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裘山山的独特之处在于借助想象力催生出的人与现实的一幕幕和解。虽说这种纯粹的同情只能是一种理想,多多少少掩盖了生活的复杂性,但从艺术上讲,她为作品设计的心理和解(而不止是情节的完满),弥合了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裂隙,同时深化与拓展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大团圆叙事。
《梦魇香樟树》是一篇批判现代文明的作品,作者用近一半的篇幅来进行铺垫,无非是向我们呈现当时的社会氛围。“我”进行过拒绝和抗争,但是无碍大局,香樟树最终还是被砍了。按正常的叙述走向来说,“我”最后应该是分到了房子。可是童年记忆中的“价值自然”已经不复存在。“我”能做的也只有一个为逝去的人类生命本真唱起哀歌的梦。梦醒之后,就算再倔强的人也会与现代文明握手言和,更何况富足、安逸的生活也是“我”想要的。似乎“我”与春草同样坚信“女人一定要自己有钱”才能把握自我的人生方向,物质现实的幸福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在一定程度上能抵消精神的噩梦,毕竟对于普通女人来说精神的幸福是要由物质来催动的。读者可以看到,“我”对于经济利益并无排拒之心,她所留恋的是童年记忆中的那份精神守望。当这份守望在被迫中无法保持下去,而且以之为代价可以换来现世的安逸,人类也就只剩妥协一条路可走。然而,我们当真要妥协吗?这是作者在纠结中的一个设问。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于1988年的《梦魇香樟树》在今天仍有意义。
“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是运用语言去阐述个人与他所面对的世界之间的关系”[6]122。这种关系在先锋作家那里是紧张的,裘山山则在假想中实现了对美好生活的祈望,也同样在假想中完成了与现实的和解。《等待星期六》里的李素与丈夫的生活很幸福,然而幸福只是表象,其下同样隐藏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王微的电话是一个玩笑,也是一个提示,加上丈夫迟来的电话,李素陷入了心神不宁状态。志文到底出差与否,处于模棱两可中。关于他的出轨,虽有旁证,但是李素与他并没有就此事直接对话,一切都在猜想中,两个证据都有疑点。第一个证据被李素自己否定掉了。第二个证据是假想中志文的出轨对象,但是我们会怀疑,出了轨的男人怎么会愚蠢到大半夜用自家电话和情人联系?因为从叙述中李素的生活轨迹看,那时她一定是在家的。这样,作者就在无意识中将可能变成了不可能,将前面所说关于志文可能出轨的种种条件全盘否定掉了。这是一个自我驳难的假定,与现实和解的愿望不言自明。整篇故事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因为志文到最后并没有回来,夫妻之间的对质也就无从开始。就算有所沟通,男方的解释是否可信?赵教授又会说些什么?就算遇见了赵教授,李素会向他倾诉吗?一切都在两可之间,替怨妇的打抱不平也就显得没有多大必要了,生活自然会给自身的波谲云诡来一个无声的解释。作者反复强调李素行为的真实性,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想象的构造。其中的关节大部分是人为的假想,反复强调真实性往往显得欲盖弥彰。人类能够想象到的就必然有发生的可能性,成熟的读者自然会心甘情愿地服从阅读的逻辑,作家不必刻意突出故事的真实性,那样做反而是对读者的不信任,也是对自己讲述策略的自卑。关于主题的阐发,裘山山的假设已经成功,如果没有王微的整盅电话,李素不会对丈夫产生怀疑,继而翻看他的通讯簿,发现他的隐秘。她对于王微的责怪其实是自欺欺人,她想在“无知”里继续享受现有的幸福。李素对生活本来很满足,并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然而正是这颗感恩之心促成的回报行为引出了日后的痛苦。看起来,作者是在提示生活的假象,内里却蕴藏着对于真相的否定。否定的结果并没有导致对于现实的批判,反而形成了皆大欢喜的结局。
《激情交叉的黄昏》又是一个关于“人与现实之间紧张关系”的故事。人类本是群居性的动物,与他人交往同时被理解是每一个人的渴望。但是,南国与陌生女人见面时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以平凡的客套话开篇,却招来女子的频繁回怼,弄得自己无所适从。他想要紧握其手以表激动,却又感冒昧,无胆实施,也就只有“重复着搅动咖啡的动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由是而生——他的表达也总是言不由衷,口出与心想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妻子凌小凡与他同样心情,但是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两场约会,前者不欢而散,后者是个骗局,他们的幻想同样无疾而终。风波过后,老夫老妻的他们重回日常生活轨道,所有的浪漫不过是想象中的昙花一现,拉拉杂杂的琐碎生活仍将继续——也只有继续。
《何处入梦》也有着与希望相关的人物对话之间的别扭,往往是自己的言不达意,或是对方的无趣倾听。艾红对于“疲惫的旅人”之探问,得到的是冷语以对,行为之间也充满了矛盾。最后来找她的男人是不是那个旅人?实耶?梦耶?又是两可之间。作品结尾稍嫌生硬,无非想要呼应梦境,给女主人公一个小小安慰。
《卡萨布兰卡》同样是一个无尾的故事,但我们根据女主和丈夫的沉默与言语完全可以一厢情愿地假定他们最后不会分手。作者似乎在为我们灌输一碗“鸡汤”:“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也是一种陪伴”,这句话无疑会给在现实中处于冷战状态的夫妻们提供些许安慰。但是,观念变了并不等于激情的回归,柳无慧和丈夫与凌小凡和南国一样复原了从前平淡的日子。他们在现实生活的平流层上挣扎的那一瞬间过后,只有接受枯燥乏味的上帝之谶。无聊与寂寞仍将无处排解,可是又能怎么样呢?柳无慧遍寻从前交往过的男性,已经发现再也没有谁能提起她的兴趣,那些大龄女性朋友是她假想中的楷模。既然孤独无法被拯救,那也只有忍了。这是人到中年的必然,没有任何命运之匙的解放,和解是唯一的选择(与世界、与他人甚或与自己),毕竟,人还是要活下去。
如果说在短篇小说里裘山山利用作者的统治力,为故事设计了种种矛盾,在个人意识里“强迫”情节朝着主观预定的方向发展,那么她的长篇看起来就显得更加水到渠成一些,和解的诉求也就更加可信一些。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很难在短篇中看到人物性格的变化。长篇则不然,在裘山山平淡的叙述里,人物的遭际看起来并不像其短篇中那样有着稍嫌过分的着力痕迹,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性格或者心理也就在他们的经历中逐渐转变。往往是人物在最初正面面对现实的矛盾,看起来似乎毫不妥协,但是随着遭遇的展开,他们改变了初衷,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与行事方式,以寻求与生活握手言和,目的同样是有一个物质的幸福或者心理的慰藉。
具有美丽生命的人物遭受苦难是裘山山常用的叙述模式,她在《春草开花》里给予了主人公春草以耐心的同情,但是与前述作品的基调一样,春草到最后也没有“开花”。春草本来是一个呆憨木讷、倔强倨傲的女孩,随着一次次的失败后来学会了圆通世故。在第一次远出做生意的路上,她的灵活变通让何水远对其刮目相看。他们占了火车过道的位置,本来列车员的态度并不友好,儿时倨傲的春草放低了她的姿态,她“帮列车员扫地拖地,还给大家倒水,忙得一头是汗,就好像她是列车员”。这种“和气生财”的“本事”让何水远不禁佩服起春草,认为她是一块做生意的好材料。到了娘舅家,春草继续发挥着低调的手段,忍气吞声,以好言好语换来生意的基础,在她看来“嘴巴甜又不花钱”“看看脸色能省钱还是合算的”,何乐而不为呢?在百货商店租摊位是她天赋生意头脑的最初显现,后来与顾客的讨价还价更是说明了她不仅能说会道,还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当一个人主动对生活伸出和解之手,可能世界就会以另一种面目呈现在他面前。春草品尝过自己的初步胜利果实后,对于从前以仇家相看的母亲也“没那么恨了”。后来她懂得了玩弄心机,学会了给人送礼,对于损人利己的事情也颇能容忍,并以报答为由自愿委身于婚外男人……这些“勾当”是少年时期的春草绝对做不出来的。但是我们能否责怪她呢?春草的性格变化显然是主动的成分居多,目的是为了换取更美好的生活,也许妥协下的和解是实现幸福的一个法门。虽然在故事的最后她并没有东山再起,但是她依然努力着,作者透露给我们的也是奋斗必胜的信念。春草还在“卯足了劲儿和外面的世界较量”,和解是她以退为进的斗争策略。
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生成了其作品的主题,由主题出发,又往往生成了他的叙述姿态与方式。我们可以从裘山山的同情以及与生活和解的态度里看到她性格里的温润一面。所谓文如其人,从艺术形式上看,这温润突出表现在其叙述节奏的把握上,平缓、淡然、没有激情四射,更没有剑拔弩张。
三、平缓的叙述
和解是一种胸襟,当一个人与现实握手言和,他的态度也就不再情绪化,创作中表现出的是平淡、冷静的气质。像是旁观,与对象之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不是余华或者新写实作家式的远观,而是不近不远、不疏不密。这就不是“零度写作”或者冰碴子式的冷酷,而是一种与人体上下接近的微温状态,这种状态与和解的愿望形成标配。裘山山的讲述语调不走极端,因为不走极端所以会让人联想起各种流派;也正是因为不走极端所以又难以被归入任何流派,这也可能是当代文学史中少有提及她的原因之一吧。
微温同情下的模糊的叙述立场会导致叙述节奏的客观化,去除暴躁凌厉,减少愤激火气,直至真实地再现生活本身。在西方,“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虚构和戏剧的叙事就引发了两个重大而反复的讨论: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模仿和真实(小说应该再现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同情,以及小说如何运用同情。慢慢地这两种反复出现的问题合二为一了,我们发现,大约自塞缪尔·约翰逊以降,基本共识是,对于人物的同情性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小说真实的模拟:去真实地观察一个世界以及其中的虚拟人物,或能拓展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同情的能力。”[1]124对于真实的再现需要一种冷静的心态,在冷静中反而能展现出作者的同情,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性的现象,但又有着确论性的基础。在中国也是如此,对于现实的摹仿是一种“弃智”行为,也是一种去情行为,它要努力摆脱自身的思考与情绪,将外部世界的图像缓缓绘来。去情与“弃智”看起来与同情正成反调,但是凡事不能走极端,这里的“弃”与“去”是对于极端的否定,微温才是人生的常态。从这个方面说,裘山山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
《脚背》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的《一件小事》,它们同样是关于两个阶层的对比。鲁迅的姿态很复杂,用的是知识分子从上到下的俯视视角,最后却站到平民的立场上。裘山山貌似站在平民立场,却又见不出对肇事男女有什么批判,如果从“碰瓷”角度看的话,她反而表现出了对严立成夫妇的同情。如上文所述,作者对小个子男人也是同情的,对双方的同情抵消掉了是非对错的判断(“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暂且不论事故双方的对与错,从这“无是非”观里见出作者心态的平和,她的立场并没有如鲁迅似的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转变,而是始终站在二者的中间地带。在这中庸的态度里,本无什么情节的叙述节奏也就自然而然地舒缓了下来。《卡萨布兰卡》讲述的是关于婚姻的故事,可是其中并没有见出一般女性作家对于性别立场的主动把持。不仅如此,她甚至对当事主人公双方同时表现出了些微的调侃意向,这种一意向表现在二者关系生成的张力空间,而不是专门针对某一个人;而且这一调侃并没有达到讽刺的程度,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无聊枯燥现实生活的调节剂,使作者、读者、人物会心一笑,仅此而已。
文本结构往往能折射出一个作家的讲述节奏,对于裘山山来说,《春草开花》这种一般结构自然不在话下,它以中国传统的节气命名提领各部分的叙述,作者信手拈出某个时间节点,如打渔人提起了渔网的总绳,在她从容的笔调之下,拉里拉杂的生活事件在其中娓娓漫延开来。她的布局少有“一起之突兀”,但是不乏时空的前后左右穿插,奇怪的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作者编排组织的着力处,反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
《卡萨布兰卡》的正面故事与作品的同名电影(或者其它肥皂剧)的放映交叉呈现,是作者理智的比衬策略。叙述时间又在现在、十年前和三个月前之间回环往复,构思的努力足见作者耐力之强,对于时间的前后把控,造就了她关于博爱心胸的左右逢源。在《激情交叉的黄昏》里作者为两个主要人物各自设置了两个场景,南国:家里——咖啡馆,凌小凡:家里——招待所。她像一个心理调研者,将假设的种种情形慢慢铺开,然后一一拆解,从中捋出人物的情绪走向。虽是“激情交叉的黄昏”,但不见叙述者热情的高涨,恰如两位主人公的生活状态不温不火、平淡静寂。《我在天堂等你》也在回忆和现在之间来回跳跃,有些地方看起来是要在过去与现在的比较中实现对当下的批判,但是只有苗头并无发展。作品一开头就铺开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似乎涉及的所有人物都处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从代际隔阂方面看,欧战军是矛盾的连接点。儿女们有的“投机倒把”,有的要闹离婚,作为父亲的欧战军从个人生活经历形成的价值观出发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了否定,所以有了家庭会议的召开。但代沟并不能概括全文的叙述要点,木鑫、木槿、木棉他们各自的处境代表的是当代生活的普遍状态。看起来矛盾重重,但是作者的叙述有条不紊,不动声色,她的语言简洁干净,很少用到额外的形容与陪衬。对于“天堂”的回忆部分基本上由过来人白雪梅讲述,作为一位在丈夫的突然去逝后精神陷入低落状态下的老者,她的讲述自然不会高昂激烈,其语速将作品的叙事带向了纡徐形态。
在上述作品中,我们很容易见出裘山山对于展现人物心理的努力,不论是《春草开花》还是《卡萨布兰卡》,特别是《我在天堂等你》的主人公视角的运用使作品呈现出一定的心理深度。她借助文本结构的时空位移,对人物心理层面的变化作出了颇为细致的把握,对于心理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叙述的硬度、增强了叙述的密度,从而引发读者对于生活现实的思考。但是能引发思考,并不代表艺术上的完美,裘山山讲述的缺陷是心理表现基本上处于直言形态。我们不能说上述作品不是感人的故事,但是作者在讲述中往往是尽心竭力让我们知道一切,无论内与外,她都始终掌控着作者的“全知”权力。虽然不乏感染力,但她很少将人物心理附着于“动作”上。古语有云:“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7]诗歌如此,小说亦如此。文学之美很大程度上在于清晰与遮蔽之间的朦胧地带,这样才能调动起读者的想象力,缺少暗示、过于直白往往削弱了阅读过程中的品咂趣味。作家本人说:“我不太喜欢象征意味很浓的东西”,[8]此处的“象征意味”主要就题材选取的历史意义而言,很适合裘山山的人格气质。但是,就创作方法来说,或许加上一点朦胧色彩也不无裨益。不管怎么说,由文本结构与心理展现生成的叙述节奏是可以视为裘山山创作特点的承载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她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芜杂,体味了世事的无奈。
军旅出身的裘山山将两只脚深深扎入平凡生活的底层,感受其中的生命温度。她没有同时代先锋作家那样鲜明的形式创新追求,也没有寻根作家那样强烈的文化精神坚守愿望,她只是平静地看取生活,平淡地予以表述。从对于现世人生的温情关怀出发,努力追求与表现着平凡的生命之美,即使受阻后的无奈和解也显示出与生活周旋的智慧。与温情与和解相适应,她的叙述笔调是平缓的,如静水流深、宁静致远。叙述氛围犹如良朋话旧,拉拉杂杂但并不枝枝蔓蔓。语言的纯粹保证了主题的明晰,她很少在作品中宣告什么高旨要义,但读者总会心知肚明。因为芜杂的生活在她缓慢的笔行进程中变得舒徐有秩,我们不需要像读先锋小说一样为了拆解一个细节与作家一起费尽心思,省下的精力也就可以仔细品味文字间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相似的生活。如此说来,裘山山必定是一位紧贴生活的作家,却又不像新写实似的冷淡,微温的同情及其带来的人生观念与艺术形态共同完成了对于当下众生生活困境的解答与表述。对于这样一位有着悲悯情怀又有着独特艺术表达方式的作家,当代文学史上理应有她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