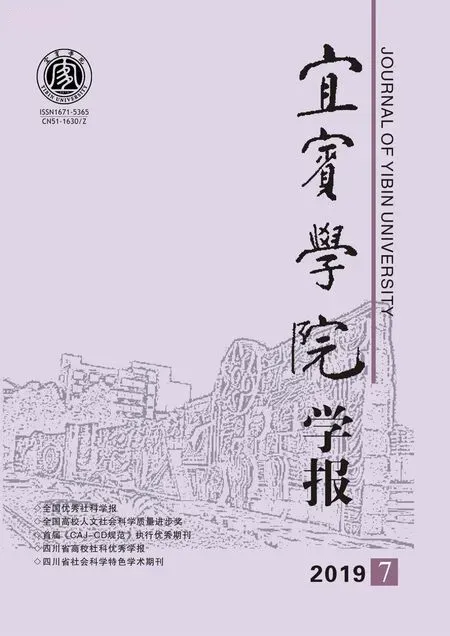追寻“小切口的痛感”
——裘山山短篇小说新论
郑依梅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在裘山山的四十载写作生涯中,短篇小说一直是这位笔耕不辍者最钟情也是最擅长的文学体裁。她虽对长篇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领域涉猎颇多亦成绩斐然,然而若单以数量论之,远不及所作短篇小说一百余篇之巨。在2016年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时,裘山山曾言,“我的短篇小说是所有体裁里写得最成熟的”“写短篇让我更快乐,更自信”[1];她也坚定地相信短篇小说的结构、叙述风格和韵味令人着迷,“不要小看短篇,一个小切口,一样会有痛感”[2]。“小切口的痛感”一语可谓道破玄机,可对裘山山的短篇小说创作作一恰如其分的注脚。
一、女性的生命困境实录——“痛感”叙事的主题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但凡有深度的文字均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将痛感从作者的笔尖传递到读者的心灵。裘山山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她对生命中痛感之特殊而凝练的表达。
裘山山的文字常被读者冠以温暖善良之名,温情脉脉,娓娓道来。这种冲淡和缓的叙述方式却被某些研究者批评为“缺乏揭露和鞭笞丑恶的深刻性”,渐而其作品被认为格调不足。此言差矣。且不提《春草》《八岁的天空》等长篇作品中人物遭遇的诬陷毁谤、猜疑妒忌与冷眼旁观,以及特殊时代带来的无知无情、无德无法与无美无赖[3]72,裘山山的诸多短篇小说创作亦始终贯穿着一种以特殊形式呈现而出的痛感,虽然琐碎平凡,但若细细品味,实则饶有兴味,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作者对人性与社会中丑恶面的暴露与反思。从《八月蝴蝶黄》(1987)中触手可及却骤然消逝的爱情,《等待星期六》(1994)中善意给予者到乞求者身份的戏剧转变,到《春天的一个夜晚》(2003)中女强人精致妆容与雷厉风行背后的脆弱无助与故作坚强,《教我如何不想他》(2004)中穷困妇女在生活重压下的选择和对爱的渴望,再到《寒露寒》(2013)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美人卧》(2014)中酒桌上女子各自的婚姻家庭困境……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直至今天这三十年来,裘山山一直借助短篇小说之形式,关注并叙说着平凡小人物生命中的挫折、逆境与磨难,无论她给予主人公怎样的结局,或重新出发迎接新生活,或就此沉沦埋头于苦痛,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痛感始终在她的文学世界中存在、氤氲、发酵,成为她短篇小说创作的一大基调,在近年的作品中亦愈发有醇厚韵致。
裘山山短篇小说中的“痛感”最为显著的表现在对家庭婚姻生活中女性遭遇之精彩书写。裘山山钟情于讲述女性的故事,她坦言“从没想过隐瞒或模糊自己的女性身份”,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亦作为广大中国女性中的一员,她更加能“体察女性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关注“她们的坚忍、脆弱、敏感、浪漫”[4],这意味着她笔下女性角色充盈丰满,生活情节真实入微,仿佛是发生在读者身边的人与事。由此番匠心与笔力,女性角色本身遭遇的痛感、作者在文中注入的痛感以及读者所感知的痛感方可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世界,从而构成裘山山对痛感的独特表达。
比如在《春天的一个夜晚》(2003)里,女老板李雪仪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女强人,工作中雷厉风行、酒席上八面玲珑的她其实遭遇了不为旁人所知的痛苦婚姻经历,只有在烂醉如泥之时她才得以将其向小助手方欣宣泄出来。如果说丈夫的狠心背叛、第三者的不知廉耻以及旁人的流言蜚语,不过是让李雪仪尝到爱情消逝与婚姻破裂的痛感的话,那么让她对男性抱有轻蔑与失望,真正击垮她对家庭生活信念的,则是被前夫剥夺看望儿子的权利,以及儿子的冷漠相待,她因此变成一个“被抛弃的母亲”,这份失去妻子身份和母亲身份的痛着实令人揪心,即便是事业上的成功也丝毫未能修复她内心的累累伤痕。再如《野草疯长》(2007)是一篇25岁女子的情感经历自述,她遇到了三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有横刀夺爱与她结婚但在她生了女儿后离婚出走的赵推销员,有只迷恋她的肉体却躲避父亲责任的毛头小子松林……可谓屡次遇人不淑,再加上她自身的优柔寡断和自欺欺人导致了这一系列不幸。小说最令人深感悲哀之处在于,她明知年轻的松林只是被她的身体吸引,也很清楚唯有以身体为诱惑,松林才会认真听她讲话、才会对她作出爱情承诺,她还是天真地相信这个尚不成熟的男人值得她托付终生,她在这场爱情中始终身处劣势,卑微至极,她的痛来自这三个男人更来自她自己。
如果说《春天的一个夜晚》(2003)和《野草疯长》(2007)等小说讲述的是单个城市或乡村女性遭遇痛感的生命体验,那么《美人卧》(2014)则毫无疑问构成一幅栩栩如生的女子群像,作者巧妙地将时空限定在一个夜晚的高档餐厅海陵阁333包房内,矛盾和冲突在一处集中,痛感如同连环的炸弹被作者果断地一一引爆。酒过半巡,九个中年女人借着酒劲吐露心声:叶晚云睹物思人,主动讲起前夫因癌症去世之事,追思当年令人感伤的青春与爱情;孙雁看似风光,却也遭受着丈夫与其前妻之大儿子对她满怀的敌意和羞辱;黄莉芳对丈夫外遇心知肚明,严防死守却四处漏水,酒精过敏的她借酒消愁愁更愁,甚至不惜用生命试探丈夫对自己是否还留存最后一丝情意。足见她们内心的痛感无不与婚姻家庭密切相关,他们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当女性进入社会、组建新家庭时,她的身份从女儿转变为女人、妻子和母亲,一切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但她们往往会对这些新的身份充满紧张、无助和茫然,她们担心由于丈夫的变心或离开而失去这些可以让她们在小家庭中安身立命的角色,从而失去来自主流价值观的肯定,为此她们或挽回或放手,或受辱或放达,但她们大都经历了种种惶恐不安与迷惘纠结和所饱尝的内心的极致痛感,正是作者试图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现实与感触,为我们今天反思女性与爱情、家庭、婚姻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拷问人性与追思生死——“痛感”意涵的深化
裘山山短篇小说的痛感表达亦表现在拷问与省思人性这一层面。裘山山的确是想借痛感表达对人性美好的向往,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故意将冲突处理得暧昧不明,无关痛痒;她也无意于创造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当代桃花源以标榜温情。相反,她总能将惨淡无情的现实与人性中最具劣根性的本质暴露在读者面前,三言两语看似轻描淡写,却能将痛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失温情的同时也避免冷峻绝望的氛围,这不得不说是她拥有成熟的表述功力所致。
《瑞士轮椅》(1999)中,企业家于叔送给残疾的年轻人一把价格高昂的自动轮椅,并要求年轻人向他的朋友、报社记者、生意伙伴一遍遍地展示轮椅,年轻人不胜其烦,但出于感激和报恩心理不得不每次都如同公园里的猴子般供看客围观,久而久之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濒临发疯,于是偷跑离家,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去继续以这种方式报答于叔,满足其虚荣心。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作者从一个具体物件出发展开她的思索:即使社会中的确存在不求回报的施恩者,但仍属少数,大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希望从受惠者或者施恩行为及其后续影响中收到感激和回报,他们甚至利用受惠者最为真挚纯洁的感激之心,以在他人面前塑造光辉伟岸之高位者形象,从而满足虚荣之心与掌控之欲;他们不会换位思考,也认为自己没有必要换位思考,受惠者的尊严与情感在他们所求之物面前毫无意义,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人的物化吗?在“看”与“被看”中这份物化无疑更为深重。而文中有一处闲笔,于叔在把轮椅从瑞士带回中国的路上,国内外机场中工作人员与普通旅客的两相对比下,尤显国人人情之淡漠。
《脚背》(2008)是篇颇具趣味的小说,篇幅不长且节奏紧凑。严立成老婆开车撞到了一个生活无着落的打工者小个子男人,他们三人一起去医院就诊,所幸只是伤及脚背,严立成打算用钱私了。小个子男人一路上和他们夫妻俩聊自己的生活聊城市的房价聊彩票,半句话不离钱但就不提赔偿,严立成怕他是个讹钱的主儿而担心了一整晚,结果那男人最后只想要两百块钱,比严立成预期少了太多。最有意思的是结尾处,当小个子男人弯下腰记下严立成的车牌号时,严立成十分愤怒,觉得他不知好歹得寸进尺,结果得知小个子男人只是想用车牌号去买明天的彩票,认为托严立成夫妻的福他能中奖。这个令人意外而饶有趣味的结局中其实埋藏着一层深意,更是作者对人性中浅陋面的揭露。为什么严立成和他的妻子、他的牌友们都在一开始便把小个子男人预设为想要借题发挥敲诈一大笔钱的人呢?是因为他的贫穷?还是因为他的工作?抑或是因为他对金钱的重视与渴望?城里人从何时开始对外来打工者带有极深的成见?为什么这两类人之间很少能够产生作为两个人类个体生命之间相对平等地交流?这些都是裘山山揭露在读者面前的血淋淋的伤口,着实叫人内心隐隐作痛。又好比《对影成三人》(2013)中老板在小刘出事故后立刻“卸磨杀驴”,急于撇清干系的丑恶嘴脸;《意外伤害》(2012)中沈庆国的英勇救人不被领导和群众肯定,还被怀疑搞外遇、贪污腐败,等等。裘山山从未对社会中的黑暗视而不见,相反,她正是将人性丑恶之痛感细密地织进小说情节之中,期待细心读者发掘其间意涵。
与此同时,对终极问题的思考也使得裘山山短篇小说中的痛感书写具备了探索生命意义的价值。生死,往往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最令人唏嘘叹惋、引得哲思万千之母题,毕竟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死,迎接己身的生死,一切凡俗琐事在生死的面前皆骤然苍白无力,人们往往能对小说中的生死母题产生强烈的共鸣。不同于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长篇纪实文学《亲历五月》等作品中所描绘的解放军战士为完成艰难任务的英勇就义,地震中人民教师们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们的壮阔牺牲等情节,给人以灵魂之震颤,渐而升起对生的向往和对死的敬畏,裘山山在短篇创作中带来的死亡叙事则更加贴近我们的个人日常生活,更具实感,比如儿女的早夭和配偶的离世,这些同样动人异常。
《寒露寒》(2013)讲述了两对夫妻时隔三十年重逢的故事。当安璐敏见到旧时的好友兼情敌乔秀云、前男友陶明亮这对夫妇之前,种种往事重又浮现眼前,她还没从回忆中完全走出,未曾料到现实中的再度相会竟是如此平淡,而更加令她惊讶的是秀云的消瘦憔悴。原来,陶明亮和乔秀云的儿子在两年前自杀殉情,夫妻二人在美国始终走不出伤痛,两年来闭门拒客,为疗愈心中的伤口、改变现状才不得不回国,“说到底,只要没有勇气死,就得活下去”[5]。整篇小说在平淡委婉的叙述中氤氲着浓郁的苦涩与伤感,人到中年罹受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瞬间失去了生活的动力,那些地位、财富、人际关系等身外之物都变得毫无意义,但又因没有自戕的决心而不得不浑浑噩噩度日,消磨着漫长艰难的人生。关于生命意义的探索,作者亦在《听一位未亡人讲述》(2018)中借詹月的回忆告诉我们一段颇具哲理的话,或可构成作者对生死观的剖白:
詹月脑子里莫名其妙出现一段话:热力学第二定律真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东西:宇宙中所有的事物无限趋向于混沌。人从出生、成长,到衰老、死亡,无限地趋向于解体、腐烂,在土中或空中消散;树和草也是这样,就连石头沙子也不能幸免。你可以想象这个过程像一场巨大的泥石流,摧枯拉朽,把一切可以称为美的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杳无踪迹,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所以,各位没必要太在意那些貌似很重要的东西,它们迟早都会消散的,包括我们自己,消散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存在于过程中,享受过程就好。[6]
诚然,生命之根柢是残酷的,没人可以躲避死亡阴影的侵袭与笼罩。无论是对生命降临的喜悦,还是对生命消逝的惋惜,抑或是对生命磨砺的畏惧,每一个人都应当在自己所能及的范围内、在有限的时空中,尽力地感受人生百味。活着,远比任何外在之物都重要,它是一种状态,亦是一种境界。即使生活充满痛感,也不要因此放弃生命。这正是裘山山痛感书写中的生命智慧。
三、生活片段中凡人小事——“痛感”自“小切口”而出
既为“小切口的痛感”,那么裘山山是如何将“小切口”这一特性在短篇小说创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呢?在笔者看来,这与其形式、取材和节奏密不可分。
首先,“小切口”这一叙事角度与短篇小说之形式无法分割。正如茅盾论短篇小说艺术时谈道:“短篇小说取材于生活的片段,而这一片段不但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并且使读者由此一片段联想到其他的生活问题,引起了反复的深思”[7]106,这也就决定了短篇小说很难、亦没有意图去展现一个长年累月发展下来的故事,去描述一个人自出生伊始之生命终结的过程,去展现一个社会人事变迁纷繁复杂的情状,而是以精简凝练的篇幅截取生活中富有意义的片段和性格突出的人物,甚至将不同的素材叠加、融合,再变形为一个崭新的素材,从而使得一连串矛盾聚集的叙事在一段相对短暂的时间里、在几处相对固定的地点中喷涌而出,表现出比这个生活片段本身更加广阔复杂的社会现象。裘山山深谙短篇写作之道,其短篇小说几乎都符合这些描述。
更进一步来讲,若用裘山山自己的话来解释“小切口”一词,则指向对生活中那些微小平凡的人与事的取材:“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值得写,小人物、小场景、小细节也值得写。不以善小而不为,用在写作上也是可以的。生活中最普通的情感、喜悦、哀伤、嫉妒、内疚、思念、郁闷、忐忑不安,都是人性的折射”[2]。以小见大,在平凡中洞见幽深,在生活中觅得隐秘,这便是裘山山“小切口的痛感”的写作风格之目的,质朴无华的语言背后是人性的复杂,其间便潜藏着无数供人流连徜徉的艺术世界。
纵观裘山山的短篇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她总是能将当下时空中凡夫俗子们身上发生的平凡小事讲述得细致入微而形态万千,不同作品之间几无雷同重复之痕迹,生活于她而言是永远道不尽的故事。你或许能在理发店里遇到一个扑闪着怯生生的大眼睛、瘦小乖巧的洗头小妹“累累”,沉默寡言的她因为讷于言辞,从来不向你推销洗发水或者怂恿你办会员卡(《累累的耳朵》,2017);你或许在傍晚时分饭后散步之际,在小区里撞见爱管闲事、啰啰嗦嗦的老太太“张淑英”,她扯住你的袖子,硬是拉着你讲着7号楼小夫妻闹离婚的争吵或是305室的女儿考上了市重点中学等与你没什么关系的琐事,嗓音朗朗如洪钟(《课间休息》,2013);你或许会为了避雨暂且躲进一家茶馆喝茶,恰好目睹了青年男女许林峰和田青青约会中的种种尴尬(《大雨倾盆》,2011);你家楼下或许就住着一位抠门的“靳师傅”,他节约得连冬天都舍不得用电暖气(《靳师傅的太阳光》,2001)……我们说,引发裘山山书写兴趣的这些小人物小事件就仿佛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正是这些发生凡世间的、由凡夫俗子亲身演绎的痛感才能更能引起读者的联想与共鸣,发现自己亦是他们中的一员,带着庸常生活中的痛感,在人生之路上踽踽独行。这种发衍自亚里士多德“摹仿论”流传至今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以生活片段为镜反思人性、窥见真谛,构成了裘山山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模式,这也是她选取小切口之真挚用心。
裘山山是一位质朴平易的写作者,她对于同读者玩文字游戏没有兴趣,也不想用华丽精致的辞藻以夺人眼球。她只是想讲好一个个故事,而事实上她也做到了。她善于把握故事的节奏,使得整个情节不蔓不枝,富于张力;在读者渐入佳境之际给出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8]的结局,使得流淌于文字中的痛感于一小处集中迸发,此亦得“小切口”笔法之妙。这种类似于推理小说的布局方式,往往在故事前中期带领读者如探索迷宫般步步深入,使读者对结局进行某种预期;随后笔锋一转,结局突变,迷宫的尽头竟是料想不到的风景,令人回味无穷。
《百密一疏》(2018)正是对此种创作方式的最佳确证之一。当读者以为侯志清与李美亚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正准备迎来一个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圆满大结局时,作者竟然以独具匠心的形式——夫妻二人的检讨书作结,李美亚以离婚的方式向丈夫侯志清谢罪,以挽回她漏报个人资产的严重失误。再如《锁着的抽屉》(1991)中方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打开的那只魂牵梦绕的抽屉,里面竟空空如也,便只能把它重新锁上,这似乎也构成对人生某些境况的隐喻;《廖叔》(1996)中廖叔对“肥肠大嫂”的怨恨构成贯穿整文的暗线,具体缘由直到结尾才得以真相大白,特殊时代所造成的伤痛其实一直存在,选择原谅他人更是放过自己……在结尾处设置情节突转,虽然可能招致生硬突兀、戛然而止之风险,但可贵之处在于,那些悲欢离合、喜怒哀惧、酸甜苦辣皆在故事的最后时分没有保留、完完整整地暴露在读者眼前,读者在瞬间明白作者在前文中的铺垫和设置是出于何种用心,理解作者创作这篇作品是想宣泄怎样的情感、表达怎样的思考。切口虽然很小,但这集中于一点、浓烈至极、深入人心的痛感,由于其身处结局之际,而更能让读者在读罢全文后回味无穷。
四、诉说痛苦而指向光明——“小切口的痛感”的背后
总的来说,裘山山追寻“小切口的痛感”,是将人世间最稀松平常的痛感在字里行间加以呈现,希望人们可以感知到这份痛感并展开对自我与生命价值的思索,期盼小说能够承担起反映社会生活真实侧面的责任。但裘山山并不想成为一个谴责小说作者,她不愿以残酷冷静的口吻讲述一个又一个痛彻心扉的悲剧,渐而让人们对同胞的人性和身处的社会失去信心、悲观消极地生存。恰恰相反,她的创作基调如午后的阳光般温暖人心,总能赋予人在艰难时世中继续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虽诉说苦痛,却指向光明,两者看似矛盾,却在裘山山的短篇小说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离不开她冲淡节制的语言风格与叙事手段。
在裘山山的叙事中,我们往往很难找到她对笔下角色的强烈情感,喜爱称赏也好,厌恶批判也罢;没有人是绝对的好人,也没有人是绝对的坏人,所有人都拥有复杂个人性的多面的人。对绝对善恶观念的消解,正是构成裘山山短篇小说之哀而不伤的情感基调之关键原因。对待痛感,她选择的语言风格是娓娓道来,偶尔夹杂以嬉笑调侃,而非肆意宣泄、歇斯底里,她不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行施加给读者,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认可这些人与事;言有尽而意无穷,她亦深谙留白的艺术,给人们留下省思之充足空间。
例如在《调整呼吸》(2017)中,作者没有直接告诉读者牟芙蓉对应学梅死在她家这件事是如何冷漠,而是通过大量侧面描写展现出来,如牟芙蓉在录口供时屡次提到瑜伽老师青师,一谈到青师平时给他们上课、他们给青师过生日的情景,牟芙蓉高兴得好像忘记了有人死在她家里这件事一样——“牟芙蓉竟然笑起来,是一种甜蜜的笑,仿佛诉说某种幸福”“牟芙蓉再次漾开笑容,仿佛刚才那一笑,波纹太强,一时散不开,必须再推送一次”“牟芙蓉呵呵地笑出了声”,三次层层递进的笑容,却一次比一次令人寒心;因为今天是青师的生日,他们向青师献上的表演也十分成功,牟芙蓉甚至认为:“我们也感到非常幸福,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把应学梅之死完全抛诸脑后;在接受问询中,牟芙蓉还总是提醒女警察郭晓萱要注意体态,打开肩胛骨,不要含胸,仿佛她不是来接受死亡事件的调查,而是来警察局闲聊一般。“郭晓萱觉得后背发凉,这个女人,揣着的那颗心,如同她那条能竖起来贴脸颊的腿一样不可思议”[9]。人性残酷冷漠至此,毫无共情之心,叫人读来心生恐怖。我们在小说中找不到作者对牟芙蓉的批判或讽刺,而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表情、言行和心理刻画,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形成了强烈的呼应,让人不由得拍案叫好。类似的例子自然还有很多,此处似无需赘言。此般语言风格意味着裘山山的短篇小说是有节制的文字,与之对应,“小切口的痛感”亦成为有节制的痛感。
有节制的痛感之呈现,不仅得益于语言风格,更依赖于“曲笔”之使用,即以委婉表达冲淡强烈的戏剧冲突。《春天的一个夜晚》(2003)中,面对李雪仪从脆弱女人重归女强人之迅速,且迅速得有些冷血无情时,方欣感到惊讶,她有些茫然地接过李总的红包,走出老板办公室,“发现窗外的树还是那样的绿着,四月毕竟是最美的”[10]223。在历经李雪仪人生伤痛诉说之洗礼后,在看到她为遮掩自身脆弱之言行后,读者会不由得产生一种对婚姻和家庭失望悲观之感,但裘山山没有让这份伤感在文中停留太久,她用这四月春天的绿意这一环境描写,将整篇小说的色调骤然调整得明亮起来,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希望已经在孕育之中,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野草疯长》(2007)中,女主人公虽然在松林出走后神伤许久,回到母亲那里养伤,又在BBS上向陌生人倾诉自己的遭遇,但她没有就此沉沦,而是:“我离开网吧,去找我的女儿。至少我应该让我的女儿,遇见一个对她负责的母亲”,在饱尝命运对自己的捉弄后,她发现在困境中“只有母亲不会跑掉”[11]283,母亲永远是子女的避风港,她也由此意识到她自己对女儿的亏欠,女儿才是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人。这是母亲身份意识的觉醒,这样一个正能量的结局无疑能够冲淡前文堆叠笼罩的痛感。
《对影成三人》(2017)则是通过为人物构造了一个苦中作乐的结局,给这场有些荒诞的事故画上了句号。音乐老师包晓妮和司机刘正萍水相逢,共同遭遇了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车祸”,还分别与自己的伴侣遭遇了分手困境,在故事的最后这两个“天涯沦落人”在医院里,与被撞的拾荒老头“对影成三人”,苦中作乐,对月饮酒,度过一个难忘的中秋。作者的幽默笔调和主人公对待困境依旧幽默的态度,使得这篇反映人心复杂的小说带有了隽永的意味。
当然,“小切口的痛感”背后,是大内涵的哲理。裘山山曾言,小说是她对生活的设问,亦暗含了她对生活的愿望[8]。裘山山在追求个人真情实感表达的同时,加以“理性控制和责任意识”,“在作品中将感性和理性交叉融合,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融入其中”[4]。在笔者看来,裘山山设问且做出解答的是,生活为什么充满龃龉与苦痛?是谁造成了人们的生命悲剧?面对生命之痛,普通人是如何逃避它、忘记它或是战胜它的?裘山山短篇小说结局的开放性与多义性也减轻了作者声音对读者思索的框定与限制,她更愿意让读者们以不同途径解读文本,将这份结合了自身人生觉悟的思索融进与灵魂、与他人、与世界的对话之中,渐而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念。裘山山借短篇小说传达她对善良、无私、奉献等人性闪光点的发掘与欣赏,而“小切口的痛感”这一书写特色,则使她这份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更加富有层次和饱含深意。正如她在《大雨倾盆》(2011)中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太脏了,需要雨水的冲洗,但“老天爷却不知道,这世界是那么不经洗,一冲刷,真相到处显露”[11],裘山山承认且深知肮脏的存在,她也在作品出表现出了残酷的真相,但她的真正目的绝非使读者感到悲伤绝望,而是期盼人们可以在痛感的磨砺中不断前行,期盼社会可以在无数小人物的努力下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