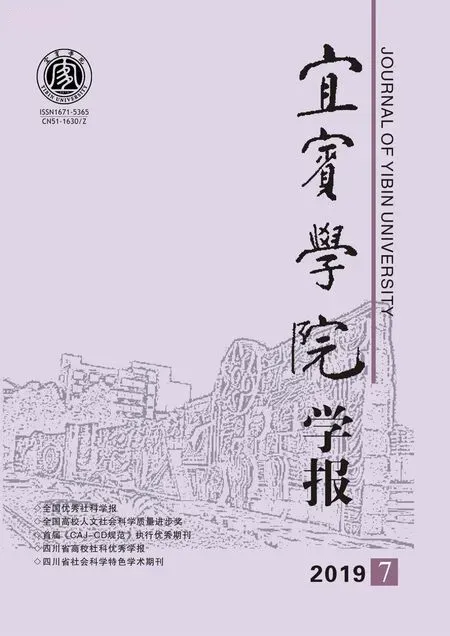裘山山的西藏情结和创作焦虑
左存文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人们普遍认为,军旅作家的创作有其特殊性,无论从主题还是从内容。但是对于作家本人来讲,首先他是一个作家,其次他才要面对“军旅”的限定;而对于“军旅”题材来讲,或者说对于军人及其生活来讲,要考虑主体的丰富性,即职业属性之外的人的复杂性以及职业生活之中的日常生活。这样,作品在普遍性的基础上表现出的特殊性才会独具魅力。以这个视角来看,裘山山军旅作家的身份配合西藏的地域书写,就更有独特性了。那么,她的西藏书写是如何表现出独特性的呢?这独特性之下的普遍性,她是如何处理的呢?当她要突破军旅题材,展现更为广阔的世界,或者深入挖掘军人及其生活的丰富性,甚至要书写历史与时代时,将会进行怎样的创作?
一、裘山山创作中西藏情结的特殊性
裘山山创作中的西藏情结,是被很多人关注到的,例如施战军、王甜、殷实的《裘山山的西藏情怀——评〈遥远的天堂〉(三题)》[1]124-126、韩骏的硕士学位论文《正确的写作——裘山山综论》[2]等。但因为她西藏题材中军旅主题的突出,使她的西藏情结发生了变异,有明显的特殊性。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情结并非作者自然而然地积累的内在经验,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体验式写作。也就是在主题先行的背景下,裘山山开始自己的西藏行走,虽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真实、深刻的体验,但是一些与主题联系不紧密甚至相背离的体验和思考就面临被舍弃的命运。如果说她早期作品《我在天堂等你》的叙述显示出作者对西藏军旅体验的“真实性”,其后出版的散文集《行走高原》则进一步证实了这部小说创作素材的直接来源。将小说《我在天堂等你》甚至后来的《河之影》和散文集《行走高原》结合起来看,其中“互文性”视角可以让读者发现其写作中“西藏情结”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她区别于类似马丽华这样长期在藏区生活的作家,更区别于西藏本土的作家。
就小说来看,《我在天堂等你》中的母亲白雪梅第一次到藏区(甘孜)时,地理因素带来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甘孜,真是无比美丽。碧绿的雅砻江蜿蜒流淌,无声无息。江两岸地形开阔,水草肥美。9月正是高原的黄金季节,蓝天白云之下,到处都可以看见黑色的牛群和白色的羊群在悠闲地吃草,还能听见牧民们悠扬的歌声。山上喇嘛寺的金色屋顶与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交相辉映,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还有那随处可见的经幡,被高原的风吹得猎猎作响,似乎没有绳子紧紧地系着,随时都可能化作五色的彩蝶,飞上天去”[3]192。这种直观体验在裘山山的散文集《行走高原》中,得到了更为全面的描述。又如小说中白雪梅登雀儿山时所看到的,“连绵不绝的雪岭冰峰,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天边,与蓝得刺目的天空镶接在一起,在阳光照耀下,整个世界晶莹剔透,如蓝色的玛瑙。这是怎样美丽的一个世界啊!你们可能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望无际的草原,可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雪山吗?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蓝天吗?你们见过一望无际的洁白和一望无际的纯蓝组成的世界吗?”[3]296-297如果说这种地理因素的“西藏情结”只是为了创作《我在天堂等你》而进行体验的收获的话,这种体验反而倒成了她一段时期内创作中绕不过去的“坎”。即使在多年以后的另一部小说《河之影》中,以地理因素为基本出发点的情结得到了延续,“成年后桃树去西藏,当她第一次在海拔五千多米的米拉山口看到猎猎飞舞的经幡时,不知怎么脑子里竟涌现出了儿时仰起脸来等待着空中飘下的传单。同样的蓝天,同样的五颜六色,同样的随风飘动,只是五色经幡是为了向上天诵经祈祷,而纷纷撒落的五色传单,却是为了表达更强硬的意志。不祈祷,只战斗。人类为什么会用这样鲜艳的色彩表达完全不一样的愿望呢?”[4]107
如此,当人们以“西藏情结”来看待裘山山的创作时,她的创作确实有了内在的脉络,只是这种脉络仅仅是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所带来的吗?显然,如果仅仅是这个程度,就不能成为“情结”了。对比她写的散文和小说,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小说中的有关西藏的情感表达和描写确实来自她的行走体验。比如她在纪实散文《沿着雪线走》中说到对西藏的情感,“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楚,那片土地上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我”[5]1。还有更为深入的表述,“但无论怎样,西藏,仍以它的魅力将我吸引,将我诱惑。它让我负重的灵魂得以喘息,让我世俗的身体得以沐浴。”[5]2小说《我在天堂等你》中,母亲白雪梅对西藏的感受如出一辙,“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心境下,西藏,惟有西藏,能让我们牵肠挂肚,能让我们忘记一切,或想起一切”[3]44。又比如,小说中的这段表述,“西藏它不仅仅是由大悲苦和大磨难形成的,它还充满了神圣、信仰和神秘。当你把头仰到不能再仰的时候,看到那绵延不绝与天相接的雪山时,你会觉得那分明是一颗颗永不言说的灵魂,你会期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座”[3]276。散文《沿着雪线走》也有相应的“互文”:“神奇的高原带着一种永恒的苍凉站在我的面前。这苍凉中蕴含着人类难以征服的力量,蕴含着我无法了解和进入的神秘。广袤的天空下,人和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天空和大地永远在目光的最尽头相逢,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博大和苍凉。”[5]1可以看出,在裘山山的文字中,其纪实的散文与虚构的小说形成了明显的对应,即作家创作经验的来源完全有迹可循。
裘山山在其散文中披露,其小说的素材来源大多是真实的故事,比如关于西藏军人的妻子形象,她坦言“在小说里多次写过西藏军人的妻子,《天天都有大月亮》里那个进藏离婚的妻子,《传说》里那个进藏找恋人的女人,《我讲最后一个故事》里那一群去探亲被困在招待所的家属,她们都是有真实原形的,都不是我杜撰的”[5]38。同样,为了塑造女兵形象,她专门去采访,这种采访是深入的,经常以月为单位而不是短短的几天,比如她提到其中有一次进藏,“此行一个月,我采访了七十多位女军人,她们给我讲了许许多多。但当我坐在书桌前打算为她们写点儿什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我带回的东西很少很少。最真实,最刻骨铭心的只有一点——对她们的崇敬和心疼”[5]159。虽然,裘山山为了创作而先进行体验,她对西藏的“归宿”感是发自内心的,并很自然地影响到她的创作,当作为一个体验者叙述的时候,她会说,“有许多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去了就会失望,但西藏却不会。它的诗意是与日月并存的,渗透在每一寸土地里”[5]155-156。当这种感受需要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她就会很自然地将其植入到小说人物中去,比如《我在天堂等你》中的欧战军,他对西藏的体验完全是裘山山式的,连加工的痕迹都不明显,“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这真正的天堂,欧战军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这辈子会和它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生命里,西藏的风是香的,西藏的水是甜的,西藏的雪是洁白无瑕的,西藏的山是顶天立地的”[3]31。在文学史上,为了写作而深入体验生活的例子举不胜举,裘山山显然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不同的是,西藏体验或者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形成了一种模式,即通过环境对比和遭受苦难来突出军人的牺牲精神,但是从外部来看,关于西藏土著的生活被屏蔽了;从内部看,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也被放弃了,这固然与她的军人身份相关,但是综观其创作历程,这种特殊的西藏情结反而倒成了一种枷锁。
二、裘山山创作的深层“结构”
与她西藏情结的特殊性相对应,裘山山在结构上也选取了相对应的策略,《我在天堂等你》以亲历过解放西藏的老军人的视角进行回忆,从而突出军人的职业精神;《河之影》以亲历者对童年的回忆为主线,儿童定位使作者更容易集中在特定的视角。两部小说都采取双向交叉叙述法,一章写“当前”,一章写回忆,如此循环往复,使回忆与“现实”不断穿插关照,这种叙述手法,或者说小说的结构,并非新颖,但其独有的魅力自“发明”以来不断在各时期作家中出现。加之裘山山要写特定的历史年代,用回忆的视角确实是很好的叙述策略。可以看出,她并未受到“隐身叙述”“作者已死”等理念的影响,而是采取有限制的全知全能的叙述方法,并突出小说的劝诫说理和抒情功能,即作者在讲故事的同时不断地跳出来介入到小说的叙述进程,直接加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例如从《我在天堂等你》这部长篇小说开始,就以评点主人公或直接插入的方式表达一些感悟和哲思,在讲述白雪梅选择从军之后,以话外音的方式反问:“难道人们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采取一个巨大的行动吗?尤其是女人”[3]64。随后又紧接着感慨,“人们往往喜欢在事情过去之后给它一个诗意的解释”[3]64。这一类叙述,有些是很容易识别的,有些则显得比较隐性,但依然可以看出作者说理意图与叙述进程的“脱节”,例如在写到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时,出现了这样的表述:“有些话,我是说我们心里珍藏着的那些表达感情的话,是应该对自己的亲人说出来的”[3]91。又比如白雪梅向她的六个孩子所说的话:“你们以你们的方式,让我在几十年后,终于尝到了被孩子们抛弃的滋味儿。这种抛弃不是以离别的方式出现的,而不以不理解不接受的方式。你们拒绝理解,而拒绝就是抛弃。”[3]92放在小说的语境中,这些话显得不合时宜,但是作者恰恰就通过这种方法来加入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让小说承载起“介入生活”的使命。
采用同样叙述方式的长篇小说《河之影》,在说理基础上“介入生活”的理念更为明显,“当下感”扑面而来。比如小说中说到主人公桃树去打酱油,作者随即将这个词放入当下的语境中,进行对照阐释:“今天‘打酱油’已经成了一个特定名词,其实早不是从前的‘打酱油’了,是买酱油”[4]41。这样一来,小说在叙述风格上,讲故事的感觉愈加明显,同时也能够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在《河之影》中,此手法比比皆是。例如写桃树和整栋楼的几个玩伴的日常活动,作者很自然地与当下进行类比:“最重要的还是晚饭后的这个聚会,每个孩子都会在大方桌上争相汇报自己一天来遇见的或听说的稀奇事,交换各自的新信息,还互相点评,功能相当于如今的微博或微信”[4]54。作者在叙述中对当下的“介入”,以幽默轻松的笔调与小说内容中的苦难形成强烈的对比,给读者一种新奇而又亲切的感受。
这种表面的结构其实有着深层的缘由,一来全是写“往事”,回忆的视角令读者感觉到亲切,这种亲切来自面对面谈心般的讲述语言,以及叙述者的在场感;二来回溯的方式容易让作品回到历史现场,展露岁月痕迹。将她的作品对照阅读,就发现裘山山在散文集《你看不见的风景》中对“岁月”的认识颇具哲理性,“岁月是什么?是一把镰刀,它一茬一茬地收割你的生命,先是童年,而后青年,而后中年,而后老年,而后连根拔起。它无比锋利,不管你的稻穗是大是小,不管你的年成是好是坏,时候一到就开镰,决不手软,无一例外。饱满的,不饱满的,统统都离开生命的田野堆进了大谷仓”[6]10。这种岁月感正是通过她小说中不断的回溯结构展现出来的,白雪梅在老年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桃树在中年的时候回顾自己的童年。更为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是用这种回溯方式?仅仅是作者为了突出岁月感吗?如果将这些作品结合起来读,会发现裘山山总是在思考人的精神原乡,这种精神原乡通常表现为地域上的故乡与人生中的童年。所以,交叉叙述的表面结构下,实际上隐藏着更为深层次的结构,即无论主人公有着怎样的经历,无论身处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他们都在以回溯的方式追寻精神原乡,虽然具体内容表现为不同的题材,这也是裘山山创作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无论是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尤其与《行走高原》对比阅读的情况下),还是其后的《河之影》,都植根于这个深层“结构”。
这种表现为深层“结构”的对于精神原乡的追寻,来自裘山山本人的生命体验。在散文集《行走高原》中,关于西藏的表述,她总是用到“故乡”这个词,这恰恰是《我在天堂等你》中主人公对西藏的定位。所以,将《行走高原》与《我在天堂等你》对读,是体验这一深层“结构”的最好方式。《我在天堂等你》中缺失的内容在《行走高原》中得到了补充,或者说在《行走高原》中西藏情结更为直观:“每每行走在渺无人烟、旷达无垠的高原,每每看见旷野中偶尔闪现的绿树和灌木,每每看见牛粪镶嵌在围墙上的藏民院落,每每看见猎猎飘扬在路上、河上、山顶上的五色经幡,甚至每每看见从山上横冲下来漫过公路的泥沙,我都会感到熟悉而又亲切,都会想起那句话: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有一个故乡”[5]2。正是为了创作《我在天堂等你》,作者曾多次深入藏区,即使在小说完成之后,仍然一次次地进藏,如她所感叹,“是的,西藏,它是我灵魂的故乡”[5]2。表面看来,这种对于故乡的体认,在《河之影》中有所转变,比如她写主人公桃树对于故乡的感受:“桃树喜欢一个地方,极少是因为那个地方漂亮,多半是因为那个地方亲切、熟悉、似曾相识”[4]118-119。这就涉及故乡的另一个元素——童年记忆了。所以她在《河之影》中写到“许多人寻找故乡,是渴望如婴儿般回到母体。”[4]119不难看出,《河之影》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至少在童年经历和内心体验上是,或许这也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内在动力,如盖格尔所认为的,“对于主体来说,那些童年时代的经验也许具有很重要的意味;它们有可能在人们的童年时代过去很久以后仍然发挥作用,给人们带来所有各种情绪上的纷扰不安;即使主体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些童年经验的意味,而且也根本没有赋予它们什么‘价值’,情况却仍然会是如此”[7]231。就深层的创作心理来说,无论对地域故乡的追问,还是对童年体验的追忆,都力足于对精神原乡的追寻,这也构成了裘山山这类小说、散文的深层“结构”。
三、裘山山的创作焦虑
正如前文所说,裘山山笔下对于西藏大多是地理特征的书写,用严酷的生存环境来衬托军人形象,抑或是西藏风景所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关于当地人的生活以及民族特性并没有出现。复杂的军人生活被剥离为严酷地理环境与责任担当相对比之下的悲壮与伟大,这就会呈现出小说平面化的特征。其实,深入探究,以《我在天堂等你》开始,裘山山的创作中存在着一种焦虑,即正能量主题之下人物心理的单一性,即便这种单一性在她的散文写作中得到了补充,但也无法让小说本身增色。所以,她这类小说有着浓厚的诗性抒情意味,尤其是“故乡”指向所表现出的西藏情结,使无论人物还是历史事件的悲壮显得有些轻柔。这种悲壮的“丰富性”只能通过阅读她的散文而获得,比如在《行走高原》中,说到西藏军人的牺牲,她用了一组数据:“从1995年到今年。1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35%,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32%。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约70%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5]81。将这种牺牲置身于全国的环境之中,就显得更加残酷,“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牺牲,他们也需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5]81。军人形象确实在她的笔下熠熠生辉。
或者说,正是为了突出西藏军人的英雄形象,小说《我在天堂等你》中,主人公的塑造也是典型的军人形象,但人的主体性放在了次要地位。《行走高原》的表述忽略则更为明显,实际上裘山山也深刻地体认到,“西藏女军人也是女人,她们也要做妻子,做母亲。而在西藏,这些普普通通的女人的愿望和职责,却要打上很深的高原印记,或者说,苦难的印记”[5]165。她在采访中注意到,“在那些女护士的房间里,我常发现她们用的往往都是最好的护肤品,什么奶液什么珍珠霜,在这上面从不吝惜钱,她们还时常向我的打听,现在哪种化妆品效果更好,或者内地又流行穿什么了。这使我感觉到她们也和普通女人一样有着对美的喜爱和追求”[5]162-163。裘山山在《行走高原》中记录了她遇到的很多女兵和军嫂,她发出这样的慨叹:“也许我无法为她们唱出英雄主义的高昂赞歌,但我将如实地记录下她们默默奉献的普通日子和平凡生活。我以为这种默默奉献的平凡和普通,比之轰轰烈烈的壮举更为不易,也更为感人”[5]159。但实际上《我在天堂等你》恰恰是英雄主义的赞歌,并没有将“普通日子”和“平凡生活”表现出来。这就涉及她写作的出发点,最终使得那些值得赞颂的被无限放大,而那些相对平凡甚至需要批判的就被舍弃了,导致其创作对历史现场的介入、对生活的介入、对现实的介入反而显得薄弱。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对女性歧视的苦恼,1985年9月5日裘山山写给她爸爸的信中说,“我要转业,他们说是人才不能放,要进创作组又嫌我是女的。据说报社想要我,也因为这一点没通过”[8]337。四十天之后,1985年10月15日,她写给爸爸、妈妈、姐姐的信中还是提到相同的境遇,“我进创作组的事再次告吹,仍是那位政治部主任不同意要女的”[8]340。其实这些才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生活经验,也是军人生活的另面存在,如果将其用于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肯定更为饱满。
如巴塔耶所说,“当文学努力描绘幸福的时候,它就搁浅了(它无法恢复一种丰富的声音)。它的目标不如说是阅读带来的快感;但这样的快感,不管它看起来如何,不能被直接地实现:一部小说必须让种种引发苦恼或笑声的困难或颓败运作起来,不然,阅读就会索然无味,给不出任何的快感”[9]76。裘山山在《我在天堂等你》中其实就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一味地赞颂军人形象时缺失的一些东西,尤其单独以职业视角出发而不是人性视角出发时,她偶尔会有所质疑,比如小说中最具叛逆精神的木鑫就直接反对欧战军的价值观,陈述一笔带过,可以看出作者其实是有着潜在的焦虑的,即如何忠实于自己的真实体验,如何带领读者进入真实的历史现场,如何真实地表现人性。
值得肯定的是,如果说《我在天堂等你》从主题到人物塑造显得扁平的话(即使也有表现人性的焦虑),那么在《河之影》中就显得丰富了起来,作者对现实的介入也变得明显,当然这种介入还时常表现为轻思考、轻发问,在深刻度和批判性上并未能完全表现出来,呈现出克制、迂回的创作特征。正如朱利安所发现的,“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将看到,中国表达法的本质(也是中国文章的特点)就是通过迂回保持言语‘从容委屈’:以与所指对象保持隐喻的距离的方式”[10]36。这固然与审美传统有关,也必然与具体的语境有关。所以裘山山的写作策略,便是以轻松而不乏幽默的叙述,以孩童的视角来写出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以间接地写出历史现场的荒诞感。整部的《河之影》,用她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就是“被欢乐强化的痛苦和怨恨会更强大,如同在油桶里浸泡过的麻绳,结实而不断。那就让它结实下去吧,牢牢捆住那样一个荒诞非正常的荒诞的年代”[4]239。从《我在天堂等你》到《河之影》,对比她的散文和书信,就会发现裘山山面对人性的丰富和时代之荒谬时深深的焦虑感。当然,她在这种焦虑中不断地突破自己,例如《春草》对军旅题材的突破;罪案小说集《死亡设置》对其固有小说形式的突破(虽然《事出有因》《正当防卫》等仍脱离不了军人形象)。
纵观其创作路径,军旅作家的标签对她有着持续但是隐性的束缚,如果抛开身份的羁绊,或许她的写作将更为丰富、深刻,“因为如果小说家用不同的方法看待自己,必将以不同的方法看待他的人物。这样一种崭新的辉煌灿烂的小说体系才会呈现”[11]153。就对历史现场的介入、对时代的介入、对人性深刻的介入来说,面对特定的主题和语境,正好构成了裘山山创作中最根本的焦虑。其实,透视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真正地书写时代所构成的“焦虑”具有普遍性。无论如何,对于作家来讲,要创作真正经典的作品,必须呈现出文学的绝对品质,“其作者必须为了他的‘时代’牺牲自己对不朽的追求,因为后者也只是一种抽象的幻想……正是凭着这一自我天赋,作家才能投身到其时代动态的最深处,达到这样一点:从那里,时代被推动着超越自身,到达另外的时代,而另一些作家则必须为这些时代‘播种’和‘收割’新的作品”[1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