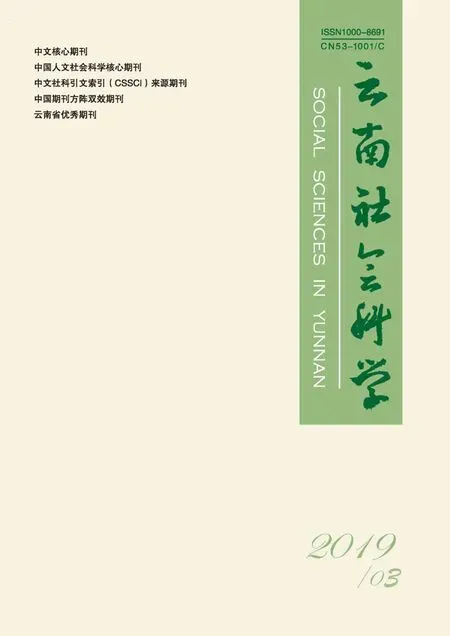有限性、可逆性、超越性
——中国当代城市小说的生产
高 志
新时期以来,随着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和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城市建设在各方面突飞猛进,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越来越明显,城市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构成相异于中国之前的任何时代,也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虽然,媒体和学者经常将中国的城市与西方城市比附,但它们在经济形态、政治基础、文化背景和伦理结构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城市文学的繁荣,“中国城市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才大量出现,并迅速在90年代形成汹涌澎湃的城市文学浪潮”①蒋述卓:《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综合场域中的城市小说具有独特的品格,它们折射出城市的变迁和中国城市小说独特性,那么城与乡、城与人、城市与未来、城市与文学是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在本文中予以梳理,并试图勾勒新时期以来城市小说的发展限度和未来面向。
一、乡村幽灵:革命、乡土、文化
城市小说是城市文学的一种类型,它的定义可参考城市文学,目前学界对城市文学有不同的界定,“一类是依据惯常的题材标准对城市文学进行定义,另一类则是突破题材的层面,从其他方面来对城市文学的特质进行界定。前者如:凡以写城市人、城市生活为主, 传出城市之风味、城市之意识的作品。”后者则“从审美、城市人身份、现代意识、都市意识、物化”②蒋述卓、王斌:《论城市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方面进行界定,对城市生活描写是反映论观念,这是“他者”视点,城市仅是故事发生、发展的客观场所;对城市景观价值和意识的凸显是城市小说的本体论观点,这是将城市作为主体来写,也就是城市精神的书写。迈克·克朗说:“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因此,问题不是如实描述城市或城市生活,而是描写城市和城市景观的意义。”①[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3页。笔者认为城市和文学是互相生产的关系,而不能仅仅用反映论或本体论来概括,应该将它们之间的互动生产的流动性作为城市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多以他者视角建构城市,城市是被动的客体。汉魏六朝时期出现的城市小说《洛阳珈蓝记》《西京杂记》,多以短篇传达教化理念;宋朝说话艺术的成熟催生了通俗小说的繁盛和宋元话本的诞生,“三言二拍”以善恶报应的道德说教为宗旨,神话、传奇和轮回为特征;勾栏等娱乐场所的诞生,青楼小说的繁盛,如《海上花列传》《九尾龟》等,成为中国狭邪小说的滥觞;明清世情小说的繁荣与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金瓶梅》《红楼梦》等家庭伦理小说书写城市人的生活与存在状态,《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幻小说,它们写人与城市以及上层统治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它们不是土地关系的反映,而是城市生产关系的表征。清末民初,讽刺小说、黑幕小说、儒林系列、谴责小说和政治小说等城市小说以救亡与启蒙为旨归,来审视城市人的表演和国家的存亡以及社会变迁。鸳鸯蝴蝶派等狭邪小说继承青楼小说的传统,融入现代理念和白话语言质素,拓展了世情小说的写作;五四时期城市小说被主流意识形态压制,鲁迅《伤逝》、郁达夫《南迁》《迷途的羔羊》、沈从文《八骏马》《绅士太太》、王统照《湖畔儿女》、老舍《骆驼样子》《赵子曰》等文化风俗小说,多在五四启蒙和救亡的背景下开展,城市和乡土被人为地进行等级划分,乡土处于中心位置,城市被搁置在边缘。“中国20世纪的文学主流就是乡土文学,城市文学只是作为一些若隐若现的片断,作为被主体排斥的边缘化的‘他者’偶尔浮出历史地表。”②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 》,《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在左翼文学中,城市小说突出阶级斗争的内核,革命加恋爱,无产阶级情感和小资情调有明显混杂情况,蒋光慈《短裤党》《少年漂泊者》等,茅盾《子夜》《第四病室》等小说探索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城市风景和生产关系是其小说的出发点。在红色经典中,城市小说则以革命和建设一体化历史建构为旨归,言说革命和建设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小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和“一代风流”系列等即建构了革命历史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合法性;《上海的早晨》书写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流程,《年青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为社会主义新人塑形,《我们夫妇之间》资本主义情调受到批判。这些小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但也遮蔽了小说的多元性,反用保罗·德曼的话,“洞见即盲视”。
新时期以来,城市小说突破了单一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书写模式,开启了城市小说的多种面向,但是城市小说仍处在艰难地探索和蜕变之中。城乡之间的差别较小,可以说,城市是乡土的微缩形式,“我们拥有广大的农村,城市中的人都有着乡土的根,我们都是农民或者农民的孩子。”③计文君:《想象中的城——城市文学的转向》,《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不同之处在于户口制度、粮食制度和文化制度,城市是权力的象征,“城市就是人类社会权力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最大限度的汇聚体”④[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页。。城市人群由企事业单位和小市民组成,城市的企事业人口多是解放后入城人员,乡村的文化、伦理道德和风俗顺理成章地侵入到城市的肌理之中,城市的生产关系依然有计划经济的残留。比如,北京的大院文化,大院的建制、格局、生活方式、等级体系和文化体系成为小说形式和内容的底色。王朔小说中大量对话的使用、痞子形象的塑造和颠覆革命话语的个人话语的重建皆是大院文化的表征,但是大院中的等级制度和风俗礼仪反映了乡村伦理关系,如《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中的家长制和礼节风俗。
城市与乡土密不可分,乡村的生育观念、人情关系、自给自足的经济和自私品格在城市中根深蒂固,这源于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混杂性,“‘城中村’、城市中的地区差等现象,表现出城市自身混杂的文化构成,设想某种单一的语言来表现城市,本身就是对城市空间的误读。”①张屏瑾:《城市中的文学空间:一种定义方式》,《文艺报》2018年1月24日。李佩甫《生命册》《羊的灯》《城的门》三部曲,以脱离乡土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叙说乡土对城市的纠缠,乡土的血缘伦理依然能够遥控城市中的新晋人群;城市的土著居民是小市民的主体,他们中一部分人种植城乡边缘地带的土地,维持的是乡土经济,有的则靠手工业和第三产业生存,自私、短见、妒忌和邻里互斗是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蜗居》《长恨歌》《启蒙年代》中的上海小巷弄堂中的居民以及居民文化,乡土文化气息浓厚。贾平凹《废都》以互文《金瓶梅》的形式传达了与乡土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堕落与颓废,既是传统知识分子被城市文明所阉割的表征,又体现了乡土培育的知识分子在城市无所适从而回归古典雅士生活的无奈和悲伤。
城市中的一系列制度严格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城市成为年青一代的梦想之地,他们只有通过招工、上大学和参军等单一途径挤进城市。他们以乡村视角审视城市,城市被他们赋予神秘、传奇和圣化的色彩,高晓声《陈焕生上城》等小说把城市高消费、卫生、稀见事物和文化等以启蒙的视角表现出来,传达支持现代化建设的意图。高晓生侧面反映了低层次城市的功能设置、管理和运行机制,在城市中,人起着螺丝钉的功能,铭刻着资本主义情调,人被社会悬隔,塑造的人物也是共名人物。作家王朔对革命的批判和对自由的向往,冲击了现代城市构建的秩序和文化,这里的秩序是指在革命现代性话语下建立的社会规则,而非建基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体系。
新时期以来,城市开始转型,计划经济主导下的城市逐渐走向市场经济。1994年,国企改革,“铁饭碗”被打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兼有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双重文化特征,城市在这方面更具典型性,乡村价值被重新发现并成为城建的重要参考,“乡村风景”“世外桃源”和“家庭农场”等词汇成为城市开发的招牌广告语。市场以利益为导向,劳动力、资本、知识、文化和地产等作为生产要素,人被禁锢在物、消费和虚拟影像的空间中,虚假与拟真是其主要特征,而实存的乡土风景和文化则作为记忆景象被唤醒。刘震云《手机》将北京放在城市封闭的空间,严守一的欺骗和说谎成为常态而导致心灵疲惫,乡村风景、故乡回忆和情感维系为城市中的身体提供了休养和医治创伤的良剂。严守一回归乡土是新时期城市发展中对乡土和纯情的呼唤,也是城市与乡土还未完全割裂的表征之一,亦是对乡土记忆的一次现实还乡。乡村对城市病疗伤功能书写源自于五四小说传统,例如:沈从文《三三》,郁达夫《南迁》等小说,“城市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在继承中不断强化旧传统,催生新传统,不断在文学观念与形式上锻造时代新质的过程”②葛永海:《论城市文学视域中的20世纪上海文学图景》,《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在西方社会,城市小说与乡土小说是两种不同的形态,巴尔扎克把《人间喜剧》分为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和乡土生活场景等,城市小说与乡土小说具有不同的主题、人物形塑、故事情节和叙事风格。而在中国小说中,新时期以来的城市小说与乡土小说有很多类似,这与中心话语和计划经济的一体化相吻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小说较为复杂,小说处于转型期,既有阶级话语的遗留,也有新话语的萌芽和发展迹象;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中,城市小说(《班主任》《伤痕》《将军吟》《乔厂长上任记》《新星》《龙年档案》),延续了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以传统的善恶道德、家庭伦理、血缘关系接续和劳动神圣等观念返回“十七年文学”革命意识形态,这些观念中混杂着乡土伦理和民间话语因子,它们通过乡土人性观弥合“文革”造成的断裂。“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城市小说接续了这一思路,刘醒龙《分享艰难》、谈歌《大厂》《车间》、何申《信访办主任》、关仁山《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周梅森《绝对权力》和陆天明《苍天在上》,把城市改革的艰难和困境通过企事业单位的问题表现出来,人情和利益成为腐化根本。作者以善恶二元对立观念生硬划分敌对双方,阶级观浓厚,其中关涉职工下岗和困难问题的处理方法,以主旋律的方式呼吁“分享艰难”,这是革命现代性的延伸和发展。
二、本体建构:多元、窄化、牢笼
马泰卡林内斯库提出现代性的5种面向:现代性、先锋性、后现代、颓废和媚俗。在《上海摩登》一书中,李欧梵从印刷、电影书刊传媒、作家、身体和城市、颓废和时代角度重新思考现代城市小说的写作与解读。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可用来透视新时期中心话语的形成,新时期以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发展促进新生产关系的形成,监控和教化由硬性的制度控制和阶级划分模式转化为文化霸权。这不仅仅是新的监控形式,更是新意识形态的反馈,“工农兵想要领导城市文化、支配城市空间和生活时,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文化,农村的生产工作经验在城市工作中是捉襟见肘的。”①李屹:《从北平到北京:〈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城市接管史与反思》,《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文学的生产、发表、出版和评奖制度都会影响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从解放区土改小说开始,城市小说创作一度中断,即使有少量的城市小说,它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人性、爱情、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等个体意识成为创作的禁忌,“城市与资本主义生活的标签间建立一种无法抹除的联系”②俞敏华:《 “本土化”之城与“想象”之城——当前城市文学的城市品格及写作期待》,《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此时城市书写者和作品会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彻底地清理,《我们夫妇之间》《红豆》《青春之歌》等小说触犯了这些禁忌而遭到批判或勒令修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变迁使城市小说获得了新的增长点。
城市地理文化特征在城市小说中是可见的存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城市重新被小说所铭刻。城市名片效应借助地理标志和地域风俗文化,城市的交通、规制、居民生活、风俗、语言、文化和气候成为小说的叙事要素,它们承载了个人的体验和意识形态的信息,“文学的地域属性就是其本根属性,根的意蕴一旦在文学的时空里展开,它就会成为一种符号和喻指,是生命在此展开与合拢的证明和叙事,而这种本根属性的深浅与长短,又成了都市文学安生立命的基点和撑持,真相与常态就是这样展现开来的,在这种基质里,永恒性与深厚才有可能得以被揭示、被还原。”③梁凤莲:《关于血脉——谈都市文学的地域属性》,参见杨宏海:《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陆文夫《美食家》对苏州民间名吃的关注,以寻根的形式发掘地理文化信息,作者表面上规避了中心话语,而本质上是彰显了诞生的新话语。从这一层面上讲,作者重新落入新意识形态的窠臼,这不仅仅是个别作家的认知,而是一种普遍的认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重新被肯定,消费不仅是生产的要求,也是对解放以来人民生活物资匮乏的补充。阿城《棋王》王一生对吃食的精细和专注,莫言《酒国》中“酒国”专门设置研究人肉制作的机构和培训学校,在其中,生产、制作和销售一体化,并按照现代流水线模式严格生产制度。北京作家邓友梅《那五》《烟壶》等京城世情小说,从文化入手以历史视角审视城市以及人的变迁,通过小说的细枝末节传达出北京城的规制、文化、礼仪和历史;天津作家冯骥才《神鞭》《三寸金莲》等文化历史小说极具津门特色,对尚武和畸形性心理进行了文化批判。这些作家以文化去撬开坚硬的意识形态的铁门,文化被有意识的作为工具使用,但并不能建构永恒的自然生态城市。文化应该与城市共生共长,是城市生命的异形同体,而非纪念碑式的历史陈旧物,“这一文化必须立足于现实的表象,必须是正面积极且具有建构性特征,而非可供观赏的、留恋的或需加以保护的博物馆式的存在。换言之,文化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非遗址或文物。”④徐勇:《文化视域中的城市文学写作》,《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第4期。所以,应该彰显新生的城市文化和一部分有生命力的历史文化,去建构城市新文化。
通俗小说是城市小说的一种类型。20世纪80年代,城市通俗小说呼应“文化热”思潮,文化反思成为小说书写的一个重要面向,作家从旧文化衰落入手,探源文化运行机制,研究国民和社会生命力衰弱的根本原因,旨归在重新形塑民族文化,这是从全球化视野寻找民族文化认同路径的尝试。作家承载了文化重建的任务,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再次苏醒,这是五四知识分子启蒙和救亡使命的延续,也是对长期不被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接受的否定和再出发。《文化与世界》丛书、文化热、寻根小说等现象皆是知识分子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表征,这离不开对知识分子地位的重新认定。周恩来总理将知识分子重新划归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从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身份被祛除,他们由被改造对象转为国家的主人翁,其主体功能再次被唤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取代商品经济,改革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强,消费驱动生产,市场分配生产要素,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移,消费者成为上帝,文艺作品不再主动承担教育功能,媚俗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特色,文学审美批判性减弱。因此,1993年,王晓明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城市小说也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状况,“日常生活美学”切入城市小说本体建构之途,这种理论 “不仅在于‘感性’重新回归人的日常生活语境,而且在回归日常生活之际,‘感性’在理论上被理解为当代日常生活中人的现实情感、生活动机以及具体生活满足的自主实现,亦即人的日常生活行动本身。”①王德胜:《美学的改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0页。在文学思潮史上,这一现象被命名为“新写实主义”,刘震云《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烦恼人生》《不谈爱情》,方方的《风景》《树下》等皆为经典作品。它们成为城市书写的主力,“新现实主义”处理的是城市与人的关系,人的日常生活与理想关系,贫穷与未来、性格与城市、城市历史和发展问题,小说展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不再出现,底层小人物成为小说主体,底层人物的生存及其困境折射出城市和社会的现状与历史变迁。比如方方的《风景》将视点对准武汉棚户区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变迁,通过一个家庭反映出社会基层群落的生态——贫穷、酗酒、帮会、暴力、苦力、子女众多、虐待、女性地位低下,城市社会底层的现实通过自然主义手法精雕细刻描绘出来。城市建基在基层民众屈辱的生存基础上,底层群体的血泪铸就城市发展史,这种左拉式书写再现了城市别样的风景,曲折表现了作者的启蒙批判精神,“零度写作”背后是批判和怜悯的热度。池莉《烦恼人生》对武汉轧钢厂工人印家厚一日充满烦恼琐事的生活进行书写,武汉的轮渡、幼儿园、早起赶车、迟到等详细信息,武汉的地理特征、工厂的监控机制、幼儿园的教育和家庭关系被客观描述出来,这种日常书写填补了左翼文学书写的空白,也超越了文学典型化模式,无产阶级文学新的书写方向被确立下来。
城市小说的日常化书写处理的是社会的微观层面,新写实小说着重城市底层民众的日常琐事书写,人与城融为一体。城市小市民的纯真爱情、亲情和友情被日常琐事和利益所纠缠,城市成为市民爱憎的载体;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雄心和激情被失望、暴力和困境所缠绕,《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太阳出世》等书写城市里的人相互利用和欺诈,将城市书写成藏污纳垢之所。武汉的作家着重描写小市民的卑微和弱肉强食的蚁民生活(棚户区和历史上的汉正街是底层和妓女居住地),作家触及到城市的腠理:居民的言行、穿着打扮、风俗礼仪和吃喝玩乐;上海作家王安忆书写上海弄堂蹩脚的生活,小市民的排外、精打细算、注重生活细节、情感细腻和虚荣性格特征被作为上海的文化名片。《好姆妈》《长恨歌》记录了城市格局、机构设置、社会制度、人物处境和社会历史的变迁,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杂糅状态表现出来。社会边缘的小资生活与处于中心的社会主义生活并行不悖,王琦瑶的人生经历即是明证。这在铁凝《玫瑰门》中也有深入的表现,司漪纹与街道主任罗大妈互相影响,她以优雅的小资情调征服了罗大妈,并且在城市中不断地改变生活策略,献媚、参加社会活动和生活才能完成身份再建构,在新的城市文化中保持自由的生存状态。上海作家《繁花》则以另类方式记录和留存了地方文化,吴方言、街道上的家长里短、偷鸡摸狗、日常聊天、交友和工作,共同再现了上海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小说继承了《九尾龟》《海上花列传》方言叙事的特长,并通过地理文化特征、人物特色和文化氛围彰显上海品格,它采用日常化书写模式,背离了宏观史诗的建构,真正回归小说本源。
城市小说日常生活书写的作家多为女性,彰显了女性独特的性别优长:细腻、温情和感觉敏锐。女性作家将个人体验和城市生活结合起来,将生活由边缘地位提携到中心位置,以个人生活替代传奇的英雄叙事,填补当代文学史的空白,重构新意识形态话语。但是,日常生活书写带有先天的不足,它淹没在日常琐事之中,文学批判和启蒙意义逐渐消逝,并且对客观现实的精细描摹缩减了抒情质素,城市成为丑恶和冰冷的代名词,被认定为无意义生产的场所。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现代主义写作模式下的城市日常生活体现的是对意义深度迷恋追寻的生命悲凉之重,那么,后现代主义写作模式下的城市日常生活体现的是意义解构后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一个是略带悲剧风格,一个是略带喜剧风格。”①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89页。但其批判力度难以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提并论。
莫言曾书写了高密东北乡的复杂现状:英雄与土匪、开放与猥琐、光荣与卑鄙、锦衣与肮脏以及太平与内乱。城市的藏污纳垢特征与民间社会类似,莫言以虚拟的手法建构了酒国世界,生产专业化,而其运行是以利益为目的,人性与人情被现代城市所删除,制度、秩序、管理和科研等现代文明形成一套“吃人”的文化工程。莫言描绘自然被城市文明摧毁的现实,反思和批判了现代文明的极端性,在这一层面上讲,城市与工业文明是同位词;现代生产要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并迫使劳动力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刺激了消费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生产力持续发展。在消费社会中,感性泛滥,壮美的现代城市建筑、强烈的消费欲望、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奇遇的期待成为城市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邱华栋《教授》,朱文《我爱美元》,池莉《小姐,你早》,阎连科《风雅颂》,贾平凹《废都》,安妮宝贝《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卫慧《上海宝贝》《象卫慧一样疯狂》,陈染《私人生活》《嘴唇里的阳光》,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皆是这方面的典型。
全球化拓展了作家对城市的想象力,并超越城市的物理规制,将城乡从对立的两极中解放出来,把全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作家从个人体验和全球经验来消费其被革命叙事搁置的剩余想象力。在远离小市民生活的高消费群体的书写中,符号化的消费品(高档名牌消费品、酒店、机场)、极端化的图像、极端个人行为(暴力、吸毒)成为颓废书写的主流,“人的物欲受到市场功利的强烈影响。人的私欲潜伏于国际品牌、都市建筑、时尚用品等琐碎的物象中,通过作家文本中琳琅满目的物象的呈现和罗列强烈冲击阅读者的感观 , 并以此传达个体精神在物欲的冲撞下产生的焦虑和困顿。”②王美芸:《物象景观中的国际想象——新世纪上海城市文学一种主题与叙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小说超越具体的城市存在,虚拟的城市只是现代社会的高度浓缩,他的书写受到港澳台和欧美影片的影响,大陆外的文艺资源和社会为作家想象力的展开提供素材,所以有些作品远离大陆城市生活和文化,例如美女作家的作品。青春写作更加极端化,它们主要包括复古和现代作品,作品中城市只是固定概念和场所的代名词,本身没有任何社会文化意义,人物悬隔于具体的城市之外,他们之间也不再是互动关系,如郭敬明《幻城》,周宪曾指出现代城市与审美之间的批判关系,“无论是韦伯所说的审美‘救赎’,还是海德格尔所钟情的‘诗意的栖居’,或是列费弗尔对‘游戏城’的向往,或是福柯所主张的‘生存美学’等,都隐含着某种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深刻批判。”③周宪:《从文学规训到文化批判》,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三、生产城市:可逆性、文化传承、虚拟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进了城市的迅速发展,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特色小镇建设方案为城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的保留做了预见性的指导。2018年3月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了“逆城镇化”构想,“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④习近平:《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新华网,2018年3月7日。“城乡融合”成为城镇化建设的目标,这是从整体上考虑城乡的互动以及辩证地建构城乡关系的尝试。城镇化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将为城市文学的书写提供更多的素材,并将拓展作者的认知,无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是乡镇升格为卫星城市,乡土文化都会大量存在于现代城市,乡土异形的城市作品也会层出不迭,孟繁华曾预言:“中国伟大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产生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这条道路上。”⑤孟繁华:《建构时期的中国城市文学—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4年2期。在小城镇或特色小镇建设中,小城镇会成为书写的重要对象,贾平凹《带灯》书写镇干部情感和处理乡里日常琐事文人情怀,小说分为山野、风清和幽灵三部,这些题名可看出作者和带灯的自然情怀,这是知识分子内心纯洁的表征,也是独立心境空间的隐喻。虽然作品中有工厂的经营纠纷、上访事件和镇干部的争斗,但是带灯的自然情怀是书眼。小城镇成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它兼具乡村和城市的双重特点,虽然《带灯》中的小城镇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它是特色小城镇的滥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逆城镇化”与费孝通的“乡村衰败”观点有类似之处,提出人才向下流动的指导意见,会促进小城镇成为城市书写的重要客体。
未来的城市小说离不开文化的积淀。如果割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城市小说将会是无根之木和无源之水,“传统乡土与现代城市交杂缠绕的写作状态,出现在城市文学书写的诸多作品中,其所秉持的审美原则既不是城市标准,也非乡土经验,而是二者之中既取舍又融通,从而形成新的文化衡量。”①郭海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书写的一种读法》,《文艺争鸣》2015年第5期。传统质素的保留和拓展是小说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当代城市小说的窄化与文化断裂有直接关系,五四直接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五四以后的城市小说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城市或作为乡村叙事的点缀,如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小说;城市或作为现代文明的批判对象出现,如老舍的北京世俗文化小说。即使直接以大都市上海为场景的新感觉派小说,也远离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城市上层社会的声色犬马生活场景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感觉为纽带,通过声光电色的蒙太奇描述,书写现代城市娱乐风景和电影片段。这与传统文化和乡土风景的断裂,影响了新感觉派的受众范围。他们的小说风格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女作家的写作。作品中的主人公以高档酒店、购物中心和商场为活动场所,将名牌衣服、箱包、香烟和毒品作为生活的必需品,物欲和情欲成为商品。虽然赤裸裸的情欲描写和物欲书写赢得了市场,但是小说与文化和传统的隔绝降低了它的格调和品格,“消费主义文化共同完成了对当代城市文化的重铸与改造,并形成了新的占主流地位的以消费为表征的城市文化形态,与传统的城市文化构成了一种断裂关系。”②杜云南:《城市·消费·文学·欲望——城市文学的叙事特征》,《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2期。因此,在2001年遭到主流媒体的封杀。从文化传承来看,新感觉派与传统断裂的原因在于上海的迅速崛起,全球化背景下的上海与国内其他城市是悬殊的两个世界。20世纪90年代的美女作家与新感觉派作品风格相似,都是对物欲和情欲的地理书写,具有一脉相承的颓废风格,研究者对此有不同声音,有学者否定其颓废情调,有研究者认同其个人书写。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土社会不可分割,只有资源和人才的双向流动才可能避免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效应与竭矿的悲剧,乡村与城市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城市会促进乡村的城镇化,乡村也会将自然和文化输入城市,城市新移民将会促进城市新文明的形成,“这些人改变了城市原有的生活状态,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多种因素的综合,正在形成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新文明。”③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因此,城市书写资源会更加丰富,思路更加宽阔,人与城市关系也会更复杂。
网络文学是城市小说发展的未来面向之一。随着网络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多元化类型将成为未来写作趋势。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瞬间性和消费性刺激了网络文学的迅速发展,从早期的榕树下,到起点中文网、纵横中文网、17K小说网、红袖添香和百度阅读等网络平台的建立为网络小说的诞生提供了场所,城市小说获得了质的飞跃,突破了纸质出版的限制;无纸化、即时化、电子化、易携带性和互动性等特点使它赢得了读者市场,网络文学想象和多元化的特征适应了年轻受众的需求,《上海宝贝》《悟空传》《蜀山奇侠传》《花千骨》《步步惊心》《青云志》《九州缥缈录》《鬼吹灯》《盗墓笔记》《心理罪》《琅琊榜》《芈月传》《欢乐颂》和《翻译官》等经典作品受到追捧。网络小说的作者借助城市生活、工作和写作的便捷条件,借鉴古典和现代文学资源,发挥想象力的巨大能量,建构了复杂而深幽的网络文学世界,“巨大的文本内容以及边写边上网而未能完成的文本内容,由于无法共时性地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从而完全成为一种想象性的存在,具有极强的虚拟性,由此所带来的感受,也呈现出与阅读书本完全不同的特性。”④蒋述卓:《城市文学:21世纪文学空间的新展望》,《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经典网络小说典型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用古典资源中的故事原型或人物展开想象力,填补历史细部的空白,通过善恶道德评价标准,深刻剖析复杂的人性,并以情节和智斗获得市场份额,如《芈月传》《鬼吹灯》;或者对古代经典进行改编,以现代思想改编古典或神话人物,如《悟空传》《新聊斋志异》《我的邻居是妖怪》等。二是,书写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小说,如《欢乐颂》《琅琊榜》《心理罪》等,它们以城市为背景,以特殊职业为兴趣元,调动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网络文学以市场为中心,生产、传播和销售等环节的赢利分成模式不可避免地驱使作者在情节、人物设置和资源选择上出现雷同化现象,并且追求情节曲折、炫富催情叙述和人物极端化书写,快节奏发表速度和大部头的系列小说成为收藏和点击率的标准和常见模型,“网络写手在创作时不得不考虑到读者的感受,读者的‘送花’、‘灌水’、‘拍砖’、‘打赏’、跟帖、点击率、订阅量等就是对他们作品创作的直接参与和评论,进而决定他们的稿酬、签约和他们的作品能否出版……我们不难理解他们的作品的媚俗化倾向。”①徐从辉:《网络文本逻辑与想象城市的方法——以70后、8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为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虽然网络小说多诞生在城市,但是城市在小说中的价值并不很突出,原因在于网络小说的多元化特点,以及主要受市场决定而窄化的创作范围及主题——通俗类小说获得市场认可,而网络上严肃文学的传播受到很大限制。事实上,很多网站对诗歌、剧本和散文都不欢迎,主要也在于很少有读者感兴趣,小说成为创作的主要门类。但仅就小说来说,小说的书写面太窄,形式不受市场欢迎,且城市的小说品类和数量都很少,类型化突出,主要集中在仙侠奇幻类、励志成长类、鬼怪盗墓类、侦探心理类、宫廷争斗类、职场勾心斗角类等类型中。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取决于市场的奖惩制度,但是市场的盲目性和无理性影响了网络文学的全面发展。因此,解决网络小说发展的困境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用力:第一,对市场加以适当调控,建立第三方评价系统;第二,网络文学应该获取公益资助或国家资助,如此一来,城市小说将会更加多元化,奇侠幻想、宫廷、鬼神和霸道总裁等文学样式将被更加多元化的局面取代,网络小说落地性指日可待;第三,重视新技术的发展。随着城市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虚拟时空成为小说书写的方向之一。这里的“虚拟空间”指游戏世界,《魔兽世界》《我的世界》《饥饿游戏》《生化危机》《征途》《贪玩蓝月》等大型游戏的出现,并随着虚拟现实设备VR眼镜和VR眼镜配套搭载的反馈系统的更新升级,虚拟时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会大幅度缩小,虚拟中的城市也会突破实体城市的样态,其结构和组成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对虚拟空间的书写将进一步解放人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漫无边际的幻想,而是建基于技术的基础上,人与城市、人的感觉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拟真化,会带来城市小说跨时代的变迁。刘慈欣《三体》是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先驱,但还没有涉及虚拟空间的书写,好莱坞电影《头号玩家》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以科幻的方式叙述拟真化的世界,游戏成为现实城市世界不可或缺的补充,游戏者为此变卖房产、生活贫穷、失业,或获得新的工作岗位以及致富,在此层面上,游戏创造了新的城市,相反亦然,“当文学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②[美]理查德·利罕著:《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结 语
新时期以来,城市小说在逃离一元化叙事的牢笼时,获得了多元发展的机遇,因此,城市小说被赋予反拨意识形态的意义,并正在重建新的意识形态,它由边缘走向中心;城市小说书写日常生活、风俗文化和城市历史变迁,城市被贴上地理、经济和文化的标签,城市小说发展成为地域名片。但是城市并没有斩断与文化传统、革命历史和乡土的联系,它仍旧承载着这些历史的重担,并且受到制度、意识形态、评奖制度和出版传播的限制,城市小说逐渐窄化和表面化。本文突破固定的城市书写的线性关系,将城市和小说视为可逆和互动的关系,“在文学与城市的关系中,城市文学之于城市,也绝非只有‘反映’、‘再现’ 一种单纯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系。”③张鸿声:《 “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这种观念有助于文学想象中城市的生产和小说的深化,如此,城市小说才有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