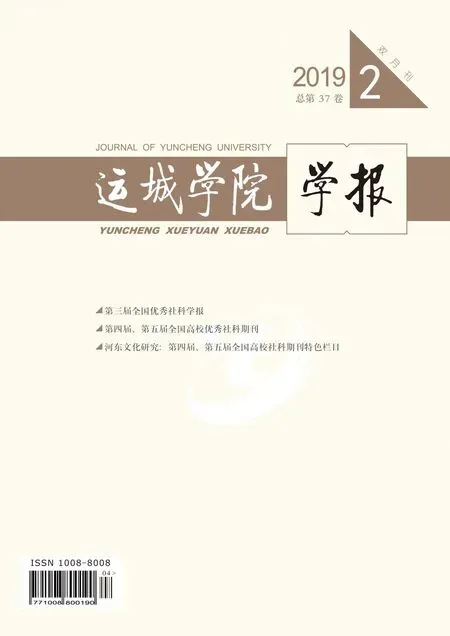追寻“自我”:《倾城之恋》细读及重释(下)
袁 少 冲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二、心灵更深层碰撞中“自我”的松动
有了海滩上那种忘我的笑打嬉戏,有了流苏吃醋中对自己的紧张与在意,范柳原才能在电话里对她说出“我爱你”。[注]虽然采取了一种不那么严肃郑重的表达方式,但其本意应该是颇为郑重的。因为,柳原之前曾给流苏这样表达过,可见并不是随便说说。面对柳原的问题“你爱我么?”流苏采用了一种躲闪的方式,答道:“你早该知道了。我为什么上香港来?”此话涵义丰富。首先,在中国的传统里,爱与不爱的言词很少直白地表达,“爱”不同于“love”常常挂在嘴边,一般要用含蓄的方式表达——这本身就是“中国情调”的一部分。其次,回答这个问题,流苏颇为难,非是没有,但她的爱里羼杂了太多沉重的东西,尤其当她初赴香港之时,对柳原确乎仅有些许好感,所以若直接说“爱”她心虚。范柳原则直接否定她,“流苏,你不爱我”,并以他对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参悟来说明。
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1]187
此段有关诗经的阐释是一个重要细节。其一,说明柳原确实对中国东西感兴趣,否则一个洋派富商为何对如此古旧的诗歌念念不忘,且有自己的体会与理解。其二,柳原希望从更深层面和流苏做情感沟通。其三,他的理解含着对其半生命运沉浮的感伤:降世即为私生子、无身份地位、流落异国他乡、长年孤苦无依、四处颠沛流离,父亲之死反成他命运折转的机缘,从此锦衣玉食、众人阿谀、风光无限——父母在(非孤儿)反而孤苦,父母亡(真孤儿)反倒光鲜。在如此大贱大贵、大悲大喜中感慨命运捉弄、见惯世态炎凉,方才对诗歌有人生大事皆受外界无名伟力之支配,个体之我卑微渺小、不由自主的感怀。这种解读契不契合诗经的原意是一回事,然终归是一种充满鲜活体验的深思,是从心底的伤痛里涌出的真话、真情。何况,在柳原看来此解读,加之于流苏何尝没有道理。因为,流苏在白公馆的境遇他早已通过徐太太得知[注]范柳原设局邀流苏赴港之前,相必早就做足了功课。况且,流苏的乖舛主要源于外在处境,不像人内在的性情心理那样难以明了。;流苏来香港见他有寻求经济、生活依靠的因素,他亦不难明白;流苏不能敞开心门了无牵挂地谈一场灵魂之恋,以至于连他的话也几乎不懂的情形,他早已察觉;因而,流苏不能放下自己的诸多原因,岂能由她个人来掌控。
然而,正如之前大多数谈话一样,柳原的许多话更为真心,生命的体悟也更加深沉,更多祈求精神的交流、心与心的懂得,而流苏的应对往往浮于表面、切己功利,致使不断地答非所问。如同这次,流苏的回应竟是气恼地说:“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想必柳原听到此话,只怕会良久愕然。她的理由仅仅就切近的事做日常化的平面理解:“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1]187若仅从流苏的角度看,这话也算在理,但从柳原的立场上说,则要让他摸不着头脑——其实柳原委实想让流苏对其内心的深层感受有深入知晓和理解,却每每被流苏从深处拉起,落在世俗生活的表层,难有心神的沟通。柳原还是坚持用自己的逻辑发问:“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主么?”依然包含着深思人生、细究人性的维度。而流苏的回答既反驳又闪躲,亦是多数女人善用的方式:“你若真的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
范柳原于深夜里,致电给隔壁的流苏,就恋爱中人而言是件浪漫的事,之所以这么做,其前提是两人在近日的相处中有了亲密举动,关系更近了一层。不想,却依然是这种自说自话的对话方式。终于,在沮丧、气恼等多重情绪驱使下,柳原断不客气地回嘴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1]187这属于那类情急之下口不择言的真话,此中的信息有:其一,柳原心目中婚姻的前提是两者之间的深挚情感与懂得;其二,他不接受毫无感情的婚姻,但细细斟酌之下,他却并未排斥婚姻本身;其三,一段毫无感情的婚姻,不仅对男方不公平,也对女方不公平,表明柳原身上还一些现代色彩的平等意识;其四,他察觉到流苏和他在一起,想要婚姻却又不释放真情,也许流苏眼里的婚姻只是生活(经济上的)与生理(肉体上的),这才愤而称之为“长期的卖淫”。
范柳原虽然一时生气,却并不真的失望,况且,他说这样的气恼之言,也是因为关系到了可以拌嘴争吵的程度。所以,情绪平复后很快又来电话,心平气和地想和流苏聊聊月亮,可惜一个巴掌拍不响。之后便是,次日清晨因柳原一句“你别枉担了这个(范太太的)虚名”,流苏认为他要逼自己做情妇。纵然范柳原有让她做情妇的意思,但二者对情妇的理解也是错位的:流苏认定的情妇注定将是无名无分的玩物;柳原则很可能是把情妇当作二人深入培养情感的一个阶段,以他对通过一个中国女人来定位、重寻自我的热望来看,若这个情妇真得走到他心里,未必没有婚姻的可能。至少我觉得范柳原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堵死这条路,因为他所追寻的“自我”最终也只能在婚姻、家庭中获得。所以,两者之间的问题主要不是结婚与不结婚的问题,而是在何种心灵相知的程度下方能进入婚姻的问题。双方基于自身的种种考虑,相互之间僵持不下。
流苏当然不满足于情妇地位。作为情妇经济上、生活上已然无虞,然而无名分地位,既不稳固又不光彩,仍然没有确定、完整的自我。白流苏重回上海之举一方面是沮丧,另一方面也是以退为进,小小地将他一军以示抗议,属于中国女人“应付人的学识”的一部分。
其实,流苏也开始注意到自己经常听不懂柳原,但她并没有特别重视,觉得“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她心目中的婚姻,生活、过日子是首要的,故以为反正“找房子,置家具,雇佣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得多”。所以,听不懂话只是个“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我认为二者对孰大孰小的判断刚好错位:流苏认为生活是大事、衣食住行是大事,精神的触碰交流是小事,该认识既从自己痛彻的境遇中得来,也带有旧式“父母之命”婚姻中灵魂交流较为稀薄的特征;而范柳原对流苏的所求,几乎都在精神的层面,他想让流苏懂他,懂到比自己还要更懂的程度,因而听不懂他的话绝非无关紧要,而是真真切切的大事。可惜,流苏始终不明白柳原对精神方面的要求,故而免不了继续误解柳原,包括这次赌气返沪。
回到与自己恩断义绝的白公馆,是一个消极的争取,孤身之时也冷静、沉淀一下,换一种心境品味自己、琢磨柳原。流苏更清晰了,她不是没有对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折服”,只是太不纯粹,所附载的“家庭的压力”、生活的着落足以使那些“风仪与魅力”黯淡无光。所以,要把这点“爱”说出来,不免难以为情。
流苏回沪像是情人间的一场别扭,和好后加深了亲密,所以才会有亲吻的举动,而且“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这是海滩笑打之后难得的一次真情流露,双方都卸了架子、放下负累。不过,这些真情还不能达到柳原“我要你懂我”的程度,所以流苏的地位看起来像个情妇。而她也继续误解着柳原,虽则,了解与理解的比例越来越多。比如,柳原到码头接流苏时说过“你是医我的药”,她就仍未懂柳原对她的希冀。
在巴而顿道亲密相处一周里,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流苏开始“取悦于柳原”了。原因一方面是两人距离拉近、真情互生;另一方面可能缘于柳原买的房子让她有了久违的家的感觉。在这里,有个人的自主空间[注]流苏回到上海的白公馆,虽说表面上仍有自己的房间,但哥嫂的冷眼热潮、亲朋街坊的闲言碎语,早就无孔不入地困扰着她。如坐针毡的白公馆再不是她的家,在那里她再无自主的“我”了。,有听凭使唤的女佣,有经济上的安全,可以任由她“在那蒲公英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
“取悦”既说明两人在感情天平上有主动被动、有利不利的差别,也说明两人之间还有刻意、故作的成分。然而,情感的磨合期,谁又会没有呢?该阶段流苏是会“吃力”,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流苏要顺着柳原的心意去观察、思考,站在柳原的角度去体悟,她需要并放下了自己。故此,虽然是短暂的一周,流苏对柳原熟悉、懂得却大有进步。付出总有回报,这就是“吃力”的收获。而柳原的“古怪”源于他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人生,源于他惯于轻浮浪荡的生活现状与不甘空虚孤独的心灵求索之间的矛盾。在流苏面前的“更古怪”、不同于此前的绅士模样,一方面表明两人关系亲密的程度,亦说明柳原的确“动了真感情”。当一个人把对方真正视为“自己人”的时候,才会逐渐显露他最真实、最任性、最恣意的面目。[注]张爱玲便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全集5》第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柳原的愈发“古怪”,很可能是故意要在流苏身上为此前的孤苦凄凉、情感创伤找撒娇般的补偿。
即便如此,在迈向婚姻的阶梯上,他们只是又向上攀登了几级而已,至于要达到双方一直坚守的那种终极期待,尚且遥遥无期。流苏是有了暂时的家、暂时的经济依靠,所以她是可以从她固守的“围城”中走出去,尝试着进入柳原的心门,从他的立场和需要上,去顺从着思考、感受。不愿尝试心灵的贴近自然不会有真的懂得,可麻烦的是,就算愿意也未必真的能懂——真爱之难、人性之顽,就在于此!两人中西新旧之间生活经验、阅历背景、价值判断、思维方式的巨大沟壑,仅靠主观意愿就能轻易抹平么?
流苏“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在这里她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1]193。由此看来,流苏对自己的定位还是一个较为传统的贤妻良母,是那种中国旧式家庭里较优秀的类型。她能管住自己不堕入“姘戏子,抽鸦片”的姨太太之路,也表明她在那个新旧过渡、伦理崩散的“夹缝”时代里,确乎代表了中国传统中较好的一面。流苏的这些“好”,属于柳原所认可的“中国传统”,所以才屡屡称她为“真正的中国女人”,对此,柳原是在乎、欣赏的,是真正吸引他的东西。因为,贤妻良母所代表的中国,以及贤妻良母为一个家庭所营造的温馨与祥和,能让长久孑然一身、孤伶漂泊的柳原找到家的稳定感,获得亲人在侧的温暖感,所以“一来就高兴”——毕竟男人也会有希望被宠着的心理,更何况内心始终孤苦的柳原。
然而,在贤妻良母之外,范柳原更想要的还有一个心心相印的伴侣——比自己都懂他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是他心灵的后盾,是他找寻(属于中国的)“自我”基点与坐标。这个期待中有更深一层的精神需求,明显超出了流苏(依据旧传统的惯常认识)对(贤妻良母式)夫妻关系中心灵相知程度的理解。整部《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在他浪荡公子的外表下,对精神上的高追求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求,为此主动出击、费尽心思。[注]因为在这种精神追求中有“自我”在。从这个角度似乎说范柳原“自私”亦无不可,只不过不是那种简单意义上的自私,在柳原的自私里要复杂得多。
不过,他要求的境界似乎过于理想化,如何才能实现呢?所以,还是得有“倾城”。
三、“倾城”中自我的释放与突围
突如其来的“倾城”之战,成了白流苏、范柳原恋爱的催化剂。
飞机、流弹、高射炮、屋檐上被击落的沙石、满地的玻璃屑、花园里被炸的大坑……所有前所未见的景象营造着万分的恐怖,“流苏知道是没命了,谁知还活着……人是震糊涂了”。此时此刻,“流苏也想到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有没有被击沉”。在生命危急时刻马上想到柳原,说明了他在流苏心中的分量,几乎已是最亲的人了。并且,她想到柳原“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所谓“隔世”,是相比之前的生活而言的,因为“现在的这一段,与她的过去毫不相干”。现在与过去对流苏而言仿佛是两种人生,因为柳原才截然不同。过去的人生结尾是被抛弃放逐、“六亲无靠”,抓住范柳原之后苦心经营、曲折辗转才有了现在的生活。虽说尚无婚姻的名分并不牢靠,但过去、现在这“隔”着的两“世”之间,哪个好些哪个坏些呢?
在过去,流苏初嫁遗少公子,丈夫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她屡遭家暴后无奈离婚;回到白公馆,身边财产被三哥四哥拿去“做金子,做股票”,踢腾干净后自己反成没落旧家的包袱,被扫地出门,不念丝毫骨肉亲情。现在的流苏,至少有一个对她“动了真感情”的人,愿意并已经给了她“经济上的安全”,使她“根本用不着为了钱操心”,这个暂时的家毕竟是属于她自己的一方天空。所以,当门铃作响流苏开门后“见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紧紧的搂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搂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扑,把头磕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1]195。这“倾城”的炮火中,生命朝不保夕的威胁中,柳原还要冒险回来,随那些头等舱乘客待在浅水湾饭店岂非更安全?其实,当流苏想到柳原感觉恍若隔世之时,柳原又何尝没思念过她。他在父母去世以后,何曾有过如此亲近的人?流苏身上有他所感受到的故国之思,中国式的低头、含蓄、罗曼蒂克构成了吸引他的“中国(女人)”特质;虽然她常常误解自己的话,也不时有一些花巧心思,但流苏毕竟善良、正派,富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她心里真的渐渐有了他;至于在巴而顿道有了“家”以后,虽仅有“一个礼拜的爱”,虽然还未到“我要你懂的我”的程度,但已经是有生以来最顺遂其心意,最能任凭他古怪、任性的人了,他品尝到一个中国女人中国式的爱,体会到一些“家”的温暖与温馨。[注]中国传统的女性,婚姻常由父母做主,因而婚前的夫妇情感较为稀薄。不过,一旦结婚之后,妻子在“夫为妻纲”的文化规训下,一般会站在夫家的角度去思考、说话、做事,想夫之所想、忧夫之所忧。流苏虽然亦新亦旧,但新观念、新做派毕竟有限,在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条件下,那种传统为妻之道的影响仍在——即所谓“应付人的学识”。因而,她在于柳原的僵持中固守自己可能更多是新观念的作用,不过,一旦过了这个坎,当流苏决定放下之时,她也会放的彻底,其立场会迅速切换到柳原的轨道。再加上经过了“一个礼拜的爱”,二者有了肉体关系,这一点对他们亦非常重要,尤其是流苏。因为传统观念中,有了肌肤之亲,她大体上就应该是柳原的人了。这种惯性心理,会促使流苏更快、更大程度地走向柳原。
在这样的“倾城”中,他们之前尚且有限的情感就已经使对方成为自己最大的依赖、最重的牵挂、最暖的安慰了——比较级成了最高级。[注]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前提,即他们俩那个最大的共同点——都是被命运、被家庭抛逐的处于“夹缝”之中孤苦的弃人。对流苏而言,柳原已经走到她心里,只是在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之时,内心多少还残留些许微妙的抗拒。在柳原来说,流苏让他一见钟情,只是自己浪荡的背后还有苛刻的情感需求,考虑到二者文化背景、人生经历上的差距,这种要求其实相当理想化,然而他骑虎难下、不得不固守这苛刻——因为有“自己(我)”在。
再总结一遍:在流苏与柳原之间,柳原总处于比较有利、主动的一面,道理就在他手中的经济优势,他只需要追寻精神上的“自我”。流苏有许多算计与心思,因为她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所以要寻求的“自我”里有太过沉重的经济包袱。前者类似于锦上添花,有所得最好,无所得大不了仍旧这么浪荡漂泊地孤独下去;后者则像雪中求炭,没有退路,所以患得患失、审慎拘谨。范柳原给流苏在巴而顿道买的房子、置办的一切,暂时地为流苏解了经济上的忧虑,所以两人在肉体、情感上的距离近了一大步。而“倾城”这种极端情境,则把财富、家境等身外之物远远击退,毕竟生命危在旦夕的当口,金钱何用?富贵何用?唯有最亲的人、最真的情、最深的牵挂,才令人觉得无比珍贵。物质的层面,两者被拉平,至少重要性急剧退却;而精神的层面,两者被拉近,且重要性大大凸显。所以,当流苏看到柳原冒险回来找她的一刹那,当柳原看到流苏开门后孩子似的扑到他身上、紧紧搂住他手臂的一刹那,淑女的身份、适当的矜持、策略性抗拒、固守的期待、他(柳原)要的懂得……仿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两个“夹缝”时代中的弃人,你在我身边,我也在你身边,天下虽大,你只有我,我也只有你。也就从这一刻起,流苏才彻底放下了自己,把她的心贴在柳原的身上;柳原也不再坚持他梦幻般的“懂我”的标准,这个怀里的女人让他已经感受到的那些中国式“自我”的影子,难道还不足够么?
由此,才能解释他们到浅水湾饭店后,于子弹穿梭中,流苏突然懊悔柳原在她身边,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弹子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得干净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1]197
流苏、柳原的此情此境,颇合乎中国传统里夫妻同心、同命相连的感觉了。“倾城”消解了他们各自心理“围城”的意义,让其此前交往中累积的相知捅破了窗户纸,爆发式地倾泻出来,在这段时光完成了心灵上的高度契合。战事“倾城”的极端情境,也使双方在面对自己唯一牵挂之时,既促激了人性的升华,又降低了各自顽守的标准,挤掉了两人关系中复杂的水分(如算计、经济、得失等),将情感的真实更加纯粹地表露出来,让他们各自清晰地看到、听到、触摸到,在放下过往执念中找寻到“自己(我)”。
于是,他们才开始少言寡语,“从前他们坐一截子汽车,也有一席话,现在走上几十里的路,反而无话可说了。偶然有一句话,说了一半,对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没有往下说的必要”[1]197。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当看到海滩,是流苏先提到“那堵墙……”,说明她此前虽句句误解,现在体验了“倾城”,已经有不同的领悟。当柳原感慨“也没去看看”之时,流苏顺着他说“算了吧”;当流苏要给柳原拿大衣,他也不再绅士,由着她来拿——用不着那么见外、客气了。
劫后的香港,他们的生活回到较为原始的吃喝拉撒、自食其力的状态,即张爱玲所谓的“饮食男女”——“每天只顾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因为早年吃过苦,所以各种粗活应付自如;流苏虽初次做菜,毕竟有传统女性持家有方的基因,上手飞快。如此情状荡涤了生活中被身份、地位、财富、文明所包装的一切矫饰,回归到柴米油盐、饮食男女最基本的生活日常。此时,那些文明世界里、文明人的、上等的、文雅的种种本领都失去了意义,反倒是之前看似无用的生存(活)技能成了必需。花巧的心机、游戏,在此不仅不必要,还那么不合时宜,只剩下情感的相扶相慰,心灵的体贴、交融。
于是,流苏才又想到浅水湾附近的“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也想到当初柳原所说的那句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1]180。在这么多外在、内在条件的催动下,此时的流苏才触摸到柳原感怀的深层,才对生命的无常,对现代文明华美之下的虚无、幻灭有所体悟。
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1]199
流苏方明白这个她在乎、又在乎她的人,才是一切里最可宝贵的,所以要“拥抱着他”,而柳原也立即接收到了她的讯息,“握住她的手”。
原子个人(主义)是整个西方现代文化的基础之一,个人私利及利益的最大化是资本主义预设的重要前提。但个人主义毕竟也有缺陷,比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夫妻之间本质上是非个人主义的,是和谐共处、灵魂相通的,是建立在超越个人主义的伦理基础之上的。相互之间的精神依赖与物质互助,比个人主义更利于在严酷、极端环境中存活。这其中,也渗透着张爱玲本人对西方文明的某种反思和对“自我”的些许领悟。
所以,“倾城”这个意外和偶然,摧毁了现代文明的华美外衣,短暂地给他们俩制造了一种更贴近传统中国的夫妻生活情境,在其中,流苏如鱼得水地发挥着她掌持家务、细心呵护等属于“真正的中国女人”的特长,柳原也在这短暂的中国式家庭生活中品味到了他要寻找的安详与完整。也正因为太过偶然,这个“倾城之恋”故事的结局不是团圆而是“苍凉”[注]张爱玲说她“更喜欢苍凉”,并说苍凉“有更深长的回味……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是一种启示”,被研究者视为张氏独特的美学。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全集5》第9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因为又有多少人心的沟壑、隔膜无法用荒诞的“倾城”来破除。[注]“倾城”的荒诞性在于,用毁灭世界的方式成就自己。不过,这毕竟是在小说里。现实中,即便“倾城”亦未必成就个人。比如张爱玲自己,她所处的乱世,与胡兰成之间亦有属于她自己的“倾城之恋”(抗战胜利、汪伪倒台、上海光复,对胡兰成而言不就是“倾城”甚至“倾国”么?),但结局却空余萎谢心伤。
此时,与萨黑夷妮公主的相遇,似乎纯粹是为了拿她与流苏作对比。花瓶般的外表、文雅的调情应酬、曼妙的舞姿、尊贵的身份,都在“倾城”中褪去了多彩光鲜的外壳,返归虚无。在生命中最需要的爱情、婚姻、家庭和“自我”里,简单、朴素、真挚的日常互助、身心扶持更为本质。在洋化(西化)的萨黑夷妮与中国化的流苏之间,这样的对比,意味深长而明确,柳原自觉地选择了中国,惟在这里,他才感到“自我”的归宿。
事已至此,结婚已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这当然并不是说,两人真能事事心有灵犀,当柳原在去登结婚启事的路上有感而发,又提到“‘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的时候,流苏还敏感地误会他要打退堂鼓。但这些小小的误解,无关大体、已不在意。
总之,《倾城之恋》主要描写了两个自我意识觉醒的弃人,都被抛置在中西新旧混杂、畸形、过渡的“夹缝”时代,失去或没有“自我”,他们需要去重新找寻真正的“自我”,并且,这种追寻要通过恋爱、婚姻、家庭的方式来实现。所以,小说表面上描写了两个自私男女互相算计、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的爱情游戏,实际更深层的主题则是对“自我”的确证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