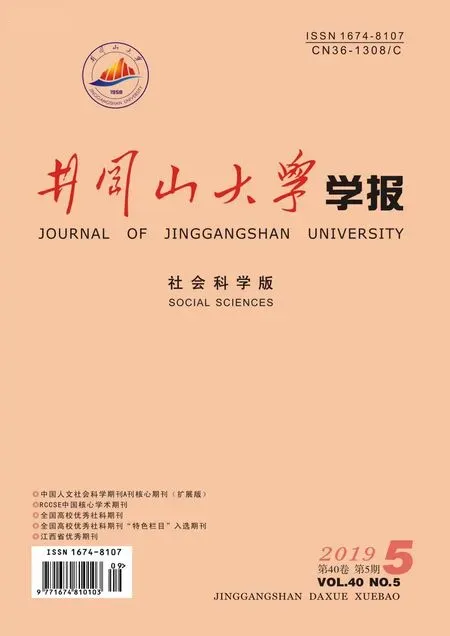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比较
向玉乔,秦彤阳
(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伦理学是一门关于人事的学问。比起窥视宇宙的奥秘,它更渴求人生的圭臬。它不像逻辑、概念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它既端坐在步辇之上,却也在陋巷兜游闲逛。以伦理学为视角,时空结构、万物肌理都在人生场域中聚结,彷佛古树的根须全都向着人类的生活延伸。幸福问题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不仅是最早生长出的问题,也是最贴近地面的问题。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最早地建构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幸福理论。自此,幸福之歌咏不绝,余音袅袅。到了十九世纪初的英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勃兴,功利主义学派又在幸福的乐谱上敲下了一记重音。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习惯性地将亚里士多德与密尔进行理性主义与感性主义的派别划分;近年来又盛行将规范伦理学划分为道义论、功利论和美德伦理学。故而,关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比较往往是求异不求同。这不仅割裂了两者幸福观内涵的相关性,也忽视了两者幸福观建构的同构性,导致人们对幸福的理解片面化、刻板化、浅层化和视域窄化。人们用心倾听便会发觉,两者之间的交流并非像斧钺碰撞般刺耳,而是如琴筝和鸣般悠扬。
一、幸福:作为欲求的目的
人的任何行为都有其目的,目的是构成行为必不可少的要素。无目的的行为只能被描述为一个客观结果。比如我们经常说某事是一个“意外”,就是指这件事的客观结果在主事人(Agent)的主观意图、目的之外。行为的目的有时是明晰的,有时则会模糊一些,但无论如何都会有一个指向。人有千万种行为,也就有千万种目的。比如治疗的目的是健康,理财的目的是富裕,游戏的目的是快乐。但有没有一种最终的目的,它是其他一切目的之目的,所有我们欲求的目的都是它的手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每种选择与实践,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1](P1-2)而有一种最高的善是一切善事物的目的,这个终极目的就是“幸福”(εν'δαιμονiα)。健康、富裕和快乐的目的都是为了幸福。关于这一问题,密尔同样认为只因其自身而被欲求的目的乃是 “幸福”(Happiness),“幸福是值得欲求的目的,而且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其他事物如果说也是值得欲求,那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 ”[2](P42)因此,亚里士多德与密尔实际上都将“幸福”放置在价值序列的终端。把幸福作为欲求的终极目的、最高价值,这是二者进行体系建构的共同前提和基础。
通过 “手段—目的—目的之目的”的层层递进,最终是要达至所有美好的事物中最美好的“幸福”。由此便确立了意义世界的秩序。既然幸福被赋予了终极目的的形式,那么幸福又具有怎样的内涵与特性呢? 古希腊语当中的“目的”(τε'λο ),是指活动的终点或已完成的事物。因此,目的也就意味着完善。 “完善”(τε'λειο )一词的词根正是“目的”。而一个有目的的、自身完善的事物,也就是“自足”的。所以幸福本身就内含了目的性、完善性和自足性。亚里士多德还划分了三种层次的目的,第一种是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目的;第二种是既因自身又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目的;第三种是始终因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目的。第一种目的实际上就是手段;第二种目的朝向最高的目的,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第三种目的就是幸福。根据亚氏对目的的层次划分,每一层次的目的都应该比上一层次具有更高的目的性、完善性和自足性,幸福则具有最高的目的性、完善性和自足性。由此构成一条完整的目的链。
密尔的幸福观与亚氏的幸福观都描绘了一幅“百川汇海”的图景,在立论上颇为相似,但也存在论证上的不同。而这个需要论证的部分恰恰是以幸福为目的的幸福观所遭受诘难的主要方面。即每个人都是特殊的存在,有着各自的成长环境、习惯和信仰,每个人都可以就什么是最值得欲求的目的发表自己的见解。人们完全可以指出生活中有这样那样的目的与幸福处在同等的序列、甚至凌驾其上。面对“每一片不同的树叶”,亚里士多德与密尔都肯定有一些东西“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这样,一方面维护了幸福的最高地位,一方面又使林林总总的欲求得到了肯定。但是亚里士多德对那种“既是手段、又是目的”的东西是从先天本性上论证的。密尔则是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加以论证的,认为这种同时具有手段价值和目的价值的东西并不是因其先天的、自然而然的特性而被划分出来的,它们原本只是手段,但却是实现最高目的的必要手段,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人们便从心理上将它们视为了目的本身。密尔还引入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来进一步说明,“幸福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整体,所以这些东西便是幸福的组成部分。 ”[2](P45)密尔之所以肯定了除了幸福之外值得欲求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觉得部分总是包含在整体之中的。
幸福观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幸福的地位问题。人人都知道幸福是值得欲求的,但是幸福在众多值得欲求的事物中有何种意义上的优先性、在我们人类整个价值观念体系中又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这是幸福论伦理学家必须说明的问题。
二、幸福与人性的关联
《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指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 ”[1](P2)或者说“万物都是向善的。”然而,这里的“万物”并不是指宇宙万物,而是指人为构建的万物。也就是说,人所构建的一切事物都以善为目的,自然事物则没有善恶。这也是为什么“εν'δαιμονι'α”不能直接翻译成“flourishing”,因为即使是一株鹭草、一墙藤葛也可以“繁荣兴旺”。亚里士多德将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做出了区分,使得他的幸福观打上了人的烙印。幸福是属人的,是为人类所独有的。因此,研究幸福就必须研究人的本性,幸福就是人性的自我实现。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把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称为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功利主义的创立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的开篇讲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3](P58)由于边沁将人性理解为“趋乐避苦”,所以边沁认为“幸福”就等于“快乐和避免痛苦”。这种快乐主义的幸福观后来常常成为功利主义遭到批驳和攻讦的主要目标。实际上,对于感性主义幸福观的批评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伊壁鸠鲁。边沁和伊壁鸠鲁的主张也常常被揶揄为“猪的快乐”。密尔是功利主义最著名的辩护人,为了让功利主义远离这些讥讽,密尔在 《功利主义》中首先就着手修正了边沁自然倾向的人性论,“人们之所以感到,将伊壁鸠鲁派的生活比作禽兽的生活是一种贬抑,正是因为禽兽的快乐是说明不了人类的幸福概念的。 ”[2](P9)密尔将人类的幸福与禽兽的快乐区分开来,从而将 “happiness”和“pleasure”也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给他的幸福观渲染了人本主义色彩。
亚里士多德指出,生命的活动是人和动植物所共有的。但是植物的活动是营养和生长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是感觉的活动;幸福则是人的特殊活动,即“理性”(λγο )的活动。亚氏进而将人的生活划分为三种:享乐的生活、荣誉的生活、沉思的生活。享乐的生活是动物式的生活,由于贪图享受意味着人向自然本能屈服,所以也被叫做奴性的生活;荣誉的生活因其实现方式具有外在依赖性,所以不是完善自足的;只有沉思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沉思就是灵魂的合乎理性的活动。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者,人性内含着理性,幸福必须合乎理性。密尔同样认为,人是一种拥有 “更高级官能”(faculties more elevated)的动物,“理智的快乐、感情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感的快乐所具有的价值要远高于单纯感官的快乐。 ”[2](P10)密尔不认同边沁所说的快乐只有“量”的差别,而把“质”的概念引入功利主义,区分了高等快乐 (higher pleasures)和低等快乐(lower pleasures)。可见,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都是奠定在人性论的基石之上的。幸福是人的专属,而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分出来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理性,密尔认为是高级官能。亚里士多德教导人们去过一种理性的沉思生活,密尔则指出高等快乐的生活更值得追求。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证明遵循抽象人性的生活、贬抑自然本性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也曾自觉“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翠羽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在李清照看来,精神充实的乐趣是要远远超过歌舞女色斗狗走马那些低级趣味的。关于这一问题,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内在善与外在善,指出理性生活的无所依赖性和完满自足性正是幸福的本质内涵,而其他的生活要么依赖于物质的满足、要么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都不是逍遥无待的。密尔则仍是给出了一种经验论的解释,认为凡是经历过两种快乐并且对它们熟悉了解的人们,都会显著地偏好那种能够运用他们的高级官能的生存方式,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
人之性之所以异于禽兽之性,除了人有理性之外,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还是政治(城邦)动物。“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4](P7)(νθρωπο φσει πολιτικνον)。结合《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这句话对于实现人的幸福有三重意涵:一是指人的本性是趋向于公共生活的,离群索居、茕茕孑立的人不可能幸福;二是指人的本性是趋向于政治生活的,因为人只有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之中才能有实现幸福的环境;三是指由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所以才有可能组成社会,幸福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运用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一致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城邦的善。这给我们追寻幸福最大的启示就是:个人幸福应该与公众幸福相统一,并且“尽管这种善于个人和于城邦是同样的,城邦的善却是所要获得和保持的更重要、更完满的善。 ”[1](P4)这里蕴含了公众幸福要大于个人幸福的倾向。而边沁却认为类似的说法没有意义,“共同体是个虚构体,由那些被认为可以说构成其成员的个人组成。 ”[3](P59)因此,共同体的利益就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只要每个人都努力追求自身幸福的最大化,自然就增进了公众幸福。基于此,人们普遍认为功利主义是一门利己主义的学说。所以,密尔在为功利主义的辩护中修正了边沁所主张的把公众幸福等同于个人幸福的简单加总,提出了“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 ”[2](P14)密尔还认为当个人幸福与公众幸福发生矛盾时,应当按照 “最大幸福原则”(greatesthappiness principle)选择公众幸福,从而肯定了自我牺牲的道德合理性。密尔为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公众幸福所寻找到的稳固基础是 “人类的社会感情”(social feelings of mankind)。这点与亚氏将公众幸福的实现诉诸于人的社会本性是有相似之处的。与以往的论证不同的是,密尔这次没有再从经验主义出发,他反而认为任何经验的、人为创造的道德都会随着人类理智的进步而被分析、被消解。人会关心他人,乃在于人类的社会感情。既然亚里士多德与密尔都认为人具有社会性,那么要实现人的幸福就必须研究社会。所以亚里士多德没有对伦理学和政治学加以严格的界定,并认为这两种学问都是关于善的学问,“城邦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政治和善的[永久]制度。 ”[4](P121)密尔则将幸福问题引向社会建制,要求通过法律和社会的安排、教育和舆论的塑造,将个人幸福与公众幸福、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牢不可破又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
三、德——福关系问题
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问题,也是幸福论伦理学家必须解答的难题。道德对幸福是一种促进还是阻碍?德福是否一致?历来众说纷纭。然而,在道义论与功利论长期对峙的背景下,人们似乎已经普遍认为遵守道德义务与追寻个人幸福之间存在张力。道义论的核心理念是“界限”,而功利论的核心理念是“最大化”。但我们应当看到的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德福相悖”的指导下生活,时代正在呼唤一种新的幸福理念。随着近年来美德伦理学的勃兴,美德伦理学与道义论、义务论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潮,德福关系问题有了新的研究思路。但当前学术界著述最丰的仍然是关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比较研究。对此,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指出:“尽管我还没有发现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路来阐释密尔的尝试,但我相信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5](P4)本文尝试论证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亚里士多德与密尔都抱持一种“德福一致”的德性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现幸福的特殊活动就是合乎“德性”(α'ρετη')的实现活动。 德性是实现幸福的必要路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本性抑或说人的灵魂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理性和非理性。理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指引我们成长为追光者;而非理性则处处反抗、遮蔽着理性,引诱我们堕落为夜行人。但是非理性并不是全然不顾理性的规劝的,它有一部分“既有理性,又有非理性”。所谓德性,就是合乎理性。理性的德性被称为“理智德性”,非理性的德性被称为“伦理德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幸福就是让理性和非理性都合乎德性的调节和规范。在密尔的幸福思想中,“德性”(virtue)同样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功利主义的反对者们经常出于道德的原因而认为幸福并不是唯一值得欲求的目的。密尔则提出德性作为幸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虽然本身也值得欲求,但仍然是内含于幸福之中的。密尔之所以主张“德性是促进幸福的首要条件”,是因为爱好德性与爱好钱权名利不同,对于后者的追求常常导致“损人利己”的情况发生;然而追寻德性是“专门利人”的,因此德性能为其他社会成员带来更大的福利,与“最大幸福原则”最为相符。纵然亚里士多德与密尔对德性的论说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们都认为德性对于实现幸福乃是必要且首要的。
幸福之实现不是水到渠成的,不像我们生老病死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幸福”(εν'δαιμονι'α),并不是指一种品质,而是指一种实现活动。酣睡之人并不因身处梦乡就失去了他的品质,但睡眠是一种静止状态而非活动状态,所以睡梦中的人不能说是幸福的。灾厄之徒并不因遭遇不幸就失去了实现幸福的品质,但这种品质只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所以不能说是幸福的。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品质与实现、德性与德行实际上是相统一的,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又是一种德行论的幸福观。虽然亚里士多德用“实现活动”将幸福引向实践,但过于强调本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充溢却不利于实践之花的培育。因为一个行为的构成不只有行为的目的,也有行为的结果,培养好的行为是需要社会和他人给予反馈的。然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好的行为本身就是奖赏。 ”[6](P116)德行本身就是幸福,这使得德行缺少生长的土壤,容易风干脆折。考虑到那些意志薄弱、易受诱惑、无法信赖的人,教导他们“德性即幸福”似乎是苍白无力的。对此,密尔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让德性与快乐、痛苦联系起来,“我们唯有将行善与快乐相联结,将作恶与痛苦相联结,指明行善中自然含有的快乐以及作恶中自然含有的痛苦,并把这一点灌输到这种人的经验中,使他彻底了解这一点,才能使他的意志向善,而等到向善的意志根深蒂固之后,起作用时就根本不会再想到什么快乐和痛苦。 ”[2](P49)密尔意识到了人们心理习惯养成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目标在现实层面上更加可能。而密尔的幸福观由于强调快乐与痛苦的感受,这就难以回答诸如诺齐克(Robert Nozick)提出的“体验机难题”,但是如果吸收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 “实现活动”的观点,就足以解答仅仅是沉浸在体验机制造的欢乐中的人为什么不幸福了。二者幸福观的互补之处在这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唯有将幸福的动机与幸福的后果相联系、幸福的感受与幸福的实践相结合,才能搭建起通往幸福的通衢。
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德性与幸福的一致性,即“德福一致”。不过亚氏更注重意愿的选择,认为德性在于正确的选择。选择必须出于意愿,是经过预先的考虑、推理,再将德性运用于实践来获得幸福。而功利主义是一种后果主义,密尔更倾向只有获得幸福之后才能彰明德性。前者主张 “合乎德性的就是幸福的”,是“以德统福”;后者主张“促进幸福的就是德性的”,是“以福统德”。虽然两者的理论路线不同,但最终都是指向“德福一致”,如果在此基础上可以熔铸两家、形塑新脉,那么德福的一致性将变得更加牢不可破。
四、余论
幸福之道不远人。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都是围绕目的论、人性论、德性论来展开和铺陈的。尽管两者的立场看似泾渭分明,但是幸福观的建构却条理相通。亚里士多德与密尔将伦理学作为一门幸福学来研究,并建构了完整的体系。但是二者的幸福观仍然存在各自的不足与偏失,在现代面临着不同的困境。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引发的最大争议是:他对于幸福的观点似乎前后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具体是指《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十卷不太契合全书的整体思想: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将沉思置于德性之上,作为最高等的实现活动、第一好的幸福。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意见,引发了“涵盖论”(Inclusivism)与“理智论”(Intellectualism)之争。涵盖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是各种善的综合,是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的统一;理智论则认为幸福就是指沉思,沉思是最大的幸福。实际上,与密尔区分高等快乐与低等快乐相似,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也对幸福做出了等级划分。亚氏认为人类最高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也就是神性)的实现活动,即沉思。这种说法单独来看似乎是融贯的,但如果我们将其放在亚里士多德的整个理论大厦中,一种巨大的张力便横亘眼前了。“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头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4](P9)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究竟是引导我们成为一位遁世的、理智的、沉思的神,还是一个入世的、伦理的、实践的人?抑或是旨在让我们寻求一种玄妙的中道?
密尔的幸福观也充斥着暧昧与纠缠。密尔先是重申了“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的感性主义幸福观,然而这更像是一种口头协定。如果说幸福是一种个人的感受,那么高等快乐的设置、自我牺牲的肯定无疑又把人引导到某种规则中去。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建立在“行为者本人的幸福”之上,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则是建立在“全体相关人员的幸福”之上。虽然是出于对功利主义的辩护,但未免有些用力过猛。以多数人的利益为核心再搭配上少数人的牺牲,这不仅是托克维尔 “多数人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的温床,也是罗尔斯的“正义”(justice)之箭所要瞄准的靶心。
哲学比较最重要的是 “让来自不同传统或具有不同风格的哲学观点进行合作式对话、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7]我们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进行比较,力图揭示幸福的各个维度,以及各个维度之间的联系与张力,最终达到一种视域的融合。要研究幸福问题,就要先认识到幸福是全人类的普遍欲求。“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建构一种幸福观,都是幸福之普遍性的一种反映,不可依据不同的派系、门头就圈定各种各样的幸福观、分而治之。从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的同构性当中,可以得出幸福的三个普遍特性:首先,幸福是目的善,区别于手段善;其次,幸福是属人的,区别于动物、植物,也区别于神;最后,幸福与德性是一致的,区别于有德无福和有福无德的论调。
对二者的幸福观进行比较研究,对我们树立正确幸福观有借鉴价值。当代幸福观的建构面临着诸多难题。当下有很多人染上了精神的流行病,他们拜金、利己、耽于享乐。他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赚尽可能多的钱,他们的活动就是一团无法浇熄的激情,他们自私、冷漠,公众的苦乐与他们毫无干系。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宁愿失去理智、失去尊严、失去道德也要追寻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难道是为了他们口中所说的“幸福生活”吗?
在多数人的幸福观已经被歪曲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与密尔的幸福观比较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二者的幸福观对我们追求幸福至少有如下启示:第一,必须坚持以幸福为人生的目的。要用幸福来衡量金钱、权力和名声的意义,而不是反过来。第二,必须坚持为了实现幸福去实行、实干。幸福不是天赐的、不是空想的,而是奋斗出来的。第三,必须坚持感性幸福与理性幸福相统一。幸福既需要物质基础和情感体验,也需要精神超越。第四,必须坚持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相统一。幸福不是一己私利,心中只有自己的人永远不会找到幸福。只有关心他人的苦乐、关心公共的福利,将个人的幸福与社会整体的幸福紧密相连、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第五,必须坚持幸福感与道德感相统一。道德感绝不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感觉,伦理学绝不是一门教人压抑的学说。“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 ”[8](P41)道德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的欲求得到最好的满足。
——读《论自由》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