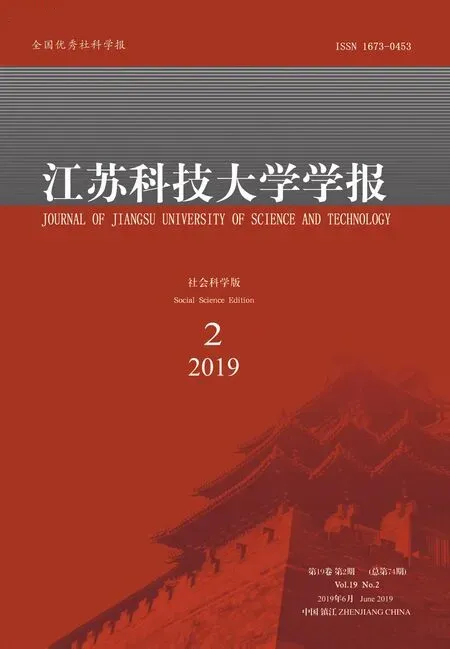康德的自由之演绎
——从实践的自由到先验的自由
张 愉
(武汉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通过自律来论证理性,从而解决了“从自由到自律、自律到道德法则”的循环,将自律作为理性权威的基础,并通过感官世界与智性世界的划分,说明人自身其实是既居于感官世界又居于智性世界的,自然和自由都是必须的。自然必然性适用于理性思辨,而自由则是理性实践的可能性道路。康德还通过第二类比时间相继的因果性分析说明了自由的必然性。因此,自然与自由并不矛盾,可以在主体中融洽地相处。
然而,在理性实践中预设意志自由是可能的,但康德对自由是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无法作出说明。康德试图通过规定道德研究的最高界限,即理性不能在超验领域运用,人类理性也不能说明纯粹理性是如何能够实践的。但这样划定界限的方式并没有成功完善对自由的阐释。
康德对自由理论的阐释最终从实践自由转变为先验自由,亨利·E·阿利森(Henry E.Allison)认为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面临的核心困难:一是康德没有做好从理知世界到智性世界的过渡衔接;二是意志与实践理性有双重含义,理知世界对先验自由概念的建立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不再从理性存在者自身出发推出自由的预设,而是从道德律出发推出先验自由的实在性。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自由的自律方面。先验自由可以使我们在面临道德冲突或抉择时自发遵循道德律,从而达到道德律所必须的自律。先验自由也就成为道德律存在的理由和根据,道德律则是自由的认识理由。
但容易遭受的质疑是,先验自由以及道德律的普遍性如何解释人类不道德行为的存在?沃尔夫(Wolff)认为不理性的行为是被胁迫的、非自我意愿的,并且在其完美遵循理性与自然强迫的行动中存在着中间层(middle-ground),人类确实会做出不道德行为,尽管这出于人们的自由选择。康德的定言命令将自身行为准则上升为普遍自然法则,体现了道德律的普遍性,然而在实践运用中,道德律作为抽象的法则,其效力远不如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即便遭受了现实的困境,不可否认的是,康德对先验自由以及道德律的阐释依旧对人们的伦理生活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自由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属性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三章的开头对自由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的概念是说明意志自律的关键,且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属性。他的论证方式是首先区分了自然必然性和自由,自然必然性是“一切无理性存在者的因果性被外来原因影响所规定而去活动的那种属性”[1]454。也就是说,在自然必然性中,因果性是受外来影响的。而对于意志来说,有生命的存在者的因果性不需要依赖外在原因来规定它的原因而起作用。而这只是自由的消极方面。从积极方面来说,自由与自然必然性不同,自然必然性受外在原因的规定而起作用,也就是遵循他律的规定。但是,自由在行动中其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也就是说,自由遵循自律的规定。康德其实是将自律性与一种将普遍准则上升为普遍法则的原则结合起来了。与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定言命令“要依照能使自己同时成为普遍法则的那种准则而行动”[1]455一致,因此,“自由意志和一个服从道德法则的意志是一回事”[1]445。在这里,自律独立于外来规定,即独立于偶然性事物、随机性事物,自律必须具有可普遍化特征,即对理性存在者都是平等公正地对待的。
在论证“自由必须被预设为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属性”时,康德要论证自由是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者的。对此,康德先下了论断,但没有直接展开。他认为,理性存在者唯有在自由的理念之下才是一个自身的意志,而且自由的理念是在实践理性中展开的,但对理性与自由的联系他并没有阐释清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康德先是针对一种理论冲突进行阐述,即我们假定自己是自由的,从而服从道德律,然后自己遵循道德律,是因为我们把自由归诸为自身。但是,一个不能用来说明另一个,即不能是一个“从自由到自律、自律到道德法则”的循环。因此,我们需要转换自己的出发点。对于理性与自律的联结,康德“不是从理性来论证自律,而是从自律来论证理性”[2]73。康德认为自律是理性权威的基础。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对理性的原则及其权威作出了解释。理性活动必须将自己置于批判之下,“理性的权威只能通过思想和行动中的自律性的自我训练建立起来”[2]73。
在消除上述的困境时,康德提供了两个世界的划分,即感官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划分。将纯然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归入感官世界,而将其中纯粹活动的东西归入理知世界。理性既可以将感官世界与理知世界区分开来,又可以明确理性本身对它的限制。而就理性存在者来说,康德认为他有两个立场:“首先,就它属于感官世界而言,它服从自然法则(他律);其次,就它属于理知世界而言,它服从不依赖于自然的、并非经验性的、而是仅仅基于理性的法则”[1]460。但康德又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我们设想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就把自己作为成员置入理知世界,并认识到意志的自律连同其结果,亦即道德性;但如果我们设想自己负有义务,我们就把自己视为属于感官世界,但同时也属于理知世界”[1]461。康德坚持认为,这两种视角——自由与自然必然性,虽然有明显的冲突但也相容,并没有真正的矛盾。
康德认为,在理性的思辨方面自然必然性显得更为适用;而在理性的实践方面,自由则是我们运用理性的可能性道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还进行了第二类比,即根据因果性规律时间相继的原理解释因果性的基础,从而解释自由为什么在实践领域是必须的,以及为何自由的行为主体对获取经验或科学的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关于第二类比,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以便为自由的必然性作出论证。在这里,首先要区分的是主观性的知觉序列与客观性的知觉序列。康德通过对房子直观的实例来解释主观性的知觉序列,即无论先从哪个角度直观房子,都可以把握经验性直观的杂多。他又通过对船的直观的实例来解释客观性的知觉序列,即看见一艘船顺流而下,人先有船在上游的位置的知觉,然后才有船在下游的位置的知觉,船在下游位置的知觉是跟随着它在河上游的知觉的。因此,“把握种种知觉相继中的秩序是确定的,而把握就受这种秩序的制约”[3]163。从这两个实例中,康德得出人们必须从显象的客观相继中推导出把握的主观相继的结论。在客观相继中,对发生事物的把握是根据一个事物跟随另一个先行事物的规则而进行的。在主观相继中,则有客体的杂多,这是完全任意的。因此,主观相继与客观相继必须区分开来。在客观相继中,人们只能在这个次序中对知觉进行把握。在主观相继中,人们难以感知显象之间的区别,从而将失去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基础。
康德接下来还分析了客观序列中的这种前后相继,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因果性解释。在这里,康德将原因与结果的相继的经验性标准归结为时间的继起。同时,“这种因果作用又导向了行动的概念。而行动则导向了实体的概念”[3]170。这同时也说明了理论的视角不可或缺,但实践的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行动永远是显象的一切变易的首要根据。”[3]171因此,人们既是感官世界的成员,同时也必然转向理知世界;人们作为行动主体,而且必须是自由的行动主体。人作为自然的部分服从自然的法则,当人们说自己自由的时候,其实是自己是在实践的意义中设想的,即在实践层面上为理性的运用开辟道路。
二、在理性实践中预设意志自由是可能的
康德在论述实践哲学的界限时谈到,只有当人不否认自己是理智的,“而且是理性的、通过理性活动的、亦即自由地起作用的原因”[3]466,把自己设想为实践的,才是必然的。实践理性若把作为消极规定的自由同时与意志的因果性结合起来,并且把行动的原则作为普遍有效性的法则,则实践理性在这个层面上是积极的。但是实践理性不能企图“从理知世界索取一个意志的客体,亦即一个动因”,否则,“它就逾越了自己的界限。妄想认识某种它一无所知的东西”[1]466。被规定在客体之上的法则都会产生他律,“他律只能在自然法则那里发现,也只涉及感官世界”[1]467。因此,理性不能“说明纯粹理性如何能是实践的,否则就逾越了自己的界限,这与说明自由如何可能的任务完全是一回事”[1]467。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三章的后半部分中论述了这一点,直到这本书的结尾处,康德也始终保留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自由作为理性的行动的根据,我们只能被迫假定它,却不能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的。理性在自由方面的实践应用也像理性在自然方面的思辨应用一样会导向绝对必然性。用一个理性存在者本身的行为法则的绝对必然性,即以一个条件为根据,来验证存在者或发生着或应当发生着的必然性,这个条件被不断地追问、不断地向前,这个绝对必然性的东西最终只能是自由,而且是被我们预设的、出自于理性自身的自由。理性通过自由的法则颁布道德法则,即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法则作为自由的最高法则,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不能理解自由是如何可能的,以及自由是如何充当理性的条件进而导向绝对必然性的。
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即使如此,康德所作出的规定界限的工作也是极为重要的。康德将划界的意义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使理性在感官世界以不至于有损道德的方式寻找最高动因和一种经验性的兴趣;另一个是不至于在超验领域进行超验运用,从而陷入幻相之中。康德将道德研究的最高界限予以界定,即人类理性无法对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这一问题作出说明,对自由作为意志的因果性如何可能也无法作出说明,排除了意志规定的感官世界的成分后,剩下的即是“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的实践法则”[1]470,以及把理性设想为规定意志的原因(也就是理性本身就是理性意志的原因),然而理性本身就是理性意志的原因这一点是可以被理解的,却是一个不能得到解释的问题。这就是道德研究的最高界限。
康德的阐释表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理性存在者的理性意志因果性,相较于自然必然性是作用因的他律而言,自由作为意志的因果性,自由是自身的法则,即自律。因此,理性自身就规定自身,理性是自律的或自我训练的。康德认为预设意志自由是可能的,而且他在实践中“把这种自由作为条件加给意志的所有任性的行为,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凭借理性的因果性、从而意识到一个意志(意志与欲求有别)的理性存在者来说,无须进一步的条件就是必然的”[1]469-470。然而,人类理性无法对纯粹理性如何能够是实践的这一问题进行说明,对自由作为意志的因果性如何可能也无法予以说明。
三、自由的演绎——从实践的自由到先验的自由
可以看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对自由理念的阐释并不充分,他的阐释相当于对自由理念的演绎,他对自由的现实性和属性并未界定清楚。同时,他对于道德律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方面的阐释也是欠缺的。亨利·E ·阿利森认为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最为核心的困难是:
第一个困难是智性世界的双重含义。康德利用智性世界的概念来践行从拥有理性推至智性世界的成员身份,然而智性世界却有双重含义。“康德既提到一个理知世界(Verstandeswelt),又提到一个智性世界(intelligibelen Welt)。他从前者滑移到后者,又没有对此作出充分的辩护”[4]344。亨利·E ·阿利森认为理知世界是包含着仅仅是智性者的世界或任何非感性者的世界,智性世界则是由道德律所支配的超感性领域即“目的国”。理性存在者是智性世界的成员,受到道德律的支配。“问题在于,拥有理性这一点本应提供通往智性世界的入口,但它仅仅使我们到达理知的世界(Verstandeswelt)。”[4]344康德在认为理知世界只是一种观点之后,又认为有一种立法观念即道德律。他将要论证的结论——从理性推至服从道德律作为前提进行狡辩。
第二个困难是意志与实践理性概念的双重含义。鉴于意志与实践理性概念等同,理性存在者拥有意识,因而可被理解为理性是实践的,或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前者与单纯实践者相关,后者与真正的先验自由相关。但理知世界只能提供较弱的主张,因此自由理念的建立,即便得到先验观念论的支持,却依旧会遭到失败。
康德本人也意识到这些问题,他通过理性的事实为道德性奠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对他的理论进行了调整。他改变了在从理性存在者的概念着手得出自由的预设以及道德律的解释路径,而尝试从作为“理性之事实”的道德律的意识推出纯粹理性的实践性以及先验自由的实在性。这是基于道德基础上的,而不再是从理性自身出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换。因此,在关于自由的演绎中,有两个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从自由方面所理解的自律;另一个是先验的自由,也就是独立于一切经验性事物、自然一般意义上的独立。在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人即便有对道德律的关切,却无法始终遵循道德律,出于对道德律的尊重而行动。关切是微弱的,力量是不足的。在先验自由方面,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纠正了对于自由的理解,将自由归结为先验的,并主张如果没有先天实践性的先验自由,那么任何道德律都是不可能的。自由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与根据。而在论证先验自由的同时,道德律的自律可以被看作是与意志自由等同的,理性存在者在感官世界中受自然因果性支配,而在实践中,存在者意识到自己是“作为诸事物之智性秩序中的可规定者而生存的”[1]367。这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的论证思路如出一辙但又有区别。区别在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对于理性能力来说,人们只能确保自己在理知世界的身份;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先验自由中表现出来的自律可以确保人们是智性的存在或超感性的存在,从而克服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的一个困难,即不能达到道德律所必须的自律。先验自由可以确保人们在面对爱好或偏好的冲击时能自发选择遵循道德律。道德律只有通过理性的事实及从中演绎出来的自由的实在性才能建立起来。另外的不同是关于意志自律的。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中认为自律建立在绝对命令的约束之下,而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认为受绝对命令的约束导向了自律。
此外,康德关于自由的理念容易受到明显的反驳,即自由其实是一种幻觉。康德对于自由的理念是否超出先验观念论的要求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是不清楚的。但通过分析自由意志与理性事实可以发现,假如自由是一种幻觉,那么自律以及作为道德行为者的理性存在者就都是幻觉了。但理性的事实表明,这些都是现实的。因此,自由意志不能被当作幻觉。另外,康德一直强调自由的实在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考虑,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自由意志的现实性得到了合理解释,因此自由意志更不能是幻觉了。明显的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建立起自由的现实性,即便只是从实践角度。但相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一书,康德已经有了新的进步,即自由是先验的自由而非实践的自由,以及从实践角度建立起自由的现实性。随着先验自由现实性的建立,道德律作为行为的规范理论的地位也就确定下来,即道德律为行动提供了理由和根据,且人们作为理性存在者具有独立于自然机制的自由选择的意志。
然而在解决了自由不是幻觉这一问题之后,建立康德的自由理论依旧还有模糊之处。从先验自由中可推导出绝对命令和意志自律的道德性概念,但对于康德道德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还未深入探讨,并且对于理性事实的解释以及道德律又是自由本身的基础这些问题中的预定和假设仍需进一步讨论。另外,亨利·E ·阿利森还提到一个困难,即理性行为能力的概念,“即使一人拒绝这一主张,即对道德律的独特且不可解释的关切指明从实践观点来看自由乃是现实的。而且,由于这一概念显然包含着非相容论的自由概念”[4]379。依旧存在这样的难题,即如何将“这样理解的自由这一预设与支配着那些被视为自然发生的人的行为的因果决定论调和起来”[4]379。而这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康德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的衔接这一问题。另外,这也表明康德在自由与决定论是否相容以及决定论是否与自由及道德责任相容的问题上还需进一步说明。
四、对自由的认识理由——道德律之普遍性的质疑与回应
另外,康德的道德哲学又引发了一些质疑。具体叙述如下:
自由是理性自身规定自身、训练自身,也就是理性自发形成的,那么意志根据理性来管理自身时,也就是依照自律来管理自身时,为何还是会出现人追求欲望、享乐或其他一些不道德行为?这似乎不得不归结到人自身。人是理性存在者,但只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人是具有欲望、倾向等感性因素的。沃尔夫在1973年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人们或者行为理性是合理的,也就是符合自律的行动,或者只是被非理性所胁迫而这么行动的,也就是他律的。这暗指非理性行为不是被意愿的。这一观点虽然偏激,但依旧有借鉴意义。恩格斯特伦(Engstrom)、雷思(Reath)和科尔斯加德(Korsgaard)都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他。他们认为人们总是假装品德高尚,从而使他们的行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合乎理性。人们认为康德理论中还存在着中间层,处于完美遵循理性与被自然强迫行动之间。特别是当人的行为不道德、意志薄弱、或被错误意愿导致误用实践理性时,人们不会将不道德行径最大化,因为人们的意愿与实践理性一致。因此,当人们行为不当时,他们不会怀疑自身,但会错误理解理性的底线。当人们把不道德行为视为理性的或是合理的,人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没有训练好理性能力,只是做了与意志相反的选择却没有意愿它,尽管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是出自自身的,因为意志会引导理性行动。但这依旧说明如果意志是实践的理性,人们依旧有可能会故意或乐意犯错。这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个挑战。
这一质疑与道德律联系密切。就道德律中的绝对命令来说,最为关键的一条是“要这样行动,就好像你行为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似的”[1]429。从康德的论述与例证来看这似乎非常完满,但当人们真的将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来时,就极有可能遭遇上一段所遇到的困境,即中间层。道德律的普遍有效性落实在具体的行为实践中,标准难免会变得不那么好把握。面对多种多样的情况及其包含的特殊情形,针对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人,如何基于普遍有效的判断来行动似乎尤为困难。同时,在另一方面,道德律本身作为抽象的意志法则,它对人们的意志活动的确有指导意义,但其对现实活动的指导意义就很有限,毕竟在行动之前确保普遍认同的法则将是十分困难的。再往前推一步,普遍认同的法则就一定是准确无误的吗?先天有效性真的足够确保它的有效性吗?另外,将道德伦理建立在人类的理性概念之上是否考虑周全了呢?
奥诺拉·西尔维娅·奥尼尔(Onora Sylvia O’Neill)针对严格主义即质疑道德律的普遍性作出这样一种解释,“如果康德确实提供了一种德性的道德,同时也提供了对正当行为分离的阐述,那么严格主义的指责就破产了”[2]198。因为康德的道德理论不仅不是道德原则,也明显不是普遍规则的规则。此外,奥诺拉·西尔维娅·奥尼尔认为康德的理论并不是产生行动规则的理论,也不是提供普遍行为规则的理论。“康德为我们提供的是德性伦理,而不是规范伦理。他并没有把人的理性仅仅视为计算性的。”[2]206因此,康德所做工作仍是值得敬重的。
笔者主要针对康德对自由概念阐释的转变以及康德道德哲学的伦理意义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康德对自由概念的阐释依旧存在着问题。
康德对先验自由的阐释是否超出先验观念论的范围这一问题是不清楚的。先验自由的认识理由是道德律,而先验自由又是道德律存在的理由与根据,它们彼此关联,但其中的预设和假定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并且它们的形而上学性与普遍性恰恰是使得自由的现实性与实践性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此外,对于先验自由是否是幻相的质疑,康德显然还面临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相容的问题以及决定论是否与自由及道德责任相容的问题。
虽然康德对自由的阐释从实践自由转为了先验自由,避免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所面临的困境,但康德对于为何存在人类的不道德行为的解释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但若从德性伦理的角度来衡量康德的道德哲学,而不是从规范伦理的角度去衡量的话,则康德的先验自由与道德律依旧可以为人们的伦理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