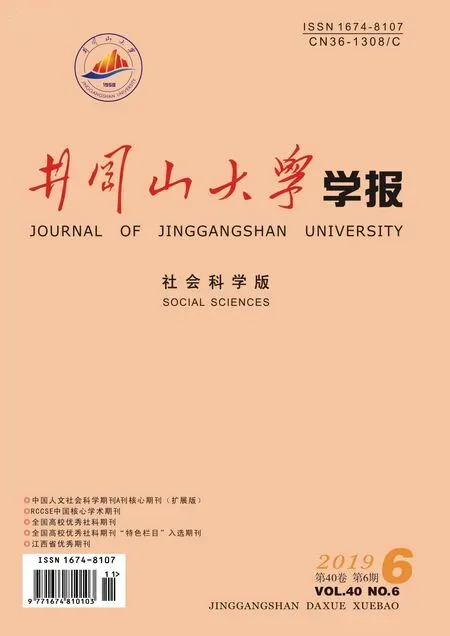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视角
于 波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330099)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P2)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已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由于社会利益关系多样化,人们因财富、地位与声望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社会阶层有其不同的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需要, 与之相适应, 反映不同阶层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也各式各样,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 因此,在社会阶层分化时空中,如何正确应对社会阶层分化, 找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成因,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恰切进路,着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度, 促进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阶层发展的良性互动,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阶层利益过度分化: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马克思恩格斯是以人的需要本性为轴心来把握和理解人的现实利益问题, 认为利益既是推动人从事生产的根本动力, 也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形成不同生产关系的现实纽带, 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利益和利益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2](P163)作为“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需要”,[3](P14)利益往往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着人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同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不同需要,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会发生一定的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言:“把人和社会联系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 ”[4](P439)“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4](P82)同时,思想价值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植根于人们特定的需要之中的, 需要和私人利益是人们思想价值观念的基础, 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P103)然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人的需要不是单向度的简单需要,而是多向度的复合需要。 随着人们需要向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人的利益诉求也更加丰富多样,利益在现代社会中也更具多样性与差异性。在利益主体上,可划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共同利益;在利益内容上,可划分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在利益实现时间上,可划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在利益实现范畴上,可划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在利益重要性上,可划分根本利益与非根本利益。虽然利益划分的方式不同,但利益关系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动态发展的, 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 考察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觅终级原因,而应当从建构人们各种不同需要和利益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 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 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 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6](P654-655)作为一种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基于自身根本利益而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一种思想价值观念的自觉反映。 这种自觉反映是由现存社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具体表征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差别的扩大化、利益实现方式多样化、利益固化态势加剧等等,社会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失衡, 从而消解了人们的利益认同,冲击着多元思想价值观念的利益整合。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是社会阶层利益多元化的现实表征。 改革开放以前,“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 是我国三大利益主体; 改革开放以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逐渐出现分化,利益主体和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现象产生,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渐趋凸显, 社会不同群体中的个体, 特别是弱势阶层中的个体往往找不到自己所处的位置,“位置焦虑” 感油然而生, 社会安全感缺乏, 社会话语权缺少, 社会阶层对抗凸显, 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效果大打折扣, 成为影响国家与社会稳定的一种隐性矛盾。“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 关系社会和谐稳定,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7](P163)事实表明, 在社会阶层利益过度分化的境遇中, 价值判断的中性化、 模糊化倾向存在于多样化的意识形态领域之中, 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陷阱、 普世价值的制度陷阱、 价值中立的逻辑陷阱等趁机渗透于我国社会诸多领域。 它们不仅腐蚀了我国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也为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贴上 “左” 的标签之嫌疑,使人们因惧怕“左”而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一种认同“间距”。 社会阶层利益过度分化必然带来不同阶层之间的思想对立和混乱, 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认同带来了挑战, 消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宣传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客观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 社会阶层利益过度分化所导致的阶层差距扩大化现状及趋势, 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大相径庭,这势必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疑惑、误解甚至质疑,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 削弱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价值认同。 诚然, 在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 利益平均走向利益分化,利益实现单一化走向利益实现多样化是一种客观趋势。 但是利益过度分化背景下产生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行业差距的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消弭了我国政府公信力, 使西方理论界鼓吹的 “塔西佗陷阱” 理论趁虚而入, 消解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致使人们对党和政府所宣传的主流价值观产生怀疑、 动摇甚或疏远、 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 直接削弱人们对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钱和基本方略的价值自信。
二、阶层思想共识离散:稀释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
思想价值观念的共识塑造是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内核, 意识形态是以价值共识为内核而形成的一套观念体系, 正如加拿大学者克里斯托弗所言:“当科学观念、公理、原理作为单纯的理论体系存在时,它们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一旦这些理论变成一种‘词尾带主义’(-ism)的抽象意义,它们就变成意识形态。 ”[8](P92)“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2](P178)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构成的,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共识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意形态形成的核心,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体系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核,支撑着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构大厦, 决定着一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与性质。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信仰与意义的正确表达。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7](P168)为此,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不仅是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其价值内核的, 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信仰与意义的正确表达。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对全国人民美好意愿的一种价值、信仰与意义的表达,在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顺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一种价值、信仰与意义的表达,在公民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立身之本的一种价值、信仰与意义的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人类价值、国家价值、 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观照中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与性质, 是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在全社会凝聚的最大社会价值共识。 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是全体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共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是形成我国社会不同阶层思想共识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促进我国不同社会阶层思想共识形成中具有强大的凝聚、 整合与引领作用。 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阶层围绕自身利益诉求表达着不同的价值、信仰与意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建构不同阶层的“重叠共识”,聚焦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关注社会全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凝聚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价值观念系统, 正确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理想信仰与价值意义,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塑造社会不同阶层“重叠共识”、“交往共识”的文化代码功能,发挥其强大的思想凝聚、整合与引领作用,消除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思想隔阂, 增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理解, 促进社会主义价值共识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实现, 进而推进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思想共识的形成。
思想共识即社会不同主体在思想价值观念上达成基本一致或共同的认识, 塑造思想共识是弘扬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所在。 社会不同阶层思想共识达成的关键是要筑牢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基础,寻求思想价值观念趋近的“最大公约数”和思想价值观念分歧的“最小公倍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7](P153)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阶层差距的扩大,社会不同阶层在某些领域中呈现了思想共识的离散状态,这集中体现在改革与发展共识上。 事实表明,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不同阶层思想观念的分歧与冲突,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与冲突,已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现实呈现, 干群矛盾与劳资矛盾往往是造成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于改革与发展共识离散的现实诱因。与之相伴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虚无论”“无用论”“过时论”“教条论”“泛化论” 等认识误区和不当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论争便是其较好的理论诠释。可以说, 社会阶层分化下的干群矛盾与劳资矛盾也直接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 造成了贫富群体思想价值观念上的“鸿沟”,加快了贫富群体意识形态的分化。贫者更贫、富者更富,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加剧了贫富群体思想价值共识的离散甚或撕裂, 直接削弱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整合与引导功能。主流意识形态在建构社会思想共识中的主导力与影响力下降,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价值观趁虚而入, 侵蚀了社会不同阶层思想共识形成的文化代码,诸如国内“新左派”与“新右派”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争论,其不仅折射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思想观念分歧,影响了不同阶层“重叠共识”的达致;也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认同偏差与迷惘以及改革发展共识的离散碎片化, 甚或有打着反思改革的“名义”谋求否定改革之“实质”的现象,出现了某些干扰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荒诞言论, 模糊人们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同,淡化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与价值认同, 稀释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度。 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洞察了当今社会中有人葫芦里卖药之本质, 强调指出:“当今, 社会上关于改革的议论很多,‘药方’ 也很多。 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9](P56)
三、阶层文化身份区隔: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
区隔即区分、隔离之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区隔”意指必然趣味和自由趣味的对立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 文化区隔乃是阶层区隔的一种重要标识, 社会不同阶层由于经济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文化身份归属, 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归属显性或隐性显示了其社会位置。 不同阶层之间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趣味标准的冲突,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区隔折射了不同阶层的权力阶位和话语区隔, 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区隔与社会身份区隔是一种结构性同源关系。 文化身份背后的象征意义和符合价值在一定意义上镶嵌和建构规定性的社会秩序, 内在蕴藏着一种文化排他性特征, 即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往往具有文化趣味上厌恶和排斥, 隐喻了不同阶层的文化趣味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与差异, 进而导致不同阶层在认同自我文化身份中对他者文化身份的拒斥。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认为资产阶级的趣味(区隔感)、工人阶级的趣味(必需品选择)和小资产阶级的趣味(文化善意)等构成了社会空间的三重维度。 其中纯形式的审美文化推崇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聚焦,日用伦常限制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聚焦,资产阶级的文化趣味与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之间是一种正统文化趣味与通俗文化趣味的对立与排斥关系, 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则是在毕恭毕敬对待资产阶级文化趣味中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文化尴尬境遇。 这三大阶级都在自我群体的文化身份归属中具有排斥其它群体文化趣味的本能,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显示其社会位置的文化象征, 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文化习性与趣味成为了他们社会区隔的重要标识。 可以说,皮埃尔·布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中看到了不同阶级阶层之间文化趣味的内在区隔所导致的不同阶层文化身份归属差异性, 认为不同阶层的文化只有在区隔体系中才得获得身份归属, 才能得到其应有的“名分”。 不同阶层的文化生产与再生产有其相对的自主性逻辑, 不同阶层的文化区隔一定程度上是阶层分化的客观结果, 文化身份归属区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自愿性的文化认同隔离。观照当今中国社会现实,虽然存在“文化阶层化”与“文化大众化”的理论分歧,但毋庸置疑,文化身份区隔是社会阶层过度分化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 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性, 同一阶层中的人也因文化习性的一致而形成共同的文化圈, 导致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区隔, 进而固化了不同阶层的文化身份归属差异, 这极易阻碍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加深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鸿沟”,诱发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对立, 甚或演变为文化话语权的争夺。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是施展权力和掌握权力的关键要素, 它绝非是一种简单透明的中性要素, 而是各种不同思想力量进行角逐的场所, 话语背后折射着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 掌握了话语资源的社会阶层意味着掌握了话语权。 在社会阶层分化境遇中, 话语权滥用或话语排斥是不同阶层之间文化排斥的一种主要表征, 话语权滥用也往往是导致不同阶层文化对立与冲突的重要诱因, 折射了强势社会阶层对弱势社会阶层的一种文化身分骄纵的排斥心态, 其不仅有可能引起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情绪冲突与对立, 也有可能引起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 因为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与话语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思想、 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2](P151)人民性的话语特质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 人民性的话语特质植根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通过人民性的话语特质来筑牢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转向。作为文化的内核,意识形态是文化软实力的内容基点,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与方向。文化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主流文化的母体性意义规定。由此可知,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 二者的关系可概括为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 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7](P163)然而,文化身份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的文化身份区隔会使个体在固守自我文化身份中对他者文化产生一种模糊与排斥感, 从而弱化对他者文化的包容与信任, 特别是强势阶层对其文化身份的情感依赖致使其不会轻易接纳其它阶层的文化元素,甚或疏远、抗拒其它阶层的文化元素,人为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身份落差, 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文化的人民性根基, 造成文化身份区隔下的身份认同困惑和价值选择迷茫, 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人民性话语特质, 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生活话语叙事, 导致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中的话语断裂,腐蚀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人民性底蕴, 削弱了人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自信。
四、阶层流动渠道梗阻:加重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
在阶层分化大背景下社会流动性不足已经凸显。 在利益考量视角下,既得利益、阶层利益藩篱固化致使阶层壁垒难以打破, 跨阶层的社会流动通道受阻、变窄。同代交流性减弱和代际遗传性加强是社会流动性不足的表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也产生了社会流动性不足现象,出现了贫富差距的阶层和代际转移,形成了“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代际传递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得不同的人群“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被进入”了不同的通道,从下向上的阶层流动成为许多人无可奈何的一种慨叹, 这是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新时代要切实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须把“阶层流动渠道梗柤”的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打破既得利益的藩篱,“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10]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也同时隐约滋生了社会流动性不足现象, 跨阶层流动通道日益逼仄,“官二代”“富二代”“农二代”“穷二代”“星二代” 等利益固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苗头, 造成草根阶层的向上流动式微、中间阶层的相对被剥夺感增强、新富阶层的移民倾向强烈, 提高了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身份壁垒和流通成本, 减少不同阶层之间的垂向流动,加剧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改革开放的成果难以在“新底层社会”实现共享。然而,更可怕的是, 有的既得利益者为了捍卫其自身利益, 错误地将社会流动性不足和社会稳定进行简单等同, 认为社会稳定与社会流动性不足是成正比例关系, 社会流动性不足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表征。 必须对这种所谓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正当性而摇旗呐喊的行为保持一种高度警惕。 需要澄明的是, 社会流动性不足极易导致利益藩篱固化和社会结构僵化, 社会流动性不足极易引发和刺激民众的社会公平焦虑和相对被剥夺感, 进而损害社会的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稳定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流动性不足, 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跨阶层的社会正常流动,需要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畅通阶层的社会流动通道, 健全阶层的社会流动机制, 惟有如此,才能阻断贫穷在代际之间的传递,社会才能得到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 为此,在某种意义上,与贫富差距相较而言, 社会流动性不足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社会中出现的权力精英与资本精英的结盟, 极易导致体制性腐败和禁锢社会活力的恶果, 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需要消弭的一道现代性伤疤。
在阶层流动渠道梗阻中, 对子女一生助力的给予和对子女一生牵绊的陪伴, 是精英家庭与平庸家庭的一种对比写照。 为此,社会中出现的“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长期稳定化现象,不仅会消解新底层社会群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而且会使他们把家庭、 出身而非个人努力奋斗作为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拼爹”“拼家庭”“拼关系”的心态胜过了拼个人努力与奋斗的心态, 走捷径的心理胜过了脚踏实地的心理。 众所周知,强势阶层、精英阶层出于对经济资源、 政治资源与文化资源的占有优势,往往会为其下一代的子女人生设置了下限,预留了人生止损线,铺设了玻璃地板,购买了人生保险, 从而规避其下一代子女滑落为弱势阶层或社会底层的风险,哪怕下一代子女一事无成,也可以成为强者世界中的一个列席者。为此,面对社会流动性不足所带来的这种社会不公现象, 有的青年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教育采取的是消极式接受、被动式认可,甚或出现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心深度怀疑或否定。事实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是因为人民性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属性, 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与政策等都是植根于维护与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之中的, 人民群众也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换言之,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与能够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相关联的。同样,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危机的产生, 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的下降, 也是与人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公平正义感缺失相关联的, 特别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资源、 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代际传承或代内复制交换, 加剧了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分化与对立, 使原具有政治荣誉感和优越感的工农阶层有着一种相对被剥夺感和弱势心理。为此,他们在面对低收入水平状况并被固化的窘境时,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等渐趋产生疑虑、困惑甚或否定,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下降, 对党和国家的群众路线方针政策产生怀疑, 加剧了对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信任危机,使党群关系、阶层关系之间的紧张状态日益显性化,“仇官”“仇富” 现象更趋白热化, 从而冲击了新底层社会群体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与信任度, 直接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
五、阶层情感共鸣式微:侵蚀主流意识形态的转译界面
实现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首要逻辑, 是建构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首要的、 根本的转译界面。 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 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团体的忠诚拥护。”[11](P58)为此,必须强化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情感共鸣, 寻求能让社会不同阶层共同接受与认可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然而,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分层背景下,身体阶层化与情感阶层化是社会分层所导致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客观现象, 特别是情感的阶层化极易造成不同阶层在主流意识形态上的情感共鸣式微, 进而侵蚀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译界面。 马克思·韦伯将财富、声望与权力作为其社会分层理论的分析工具, 并以财富、声望与权力为分析变量,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国内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亦基本沿袭了马克思·韦伯的分析路径。 毫无疑问,随着我国以市场化为先导的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 经济学意义上言说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得以诞生。尽管他们获得了经济上向上流动的可能, 但依然面临着阶层身份的文化意义上的尴尬与无奈。 文化意义上的阶层身份建构乃是研究社会阶层分化所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 因为文化是建构社会阶层结构的一种重要方式。 这种阶层身份的建构是通过人们的身体和情感来加以建构的, 是与强势阶层的优越感和自豪感紧密相关的, 身体和情感也往往成为了阶层身份的一种表达工具。 阶层身份的身体和情感建构所导致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可能阻隔了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 从而导致身体阶层化和情感阶层化的现象产生, 使社会充斥着有关身体与情感的阶层想象, 如社会上流行的“高帅富”、“白美富”“矮挫穷” 便是身体阶层化的现实脚注,“剩女”与“吊丝”便是商品逻辑宰制下的一种情感阶层化的隐喻。 情感的阶层化既隐喻了情感具有阶层属性, 对于新底层社会中的人来说,美好的“爱情”往往是累人的,“剩女”不是因为自身家庭出身不好、 颜值低、 身材差而成为“剩女”,而正是由于不愿让美好的“爱情”接受商品逻辑的宰制而追求“情感”的“纯粹”、“圣洁”而成为“剩女”。同时,情感的阶层化也折射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念差异和生活方式差异, 表明了文化对情感的剥夺,而非家庭出身等因素,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消解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鸿沟”。《新结婚时代》《失恋33 天》等电视剧的上演便是对情感阶层化的一种较好佐证, 反映了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有着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阶层身份差异的尴尬与无奈,如果这一事实放大到整个民族的话,其剥夺的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尊严, 而不是一个个体的身体和情感。
“一种观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旦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的正确性, 它就会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无论遭到的障碍有多大,它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12](P46)同理,身体阶层化和情感阶层化的思想观念一旦被认为是正确的, 并以文化方式对其标准加以建构的话, 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对人们身体和情感的剥夺, 而是对整个民族精神和尊严的侵蚀。 因为当人们的身体和情感受到了商品逻辑所宰制时, 对于处于弱势阶层的个体而言,财富、声望和权力的阙如,往往可能致使其情感的飘零和身体的流浪;工作的挫折、爱情的失败,往往会滋生其对社会的泄愤和国家的不满;生活的无望、未来的迷茫,往往会粉碎其人生的梦想和激情的岁月。 当今身体和情感的阶层化所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上的情感共鸣式微, 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不同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译界面。 特别是消费社会中对身体和情感的文化剥夺, 已使人们的情感陷入市场和商品逻辑的漩涡之中,“剩女”“吊丝”便成为了“情感抗争”的衍生品。 同时,由于情感认知具有阶层属性, 情感的阶层化架设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情感认同框架, 不同阶层在情感能量上的不平等也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原因。 诸如新底层社会群体人员的负性情感滋生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各种政治调侃或语言嘲讽也从侧面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一种情感式抗争或“正义式愤怒”, 导致了不但没有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共鸣, 反而侵蚀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译界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 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7](P4)为此,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括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承载的根本的、 首要的转译界面。如果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能够得到有效实现,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能够回归到生活的本位,走出“闪婚”“闪离”的情感快餐化误区,人们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情感上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人们的身心也能得到愉悦地安放, 自然而然会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深切情感认同。所以,包括美好情感需要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度是支配不同阶层群体人员的根本行动逻辑。 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 必须关注不同阶层群体的情感世界,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情感需要,实现不同阶层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