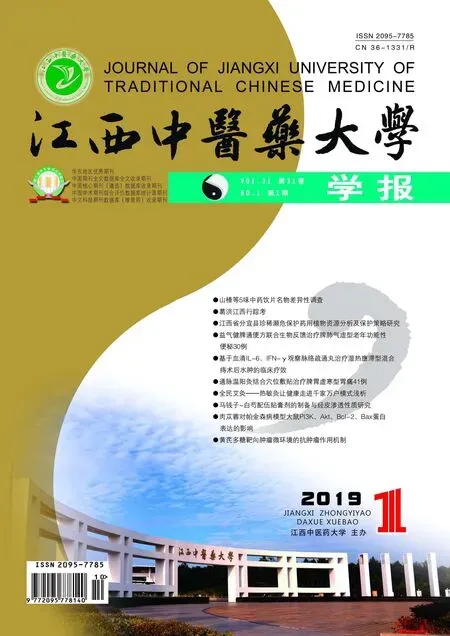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教育探析
★ 王尊旺 张孙彪
(1.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福州 350122;2.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福州 350122)
民国时期,福建各地兴起中医学校教育,中医界试图通过办学求得中医学术自强。此时期涌现的一批中医办学机构,以办学成绩彰显学校教育模式的独特优势和后续影响,在艰辛困难的办学环境下,民国福建中医学校从未放弃摸索实践,取得值得称赞的成果。
1 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教育概况
有关该时期福建中医学校办学的历史面貌,刘德荣曾撰写《近代福建的中医教育》一文[1],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列举了6个代表性医学教育机构,但刘德荣并未统计近代福建中医学校的具体数量。据《百年中医史》统计,“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的中医办学机构约219所,其中上海地区最多,约42所,其次为广州29所,福建22所。”[2]从创办时间而论,1917年8月正式开所的福州三山医学传习所开启中医办学先河[3],其开办时间紧随中国近代第一所正式中医教育机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之后。而本区域中医学校创办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此时期教育机构开办数量达16所,占民国时期开办总数的七成。但以存续时间观察,除了福州中医学社、福州中医专门学校、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等,其他中医学校机构坚持办学时间普遍较短,一般招收毕业一届学生;从学校分布位置来看,多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尤其是福州、莆田、厦门三地,内陆地区仅开办有龙岩龙岗国医学校(1928)、建瓯县国医传习所(1935)、浦城国医训练班(1935)。这种状况显然与福建沿海和内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相关。
据现有文献资料可见,民国时期的福建区域中医办学教育,涵盖了各种类型的教育形式,主要有中医专门学校(传习所)、业余教育(夜校)、讲习所、训练班等等,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兼有,修业年限长短不一。由于民国政府长时间不给予中医教育官方身份,此时期出现的中医学校机构大多数为民间自发办学,大都由当地中医药界名人倡议筹建,所依托的办学主体有中医学术研究团体、中医行业公会、地方慈善团体等。
2 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教育办学特征
2.1 经费来源及机构设置 由于近代中医长时间未被纳入国家官方教育系统,除了极少数中医学校,大部分都得不到官方教育经费的资助,所以办学经费基本上来自中医界自筹。福州三山医学传习所的办学经费主要由主持者陈登铠筹划出资,除了向学生收取学费之外,非常依赖于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资助学。曾担任福州中医学社训育主任的陈守基在《福州中医学社史略》中回忆,学社“自创社以来,经费依靠自筹自给,当时政府毫无支持及补助。其收入来源,一方面靠社会缴纳常费及董事乐捐或向社外人士捐募,另一方面靠学员学费收入”[4]。仙游国医专科学校,其前身为国医学社,成立初期“按月由(县教育局)教育款经理处拨给社费五十元,领未及年,局变为科,县教育科长曾天民以本学社非教育直接系统,该社款停给注销”[5],失去官方教育经费的支持,学社发展顿时陷于困境。莆田国医专科学校,其办学经费除了学生收费之外,主要依赖于当地行业公会的支持,“由国药公会向行业及私人筹募开办费银元六百元,作为校舍修理、课桌椅及医院设备购置等开支,由兴化桂圆公会每月拨银元一百元作为经常费”[6]。由于仰赖当地民间资金的支持赞助,这就是上文提及该时期学校分布集中于沿海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根本原因。
福建各地中医学校成立时均建立起校内组织架构,校董事会制、校长负责制是主要形式。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筹建之时,广邀厦门各界名流参与其中,成立组成人数众多的董事会。如此设计安排,校长吴瑞甫考虑“以自己在医学界的地位和声誉,想方设法,邀请一些社团领袖和商界士绅,只要他们热心于振兴中医事业,肯以其经济和声望支持办校,就礼聘为董事或董事长,学校有了这些名流作后盾,为办学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7]。莆田国医专门学校设立董事会,董事长由涵江商会会长陈杰人担任,董事4人,由国药、桂圆、豆饼等公会主席分担之,显然也是出于同样的考量。
2.2 学制课程设置与教材讲义编写 民国政府对于中医学校学制、课时、课程设置和教材的规定,迟滞不出,直至1939年5月才公布施行《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福建中医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设定学制、课程、课时,自行编写使用教材。总体而言,进修、夜校及社团教育学制较短且较灵活,全日制学校的学制设定较为固定规范,课程设置也比较系统全面。
福州三山医学传习所学制设置为4年,每个学年又划分3个学期,开设课程23门,课目既涵盖医学基础课程,又包含临床实习课程,课程较为全面丰富。因应近代中西医汇通的时代学术潮流,民国时期福建医校在课程设置上还注重中西医兼授。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修业年限制定为4年,初期开设的课程有“党义、生理学、解剖学、国文、理化学、病理学、药物学、医史、卫生学、体育、方剂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法医学、伤科、喉科、眼齿科、针灸科、推拿科、花柳病学、实习等科”[8]。而后校长温敬修认为中医教育不应固守原有的中医经典知识传授,在课程设置上“似应增入物理、化学、心理学三科”,因为“物理之光学对于四诊中之望及眼科,声学对于四诊中之闻及喉科,热学对于气候及体温,力学对于气压及地心引力,电学对于电疗及针法,均有密切关系也,大凡人体之构造、药物之分析,皆有必要之化学成分也”[9],彰显该校在课程设置上紧跟时代风气、勇于创新的姿态。
吴瑞甫在主持厦门国医专门学校期间,编撰出版众多中医教材讲义,不仅在数量上独占本区域鳌头,影响力更是远播海内外。学校各科讲义“近因国内外来函索赠者甚众,特将全部重付铅印,以广流传……其讲义虽在百忙中编就,然提要钩玄,最切实用,嘉惠后学,殊非浅鲜云”[10]。《绍兴医药月报》曾屡次推荐吴氏编写的《中西脉学讲义》,评价该讲义“鉴别甚精,体例亦善,足为近今中医学校教授之善本也”[11]。同时期本区域对中医教材编撰用力甚勤的当属仙游国医专科学校校长温敬修,其编撰有《最新实验药物学》《针灸学讲义》《化学讲义》等。其中最具学界影响力的是《汇症药用植物学》一书,此书乃温氏在任课期间随编随授之成果,全书“凡九万八千余言,绘图凡六百余品,采集阅四十余年,整理经一寒暑”[12],后经上海名医秦伯未审阅更名为《最新实验药物学》,并由上海中医书局于1935年正式出版发行,深受业界赞誉,销售国内及东南亚、日本各地。
2.3 招生情况及考核制度 此时期福建中医学校机构的招生规模普遍不大,以办学时间持续九年的福州中医学社为例,最终培养毕业学员198人,由此窥见其年均招生规模的大小。莆田国医专科学校原定招收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入学,后又录取部分同等学力的,年龄不限,有年逾不惑的农村开业医生,有年才十四、五岁的青少年,均以考试形式录取,最终首届只招收44名,第二届招收48名,学员素质参差不齐。对应于不同的学制,学校对入学资格会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在招生广告中言明:“凡初中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者,得应预科考试;凡高中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者,得应本科考试;凡经行医三年以上者,得投考训练班”[13]。而属于内陆地区的建瓯国医传习所开办之初,计划招收正班(四年制)和补习班(二年制),后因报名和符合正取条件的学员数量较少,只能“暂缓开班,先办补习科一班”[14],学生仅40人。该时期医校主持者虽然立志扩大办学规模,但对于生源数量并不一味贪多。厦门医学传习所(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的前身)因办学质量优异,要求入学进修者为数日多,所长吴瑞甫“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对生源严加筛审,非有一定医学水平者,即使亲朋善友,一概不予接受”[7]。
各个中医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制定了学习成绩考察评定、日常考勤和奖惩等管理制度。如仙游县国医专科学校对于学员学业进行全程考核,除入学试验另有规定外,尚分按月试验、学期试验、学年试验、毕业试验四种。学员的每学年试验成绩及操行成绩,列表报告学生家长,假使“学生如有应履行之义务尚未履行者,得停止其试验及毕业证书之授与”[8]。民国时期,福建各医校都主动邀请中央及地方医政部门派员监考毕业试验,及时将学期、学年和毕业试验成绩结果呈报中央国医馆进行备案鉴核。严格的成绩考核与日常考勤,推动校园良好学风的形成。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自从“开校以来,教授之精神讲解分明,惟恐听者之不明了,且一年之中执教鞭者曾无一时之缺席,此最难能可贵者也。学生之注意凝神静听,惟恐医理之不精深,非不得已之事情不敢旷课,学期试验,成绩斐然”[15]。
2.4 临床教学实习的开展 民国福建中医学校创办过程中,主持者对于学生临床实践较为重视,提倡学以致用,主动借鉴西医创办附属医院作为临床实习基地的培养模式。福州三山医学传习所在第4学年安排有实验治疗学、实习(临床讲义)课程,“学生实验,每日上午分派中西医院实习,并派各教员;门诊实习,每处约派五人及一学期轮流调整,以增知识而免固执”[16]。福州中医学社“数年来努力经营……最近将设立诊病室,由教职员分科担任诊察,以供学生实习”[17]。在此方面较为突出者,当属仙游国医专科学校,学校原就附设于医院之下,创办者温敬修最初的想法即是国医院“不特帡幪贫病之人,且预为医校学生实习之地”[18]。其后制定的学校章程明确规定:“本学校第三年级、第四年级学生得在国医院及指定名医处实习”[8],乃“由医校教员江谐、林伯渠、胡友梅兼任医院诊疗,同时指导学生临床实习工作”[19]。
不过,以当时福建中医学校的办学力量,欲创办附属实习医院并非易事。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创办伊始,校董事会即有建立附属中医院的计划,以便安排学生临床学习,惜因诸多原因而未能实现。1932年,校长蔡人奇在纪念医校建校一周年的文中,对此流露出遗憾与憧憬夹杂的心迹:“反观吾校此举,尚付阙如,吾人所以日怀煞憾也。尚望诸君竭绵薄之力量,向外醵资。此举有成,不独吾校之光,抑亦社会之福也,吾愿与诸君共勉之”[15]。附属医院迟未建立,成为学校管理者心中一大遗憾。时局动荡和经济萧条,最终使得建设附属医院的计划无疾而终。对于学员临床见习实习,校方只能通过安排学生到市区各名医诊所实习而加以弥补。
3 结语
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的兴起和发展,为本地区中医人才培养和中医学术传承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
第一,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尽管在数量上位居全国前三,但这些学校普遍持续时间较短,没有产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中医教育机构,其社会覆盖面和知名度不但无法与上海、广州相比,即便与北京、山西等地的中医教育机构亦无法比拟。民国末期中医师检核委员会审核全国各地中医学校的办学情况,确定了颁发毕业证书直接有效的中医学校及需要面试的中医学校。截至1947年,中医师检核委员会历次会议通过准予及格的中医学校,福建地区仅有四所入选。
第二,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教育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产生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东南亚中医药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办学期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学生,纷纷来厦报名入学。这些在厦门学习的海外学生,成为东南亚各国中医药界的中坚力量。该校创办人吴瑞甫移居新加坡后,组织当地中医界华侨成立新加坡中医师公会,并积极筹备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吴氏去世后,其嫡传弟子陈占伟、曾志远、游杏南等人继承先师遗志,于1953年创立新加坡中医专门学校,其办学理念和思路与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如出一辙。
第三,民国时期福建中医学校教育开创了海峡两岸合作办学的先河。民国时期,日本殖民政府限制台湾中医发展,一批致力于中医事业的仁人志士远赴大陆研习中国传统医学,他们返台后不但个人无法注册获取行医执照,复兴台湾中医
的愿望更无从实现。毕业于上海中医学院的台湾人杨忠信联络台湾苏锦全、福建贺仲禹等志同道合者,在厦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于鼓浪屿创设“华南中西医学专门学校”,以招收闽台地区有志于中医者为主。闽台通力合作,双方共同编纂教材,开展中医教育,为民国时期台湾中医药的存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