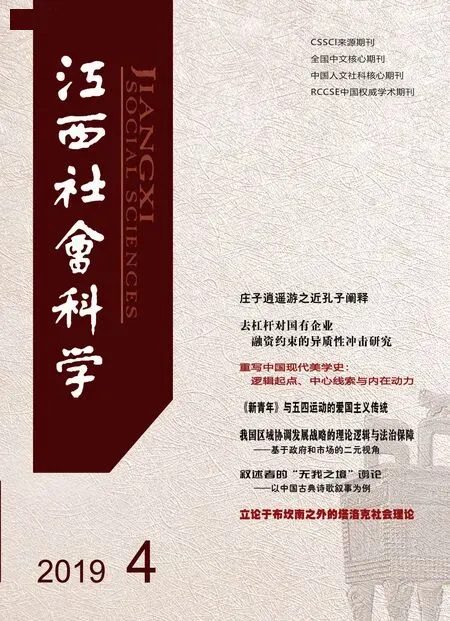晚清民国词学观念的演变
——以论词绝句为考察对象
晚清民国时期的论词绝句,普遍体现出两大倾向:一是在取径宗范上,表现为由习效姜夔、张炎转变为标举苏轼、辛弃疾;二是在艺术尊尚上,表现为由尊南宋抑北宋转变为抑南宋尊北宋。晚清民国时期词学批评与艺术宗尚在论词绝句领域的这两大变化,是不同社会文化、时代精神所催生与引导的结果,显示出我国传统词学所内含的生生不息之精神及所呈现之独特面貌。
有清一代,乃词体的中兴时代。继元明词体的渐趋寥落,清词在一片颓然灰败中重现出盎然的生机,在词学史上格外引人注目。清词的璀璨流丽,并非是简单地对宋词发展盛况的继承或沿袭,而是一种既为偶然、又为必然的文学现象。词体“要眇宜修”的抒情美质,决定了它将在某一时期脱离文学发展的固定轨道,而分出异彩纷呈的一支。论词的风气,常随着创作的兴盛而发展。以清词中兴背景系之,晚清时期词的大量创作为论词绝句提供了宽广丰实的批评场域,晚清论词绝句的发展同样迎来了它的春天。而经历有清一代蔚为大观的论词绝句创作,民国词坛为其流风余韵所惠,犹能沿波得奇。这两个时期,其论词绝句一脉相承,却又有着不同的词学宗尚与取径引导。
一、词人宗范之变:从取径姜、张到标举苏、辛
明清易代之际,云间派领袖陈子龙登高而呼:“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1](卷二)倡导以远承诗骚而来的比兴传统言词,为词体在新境遇下的革陋图强指出了一条新路。陈子龙的这一观念,不仅引导云间后学,更为清词的衍化奠定基调,对有清一代的词风无疑产生不小的影响。继轨于此,浙西派盟主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提出:“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2](卷首)本就起于市井饮水之处的词体,即使在发展炽盛的两宋时期,仍以俚俗的姿态保持着与民间的紧密联系。不满词体流于尘俗的朱彝尊,力倡“词以雅为尚”,为雅词与格调卑弱的“巴人之唱”严分疆域。其《陈纬云〈红盐词〉序》认为:“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3](卷四十)也即是说,词欲达乎“雅”,并非无术可循,便是要承衍《离骚》中的美人香草一脉,以“寄托”为入门阶陛,用比兴托意之法补救其固有的陋处。在《黑蝶斋诗余序》中,朱彝尊为侪辈学词指出路径,“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词莫善于姜夔”。[3](卷四十)在填词实践中,他又将堪与姜夔相鼓吹的张炎作为追摹对象,自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珮令·自题词集》)。朱彝尊揭举“醇雅”,主张取法南宋,并以拔于流俗的姜夔、张炎为学词鹄的,遂开一代宗风,以至于有清一代,“家白石而户玉田”。
论词绝句发展至晚清,播扬姜、张之风习犹存。谭莹《论词绝句一百首》(之七十二)云:“石帚词工两宋稀,去留无迹野云飞。旧时月色人何在,戛玉敲金恐拟非。”[4](P457)张炎《词源》曾道:“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5](P259)在张炎看来,词“皆出于雅正”,为他所指斥的柳永、周邦彦等人,其词皆失于雅致正则。几为张炎设为立论之基的“雅正”一词内涵纷杂繁琐、包蕴深厚,然姜夔之作却独秀于词坛,不失雅正,“特立新意,删削靡曼”,既有立意的高雅超拔,也未失用语的典丽清雅,故足为方家。谭莹从张炎之处借语,对姜词的推赏溢于言外。其评张炎又云:“悲凉激楚不胜情,秀冠江东擅倚声。词格若将诗格例,玉溪生让玉田生。”[6](P214)在谭莹看来,张炎词中至佳处不在“清空”,而在“悲凉”。张炎经历半生富贵后陡然遭遇国家之变,原本风流自赏的他以有限之身历经巨大的时代悲痛,心情激荡,遂发不平之鸣,后半生的失意寥落便是其苍凉之音的源头。“悲凉激楚不胜情”一句,化用四库馆臣之评:“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7](P1822)谭莹认为,张炎之词能媲美李商隐诗作,二人自有一段风流,而张词的超拔脱俗正缘此“满心而发”处。华长卿《论词绝句》(之二十五)云:“缝月裁云推妙手,敲金戛玉诩奇声。咏梅绝调高千古,岂止词华媲美成。”[4](P496)南宋诗人范成大对姜夔极为推许,赞其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及至明代,毛晋又以此移评姜夔之词。张炎在《词源》中云:“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5](P266)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也道:“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8](P64)华长卿以此本事入诗,可知其揄扬之意。亢树滋《题宋浣花词稿》云:“镂月裁云笔一枝,个中情味几人知。妒他小宋风流甚,一瓣香薰白石词。”[4](P543)谓宋志沂词中的韶秀之处,皆瓣香姜夔,一方面昭示出姜夔是以宋志沂为代表的词家心摹手追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显现了作者对姜词的肯定。狄学耕《怀人绝句五首》(之一)云:“流传一卷水云词,能把姜张正脉持。”[4](P585)《水云楼词》乃蒋春霖所作,其能脱却浙西、常州两派窠臼,自立一宗,狄学耕以“姜张正脉”称赏其词,足见出姜、张二人对于清词创作的本体性意义。陈作霖《题张次珊通参词集》(之三)云:“老来绮语待君删,自愧填词律未娴。宗派欲寻正法眼,瓣香白石玉田间。”[4](P606)实示姜夔、张炎一派乃为时人公认的学词路向与创作门径。
宋代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曾云:“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吾宋之兴,宗公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犹祖其遗风,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而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艳咀味,尊于朋游尊俎之间,以是为相乐也。”[9](P249)词体发展之初,长期在“花间”的冶游使它无可避免地形成软媚柔婉之风。早期词体怡情助兴、佐酒侑觞的娱乐化性质,更加速了它向绮艳茖丽风格的靠拢。陈洵《海绡说词》云:“温韦既立,正声于是乎在矣。”[5](P4837)《花间集》不避俗艳之笔,多吐风月闺音,词境较为狭窄,风格以轻艳婉转为主,表达上崇尚婉曲细腻、幽微蕴藉。可以说,它不仅设立了一种后人可学的范式,更确立了词体风格的本色特征。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之风熏染词坛良久,直至苏轼提出“以诗为词”之论,别启户牗,为词体拓疆千里,词体才大开声色而活力还发。胡寅《酒边词序》云:“唐人为之最工,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10](P595)词导源于花间,不久便为处于安逸闲适生活中的士大夫阶层所习染,播而为浇风,熏然成俗,流传甚广。一方面,它上承南朝宫体诗之余绪,本就不失绮色;另一方面,又为其“用资羽盖之欢”的性质所拘局,内容多囿于艳情绮思,词体便在文人拟女音以合流俗的举动中倍加靡丽,逐渐陷入言必及风月的抒情格局。而一旦“言情”成为词体展现自身的唯一合法路径,它便难与庸俗卑下的文体性质撇清关联。至于北宋,“艳科”一道已曼衍繁昌,词人多以男儿之身衍为女调,用辞造语极尽缠绵却湮没了主体自身,本用以抒表情性之作,反将人们脏腑中的烟云尽数遮掩,使得真情衰矣。自冯延巳、李煜等人以“我”入词始,词坛对以直寄其意之行径似乎不再那么讳莫如深。
北宋中期,伴随着词人以词体抒志意、表情性的审美诉求,苏轼有意识地提出“以诗为词”“自是一家”,将主体情性表现大量引入于词中,进而别开豪放一路,拂散了自五代以来在词坛弥漫已久的风尘之气。在苏轼的观念中,“词”仍是一种文学体式,“诗”却更多地指向了一种风格。他力主“以诗为词”,并非要取消词体的相对独立性而使诗词之体合流,进而令髙居于文坛正统地位的诗体兼并尚被轻视的词体,而是旨在将诗之创作法则引入于词的创作中,在“诗庄词媚”的抒情范型之外另辟蹊径,以期扩大词体的表现功能,为以词体寄意述情提供方便法门,从而将词体从尘下之所拔至高妙之境。这与先前词坛纯以词体为娱宾遣兴之具相比,显然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苏轼注重以主体的情性才思入词,将香艳婉媚之体变作洪钟大吕之音。与其相类似,辛弃疾更多地寓时代精神于词,将个人抱负与时代悲愤一寄其中,真力弥满,摧刚为柔,同样为词体的振衰起弊做出独特的贡献。后世不乏学苏、辛者,蔚然成为一个流派。
民国时期,汪朝桢《倚盾鼻词草题辞》云:“射雕手段上强台,压倒当时词翰才。拍到苏辛豪放句,天风海雨逼人来。”[4](P697)苏轼《鹊桥仙·七夕》曾云:“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女。风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银河微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汪朝桢以“天风海雨”谓苏、辛词中的壮志豪情,甚为彰显其推许之意。柳亚子《题俞剑华〈小窗吟梦图〉》云:“梦窗七宝楼台耳,南宋词人貉一丘。欲向韩陵求片石,霸才青兕我低头。”[4](P771)其《为人题词集》云:“慷慨悲歌又此时,词场青兕是吾师。裁红量绿都无取,要铸屠鲸剚虎辞。”[4](P771)可见其追慕之心。辛弃疾以浩然才气在词中寄寓爱国情志,使其词壮伟豪逸,催人奋起。柳亚子素斥南宋骈艳词风,却独重辛弃疾之作。他认为:“在南宋词人中,也有崛然奋起,好和北宋词家抗手的,却是稼轩。”[11](P662)“青兕”一词,为《宋史·辛弃疾传》中之语,其云:“义端曰: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后人便以此代称辛弃疾。在柳亚子诗词中,“青兕”意象数次出现,其词亦多发豪放之声,这也可从侧面见出其推崇辛弃疾之意。高旭《论词绝句三十首》(之十二)云:“关西大汉粗豪甚,铁板铜琶未敢夸。除却乘风归去曲,倾心第一是杨花。”[4](P727)又云:“稼轩妙笔几于圣,词界应无抗手人。侠气柔情双管下,小山亭酒备酸辛。”[4](P728)即可从此窥见高旭对于苏、辛二人的称赏之心。
豪迈壮伟的士人风骨,沉重悲怆的文人诗心,锐意进取的男儿志气,与我国文学中源远流长的比兴寄托传统一道,共同酝酿出苏、辛词中的浩然正气与深广内蕴。苏、辛二人因主体的磅礴才性雄居于文坛高处而能望远,更以高世之才冲破词以婉媚香艳为本色的藩篱,别开一境,对词体的发展无疑有着救弊补偏之功。民国时期论词绝句之推举苏、辛,从中可见出的,便是时代精神的更迭与审美风会的转移。正如吴锡麒《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所云:“词之派有二:一则幽微要眇之音,宛转缠绵之致,戛虚响于弦外,标隽旨于味先,姜、史其渊源也,本朝竹垞继之,至吾杭樊榭而其道盛。一则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抗秋风以奏怀,代古人而奋愤,苏、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铜而其格尊。”[12](卷八)从晚清至民国时期,论词绝句由推重“幽微要眇之音,宛转缠绵之致”衍化为追求“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便是时代审美与文化精神移易变化的结果。
在一个时代被引为主流的社会精神,往往会同时延展为两个分支。一方面,它以刚硬的理论形态存在于社会政治思想之中,为社会基本体系的形成搭建躯干;另一方面,它又以感性的方式表现为各种类型的文艺作品,以柔和的形态为社会精神添叶着花。而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便是杂融兼和二者的产物。文艺思想与社会精神,基本上可以互相发明。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既可以从文艺思想中寻迹,又引导着文艺思想的走向。有清一代,统治阶级为固化其政权,大施“文字狱”,饱学之士为避无端灾祸,有意隐藏锋芒,避谈现实,转而埋首故纸堆中寻求精神的自足,并在历史发展惯性作用下将此风绵延至晚清。晚清学者们设立学词典范,所求并非“有补于世”,而纯为词体创作寻求可循之径,姜夔、张炎乃为其所认可的高品词人。更为现实的原因在于,彼时赫赫皇权对于士子思想的禁锢已渗透到每一个细微的举动中,为免无妄之灾,他们不得不淡化从笔下流露的个人情感。姜、张之词的清虚醇厚、骚姿雅骨正是一层坚硬的外壳,能将词人的真实情愫深隐于字里行间,其意图旨向实非浅尝之人所能探也,对噤若寒蝉的清人而言无疑是有利的选择。王鸣盛《评〈巏堥山人词集〉》有云:“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5](P3549)以姜夔为首的“清空”派词人,在婉约绵丽与豪宕疏放之外自立醇厚骚雅一宗,在词史上影响甚巨。朱彝尊论词主“雅”,既是他在云间派复古主张“染指遂多,自成习套”,以致被尚俗之音充斥境遇下所推扬的补救解脱之法,又是他以经学家身份所发现的行之有效的填词门径。另一方面,词体作为“音乐的产儿”,兼有音乐与诗歌的双重属性,其“倚声”别称就直接体现了它与音乐的难解之缘。词体随此流波而向前发展,最终在文体的独立化运动中被剥离了与音乐的黏合关系。在词体正式成为“案头文学”之前,以音律绳约词体乃是作手的普遍共识。朱彝尊便重视音律,他在《水村琴趣序》中批驳明词云:“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3](卷四十)明词音律不协,而姜夔“审音尤精”,朱彝尊之推崇姜夔也有音律上的考虑。张炎作为姜派词人,为朱彝尊所追摹亦在所难免。朱彝尊之学张炎,也有身世情怀类似的缘故,所体现的乃是知识分子超越时空的知己意识与认同心理。朱彝尊开此宗风,为清词的创作另开“清空”一路,此风流传甚广,绵延至晚清未曾断绝。如此,晚清论词绝句之标举姜、张,便是题中之意。
逮及民国时期,社会背景发生巨大变化,现实的喧嚣纷乱震醒了知识分子沉睡的耳膜,连绵的战争令他们不断反思,国家的处境更令其痛心不已。他们需要的不再是不涉功利的纯词,而是充沛的爱国热情,是鼓舞人心的激昂力量,更需要有人为正处于失落和迷茫之中的士子精神引路。苏、辛词中的豪宕雄杰之思、慷慨激昂之气,对民国时期论词绝句作者而言,无疑是符合时代主题的“力”的艺术。这种积极“补世”的人生心态,正是民国时期社会精神的核心。苏轼与辛弃疾在时代波折的催化下所显现出的风流人品,更是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追求的中国传统文士们寻觅已久的人格范式。在历史情境的变化下,论词绝句所设立的词人宗范自然也会随之演变。
二、整体尊尚之变:从尊南宋到尚北宋
唐诗有初盛中晚之分,宋词则有南北宋之尚。早在南宋时期,柴望《凉州鼓吹自序》即云:“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莫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仿佛焉。”[13](P284)此说将生活在北宋宣和、靖康时期的周邦彦、康与之与南宋时期的姜夔区别对待,已初孕以词之风貌对南北宋进行划界的意识。词至于宋,技艺已经纯熟,诸体可谓兼备。宋词作为“时代之文学”,在艺术上已达自足地步,故而词体风貌深受其内容的影响,会在不同社会环境作用下形成迥异的美学特色。历史上的南北宋社会环境自然悬殊,也同样影响了时人的创作,使南北宋词呈现出各异的面貌,从而引发词史上积日累久的南北宋之争。及此,民国时期论词绝句多“谓文学后不如前”,以为北宋词实优于南宋词,这与清代论词绝句多推举南宋、贬抑北宋大有不同,亦可从中见出词学观念与批评风气的变迁移易。
明清之交,云间派偏取五代北宋之词。清初,朱彝尊一变时风,他在《词综·发凡》中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11](P919)以之为代表的浙西派,在明末清初词曲合流、词之内容愈见俗化的背景下,独标醇雅清虚,乃以词风本色的姜夔、张炎为师法对象。此论甫出,影响渊远,一时论词之人必举姜、张。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云:“至朱竹垞以姜、史为的,自李武曾以逮厉樊榭,群然和之,当其时亦无人不南宋。”[5](P3530)道出了自朱彝尊后词坛群起和之,一时间论词必举南宋之盛状。嘉庆年间,为词欲“雅正”普遍风气所迷,浙派末流一味在声律格调上着力,酿成饾饤寒乞之习,下笔时流失真性,取径偏狭,空砌辞藻,常有无病呻吟、为文造情之举。张惠言为挽此颓风,领导常州派异军突起,乃以“比兴”“寄托”之旨托尊词体,而推崇王沂孙。行至晚清,常州派后进王鹏运、朱祖谋等人,又转而膜拜吴文英,一时推为极则。正如吴征铸在《评〈人间词话〉》一文中所云:“有清一代词风,盖为南宋所笼罩也。”[14](P117)这样的创作倾向在清代并不鲜见。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云:“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园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此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矣。”[15](卷四十一)王昶极为叹赏姜夔、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之心意高洁,认为诸人之词既天真可亲、颇显深情,又技巧圆熟、达于高格,非北宋词人所能望其项背也。郭麐《灵芬馆词话》又道:“词之为体,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竹垞之论如此。真能道词人之能事者也。又言世之言词者,动曰南唐、北宋,词实至南宋而始极其能。此亦不易之论也。”[5](P1504)观其宗尚,自是以南宋为归,此与朱彝尊之论不谋而合。视南宋之词为嫡系的论词倾向,在清代论词绝句中也多有浮现。如席佩兰《题吴慰光〈小湖田乐府〉》(之四)云:“不师秦七与柳七,肯学草窗与梦窗。一片野云飞不定,并无清影落秋江。”[4](P225)其谓作词不须肖北宋秦观、柳永,而应学南宋名家周密、吴文英。“野云”一句,为张炎称赞姜夔词作清空质实之语,则席佩兰推赏之意可知矣。赵同钰也云:“姜张风格本超然,写遍蛮方十分笺。一洗人间筝笛耳,玉箫吹彻彩云边。”[4](P228)在同样受崇南宋之风笼罩下的晚清论词绝句中,也多有关涉之语。丘逢甲《题兰史〈香海填词图〉》(之一)云:“南宋国衰词自盛,各抛心力斗清新。”[4](P674)南宋国衰词盛,众词家抛尽心力、各逞其才的景象如在目前。杨恩寿评朱彝尊曰:“风气能开浙派先,独从南宋悟真诠。自题词集夸心得,差喜新声近玉田。”[4](P599)杨恩寿虽未直言他对南北宋宗尚的态度,却仍可见出朱彝尊所倡的崇南宋与学姜、张之风习对国朝词家的渗透。曾习经《题〈冷红簃填词图〉》则道:“西风久下藤州类,社作今无竹屋词。解识二窗微妙旨,樵风一卷亦吾师。”[4](P685)又可见清人以南宋周密、吴文英为师。足见有清一代,世人言词多称南宋。
及至清末,王国维较早表明对南北宋尊尚的立场。其《人间词话》云:“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16](P240-241)对南宋词贬抑之意大体可知。其评姜夔曰:“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16](P212)评吴文英曰:“映梦窗、凌乱碧。”[16](P215)王国维认为,南宋词人中,“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16](P213)逮至民国时期,论词绝句多以北宋词为宗尚,反视南宋词为乱流,从王国维之处已见端倪。
民国时期,夏敬观《蕙风词话铨评》称:“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于北宋。”[5](P4585)夏氏言南宋之词较北宋之作纤巧有余,不若北宋词之朴拙更得真味。其《忍古楼词话》也道:“宋词少游、耆卿、清真、白石,皆余所宗尚。梦窗过涩,玉田稍滑,余不尽取。”[5](P4768)除去姜夔一人,其所好者皆为北宋词家,而他所批驳的吴文英与张炎,又皆属南宋。夏敬观《还友人词卷》还云:“淮海清歌玉貌人,梅溪大雅不伤新。”[4](P722)激赏秦观、史达祖词风本色、清丽雅正,盖可见其称誉北宋词之意。张素《暑日杂诗》云:“学诗须学初唐诗,学词须学北宋词。初唐北宋不易到,清淡微远是吾师。”[4](P735)谓北宋词“清淡微远”,读之如食橄榄,咀嚼有味,直将北宋词人作为正统的规摹对象。赵熙《论词》更云:“词家北宋最光昌,犹似诗人有盛唐。南渡才人工织锦,机声轧轧碧鸡坊。”[4](P688)盛赞北宋之词足与盛唐之诗相媲美,几乎有溢美之嫌。赵熙痛诋南宋人作词有如“织锦”,乃责其堆砌辞藻之弊,实与夏敬观斥南宋词过于纤巧之论一脉相承。梁启勋《曼殊室词话》云:“词由五代之自然,进而为北宋之婉约,南宋之雕镂,入元复返于本色。本色之与自然,只是一间,而雕镂之与婉约,则相差甚远。婉约只是微曲其意而勿使太直,以妨一览无余,雕镂则不解从意境下工夫,而唯隐约其辞,专从字面上用力,貌为幽深曲折,究其实只是障眼法,揭破仍是一览无余,此其所以异也。”[17](P2944)词体寥寥数字,尽缚于纸笺之中,而其所涉所指则别开字面之外,远遁于无形。词的“幽约怨悱”之意,要求词人以一唱三叹之笔运绵邈蕴藉、宛转幽深之思,以达成“曲径通幽”、一石落而涟漪不尽的艺术效果。故而,词体隽永委婉、曲尽人情的文体特性,决定了填词之人必然追求寄意的深隐与情感的丰足。词家对词体幽隐之美的孜孜以求,又必然使词作丰富多样的内涵深藏于字面之外,而直扑读者眼前的,仅是字面上一些起着暗示或象喻作用的意象群。于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为众多词家所严格遵循的“思深言婉”的抒情程式,常导致词体的襞积纤巧、雕镂板滞之病。在梁启勋看来,北宋词“婉约”有法而能“言长”,南宋词则不求意境思致之新异,专在字语的陌生化上用力,雕琢过度以致语涩旨枯,人力斧凿痕迹彰显,难免失之自然。赵熙之谓南宋词人专工“织锦”,亦是此理。
柳亚子同样注意到南宋词的这一弊病。其《南社纪略》谓:“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和南宋词的,我却偏偏独持异议,我以为论诗应该宗法三唐,论词应当宗法五代和北宋。人家崇拜南宋的词,尤其是吴梦窗。我实在不服气,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子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18](P84)柳亚子更在《词的我见》一文中为词定品道:“我以为唐五代的词最好,北宋次之,而南宋为最下。”[11](P662)其论词绝句亦云:“梦窗七宝楼台耳,南宋词人貉一丘。欲向韩陵求片石,霸才青兕我低头。”[4](P771)张炎指摘吴文英之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柳亚子不啻对意象繁复、风格浓艳的吴文英之词持贬斥态度,更认为词至于南宋,茖丽之流弊益多,除辛弃疾外,其他词人皆未能脱此窠臼。刘咸炘亦承此论,其《说词韵语》(之十二)云:“落日长烟穷塞主,疏桐缺月见幽人。如何辛陆姜王外,面目模糊认不真。”[4](P790)“落日长烟”“疏桐缺月”之句,乃从范仲淹《渔家傲》“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与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二句脱化而来,刘氏欲借此说明北宋词人“各名于世”。刘咸炘之推举北宋,贬抑辛、陆、姜、王之外的南宋大家,乃因比起北宋词人之各有面目,除却辛弃疾、陆游、姜夔、王沂孙,其他南宋人作词则多流于空疏浮薄,骨气笔力未能入词之腠理,在风格面貌上显得如出一辙,更无甚性情气象流贯于其中。
除开直接表述对南北宋词之比较的言论,亦有间接涉及之语。张尔田评陈洵《海绡词》一首中道:“解从南宋溯清真,始信霜腴有替身。”[4](P713)这里,张尔田指出了一条学词的根本路径,即从南宋上溯北宋,由吴文英上溯周邦彦。自南而北,由易入难,沿流溯源,方为学词正途。陈匪石《宋词举》之举隅即用此法,此更与周济《宋四家词选序》中所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的学词门径有异曲同工之妙。逆溯学词之举,乃有寻源探本、剥蕉取心之意味,张氏沿袭此法,亦露其视北宋词为本体的持论取向。
自南北宋之尊尚的立场而言,民国词坛的整体倾向较晚清词坛有着显著不同,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自然不胜枚举。总的来看,朱彝尊之独取南宋,一方面是其以姜、张之“雅”对云间后学尚俗风气的反拨。他在《静惕堂词序》中云:“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昭宣六义,鼓吹元音。”[19](P543)希图用比兴寄托之法比附词体,力戒浮艳,刻意淡化风月以洁其香艳流俗之态;另一方面,则缘于对慢词的推扬。其《鱼计庄词序》云:“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3](卷四十)慢词调长字足,可铺张情节,更宜于抒情。对于慢词的偏嗜,在朱彝尊的创作中已有体现。又有原因在于,如前述及,清代的政治高压使知识分子多处于自危的境地,在治学上亦存有止祸之心。盖如刘缉煕所言:“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北宋直,南宋曲。”[11](P1280)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也曾云:“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5](P1630)南宋词中的比兴寄托、委曲深婉,无疑是阻碍文学家与当朝政治产生直接关联的一道天然屏障,这正是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处于穷途的避祸之法,故自朱彝尊倡扬此风,便为四方之士所推崇。逮至民国时期,西学的渐入开放了知识分子原本闭塞的视听,国家危难更使他们心起壮志。此时,南宋词的寄意深曲、刻意雕缋便显出了婉媚香弱之态,对多向往建立事功、救国于危难之际的民国词人们而言无疑是值得诟病的。晚清学者普遍存在的惊悚避祸之心使他们独贵于意义之“能留”,于词则偏重其“不肯直叙”,与之相反,民国词人们更喜直率的“真”音,崇尚刚健的词风。结合所反映的词坛倾向来看,其论词绝句之大多推尊北宋,盖有北宋之词较南宋之作更为自然天真,稍加斧凿却不至纤巧,漫有兴寄却不至肖似,而能示词作真情本色之缘故。总而言之,词坛的整体倾向与社会形势息息相关,太平之世多耽溺于莺歌燕语之什,变荡之际则多贵于激切胸臆之作。实际上,词学所宗尚之北宋南宋,并无断然的高低之分别,乃时势所然也。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从晚清至民国时期,论词绝句于论说取向上的演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词人宗范显示出极大的不同,表现为时人由取径姜夔、张炎转变为标举苏轼、辛弃疾;二是艺术尊尚发生重大的变化,表现为时人由尊南宋、抑北宋转变为尊北宋、抑南宋。词学宗尚反映的乃是一个时期词坛的整体倾向,其审美宗尚的演变更是社会变革在文学之体上的集中体现。晚清固权而致人人封缄思想、偏安一隅;民国求新而令西学渐入,眼目得以开放,国家危难又使民众壮怀激烈、心中愤然。这两种迥异的时代风气与社会环境,导致晚清民国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词的审美上也生成完全不同的诉求,并形成大相径庭的论词风习。晚清民国时期论词绝句所揭橥的词学演变,显示出我国传统词学所内含的生生之精神及所呈现之独特面貌,它对于我国传统词学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朱彝尊与书法篆刻家的交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