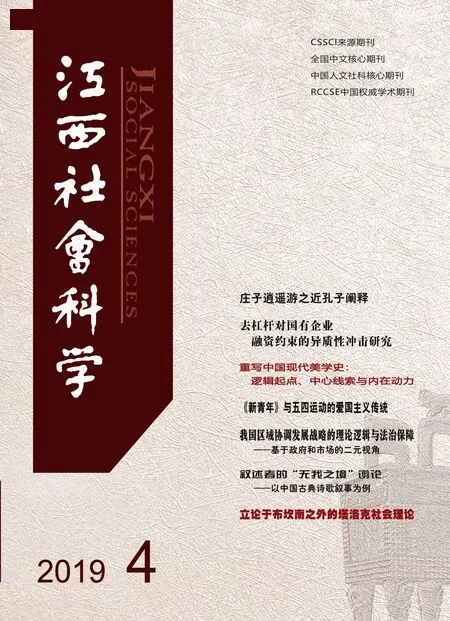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反思与自觉
徐复观不论在人生经历或学术思想上都有特殊贡献,尤其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上,徐复观有着较早的反思与自觉。反观徐复观思想的具体发生,不难看出,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首先来自于对当时学界两种不同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即以傅斯年为代表的语言实证进路和以牟宗三、唐君毅为代表的形上思辨进路。而这两种诠释进路的对象化、抽象化、知识化带来的脱离现实人生、丧失儒学真精神的问题,使得徐复观返归自我,对自我精神价值进行重新定位。徐复观选择回归现实世界的农村乡土,肯定人性中的心性力量。而在学术研究中从具体生活的角度出发,强调研究者在“追体验”的过程中与古人心灵世界的契合。因此,“追体验”的展开是一个从具体世界层层提升,指向超越性价值世界的过程。对徐复观而言,这既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其目的本身。
在20世纪港台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1904—1982)不论在人生经历或学术思想上都可谓独树一帜。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遭遇的冲击,毕生殚精竭虑地思考“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上,徐复观有着较早的反思与自觉。他认为,学界至今为止并没有出现一部“像样的”关于思想史研究的综合性著作,他强调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重点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而这一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方法和态度的问题”[1](P2)。徐复观这里所谓的“方法和态度的问题”是一种如何进入古人思想话语世界的路径。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可能就会形成不同的诠释方法,而这一诠释方法是否贴合古人思想的语脉,则又成为我们理解古人思想的基始性问题。
一、两种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
徐复观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长期自觉地对研究方法进行思考探索,并最终形成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诠释方法。从徐复观的学思历程来看,他对思想史研究方法和态度的探索,始终伴随着对当时学界两种不同思想诠释进路的反思,本文以此为基点,展开徐复观是如何对思想史方法论进行反思。
与徐复观处于同一时代的傅斯年,对研究思想的方法论问题同样重视,并且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诠释进路中极具典型性。傅斯年提出影响最大的主张就是:“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研究起来终归只能是一门史料学,其表现出来的历史过程就是用自然科学工具来整理一切史料,所以近代历史学的范畴可以涵括地质学乃至眼前的新闻纸等科学技术。基于这一认识,傅斯年所谓的“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也就是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将历史看作史料而加以对象化的剪裁,在他的语境下,历史离不开人们对史料的处理。所以,史学的研究在傅斯年看来也就只是史料学,这一认识无疑是由其科学实证主义的诠释立场决定的。傅斯年曾在谈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方向时指明这一立场:
本所同仁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2](P276)
傅斯年认为,史学的根本要义在于史料所呈现出的“史实”,而不是急于在历史中寻找脱离史料的“史观”。显然,他的这一立场是典型的科学实证主义,他所著《性命古训辩证》一书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方法对思想史进行诠释。
傅斯年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遭到徐复观的强烈批判。徐复观指出,傅斯年所著的《性命古训辩证》表现的科学实证主义是将西方语言学与清代乾嘉学派训诂方法结合起来的结果:
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常常是把思想史中的重要词汇,顺着训诂的途径,找出它的原形、原音,以得出它的原始意义;再由这种原始意义去解释历史中某一思想的内容。[3](P1-P2)
徐复观在这里将傅斯年语言实证法与清代乾嘉汉学的训诂考据相比附,批评其将字义从思想发生的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仅从语言学的角度还原其字义,就会忽略不同字义在不同思想系统和话语背景中的具体性。由此形成的原义也就只是抽象而独立的文字义,这对思想史的研究意义不大。在徐复观看来,这样一种仅找出原形、原义、原音的语言实证法难以满足思想史研究的要求。因为就语言本身来说,它的原始意义并不足以诠释自身,也就是说,语言在被思想运用的过程中,其含义已经随着时间而发展演变,语言实证主义忽略了语言的变化性。同时,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字具有特殊性,所以,从语言的源头找出思想演变的脉络是有益处的,但要注意的是每个思想家运用的名词是在不同语境下进行的。因此,他反对以乾嘉汉学为代表对思想史进行抽象、客观的事实描述。
但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并不反对将文字字义的考据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相反,他认为学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在字到句再到章的积累过程中,清代的训诂之学是理解全书之义的基础。也就说是,徐复观并不一昧反对考据之学,而是反对清人以及沿此进路的今人以语言实证的方式割断思想与生活、人生的关联,进而将思想文化发展成一套烦琐的知识。这一方式与现实人生脱离的同时也就与古人的思想语脉彻底绝缘。这也是徐复观对以语言实证为进路的学者批评理由所在。
唐君毅、牟宗三与徐复观同为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三者有着共同的文化价值关怀。但在具体诠释进路上又有所差别。黄俊杰较为准确地指出这一差别,他认为徐复观的思想史是人的观念与残酷现实战斗的血泪史,而牟宗三与唐君毅在历史的进路上走上了超越永恒的天道在人间的展现:“如果说徐复观将人视为在历史洪流中艰苦卓绝的战斗主体,那么唐、牟可以说是将人视为超越的存在。”[4](P22)黄俊杰在这里指出的这一思想差别正来自于徐复观对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唐君毅与牟宗三在面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困境时,选择在中与西的哲学会通中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承担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唐、牟二人在如此强烈的现实关怀下,一方面在为学态度上对儒家抱有极强的信仰精神,另一方面则又不得不从西方哲学的“客观了解”进至“理性了解”才能容纳于真实的生命之中。因此,他们所谓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是以其生命信仰与理论思辨为基础的。正如唐君毅所言,他的研究方法是“即哲学史以论哲学”,认为哲学范畴的诸义理是永恒的,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会被哲学家以不同的言语来表述,从而展现出不同的谓述形态,故对哲学史的梳理便能透显义理之本身。
可以看出,唐君毅是就哲学史体系内的概念系统言思想,而徐复观对此并不赞同,他主张从具体的历史境遇出发,强调思想的具体性和整体性,反对哲学概念的形上学倾向。在此基础上,徐复观对其师熊十力以及唐、牟都有批评,他认为尽管上述三人都对中国文化用功很深,但他们的为学进路却是从具体生命、行为反溯形而上的天道、天命,这样的反溯根基不稳。徐复观首先肯定熊十力、唐君毅都对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认为此二人受西方体系哲学的影响,反而把中国文化发展之方向弄颠倒了。徐复观之所以如此评价熊、唐二先生,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诠释顺着思辨哲学而取径,文化的精神价值也就会与人生社会越离越远,最终脱节而成为一纸空言。值得注意的是,徐复观反对形而上学并不是指谓儒家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而是纠偏脱离人生实际生活的抽象思辨。所以,徐复观十分注重中国文化的具体性智慧,他曾在评价孔子的思想性格时说道:“孔子把他对人类的要求,不诉之于‘概念性'的‘空言',而诉之于历史实践的事迹。”[5](P157)这是徐复观反对形上学的原因所在,即在他看来,研究者应当是在具体的人类历史实践中去体会人类的理性,而不是停留在概念性的思辨中。
二、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关怀与自我定位
徐复观对科学实证主义和形上思辨两种不同诠释进路的反思,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体贴和关怀。因此,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立场和关怀,也就成为我们理解他对这两种研究进路的反思,以及其自身研究进路侦定的中间环节,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1949年以后,港台当代新儒家的学术精神世界共同面对“中国文化往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一问题的展开过程中,新儒家的学者们始终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认同和现实关怀。在文化价值的认同方面,他们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精神有着较强的价值认同,在他们看来,儒学绝不是与我无关的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而是与个体自身息息相关的安身立命的价值关怀。新儒家在传统学术的诠释方向和立场上始终是价值论的。因此,新儒家对儒学的研究是一种价值关怀的认同,而非客观的事实描述。而在现实关怀上,新儒家面对时代对民族文化的冲击,试图从儒学研究中找到民族精神的希望和出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中,不论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塑还是对现实政治的针砭,都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既是新儒家学术研究中蕴含的基本特征,也是港台新儒家的共相,徐复观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徐复观有着较为鲜明的个人学术风貌,时代给予他的“愤慨之心”成就了他的学术精神。他曾以四个因素总结一个人的思想成因:
一为其本人的气质。二为其学问的传承与其功夫的深浅。三为其时代背景。四为其生平的遭遇。[6](P563)
以此标准来看其人其学,不难发现,不论是时代背景抑或是本人的生平遭遇,众多复杂的因素造就了徐复观鲜明的学术特征。而这鲜明的学术特征便是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无不感受到那颗“感愤之心”,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在悲剧时代所形成的一颗感愤之心……最奈何不得的就是自己这颗感愤之心。”[7](P2)徐复观的这颗“感愤之心”既是他个人精神生命的跃动,也是他面对民族文化精神困境的感发,更是他在面对时代困境时激发出的精神跃动。与此同时,也是他重新解释中国文化的动机,这颗“感愤之心”的跃动既是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关怀所在,也是促使其重新解释中国文化的动力。
如果说徐复观治思想史缘起于时代与生平带来的这颗“感愤之心”,那么,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治思想史则需要他不断地澄澈自我,进而步入古人的思想世界。从徐复观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自我最为质朴的定位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饱含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孺慕之情。徐复观认为,农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孕育中华民族的土地,更是造就中华文化精神的源泉。他认为,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不在别处,而是在广大的农村之中。他在《谁赋豳风七月篇》中这样动情地言道:
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8](P72)
在徐复观笔下,农村乡土不仅是养育其个体生命的故土,更是孕育质朴、率真、忠孝、勤俭、善良等人性之质的故土。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关于人性的美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表征,也成为徐复观的精神故土。徐复观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录他作为一个流亡者的精神困苦:“流亡者的灵魂的安息地方,不是悬在天上,而是摆在你所流亡出来的故乡故土。”[8](P72)徐复观语境下的故乡并不是寄托乡情的故土,而是作为个体精神家园的源泉所在。那么,不禁让人追问:农村乡土作为徐复观的精神故土究竟承载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使得徐复观用她来表征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深入徐复观笔下的历史环境和人物,不难看出,农村乡土孕育的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世界,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本然地存在于实然的现实世界。在这样一个现实世界中,每一个人都生活于“我”的当下人生,既有生活中肩挑手提的艰难困苦,又有人性中最为美好的品质。在徐复观笔下,中国农民的纯朴、诚恳、率真就真实地扎根于现实的一元世界,并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中指向超越性的价值与意义的提升。可以说,徐复观之所以对现实世界如此认同,离不开儒家传统对现实的坚守,自孔子始对人性、心性力量的肯定,使得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都能在自身的生命中发掘出道德、价值的根源,自我的主体性通过现实得以彰显。正如徐复观所说:“每一个人,能在自己的一念自觉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之中生稳根、站稳脚。”[9](自序,P1-2)正是基于此,徐复观才会坚定地认为,农村乡土既是孕育中国文化价值的源头,也是其个人精神家园的故土,而这也正是儒家文化性格的表征。
如上所述,徐复观始终没有离开自身的精神定位,即从个体生命出发体验现实世界,始于关怀。他真切地感受到孔子的世界是具体的、有感情的:“孔子的最高任务,不是要建立什么形而上的理型理念,而是要在有感情的世界中尽到自己的责任。”[10](P778)在徐复观看来,儒家本无所谓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只是关注个体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安顿与成就,“现实”是儒家的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正是对现实世界和主体性精神的强调,使徐复观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对现实生命极强的关怀。关于这一思想特点,黄俊杰有着准确的概括,他认为徐复观在思想史研究中看到的首先不是概念,而是存在历史中活生生的人:
作为一个思想史家,徐复观与当代其他儒家学者最大的相异点之一就是,他对人的具体性与复杂性具有深刻的了解。……徐复观笔下的“人”是活生生的、实际参与生产活动的具体的人……[4](P44)
从黄俊杰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徐复观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与现实脱离的精英群体,而是立足于现实,在两千年来专制统治下为苦难人民寻求正义的鲜活形象。也就是说,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基于对人之存在的具体性的认知,而非“象牙塔里的‘知识游戏'”[4](P44)。而这样一种具体性的认知是在具体的历史生活情境中展开的,在这里,他们会面对生活的艰难困苦,会面对专制政治的压迫和苦难,也会面对自我安身立命的抉择。这正是徐复观的学术关怀所在,也只有这样活生生的具体活动的人物才是徐复观心中关于人的本质形式。这一认知不仅仅从他对中国文化学理性的认知而来,更是他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切身的体会而来。这也成为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关怀和基本定位。
三、追体验——徐复观思想史方法论的自觉
徐复观对思想史方法论的自觉,来自于方法的反思与自我精神的定位。不论是对方法的反思还是自我精神的定位,二者共同指向儒家强调的下学而上达的精神。这也就构成了徐复观进入古人思想世界的基本门径,即从具体而非从抽象出发。
徐复观对中国思想史理解与感悟,大多来自于现实生活的体验,而非形而上的逻辑推理。徐复观以具体的、生活的方式接近孔子,他说:“从具体生命、生活上去接近孔子,较之从形而上学,从思辨逻辑上去接近孔子,远为正确而亲切。”[11](P303)徐复观认为,孔子的思想本身就在具体生活中展开,这既是孔子的思想方式,也是儒家思想的特质。徐复观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思想家的特征是具体性而非抽象性,其原因在于中国思想家大多以生活体验而反省提炼自身学说,其思想学说的合乎逻辑性以活生生的而体验为前提。这也是徐复观所谓“‘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1](P3)。在这里,徐复观既认识到中国智慧的具体性特征,也看到了具体性中的理性成分。他认为中国思想的具体性并非个体的支离,而是在个体的内外生活境遇中具有的连续性、整体性的具体想表达。
上述对具体性智慧的理解也就构成徐复观治思想史的基本态度,他认为他在作思想史工作时之所以可以在混乱中找到清楚的条理,“主要得力于‘动地观点'、‘发展的观点'的应用”[9](P7)。徐复观这里所说的“动地观点”“发展的观点”主要是指在古人思想的研究中从整体而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思考一个人物、一段历史。换句话说,徐复观认为,一个人物的思想本身并非一种脱离于现实的抽象观念,其思想的形成、价值及其意义都是在生活境遇里的具体表达。以研究董仲舒为例,先将其人其学置于大一统专制体制下的历史背景,才会得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为专制体制套上笼头。就一段历史而言,一个思想系统在历史上的发生与演变是具有脉络化的特征,研究者想要进一步厘清思想形成的线索离便不开具体的发生过程。在《两汉思想史》中,徐复观对周、秦、汉的社会政治结构演变的个案梳理成为我们理解先秦两汉思想主旨的基础,他从具体制度问题出发,对问题的解决成为“思想史”的目的所在,由此进入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
反观徐复观所谓的“动地观点”“发展的观点”的方法论,不难发现,不论是对一个人物还是一段历史的思考,都离不开具体的、动态的、整体的方向,而其在研究过程中具体展开则表现为局部和全体的关系,徐复观总结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印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靠方法。”[1](P132)在这样一个具体地、动态地、整体地展开思想的过程中,思想本身也就不仅仅是观念事实的描述,而是一种意义关联的生成。在徐复观看来,思想系统是由思想者和他的研究对象共同构成的一张意义之网,所以对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呈现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性的一种对话性关系,而非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的抽象性思辨。这也就构成如何进入古人思想世界的基本问题。从具体而生活的角度出发,徐复观强调研究者与古人心灵世界的契合,并将此种方法称为“追体验”的工夫。他所谓的“追体验”是指我们在不断体会古人的作品时,作品本身会引导我们回到古人世界中去,这种引导与体验使得研究者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以致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尽可能站在作者的角度来体会作者本身面临的问题。
在徐复观的语境下,研究者对思想史追体验的过程,本身就与作者有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而非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在这种互为主体的关系中,徐复观认为研究者在愈深入自己的主体性的同时,就愈能进入古人的思想世界;同时,这种作用也是相互的,对古人的主体性世界研究愈深,也愈能体会自身的主体世界。对此,徐复观有着较为清晰的讨论:
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我们不仅是在读古人的书,而是在与古人对语。[1](P133)
徐复观认为,研究古人的思想,不仅是阅读他们的著作,更重要的是研究者与作者本身的对话。徐复观指出,在这样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回到具体的往复过程中,包含解读与诠释两个层面的活动。解读是指研究者进入文本、理解文本,并以具体的方式展现文本本身具有的意义。也就是徐复观所谓的与古人对语,在与古人对语的过程中尽可能还原古人思想的真义。而诠释则是对文本价值与意义的叩问和反思,即在与古人对语的过程中,研究者又因文本的意义系统而不断地扩充主体的精神世界,从而对文本做出新的价值与意义的诠释。这一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的过程,就是进入古人思想世界的基本路径。徐复观认为,在读古人之书时,首要任务不仅是发现其抽象思想的价值含义,而是要透过此抽象思想看到作者本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时代问题所赋予作者的印记。他说:“一切思想,都是以问题为中心,没有问题的思想就不是思想。”[1](P132-133)
徐复观认为,在对思想史进行解读时,应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切入古人的问题意识,了解古人接触的问题的真实性。第二,古人在解决问题时在人格和思想上所做的努力是什么,古人对问题解决的方法有何可能性与有效性。第三,古人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研究者所处的时代是否有现实有意义。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便是对思想史的“追体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徐复观所谓的“动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即在具体的、动态的、整体的意义关联中,思想的形成不再是一种逻辑思辨的抽象存在,而是与具体的生活、实践相关联,由切实的工夫践形才能得以真正实现。这种实现方式既是古人思想形成的关隘,也是今人研究者所要遵循的证成方式。
“追体验”的展开是一个从具体世界,层层提升,达致超越性的价值世界的过程,因此,对于徐复观而言,“追体验”不仅是其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其目的本身。因为思想史研究之于徐复观,不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方式,更是改变这个忧患世界的希冀。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怀,徐复观十分强调儒学的实践特征。他在解释孟子的“践形”概念时曾这样表达:
践形,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从充实道德的主体性来说,这即是孟子以集义养气的工夫……从道德的实践上说,践形,即是道德之心……通过官能的活动,可以把心的道德主体与客观结合在一起,使心德实现于客观世界之中,而不是停留在“观想”、“观念”的世界。[3](P185-186)
从上述对孟子“践形”概念的解释中可以看到,徐复观在这里一方面强调道德主体性,另一方面又突出在道德主体的客体化,即在道德实践上言主客体世界相贯通,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从具体的道德实践来说的。因此,徐复观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上,并不认为儒学研究是一个观念世界的构筑,而是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道德之实践。
正如徐复观对考据学和形而上学的态度一样,对于考据学的局限性,徐复观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对思想史上存在的各种观念,不能将字义单独地从思想家的思想系统中抽离出来而加以解释,而是应当将观念本身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的线索中加以理解,单纯的就字义理解观念是无意义的。在曾经志同道合的师友们纷纷追求形而上学时,徐复观选择离开形而上学,直面现实世界,生活在具体的现实世界中,以具体的道德实践的发生来成就自身与世界。因为观念世界的对象化、抽象化、知识化使得儒学与每个个体生命毫无关联,从而丧失儒学的真精神。这既是徐复观反对清人训诂考据和形而上学的真正原因,也是他强调“追体验”的思想史方法论的真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