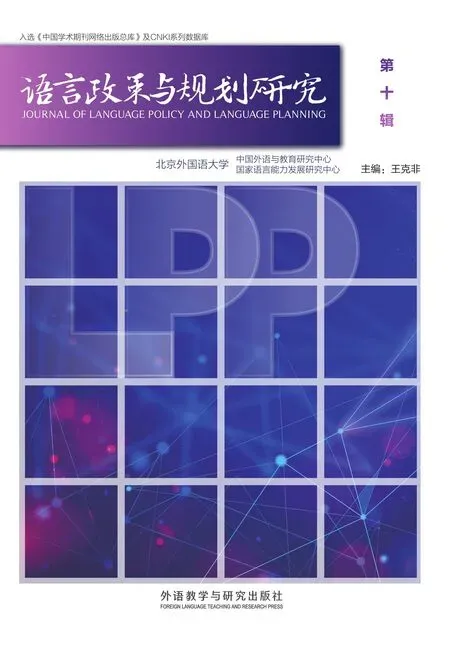《语言政策与语言习得规划》评介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外国语学院 沈 茜
《语言政策与语言习得规划》是《语言政策》这套书的第15卷,共收录了13篇文章。本卷收集的文章选自2015年在瑞典隆德举办的“语言习得和语言政策的融合”研讨会,该卷内容从概念和实证角度呈现与语言教学和学习相关的语言规划。
1. 内容介绍
此卷编者Maarja Siiner, Francis M. Hult以及Tanja Kupisch在书的引言《语言习得规划的情景化》中从三个方面对整卷内容进行了梳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收录的文献主要探讨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环境中的语言习得规划问题,研究范围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凸显问题为:在全球化进程中,仅仅掌握英语是否足够应对多元化的社会交际?此卷的第三部分,研究人员对语言习得规划提出了一些认识论和概念上的挑战,这些挑战表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政治化倾向。
该卷第一部分包含六篇文章,从社会不同层面探究语言实践、语言意识形态以及语言管理,研究围绕语言教育实践展开论述,跨度包括0到3岁的早期语言发展、小学阶段以及中学阶段。《这很自然:美国西海岸的1.5代中国移民家庭语言政策的个案研究》作者Lu Liu对美国西海岸的中国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了个案研究。移民家庭对语言态度、语言信仰以及语言行为的常识性认识,往往会导致语言与社会的不平等,促使移民家庭的继承语成为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建构种族和民族身份的基本方式。作者试图探讨这种普遍存在的语言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父母实践家庭语言政策,以及建构其后代的种族和民族身份。该研究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基于观察法及访谈方式,采用Spolsky(2004)的语言政策分析框架,分别从语言实践、语言管理以及语言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试图阐释移民父母是如何在以英语为主导的多元社会文化中维护其继承语(汉语)。作为家庭语言政策与语言习得的纽带,此研究也进一步阐明家庭的语言实践会给孩子在社会、认知以及情感发展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捷克是一个单语国家,但近些年来的跨国组合家庭逐渐呈现出语言和民族多元化的背景趋势。家庭在多语环境中对语言维护、语言传播和语言习得都起到重要作用。《在实施与创造之间:多语家庭背景的儿童母亲与捷克共和国的语言习得政策》作者Helena Özörencik和Magdalena Antonia Hromadová通过分析多语家庭中母亲的话语资源以及叙事策略,采取以主题为导向的传记采访,试图阐释多语家庭的母亲如何处理自身经历与语言习得政策间的关系。此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多语家庭母亲的叙述再现了捷克社会的单语认知,但一些母亲的叙述对其作为政策“实施者”的单一角色提出了质疑。当她们的语言构建不符合机构期望模式时,便会采用特殊的叙事策略,比如论证和辩护,暗示她们不想成为被动的政策实施者。多语家庭的母亲一方面积极地重塑她们在语言习得管理中的角色,不断发展对政府语言政策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在构建自身的语言政策,从被动的政策执行者转换为积极的政策创造者。
《法国多语托儿所的语言政策:语言政策如何与语言习得观念相联系?》作者Eloise Caporal-Ebersold探讨了法国斯特拉斯堡英法双语托儿所的语言政策,主要针对0到3岁的早期儿童教育。作者认为,早期儿童教育与看护(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简称ECEC)的语言政策研究在多语环境中十分必要。托儿所里的早期儿童语言习得过程因其社会和政治环境而有别于家庭,此研究为家长、语言专家以及政策制定者针对多语儿童语言发展条件的认识提出见解。该托儿所采用了官方推行的“一种专业一种语言”政策(One Professional-One Language,简称为OPOL),目的是给孩子提供足够的双语输入,同时简化复杂的多语现实。但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与托儿所老师的隐性语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语言习得观所决定。儿童在双语托儿所里的语言习得处于关键期,如何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双语输入,如何避免语言混用以及如何习得最佳的语音是双语习得发展中的常见问题。OPOL作为一种广泛被采纳使用的策略,在托儿所的日常情境中却难以付诸实践。因此,作者认为ECEC作为孩子在家庭和学校之间的中间阶段,为研究语言政策规划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建构了最佳的研究语境。
一直以来,语言教育政策中存在一种声音——语言学习越早开始越好,此教育理念被世界很多地区的教育政策吸收采纳。《利用二语习得的研究发现指导语言教育政策:印度尼西亚早期英语教学案例》作者Puput Arfiandhani和Mochamad Subhan Zein以印度尼西亚的教育环境为背景,揭示了当地的语言习得观如何影响学校低年级的语言教育。作者依据二语习得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年龄对语言学习的影响。作者认为,有关年龄对语言习得的影响并未给语言教育政策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指引,因此研究者不应再强调二语习得的年龄层面。结合宏观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因素对语言教育的影响,作者指出未来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应当考虑学生的社会化需求,同时借助二语习得的理论原则制定适用于终身二语发展的课程。作者呼吁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规划语言教育政策时应当考虑其多语的环境,政策应聚焦如何在印度尼西亚的多语环境中有效地实施印尼语和地方语的教学,同时将英语作为各个小学的必修课程。
《葡萄牙语作为附加语言:青少年学习者的语域应用》作者Ana Cristina Neves关注小学正式教育环境中的葡萄牙语的使用情况。此研究中的对象分布于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佛得角(非洲)、瑞士和中国澳门。在这些地区,葡萄牙语作为附加语来学习。作者选择在三个不同的社会语言环境中,对小学生葡萄牙语的使用领域进行调查,同时发掘不同社会语言环境中政策制定的不同层面。研究结果表明,三个地区呈现三种学习模式:在佛得角群岛,葡萄牙语作为第二语言,主要是在学校领域中使用;在瑞士,葡萄牙语作为继承语,主要是用于跟家庭中的长辈交流,有时候也用于跟葡萄语老师的交流;在中国澳门,葡萄语作为一门外语,其使用域仅限于课堂上与老师互动以及葡萄牙语作为科目作业。作者通过绘制葡萄牙语作为附加语的不同使用维度,表明语言使用的领域不一定与政策制定的宏观层面直接相关。文章最后指出,语言的选择是否决定语言在某一具体领域的应用,以及语言选择与社会政治因素间的复杂关系是否会导致语言选择容易受到由上而下的管理制度约束,这两点作者都很难做出判断。
《美国的语言教育政策与实践:努力增强所有教师对语言发展与学习的理解》作者Peggy Mueller以及Aida Walqui记录了在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一项研究,其目的是增强美国学校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语言和读写教育的实践。此项研究汇集了当地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教师职业发展专家以及学区相关领导,目的是让专家领导更好地厘清英语作为二语的教育实践、经验与知识。在芝加哥地区的公立小学中,英语学习者占据了入学生源的五分之一,许多教师对如何帮助这些英语学习者成长缺乏经验,这对教师的教学以及专业发展都带来了巨大挑战。参与此项目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地区领导反思了他们的经验以及指导教学实践的教育理论,其目的是制定新的政策和实践解决方案,帮助英语作为二语的学习者同时促进学科知识的学习和语言的发展。此项目涉及多方的合作努力,迫切地希望学校对核心课程的教学规划、教学执行以及教学测量方式做出一些调整,从而应对语言发展和学习间不断发展变化的关系。作者呼吁将语言学习和语言教育政策领域结合起来,完善教师的教学实践,最终形成支持所有学习者的教学实践和教育政策。
此卷的第二部分主要研究高等教育中的语言习得和语言规划,一共包含四篇文章。在崇尚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国际化背景下,这意味着在大学中减少其他语言的教育资源。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为了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留学生,实施了“more languages for more students”(让更多学生使用更多样的语言)语言战略,为用其他语言进行教学的课程提供资助,这种做法被看做是提升教学课程质量的一种途径以及巩固学校国际化的市场地位。《构建丹麦多语的大学语言政策:变革的守旧者与驱动者》的作者Holmen从语言教育政策出发,通过对不同层面的需求分析,包括学生需求、教师需求以及机构管理层面的需求,来探讨在实际语言习得规划中应当包含哪种语言和哪些语言技能。此研究的核心任务是厘清语言需求与具体学习课程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需求与学生学习需求和未来发展之间的联系。研究表明,创立一种新的形式将语言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非常必要,可以培养学生对语言在其学习技能和职业发展中的角色意识。除此以外,变革的驱动者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向那些墨守成规的守旧者证明,帮助学生习得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会给学生的未来发展增添重要的筹码。
《全球化、外语习得规划与课程实践:日本大学英语课堂中跨国小组互动的个案研究》聚焦日本大学多元文化的英语课堂,探外语教育政策的实施和实践如何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作者Hirokazu Nukuto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日本某大学中的托福备考课程进行了一学期的跟踪研究,这些课程旨在吸引其他国家的学生,并为日本学生的全球化做好准备。作者聚焦了两个研究问题:(1)全球化如何影响外语教育规划目标以及课堂的微观语境如何帮助学生构建宏观的全球化场景?(2)学生如何在课堂中发展英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教育规划的过程与全球化社会进程息息相关,学习者不仅需要习得一门新语言,更要具备完成课堂活动任务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此研究也向英语为非母语的外语教师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包括外语教师在词汇和语法层面讲解的精确度,运用幽默的能力,故事讲解和文化阐述的教学能力,以及外语老师不断增加的工作量。
在《巴西语言政策与权利中科学无国界、英语无国界以及语言无国界项目的反拨效应》一文中,作者Kyria Finardi和Renata Archanjo首先向读者描述了巴西当代的语言和政治形势,然后对巴西政府资助的科学无国界以及其衍生的子项目英语无国界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巴西的大多数语言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语言政策规划,并未认真考虑和吸纳专家和社会大众的建议。在三个国际化项目中,英语无国界项目成功地建立了教师与语言专家之间的联系,推崇一种自下而上的政策规则。此外,此项目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语言政策规划相整合,在巴西高等教育中对国家的语言政策和权利产生了反拨效应。作者认为,科学无国界和语言无国界/英语无国界项目可以促进和影响巴西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权利,但教育政策与语言习得政策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同时多语制问题也未引起政府的重视。文章最后指出,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能忽略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环境。
哥本哈根大学推行“双语并行战略”,将英语作为学校教学和行政语言的同时,也极其重视丹麦语作为学术语言的地位。在《现实中的语言政策——哥本哈根大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两门课程的语言使用研究》一文中,作者Camilla Falck Rønne在哥本哈根大学中选取了两门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为研究对象,研究重点为课堂中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以及学生的语言态度。结果表明,学生并非依据语言政策选择语言的使用,而是依据交际中的有效性进行选择。丹麦语的本族语者在专业以及社会交际层面使用丹麦语和英语沟通,而国际学生则只能局限于英语交流,由此产生了课程中语言使用的不对称。作者认为,学校推行的双语并行以及国际化战略并未在课堂实践中产生良好效果,语言政策的规划与实践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语言政策的制定者要考量学生的社会文化以及学术背景差异,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差异。作者提出语言政策的规划要重视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习得,呼吁更为具体详细的语言政策和语言实践准则,在双语并行的战略下,将更多的语言和文化引入到课堂讨论中,但这需要语言政策的规划者与实践者共同的努力。
此卷的第三部分内容对语言习得规划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共包含三篇文章。《共鸣:从复杂理论视角解析第二语言发展与语言规划和政策》作者Diane Larsen-Freeman 探讨了如何应用复杂理论解释语言教育中的多方因素的相互作用。首先,作者阐释了复杂理论的五个基本原则,分别为复杂系统中新形式的突生,成分间的相互作用,时间上的变化性,系统的非线性和动态性,以及复杂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进而回顾了这五个原则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二语学习的动态特征。作者从意识形态、结构的多层次以及对初始条件和语境内嵌的敏感性方面,阐释了复杂理论、二语发展以及语言政策与规划是如何产生共鸣及相互关联。作者最后提出,面对种种不确定性,语言政策与规划应因地制宜。任何的语言规划都要为语言发展建立最佳的环境,同时意识到语言发展是非线性的且不可控的,随语境与个人的差异而变化。因此,二语发展与语言政策与规划之间的关系要在一个复杂动态系统的环境中进行深入探讨,语言教育者和政策规划者需要认真思考在复杂系统中规划和实施教育政策的意义。
欧洲语言政策的多元化在实施阶段常常面临挑战,因此一体化教育成为了当代语言习得规划的关键因素。为确保所有学生在主流课堂上接受有效的教育,欧洲的教育政策正在转向融合教育。《融合教育:语言政策和语言研究面临的挑战》作者Mark Fettes和Mahbod Karamouzian从理论层面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了融合教育,并根据融合教育的政策目标,探讨如何将语言政策与规划和第二语言习得原则相结合,从而为语言多样性管理提供信息。但是,融合教育运动的政策和研究框架与语言教学和学习的研究和政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作者探讨了差距的原因,以及采用融合教育对学校教学实践、教师教育计划及第二语言习得和语言政策的学术思考和实践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有效地融合需要学校、大学和社会真正致力于将融合教育作为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对外部环境的一系列临时适应。语言习得研究者是实现此价值不可或缺的部分,必然会影响融合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从语言习得的普遍模型转向以背景和文化导向的研究,这种转变对政策和实践都会产生根本性影响。
《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全部事实,片面事实和虚构成分》是此卷第三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作者Virginia Mueller Gathercole探讨了影响双语儿童语言发展的一系列因素。作者列举出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普遍因素,其中包括语言输入的数量、语言输入的质量、个人差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除此以外,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比如两种语言在儿童语言运用中的互补分布情况以及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教育实践、言语和语言治疗以及语言政策中的循证实践,需要全面地理解这些因素间如何相互作用,影响双语儿童和双语成年人的语言发展和使用模式。本文通过研究双语儿童语言发展这一广泛的领域,试图将事实与虚构分开,也将全部的事实与片面的断章取义式的陈述剥离开,消除人们对双语儿童语言学习的误解以及造成的不良影响。
2. 主要特点
该卷所收录的文章探讨了当前世界各地的语言习得规划,旨在向读者提供世界不同地区的语言习得规划以及语言学习和教学的实践。
2.1 明晰语言习得规划研究的领域以及影响因素
该卷中文献主要探讨世界各地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环境中的语言习得规划问题,研究领域包含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收录文献的研究对象范围涵盖了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地区,研究领域涉及家庭语言政策、国家和各级机构的语言教育政策。基础阶段的语言习得规划以捷克、法国、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多语国家的语言实践为例,阐述了包括0到3岁儿童语言发展、小学和中学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规划,研究多围绕家庭与地区的多语制保护问题。高等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规化强调语言学习是未来获取社会资源的有效途径,此部分内容聚焦丹麦、日本和巴西三个国家的语言教学现状。无论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双语并行战略、日本高校以全球化背景为依托的英语课堂教学还是巴西推行的英语无国界项目,高等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规划注重发展学生的英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该卷中的焦点主题包括外语习得和继承语维护,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语言意识形态经常与国家宏观的语言政策背道而驰,造成此差异的影响因素包括家庭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与语言相关的包括语言态度、立场及观念在内的语言文化等因素。家庭的语言意识和语言信仰发挥隐性语言政策的作用,是家庭语言政策潜藏的力量(Gibbons & Ramirez,2004)。社会文化、身份认同等因素会引导父母制定显性或隐性的语言政策,这种微观层面的自下而上的语言政策对语言实践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以外,教育机构作为语言习得规划研究的重要场所,在意识形态再创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地方的实际语言教育环境会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哥本哈根大学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在日本与巴西都将其作为外语来学习;有时差异甚至来自一个机构的内部,例如在哥本哈根大学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不同课程中,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以及学生的语言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教育机构中的语言实践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国家的语言政策、教育机构的语言决策、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活动、社会环境中的语言意识形态、教师以及家庭的语言管理等。语言习得规划的根本应当重视家庭、学校及社会环境中的语言实践,聚焦影响语言实践本质的关键因素,增强对语言实践的深层理解。
2.2 多语制在语言习得规划研究中不断深化
语言习得规划作为一个研究和政治领域,经历了从单语到多语语言观的几种范式转变(Schjerve & Vetter,2012)。多语制从广义上理解为拥有两种以上语言的知识,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则定义为致力于改善个人水平或社会标准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肯尼,2014)。在全球化的今天,多语制不仅被看做是一种认知财富,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经济财富,而语言中的单语制被视为语言习得规划亟待解决的问题(Arfiandhani;Özörencik & Hromadová,此卷)。由于多语制的历史与政治因素,如该卷的一些作者(例如Holmen和Mueller Gathercole)所述,多语现象是一个模糊且矛盾的术语,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紧密相联,语言习得规划常常忽略其内在的复杂特征。英语化现象虽然已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语言政策规划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仅仅掌握英语是否足够应对日趋多元化的社会交际?针对此问题,该卷中的八位作者提及并讨论了英语化现象在全球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获得除英语以外的哪些语言资源成为了当今语言习得规划研究一个凸显主题。
多语制的包容性和社会凝聚性是构成全球公民的基础,若将多语制作为一种市场营销的策略,与将其视为促进平等和民主的人类最基本权利之观点难以融合(Hult & Hornberger,2016)。语言的多元化与政府的多语言教育政策密不可分,教育领域对维护语言与激发语言活力有巨大作用。多民族国家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应特别重视语言教育问题,在教育的各阶段鼓励学习者使用对象语言,增加多语项目,促进语言间的交流,保护语言生态。
3. 简要评价
该卷内容紧紧围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语言规划问题展开论述,既聚焦语言实践,又有关注理论研究的融合深化,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1 聚焦语言习得规划中的语言实践
该卷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语言习得规划中的具体实践问题,基于民族志学的研究方法,对不同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规划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地呈现出语言习得规划研究的范式与领域,剖析了影响语言习得规划的因素,如民族或种族权力关系、历史情境中的政治体系、语言意识形态、社区语言社会化、社区和学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例如,学生、家长、教师和管理者),人际交往和内部发展(社会和认知)。
3.2 理论研究的融合深化
该卷的第三部分从复杂理论、融合教育以及双语儿童的语言发展三个层面就语言发展和语言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语言发展与语言规划要在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中进行研究,要更加关注以背景和文化导向的研究。将语言习得领域的原则和研究成果与语言政策研究相结合,不断更新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为语言的多元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面对种种不确定因素,语言政策要因地制宜,充分理解语言发展中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关联,借助理论指导实践,基于实践来丰富理论的创新发展。
3.3 不足之处
此卷收录的文章的研究范围虽然包括了多个地区,但由于各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教育环境以及文化背景存在巨大差异,整卷内容也只是展示了语言习得规划的冰山一角。对美国移民家庭的语言政策的研究只聚焦于个案分析,研究结论是否具有推广性值得商榷。捷克的多语家庭以及法国的双语托儿所的语言政策都显示出政策执行者的语言意识形态与国家和机构的宏观政策相违背,但如何协调微观实践与宏观规划之间的分歧,研究者并未进行深入讨论。
高等教育阶段的语言习得研究仅仅聚焦了丹麦、日本和巴西三个国家的教育实践,其呈现的语言教育现实不足以映射出相同地域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的真实状况。例如,在亚洲,英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作为二语来习得(如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在中国大陆地区英语则作为外语来学习。学习一门外语和习得第二语言在概念和实践层面都存在差异,不管是政策的制定还是实施,都要考虑各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各国家的语言发展战略。丹麦的高等教育实施双语并行战略,研究者只基于两门课程的语言使用情况分析其效果,研究对象的辐射程度较小,并且专业之间的差异也会影响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所以双语并行的语言政策产生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论证。除此以外,该卷中许多研究者提到了英语化现象产生的影响,但对于如何抵消英语化现象带来的语言资源分配使用问题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也是当今语言习得规划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