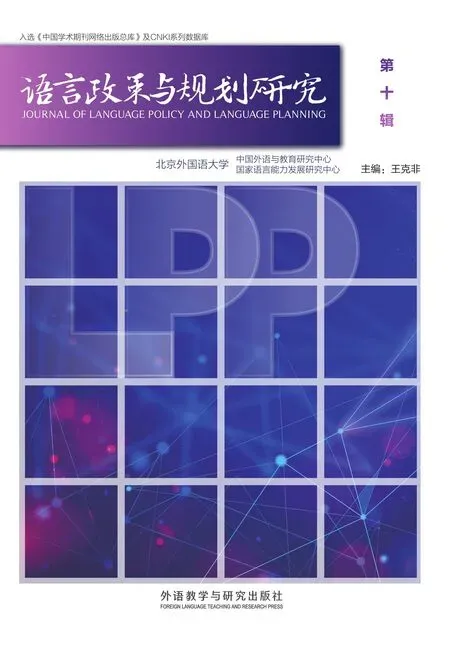土耳其语言政策演变的历史路径
中国传媒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龚颖元 陆 香
提 要:本文以土耳其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为主线,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重要语言政策的内容、成因及影响。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土耳其语作为主体民族语言,其官方性、权威性和唯一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语言政策上,特别是针对库尔德民族的语言政策折射了土耳其在现代民主化进程中不断调整方针,以适应国家发展需求的灵活且务实、多变且矛盾的态度。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我国应结合土耳其语言政策的特点主动积极地应对,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需求和国家语言安全部署。
1.前言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起于中国,止于土耳其。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此相关的国家也进入国人的关注与研究视野。这其中,土耳其受到了格外关注。土耳其是欧亚大陆上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的区域性大国,对“一带一路”具有重要作用(昝涛,2016)。土耳其与中国都是有着古老文明和强劲经济发展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别(王勇,2015)。土耳其作为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的奥斯曼帝国的唯一合法继承者,在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不能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需求,要强有力地保护多民族多宗教的帝国遗产就必须在国家内部形成各族群成员的高度认同感,语言认同则是重中之重。为了加速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建设,土耳其在建国初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凯末尔主义的积极倡议下,建国之初的土耳其坚定不移地把西化作为国策,语言文字的拉丁化改革成为了西化进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通过梳理土耳其前后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阐述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重要语言政策的内容、成因、特点及影响,以期为我国制定相关语言政策提供参考,为有步骤地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类人才规划提供依据。
2. 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
语言政策和规划涉及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社会精神活动的面貌,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色彩也最为明显。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土耳其语言政策的基本面始终如一。从《宪法》层面看,土耳其政府对本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及其地位只字未提。土耳其始终贯彻单语制国家政策,只承认土耳其语为国语或唯一的官方语言,这些提法某种程度上遮掩了国家内部错综复杂的语言实践和语言生态。
本文认为,从奥斯曼帝国后期至今,土耳其的语言政策大致经历了四大变迁。一是奥斯曼帝国末期的坦齐马特改革,把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官方地位写入首部《宪法》,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吹响了前哨。二是20世纪20年代,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初期,把语言文字改革作为政治生活和国家治理的头等大事,从《宪法》层面巩固土耳其语的国语和官方语地位①土耳其《宪法》第42条第9款明确提出,“除土耳其语之外,任何教育机构不可将其他语言作为母语来讲授”。,并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旨在摆脱阿拉伯、波斯世界,同时靠近西方,建立新型现代化国家的拉丁字母革命。三是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强化土耳其语的官方性和唯一性,除了修改《宪法》的相关表述外,还通过其他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使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四是2002年之后,为实现入欧大业,在一些法律法规上做出适当调整,如放宽对少数民族学习、使用和传播本民族语言的限制。
2.1 主体民族语言首次作为官方语言写入宪法(1839—1922年)
早在奥斯曼帝国成立之前,波斯语就是突厥各汗国的官方语言②奥斯曼帝国的前身塞尔柱王朝在公元10世纪皈依伊斯兰教,在王朝不断的扩张中伊斯兰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逐步融入到王朝内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成为主要语言,伊斯兰文化成为王朝乃至后来的帝国时期所推崇的文化。,科技类用语多为阿拉伯语,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帝国时期。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政策,各民族都可以在各自的语言社团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多元的文化在这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帝国呈现出高度多语化的特征。根据语域,帝国境内使用的语言主要分为三种:一是深受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影响的宫廷语言,通常在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使用;二是主体民族使用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该语言是主体民族奥斯曼人使用的语言,和宫廷语言差别极大,几乎不能沟通;三是非主体民族在各自语言社团内部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在西部及中部的库尔德人聚集区,当地学校除了使用阿拉伯语教材之外,还同时使用库尔德语配套教材。帝国时期三类语言的割裂加速了社会阶级的分化。1839年帝国颁布坦齐马特诏书,开启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革命,消除语言文字各自为政的割裂局面也成为了这场自我革命中着重发力的方向。这一时期语言文字改革的关键任务是简化华丽词藻堆砌的宫廷语言,缩小其与奥斯曼民众日常用语间的差异。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年),留学西欧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提出“新奥斯曼主义”,倡导建立语言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报纸、杂志和社团纷纷响应,创设专栏或特刊对语言文字改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在《晨报》首次提出把奥斯曼土耳其语①尽管帝国时期深受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影响的宫廷语成为政治、外交、文学、法律、科技等各领域的语言,然而这种脱离主体民族广大民众的“再生语”终究不可能取代扎根于民族精神内部的土耳其语,特别是语言系统中最牢不可破的语法系统,更是为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提供了的保障。确立为帝国官方语言的主张②革新派在《晨报》报发表了题为《公共关系中的官方语言》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地位的问题,并强调从法律政策层面在国家内部实施。。随着呼声的不断高涨和改革倡议的持续发酵,1876年的《宪法》把坦齐玛特改革推向顶点。这部帝国历史上的首部《宪法》提出建立两院制议会,各民族人民按照一定比例获得代表权,重申帝国内所有臣民不分种族与宗教一律平等,保证宗教信仰、教育与出版自由;课税平等;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格外引人关注的是,这部宪法明确了奥斯曼土耳其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规定在社会各层面推广和传播奥斯曼土耳其语。1921年,土耳其共和国宪法前身的《宪法基本法》第2条再次明确了土耳其语的官方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土耳其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坦齐玛特时期的一系列改革虽然未能使庞大的帝国摆脱改朝换代的命运,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自我革新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语言立法是语言政策的最高体现,帝国时期在《宪法》层面把土耳其语确定为国家唯一的官方语言,体现了统治阶级对管理民族国家的进步意识,为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成功推行语言文字改革奠定了的基础。
2.2 文字改革和语言净化运动(1923—1980年)
土耳其共和国从建国初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建立世俗化的单语国家,以取代奥斯曼帝国的神权统治和多民族政体结构。其国内族群使用的语言不但混杂着大量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还有库尔德语、南高加索语(拉孜语)、波斯尼亚语、北高加索语(切尔克斯语)、保加利亚方言(波马克语)、阿拉伯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如何从高度多语化的奥斯曼帝国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单语制国家,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出于对民族分裂问题的极度担忧,少数民族语言在教育、经贸、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被严格限制,库尔德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期甚至未能获得法律的认可。
土耳其共和国把推行世俗化和西化作为国家的治国方略,192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以下简称“议会”)把土耳其语的唯一官方语言和正式语言地位写入《宪法》第2条。为了排除多民族多语言的国情的干扰,摆脱宗教对土耳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制约,早日建设统一的新型现代化民族国家,在国父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土耳其掀起了一场通过行政强制干预、自上而下的文字拉丁化改革和语言净化运动。1928年议会通过《土耳其新文字法》,同年还颁布了《关于接受和实践土耳其字母法》等具体实施法案。为了体现语言文字改革的学术规范性,1932年土耳其专门成立语言研究协会(以下简称“语协”),组成专家团队从学术层面提出文字拉丁化的具体理论、实施方法和具体步骤。此外,国内各大报纸、杂志、期刊等传播机构也积极宣传,调动了尽可能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为全社会范围内推行拉丁文字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十余年时间里,语言文字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本全面实现了字母的拉丁化。
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改革中,字母拉丁化是最具革命性的一步。土耳其共和国把传统的阿拉伯字母进行拉丁化,标志着现代土耳其语发展的新起点。通过采用西方字母,也表明了新生的共和国从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脱胎转型的坚定决心(昝涛,2009)。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新字母体系与之前所采用的阿拉伯字母相比,在阅读和书写方面体现出了语言的经济性,国民的识字率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不但为土耳其更好地融入西方世界准备了条件,也为西方世界了解土耳其提供了便利。拉丁化改革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字母的拉丁化使没有受过专门教育的当代土耳其人不能看懂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混合而成的宫廷语言书写的文献,某种程度上割断了当代土耳其人与历史的联系。另一方面,波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分属不同的语系①波斯语属于印欧语系,阿拉伯语属于闪含语系,而土耳其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三种语言的起源和逻辑构造有着本质的区别。,且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主要集中在政治、外交、文学、科技、医学、法律等专业化程度和抽象化程度较高的领域,这些不可回避的差异使得语协面临着比字母拉丁化改革更大的挑战,即根据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构词特点和语法规则,利用突厥语词根创造新词汇来代替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词汇。语言政策和规划具有社会性、系统性、连贯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等特征,需要相关机构、社会团体、学术部门等群体,对语言文字的形式与功能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整(陈章太,2015),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仅凭语协一家之力挑起文字净化运动不得不说是有违客观规律的激进之举。
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初期大刀阔斧的语言革命在国家内部强化了“西化从拉丁化开始”的政治方略,巩固了主体民族语言土耳其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了稳固国家根基,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团结,土耳其以推行统一的“新土耳其人”身份和建立世俗的集体身份为由,在少数民族群体中推进语言同质化进程。此外,由于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传播等领域土耳其语是唯一的通行证,因此少数民族的本族群语言除了在私人生活中有使用的空间之外并无他用。可以说,近代以来,土耳其实施的单语政策没有遭遇到来自少数民族群体的抵抗也是情理之中(Sadoglu,2017)。
语言纯粹主义可以作为一条理由用于不同的目标,如宗教、族群、古典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斯波斯基,2011)。历史证明,为了加速国家现代化、民族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全力推行拉丁化改革和语言净化运动是土耳其的不二选择。土耳其推行的语言文字改革和单语制政策,不但为推进土耳其的现代化、民主化、世俗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其他突厥语族语言国家的文字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①2017年10月27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将哈萨克文字母表由西里尔字母转换为拉丁字母的第569号总统令,正式批准根据基于拉丁字母脚本的哈萨克文字母表,确保哈萨克文字母表在2025年前分阶段过渡到拉丁字母脚本。
2.3 主体民族语言地位的强化(1980—2000年)
1991年,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祖国党废除了“9·12”军事政变时期颁布的《关于土耳其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出版物的法令》。1991年4月通过的3713号《反恐法》把库尔德语从“禁止的语言”中删除,同时允许库尔德语在报纸、杂志、书籍等大众媒介传播和使用。这一政策的修订是土耳其建国以来首次从法律层面对库尔德语政策的松动。然而这一修订与1982年《宪法》第26条和28条,《新闻法》第16条和《政党法》第81条的相关表述有明显的矛盾。1980年“9·12”军事政变后,土耳其政府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其中关于土耳其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问题,新《宪法》第3条把“土耳其语是国家的官方语言”的表述更改为“土耳其语是国家的语言”,《宪法》第26条规定“禁止公开传播少数民族语言”,第42条还规定“除土耳其语之外的任何少数民族语言不能作为母语在教育机构讲授”。从这一版《宪法》的表述上看,拿掉“官方”二字,表明了土耳其语除了是唯一的官方语言之外,还是全体土耳其公民唯一的语言,同时还否认了公开场合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合法性。除《宪法》的修订条款之外,其他一些法律法规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政党法》第81条规定,“禁止任何政党在一切政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使用除土耳其语之外的语言”。1983年10月颁布的2932号《关于使用除土耳其语之外的语言进行传播的法律》第2条规定,“除唯一的官方语言之外,任何语言不得用来从事传播活动”。此外,5680号《新闻法》第16条规定,“凡是使用禁用语言进行传播的机构,其负责人将处以罚款或承担刑事责任”。②用库尔德语发表竞选演说的竞选者被判事处罚和民事处罚;2000多名母语是库尔德语的大学生在提交要求用库尔德语上课的申请后被学校开除等情况屡见不鲜。对包括库尔德语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的限制一直到2002年才稍有放宽。2002年对2923号《外语教育教学法》的第1条和第2条进行修正,“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允许除土耳其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在私立培训机构讲授”。2003年土耳其通过了《关于土耳其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同语言和方言的条例》,该条例某种意义上解除了此前对少数民族把族群语言当作母语来使用和学习的限制。《条例》颁布的第二年,第一所库尔德语语言机构在东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巴特曼省正式开办。然而政策实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操作性。比如,增加“语言机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大学文凭”等附加条款对政策的落实设置障碍。虽然1991年的《反恐法》和《条例》看似对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有所放松,但由于《宪法》《新闻法》《政党法》和附加条款等多种因素的牵制,2002年之前针对库尔德语的政策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2.4 脱亚入欧国家战略下的语言政策(2000年至今)
土耳其的入欧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土耳其首次提交入欧申请到2005年为第一阶段。为了获得欧盟完全成员国身份,2005年土耳其正式开启与欧盟的实质性谈判到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为入欧的第二阶段。2016年“7·15”未遂政变后,欧盟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大规模整肃运动表示不满,土欧紧张关系加剧,使得土耳其不得不再次从国家利益层面重新评价入欧政策,此为第三阶段。
入欧初期,把入欧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土耳其为了消除入欧障碍作出了多方面的妥协,语言政策方面的适时调整是入欧进程中备受关注的焦点。欧盟历来推崇“尊重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应尊重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①除西班牙语之外,自治区的民族语言也拥有第二官方语言的地位。的语言政策,如芬兰的官方语言为芬兰语和瑞典语;该国法律规定,该国政府机构的人员必须掌握两门官方语言;此外,分为8个自治区的西班牙也有类似的规定(埃杰,2012)。类似的语言政策在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宪法中也都有所体现。为了表达入盟的诚意,土耳其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适时调整语言政策。2001年10月,1982年《宪法》中关于“禁止在公开场合传播禁用语言的”第26条和第28条被废止,2002年颁布的5680号《新闻法》中关于“禁用语言”的表述被删除。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少数民族语言在大众传播领域的使用扫除了障碍。2002年3月颁布的4748号《关于修订各类法律法规的决议》第7条和5680号《新闻法》第16条中均有关于“修改语言禁令”的表述。紧随其后的4771号《关于修订各类法律法规的决议》第8条和3984号《广播电视机构建立与运营法》第4条规定,“土耳其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传播本民族语言或方言”。2002年8月议会通过了“允许在广播和教育中使用库尔德语”“允许各少数民族语言公开传播”的决议内容。同年11月,土耳其广播电视高等委员会批准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公司用库尔德语或地方语言每天播出不少于45分钟的广播节目。2004年1月出台的《关于广播电视机构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法律》是第一部专门为少数民族语言立法的法律。该法律的出台,首次承认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合法地位,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公开传播提供了法律保障。2004年4月,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公司开设“TRT Ses”频道,播放包括库尔德语、阿拉伯语等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节目。2009年3月8日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批准迪亚巴克尔省宗教事务局在圣纪节(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期间在乌卢清真寺用库尔德语念诵经文。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公司“TRT-6”频道对该活动进行了全程实况转播。2010年10月,第一家库尔德语电视台“世界电视台”在加齐安泰普省成立(Salihpasaoglu,2007)。
为了加入某一个超国家的地区性组织来取得经济繁荣和安全利益,一个国家可能会放弃民族同一性(赖特,2012)。本文认为,土耳其语言政策的不断调整,特别是对库尔德语态度的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长期以来,把“入欧”视为国家发展大计的土耳其在欧盟的压力下,不得不调整对国内少数民族群体的语言政策,以此换来入欧谈判的砝码。其次,随着土耳其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语言政策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被剥夺语言权利的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发展受到严重限制,在传承民族文化的道路上更是无计可施。2003年的数据显示,母语为库尔德语的人口中有46%小学肄业。而母语为土耳其语的人口中,小学肄业的比例仅为9%(Tüzün et al,2009)。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被边缘化的困境逐渐上升为土耳其现代民主化进程道路上的障碍。最后,随着全球化趋势下多元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少数民族的权益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想要在地区事务和国际舞台扩大话语权的土耳其需要经得起国际社会和组织内部标准的考量和检验。
3. 结语
语言政策是在充满各种环境变量的现实世界里对语言作出选择。语言政策必须在动态调整中以“不变应万变”的底气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才能妥善解决出现的问题。作为重要的地区大国和“一带一路”的节点国家,土耳其在语言政策方面始终结合现实语境,不断调整,展示了一条灵活务实的路径。土耳其入盟已成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遥遥无期,但矢志不渝。而欧盟虽对土入盟采取消极态度,但也未拒千里之外。欧盟是土耳其最大投资方,在土耳其的投资占其外来投资的75%(郑东超,2019)。近代以来,能从根本上使土耳其对语言政策进行调整的除入盟之外并无其他。因此,土欧关系的发展将进一步影响土耳其在语言政策上的态度。
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语言生态复杂,文化差异巨大,借助英语等中介语无法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也无法融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目前正处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认知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紧迫。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和社会,必须对沿线国家的一手资料进行分析,全面掌握前沿动态,必须针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需求和国家语言安全部署,平衡关键语言、小语种语言、通用语言及非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对语言资源做好储备工作。本文通过研究一手文献,追溯和梳理奥斯曼帝国及其继承者土耳其共和国语言政策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一方面有助于揭示土耳其语言政策的脉络,把握土耳其语言政策的基本面,另一方面对我国开展对土传播、开展外语教学、完善语言战略统筹等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