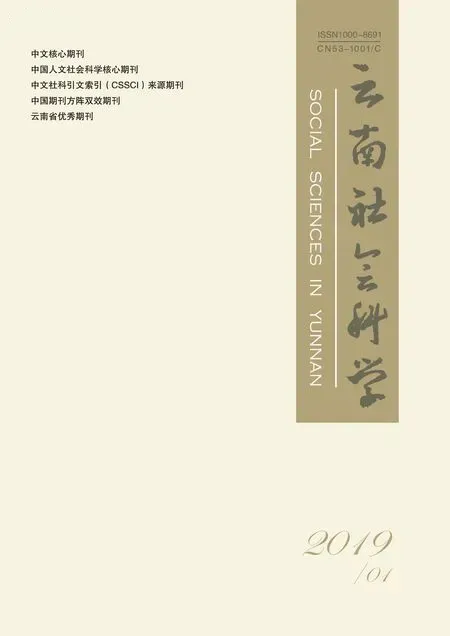“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
——明清“市民社会”说再探讨
林文勋 张锦鹏
一、问题的提出
在明清社会研究中,明清“市民社会”论是颇具冲击力的一家之说。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异质特征——经济转型、市民阶层兴起、思想启蒙运动、公共领域活动以及大众意识兴起等诸多方面,并试图用这异质特征来界定明清的时代性质,并以此为据,提出了“市民社会”之说。他们的观点主要体现于三方面:一是明清资本主义性质因素兴起。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出现多种类型的富户,这些富户即为“市民”,明清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并在反专制、反封建的斗争中崭露头角。[注]①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傅衣凌、侯外庐等主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观的一些学者。参见: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以上两部著作及傅衣凌相关成果均收录于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傅衣凌著作集》丛书中。侯外庐从思想史视角也讨论了相关观点(相关著述见下)。二是启蒙思想出现,这是明清走向市民社会的思想动向和社会意识形态。[注]②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侯外庐、艾尔曼、沟口雄三等。相关成果见: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三是“公共领域”的发展。明清士绅、商人在许多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形成具有自治特征的团体生活,甚至发挥出批评政府的功能。[注]③这一观点代表人物是罗威廉、兰京、卜正民等。相关研究可见:Rowe,W.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Modern China 16.3,pp.309-329.1990.Rankin,M.Elite,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The origins of a Chinese public sphere:local elites and community affairs in the late-imperial period”,Etudes Chinoises 9.2,pp.13-60.1990.这种观点与明清停滞论[注]④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明清社会停滞论,如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乃至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也意在论证明清中国的停滞衰落。形成鲜明对立,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
笔者认为,明清社会既不是有新生力量涌动的“市民社会”,也并非缺乏发展动力的停滞社会,而是“富民社会”。所谓“富民社会”,是从“民”的演变历史轨迹来考察的、对中国传统社会性质而提出的一种“假说”。中唐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为“富民”作为一个重要的财富力量成长起来,成为社会的中间层、稳定层、动力层;这一社会中坚力量推动着社会前进,使唐宋及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与以前的汉唐社会不同的历史特征。“富民社会”具有的流动性、市场化、平民化特征,体现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均质运行。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都具有“富民社会”的特点,都具有同质性,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社会阶段来看待。
二、明清富户不是“市民”而是“富民”
20世纪50年代史界前辈傅衣凌先生认为,明清江南社会出现了大量农业型、产业型、商业型富户,这些主要“依靠工商业”积累财富的“富户”,“更加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并在工商业中出现有大批的中小工商业者,这般中小工商业者广泛地散布于江南的乡村城镇中,形成为广大的市民阶层”,“动摇了自然经济,也改变了整个的社会阶级的比重”[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收录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63页。。
笔者认为,“江南富户”并非“市民”,而是“富民”阶层。将傅先生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下文简称《试探》)一文“富户”的史料与唐宋时代史料所见“富民”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明清“富户”与唐宋时代“富民”有诸多相似。《试探》一文指出:明朝“以田税之多寡者较之,惟浙西多富民巨室”[注]《明太祖实录》卷49,洪武三年二月庚午条,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65页。。明初徙天下富户以实京师或其他地区,仅洪武二十四年(1391)迁徙富户14300余户,永乐元年(1403)迁徙富户3000余人。[注]傅衣凌:《明清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34页。唐宋时期类似的“富民”史料亦不少见:“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注](宋)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55页。“乡村上三等户及城郭有物业户”,“是从来兼并之家”。[注](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刘琳、刁忠民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053页。若就个案来看,《试探》一文列举明清有“以力穑致富,甲于县中”[注](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25《行状·魏诚甫行状》,周本淳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92页。的魏氏、有“累赀至千金”[注](明)缪昌期:《从野堂存稿》卷5《仰峰王君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73册,第472-473页。的王守玺、有“起机房织手”“至百万”[注](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8《果报·守土吏狎妓》,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13页。的苏州潘氏、有“以巨赀为番商”[注](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页。的童华、有以一张织机起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6《异闻记》,盛冬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页。的张氏等。而唐宋时代个案亦多,有“至富敌至贵”[注](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95《杂录三·邹凤炽》,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063页。的王元宝、有“家有绫机五百张”[注](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3《治生·何远明》,第1875页。的定州何明远、有“用机械起家”财富累积至几十万的“富民张三八翁”[注](宋)洪迈:《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雹》,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9页。、有被“赀至十千万,邢人呼为‘布张家’”[注](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7《布张家》,第242页。的张氏、有“积资至巨万”[注](宋)陈亮:《陈亮集》卷30《何夫人杜氏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6页。的东阳何氏等。可见,明清“富户”与唐宋“富民”不仅在史料的文本表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他们起家致富的方式以及财富多寡等方面,也并无明显的差异。明清“富户”应与宋元“富民”看作为同一类群体或同一社会阶层。
当然,这种“选精”式个案比较并没有太多的意义,科学研究更需要的是从整体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傅衣凌先生从“江南富户”经营活动,看到了明清契约关系发展在生产关系上呈现出的“若干的新因素”;从江南城镇下层市民反封建运动,“隐约地反映出新的市民意识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包含着新因素、新意识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特点。[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63页。但是,持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学者,却无法解释一个问题,即明清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种种“新因素”几乎都能在唐宋甚至汉唐时代找到其踪影,对此傅衣凌先生用“中国历史的早熟性”来解释它,[注]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收录于《傅衣凌著作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6页。虽可解释其“萌芽”而不“成长”之原因,但却不能对已经出现新因素的汉唐不被纳入“萌芽”期做出合理解释。
毋庸置疑,明清商品经济的深化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但是这些新动向主要是富民阶层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离开了富民,很难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唐宋时代可以见到诸如王元宝之类的大商人者,但是这样的人数寥寥,尚未形成规模,而明清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宋代有蜀商、南商、北商等地方性商人群体,而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诸如徽商、晋商、闽商等大商帮,其兴起地域更多、市场活动更广。但是他们的经营活动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传统型的,只能归结为对宋元商业的扩张型发展。吴承明先生的研究颇具说服力:明代“国内市场显著地扩大了,这表现在商运路线的增辟和新的商业城镇的兴起。但明代商路的增辟主要是在南北贸易方面,尤其是大运河的利用;这包括有政治因素,不完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长距离贩运贸易有了发展,并且已逐步由奢侈品以及特产品贸易专项以民生用品的贸易为主……但是,终明之世,长距离贩运贸易在整个市场交易中仍很有限,而其中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并不占主要地位;农村产品,大半还是单向流出,得不到补偿和交换……徽商、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说明国内市场有相当的积累货币资本能力。但这种积累主要是经营盐及茶布等商品而来,多少是假借封建政权的力量形成的。”[注]吴承明:《论明代国内市场和商人资本》,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1983年第五集,后收录于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111-165页。唐宋租佃制和雇工制有不少新变化,租佃关系的市场化和契约关系的明晰化是私有制下富民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而明清时期“田底权”和“田面权”的分离,则使土地产权多元化,也使产权的实现方式更加合理化,这是一种保障土地经营主体多方收益权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在商品经济下富民与其他阶层的民众通过利益共享而达到经济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宋代的佃农已经拥有了较大自由租佃权,但是地主和佃农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官方多次颁布不得“强抑人户租佃”[注](清)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58之24,第4627页。的法令。明清时期,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但是多数佃农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主仆关系。有关徽州文书研究显示:要求脱离佃仆身份的佃仆与极力维持“主仆之分”的主家纠纷,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仍然是徽州诉讼中最严重的问题。[注][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8页。
可以说,明清时期种种“新因素”,实质上是唐宋富民阶层崛起以来在经济领域内出现的种种现象,这些现象产生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深化,也必然表现得更加典型和更加突出,但是其发生机理和现象本质并未出现质的变化。只有从“富民”阶层成长和“富民社会”这一框架下来分析和理解这些明清出现的新动向,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三、明清士绅由“富民”转化而来
罗威廉认为“士绅”和“工商业者”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注][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载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附录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5-253页。傅衣凌先生也认为一部分下层士民,如生员、监生、儒童之类,参与了反封建斗争,他们是市民阶层的组成部分。[注]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8页。
何谓“士绅”?明末清初的颜光衷说:“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注](清)颜光衷:《官鉴》,见(清)陈弘谋辑:《从政遗规》卷下,金华:国民出版社,1940年,第122页。清代《钦颁州县事宜·待士绅》也说:“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注](清)田文境、李卫:《钦颁州县事宜·待士绅》,同治重刊版,第22页。日本史学界有关士绅的定义可归纳为三种:一是包括现任官、退任官、卸任官以及未初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二是仅指在野的官僚;三是认为士绅由地方名家大族、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有官职功名者组成。[注]郝秉健:《日本史学界的明清“士绅”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张仲礼将“绅士”定义为“通过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身份地位者。[注][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页。徐茂明认为:“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注]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这些界定说明学界对士绅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是有较大差异的。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宋元明清)社会群体可分为官、绅、民三个阶层:在职的官员属于官僚层;民属于无特权层;士绅则居于这两个阶层中间,是官僚与民众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既与权力有一定关系又不完全属于权力阶层。士绅具有较为突出的在野性和地方性的特点。士绅并非“市民”,是明清时期从“富民”阶层转化而来的一个阶层,它本质上属于“富民”,士绅阶层即为“富民”阶层。
富民向士绅转化的动力机制是财富保持和社会地位获得,其转化关键通道是科举制度。转化步骤有三:(1)通过接受教育实现知识获得,形成文化资本;(2)通过科举考试追求功名,实现特权获得,形成政治资本;(3)通过参与地方社会活动,实现威望获得,形成社会资本。据此,富民将其财富资本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了富民阶层的成长,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富民士绅化。
具体而言,财富是富民在社会上立足和发挥作用的基础,但在商品经济竞争性、流动性规律的作用下,贫富分化和流变十分频繁,“千年田换八百主”,拥有财富者要保持家业的长久兴旺,必然倾向于追求更为稳定的职业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进入官僚阶层显然是当时最理想的选择,宋代一位官员曾说:“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注](宋)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20《仙居劝学文》,《全宋文》(第50册)卷1083《陈襄七》,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由此在社会中形成“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注](宋)张守:《毗陵集》卷7《论措置兵民利害劄子》,《全宋文》(第173册)卷3786《张守八》,第320页。的风尚。宋代以后蒙学、乡学等乡村教育的发展,则是广大庶民特别是富裕之家为追求社会地位改变而戮力推动的结果。
从明代进士家庭成分统计表来看,永乐九年(1411)至成化五年(1469)之间,社会流动率在60%-86%之间,弘治十八年(1505)以后在38%-55%之间。有明一代基本保持50%左右的上升率。[注][美]何炳棣:《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王振忠译,《历史地理》第1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明代后期到清代,科举制度形成的社会流动逐渐减弱,但是仍然具有流动意义。钱穆认为中国社会特殊性有三,其中之一是“士常出于农民之秀者,后世之所谓耕读传家,统治阶级不断自农村中来”[注]钱穆:《政学私言》,《钱穆先生全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所言就是富民在科举制度的激励下支持弟子读书,通过考试选拔机制使家庭中的成员进入官僚集团,从而稳定家业和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现实。在此过程中,富民实现了向“士”转化的过程。
科举制度被认为是具有“平等精神”的人才选拔制度,事实上这是对富民阶层更为有利的制度。在缺乏公共教育制度的古代社会,延聘塾师或是将子弟送入私塾,以及不断参加各级考试的考试费和旅行费,都需要长期支出不菲费用。故虽有异质才俊者出身贫寒,但大多数中举者都是家庭殷实者。另外,富人实现纵向社会流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便利,就是他们可以通过捐纳买官,如清代可通过捐例监生和例贡生跳过“童试”,官方还专门为特殊商人(盐商)设立单独考试名额。[注][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202页。
当然,通过科举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这一通道仍然是狭窄的。即便是北宋以后科举取士名额不断增加,国家官僚制度能够容纳的人数的有限性与富民群体规模扩大、考试大军人数逐年增长的矛盾仍不断加剧,科举入仕之途始终处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态,能够通过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最终进入国家官僚体系的人为数寥寥。即便经过千辛万苦实现了科举登第,士人的仕宦命运也颇为艰难。随着读书应试人员规模扩大和科举取士名额增多,官僚职位有限,获得选人资格者虽能得到一个官职头衔,但是需要经过多年的“选海”和“待阙”并在多位举荐官推荐之下方得“破白”改官。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大量无权无势的士人流向地方社会。[注]王瑞来:《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与此同时,一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在官僚体系任职者,在其致仕之后也回流到地方社会,此即在官为“士”、在野为“绅”。需要强调的是,明清时期在乡村社会里十分活跃并呈现出地方代言人特色的,当属那些获得官方正式认可的学衔和官职、但是并没有资格实际任职的群体,例如明清时期通过“童试”获得生员头衔者,以及那些通过捐纳、举荐、赐爵等方式获得官职或者某种功名(如监生、例贡生)者。这些人被张仲礼称之为“下层绅士”,所享有的官方特权十分有限,在社会声望方面也大大低于“正途”获得功名者,却构成了这一阶层庞大的数量规模。[注][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1-75页。
由此可见,富民阶层士绅化的过程,也就是富民阶层在追求更高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发生分化而走向地方化、民间化的过程。正是由于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手工业和商业结合得更加紧密、商品经济得到更为广泛和更加深化发展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财富与知识、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的程度不断加深,士绅阶层也因此应运而生。可以认为,士绅实质上是富民阶层的一部分,富民才是士绅的基础。富民士绅化并非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富民发展壮大后的一种必然趋势。
四、明清社会是“市民社会”吗?
“市民”并非一个空间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概念,是10世纪以来西欧城市复兴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社会力量,他们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化,以发展工商业为主;在政治上批判专制主义,寻求政治的民主;在价值观念上,追求人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市民社会是市民阶层为主体、追求个人自由和法治社会而产生的一种新社会形态。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获得。霍布斯指出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国家提供社会秩序保障。马克思强调了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下缔结的社会关系的总体呈现。葛兰西认为在社会意识形态上掌握权力才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哈贝马斯进一步将市民在“公共领域”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作为理解市民社会的维度。从十四五世纪到十八九世纪,西欧社会经历了城市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推翻了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其制度基础的市民社会。从黑格尔到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种种表述,正是上述历史过程的理性观照。一些中外学者将明清社会看作是“市民社会”,似有西方经验套用中国问题研究之嫌。
(一)明清“反封建”斗争是富民阶层与国家的矛盾而非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运动
前文已述,一些学者强调明清时期新兴的“市民阶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所发起反封建斗争。应该看到,富民与国家始终处于既依存又对立的关系,富民与国家的博弈长期存在。如在北宋时期国家按户等摊派差役,主要依靠富民提供公共服务,有不少富民不堪差役之苦采取“析居”等方式逃避之法。又如南宋时期地方官员依靠富民赈灾救济,但是一些富民却采用不予理会或公然反抗的方式抵制。[注]参见张锦鹏:《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财富改变关系:宋代富民阶层成长机理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明清时期的确出现了不少与富民、士绅组织或参与的社会冲突,典型的事例如苏州机户抗税运动、苏松地区的抢米风潮等等。[注]相关事件可参阅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287-335页。不过,这些群体事件所表达的诉求,仅仅是罢税和抗议物价这类经济诉求,或者是对贪官污吏的惩罚,没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权力要求。一旦官府为平息势态取消不合理科索或惩罚当事官吏,反抗者的诉求得到回应,斗争随即平息。但是,经济领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制度依然普遍存在,广大工商业者相同的命运依然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继续上演。这表明,这些财富实力有进一步增长的工商业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命运而非群体的命运。同样,在各种反抗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下层士民”,是士绅化的富民,也是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个体性表达,他们与国家的矛盾,即是富民与国家的矛盾而非其他性质的矛盾。这种矛盾自富民阶层产生起就一直存在,并伴随着富民阶层的成长过程而呈现出多样性。
(二)明清时期思想领域的新思维是“保富论”的继承发展而非启蒙思想出现
明清时期是否出现启蒙思想的问题,也是讨论明清是否是“市民社会”的一个焦点。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章学诚、龚自珍等人的思想,常被看作是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但21世纪以来已有不同的评价。叶世昌分析了王夫之早期的保商思想和晚期的抑商思想,认为抑商思想是王夫之的主流思想;对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也从其特定涵义去理解,进而否定其“启蒙”性。[注]叶世昌:《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笔者认为,明清时期在思想领域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都是唐宋以来思想观点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根本上没有脱离传统思想的范畴,所以很多思想家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表现出矛盾性和两面性。
讨论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宋代以来“保富论”的新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所谓“保富论”就是公开宣扬富民的重要性,并主张对富人予以保护。宋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如何看待富民和贫富不均问题,苏辙认为:“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注](宋)苏辙:《栾城集》(下)卷8《杂说九首·诗病五事》,第1555页。司马光认为:“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注](宋)司马光:《司马光集》卷41《章奏二六·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0页。明代邱浚也认为:“天生众民,有贫有富。”[注](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上)卷25《市籴之令》,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王夫之认为“兼并”“积习已久……而弱者亦且安之矣”[注](明)王夫之:《读史通鉴》卷5《哀帝》,《船山全书》第10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这种情形“非豪民之能钳束贫民而强夺之”[注](明)王夫之:《宋论》卷12《光宗》,《船山全书》第11册,第277页。。这说明,宋以来人们对存在富民阶层这一现象已达成共识,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各阶层都应该接受贫富分化这一事实。从富民与国家的关系来看,由宋元至明清,很多思想家都极力强调富民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如叶适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注](宋)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叶适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657页。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之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注](明)丘浚:《大学衍义补》(上)卷13《蕃民之生》,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王夫之亦言:“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注](明)王夫之:《黄书》大正第6,《船山全书》第12册,第530页。“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注](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汉高帝》,《船山全书》第10册,第89页。清末的魏源也提出:“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依赖焉,大兵,大饥馑,皆仰给焉。”[注]魏源:《古微堂内外集》卷3《治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4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64页。顾炎武针对江南地区重赋的问题对朝廷提出严厉批评,正如今人郑天挺所评论:“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赋重,这是事实,但是官僚吵嚷赋重,是代表谁说话呢?他们不是代表一般农民,而是反映富户的愿望。”[注]郑天挺:《读〈明史·食货志〉札记》,《及时学人谈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3页。至于东林党人反对矿监监税使、体恤富民的思想,是城市经济发达以及商人和富民力量增强的反映。与一些学者将东林学派的主张看作“市民意识”观点不同,亦有学者认为,明代后期阳明学派、东林派、朱子学派所共有的理念,就是藉“礼”实现宗族、乡村秩序的确立。[注][日]小岛毅:《中国におけゐ礼の言說》,第七章至末章,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揭示了明清思想领域的主流与本质。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这些思想认识与宋代“保富论”一脉相承,是宋代“保富论”的继续和发展,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明清时代的思想家呼吁保护富民的言论更多了,讨论如何处理富民与国家关系问题更为深入和多视角了。如黄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思想颠倒过来;又如,顾炎武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实现国家富裕的结果,[注](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13《名教》曰:“司马迁作《史记·货殖列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吏土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为最劣。爪牙毛皮,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黄汝成集释、栾保群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67页。与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所分析“个人恶行能导致社会繁荣”[注][荷兰]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的观点异曲同工。这说明,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在对经济现象的本质性认识较之前的思想家更进一步。
(三)明清民间组织并非为批评政府的“公共领域”而是“国家话语”的地方代言人
关于明清出现“公共领域”这一问题,如兰京和罗威廉通过对浙江和汉口的个案研究,强调清代城市体系里有一个由商人、士绅所主导的公共领域,发挥了城市自治功能和对政府的批评功能。如罗威廉指出,“19世纪中国城市中,不仅形成了城市阶级,也出现了城市社团”,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这说明,政治功能的逐步普及化是以经济力量的‘私域化’平行展开的。”[注][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5-421页。不可否认,明清时期商业行会、商人会馆、善堂善会、地方宗族等成长很快,并且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这些中间组织并非明清时代的产物,如明清时期十分兴盛的商业行会、会馆,其前身即为宋代的行会,这是宋朝官府为了便于对商人征税敛费而成立的行业中间组织。明清时期商业行会、会馆虽已褪去官方色彩,但也并非是国家的异己力量。王日根对明清会馆进行全国性和整体性考察发现:至明清时期,在商业会馆、士绅会馆和移民会馆中,“士绅、士商或绅商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人的士人化、士人的商人化是明清市场经济发育的直接产物,也注定了这一时期从商人员尽管众多,却并无明确的政治地位,自我独立意识亦不显著,从而使明清社会在总体上尚未脱离传统社会轨道。”[注]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442页。究其史实,商人会馆多以商务和教育为其首要目标,以信息融通、互助协作的方式拓展商务,是“富民阶层”追求财富为其目标而抱团求利的产物。会馆也承担了支持商人弟子或同乡党族科场考试“俱乐部”的教育功能,表明会馆在“富民阶层”士绅化中所发挥的平台作用不可忽视。王日根进而认为会馆在社会整合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在会馆竭力谋求本会馆成员间的感情联络、信息交流与稳定发展,实际上也维持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弥补了封建管理体制管理社会的不足之处”,因此“会馆的发展是明清中央集权加强与基层社会自我管理机制不断建立与完善的结果”。[注]王日根:《中国会馆史》,第443页。李约瑟也曾经说过:“中国的商会也是社会上的一部分团结力量,只是它并不像欧洲的商会那样具有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注][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9页。
至于明清华南宗族的发展,亦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国家礼仪改变并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这个趋向,显示在国家与地方认同上整体观念的改变。宗族的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推广他们的世界观,在地方上建立起与国家正统拉上关系的社会秩序的过程。”[注]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而由地方士绅所兴办和领导的明清民间慈善机构,主要起到的是国家制度和传统秩序的维护作用,而非独立运行的、甚至与政府对抗的异己力量。[注]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这些富民阶层利用组织和运营民间慈善机构来传播儒家价值,推行儒家秩序,以纾解明清时期因经济发展和各种社会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焦虑,“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善堂对既存社会秩序及政权提出挑战,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巩固既存秩序”[注]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322页。。
总体来看,学界有关明清“市民社会”的分析和论证,对学界充分认识明清社会的变化有很大的启发。但是认为明清是“市民社会”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这是以西方坐标来标示中国社会,是用西方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并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
五、明清社会依然是“富民社会”
综上所述,明清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富民社会。明代陈邦瞻在编撰《宋史纪事本末》时指出:“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注](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附录1《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第1191页。按照他的说法,宋代形成的新的社会,到明代还在继续发展,并未达到它的顶点。近代思想家严复也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成,什八九可断言也。”[注](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13期,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2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在严复看来,由宋而起的一些重要因素长期地规定着社会发展走势,从宋代到他所处的近代都是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亦指出近年有关研究呈现一种趋势:“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对于宋至清这一传统中国的后期,有明确区分为‘宋元史’与‘明清史’的倾向。但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无论是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相比元、明间的中断性,反而更重视起来连续性。”[注]中岛乐章举出砂明德的《江南史的水脉》、檀上宽《明初帝国体制论》都是这倾向的成果,他自己亦持有相同的观,参见其著作《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这些认识与我们对历史发展演进的阶段性判断是一致的,宋元明清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明清社会仍然是“富民社会”。理由有三:
其一,“富民”阶层依然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层。富民阶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富民阶层壮大。在追求自身财富的过程中,富民阶层作为社会的动力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李伯重对江南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并未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经济仍然呈现出继续发展的特性。推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力量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即“斯密型动力”。[注]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按费维凯的分析,“斯密型成长”模式经济总量、劳动生产率都能够提高,但是技术变化不大。[注]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Journal of AsianStudies (Ann Arbor),Vol.5,No.4.为什么这一时期技术创新动力不足,而以集约化劳动方式或以专业化方式提高生产率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关键因素在于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背后推动力量,主要靠的是富民阶层。“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是富民阶层藉以成长为财富力量的源泉。与技术创新风险大、周期长、需要特殊才能相比,最大化利用土地和最合理利用劳动力成为有财富实力或投资能力的富民,是成本最低、风险最低、收益最明显的选择。从产权角度来看,富民阶层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推动了农业经济中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深化发展,促进了产权实现形式多元化和资源配置方式合理化。这就是继宋代农业发展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之后,明清时期继续保持了稳步增长原因所在。在工商领域中,富民阶层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则是扩大了市场容量,促进了产品商品转化率和商品市场扩散度。仅以与富民生产经营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粮食贸易而言,郭松义估测乾隆时期商品粮长距离运输4350—5450万石,另有跨省的中距离粮食运输约300万石。[注]郭松义:《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数量的估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龙登高估计乾隆时期米粮长距离贸易为4600—4800万石,可能达到5000万石。[注]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77页。以国内市场中的大宗商品结构来看,清代市场上最大量值的工业品已经从明以前的盐向棉布转换,吴承明先生精辟地指出:“这是一个进步。因为盐的产量,仅决定于人口数量;布,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关系。”[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这些发展变化,无不以富民阶层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动力直接勾连。这便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每个个体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最终导致的是国民财富的增长。[注][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其二,富民依然是国家统治所依赖的中间层。自富民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富民就是国家统治者所依赖的对象。中唐“两税法”的改革将国家税赋征收依据由人丁转向资产,两宋按民户资产高低来征取役钱和差役的趋势进一步扩大。[注]参见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数辨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辅论》,《暨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柳平生、葛金芳《南宋摊丁入亩考析》,《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明清时代通过“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的改革,以财富丰少决定承担赋役多寡在制度上更明晰化和在差派上更便利化,其目的同样是达到国家租金最大化。明初推行依靠富民的粮长制,任用富民担任粮长并给予具有皇权特色的仪式性奖励,其目的在于“以良民治良民”。[注]《明太祖实录》卷68,洪武四年九月丁丑,第1279页。朱元璋在晚年颁布《教民榜文》:“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由本里老人、里甲断绝。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注]一凡藏书馆文献编委会:《古代乡约及乡治法律文献十种》(第1册),明太祖钦定《教民榜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9页。能担当此责的耆老,不仅是年高者,“其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注]何广:《律解辩疑》卷4《户律·禁革主保里长》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1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实则由有财富、有文化、有威望的年长的富民来担当此任,这也是国家充分利用富民在地方的社会影响力来实施社会控制、降低官府行政成本之举。不少实证研究表明,明代中后期仍然有相当多的地域性民间纠纷是通过乡绅等名望人士“排难解忧”,或豪民等“武断乡里”“私受词状”。[注][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283页。岸本美绪也指出清初期无论是“国家审判”还是“民间调停”对当时地方社会的人们来说,都是休戚相关,十分盛行的。[注][日]岸本美绪:《〈历年记〉所见清初地方社会生活》,初出《史学杂志》95编6号,1986年。后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有学者指出:明代地方社会“这是以南宋至元代不断增强的士人和当地有势力者、有名望人士通过精英主义完成‘自下而上’社会秩序形成为基盘,通过国家控制,重新构建‘自上而下’的乡村统治体制”[注][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第284页。。清代统治者借助保甲制度实施基层控制,保长、甲长仍然是由地方富民、富户担任。士绅阶层由富民转化而来,因其具文化优势和特权荣耀,更容易形成地方性影响力,统治阶层深刻地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主动利用他们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晚清时期面对白莲教反叛等社会秩序失控情势,朝廷在各地倡导兴办团练,其团练负责人,亦从士绅中选拔。应该看到,武装力量的地方化和非国家化,客观上会对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造成很大的政治风险,不过清朝团练“地方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具体化”[注][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页。。这表明,主持团练的士绅仍然是以国家意志为社会担当。毋庸置疑,在国家统治者极力利用富民来进行社会秩序控制的实践中,重构和强化了富民作为社会中间层所发挥的作用。
其三,富民依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定层。一些学者将明清社会称之为士绅社会,充分肯定士绅在介于国家行政机构和个人或家庭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明清的国家制度设计上确实体现了“皇权不下县”,以缙绅地主、乡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对乡村社会形成了实际控制权。需要强调的是,士绅所发挥的作用并非代替国家进行乡村自治,而是主动配合国家进行社会治理。众所周知,乡约、社学是明中叶以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层教化组织,是乡绅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的舞台。清代乡约的主要职能是定期宣讲圣谕(康熙《圣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等),社学宗旨是“教子弟以正其身心为首务”,“凡学徒入塾,须先读《小学》、《孝经》,以端其本”[注](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9《札苏藩司饬属设立社学》,《丁日昌集》(上)卷4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1、492页。。它们都是主动配合国家治理需要,以传播和强化统治者意志为其宗旨。明末同善会以代表儒学正统的孟、荀、扬雄、王通、韩愈等“贤人”为崇拜对象,到了清中期,道教的文昌帝君代替了“五贤”而成为同善会的神祗。[注]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159页。梁其姿分析这一变化原因是办会组织者从名流大儒向地方一般士人转变,行善目的从积善避灾向追求功名转变。从明代儒学道义转向清代追求科举功名这一变迁路径来看,善会组织中本质性的东西并没有改变,行善的目的在于通过积德积善来提高自我修养,进而踏上功名之路,而这一切是以遵循国家正统和儒家文化价值为其前提的,是士绅主动向国家意志靠拢的体现。善堂善会的组织者多为中低级士绅,而以高级士绅为主体的学术界、思想界,亦盛行同样的价值理念。在其他地方性公共活动中,这些被称为地方精英的士绅们,也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倡导的儒家价值约束自己、规范他人,积极地以贯彻国家制度地方化实践为其荣耀,从而形成了事实的乡村自治或地方化运动。政府虽然不在场,但是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家意志时时刻刻规范着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正是明清富民阶层在地方社会中主动维护国家秩序的结果。
六、余 论
不可否认,明清社会从表象上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变化和新事物,然而若从社会特质视角去探究,我们发现,这些新变化和新事物都发端于唐宋社会变革之际,且与富民阶层息息相关。自晚唐以降,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富民”阶层崛起,并在宋元明清这一长时段中发挥着社会的动力层、中间层、稳定层的作用,使这一时期成为与上古三代的“部族社会”、汉唐时代的“豪族社会”完全不同的“富民社会”。
就本文考察的明清社会而言,这一时期的富民、富户并非市民,他们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市民阶层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富民”阶层在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走向多元化,提供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动力;朝廷利用富民的财富力量增强了国家的社会保障力和地方治理力。他们是推动社会沿着原有轨道继续向前的强大驱动力,而非变革传统制度的新兴资本主义力量。明清时期在各种“中间领域”或“公共领域”中盛行的价值理念,也始终与国家意志和儒家价值保持一致,主动与政府同构社会秩序,这与西方市民社会中国家与个人之间具有独立主体意义的“公共领域”有着根本不同。因此,明清社会不是“市民社会”,而是与宋元一脉相承的“富民社会”。唯有把宋元明清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突破断代研究的局限性,做跨时段通贯性研究,才能找到解构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钥匙。
明清时期“富民”阶层的士绅化,既增强了“富民”阶层的社会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也为“富民社会”的衰落和走向终结埋下了伏笔。拥有文化知识成为“富民”阶层的利器,既可通过科举渠道获得政治特权,也可通过文化资本获得地方权力,无所不在的明清士绅地方控制就是主要以其政治特权和文化资本而获得的。纵观历史的发展,任何一个阶层,一旦取得政治特权并形成一定的垄断之后,必然走向反面,士绅阶层也是如此。当通过“士”与“官”成功对接,富民就脱离了“民”,成为“官”的支持者而非“民”的代言人。当富民为科举入仕为目标按照国家价值导向学习知识,他们所形成的文化权力在进行基层控制时,必然成为国家秩序的维护者而非个体价值的倡导者,这个阶层就越来越远离了“民”的特色和活力了。由此可见,“富民社会”向“士绅社会”转化时,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自掘坟墓的逻辑,那就是“士绅社会”是“富民社会”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富民社会”的发展前景应是近代的“市民社会”,中国社会演进之路终将被近代化的曙光照亮而迈向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