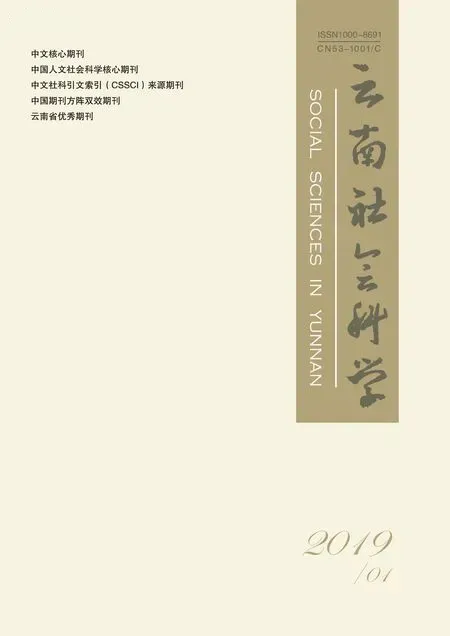库恩后期的“新康德主义转向”是错误吗?
贾向桐
一般来说,库恩总是与自然主义哲学倾向相联系的,这主要源自于其《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深远影响,因为无论是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还是理论主张,其中的自然主义色彩都是极为浓重的。但事实上,库恩后期的思想却发生了很大转变,他的自然主义立场逐渐转淡,而与之相对的先验论倾向则日渐突出。当代一些重要的科学哲学家,如伯德(Alexander Bird)和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等人都特别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其中,伯德称这一转向为“错误的转向”,这种康德式的先验转向“不单单意味着一种风格的转变。从自然主义转向一种先验论进路是和哲学自身流行运动相反的方向。”[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2,Vol.33,p.444.弗里德曼却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这种转向的价值,并尽力挖掘库恩哲学转向中的康德主义内涵及其意义,“弗里德曼表明,库恩言及的范式转换,特别受到新康德主义精确科学通过一系列结构转变演化概念的影响”[注]Chignell,A.Neo-Kantian Philosophies of Science:Cassirer,Kuhn and Friedman.Philosophical Forum,2008,Vol.39,p.253.,科学哲学超越相对主义的路径则在于发展一种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相对化先验原则的新康德主义”。[注]M.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CA:CSLI Publishers,p.xii.鉴于学界对后库恩时期哲学转向的理解和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本文将立足于库恩思想本身与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背景,具体分析和梳理库恩后期思想转变的思路、根源以及历史地位问题。
一、从自然主义到新康德主义
库恩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后期思想:“我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的康德主义。像康德的范畴概念一样,词典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前提基础。但词典的范畴并不像康德式的前辈那样,它们可以随着时间和共同体转变发生而且发生变化。”[注]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1990,Vol.2,p.12.较之于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强烈自然主义倾向,其后他的整体思路的确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总体上不断趋向于新康德主义传统,这种观念的差异是有目共睹的。伯德分析了库恩前后存在的巨大差异,“《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进路上属于自然主义,这建立在经验和科学发现的基础上,他的后期工作则更多是哲学的方式,在方法论上却是先验性的。”[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p.444.客观地讲,伯德的这段话既客观揭示了库恩后期走向新康德主义的思想理路,又进一步彰显了其先验论转向的基本特色,这一概括为进一步理解和解析库恩思想的逻辑变化发展提供了关键线索。
较之于奎因式的整体论自然主义,库恩最初是从自然科学和科学史角度描述和揭示科学变动问题的,这种自然主义立场或倾向更多属于一种潜在无意识或职业直觉,这与奎因自然主义得出的逻辑并不相同。当然,在实际效果上它可能还是与奎因将认识论归于自然科学分支的研究模式相一致的,但其思想脉络却是反方向的:“库恩自然主义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对历史证据的使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一大特征就是库恩大量利用了自然科学案例来证明或反驳一系列科学哲学的相关命题和观念,如“库恩引用格式塔心理学,这是由他的哈佛大学同事布鲁纳、普斯特曼进行的实验,甚至计算机感知判断的模式”。[注]Alexander Bird,Naturalizing Kuhn,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New Series,2005,Vol.105,p.99.这一自然主义方法是库恩最终确立一种新的“大异其趣科学观”的出发点,他将传统科学哲学“教科书”式的僵化科学形象纳入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史之中,即,让科学的历史本身说话,而这样一来科学哲学便只是一门描述自然科学的历史而已,是对自然科学描述性的解释学。按照库恩的这种思路,正如伯德后来所归纳的那样,库恩的论证依据多为经验科学材料,而少有哲学文献方面的借鉴,“库恩自己把他的书当成哲学目的而完成的历史著作。但有意思的是,库恩为这些哲学主张援引的证据大部分却在本质上不是哲学,而是相反来自于经验科学以及科学史。”[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p.446.如此,库恩就从与奎因不同的角度实际肯定了科学与哲学存在的连续性,特别是具体践行了自然主义的替代性命题(the replacement thesis)。
因此,在库恩看来,传统科学哲学的“合理性理论并不正确,我们必须调整或变动它们以解释科学工作为什么是如此的”。[注]Thomas S.Kuhn,Reflections on my critics,In I.Lakatos& A.Musgrave (Eds.),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264.在这看似并无多少新意的逻辑之下,库恩却在暗中撬动传统科学哲学规范化理路的其他可能性,因为新科学哲学应该把科学实践作为一种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的经验现象加以科学考察和研究,为此哲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探究规范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规则,而转变成了描述和总结实际上科学家如何工作的新“科学”。如此一来,传统科学哲学的规范性目标失去了合法性,在此意义上科学哲学的确就成为了一门自然科学学科,并由此回答了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问题:“如果一个人承认认识论是规范性的,那么他就不能从科学史中获取认识论,除非这提供了解释规范性是如何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哲学说明。”[注]Samuel Schindler,The Kuhnian mode of HPS,Synthese,2013,Vol.190,p.4138.无论是库恩对常规科学还是科学革命的描述,科学实践都成为考量和评价科学认识的根本视角,科学哲学的逻辑重建必须以准确描述科学的历史为基本,作为“一门纯粹的描述性学科”,必须打破“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的二分,以至于“许多概括涉及到科学家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注]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从当时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情况来看,库恩的这些思想确实为之后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打开了一扇大门,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认识论都从中汲取了各自的理论营养,“库恩乐于使用各种经验科学和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和历史学)的途径来处理(至少是部分)哲学问题”,这意味着他“倾向于用自然主义元素取代更传统哲学的、先验的方法”。[注]Alexander Bird,Kuhn,Naturalism,and the Positivist Legacy.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4,Vol.35,pp.337-338.
但库恩的后期思想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自然主义研究范式之内,他出乎意料地却转向了先验论进路的新康德主义:“‘我是一个可变动范畴的康德主义者’,为回答弗里德曼的评论,库恩承认最初莱辛巴赫在其著作《相对论》中对先验知识的区分,其中,构成性先验知识与知识过程的历史变化(时间、地点和文化)相联系,而不变的、绝对固定的先验知识则不随时间而改变。前者在相对意义上只是知识对象的构成性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库恩宣称了其康德主义的立场。”[注]M.Ferrari,Between Cassier and Kuh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2,Vol.43,p.20.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前后科学理论或范式的转变是必然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范式(或词典)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它有着类似于莱辛巴赫构成性原则或卡尔纳普理论框架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无论是科学共同体在时间上的交替,还是概念空间上的变化,它们的词典结构一定会在某些主要方面存在重叠,否则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就没有学会其它词典的可能性。”[注]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SA: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p.12.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库恩后期转向语言学角度来探讨科学发展连续性问题的思路,理论术语和指称等哲学问题也成为他思考科学合理性问题的新角度,就此,科学革命前后范式的不可通约问题转换为了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问题。无疑,库恩语言学讨论的深层原因在于语言框架的构成性作用,而且语言框架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好对应着以往的不可通约问题,所以,库恩才说,“要在共同体之间架起桥梁,这就需要把一种类词(kind-term)加入到存在重叠、并拥有共同指称的词典”,由此,“不可通约转变成为一种不可翻译性,这限定在了两个不同分类词典的某个领域。”[注]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1990,Vol.2,pp.4-5.
在库恩看来,拥有不用“词典”的科学范式的交流障碍或分裂是很正常的,他将其比喻为生物进化时物种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借助生物学的这种观念给予解答。为了克服人们对其理论的相对主义解读,库恩指出,“在本质上我并不是(相对主义者)”,“必须澄清的是,我对科学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进化论的。因此,可以想象一个进化树来代表科学学科物种从共同起源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就像生物进化一样,是单向和不可逆转的”。[注]Thomas S.Kuhn,“Reflections on My Critics,”In:Lakatosandusgrave,eds,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64.进一步讲,这种库恩所谓的“后达尔文主义”必须要和新康德主义对科学知识存在先验成分的主张相联系来理解,因为“语言学转向的结果——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之间的区分变成了需要科学词典变化和不需要变化活动之间的区分。在科学革命中,新的发现不能在现存词典框架内得以描述,因此科学家被迫采纳新的词典,科学革命中用格式塔转变词语的心理学描述消失了。”[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8,p.143.可见,这种新的思路使得库恩又走上了他曾经所批判的逻辑经验主义的路线,“在库恩对科学革命本质和特征的反思中,我们可能会找到逻辑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相对化先验构成性原则的非正式性对应物。库恩主义在常规科学之外范式变化和常规科学时期活动之间的区分,反应了卡尔纳普在语言或语言框架变化和在这种框架操作下有规则活动之间的划分。”[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p.179.这样一来,库恩前后思想本身也实现了一场“库恩式”的哥白尼革命,而这场理论变动的合理性问题成为把握库恩整体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
二、两种“范式”转变的内在根源
比照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库恩后期的思想转变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从当时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这种转向甚至有些逆势而动。因为当代科学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普遍趋势是走向自然主义,人们一般还把库恩和奎因等人同样视为这场运动的关键发起者,但库恩在此之后却不断在远离自然主义,为此伯德才颇为遗憾地指出:“尽管库恩在20世纪后半期具有巨大影响,但为什么他没有留下独具特色的库恩式遗产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库恩自己思想的发展方向正好与科学哲学的主流相反。七八十年代的科学哲学接受了普遍意义上外在主义关于指称和知识的观点,越来越同情哲学问题的自然主义进路”,但在这时,“库恩的工作却带有了更纯粹哲学,先验论的味道”,这是一种“错误的转向”。[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Vol33.p,443.为了更清楚理解和进一步评判库恩思想发生的这种巨大转变,或套用库恩自己的话说就是,“前库恩”与“后库恩”范式革命的发生是否具有合理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先理清库恩前后转变背后的原因,然后才能对库恩的整体走向给出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鉴于库恩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史上的特殊性,我们要梳理清楚他思想变化的原因,其中的关键一步在于分析库恩本人思想与当时科学哲学的整个发展趋势的关系问题。须知,我们并不能把库恩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当时科学哲学的总体发展趋势完全相一致起来,这也是许多人(如伯德)批判库恩“错误转向”的根源所在。但换一思路,是否还应该继续追问——在此发展过程中库恩自身思想的独特演变逻辑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因为库恩理论与当时自然主义流行倾向相悖并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所谓的“错误”,这正如库恩自己表明过的科学理论并不能仅仅由当时的经验证据所完全决定,还要进一步着眼于库恩思想本身的合理性及其未来影响的问题。在这方面,库恩思想的这种特殊逻辑的展开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库恩科学哲学观念本身的特殊演变;二是库恩对《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自然主义进路遗留难题的解答思路造成的。随之,这两方面也将成为深入探讨库恩后期转向合理性问题的主要参照点。
首先,来看库恩本人哲学观念的转变问题。库恩曾这样评价他自己对自然主义的看法,“当我第一次接触如今被称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也就是大约30年之前的时候,我与我的大部分参与者认为历史是作为一种经验证据的根源起作用的。这些从历史事例研究中发现的证据,促使我们更紧密关注于真实的科学。现在我认为以前我们过于强调了事业的经验方面,因为进化认识论不一定必然就是自然主义认识论。对我而言,最本质的东西在于研究历史案例的视角或者意识,而非具体的案例细节。”[注]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6.库恩相当客观地描述了自己观念的转变历程,伯德为此又对库恩哲学立场的变化做了一系列更深入评析,认为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库恩和学院哲学的关系”,“一方面库恩受到的哲学训练很少,另一方面他又强烈期望成为一位哲学家。库恩是作为一名科学史家开始其学术职业的(他已经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且进而跨学科进入哲学领域。这种学术转变和库恩思想的哲学转变相一致。然而,由于没有受到20世纪哲学的彻底训练,库恩没有意识到他从事工作哲学观念的历史和辩证起源。”[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p.445.姑且不论伯德观点正确与否,但他确实道出了库恩前后哲学倾向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库恩本人在学术方面的特殊经历,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的发展心路。
其次,是库恩对其前期难题的回应,特别是对不可通约和相对主义问题的解答。在这其中,后期库恩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回答“不可通约性”难题,这正如伯德所指出的那样,“库恩著名的不可通约命题是其从自然主义转向先验论哲学思维的基本载体。”[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p.451.库恩在《结构》中主要是借助于心理学来说明科学革命前后世界观的转变问题,“早期求助于格式塔转换,我把世界理解为依赖于心灵的,但这种依赖于心灵的世界隐喻。正是群体以及群体的实践建构了世界,科学发展的基本单位是群体,但群体并没有心灵。”[注]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10.但众所周知,面对相对主义的指责,库恩一方面将科学的发展与生物进化相类比,另一方面又将“科学变化的进路解释为一种康德主义的修正形式,在此意义上,他把自己当成战后分析哲学中康德转向的一部分。”[注]ThodorisDimitrakos.Kuhnianism and Neo-Kantianism:On Friedman's Account of Scientific Change.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6,Vol.30,p.361.这种康德主义,是一种相对化的、变动的先验论,“当后者(构成性先验知识)在其相对化意义上,我的结构性词典类似于康德的先验知识。它们都是世界可能经验的构成,但都没有指明经验到底是什么。反之,它们是无穷可能性经验的构成,这些经验可以被想象出现在任何可能的实际世界。”[注]M.Ferrari,BetweenCassier and Kuh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12,Vol.43,p.20.只有相对化可变动的知识原则才是范式或词典的核心部分。
事实上,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是相互统一的,而伯德却将库恩和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大背景的差异视为“错误”,这才导致他没有进一步讨论其中更深层次的背景问题,因为这种新转向与自然主义整体发展趋势相悖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是有问题的。进而言之,库恩触及到的正是当代以来科学哲学的一个最大难题,即科学哲学的规范化和自然化之间张力的矛盾问题,只是他与奎因的思路相对而行,从看到描述性、自然化的科学哲学需要面对相对主义而试图通过先验论理路来实现拯救。而奎因则相反,他从规范化认识论意识到先验论传统的不可实现,转而走向对认识论的自然化,但时至今日自然主义依然无法摆脱描述性带来的相对化难题。所以,库恩前后思想转变的原因仍是基于两大传统的矛盾与问题,而人们对库恩后期思想发展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是过激的,只是原因更多却仅仅因为与他们的原有期望或设想不一而已,这时许多人发现库恩原来离传统科学哲学这么近,“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在一种统一的概念框架之下活动……用卡尔纳普自己的话说,它们构成语言框架的支配规则,并界定着一套内部问题”;而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们失去了参考的基础,这使得他们可以推动和支持向新范式的转变。用卡尔纳普的话就是,科学家们面对外部问题,这是关于语言框架被新规则替代的问题,这往往完全不同于旧规则。”[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08,p.179.
可见,库恩转向康德传统寻求解答的逻辑,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突兀和不可思议,在此转变过程中,库恩并非跳跃性一下子得出这一结论的。为此,伯德的结论可能还并不充分,“没有理由假设他(库恩)与康德哲学非常熟悉”,“库恩似乎直到70年代才明显有了康德主义的意识”。[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p.455.在此问题上,笔者更同意豪宁根-休尼(Hoyningen-Huene)的观点,“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可以看到,‘世界’一词的使用有些模糊,这一点恐怕库恩本人也没有注意到。首先‘世界’意味着一个‘早已在感觉和概念上以某种方式划分过’的世界。……范式——不管它指什么——都是在感觉和概念上分化世界的要素。用更传统的术语就是:知识的主观性在于知识对象的构成方式(通过范式)也即它们排列这些对象世界的结构。”[注]Paul Hoyningen-Huene,Idealist Elements in Thoma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1989,Vol.6,No.4,394.也就是说,库恩观念中的康德因素确实是早就存在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描述的自然世界是二分的,“这个世界很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相应的,主观方面类似于康德的表象或现象的整体,‘所有可能的经验对象’。”[注]Paul Hoyningen-Huene,Idealist Elements in Thomas Kuhn's Philosophy of Science,pp.394-395.根据以上原因我们可以说,库恩前后思想的转变,是存在一定原因和过渡性的,并非完全的所谓库恩式的不可通约的范式革命。
三、库恩的新康德主义转向的内涵与意义
从库恩思想前后转变原因和思路来看,伯德等人所说的“错误转向”主要是侧重于科学哲学大背景与库恩自身观念变化之间不一致性维度而言的。其实,无论是库恩缺乏“全面哲学训练”还是对相关哲学论题的不熟悉,这都不是造成库恩从自然主义转向康德传统的根本原因,伯德所列的那些理论背景和库恩走向先验论的逻辑是否合理之间并无必然关系。而且,康德进路在当时已经不占主流地位,即使库恩渴望获得哲学认可也大可不必走向自己的反方向,因为在哲学家眼中“自然主义因素”才是“库恩思想中最具原创性和富有成果的东西”。[注]Alexander Bird,Kuhn,naturalism,and the positivist legacy,p.338.因此,这种转向的原因更多是出于库恩理论本身内部存在的困难,“他(库恩)兴趣的焦点从范式的功能(function)与感觉经验的本质转到(研究)科学中使用语言的本质”,但对语言的研究即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只有唯一一条路径可走:库恩可以对“理论转变、世界的转变和不可通约性给出一个完全的自然主义说明”,[注]Alexander Bird,Kuhn's wrong turning,p.449.但同样,库恩也可以诉诸于康德传统,因为这两种理论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康德范畴的构成性功能在库恩这里转变成了语词的分类。而且,康德的范畴是固定的,普遍性的,而库恩的语词分类则是随着历史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库恩看来,存在多种现象世界,但只有一个实体的世界。”[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pp.143-144.这样看来,要判断库恩后期的转变是否具有合理性,关键在于评价其与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的关系以及自然主义科学哲学本身的合理性问题。
按照传统的理解,《科学革命的结构》是致使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标准科学哲学研究传统转向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品,“这部著作(指《科学革命的结构》)被视为逻辑实证主义走向衰落的关键”,[注]Alexander Bird,Naturalizing Kuhn,p.100.它引发了之后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新方向。而且,毫无疑问,自然主义仍是当代科学哲学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但这并不表示自然主义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最明显的是,历史主义以及奎因对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解释没有摆脱掉相对主义的纠缠,科学哲学的自然化同时意味着科学哲学的相对化,这也是奎因等人最后都将科学合理性诉诸工具主义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看到自然主义与相对主义总是相伴而生的原因,那就是科学认识中非规范性维度的缺失:“自然主义是和规范性相对的,自然主义的意图是描述、说明和解释”,[注]William J.Devlin Alisa Bokulich,Kuhn's Structure of Scienti?c Revolutions-50Years On.Springer,2015,p.13.对知识或认识的描述性并不能回避其规范性(normativity)或相对确定性(certainty)的一面。当然,传统哲学理解的知识绝对确定性和先验性的确难以维持了,所以,库恩后来宣称自己坚持康德意义上范畴的“可变动性”,这也是他试图综合它们二者关系的一种理论努力,在这中间,库恩后期的核心概念“词典”确实起到了这一作用,“结构性词典起着建构世界和经验的作用,这就是以前范式所要起的作用。它们变成了相对化的康德范畴。”[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p.143.
弗里德曼进一步明确了以上思路,并分析了库恩理论中范式概念原已蕴含层次性特征以及所起到的建构性作用。一方面,范式中包括“符号概括”“范式的形而上学”等内容,由此可见科学范式是一个“分层的,或者说差别性的知识系统”,而非像奎因认为的那样科学理论建立在经验命题并存平等的自然主义状态之下的。另一方面,范式构成科学理论的基础,换作弗里德曼的解读,范式或词典即是相对化的先验性原则,“这些相对化的先验原则构成库恩所说的范式:至少是相对稳定的一系列游戏规则,它决定着或者说使得常规科学的解题活动成为可能”。[注]M.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p.45.如此看来,库恩的早期思想并非最初人们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反实证主义传统的,在他的理论中,是有多种哲学倾向同时存在的,其中,“库恩早期工作存在两种占支配地位的对立因素:首先是一种强烈的自然主义成分,这是他反驳实证主义方面的主要武器”;其次是对“其它实证主义命题的承诺”。[注]Alexander Bird,Kuhn,Naturalism,and The Positivist Legacy,p.355.准确一点说,库恩科学哲学更多是对实证主义传统将科学静态逻辑化狭隘理解的一种反思,其出发点和立论仍是站在自然科学角度的,其哲学观念则是较为模糊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基于这一视角,库恩历史主义的走向其实并不明确,可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认识论的自然主义,也可能最终是反对自然主义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将会使我们抵制这种观点,即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被吸纳进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如赫尔姆霍兹的心理学概念,或者是数学科学(如卡尔纳普式的科学)。”[注]M.Friedman,Dynamics of reason:The 1999 Kant Lectur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p.43.从这一点来看,弗里德曼对库恩后期动态化先验论解读并非没有道理,而且,这也可能是一条走出科学哲学相对主义难题的路径。
因此,从库恩后期的转变情况可以更清楚看到逻辑实证主义、先验论和自然主义之间更复杂的关系,“库恩对科学革命本质和特征的理解可以在由逻辑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相对构成性先验原则中发现其非正式的对应物。库恩在非常规时期范式变化和常规时期科学活动之间的区分反应了卡尔纳普在语言或言语框架变化与在此规则支配下认识活动之间的区分。”[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p.179.如果将克服相对主义作为衡量科学哲学发展的关键标尺,那么就可以说,库恩后期的道路又揭示了其早期所未能展开的另一维度,即某种“先验”框架对科学理论的意义,因为“实在并不是直接可知的,不求助于词典甚至都不能表达。‘任何描述性表达、关于游戏真假的陈述,’库恩说,‘需要一个先验的词典,并且词典会带来某种与之相关的相对关系’。换言之,词典决定着关于世界及其真理性陈述的可能性。”[注]James A,Marcum.Thomas Kuhn's revolutions:A Historical and an Evolutionary Philosophy of Science.Bloomsbury Academic,2015,p.140.按照维特根斯坦的分工理论,库恩对哲学维度的重视,也就是“范式的中心是它的哲学方面”,[注]Thomas S.Kuhn,Reflectionson My Critics,p.315.意味着“哲学为经验科学提供了一个非经验前提的说明”。[注]Nicolas de Warren,Andrea Staiti.New approaches to Neo-Kantia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70.相对于自然主义,库恩的新康德主义走向更彰显了科学实践的丰富性和多维性,他强调的是让哲学和自然科学联合起来,而非将哲学简单融入自然科学。
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全盘接受弗里德曼的观点,毕竟库恩的思想更多仅是蕴含了将科学理论结构和功能化的倾向,而且弗里德曼也没有能够完全解答由此引出的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在一定意义上肯定这种进路的价值,而且这是在某种自然主义层面上对反先验论的反思,库恩从另一方面质疑了经验论传统的一个基本信念:“我们所有关于世界的知识都要通过经验获得。关于世界的先验知识——基于诉诸于理性的知识,它独立于经验——是不可能的。”[注]N.Maxwell,A Priori Conjectural Knowledge in Physics,in Michael Shaffer and Veber (eds),What Place for the A Priori? Open court,p.211.因为所有经验观察都是负载理论的,而范式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关键构成部分,这种“概念框架不是一组信念,而是一种特殊的形成的信念心理模块的操作模型”,[注]Thomas S.Kuhn,The Road since Structure,p.5.在科学理论的功能角度上,这种概念框架是具有某种先验性的。相对于自然主义彻底将理论乃至人类理性都经验化的作法,库恩在科学活动中保留一些经验之外的因素存在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科学认识毕竟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形式,即使是按照语言哲学的说法,“真理和合理的可接受性”也是“相对于我们使用的语言和身处其中的语境而言的”。[注]Hilary Putnam,Why Reason Can't Be Naturalized,Synthese,1982,Vol.52,No.1,p.8.较之现代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的整体极端化发展,库恩的走向倒是具有更强烈的理性色彩。
基于以上原因,如果将库恩的后期转向放在自然化和规范化之争的科学哲学大背景下看,库恩的先验论转向就明显显现出与伯德在自然主义背景下比较的不同结果。无论是真实的科学活动还是抽象的科学理论,都是科学家与自然界交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家的能动性和受动性均是无法抹杀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简单将科学认识论的能动性这个重要维度取消并不能解决问题,即认识论的自然化不能取代规范化的作用。与科学认识规范化直接相关联的背后基础在于人类理性对经验的规范和整理,就此,科学理论的经验命题以及分析命题才得以区分,其成立前提在于“我们拥有一个概念系统,它是中心化和先验性的”。[注]Hilary 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40.库恩在强调科学经验化特征的同时,在后期关注和发展相对性的科学规范化的一面,也就是他所谓的“变动性先验原则”主张,对自然主义的绝对化倾向具有纠偏意义,有助于人们重新重视科学理性与经验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也就有力回应了普特南的判断:“如果正确性、包括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概念都被消除了,那么我们的陈述除了是制造噪音还能是什么呢?对规范化的消除意味着尝试在精神上的自毙。”[注]Hilary Putnam,Why Reason Can't Be Naturalized,Synthese,1982,Vol.52,p.20.从这一角度来看,库恩的新康德主义走向并非没有意义和影响,正如“在写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之时”,库恩还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持,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他领先了他的时代”,[注]Gattei,Stefano,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p.213.这种新走向也可能如此。库恩后期转向虽然没有再能激起巨大轰动,但他始终准确把握着科学哲学的时代脉搏,并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一条超越自然主义的可能性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