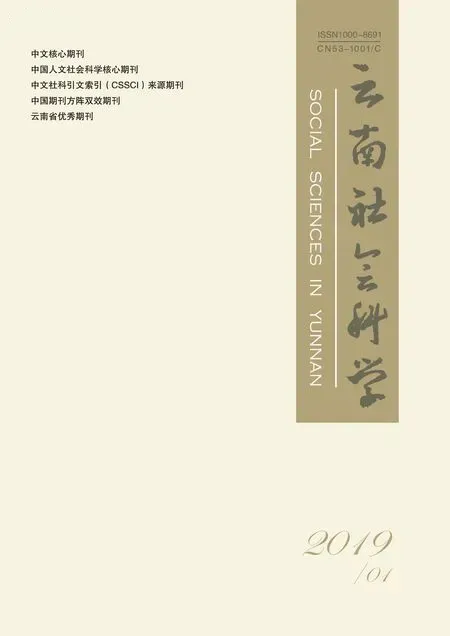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径
赵轶峰
以将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称为“帝制农商社会”为话语轴心来展开的关于明清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的学术探讨已经提出11年了。[注]①这一论说最初提出在2007年,参看赵轶峰:《明代历史趋势:帝制农商社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其后陆续有多篇论文刊出,最近集结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近年来,此说与葛金芳先生以唐宋时期社会经济为考察重心的“农商社会”说、林文勋先生以唐宋以降中国社会主导力量为考察中心的“富民社会”说一起受到日渐增多的关注,以相关概念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已经连续举行5年,并被各种评论所涉及。[注]②参看林文勋、张锦鹏主编:《中国古代农商·富民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种关注,必然鞭策相关论说的提出者对自己的学术主张进行深入、缜密的省察。恰逢《云南社会科学》拟对这几种论说的学理构成做一次集中呈现,并由葛金芳先生再加评点,这提供了笔者对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径做一些阶段性学理自查的机缘,若能由此获得同仁的进一步评析,于相关探讨的深入应更为有益。
一、问题的由来
20世纪70年代末,笔者开始在李洵先生指导下从事明清史的学习与研究。李洵先生关注的根本问题是“明清社会结构”。其基本含义与当时学术界主流的理解一致,主要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生产方式。所以,先生特别关注对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但他并未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局限在生产关系,而是扩展到更广大的社会,提出了关于明代流民与海盗与资本主义发生趋势相关联的看法。[注]③参看李洵:《下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他的研究,引领笔者很早就把明清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置于思考的中心。当时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具体层面有多种分歧,但在基本理念层面是一致的。研究者都主张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解体的时代,也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是中国显示出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初期,分歧则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具体表现、程度,以及如何解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最终没有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笔者最初尝试沿着学术界的主流方式考察下去,首先想确证明清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与同时期的西方相似,在向一种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但很快发觉证明不了。把前辈们发掘出来的资本主义萌芽证据加在一起,能够确证明清中国经济领域充满活力,在变化、发展,不能确证这些发展已经汇流成为一个确定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或过程。而且,学术界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已经揭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基本面相,还会有新资料的发现,但很难达到足以改变当时对明清经济基本面相判断的程度——后来30多年的文献研究实际证实了这一点。至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未能发展成资本主义大树原因的分析,在当时语境中,都属于对推论必然发生而又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解释。历史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已然之事,对未然之事虽可推测展望、连带思考,但不可能用实证方法考察,就只能形成“观点”而不是“事实”性质的判断。所以,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发展开资本主义社会更接近于在探讨理论,从历史学意义上说,远不如讨论明清中国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更有意义。于是,明清中国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如何透视其基本组织运行方式并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阐明其类型特征及其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方式,成为充满魅力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笔者既在钻研前贤研究从而形成基本知识的过程中也察觉到前贤研究的视角可以调整,就去梳理更早的问题和方法论渊源,于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亚细亚形态说、东方专制主义说,以及相关的思维方式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对历史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进行钻研。这时候发觉了3个相互关联的情况。第一,参与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多数学者没有特别注意区分“资本主义”是被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还是经济体系的问题。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学者大多自然地倾向于经济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因而觉得二者区分的意义不大。但是如果那样,在思维层面就落入了单向决定论,这种思维不适合用来讨论复杂系统,而社会历史的形态演变就是复杂系统。如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生产关系领域的雇佣劳动关系萌芽现象只表示出现了在性质意义上与资本主义经济契合的情况,不表示已经发生了在历史趋势意义上向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演变过程,因而不应该将之称为“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个被抽象化的经济类型,那么雇佣劳动关系就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中国学术界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来讨论的,但其言外之意,又几乎没有例外地是把生产关系作为整个社会之性质的基础的,有比较明显的单向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思维色彩。第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的方法论都立足于人类社会五种形态依次演进的学说,并且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笔者做了认真的梳理研究,最终判定:马克思表述过两种社会形态概念系列,一是三大形态系列,一是五大形态系列。其三大形态系列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其五大形态系列是逻辑的,而不是历史的,而且马克思的五大形态是指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学术界习惯表述的不同,而且从来没有表述过五大形态是作为世界普遍规律的表现而依次递进的。以往中国学界习惯表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依次发生,前者孕育后者的模式是苏联理论家以斯大林名义表述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习惯于假定几位“经典作家”的观点一致,在自己的表述中让他们相互代表,相互解释,从而也就时时把斯大林的言论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但就他们的论说分析下去,差别其实很大。如果我们真正尊重这些思想家,就应该尊重他们各自思考的历程和特殊之处。[注]这些研究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的期刊上发表,后收入《学史丛录》,参看赵轶峰:《学史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8-88页。第三,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历史学,都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资本主义萌芽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与西方中心主义有些关联。因为,这个问题的论证指向是求证中国历史发展符合世界历史普遍规律。需知,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需符合历史的经验事实,起码是基本事实,按照中国在人类历史中波及的空间范围、人口占比、文明表现,如果中国历史与“普遍规律”不符,该规律就不普遍。换言之,我们原不应该提出中国历史是否符合人类历史普遍规律这样的问题。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浸润人类思想的观念,深入到思维方式层面,并不是选择情感立场这样的简单问题。这些考察使得明清时代社会结构和历史趋势对笔者说来,回归成为一个需要从根本层面重新探讨的学术问题。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加拿大求学,收获主要在对史学理论、社会史、世界史以及对西方明清史研究的了解方面,但所有的思考依然会投射到前面提到的基本问题上去。把其间重要的心得归纳一下的话,可以这样表述:
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特殊话题,虽然在亚洲其他国家史学界也有讨论,但不是国际学术界的前沿话题,西方学术界主流不使用这个概念,也不赞成这样提出问题,其中未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成分,但也有学术方面的理由。国际学术界认真对待的问题,其实是现代性在中国发生的历史过程,以及是否存在本土文化、社会、历史依据的问题——这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很大不同。世界历史上只有西欧的历史接近于斯大林图式的五形态递进历程,其他地区、民族、国家皆非如此,所以五形态依次递进不是定律。文化差异对于理解宏观历史演变,尤其是文明的推演,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以前思考社会历史时对文明视角过度忽视,接近于把历史演变当作经济带动的过程,人类历史演变中的普遍逻辑和共性并不严格规定各文明、文化、社会自身历史演变的道路。西方学术界也没有关于明清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的现成答案,相关的研究能够带来很多启发,但并无定论,且时时可见较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而中国学术界的教条主义其实是一种另类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历史演变必须通过历史的方法即考察已然历程的方法来认识,不能用演绎的方法来认识。认识中国历史演变的独特性征与认识中国历史与其他民族、社会历史的共同性同样重要。中国的晚近发展其实正在日益提示醒目地中国社会、历史道路的独特性。后现代批评思潮已经揭示出“现代社会”存在种种局限,因而,“现代社会”并不是历史的终极目标,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们都需要继续思考社会合理性的建构问题。这些认识如果展开,需要很多文字,这里不能详说。
二、研究范式的检讨
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涉及面很宽而又有许多前贤研究过的问题,就一定要对前人研究的范式进行深入剖析。这类问题其实不可能因为一两个实证性环节而至于长期不能达成共识,所以如果有重大分歧或难点,就一定在研究范式层面有些问题有待澄清。我们暂且采取把现代性发生作为思考明清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的核心,那么,已有的各种相关研究范式在笔者的梳理中会大致呈现为下述情形。
(一)中国学术界的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这个视野下显示为“资本主义发生障碍范式”。这种研究偏重强调经济因素必然带动社会整体形态向某种世界性普遍同一的模式演变,理论预设性强,而实证依据不足。此点前面已经谈及,不再重述。应该略加注意的是,参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学者虽多,但以经济史家为主,绝大多数经济史家偏重于从经济角度审视整个社会,所以“资本主义”在多数情况下既被作为一种经济体系,也被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类型。其背后的思维逻辑是,经济体系会自然而然地确定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但这是一种要素决定论的思维——无论经济在整个社会体制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它都不能单独“决定”整个社会体制。所以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是有差别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初看是在讨论经济生产方式,实际的指向却是整个社会的基本体制,这是论证难以通透的原因之一。把问题提升到现代性发生的层面,这个困境则可以化解,但接下来其路修远。
(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促发资本主义说提供了一种从信仰倾向角度解释资本主义发生过程的研究范式。[注]韦伯著作,近年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结出版的中译本,参看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他本人甚至研究了中国各种信仰与资本主义在逻辑上的可契合性问题。[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年。他以这种范式解释英国资本主义起源的论说在西方学术界既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诸多质疑,包括认为他夸大了新教伦理推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后来一些评论者借助此范式解释20世纪中后期亚洲几个国家的经济崛起。余英时先生受韦伯影响,写了《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提示中国“近世”也存在新的宗教伦理和商人精神。[注]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这种范式对关注信仰方式于社会结构推演的作用有启发意义,但因夸大宗教伦理引导新质商业精神的作用,忽视经济、政治等诸多其他重要领域,并不能透彻说明明清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
(三)伊懋可(Mark Elvin)在1973年出版《中国历史的模式》,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说。他承认明清中国经济有一定发展,但认为依赖高密度人力投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最终陷入发展停滞。[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该书第三部的几个标题准确表达了伊懋可的核心主张:第三部分标题是“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out technological change”(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增长);该部分中一个小节题为“Quantitative growth,qualitative standstill”(数量增长,质量停滞);其下一个小标题为“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高水平均衡陷阱)。参看该书第203-319页。他不是明清史研究的实证史家,所有分析资料都借助二手或更间接的资料。他的论说之重要性,一是虽然最终判定明清时代中国经济还是陷入了停滞,但表达出尝试摆脱中国历史长期停滞说法的意图;二是提出了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种模式说。该书长期没有中译本,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小,但对后来兴起的加州学派影响很大。
(四)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中译以后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不小影响。[注]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弗兰克是依附论的主要论说者之一,而依附论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关照拉美国家经验而兴起的影响最大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具有全球史观含义的现代国际关系结构论说。从历史角度看,弗兰克强调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就已存在的商业世界体系的中心,白银和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虽然梁方仲、全汉昇等人曾对明代白银输入中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但偏重实证,弗兰克的考察虽并没有使用明清中国的原始资料,却具有非常宽广的世界眼光和理论性,比较深刻地阐释了明清中国与世界大变迁的关联。不过,弗兰克带有依附论者刻意从非欧洲范围梳理现代起源的主观倾向,夸大了白银和中国市场对现代世界兴起的作用,没有把前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与现代经济、社会体系之间的差别说清楚,当然也没有正视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究竟如何的问题。另外,他当然也不是明清史领域的实证史家,在论述中曾借助于前述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说。
(五)加州大学黄宗智的明清经济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与伊懋可的高密度陷阱说很相似。“内卷化”概念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hifford Geertz),指一种系统在发展到某种模式之后无法转化进入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他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借用这个概念,并将之重译为“过密化”,用来指明后期以降“总产出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的经济模式,这种通过过密化而实现的增长,不仅不会导致小农经济让位与大规模生产,甚至会因为单位劳动力报酬更低而阻碍雇佣劳动生产的发展,所以也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2页。他在题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的论文中对这一主张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明确指出,“过密化解释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注]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第426-428页。该文最初与1991年以英文发表于Modern China,Vol.17,No.3,后曾刊于《史学理论研究》,再后作为附录收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在黄宗智的论述中,这种过密化的经济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正因为如此,该说作为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假说,对认识直到晚近的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意义很大,但是作为解释明清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趋势的研究,问题就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农业生产中的“过密化”与土地、人口数量高度相关,江南在明前期就已经出现土地不足,人口密度偏高,而其他诸多地区并无同样、同程度的问题,明清继替,全国的农业可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就全国而言,“过密化”是否构成普遍事实、具体情景如何,还需要经过大量黄宗智并没有进行的实证研究。其次,他虽是大量运用原始文献的经济史家,但他喜欢大时间跨度地分析史料,一些重要数据的考证难以令人信服。[注]参看苏新红:《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中心》,《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
(六)加州大学的另一位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提出了“大分流”说。[注]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其鲜明特色之一,是努力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社会兴起叙述,强调中国、亚洲及其他非欧洲社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尝试。但他的论说也带有比较突出的经济决定论色彩。该说用GDP作为一个比较的尺度,判断17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经济水平与同时期英国约克郡相当,到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才“分流”,而“分流”的重要原因是欧洲开始大量使用新的矿物能源。他把江南地区孤立出来与英国的一个郡比较,这是无法说明作为整体的中国的社会历史趋势的。[注]该说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反馈到西方学术界,如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中国历史研究》)的2011年秋季号(总第45卷第3期)就曾以“The 'California School' in China”(加州学派在中国)为该期主题,刊发了龙登高、史建云、王家范、赵轶峰、李宪堂分别撰写的5篇评论文章。他的这个颇为复杂但并没有系统使用明清中国原始材料的论说中有一点非常凸显,即被黄宗智归入“内卷化”的17世纪中国,在彭慕兰的论说中却被认为是持续发展的。这表明这两位皆来自加州大学的学者的主张有很大差别。[注]参看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不过,在方法论层面,两人都过度偏重从经济角度看问题。在本文思考的视角下看,与伊懋可的高密度陷阱说以及加州大学其他学者的研究方式类似,这种考察把历史问题过分经济学化,把经济从复杂的社会、文化、制度中抽离出来,假定其在很大程度上单独运行,这作为旨在建构模式的经济学方法无可厚非,但作为旨在解释历史的方法就显得建构性过强而忽略的关联事实过多了。而且,把发展理解为关于一个社会人均增长力增长的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主要观点之一,而该理论的局限已经受到学术界多角度的批评。[注]现代化论对亚洲历史的理解方式曾产生普遍而且深刻的影响,但其可议之处甚多,有待深入分析。对于该理论的简要评论可参看皮特·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赵轶峰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10页。
除了前述这些之外,还有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对明清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从方法论层面看,要比前述几位学者的影响力弱一些。前面提到的几种研究范式在本文思考的问题视角下各自显示出一些局限,同时也各自带来一些启发,而其全面学术含义还要以更细致的方式梳理和评价,那不是本文能够处理的。
这里有必要稍微窥测一下前述各种范式背后更深一层的思想背景。如果把关于中国历史“停滞”的各种表述追溯上去,可以看到从魏特夫、马克思到黑格尔,再到16世纪前后欧洲旅行家和传教士言论影响形成的东方知识和东方意象,有一条欧洲中心主义推演的线索。中国多数学者不赞成中国历史停滞论,但他们反驳的路径大多是从主张中国历史符合世界历史普遍规律切入,而他们心目中的“普遍规律”又是在很大程度上以西方经验为中心概括出来的,从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常常陷入两难。
在更“普遍”的层面,西方中心主义和中国历史停滞论紧密纠缠,其背后的思维取径都与人类历史单线进化发展观和单一因素决定论有关。所以要突破中国历史停滞论,就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就要突破线性历史发展观;要突破线性历史发展观,就要突破历史的单一因素决定论。持定单一因素决定论,就会演绎出线性历史发展图景,在现代性起源问题上就会把欧洲代表的现代社会作为历史目标,认为其体现历史必然和普遍真理,与之不同的历史趋势也就会被视为“反常”或者缺乏实质意义的。类似明清中国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这样的问题,关涉诸多因素,是任何单一因素决定论都阐释不清的。
弗兰克的论说带有依附论色彩,而依附论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既有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也带有拉美社会的反西方情感色彩,亚洲历史研究者很容易出于情感而对其论说产生共鸣。从现实归属情感出发而在历史分析中尽量凸显本民族、本国或者更大归属单元的历史重要性的倾向,可以在许多历史研究中看到,虽然可以理解,但常常影响研究的客观性,需要特别警觉辨识。此外,绝大多数关于明清中国社会结构和历史趋势的说法,最初都是由理论家或者宏观经济史家提出来的,而不是由具体考察明清中国的历史学家提出来的,他们在证据层面皆有许多勉强甚至不成立的判断。
所以,我们不能通过傍依前人来解决原初的问题。中国优秀的历史学者研究问题其实比较严谨,但他们似乎偏爱经学家本领,习惯沿着名家的主张申说,而怯于兜底重构。这可能与中国历史研究者在思考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时相对谦卑有关,心理上缺少理论质疑、建构的勇气。笔者自己的理论知识也很有限,但笔者知道自己研究的是历史,历史的判断和解释不能与证据反悖,理论无论多高深,如果不与证据契合,就有修正的余地。因为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问题的解说涉及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而大理论家多不做实证功夫,所以做断代史的人尽可以用证据去打磨理论。于是,虽然理论知识多有欠缺,笔者还是在许多年间,陆续把前人的研究路径和结果做比照分析,辨析得失,尝试梳理出一种最大限度规避其局限而又与证据最大限度吻合,在反向推论中找不到重大反证的研究路径来。
在笔者的研究中,有3个原则很重要:一是结构分析。笔者把所有社会视为“系统”,避免任何决定论,无论是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还是信仰决定论,主张从整体构成的要素、方式、功能多重角度来把握社会形态及其前景。二是实证。历史研究的根本性质是澄清事实,虽然也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建立、证明、反驳理论,但所有这些都要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所以所有前人的理论只能被当作思考的资源,而不可受其规定,不能强证据以就理论。如果发现理论与事实不合,只能修改理论。坚持实证的尺度,其实也是坚持把这项研究作为历史学性质的研究,这会使思考的方向永远不会脱离证据面,也不会轻易被声名显赫的学者裹挟而去。三是文明史观。迄今为止,研究社会结构和历史趋势的概念,大多沿着社会发展史的思考线索展开,或多或少,都把人类社会的演变看作是沿着同一轨道的现象。这样来思考,在承认人类社会演变存在普遍法则的意义上有可取性,但却非常容易把普遍法则夸大成为严整的形态规则性,从而忽视差异性。历史演变的最大差异性在于文明的差异。文明作为最大的社会共同体,会在演变中形成各自特有的文化精神,渗透到其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制度中,从而,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推演潜质和倾向。各文明在逐渐增多的接触中会有所融合,但也会长期保持各自文化精神和社会组织方式的特质,因而不可能走同样的社会形态演变道路。即使到了现代,文明的差异也难以尽皆消失,所以现代社会依然是多类型的。在这种视角下,明清中国与同时期的欧洲并未在同一条轨道上推进,其差别不能完全用先进和落后来区分,也不能完全用经济尺度来区分。除了将研究的视角从发展进化的单一视角增益成为复线的视角,文明史观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即在面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时,可以做出更合理的说明。这一点以后会再加讨论。
这样看,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方法论主要是在对已有方法进行批评性审视基础上做出“综合修正”的结果。至于这项研究的目标,最初时候是为梳理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后来的方法论探讨中,调整为现代性在中国发生的缘起问题。在晚近一段时间,笔者察觉到,无论如何定义“现代性”,要把“现代性”与欧洲经验彻底分开,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性在人类历史上的展开是有时间差的,而在欧洲的表现最为确切可辨,并且事实上影响了非欧洲世界的历史运动。因而,在保持对现代在中国发生缘起问题追问的同时,必须同时注意这样的基本问题:从社会结构与历史推演的趋势意义上说,明清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后者肯定与现代性有诸多关联,但未必所有情况都可以被纳入现代性发生的视角下来阐释。至此,研究的问题已经扩展到从基础概念层面开始重新认识明清社会和现代中国。从而,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就具有了更多方法论和研究视角的意义,不再是对一个特定问题的解答。
三、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要点
前文已经表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是一个在多年延续的探索过程中理路逐渐明显的论说。其基本目标是,就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结构、形态特征及其演变的由来与趋势做出判断。由于这是关于一个长达500多年历史时代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基本看法,带有审视框架(framework)和方法论(methodology)的性质,同时又要落实于多方面的实证考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具体观点,所以对该说做简单的概括其实总是难以周全地表达其含义,而且研究依然在继续,未来也必定会有些修正。[注]此说各项主张在2007年以来陆续以专题论文方式发表,其大部分已经收入《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尚未收入文集者及后续研究将汇集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续编》《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三编》在稍后数年内出版。但是,该项研究推进至今,触及的问题领域一直扩展,不断引发新的问题和思考,使提出者自己也感到难以驾驭。该说必须呈现给学术界,以获得评论,或者成为更多学者思考的问题,才可能真正深入下去。为此,这里还是尽量对该说做出概括。
用最简短的方式表达,该说主张: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陷入停滞,而是发生了多方面的发展,并与该时代的全球化运动相关联。依据其结构性特征,明清中国应被称为帝制农商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农商经济共同构成社会基础且与帝制国家体制形成共生格局。其演进的基本趋势是,在帝制农商社会基本框架下继续发展,有更大规模市场经济化的前景,但没有西欧同时发生的那种资本主义、议会民主政治的前景。该时代的中西方文明有交集,但演进路径不同。
稍微具体一些,在偏重于与先前学术界主流看法有所差异的意义上,该说包含下列认识:
1.明清中国社会没有停滞,有多方面发展,尤其表现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方面。这与各种中国历史的停滞论划清了界限,同时注意到,与在性质上与“现代性”契合的“发展”并非均衡地展现在所有领域。
2.该时期又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基本完成的历史时期,这是与“现代性”之发生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发展。“现代性”具有人类历史普遍性,后者则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变的特殊表现,二者的关系还有待论证,但这肯定构成明清中国历史发展主题和方式独特性的基础之一。
3.明清时代中国的国家体制是帝制而不是封建制。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名称问题,而是一个实质性问题。帝制是中央集权的,不是层级分权的,由皇权、郡县体制、官僚体制作为骨干支撑。帝制与大规模市场可以共生,封建则趋于自给自足或者地方市场——大规模市场会瓦解封建体制。封建制作为历史孑遗在明清时代依然存在,但并非国家主导体制。明清帝制常态运行且趋于强化,并非处于自我否定、瓦解过程中,也并没有明确地向任何其他体制“转型”的动向。明清嬗替,皇权趋于强化,贵族政治精神也有复兴倾向,但仍未脱离帝制总体框架。从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从而自我瓦解的逻辑来看明清社会是不得要领的,中国帝制体制的推演轨迹需要用另外的逻辑来说明。
4.明清社会不是完全封闭、“闭关锁国”的,也不是完全开放的,是有限开放的。有限开放是帝制体系的内在性质,并不瓦解帝制,且可以提供对帝制的支撑。基于这种有限开放性,中国在早期经济全球化历史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贡献于早期现代世界经济转型,也受到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影响。
5.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与帝制国家体制形成一种共生态。该时期形成了白银货币体制、货币主导的国家财政体制,地域商帮兴起,商业资本繁盛,出现较多雇佣劳动关系。这些现象在抽象的性质意义上与现代社会具有很大契合性,意味着具有很大的商品经济发展前景,但其表现并没有构成对帝制体系的解构,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也没有显露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面特征。明清两王朝在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变迁中并非顶层设计主体,也不是一味阻碍者,而是调适适应者,是新水平商品经济与帝制国家体制共生并荣格局的参与者。商品经济的一般发展并不直接瓦解帝制体系。
6.明清中国没有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迹象。以往研究过分重视生产关系,夸大生产关系领域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或把GDP标志的经济总量当作尺度,不甚关注生产力。明清中国显然没有发生科技革命,而古代科技不足以推动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则不可能形成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这一角度看,明清中国不仅事实上没有,逻辑上也不可能先于欧洲发生工业资本主义。
7.明清思想学术仍以儒学为主流,没有文艺复兴,更无启蒙思潮。中国古典文化不曾断绝,故文艺复兴无从谈起,梁启超、胡适等人关于清代汉学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不成立。儒学有诸多优长,但不孕育现代社会。没有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文化毕竟还是沿着传统的基调推演。
8.明清国家政治、政治文化基本在传统轨道上运行。帝制体系继续发挥功能,皇权趋于强化。其间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突出体现在士大夫政治在明代出现高潮,而在清代基本消失,以及贵族政治在明代趋于沉寂,在清代趋于复兴。中外史学界都还没有实现对明清政治历史与经济历史推演之间关系的透彻说明。
9.明清社会结构变迁也与帝制体系互洽。明代社会自由度增强、庶民文化发达,清代社会层级化增强、庶民文化继续发展、社会控制强化。这些变化与帝制体制持续发展并行。明清宗教也由帝制国家统摄,多元并存。
所有这些要点皆表示,明清中国社会构成一种学术界以往熟知的各种理论、模式说都不曾具体阐释的形态。对这种社会形态的探索、论证,有助于认识现代中国起源的历史逻辑,也可能会推引出诸多历史研究方法方面的新认识。
四、几点回应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核心主张已经初步表达出来,但还有若干重要侧面有待专门论述,对于同仁提出一些追问,也需要回应。[注]学术界对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报道和一般介绍很多,深度评论则主要体现于高寿仙的论文中。参看高寿仙:《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这里就同仁提及而笔者先前注意不够的问题略做说明,深入考察需在后续研究中逐步展开。
(一)既然明清时代农业依然是社会经济的第一基础,农业人口依然是帝制国家统治的基本对象,“为何将这样的社会称为‘农商社会’”?既然商业是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早在帝制初期甚至帝制时代以前,商业已经在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比例,为何断言直到明清时期才进入“农商社会”而不是更早?此与葛金芳等先生所说宋代的“农商社会”如何区分?[注]高寿仙:《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高寿仙先生提出的这些追问显示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中迄今比较模糊的一个侧面。在系统量化明清时代商业经济的数据基础上,才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而目前为止,这样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凸显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假说性质,也指出了未来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在充分量化之前,把明清时代称为农商社会的着眼点主要有3个。其一,“农商社会”是从结构特征角度上拟出的称名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农业和商业皆构成社会经济体系中的支撑性产业,其重要性皆超过其他产业,并形成普遍认可商业价值观念的社会。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商业占比很小并被普遍漠视的社会。综合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明清时代商业的研究可以判定,商业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仅次于农业的支撑性产业,其合理、合法性得到从政府到民间的普遍认可,市场、货币、商业都市的发展都达到空前水平,并促使国家制度、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动。其二,明清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全球化过程同步,并且深度卷入了当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流动,这意味着,明清时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与宏阔的全球经济格局、体制变迁密切关联,与现代社会的全球兴起关联,从而具有了与中国历史上以往时代的商品经济繁荣不同的属性和大背景。其三,帝制并不绝对排斥商业,而且会为商业提供大规模市场秩序条件、统一货币、大空间物流。但是,早期帝制对市场、商人管控过严,货币形态变动不居,劳役和实物赋税比例很大,人身依附关系普遍。商业的自由发展空间在宋代大为改观,北宋东京和南宋的临安都已经是非常繁荣的商业都市。但宋朝,尤其是南宋,管理的区域空间狭小,且多政权并立使得制度环境稳定性低,且屡有更改,而且南宋灭亡之后的商业发展情况尚未考察显明。明初商业黯淡,到明朝中叶以后才进入商业持续发展的不逆转过程,且覆盖了广大的地域空间。仅就商业发达的一般性质和表现而言,葛金芳先生所说的宋代“农商社会”与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是一致的,存在先后关联。[注]2018年5月昆明会议期间,笔者与葛金芳先生就此点交换意见,皆认为宋与明清的商业制度、商业思想之间的联系应该再做梳理。但“帝制农商社会”推演作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一段历史过程是独特的,其综合表现也远比前代复杂。
(二)明代的白银货币运行和货币财政体制发展是否意味着国家转型?[注]如高寿仙先生指出的,笔者与万明先生在关于明代历史的诸多方面见解高度吻合,但在前述问题上说法不一致。参看高寿仙:《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万明关于明代“国家转型”的论述请参看万明:《明代货币白银化的总体视野:一个研究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纶》,《文史哲》2015年第1期;万明:《中国的“白银时代”与国家转型》,《读书》2016年第4期;万明:《〈万历会计录〉与明代国家和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7-69页。刘志伟先生也认为明清时代发生了“国家转型”,参看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极其重要,但其实证的性质不及前一问题而阐释性过之,所以虽然同样需要将来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但基本看法却比较确定。明代发生了从实物为主的财政体制到货币为主的财政体制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意义主要在经济领域,其次也涉及国家政治,但经济层面的含义是确切的,政治层面的含义是不确切的。也就是说,财政体制这种变化的国家政治体制含义还要结合政治领域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情况综合考察。而笔者对于明清国家体制的多项考察都指向这个时代的国家政治,尤其是从基本体制上说,没有发生明显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转型”——万明和刘志伟先生所说的“国家转型”都指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赋役制度和财政制度都与国家形态(类型)相关,但如果要以赋役制度或财政制度为着眼点来判定国家在某个时期转变了类型,不能仅仅局限在赋役或财政领域,必须对国家类型做个直接的观察。因为大家都在把张居正改革的万历初期作为“国家转型”的节点,依照国家转型说的逻辑,其后的国家就具有更多近代或现代的属性。然而,后张居正时代的国家基本体制没有改变,把政策面的大事理一理,也不见明显的近现代性质的举措。然后明清易代,帝制国家体制进入一个高潮期。如果康雍乾是近现代“国家”,那后来的“挨打”也就未必会发生了。“国家”的“型”和性质判定,可以把经济状态、财政体制纳入考量,但无论如何必须要把政体属性、国家理念、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也纳入考量才行,因为“国家转型”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单纯经济问题。笔者也不认为“赋役国家”和“赋税国家”这两个概念可以用来有效地区分国家是否发生了近代意义的转型。因为,无论直接的劳役、实物赋税、货币赋税,本质上都是赋税。三种赋役形态比例的变化,体现社会成员对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程度的变化和货币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却并不直接体现国家的性质——虽然货币赋税比劳役税与现代社会更吻合一些。况且,在张居正改革之后,实物赋税并没有全然消失,直接的力役也有存在,国家对于社会普通成员的人身控制也存在。笔者会争取在将来与相关的几位学者就前述话题做一些深入的交流、研讨,以便把分歧的节点梳理得更清楚一些。其实,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迄今都还表达得比较笼统,共同关注都在于试图对明清时代的新质社会情状进行解读,研讨之后,大家的表述可能都会更明确一些。
(三)帝制农商社会说主张明清时代对外方针皆为“有限开放”而非“闭关锁国”,但在讲到与清朝同期的江户时代日本时称其为“闭关锁国”时代,当时中国和日本皆有一定量的对外贸易,何以说法不同?[注]高寿仙:《建构中国本位的历史发展体系——读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研究(初编)〉》,《史学月刊》,2018年第3期。论证江户时期日本不是笔者的专业,也不是笔者的目标,说其“闭关锁国”不是为了论证这样一个观点,是沿用了学术界习惯的看法。这样讲的学者,一般是指德川幕府在1633到1639年间5次发布涉外禁令,其中包括除经特许,不可有其他船只驶往外国、日本人不经特许不可前往外国、不接受旅居海外的日本人回国、除中国和荷兰商人可在长崎通商外,禁止欧洲人前往日本。1640年,葡萄牙人来日本要求贸易,船只被焚毁,61人被杀。虽然已有学者指出,17世纪的日本文献中并没有使用“锁国”字样称呼这些禁令,该词汇是在1801年日人志筑忠雄翻译德国人恩格尔贝特·肯普弗(Engtlbtert Küempfer)所著《日本志》时才使用的,但这些政策具有主动切断日本与外界主要关系渠道的意味,所以前述禁令迄今依然被许多学者统称为“锁国令”“锁国体制”这样的概念也依然使用。[注]参看马依弘:《西力东渐与日本的锁国》,《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冯玮:《重新认识“锁国”政策对日本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世界历史》1992年第5期;朱海燕:《“漂流民”与德川时代日本的“世界”认知》,《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王来特:《清初中日交涉模式的形成和贸易主动权的消失》,《日本研究》2013年第3期;李若愚:《试论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西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同一时期的中国清朝,只在台湾统一之前有迁海之令,一旦统一,立即展界、开海,并没有同样明确持久实施的切断中外往来的锁国政令,故有前面表述。其实,如高寿仙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江户日本还是清代中国,都没有彻底停止一切对外贸易,也都没有处于与外部世界的完全隔离状态。
(四)在笔者与同仁的交流中,多次遇到的追问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帝制”与“帝国”这两个概念要如何区分清楚?帝制是国家体制概念,核心含义是由皇帝、郡县、官僚为鼎足而立的中心架构组成的国家权力体制。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体制从秦代开始,到清末结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中华文明核心区无论是大一统王朝还是局域王朝,无论强大政权还是孱弱政权,都采取这种国家体制。帝国则是从地域和认同角度定义的一种权力结构,指政权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强力征服缺乏文化或族属认同的他者的体系,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等等。帝国作为一种性质,有成色深浅程度差异。如南宋肯定是帝制的,但没有什么帝国色彩,而元朝和清朝则有比较浓的帝国色彩。所以帝制不等于帝国。这里可能应该提到美国的“新清史”。这种研究强调清朝的满洲特色和帝国性质,这些在先前的研究中常被忽略,所以新清史有值得注意的学术见解。但是新清史过分夸大了清朝的满洲特色和帝国性质,没有看到清代中国的内地与边疆聚合是中华文明长期聚合运动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单纯依靠政治力的组合,与同一时代的殖民帝国有很大不同。“新清史”还采用一个笔者不赞成的切入方式,就是把清朝的统治能力和统治时间长久作为清朝“成功”的依据,又在此基点上来讨论清朝为什么“成功”的原因。这种取径不仅过分局限于政治,而且局限于统治者立场,现代历史研究者带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统治代入意识是令人费解的。
帝制农商社会说一直在追问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因由,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沿着启蒙理性路径的思考。所以,笔者虽然也关注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潮,但肯定没有时髦到自称后现代主义者的程度。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局限,笔者自己也不知道,但将继续沿着自己所理解的路径思考。此外,如果卡尔·波普尔是对的,一种思想或论说公布之后,就成为“客观知识”,论说者并不拥有也不能控制其展开的结果,那么,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逻辑展开,可能会有助于重新认识更宽领域的问题,而不会为笔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兴趣所局限。坚执此说绝不是笔者的目标,沿着此说提示的思考方向找寻新的景致,却令笔者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