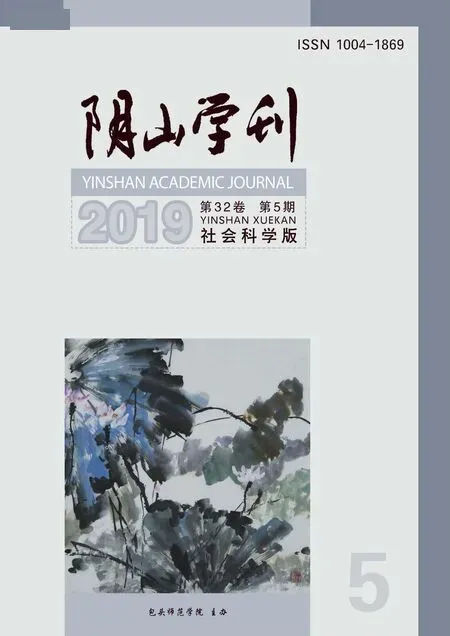个体意识与创作自觉
——论李贽“童心说”与本居宣长“物哀说” *
黄 伟 芯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
吴调公在一篇文章中说到,“人民在精神世界中所受的压迫愈甚,潜在心灵的飘风急雨的萌芽也愈甚。处于长期封建统治社会中,这种潜在心灵的狂飙主要表现为人的自觉以至文的自觉的呼唤声声,而提到哲学高度,则是人们对主体意识的尊重、追求和审美感受的自我涵茹。”[1]这一论断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李贽和本居宣长所处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的存在状况。他们都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儒家思想以“理学”的形态取得了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实际上是以极其不合理的方式对人性的过度压抑乃至扼杀。在中国,王阳明“心学”的出现,打破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将天理拉到人的内心,从而刺激了一批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李贽就是一个以“异端”自居的人,他反对所谓的“天理”,而高度重视人的生命本身,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等言论。在《焚书》中,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著名的“童心说”。“童心说”实际上是在反对普遍的道学家的虚伪的背景下,肯定人之“真”。而人之“真”是建立在人的独立自主的前提之下,不受外界“闻见”“道理”的束缚,而保持其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能力。“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童心说》)文学表现生命个体真正的情感和思考才会成为好的文章。而在日本,“随着德川幕府的成立,儒学受到了武家政权的庇护,开始脱离佛教,得以独立的传播和研究,此时朱子学占压倒性的胜利。”[2]与盛行程朱理学的中国一样,日本同样面临着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和破坏。日本对儒学的突围是以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为代表的古学派,以复古的方式重新阐释儒学,使受压抑的人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在文学领域,伊藤仁斋论述了人情说,“其观点一是文学要述一般人之情;二是文学非劝善惩恶之工具,它表现共通人情,使人完善……仁斋的人情说很快风靡一时……”[3]41如果说在中国是以“人性”对抗儒家不合理的伦理秩序的话,那么在日本就是“人情”。伊藤仁斋的“人情说”在近世日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契冲、近松、松尾芭蕉、西鹤和荻生徂徕等人的文论思想都受到“人情说”的影响,并在这一方面都有所论述。受到此影响,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说”亦强调文学要表现人之真情。“诗既本为吟咏性情之艺,则当有女子童儿虚无朦胧之语。”[4]775同样强调文学表现之人的真情应该是不受或少受外在因素所规训的女子或儿童的“虚无朦胧之语”。可以发现,无论是李贽的“童心说”还是本居宣长的“物哀说”都表现出了一个共象,他们高度重视创作主体的独立自由,即他们都是在确立个体意识的前提下强调文学应表现个体生命最“初”、最“真”之情。进而言之,个体意识的确立进一步增强了主体意识的崛起,使文学的个性特征也随之而鲜明,这就是文学创作自觉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
从根本上而言,文学亦是人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把人作为全部哲学基础提出来的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他的这一做法标志着传统哲学的知识本体论、神学本体论开始向现代哲学的人学本体论转移。”[5]可以说,“人本思想”是封建社会后期以至近现代西方人们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之一,也是促成西方哲学和文学实现变革与转型的一个重要内驱力,“主体性”的张扬在整个西方发展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日两国虽然没有关于“主体性”的严整论述,但是他们对生命个体的关注亦彰显出以“个体意识”为重要内容的哲学及文论显示出“主体意识”的萌芽。个体意识的确立和肯定又促进文学的自觉,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与西方世界的同步和接轨。
个人独立地位的确立是个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学自觉的前提,它表明创作主体将关注对象置于创作主体自身。个人独立地位的确立首先表现在个人对封建秩序下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对人的发现和个体意识的崛起是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诉求,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在强大的金钱驱力下开始慢慢瓦解。封建社会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加之商业的迅速繁荣,越来越多的人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中脱离出来,一部分人成为逐渐占据经济优势的新兴商人,一部分人加入了日益壮大的市民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取得独立,便对严格控制人身自由的封建伦理纲常不满,提出了取得个人独立地位的诉求。这一诉求通过对人性中本然天性的“私”和“欲”的追求实现,所以,个体意识还表现在对个人天性和价值的追求。商业的繁荣刺激了他们对“财”“货”的追求,而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世界,日益壮大的市民阶级,对人性中“私”和“欲”有了更大胆和执着的追求。于是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合理要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潮流下逐渐瓦解。李贽26岁中举,30岁而为官,但“此后他从没去考过进士”,做官之后“便陷入南来北往为父亲、祖父丁忧守制乃至安葬曾祖父、婚嫁弟妹的家族事务中”,因此他“长期辗转于下层官员的贫贱位置上”[6]因为这样的经历,李贽与市民阶级、商人阶级有了更多的、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逐渐接受了心学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点,形成自己富有个性和战斗性的思想。本居宣长出身于商人家庭,家运衰落后成为一个商人家庭的养子,“23岁时到京都学医和儒学,师从贺茂真渊,修和歌并从事古道研究。他排斥儒道佛,倡导复归古道……”[7]实际上,本居宣长是以复古的角度批判现世的儒学,即程朱理学的不合理之处,重新肯定人性之自由。李贽的“童心说”和本居宣长的“物哀说”都具有这股发现、肯定和追求人性之“欲”的倾向,甚至李贽就是这股潮流的先驱。以肯定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欲望追求为背景,他们的文论中提出文学要摆脱文学“劝善惩恶”的工具属性,反对虚伪的道德说教,表现人性、人情之真,而这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重要表现。
个人意识与文学自觉的关系是:文学应表现“人之真”,其表现方式应该是“有感而发”,这是文学对创作主体提出来的本质要求。“童心说”和“物哀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自觉也首先表现在“人之真”。李贽在《童心说》一篇中开宗明义地说到,“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童心就是真心,就是未受外界“污染”的最初之心。童心与人与文的关系在于:失却童心就不是真人,不是真人就写不出天下之至文。李贽的论述是“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本居宣长也有相似的论断,在程朱理学的“天理”盛行的日本,个体进行道德选择和认同上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同样被抹煞,那么文学要获得自觉就必须首先要使人获得“突围”。所以本居宣长也是在强调人性之真的前提下提出“唯于本来之面目,有朦胧之情味”,认为“诗本为吟咏性情之艺,则当有女子童儿朦胧之语。”“女子童儿”之语与“童心”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未受或少受外在伦理纲常、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人之状态,这种状态的核心就在于“真”,它是生命的真实状态,也是情感产生和抒发的真实 。李贽和本居宣长主要从三个方面肯定“人之真”,一个是“反假”;二是肯定生命之真,三是肯定情感之真。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促使新兴市民阶级的壮大,他们提出异乎封建伦理纲常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诉求,于是在伦理规范与个人感性欲望和自由之间就形成严重的矛盾冲突。这就造成了一批既无法完全遵守伦理规范,也无法完全承认个人之欲望与自由的人的出现,这就使得社会中充满了满嘴仁义道德的虚伪之人。李贽和本居宣长都十分反对这些虚假,李贽认为“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也,非童心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李贽所说的“闻见”“道理”实际上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如果被这些外在的“闻见道理”所左右,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李贽所说的“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三教归儒说》)之人。本居宣长也说“世之诗忘其根本之意,万事不离生硬说教,连不可粉饰之性情亦痛加涂饰,看似庄重严整,却非人情之本来面目,皆为表面装模作样之情,纵然如何精妙端丽,亦何换焉?”[4]775在反对虚假的同时,他们认为“人之真”应是生命之真,而生命之真并不像程朱理学那般否认人的正常欲望与压抑人性的自由。所以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和“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等看法。本居宣长对人性中的色欲更是持肯定态度,“所谓深刻之物哀,其中必多包含淫事。此为天理,源于好色尤与情深相关。”[7]正是在肯定人性之真的基础上李贽和本居宣长都进一步提出文学要表现人的情感之真。李贽提出“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本居宣长说到,“不论大人先生如何圣贤,探求其内心深处则与女子童心无纤毫异。所谓诗歌,乃愁思郁结咏出以驱愁遣闷者也”。情感之真就是人的喜怒哀乐,于本质上而言,圣贤与儿童无异,都具“人之真”的状态,都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诗歌就是这些情感的真实流露。
“有感”是从发生论上而言,情感产生于创作主体感于物或感于事。在中国传统中就有“感物”“物感”和“感兴”等术语描述这一情感的产生方式;在日本则有“哀”与“物哀”。文学是人学,那么情感属性就应该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且这里所说的情感应是创作主体最真实的情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到,“……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便强调了“发愤而作”的创作因由与方式。但是在李贽和本居宣长所处的时代,这一创作方式遭到了严重的中断,人们专注于对“四书五经”的学习和阐述,所写之文多是“八股文”或当时的台阁体。这类的文章“言虽工,于我何与!”李贽强调好文章需要心有郁结,进而触景生情,直抒胸臆,“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此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同样地,本居宣长强调“彼虚幻无实、物动心摇、依依堪怀之事咏而为和歌。”两者都强调情感的缘起应该是“触景生情,触目兴叹”,或者“物动”而“心摇”。从这一点而言,他们回到了传统重视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的发挥,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具有新的时代意义,不仅顺应了人的重新发现和解放的潮流,更是推进了文学的进一步自觉。
三
“如果说‘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意在揭示人类文学的纵向联系,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则要揭示人类文学在精神上的横向的相通性和差异性”[8]。就“相通性”而言,李贽的“童心说”和本居宣长的“物哀说”都是在肯定个体意识的背景下使文学回归到表现人、抒发人之真情的道路。与文艺复兴背景下西方的解放思潮遥相呼应,显现了中日两国所在的东方世界也加入了这场人学革命和文学革命。就“差异性”而言,“童心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自觉是反对儒家伦理对人的束缚下,突出强调人的个体意识,而对于个人的重视则使文学进一步与世俗化、通俗化结合起来,由此驱使中国传统文学向近现代变革;“物哀说”是在反对中国儒家伦理和文化的前提下,立足于传统和民族本位,从“和歌”跟“物语”中归纳总结出日本民族特有的“物哀”,从而使日本文学获得不再依附于中国文学的独立地位。所以,它们各自展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追求。
文学自觉并不仅仅表现为对人的关注,还在显示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特质上,“童心说”和“物哀说”不同的“物”“我”关系是其中一方面,“童心说”强调“心”对外在“事”和“物”的主导地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物哀说”强调物我之间的浑然交融,“物”不仅仅是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投射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情感意志的“主体”,物我关系实际上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前者在个体意识前所未有地张扬的同时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求新求变的特质,后者体现具有强烈情感属性的“物哀”文化。中国“感物”“物感”“感兴”是中国传统文论和美学中的重要范畴,“感”字是指人与外物之间相互勾连的一种关系,而在处理人与外物的关系中,中国往往强调“感时兴叹”“缘事而发”,视人为主体,以心感物;视物为客体,心离不开物,受制于物。但是,在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受到程朱理学的畸形压抑下,它造成强有力的反弹,那就是对人性和人欲的极力张扬。李贽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人,他的学说就是反弹的结果。他在承认“私”和“欲”的人类本然天性的基础上,强调心性的解放,“寻求个人心性的快乐自在”,所以实际上李贽将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拔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童心说》中指出童心失却的原因的时候说到,“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也就是说,对于外在之物,唯其“心”主于其内,才不至于使童心失却,被外在事物或事理占据内心的主导地位,那么就会失却童心,要保持“童心”就要摆脱一切外在“闻见道理”的遮蔽和干扰。对人的高度关注,加之关注的视点转向市民阶级,显示中国传统文学中新的文化特质,即创作主体精神的高扬,个性和人欲的表露,世俗化、趣味化的倾向。本居宣长是复古学的代表,“物哀说”的提出是本居宣长在研究和歌发展史中所总结出来的一个审美范畴,也是一个以情感为中心的审美标准。“物哀说”贯穿着以自然为本体的“神道”精神,和上代朴素炽烈情感为中心的基调是一致的。本居宣长说到“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还是耳之所闻,还是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感知‘事之心’、感知‘物之心’,也就是‘知物哀’。”在日本古代文论与美学文献中,人们所感知的“物”都是具有主观性的。“物,作为一个语素的时候,往往具有表示某种抽象的、难以把握的存在,因而以物作字头的词,也常常带有负面的、消极的意义。如物忧(慵懒、倦怠)、物悲(难过、悲伤)……”在对比“物哀说”中物我关系时,王向远说到,“日本是以心‘感心’,心可以离物而独立……其中‘物哀’之‘物’被置换为‘物之心’,从而将‘物’加以‘心’化,称之为‘物心’”[9]可以说,“物哀”是日本人过于充沛的情感流溢的结果,其间充满敏感细腻、多愁善感等特质,显示出“以悲为美”的总体特征。更有学者提出,“这种传统的回归,还表明了日本远古‘女性文化’的复辟。宣长重拾平安时代女流文学‘大和心’,从《源氏物语》的梳理中得出物哀的结论以及反复强调‘女子’等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历史、风土形成的日本文化的核心是‘女性文化’”[10],在文化追求上,“童心说”更倾向于世俗化和通俗化的发展方向,它代表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诉求;“物哀说”是对日本传统文化精神和内涵的总结和概括以及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弘扬。“童心说”所反映出来的文学自觉是明代中后期文学追求人性解放和个性张扬,它最终倾向于文学的世俗化和通俗化。由于对个人的高度肯定以及对“真”的执着追求,所以李贽的作品多是“直率辛辣,锋芒毕露”,同时他的一些作品“以坦直率真的笔调对自我作了写照,显示自己不向世俗屈服的个性。”受到李贽影响的公安派,他们以“性灵说”为口号,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主张。但是从李贽起,由于过于强调创作主体个性的张扬,他们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即他们的有些作品往往过于率真浅俗,甚至“戏谑嘲笑,间杂俚语”(《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李贽的理论主张还影响诸如汤显祖“至情论”的提出和冯梦龙在三言二拍里“情教”的体现,乃至世情小说、艳情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大兴亦与李贽有一定的关联。人的解放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作为一个代表和先驱,李贽及其提出的“童心说”还是在这场文学变革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显示中国传统文学向近现代变革的趋势。“物哀论”既是对日本文学民族特色的概括与总结,也是日本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试图摆脱对中国文学的依附与依赖,确证其独特性、寻求其独立性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日本文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转折。日本文学长期以来都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第一部歌集《万叶集》就是综合使用音假名和取汉字之意的训假名编纂而成,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之深。然而就诗歌本身而言,它是日本自身的文化——和歌,“物哀说”的提出与本居宣长对和歌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本居宣长说和歌的本质是“和柔、情趣自然”,情感的产生方式与抒发方式是“触物感怀,随其心自然表露”,这都与“物哀说”所强调的是一致的。
个人意识的确立与肯定,使文学更注重人本身,李贽和本居宣长强调文学应表现人的真实情感,文学应“有感而发”,这实际上也是时代发展的呼唤。文艺复兴于16世纪在欧洲大陆盛行,由此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这是一场文的解放,也是一场人的解放。远在东方大陆的中国和日本在严密的儒家思想体系和封建秩序的控制下,其自身孕育的思想解放潮流并没能冲破自身的束缚,李贽只能以“异端”自居,最终被统治者杀害在狱中。但是无法否认,在大的时代潮流之下,中日两国也表现出自身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在西方,“文艺复兴”这一思潮成为了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一个号角和先驱。在中日两国,无论是“童心说”还是“物哀说”,更多地仍囿于文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特征和文学追求。
——以黄麻士绅纠葛为中心的讨论
——《李贽学谱(附焦竑学谱)》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