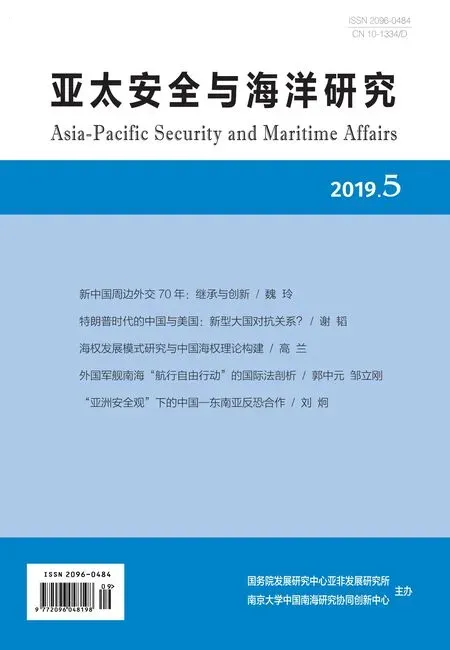我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的国际管辖权问题研究
吴盈盈 孔庆江
[内容提要]国家包括地区间的海洋争端,主要有领土主权、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划分、矿产及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地物的地理特征属性等多种之争。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间的海洋争端,也大致如此。解决这些海洋争端,国际司法或仲裁无疑是两条重要途径,这其中首先需厘清管辖权问题,即法院或仲裁庭是否有权审理相关争端。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引入“强制管辖”条款,管辖权问题更为关键,包括强制管辖的适用范围、主体、例外等。通过分析国际司法的同意原则和自裁原则,探讨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海洋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权的基础问题,特别是这些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的可能性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我国的周边海域有黄海、东海和南海等。在这广阔的海域上,我国与周边国家还有一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议,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之间存在着岛屿领土和海洋划界等争端;在东海,与日本存在着钓鱼岛主权等方面的争端;在黄海,与韩国存在着苏岩礁领土及渔业纠纷等争端。
解决争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通过外交途径的谈判、斡旋,有第三方介入的调解、仲裁,有非和平方式的武力等。我国向来主张和平解决争端,坚持平等、公平等原则。鉴于南海问题中,菲律宾将部分海洋争端提起国际仲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对我国产生的潜在影响,有必要针对强制国际仲裁或司法进行研究。能够将海洋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第一步则是管辖权问题,即该仲裁庭或法庭是否有权对此争端进行审理、裁决。若没有,则该争端不能被继续审理。若有,则仲裁庭或法庭将对该争端的实质问题进行审理。因此,有关国际仲裁或司法的管辖权至关重要,它涉及管辖的门槛问题。
本文着重对我国周边海域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程序的管辖权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其中侧重针对东海问题中的海洋争端类型,通过法律分析和案例分析法,阐述可能会被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的途径和国际法依据。主要从三方面展开:首先简单梳理争端的类型和种类,比如领土主权之争、海洋划界之争、油气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争、渔船碰撞之争、地理性质特征之争等。其次,通过案例及法律分析来阐释当前国际法中将海洋争端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的规定,进而阐明管辖权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各种不同种类的争端被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的可能性和前提条件等情况,提出简要的结论和建议,从而为解决我国沿海周边海洋争端,尤其是针对东海问题中中国与日本的海洋争端提供法律依据和论证,通过分析国际仲裁或司法的管辖权问题,争取较好预见日后不同类型的海洋争端被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的可能性,进而为我国的应对措施提供法律意见和参考。
一、周边海域争端的性质、种类
分析我国与周边海域国家和地区已经存在或者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争端,以及争端的类型,很有必要。下面侧重围绕东海海域争端,包括主权领土之争、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划分之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争、渔业领域的开发利用冲突之争、某地物的地理特征属性之争等等进行探讨分析。这些争端类别不一,导致其在法律上的分析也会依据争端的本质、性质、类别而有所不一。 而当事国双方往往对于争端的定性也存在分歧。比如争议的性质可能会被包装而呈现不同的样态。此外,需要解释的是,这些争端之间错综复杂,比如地物性质界定、资源开发利用等都与主权之争交错着。
(一)领土主权之争
领土主权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各国都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海洋争端中也牵涉到领土主权之争,且是最棘手、最难解决的争端之一,如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由来已久。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主权发生一系列争执,两国均称对此岛拥有主权。中国政府基于地理、历史、使用角度、国际条约等依据,主张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基于历史地理、国际条约、有效管辖等因素,也对钓鱼岛主张主权。1972年中国政府在与日本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提议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解决,日本政府予以接受。1979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于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谋求“共赢”的考虑,在钓鱼岛问题上主动向日本倡议“由双方商量,搞共同开发,不涉及领土主权问题”。中国就钓鱼岛问题主张 “搁置主权,共同开发”原则。(1)参见《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67页。搁置岛屿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海洋资源,是中国解决同周边邻国海洋争端的一贯主张。只是后来日本政府出尔反尔,对搁置争议事宜予以否认。
(二)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划界之争
在东海大陆架的划界中,中国坚持自然延伸原则和公平划界原则。中国坚持大陆架是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支持大陆架可以超过200海里的观点,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关于“大陆架外部边缘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350海里”的规定。因此,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 在此基础上,中方根据《联合国海洋法条约》第76条和77条,主张大陆架延伸理论,坚持按中琉海沟(冲绳海沟)来为中日两国专属经济区分界。《公约》规定2500米深度是切断大陆架的标准,而中琉海沟深度达2940米。而日本坚持“中间线”原则。日本基于《公约》规定,由领土向外延伸200海里之内,属于所有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主张两国在划定距离不足4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分界线时,要以双方等距离的中心线进行划分。在“中间线”划分下,钓鱼岛在中间线以东。
(三)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争
1969年,美国海洋学家埃默里等人所著的《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一文发表,其指出东海的石油蕴藏量极其丰富,即在东海的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公约规定,本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其中,自然资源包括海床和底土的矿物和其他非生物资源。因此,钓鱼岛的实际价值更在于以钓鱼岛为中心,直径为400海里的辽阔海域以及此海域内的海洋资源。
日本主张“吸管效应”,即认为中国在东海的油气开发,把日本的资源“吸”走了。中方的“春晓”、“天外天”、“平湖”和“断桥”四个油气田的开采位置,均在日方所强调的“日中经济海域分界中间线”的中方一侧,最近的距“中间线”也有五海里。但因为海底油气资源连在一起,并存在流动性,所以日方担心中方在距“中间线”如此之近的距离进行开采,会将中间线日方一侧的资源“吸”过来。我国认为,日本的“吸管效应”是基于“中间线”主张,而我国不同意“中间线”划分。其次,东海大陆架是西高东低,油作为液体,即使流动,也是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那边流。因此,两国有关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争端,此争端也是基于两国有关主权、海洋划界上的分歧而产生。
(四)渔业资源之争
东海海域曾多次发生中日撞船、船长被逮捕等事件。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国渔船在钓鱼岛海域先后与两艘日本巡逻船相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随后奉命约见日本驻华大使,要求日方停止非法拦截行动。当晚,日本海上保安厅决定以涉嫌妨碍公务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同时对该船展开调查。2003年,中海油、中石化与美国两家公司签订东海西湖合同。日方频繁出动舰船和飞机到中方作业现场进行监视、侦察和骚扰。此外,在黄海领域,也时常发生此类争端。2011年韩国海岸警卫队员登上黄海海域的中国渔船检查,中国渔船船长刺死一名韩国海警,后被韩国法院判处30年徒刑。中国强烈反对韩国单方面适用“专属经济区法”对中国渔民作出判决。有关渔业资源之争,也是基于有关主权、海洋划界上的分歧而来。
(五)地理特征、性质之争
法律上有关一个地物的定性,直接影响其享有的法律地位。比如,在法律上,岛屿是指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可以维持人类居住及其本身的经济生活。而岩礁(rock)是指四面环水并在高潮时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陆地区域,但无法维持人类居住及其本身的经济生活。这两者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完全不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规定:“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rock),不应享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在南海案件中,在2016年公布的“南海仲裁案”仲裁结果中,仲裁法庭认定“太平岛”属于“岩礁”而不是“岛屿”。而太平岛在南沙群岛中是最大的天然岛屿。“太平岛”被定义为“岩礁”意味着南沙群岛所有的“岛”最多也只能是岩礁。而岩礁没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同样,有关钓鱼岛是否是“不能维持人居住或者其本身的经济生活”的岩礁,双方也存在争议。中国与日本之间有关“冲之鸟礁是属于岛屿还是岩礁”存在着争议。这些有关地理特征、性质之争,都是源自两国有关主权、海洋划界上的分歧而来。(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2012年9月25日;Schoenbaum Thomas J., Peace in Northeast Asia: Resolving Japan’s Territorial and Maritim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8。
二、提交国际仲裁的管辖权问题
当前的国际仲裁有常设仲裁庭、国际海洋法法庭、特别仲裁庭等。将海洋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第一步就是管辖权问题,即该仲裁庭是否有权对此争端进行审理、裁决。若没有,则该争端不能被继续审理。若有,则仲裁庭将对该争端的实质问题进行审理。管辖权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在仲裁及司法实践中却极为复杂。下面就常设仲裁庭、国际海洋法法庭等的管辖权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探讨。
(一)常设仲裁庭(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1899年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 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分别制定了1899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设立了常设仲裁庭。该国际常设仲裁庭的管辖权并不是强制性的,需要案件当事方的共同同意将争端提交该国际仲裁庭。(3)The Statute of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具体而言,作为1899年和1907年公约的成员国,并不代表它们有义务将争端提交仲裁。(4)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istory of 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http://www.icj-cij.org/en/history [2019-06-10].中国在1904年和1910年分别加入这两个公约(1899年公约和1907年公约),日本则分别于1900年和1912年加入。国际常设仲裁庭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它接受国家间的争端解决、国家间争端调解、其他国家间争端解决、国家—投资者仲裁以及其他仲裁等。比如,厄瓜多尔根据 2012年《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和保护公约》,对南太平洋领域渔业管理组织委员会的有关措施不满,提起审查程序,提交到该国际仲裁庭。(5)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Review Panel Established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 in the South Pacific Ocean,” https://pca-cpa.org/en/cases/156/[2019-06-10].该组织主要为当事方提供仲裁、调解等争端解决的各种服务,包括提供场所、程序、登记服务,以及选择仲裁员或调解员、调查事实等服务。(6)The website of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pca-cpa.org/en/home/[2019-06-10].
因此,常设仲裁庭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方的同意。通常情况下,往往是在争端发生后,当事方协商后一致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或者,在协定、公约中等有规定将争端提交该国际仲裁庭。经审查,如中国、日本参加的有关海洋的协议、公约中,我国事前给予同意的较少,主要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7)中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强制管辖的主体(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庭、仲裁庭等)没有进行选择,因此按照该公约规定,推定中国选择仲裁。
(二)国际海洋法法庭(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强制解决争端的谈判历史
二战后,联合国分别于1956年、1960年、1973年召开了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一次会议达成了四个公约,第二次会议没有任何成果,第三次会议经过漫长的长达九年的谈判,在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在1994年,即在第60个国家签署之后,开始生效。关于争端解决机制,在1958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参会国就已讨论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比如,德国支持争端解决机制,尤其是针对大陆架定义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争端。印度等另外一些国家,则反对扩大国际法院的任意管辖权。
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在冷战期间举行的,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部分其他国家,基于国家主权概念,主张充分尊重一国选择是否接受国际义务、国际强制解决争端体系的意志。尽管如此,与会国提出必须将争端解决议题从其他讨论议题中单列出来,进行讨论。对于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应包括哪些具体内容,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争议点在于争端应该提交给哪个法院或法庭,以及适用强制解决的争端范围,因为有些国家不愿接受法庭就其主权问题作出的裁决。一些国家如瑞士和日本,倾向于选择国际法院,另一些国家如法国和英国,则更愿意选择仲裁庭。第三类国家群体包含苏联和东欧国家,它们倾向于设立特设仲裁庭,要求在渔业、污染或科研案件中适用特别程序规则。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则提议成立单一仲裁庭,而另一些国家则更愿选择一个还能受理国际组织、个人案件的仲裁庭。
为了避免国家在其认为高度敏感的问题上做出过多保留,1975年各国达成了一份敏感问题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争端:(1)有关沿海国根据其在《公约》下的监管管辖权和执行管辖权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争端,滥用权力者除外;(2)有关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及历史性权利的争端;(3)有关军事活动的争端;(4)涉及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行使其职权的争端。这四类在1982年的《公约》中以不同形式呈现。(8)有关谈判的历史,参见: Geneviève Bastid Burdeau, “Compulsory Dispute Settlement Methods under the UNCLOS:Scope and Limits under the Scrutiny of the Jurisprudence” , China Ocean Law Review, 2017, pp. 11-21。
2.强制管辖的前提条件
《公约》第15部分有关争端解决,是在各国妥协中达成的。具体而言,第15部分第2节是关于强制解决争端,而第1节规定了争端解决的其他方式,比如争端各方协议约定的解决方法、按照《公约》附件五第1节规定的调解、交换意见等。其中,有些被视为依据第15部分第2节采取司法和仲裁方式解决争端的“先决条件”。
(1)选择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其他解决方法的权利(替代性的争端解决)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1条和282条的规定,有关该《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各方,可以通过协议约定采用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如果争议双方有双边协定或参与的多边协定,这些协定中有规定导致有拘束力判决的争端解决程序,那么,可以替代《公约》第15部分第2节中有关强制争端解决的程序。在大部分案例中,法院或法庭将必须对缔约国援引的替代第15部分程序的协议条款作出解释,首先确定其是否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协议,其次甄别这个协议是否能提供一个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程序。
(2)交换意见的义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规定了交换意见的义务,即“1. 如果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就以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2. 如果解决这种争端的程序已经终止,而争端仍未得到解决,或如已达成解决办法,而情况要求就解决办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协商时,争端各方也应迅速着手交换意见。” 因此,交换意见的义务,也是诉诸强制争端解决的先决条件。然而,交换意见的义务范围并不清晰。有关交换意见的规定,“旨在确保一国在被提起强制程序时不会完全措手不及”。
交换意见的义务往往止于形式、程序,而非触及实质性问题。而且,也从未被认为可以阻碍仲裁庭的管辖权。因此,仲裁庭在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仲裁案的裁决中,认为这是一种程序性要求,即争端各方必须就解决争端的方法交换意见,但这不是一项就争端的实质问题进行谈判的义务。(9)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18 March 2015, p. 378.在中菲“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将这项义务解释为程序性义务,即如果有证据表明曾就争端的解决方法举行过会谈,那么就满足第279条的要求。仲裁庭认为:“第283条第1款不要求争端各方就争端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谈判。”(10)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29 October 2015, pp. 333,349.
在“北极日出”号案和“大吉正直”号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只要双方交换过一些官方文件就满足了交换意见的要求,即使没有重要证据表明双方之间的通信提及争端解决方法或程序方面的内容。(11)Arctic Sunrise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v. Russian Federation), Award on the Merits of 14 August 2015, para. 151. Duzgit Integrity Arbitration (Malta v. Sao Tome and Principe), Award, 5 September 2016, p. 199.另外,意见交换必须成功地明确争端各方对争议问题的立场,且各方必须同时“本着诚意进行协商,并且真正有意寻求各方均同意的解决争端的方法”(12)Barbados/Trinidad and Tobago, Award of 11 April 2006, pp. 201-205.。
关于双方事先是否交换了意见,在具体案件中,往往最后变成让申请方自行判断是否无法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第1节规定的争端解决方法,并决定是否提起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程序。在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仲裁案中,仲裁庭认为,毛里求斯和英国就争端事项进行了谈判,尽管受限于当时的有限条件使得会谈无法再继续。基于交换意见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毛里求斯认为双方已经没有可能就进一步协商的条件达成协议。接着,本案的仲裁庭根据马来西亚诉新加坡案件中的观点(13)Land Reclam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s of Johor (Malaysia v. Singapore),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 of 8 October 2003, ITLOS Reports 2003, pp.10 , 47.,进一步认为,当毛里求斯单方面决定双方已经没有可能就进一步协商的条件达成协议时,毛里求斯没有义务继续交换意见,因此毛里求斯有权选择通过仲裁强制解决争端。仲裁庭最终裁定,毛里求斯已满足第283条规定的就争端解决交换意见的要求。(14)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18 March 2015, pp. 385-386.
3.强制管辖的主体
根据第287条,一国有自由发布声明,表明其选择的争端解决方法: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或仲裁庭。如果争端各方选择的解决方法一致,则此方法优先适用。如不一致,除非争端各方决定采用约定的其他方法,否则应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仲裁。另外,根据《公约》第287条第3款规定:“缔约国如为有效声明所未包括的争端的一方,应视为已接受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 换言之,如果一缔约国没有作出第287条的声明,则推定为接受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中国在1982年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公约得到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在2006年做出了有关第298条的声明。但中国没有作出第287条的声明。因此,默认强制解决争端的程序为附件七所规定的仲裁。
不同管辖主体的管辖范围有所不一。其中,国际海洋法法庭还有特殊管辖权,即第292条规定的该项权限涉及船舶和船员的立即释放,具体规定:“1. 如果缔约国当局扣留了一艘悬挂另一缔约国旗帜的船只,而且据指控,扣留国在合理的保证书或其他财政担保经提供后仍然没有遵从本公约的规定,将该船只或其船员迅速释放,释放问题可向争端各方协议的任何法院或法庭提出,如从扣留时起十日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则除争端各方另有协议外,可向扣留国根据第287条接受的法院或法庭,或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
因此,除船舶扣留时起十日内各方另有协议外,这类争端可提交扣留国根据第287条接受的法院或法庭,或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通常情况下,此类案件在实践中大多提交给了国际海洋法法庭,而非其他法院或法庭,海洋法法庭也由此逐步制定了针对这类案件的重要审判规程。如果涉及中国的船舶与他国发生争议被扣押或中国扣押别国船舶,即涉及船舶的立即释放,则此类争端可提交中国根据第287条接受的仲裁庭,或者扣押国(如日本)根据第287条接受的法院或仲裁庭。
4.强制管辖的范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是有关管辖权范围。首先,第286条的一般管辖权条款规定:“任何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即有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和适用,属于强制管辖范围。
其次,第288条第2款的规定,《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可扩展适用于其他与《公约》目的相关的公约。换言之,与海洋法目的相关的其他公约或协定若规定了将争端提交《公约》的争端解决程序,则有关这些公约或协定的适用或解释都属于强制管辖的范围。而与海洋法“目的相关”在范围上可以涵盖很多其他公约,例如,《跨界鱼类种群协定》就提及了《公约》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因此,有关《跨界鱼类种群协定》的解释与适用的争端,也适用此强制管辖。
此外,还有一系列公约,如《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1982年12月10日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的条款的执行协定》《1996年“关于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造成的海洋污染公约的议定书》《保护东南太平洋公海海洋生物资源框架协定》《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内罗毕废除残骸国际公约》,2007年《关于确定次区域渔业委员会(SRFC)成员国管辖海域内海洋资源获取和开发最低条件的公约》《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管制捕捞的港口国措施协定》《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等等。(15)有关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的公约,参见: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Conferring Jurisdiction on the Tribunal,” https://www.itlos.org/en/jurisdiction/international-agreements-conferring-jurisdiction-on-the-tribunal/[2019-07-20]。
再次,第288条第3款规定“按照附件六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海底争端分庭的第11部分第5节所指的任何其他分庭或仲裁法庭,对按照该节向其提出的任何事项,应具有管辖权” 。
最后,第288条第4款规定了自裁原则,如果发生争端,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
5. 强制管辖的例外
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与会国的第二大争论焦点在于是否能将某些类型的争端排除在强制管辖之外。对许多国家来说,只有将特定事项排除在外,才能接受强制管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9条包含了对保留的一般禁止性规定,其规定“除非本公约其他条款明示许可,对本公约不得作出保留或例外”。这一则条款,排除了缔约国擅自作出保留的可能性。《公约》第15部分第2节(即第286条至296条)规定“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即将争端提交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义务。而第3节(即第297条至299条)规定了“适用第2节的限制和例外”,即限制强制程序的几种例外。
(1)自动例外
第297条第1款规定:“关于因沿海国行使本公约规定的主权权利或管辖权而发生的对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争端,遇有下列情形,应遵守第2节所规定的程序: (a) 据指控,沿海国在第58条规定的关于航行、飞越或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和权利,或关于海洋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方面,有违反本公约的规定的行为; (b) 据指控,一国在行使上述自由、权利或用途时,有违反本公约或沿海国按照本公约和其他与本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制定的法律或规章的行为; 或(c) 据指控,沿海国有违反适用于该沿海国、并由本公约所制定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外交会议按照本公约制定的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定国际规则和标准的行为。”一般而言,第297条处理沿海国被指控在行使其航行或飞越自由和权利时有违反《公约》规定的行为时可能产生的争端,适用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强制程序的原则。
该条规定到底是限制性条款,还是肯定型的重申性条款?仲裁庭在查戈斯群岛案中指出:“第297条第1款的措辞完全是肯定性的,未提及在哪些例外情形下仲裁庭不能行使管辖权。”“因此,从公约文本来看,第297条第1款重申而非限制了仲裁庭根据第288条第1款所享有的管辖权。” 因此,“不是说双方之间的争端必须属于第297条第1款规定的情况”,仲裁庭才能继续进行程序。(16)Geneviève Bastid Burdeau, “Compulsory Dispute Settlement Methods under the UNCLOS:Scope and Limits under the Scrutiny of the Jurisprudence” , China Ocean Law Review, 2017.
第297条第2、3款肯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洋科学研究(第297条第2款)或渔业(第297条第3款)的规定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应按照第2节(强制管辖)解决。然而,第297条其中规定了几个例外,规定沿海国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无义务同意将争端提交第2节规定的解决程序,这三个例外情形主要是关于几种海洋科学研究、生物资源的权利与权力的行使,具体而言是:(1)沿海国为在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而行使权利或斟酌决定权所引起的争端(第297(2)(a)(i)条和第246条);(2)沿海国决定命令暂停或停止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所引起的争端(第297(2)(a)(ii)条和第253条);(3)有关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或此项权利的行使的争端(第297(3)(a)条)。
有关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或者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争端,比如分配可捕鱼量,并不适用强制管辖程序。同时,有些情况需要调解程序,比如对于他国请求捕捞的种群,拒绝决定可捕量。
具体体现在第297条第3款规定:“(a) 对本公约关于渔业的规定: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应按照第2节解决,但沿海国并无义务同意将任何有关其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或此项权利的行使的争端,包括关于其对决定可捕量、其捕捞能力、分配剩余量给其他国家、其关于养护和管理这种资源的法律和规章中所制定的条款和条件的斟酌决定权的争端,提交这种解决程序。 (b) 据指控有下列情事时,如已诉诸第1节而仍未得到解决,经争端任何一方请求,应将争端提交附件五第2节所规定的调解程序: ⑴ 一个沿海国明显地没有履行其义务,通过适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不致受到严重危害; ⑵ 一个沿海国,经另一国请求,对该另一国有意捕捞的种群,专断地拒绝决定可捕量及沿海国捕捞生物资源的能力;或⑶一个沿海国专断地拒绝根据第62、第69和第70条以及该沿海国所制定的符合本公约的条款和条件,将其已宣布存在的剩余量的全部或一部分分配给任何国家。 (c) 在任何情形下,调解委员会不得以其斟酌决定权代替沿海国的斟酌决定权。(d) 调解委员会的报告应送交有关的国际组织。(e) 各缔约国在依据第69和第70条谈判协定时,除另有协议外,应列入一个条款,规定各缔约国为了尽量减少对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的可能性所应采取的措施,并规定如果仍然发生争议,各缔约国应采取何种步骤。”
(2)任择性例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明确列出可以排除的例外,允许缔约国将有限类型的争端排除在有拘束力的争端解决之外。第298条采用的立法技术意在限制并规范强制管辖的例外情形。该条明确列出了属于例外情形的事项,任何缔约国均可事先声明这些事项不接受强制管辖。因为缔约国无权起草文案,只能选择第298条下几款条文的表述,即(1)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第15、74和83条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或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2)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3)正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的争端。
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争端(有关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的争端),争端各方有义务进行协商,如未在合理时间内解决争端,应争端任何一方要求,各方必须接受将争端事项提交给《公约》附件五第2节下的调解。比如,东帝汶和澳大利亚案件,调解委员会宣布其有权受理相关争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部分第3节还规定了单方声明的一些程序。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均可作出声明,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撤回声明。第298条规定:在不妨害根据第1节所产生的义务的情形下,一国可以书面声明对于下列各类争端的一类或一类以上,不接受第2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大部分国家, 都交存了声明,排除了第298条列出的所有争端。中国在1982年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公约得到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在2006年做出了有关第298条的声明,排除这三种争端被强制管辖。(17)United Nations, “China, Declaration made after ratification,” 25 August 2006, http://www.un.org/depts/los/convention_agreements/convention_declarations.htm [2019-06-10].
(3)自裁管辖权原则、解释方法与管辖权终裁
根据288条第4款规定:“如果发生争端,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因此,依照自裁管辖权原则,仲裁庭有权判断自身的管辖权范围,以及判断争端的实体问题是否明确涉及第298条规定的例外情形。而仲裁庭有关管辖权的判定是最终裁决,仲裁庭无需在实体阶段重新审议这一问题。
那么,如何解释这些例外?例外应该被限制性解释还是扩张性解释?其他仲裁庭是否能作出其他解释?解释方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缔约国只能从几种情况中选择想要排除的,而不能自己起草、新增排除的争端类型,只能解释现有的这三个种类。比如,俄罗斯做出的声明中,其提及第298条列出的三类争端后,补充道: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针对关于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执法活动的争端,其不接受《公约》第15部分第2节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的裁判程序。但这种情形最终却被归入了第297条有关自动例外的规定。在荷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极日出”号案中,仲裁庭在有关管辖权的裁决中指出,对于涉及专属经济区执法活动的争端,仲裁庭管辖权的唯一限制只能源自第297条第2款和第3款认可的限制。
有观点认为,由于例外情形是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而非缔约国起草的,所以必须进行统一的解释。 在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南海仲裁案”管辖权与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中,仲裁庭认为,菲律宾要求将某些海中地物的法律地位判定为《公约》第121条规定的“岛屿”或“岩礁”或第13条规定的“低潮高地”,这类诉之声明不涉及“划界和主权归属”,不属于第298条规定的例外情形。换言之,仲裁庭对此有管辖权。因此,争议的性质可能会被对方通过法律解释,进行包装改变,从而提交到国际法院。而仲裁庭在管辖权上作出的裁决是终裁的。
有关仲裁法庭、特别仲裁庭,依据《公约》第287条,基本同上分析。
三、提交国际司法的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院具有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以下将简要介绍这两种类型的管辖权,并结合不同的争端种类,分析将这些争端提交到国际法院的可能性和可能的结果。
(一)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
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是联合国的机构之一。国际法院所依据的《国际法院规约》是联合国宪章体系的组成部分。(18)“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risdiction,” http://www.icj-cij.org/en/history[2019-07-20]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之一是诉讼管辖权(contentious jurisdiction),即国际法院有权对争端当事国提交的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和判决。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分为对人管辖权和对事管辖权。关于前者,只有国家才能在国际法院起诉或被诉。(19)参见《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第1款。
1. 同意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33条规定了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但该义务被视为一项避免使用武力的义务,并不是等同于接受强制争端解决程序的义务。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基于同意原则。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1款规定“法院之管辖包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即当争端出现时,当事国双方都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或者双方都是某协定的成员国,而该协定约定缔约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或者是根据联合国宪章中所特定的需要提交国际法院的争端。另外,国际法院的缔约国可以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进行申明,接受强制管辖。
此外,第37条规定,“现行条约或协约或规定某项事件应提交国际联合会所设之任何裁判机关或常设国际法院者,在本规约当事国间,该项事件应提交国际法院”。因此,国际法院接受管辖是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原则。需要缔约国同意才能将争端提交司法程序、国际法院。诉诸到国际法院的很多案子,争议点往往是管辖权,而大多数案子因为没有管辖权而被驳回,或者被诉国频频提出异议,进而致使案件审理时间冗长。
有关自愿性强制管辖,《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规定“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子)条约之解释。(丑)国际法之任何问题。(寅)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卯)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上述声明,得无条件为之,或以数个或特定之国家间彼此拘束为条件,或以一定之期间为条件” 。第36条第2款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争端问题。
具体到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首先,需要审查我国以及与之发生海洋争端的周边国家,是否是国际法院的成员国,并且是否依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作出申明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其次,需要审查我国是否与这些周边国家有双边或多边协定,而该协定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我国和日本都是联合国成员国,因此也都是国际法院的成员国。其次,日本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20)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recognizing as compulsory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under Article 36, paragraph 2, of the Statute of the Court,” 15 October 1946,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IND&mtdsg_no=I-4&chapter=1&clang=_en [2019-06-10].但强制管辖的适用前提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的人和其他国家”,即当事方国家都做出强制管辖的申明,而我国没有作出这样的申明,因此,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不适用于此。韩国也是联合国成员国,是国际法院的成员国,但其在2006年撤回了其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而另一种情况,即双方都是某协定的成员国,而该协定约定缔约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即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
若我国日后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作出申明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则与日本之间的海洋争端,会被国际法院强制管辖。但与韩国之间的海洋争端,并不立刻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因为韩国没有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
2.自裁原则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6款,有关管辖权争议,国际法院有权决定其是否有管辖权。且该裁决是终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9条,修改之的程序等同于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要想修改自裁原则,难度甚大。
(二)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国际法院的第二种管辖权是咨询管辖权 (advisory opinion)。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65条规定:“法院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见。”具体而言,联合国机构(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大会临时委员会)以及相关组织目前也有权请法院就各该组织活动范围内出现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比如其中的国际海事组织,可以请求国际法院就国际海事组织活动范围内出现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理论上,发表的咨询意见可能涉及我国周边海洋争端。咨询意见的法律效力,原则上虽然没有拘束力,但依旧可以提供软法性质的指导与指引。(21)参见曾令良:《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与现代国际法的发展》,《法学评论》1998年第1期。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的沿海海域宽广,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各种海洋争端。我国周边海洋争端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主权领土之争、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划分之争、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争、渔业领域的开发利用冲突之争、某地物的地理特征属性之争等等。这些争端类别不一,但本质上或多或少与主权、划界争议相关。以何种方式解决上述争端,将间接影响最终的结果。因此,选择适当的方式解决上述海洋争端,可以维护我国的海上利益。争端解决的方式有很多,包括非和平方式、和平谈判、磋商、调解、仲裁、司法裁决等。其中,国际仲裁或国际司法是由独立第三方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而提交到国际仲裁或司法的首要问题是管辖权问题。通过研究不同仲裁机构和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基础和法律依据,并结合不同类型的海洋争端,有助于较好分析和厘清不同类型的争端提交到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的可能性。
不论是国际仲裁还是国际司法,都基于一个共通原则,即自愿原则。任何当事国之间的争端发生后,包括海洋争端,若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均可提交国际仲裁或国际法院。比如国际仲裁庭,能够为当事国提供一系列良好的仲裁服务。换言之,国际仲裁庭或国际法庭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国的同意。
“同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该“同意”是事前已经在有关公约、协定中授予了;二是当争端发生后,就针对该特定争端,同意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主要的分歧发生于前一种情况,即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法院规约》等公约、协定中,缔约国已经事先授予了同意,即同意强制管辖。而在这些强制管辖中,往往有些例外供缔约国选择。我国声明选择了这些例外。因此,发生的纠纷或分歧往往在于如何解释当前的强制管辖,以及强制管辖的条件和例外。这些例外往往针对争端的种类。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争端,会有如下可能的情况。
第一,有关涉及中国的船舶与他国发生碰撞等争议被扣押或中国扣押别国船舶,即涉及船舶的立即释放,则此类争端可提交国际仲裁,或者提交中国根据第287条接受的仲裁庭,或者提交扣押国(如日本)根据第287条接受的法院或仲裁庭。但这不是强制管辖。
第二,有关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的争端,属于强制管辖的任择性例外。因此,如果我国海洋争端中涉及划界、历史性海湾、主权方面的争端,不适用强制管辖。但是,各方有义务进行协商,如未在合理时间内解决争端,应争端任何一方要求,各方必须接受将争端事项提交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五第2节下的调解。
第三,有关沿海国被指控在行使其航行或飞越自由和权利时有违反《公约》规定的行为时可能产生的争端,适用《公约》中的强制管辖程序。
第四,有关特定的海洋科学研究,尤其指沿海国为在专属经济区内或大陆架上进行海洋科学研究而行使权利或斟酌决定权所引起的争端、沿海国决定命令暂停或停止一项海洋科学研究计划所引起的争端,是强制管辖的自动例外,即不会被强制提交到国际仲裁或司法。
第五,有关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或此项权利的行使的争端,也是强制管辖的自动例外,即不会被强制提交到国际仲裁或司法。具体而言,有关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主权或者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争端,比如分配可捕鱼量,并不适用强制管辖程序。同时,有些情况需要调解程序,比如对于他国请求捕捞的种群,拒绝决定可捕量。
第六,有关石油、油气开采利用的争端,并没有被明确排除在强制管辖之外。但是,石油开采利用的争端往往是基于大陆架划线、专属经济区划界上的分歧。因此,对于此类争端,可以抗辩说,其涉及有关海洋划界、历史性海湾的争端,属于强制管辖的任择性例外,争端各方有义务进行协商,如未在合理时间内解决争端,应争端任何一方要求,各方必须接受将争端事项提交给《公约》附件五第2节下的调解程序。
第七,有关海洋上某地物的特征性质认定,如某小岛是属于“岩礁”还是“岛屿”,并没有被明确排除在强制管辖之外。但是,关于某地物性质的界定,直接影响到主权、界线的划分,因此可以抗辩说,此类争端是属于历史性权益、主权、海洋划界争端,从而构成强制管辖的例外。
综合而言,上述不同类型的争端被强制管辖的可能性较小。国际法院也有强制管辖,但我国之前没有申明接受,故上述争端没有被强制提交到国际法院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强制管辖领域中,基于自裁原则,即有关该法庭或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则由该法庭或仲裁庭决定,并且该裁决是终裁。因此,当事国对于管辖权问题,其享有的自主权较少,无法就管辖权问题进行上诉或请求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