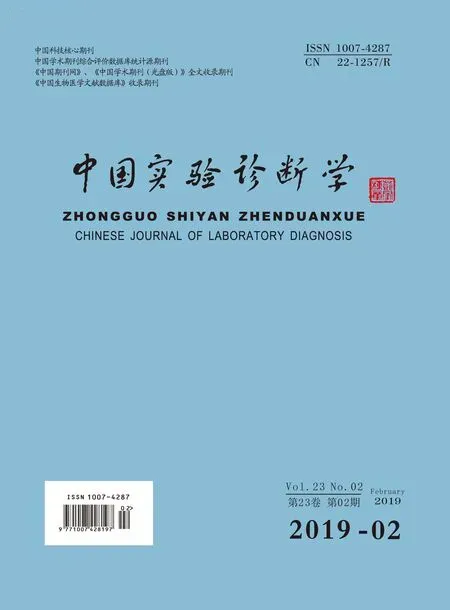颅骨缺损修补术后并发恶性脑水肿1例
吴佳桥,段宗生,孙艳平,李建云,王虎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麻醉科,吉林 长春130021)
1 临床资料
1.1 患者资料
患者:男,24岁,因车祸后右侧肢体活动不灵伴言语障碍3月余入院,头核磁示:左侧额颞顶颅骨局部缺损,脑组织外膨;左侧额颞叶、岛叶、基底节区缺血,部分呈亚急性期表现;伴左侧颈内动脉颅内段闭塞;鼻窦炎。并于2016年06月29日行“去骨瓣减压术”,术后患者清醒,遗留右侧肢体运动障碍及言语障碍,后行系统康复物理治疗近2月,病情好转。遂于2016年11月14日于全麻下行“颅骨缺损修补术”,术后病人意识朦胧,无明显自主呼吸,入ICU科给予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抗感染、保护脏器及对症支持治疗。并于2016年11月15日急诊全麻下行“左侧额颞顶部去骨瓣减压术”。患者术中核磁显示右侧小脑半球、左侧额颞顶叶伴多发异常信号,脑梗死或脑水肿有待鉴别;术中MRA示左侧颈内动脉、左侧大脑中动脉细且显影不清晰,左侧大脑中动脉分支显示不清(图1)。术中MRV示左侧横窦、乙状窦及上矢状窦前1/3细且显影不清晰(图2)。

图1左侧颈内动脉、左侧大脑中动脉细且显影不清晰,图2左侧横窦、乙状窦及上矢状窦前1/3细且显左侧大脑中动脉分支显示不清影不清晰
1.2 麻醉方法
患者带管入室,入室无创血压131/78 mmHg,脉搏110次/分,外周血氧饱和度99%。监护仪心电图提示正常窦性起搏心律。在患者右上肢开放静脉通道立即滴注晶体液醋酸钠林格注射液。麻醉诱导:1%丙泊酚120 mg(2 mg/kg),芬太尼0.2 mg(0.03 mg/kg),顺式阿曲库铵10 mg(0.15 mg/kg)。呼吸机行容量控制通气模式:潮气量8 ml/kg,气体流量2 L/min,呼吸频率10-16次/分,氧气和空气混合气,氧气浓度50%,维持气道峰压16-20 cmH2O,呼吸末CO2分压在30-35 mmHg。置入7.5号气管插管[1]。麻醉维持:浓度为2%的七氟烷术中持续吸入,右美托咪啶4 μg/(kg·h),2%丙泊酚6 mg/(kg·h),每20 min给予0.03 mg/kg的顺式阿曲库铵。术中血压波动不明显,血压维持在110-120/50-70 mmHg之间,心率变化在 60-80次/分,外周血氧饱和度为98%-100%,手术中心电图未显示异常。手术历时2 h,术中输注晶体液约1 500 ml,出血量100 ml,尿量300 ml。术毕患者行机械通气3 h,仍未恢复自主呼吸,但意识朦胧、呼唤可睁眼。遂带气管插管回到神经外科监护室。术后18 h测血压125/68 mmHg,心率101次/分,浅昏迷状态,无自主呼吸,瞳孔直径右侧3.0 mm,左侧4.0 mm,直接及间接对光反射迟钝,疼痛刺激左侧肢体可动,右侧肢体少动。硬膜外引流通畅,引流出血性液体约100 ml。由于患者长时间未恢复自主呼吸,遂拟将钛网取出,手术过程顺利,患者生命体征维持平稳。钛网取出术后血压135/75 mmHg,心率110次/分,呼吸机辅助呼吸,自主呼吸弱,潮气量约350 ml,频率6次/分。间断躁动,给予丙泊酚联合芬太尼镇静、镇痛。查体瞳孔直径右侧2.0 mm,左侧3.0 mm,光反射迟钝。术后第3天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意识逐渐清晰,双侧瞳孔等大同圆,光反射灵敏,给予试脱机。术后第6天患者自主呼吸恢复,神志清楚,可回答简单问题,遂拔除气管插管。术后17天随访,患者意识清楚,语言欠流利,双侧瞳孔等大同圆约3.0 mm,对光反射灵敏,右侧鼻唇沟浅,右侧肢体肌力Ⅲ级,左侧肌力Ⅴ级,在他人搀扶下可行走。
2 讨论
颅骨修补术后发生了弥漫性脑水肿是非常罕见的,对甘露醇联合地塞米松的治疗反应很差。脑水肿可以在修补术后立即发生,也可以在术后7天之内发生[2],这种并发症的发病机制目前还未确定。可能与植骨术术后凹陷处颅内负压的消失导致大量脑组织向植骨部位移位进而产生致命性的血管紧张性反应和大脑自动调节功能障碍有关。同时,脑室腹腔分流术、脑血管畸形、脑肿瘤、肿瘤囊肿及感染可能也是其危险因素。
中枢神经系统发生急性损伤时,首先活跃的是脑血管内皮细胞、星形胶质细胞中的离子通道和转运蛋白,从而导致异常的离子转运和异常渗透力的产生,最终表现为脑水肿和脑肿胀[3]。目前可分为细胞毒性水肿和血管源性水肿两类[3]。在缺血,创伤,低血糖,癫痫持续状态和暴发性肝衰竭等损伤中,中枢神经系统受损,星形胶质细胞对损伤快速作出反应,引起Na+、Cl-和水等渗透物在细胞内聚集,形成细胞毒性水肿[4]。渗透物的流入是靠主动转运或二次转运提供能量的,主动转运主要是靠Na+-K+-ATP酶和Ca2+-ATP酶介导,而二次转运主要是靠离子通道和共转运蛋白如Na+-K+-Cl-共转运蛋白和Na+-Ca2+交换剂介导的。在许多类型的中枢神经损伤之后,细胞内ATP被消耗,因此,独立于细胞内ATP的机制,如二级转运,更可能与离子水肿的形成相关[5]。
血管源性水肿是一种细胞外水肿,其特征在于血脑屏障的完整性被破坏,形成跨内皮通透性孔隙,允许水和血浆蛋白外渗到脑间质中。与出血不同的是,在血管源性水肿期间毛细血管结构是完整的,从而禁止红细胞通过,因此,血管源性水肿被视为无细胞血液(即血浆)的滤过。血管源性水肿主要由静水压力和渗透压力梯度决定,其中静水压力是血管源性水肿形成的主要驱动力。静水压梯度的决定因素,如颅内压,全身血压,毛细血管闭塞和血管痉挛,对血管源性水肿动力学很重要;渗透压梯度的决定因素,包括所有渗透活性分子,如Na+和蛋白质,也会影响水通量[3]。
手术前的准备:对于去骨瓣减压术术后需要植骨的患者,术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情绪改变甚至癫痫、偏瘫等症状[6],如果术前患者有大面积脑梗塞,需外科大夫评估术后发生脑肿胀的风险,建议植骨术前进行相关脑血管影像学检查。早期预测恶性脑水肿发生的风险对于改善疾病预后有重要意义。2008年的一篇Meta分析提出可预测恶性脑水肿发生的影响因素,其中首位的是脑梗死面积,其次是血管因素,血管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大脑中动脉,其他因素包括年龄、低灌注、出血等。术前可以进行一些影像学检查以预测恶性脑水肿的发生,MRI弥散加权成像(DWI)是判断脑水肿的有效方法,但因MRI扫描不如CT普及,而且费用贵,耗时长,因此一般不作为预测脑水肿的首选。因此,我们可以使用CT平扫及CTA,CTA可用于预测急性脑梗死并发恶性脑水肿,为早期识别恶性脑水肿提供影像依据[7]。Horstmann等人研究发现,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和CT结果之间有密切的联系,而超声检查无创又价格适宜,可以作为常规术前预测脑水肿的影像学检查[8]。麻醉医师也应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在术前访视患者时应密切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评估患者的呼吸、循环功能及对手术的耐受能力,与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制定严密的个体化麻醉方案。
麻醉方式的选择和处理:我们选择了静吸复合、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方式,该患者对于麻醉药没有特殊反应。从这1例患者中总结出一些麻醉经验,例如,全身血压特别是收缩压必须保持足够高以维持脑灌注,但过高会促进脑出血的发生,此外,颅内压必须保持足够低以维持组织灌注,但又需要足够高以抵消水肿。因此为预防插管时的颅内压急剧增高和产生的相应心血管反应,我们麻醉诱导时缓慢给药,充分去氮给氧,使用了足量的芬太尼和非去极化肌松药、用喉麻管以2%利多卡因行舌根及咽喉部表面麻醉等多种方式,使插管前后心率、血压等心血管反应变化不明显,从而避免了颅内压的急剧增高。在麻醉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PaCO2维持在30-35 mmHg,过度通气虽然有利于缓解颅内压,但若PaCO2降低过多,可致脑血管收缩,脑血流量减少,进而增加了脑缺血的可能,因此PaCO2不适宜过低。此次手术时间短,术中少量失血,平均动脉压保证在65 mmHg以上,保证了脑血流的自主调节机制,避免了脑缺血的发生。若外科医生开颅后认为需要降低颅内压,我们准备了静脉输入甘露醇来达到脱水降低颅内压的目的。
弥漫性脑肿胀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标准和良好的预防方法,而恶性脑水肿的死亡率极高。这些年治疗措施主要是脱水降低颅内压及外科行去骨瓣手术减压治疗。因此我们需要更透彻的了解脑水肿的病理生理机制,如果可以研究出以脑水肿形成为生物靶点的药物来预防脑水肿的形成,将会形成新的突破[9],可以尝试以发挥作用的离子通道和蛋白酶作为生物靶点。有研究证明,贝伐单抗可治疗难治性脑水肿,有效率为84.74%[9]。而外科医生可以通过积极的扩大去骨瓣减压术治疗,这对麻醉方式的选择和麻醉管理有一定的要求。因此麻醉医师在术前,应和外科医生有个充分的沟通,并做好术前评估[10],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麻醉方案,合理使用诱导及维持药物,及时处理术中出现的异常情况,维持呼吸、循环功能的稳定,还可以对体温等进行监测,例如术中可以全程使用保温硅胶床垫。有研究提出,先天性的颅内血管异常也有可能是诱发因素,所以术前能准确判断患者血管结构,对术后恶性脑水肿的发生有很好的预防作用。我们可以从血清标记物、神经影像学、神经保护剂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为恶性脑水肿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新的方法[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