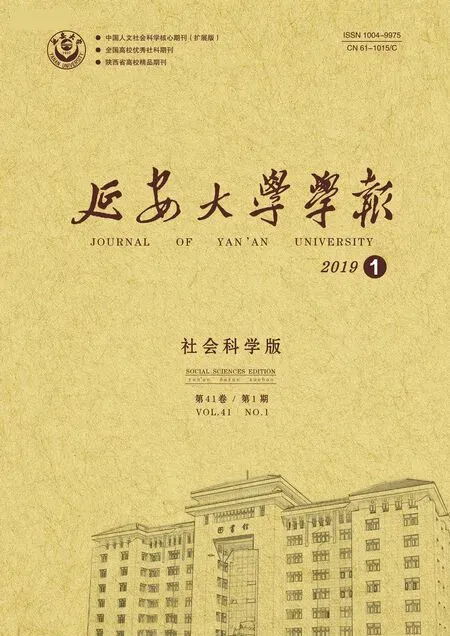北宋荫补制度下的家族仕途选择与转变
张心怡,杜林渊
(延安大学 历史系,陕西 延安 716000)
职官选任历代均有,发展到宋代,最具影响的是科举与荫补两项。尤其是科举制度,在宋代取士人数大为增加。张希清经统计得出:“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约为元代的30倍,约为明代的4倍,约为清代的3.4倍。”[1]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宋代科举的盛行、寒士的崛起是对魏晋隋唐贵族政治的重大变革。
那么科举制度于宋一代的发展是否真正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笔者选取了北宋真宗朝咸平元年戊戌(998年)登进士的51人[2],通过对其官阶品位进行统计[注]选择真宗朝是因为此时随着制度的完善、统治者对于科举取士的重视及优遇,科举之风开始盛行,而对于咸平元年登第的进士进行分析则属随机选取。,发现这51人中,后续发展有明确记载的为35人,其中累任官职正五品及以上者共7人,正三品两人[注]累任官职正五品及以上的7人为孙瑾(授舒州团练推官,复举贤良方正科入等,历右言正、知制诰,权知开封府,终官给事中)、李若谷(初授长社县尉,历尚书工部侍郎、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进拜参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唐肃(仕至龙图阁待制,知审刑院)、凌震(累迁翰林学士)、盛京(历谏议大夫、知江宁府,仕终于工部侍郎)、刘筠(授馆阁县尉,历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终龙图阁学士)刘烨(终刑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知河中府);其中官职为正三品的2人为凌震、刘筠。其中对凌震的记述现存于《咸淳临安志》及《光绪浙江通志》等地方志书之中,《宋史》未对其列传记载;刘筠则在《宋史》卷三百五,第10088页中有列传记载。。51人中仅李若谷以参知政事为副相,然其本官又仅为尚书工部侍郎。以上虽是个案,但可发现,科举取士在宋代人数虽增,但入仕者身居高位的仍是少数,且其中不乏家族显赫者,而由寒士经科举而置身高位的则少之又少。正如邢铁先生所言:“虽然有不少的例子反映平民乃至贫民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一举成名,家庭家族也因之改变了处境,这都是因为事情稀罕而被记载下来的。”[3]119
以往学界在面对宋代的入仕途径时,更多的关注了科举取士的影响,而将其他选官途径置于辅助层面。荫补制度[注]游彪先生在《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自序部分对荫补制度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梳理概况:荫补制度衍生于世卿世禄制度,但不同于世卿世禄制度下特权阶层拥有的法定世袭权力,在荫补制度下官位不具世袭性,尽管官员子弟可以依据其父祖辈的官职荫补入仕,但绝不能与世卿世禄制度划等号。作为宋代重要的取士方式,近三十年来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其自身名目、制度演变脉络、冗滥原因及消极影响方面,进行了明确而完善的研究[注]游彪《宋代荫补制度研究》、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关履权《宋代的恩荫与官僚政治》、金旭东《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白文固《北宋文武官员恩荫制度研究》、《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任敬《论宋代恩荫制度的特点和影响》、董名杰《析探宋代“恩科”之弊》等均对荫补制度进行了研究;此外,李裕民、张希清、文畅平、刘立夫、龚延明、曾小华等学者在文章著述中亦将荫补制度与宋代的科举、磨勘以及冗官现象结合起来探讨。,但关于荫补制度终宋一朝,其积极影响及存在的合理性,考察角度仍稍显单薄。
荫补制度自形成起,其评价便较为负面,但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然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4]因而,荫补制度能够存在千年之久,必定符合了彼时的诸多需要,又在各层面的制衡与妥协间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的。
2013年李裕民先生在《寻找唐宋科举制度变革的转折点》余论部分,以宋代科举取士在高淘汰率、高成本投入的冲击下,如何使科举制度对百姓长时期维持吸引这一背景为着眼点,从参加科举的寒士心理层面入手,得出荫补制度于宋王朝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对打开问题的视野大有裨益。
这一论述给予笔者诸多启示。目前学界对于宋代荫补制度本身的研究已较为完善,因而笔者尝试转换角度,不再拘于荫补自身层面,而将其置于宋代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下,与家族研究相结合,从官宦家族及普通科举家族自发的选择转变入手,分析荫补于宋代选任层面的后续影响,进而讨论其存在于有宋一代的积极层面及合理性。因两宋共历十八帝,体系庞杂,故将关注点集中于北宋。
一、北宋荫补制度发展特点
荫补制度是宋代重要的选任制度之一,相较于前代以恩例为主要表现,荫补于北宋一朝的发展呈现出恩例与限制并存的特点。
一是荫补之恩惠下众多。主要表现为恩例名目繁多,具体有“南郊大礼及诞圣节荫补、遗表荫补,此外还有后妃、宗室以及宦官养子等一系列的荫补名目”[注]游彪《北宋荫补制度研究》中设有专门章节对以上荫补名目进行研究。。由此“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5]536除以上定例外,皇帝亦常给予去世功臣种种特恩,其子弟、门人故吏受荫补特恩入仕也更为便易[注]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九月己酉条,第2080页载:“(王旦去世)上遽临哭之,废朝三日,优诏赠太师、尚书令,别次发哀……谥曰文正,录其子、弟、侄、外孙、门人、故吏,授官者十数人。及诸子服除,又诏各进一官。”;对殁于王事者,其子弟荫补亦较为普遍,几乎历任君主都颁布诏令对此做出规定[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卷二十、卷一百三、卷一百三十八、卷一百三十九、卷一百四十七、卷一百四十九、卷二百七十七、卷二百八十七、卷三百四十九均对殁于王事恩作出诏令规定。。种种恩例持续发展,荫补取士的冗滥局面最终形成。
二是荫补之限多于前代。尽管荫补之例在北宋史籍所载颇多,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仍存有许多限制。
首先是对官员子弟荫补范围及官资[注]官资是指官员的资历职位。的限制。通过对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庆历三年、仁宗嘉祐元年以及哲宗元祐三年这四次较为集中完备的诏令进行梳理,以宰执官员为例分析可知,北宋对官员子弟荫补的范围及官资的限制是非常明确的。
如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对承天节与南郊奏荫子弟的恩例做出规定,对已身官员其子及弟、侄、孙官职的授任加以区分。诏令规定[注]诏令内容由笔者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春正月己丑条(第1911-1912页)内容进行梳理总结得来。,宰执类官员其子可根据已身官阶高低,分别补为东头、西头供奉官,其弟、侄、孙可被补为左、右侍禁,位次于供奉官。至此以下,根据已身官员官职高低,其子与弟、侄、孙所补官职以是为差。其中由宰臣、枢密之子所荫补的东头供奉官仅为八品武阶,这相对于唐代高门子弟所荫官职是明显降低的。
又如仁宗庆历三年,对荫补的具体规定更为细致[注]以下所述两点具体表现是笔者对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五,十一月丁亥条(第3503页)所载诏令内容加以分析概括所得。,表现在:一是对文武官员荫补权力的划分,形成文官子弟荫文官、武职子弟荫武职的局面;二是对子及期亲[注]期亲又称周亲,是亲属关系的一种。期,一周年。我国古代以丧服种类及服丧期限的不同确定亲属关系。按丧服种类,五服亲属分别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齐衰亲中服丧一年的亲属即为期亲。之外的余属可获恩例做了规定。以宰执类官员为例,仁宗前期文官可荫子为将作监丞,朝亲太祝、奉礼郎,庆历三年对子及期亲荫例如旧,另外规定余亲以属远近补试衔。仁宗前期武官子弟及期亲可荫官职与真宗朝时几乎未有变动,庆历三年亦如旧,但同样对余属做了新的规定[注]同上,第3504页载:“其武臣:使相,子为东头供奉官,期亲左侍禁,今子及期亲如旧,余属自左班殿直第官之。”。
由此可见,宋制对荫补官员的内在限制之严格。且这些限制,在仁宗嘉祐元年“两府及使相,宣徽、节度使三年荫二人,已减旧恩之半”[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二,夏四月丙辰条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第4402页。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仁宗下诏:“见任二府、使相,宣徽、节度使、御史知杂悉罢乾元节恩荫”[6],同时对文武官员每遇郊礼所荫亲属做出限制、对致仕恩进行了一定的降等。至哲宗元祐三年,又诏减任子恩泽,对宰执类官员“给使人应得恩例,并四分减一”[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十七,十一月乙丑条,第10128页有详细记载。,以下官员各有差减。
其次是对荫补入仕者初官的限制。与科举入仕官员可直接获得实际差遣不同,北宋时期逐步创立、完善了荫补入仕者考试合格后方得委派差遣的铨试、呈试之法。这就使完全依靠荫补、而无真正才干的入仕者在获取官资之后,难以获得实际差遣。此外,即便其通过铨试、呈试获得差遣,一开始也不能担任亲民官[注]亲民官在宋代是指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统称。自知州、知县至监镇、知寨,皆属亲民官。,只得从低级的监当官[注]监当官是对宋代诸州粮科院、钱监、监仓、监盐、监酒、监镇、作院、交引、库务、监门、监茶、监场、监务等官的统称。做起,几任之后凭借功绩和资历,才或许能够升任为亲民官[注]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对荫补入仕者初官的获取有过表述:“他们不能直接担任知州、知县、通判等亲民长官。初官一般只能担任远小州县最低级的监当、主薄、县尉等差遣,凭功绩和年限积累资格,升为亲民资序,方可担任较重要的差遣。”。
因而,尽管北宋对官员荫补子弟亲属恩遇颇多,范围颇广,但在上述两方面的限制下,荫补入仕者希望单纯以荫补手段取得官位的高升、家族连续几代的稳固,便不再如前代那般容易。
二、荫补制度下官宦家族及普通科举家族的发展困境
荫补制度在北宋呈现出限制与恩例并存的演变特征。一方面,在王朝对荫补入仕者的层层限制下,官宦家族子弟单纯以荫补作为入仕途径,便不可避免的在后续发展中遇到困境;另一方面,尽管北宋时期科举之风已经盛行,但普通家族子弟以科举入仕仍面临许多现实困境。这种情况下,维系于特权政治下的荫补制度所能为家族带来的持续恩例,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这类家族将荫补与科举分离对立的固有观念。
(一)荫补之限下官宦家族子弟的仕途发展困境
北宋官制将官员类别分为武官与文官,这两类官员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其家族子弟便可受荫获取官资。
1.武官家族
北宋时期,官员入仕的途径主要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种,其中“武选官的入仕,杂此五途,而以恩荫为大宗”。[7]北宋以荫补作为子弟主要入仕途径的武官家族有石守信、韩重赟、慕容延钊、李继勋、党进等家族。
石守信作为北宋著名开国功臣,其子弟均以荫补入官。长子保兴以荫补供奉官入仕,历任顺遂,“世豪贵,累财钜万”然“悉为季弟保从之子所废”。[8]8812保兴子元孙,以荫补东头供奉官入仕,其官累迁至如京副使。康定初年,元孙与夏人战于三川口,军败后传者以为其已战死,朝廷荫补子孙七人。后了解到其未死的真相,朝堂官员大都认为元孙兵败不死是为辱国,请求将其处斩,虽然仁宗最终将其安置于全州,但背负着辱国的骂名,元孙及子弟之后境遇必然艰辛。
守信次子保吉“初以荫补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开宝四年)选尚太祖第二女延庆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俄领爱州刺史”,其发展过程也因父恩较为顺遂[注]脱脱:《宋史》卷二百五十,第8813页对其任官过程有详细记载:“真宗即位,加检校太尉,保平军节度……景德初,改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大中祥符初,从东封,摄司徒……卒,赠中书令。”。但保吉“好治生射利,性尤骄倨,所至峻暴好杀,待属吏不以礼”[注]脱脱:《宋史》卷二百五十,第8813页载。,其品德如此,子弟的才学素养亦可预料。保吉子贻孙任崇宁使,后因坐事而遭免职。子孝孙,任西京左藏库使,《宋史》中未再有对孝孙的详细记载。
石守信家族作为武官家族的代表是较为典型的。这类开国功勋家族,因战功及与皇室姻亲等原因,在最初一二代间仍可保留其显赫的资本,但子孙单纯依靠荫补入官,不重才学道德,其家族最终只能走向衰落。
2.文臣家族
文臣家族中,北宋吕端、李昉、范仲淹等家族子弟多以荫补入仕。笔者将从吕端及其子孙仕途发展走向入手,对幽州吕氏中吕端这一支,子弟典型以荫补入仕的情况进行分析[注]北宋时期的幽州吕氏家族,其子弟亦有以进士入官者,如吕诲。但因只是少数,其家族还是以荫补入仕为主,故将其归入此类。。
吕端以荫补千牛备身入官,先后拜参知政事、平章事,官至户部侍郎。吕端去世后,四子具得荫补。但在荫补层层限制的大背景下,四子均发展困难。以至于“景德二年,真宗闻端后嗣不振,又录蔚为奉礼郎……藩兄弟贫匮,又迫婚嫁,因质其居第。真宗时,出内府钱五百万赎还之;又别赐金帛,俾尝宿负,遣使检校家事”。[8]9517
这种境况的出现固然有吕端为相时清正廉洁、不蓄资产的原因,但其子弟单纯依靠荫补入仕、个人才学能力的平庸,才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直至吕荀之子吕诲进士登第后才有了一线转机,而吕诲选择科举,固然有个人追求的转变,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其父官职仅至国子博士,以此再难荫得如意官位,这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吕诲之后,其子由庚、由诚等又转为荫补入官,之后发展未见于史册。
如此可见,在统治政府对荫补制度的层层限制之下,家族子弟若仍单纯依靠父恩而不求取自身能力的提高,其前途发展终会受到阻碍,家族亦将趋于颓衰。
(二)普通家族面临的现实困境及荫补之恩对其固有观念的冲击
传统观念认为,与“落后”的荫补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是进步的,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一次巨大变革。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确使我国古代政治出现了拔掘寒门的新气象,也为普通家族一举中第、光耀门楣带来了可能。
科举制度于北宋一代的发展恩例颇多。例如科举之后为防止人才有所遗漏,皇帝有时会对黜落者再进行选录[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二月辛酉条,第167页载:太祖乾德四年,“进士合格者六人,诸科合格者九人。上恐其遗才,复令于不中选人内取其优长者,第而升之。”,伴随着重文抑武局面的形成,科举取士之多、待遇之厚是空前的。
然而,即便宋代科举取士人数大增,这些登进士第步入仕途的普通家族子弟,最终能够位居高官的只是极具才干的少数[注]前文中对真宗咸平元年戊戌登进士第的51人其后续发展的统计分析可作为此论点的例证。。而由一般家族及寒士阶层步入仕途的低级官员,大多缺乏官宦家族子弟所能获得的良好教育资源及其所具备的人脉帮扶,向上发展困难颇多。实际上,北宋在文官升迁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视荐举保任的。
初入仕途的文官往往注授判司、簿、尉之类的低级职位,需历三任或二任,每任三年或四年,由举主保荐,循资升为县令或录事参军。再历三二任,有规定的官员推荐,无过犯,方可改京官,差注知县。知县二任有举主、有政绩,可升通判。通判二任有举主、有政绩,可升知州。[9]154
由此可知,官员们在接受磨勘以期转改寄禄官阶时,必须审核各类文状,其中一项便是由举主所写的推荐书。而当时常有因人脉缺乏难以得到推荐的情况。武官方面,在以荫补为武选官大宗来源的同时,武举取人实际极为有限。
因此,鉴于普通家族出身的官员后续发展中所遇困难之大,加之引试的严苛[注]脱脱:《宋史》卷一百五十五,选举一,第3605页载:“既集,什伍相保,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徙……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稽其版籍,察其行为,乡里所推,每十人相保,内有缺行,则连坐不得举。”、对违规者惩治的加重,最终引发了这类官员对分离对立的荫补、科举两类制度的重新思考。
三、北宋荫补制度下官宦家族及普通科举家族的选择与转变
北宋元丰改制前官制名不符实,“至于官人授受之别,则有官、有职、有差遣”。[8]994这一时期,本官只作为寄禄官而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职事官则是差遣。当官宦家族子弟以恩荫、普通家族子弟以科举,获得初步的寄禄官衔,其仕途起点基本一致,想要谋求仕途的发展,差遣的获得、或者说重要差遣的持续获得,尤为重要。
荫补入仕者获取差遣是较为困难的,文、武官必须通过铨试、呈试的考核。这与科举入仕者,初授官便有差遣相比,的确不占优势。但另一方面,科举入仕者所获差遣多是级别较低的幕职州县官[注]苗书梅在其专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395-401页中对幕职州县官作出解释:“(宋代)幕职官与州县官同属吏部流内铨(《中国官制大辞典·上卷》指出,流内铨是指宋代所置的官署名,属吏部。掌文官自初仕至幕职州县官的铨选注拟和对换差遣、磨勘功过等事。)铨选差注的低级文官,二者常被并称为幕职州县官,又称为选人。”,之后缺少人脉的帮扶,实际很难获取更进一步的差遣,至于改官为京官、乃至朝官则更加困难。而荫补入仕者,铨试制度虽对其有诸多限制,但具体执行过程中,却仍有某些可供人脉渗透的空间,“官僚权贵之子弟,可以凭借父兄特权取得免试出官的机会……未经呈试人往往以‘出疆’‘接伴’‘馆倬’或‘使相宰执奏辟使臣’等经历作经任人,未出官小使臣,‘一或占此,不三数月,或旬日间,便可作经任人,暗免呈试参选’”。[9]240-241而当其获取差遣之后,凭籍家族的资源与优势,持续差遣机会的获得,比普通科举家族子弟更为容易。
以上各具损益的发展情况,客观上引发了北宋最为重要的两类家族——官宦家族及普通科举家族对子弟入仕途径及家族如何获取良好发展的思考。
(一)荫补之限下官宦家族的深层转变
北宋对官宦家族的限制是多重的,除了国家颁布的制度化诏令外,还有许多隐含于现实操作中的表现。如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其子陶邴凭借自身学识考取进士后,却因其父在朝为官不被太祖信服,要求他进行复试[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三月癸巳条,第200页载:权知贡举王祜擢进士合格者十人,陶谷子邴,名在第六。翌日,谷入致谢,上谓左右曰:“闻谷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书复试,而邴复登第。因下诏曰:“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接上页)党与,颇容窃吹,文衡公器,岂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即便陶邴再次登第,但官员子弟须再行复试却被规定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对官宦家族子弟正常参与科举的限制。
因此,一批身居高位、对世事深切洞察的家族领袖同族人一起,共同开启了对传统入仕途径的自发转变。
1.东莱吕氏家族
清赵翼言:“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已属仅事,宋则有三世为相者。吕蒙正相太宗,其侄夷简相仁宗,夷简子公著,哲宗时亦为相,传赞为世家之盛,古所未有。”[5]557-558所谓的一门三相,指的就是北宋的东莱吕氏家族。其于政治上世代簪缨,一门七执政,子弟入《宋元学案》者共十七人,在学术文化上亦做出重要贡献,这应与这一家族及时明确的选择与转变有着极大关联。
王善军先生曾指出:“对世家大族来说,已有权势是最为丰厚的政治资源,它不但在许多方面公开或潜在地发挥着巨大作用,就是在相比之下最为公平的科举制度方面,亦能深深地介入其中。”[10]纵观东莱吕氏家族于北宋一朝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家族子弟,转变了以往世家多单纯依靠荫补入仕的方式,而以进士登第与荫补入官皆有之。家族中进士登第的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注]吕公著先以荫补入官,后考取进士。《宋史》卷三百三十六,第10772页载:“(公著)恩补奉礼郎,登进士第,召试馆职,不就。”、吕蒙休、吕蒙亨、吕居简、吕希纯等,这些子弟,因其良好的才能品行与家族内在的优势,其升迁较一般的登第官员更为迅速。其中,蒙正、夷简、公著一门三相,其后续发展之显赫自不必多言,其他子弟亦多顺遂。如蒙正子居简先任殿中丞、提点京东刑狱,后“迁秩判官,拜集贤院学士,知梓州、应天府,徒荆南,进龙图阁直学士、知广州……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台”。[8]9150而公著子希纯亦进,进士登第,为太常博士,后历任中书舍人、宝文阁待制、知亳州等,“徽宗闻其名,数称之”。[8]10780后因崇宁党争等原因,发展颇具曲折,“希哲、希纯世济其美,然皆陷于崇宁党祸”。[8]10780如若不是这个原因,其自身才学加上家族助益,发展必定顺遂。
而家族中的其他子弟则多以荫补入官,且凭借家族的资源与优势,多被赐进士及第,升迁迅速,如:
(公弼)赐进士出身,积迁直史馆、河北转运使……夷简之亡也,仁宗思之,问知公弼名,识于殿柱。至是,益材其为。擢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瀛洲,入权开封府。尝奏事退,帝目送之,谓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8]10213
不过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到的是,隐藏于外在入仕形式转变背后的,是家族内在的选择与转变,这与东莱吕氏对家学家风的重视直接相关。这样的转变是现实困扰下自发的及时调整,蕴含着家族的洞察与智慧。与以往荫补入仕者的才学低下不同,其子弟即便以荫补入仕,仍颇具才学。作为世家典范的东莱吕氏,其显赫奠基于吕蒙正时期。蒙正本人颇具才学,为官过程中凭借才识三入上相[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五○册,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十五,《吕文穆公蒙正神道碑》第130页载:未几,代赵普为上相,淳化二年罢为吏部尚书奉朝请,四年复为上相。至道元年除授左仆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真宗绍位就加左仆射,咸平三年诏归,四年复位上相。,这样可供以身正教的典范,对家族发展是极为难得的。作为家族的奠基者,蒙正对家族子弟的品性道德具有深刻劝诫:
公退居于里,常召诸子立庭下,诲之曰:“……吾幸生盛时,硕茂尊显,今又奉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为王官,其无为。世胄子弟之为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污吾而,将以累吾家。”由是,诸子夙夜相警劝,不忘诏教,持身谨勑,咸称善人。……孙二十五人,曾孙三十一人,并传公之所诲。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于是又知公之义训大施于其后。孙皆有官,而曾孙亦有出仕者。[11]
纯正的家学渊源加之家族优质的资源依托,使东莱吕氏的家学传统不再只是用于谋官的凭借,而转变成为博雅平和的内在力量。而这样深厚渊源的底蕴与优势,贯穿了东莱吕氏家族终宋一代的整体脉络,使子弟在入仕为官后更加游刃与从容。如此,以内在的转变带动外在的选择,将子弟荫补入仕与进士登第两类方式有机的结合于家族乃至子弟个人发展层面,东莱吕氏家族最终实现了家族的深层转变,成为宋代官宦家族区别于前代门阀贵胄的重要代表。
2.真定韩氏家族
荫补之限下,真定韩氏家族亦做出相应转变。不过,与东莱吕氏稍显不同,真定韩氏根据宋代“凡有官人不入学而愿试贡士者,不以文、武、杂出身,悉许之……中选人上等者,升差遣两等,赐上舍出身;文行优者,奏闻而殊擢之”的规定[8]3665,多令子弟先以荫补入官,后再以有官人[注]有官人是宋代官员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即指未参加科举考试却因各种关系而拥有官职之人。的身份考取进士,从而获取更大程度的升迁与恩遇。这种将荫补与科举有机结合的途经转变,普遍存在于子弟之中,同时加以家族内部的人脉帮扶、政治资源的有力支持,子弟发展普遍良好[注]例如,脱脱《宋史》卷三百一十五,第10300页载:真定韩氏家族其奠基人韩亿之子韩综,“荫补将作监丞,迁大理评事,举进士中第,通判郑州、天雄军……吕夷简自北京入相,荐为集贤校理、同知太常院……累迁刑部员外郎、知制诰”;卷三百一十五,第10301页载:韩纲子宗彦“荫补将作主薄,举进士甲科,累迁太常博士。以大臣荐,召试,为集贤校理。”。
真定韩氏家族的转变是世事洞察下的睿智考量,这种转变与家族内部已有的政治资源深切嵌合,最终促使了荫补之限下,家族仍能作为世家的典范,将已有的资源数代延续。
(二)荫补之恩下普通科举家族的立场转换
在科举制度的优遇下,普通家族子弟大多渴望以此入仕改变命运、光耀门楣,但这在具体操作中却困难颇多。除了前文提到的现实困境外,我们也常忽视了,科举实际“并不排挤士族,而且士族在考场竞争中具有文化上的优势;科举制度剥夺的只是士族垄断仕途的权力”。[12]事实上“科举考试的主力始终是那些有家学背景的士族子弟”。[3]119
这种情况下,普通家族子弟其心态逐渐发生转变。当其以科举应试者的身份进行准备时,内心或许是有完成抱负、改变家族命运甚至改变荫补这样“落后”的特权恩例的理想。但当其经历层层选拨,真正置身官僚体系中,便会认识到建立在特权之上的王朝,其巩固发展长久以来所依托的,都是制衡与特权并存下的家族,与家族内部几代效力、层层关联的士族官员。
王朝拔擢寒门、实行科举的确有着选拔平民精英完善政治、制约世家的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王朝的根基并不在此。历数各朝可以发现,无论王朝的建立者是平民抑或贵族,经历最初制度的确立与一二代的发展后,王朝统治所依托的核心,都是那些经学传家之下,政治资源相辅相成、相系相托的世家大族。而北宋时期的世家子弟经由荫补之限后,俨然实现了由内而外,才学与资源深层嵌合下的转变。
于是,这些经由科举入仕的普通家族子弟,其心态最终转变。现时的权力来的颇为不易,如若子弟再来一遍未必还能成功,于是这些官员对荫补的渴求,甚至超过了已具备优厚资源的高官世族。尽管他们仍将科举作为“正途”,但却不会轻易丢弃荫补子弟的恩例。这实际是其内心对荫补的认同,以及基于现实考量而进行的选择与转变。
范仲淹早年生活艰辛,进士登第后于仁宗庆历三年九月进奏提出“抑侥幸”,希望对官员荫补、奏荐子弟加以限制,但其四子纯祐、纯礼、纯粹、纯仁又均以父恩荫补入官[注]脱脱:《宋史》卷三百一十四,第10276-10281页载:纯祐“荫守将作监主薄,又为司竹兼”;纯礼“以父仲淹荫,为秘书省正字”;纯粹“以荫迁至赞善大夫、检正中书刑房”;纯礼“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欧阳修自幼丧父生活艰难,进士登第后同样于仁宗庆历三年十一月对限制荫补子弟提出建议,但其子发仍“以父恩,补将作主薄,赐进士出身,累迁殿中丞”。[8]10382范仲淹与欧阳修这类对荫补制度提出限制要求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他科举入仕家族对荫补的需求只会更加强烈。
四、余论
家族作为国家有机的构成部分,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王朝的运转依托于家族的稳定,以及家族子弟对政治生活的内在推动;王权的稳固则取决于其对家族特恩给予的安抚,以及制约限制下的权衡。北宋的荫补制度,在其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限制与恩例并存的特点。在对入仕子弟的限制下,诸如东莱吕氏、真定韩氏之类世家的家族领袖,凭借其对世事的深刻洞察,转变了以往世家多以父恩荫补的入仕途径。以对家学家风的重视为子弟发展的内在依托,将可擢拔的科举与可固恩的荫补有机结合于子弟的发展,同时亦将家族已有权势下的政治资源与人脉帮扶嵌入其中,最终实现家族的转变与新生。而以科举入仕的普通家族,则在特权政治所带来的现实困境下,实现了对荫补制度由鄙薄排斥、权衡思考、实际接受再到内心认同的切实转变。
由此可见,荫补制度于北宋一代的演变轨迹,及其对家族发展所带来的后续影响,恰如其分的实现了王朝对家族的制衡,从而促使了两类家族自发的转变与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一转变,又使荫补制度深深介入家族发展与王朝稳固过程之中,成为其内在需求与现实依托,其存在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而北宋一代的荫补制度,也终因对家族转变过程所发挥的推动作用,更新了两类家族传统的发展道路,无论是高门世家或是普通科举家族,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举与荫补制度的调和。纵观北宋一代的发展,很难将某一家族单纯定义为科举家族或是荫补家族:三槐王氏被称为科举世家,但其子弟发展亦多维系于荫补特恩之上;东莱吕氏被称为高门世族,但蒙正、夷简、公著一门三相又均以进士登第。因而,北宋时期的家族区分,并不如魏晋一般等级分明,也不同于唐代士庶两族斗争尖锐、最终引发了为乱朝政的牛李党争那般难以调和,北宋时期不同类别家族之间,因为其内在的选择与转变,界限日渐模糊、矛盾逐渐缩小。
这一方面使宋代科举人数远超前代成为可能。世家的转变使他们基本没有唐代世家子弟对科举制度的内在排斥与行为破坏,从而为科举于宋一代的发展完善与广泛推行消减了阻碍,使其真正成为王朝政治下,被各阶层所认可的选任制度;另一方面,两类家族之间矛盾的趋于平和为内政的稳定、王朝的巩固提供了可能。这两类家族子弟在转变中,均更加重视才学与能力的提高,这些有才之士积极投身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王朝内政的稳定与完善。而有宋一代在外部环境的巨大压力下,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盛,与家族转变所带来的平和进取、稳定繁盛的政治局面是分不开的。
将魏晋隋唐时期的家族与北宋转变之后的家族相比,诚然是可见“变”的痕迹在其中的,这种由荫补制度恩例与限制并存的演变特点,引发而来的家族内部转变,为有宋一代政治格局的发展带来了自内而外的进取动力,荫补制度就其本身的诸多限制与前代相比,已经是一种进步。而由其所带来的上述后续影响来看,荫补制度确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层面的。诚然,这项制度带来了诸如特权、冗滥等诸多弊端,但也不应否认其存在于北宋一代的合理意义与社会政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