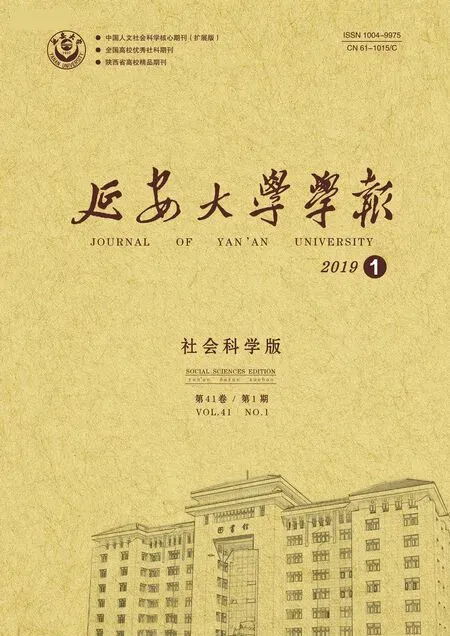宋代曲宴及其相关仪制考论
张志云,石佳翔
(延安大学 历史系,陕西 延安 716000)
宴飨亦作“宴享”,指称古代帝王宴饮群臣或国宾的活动。宋代宴飨种类众多,从举行场合、参与者身份及规模来划分,主要分为大宴、曲宴、节日赐宴和赐进士宴等。宋代大宴是皇帝参与、规制最高的宴饮活动,其“不仅在殿庭陈设、座次安排、程序及用乐等方面设定了一定仪制,而且针对大宴违礼现象制订了相应的纠察弹劾制度”。[1]关于古代曲宴,也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然而对于宋代曲宴类型及其相关仪制等问题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注]张胜海考察了古代曲宴的由来及演进,并对宋代曲宴之私宴、非常设及常附有赋诗游赏等特征作了分析。参见张胜海《帝子设宴纳宾贤,赏花钓鱼赋太平——中国古代曲宴初探》,《学术探索》2005年第3期。李鹏则通过分析清乾隆皇帝御制紫光阁曲宴外藩诗来探讨乾隆移宴紫光阁之目的。参见李鹏《乾隆御制诗中的紫光阁曲宴外藩》,《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4期。。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古代宴飨及曲宴的概念、宋代曲宴的类别及相关仪制等问题加以考论。舛误之处,尚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宴飨及曲宴的界定
宴飨在古代是一种高规格的礼仪活动。《周礼》记载“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2]卷33《春官·大宗伯》此飨燕之礼是指古代天子招待四方宾客,举行食宴之礼。宋代之前的官方礼典诸如唐代《开元礼》未有“宴飨”的礼仪条目,直至北宋徽宗朝发生变化。徽宗认为“宗室亲王在岁时都参加赐宴,这便就是古代饮食之礼,应予制定相应礼仪”[3],故礼官在修定《政和五礼新仪》时秉承徽宗旨意,在嘉礼之下始列“宴飨”之礼,但视其为宫廷礼仪,并不涉及下层百姓。明清礼典亦沿用这种分类方式,《明史·礼志》载“(嘉礼)行于朝廷者,曰朝会,曰宴飨,曰上尊号、徽号,曰册命,曰经筵,曰表笺”。[4]卷53《礼志七》清代礼典《大清通礼》在“嘉礼”之下也细分了众多宴飨之礼,其名目有“太和殿燕、慈宁宫燕、岁除燕、临雍燕、经筵燕、修书燕、凯旋燕、乡试燕、会试燕、恩荣燕、会武燕、燕衍圣公、燕外国贡使、王公燕等”。[5]卷37《目录》,16总之,在中国古代“五礼”体系中,宴飨属于嘉礼之一,它是一种行于朝廷的宫廷礼仪。换言之,僚臣、士人之间或者普通百姓举行的宴饮活动不能视为宴飨。
宋代宴飨主要有大宴和曲宴,此外还有时节赐宴。《宋史》记载:“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罢。”[6]卷113《礼志十六》,2683可见,宋代举行大宴的时间及场合多为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与八月)、皇帝或皇太后生日、郊祀或籍田礼结束、皇帝巡幸回京之时以及国家举行大庆之际,如果出现大灾大疫则会取消举行大宴。
古代“曲宴”最早指称规模较小的私宴。《资治通鉴》载:三国时期“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西平郭夫人有宠于帝,毛后爱驰。帝游后园,曲宴极乐。”元人胡三省将“曲宴”注解为“禁中之宴,尤言私宴也”。[7]卷70,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关于宋代曲宴,文献载“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设宴,惟从官预,谓之曲宴。或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则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预。暮春后苑赏花、钓鱼,则三馆、秘阁皆预”。[6]卷113《礼志十六》,2691此段文字先界定曲宴是皇帝和部分臣僚到苑池游览,或者观稼、狩猎之时,在所到之处所设之宴。其后又补充“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和“赏花钓鱼”之宴。由于“赏花钓鱼”宴是在暮春时节后苑举行,因此可以归于皇帝幸苑囿、池籞所设之宴。这段记载还表明,宋代不同的曲宴,参与的官员身份也会有所区别。
有学者对上引《宋史》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曲宴绝非设于宫殿之大宴、次宴或小宴,‘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不属于曲宴”。[8]其实,宋代曲宴也会设于内殿。史载,“建隆元年九月辛丑,(太祖)宴近臣于万春殿,后九日,又宴于广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无常,惟上所命”。[9]卷1,建隆元年九月辛丑,23这里不仅明确指出宋太祖在万春殿、广德殿宴近臣为曲宴,而且指出曲宴的一大特点就是其设置无定制,唯皇帝决断。此外,文献中多有“曲宴辽使于垂拱殿”[注]如《宋史》载,绍圣四年十二月甲申,曲宴辽使于垂拱殿。参见脱脱等《宋史》卷18《哲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9页。记载,这表明宋代曲宴确有多种类型。
二、宋代曲宴的类型
依据曲宴设置的场地及其功能不同,宋代曲宴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试分析如下:
(一)内苑赐宴
此种类型正是《宋史·礼志》提到的皇帝到苑池游玩或观稼、狩猎时在所到之处所设之宴。南宋赵昇在《朝野类要》中也记载,“有旨内苑留臣下赐宴,谓之曲宴,与大宴不同之义也”。[10]卷1赵昇把宋代曲宴直接定义为“有旨内苑留臣下赐宴”,显然有失偏颇,因为宋代曲宴还有其他类型,不过,这也说明宋代曲宴中,内苑赐宴最为常见。此外,《宋会要辑稿》记载大量喜雪宴、喜雨宴、观稼宴,此类宴会均可归于此类[注]参见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6—1743页。。此外,皇帝在行宫设宴亦属曲宴。如《宋史》载,“建隆元年七月,太祖亲征泽州、潞州,宴从臣于河阳行宫”。[注]脱脱等:《宋史》卷113《礼志十六》,第2691页。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建隆元年六月丁亥,车驾入潞州,宴从官于行宫。”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六月丁亥,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7页。
赏花钓鱼宴虽有固定的名称,但它也是皇帝与随从臣僚于后苑设宴,因此可将它归于内苑赐宴。《宋史·礼志》之所以把赏花钓鱼宴单独抽离出来与皇帝“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设宴并列,估计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曲宴时三馆和秘阁官员要参加。宋初沿袭唐五代之制,以昭文馆(唐五代称弘文馆)、史官、集贤院为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新建三馆,统称为崇文院。端拱元年五月建秘阁于崇文馆内,从此,三馆秘阁并列。宋初三馆秘阁是掌管禁中图书之府,编书、校书、读书之局,储养名流贤俊、备咨询访问之地,培养两制、执政乃至宰相等高级官员之所。[11]其二,赏花钓鱼宴从太宗雍熙二年设置以来,每年都举行,形成定制。史载雍熙元年三月乙丑,宋太宗召宰相近臣于后苑赏花,太宗曰“春风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这便是宋代赏花赋诗的开端。[9]卷25,雍熙元年三月乙丑,567雍熙二年夏四月丙子日,太宗“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9]卷26,雍熙二年四月丙子,595可见宋代赏花钓鱼曲宴始于太宗雍熙二年。宋代皇帝有时也会在曲宴亲自赋诗,如宋太宗很器重吕端,想让他做宰相。在一次后苑曲宴上,太宗作《钓鱼诗》,诗云:“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6]卷281《吕端传》,9515磻溪在今陕西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太宗此诗把吕端比作姜太公,用意在于擢用吕端。果不其然,数日后罢免吕蒙正宰相职位,以吕端取而代之。又如咸平三年二月晦日,宋真宗率近臣赏花并设宴于后苑,“帝作《中春赏花钓鱼诗》,儒臣皆赋”。[6]卷113《礼志十六》,2692
(二)垂拱殿宴辽使臣
宋代在垂拱殿多次宴请辽国使臣,在哲宗朝尤为多见。史载元祐二年秋七月戊午,“以辽萧德崇等贺坤成节,曲宴垂拱殿,始用乐”。[6]卷17《哲宗本纪一》,325元祐四年十二月庚子,“辽使耶律常等贺兴龙节,曲宴垂拱殿”。[6]卷17《哲宗本纪一》,330绍圣四年十一月甲申,“曲宴辽使于垂拱殿”。[6]卷18《哲宗本纪二》,349又元符元年二月,宋夏发生战事,知兰州王舜臣讨伐西夏于塞外;元符二年二月,鄜延钤辖刘安在神堆战败夏人。[6]卷18《哲宗本纪二》,349-351西夏接连上表,请求辽朝出兵,辽朝征集大军驻扎宋辽边境,作出大举南下之势,派萧德崇到开封劝和,并提出让宋朝将攻占西夏的领土,归还西夏。史载元符二年三月丙辰,“辽国泛使左金吾卫上将军、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副使枢密直学士、尚书礼部侍郎李俨见于紫宸,曲宴垂拱殿,其遣泛使止为夏国游说息兵及还故地也”。[9]卷507,元符二年三月丙辰,12075以上四次在垂拱殿宴辽使臣均为哲宗年间发生,且文献均记为曲宴[注]由此可见,陈戍国先生认为“‘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不是曲宴”一说值得进一步探讨。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然而尚存疑惑的是,《宋史·礼志》载“曲宴,或宴大辽使副于紫宸殿”。[6]卷113《礼志十六》,2691检索宋代文献,哲宗朝为辽国使副举行曲宴均设置于垂拱殿。史载:“大庆殿北有紫宸殿,视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拱殿,常日视朝之所也。”[6]卷85《地理志一》,2098可见宋代垂拱殿和紫宸殿尽管都用作皇帝视朝场所,但所处方位不同。
此外,还有一条史料可以佐证宋代接待外国使臣时于内殿设曲宴。宋真宗天禧元年十一月己亥,右正言、直集贤院祖士衡进言:“伏睹将相及远方使辞见,并于内殿特开曲宴,比至罢会,日已逾午。百司例各还第,而乘舆复御便坐决事,殆非君逸臣劳之旨。欲望自今曲宴特辍视事,著为令。”[9]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己亥,2085祖士衡指出,凡将相和远方使臣朝见或辞行,都会在内殿为他们举行曲宴。宴会结束已过正午,按惯例百官各回府第,而皇帝却要坐着轿子去处理政事,这有悖“君逸臣劳”的主旨,故请求真宗下令曲宴之后停止视事。真宗采纳了祖士衡的请求,并于当日下诏“曲宴日辍后殿视事”[6]卷8《真宗本纪三》,163,即皇帝在曲宴当日不必再到后殿处理政事。
(三)其他内殿赐宴将相或外国使者
宋代在将相或外国使臣见辞时会举行宴会,此类宴会应归于曲宴。此类曲宴包含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地方节度使来朝。如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十七日,“宴宰臣、节度、防御、团练、诸军指挥使以上于广政殿,以忠正军节度使杨信来朝”。[注]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第1711页。然《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建隆元年五月乙卯,宴近臣于广政殿,以忠正节度使、兼侍中杨承信来朝故也。”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五月乙卯,第16页。其二,地方或外国遣使朝贡或庆贺。如开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宴宰臣、见任前任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统军、侍卫诸军将校及外国使于广政殿,以江南、两浙、高丽、三佛齐皆遣使朝贡故也”。[12]礼四五,1712此外,《宋史》还记载“群臣朝觐出使宴饯之仪”[注]《宋史·礼志》将其列入宾礼。参见《宋史》卷119《礼志二十二》,第2800页。然《宋会要辑稿》将其列入“宴飨”。参见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第1765页。。北宋太祖、太宗朝,“藩镇牧伯,延五代旧制,入觐及被召、使回,客省赍签次酒食”。[6]卷119《礼志二十二》,2800即地方藩镇凡朝觐、被召见或者大臣出使回朝时,由客省负责赐予酒食,安排学士、皇亲观察使等官员参加宴会。史载:“故事,枢密、节度使、使相还朝,咸赐宴於外苑。见、辞日,长春殿赐酒五行,仍设食,当直翰林、龙图阁学士以上、皇亲观察使预坐。”[12]礼四五,1756此宴饯之仪到南宋中兴仍奉行,“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或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6]卷119《礼志二十二》,2801可见,宴饯之仪在两宋一直奉行,它不仅是一种接待外国使节的礼仪,而且成为古代帝王用来笼络重臣的手段。
(四)宋代修书宴、讲书宴、观书宴
宋代还有一类曲宴与修书、讲书、观书相关,且设宴地点不确定。
其一,修书宴。宋代承续唐代修史制度,设置修史院撰修《实录》《国史》,一旦修成,皇帝会赐宴修史官。史载:真宗“景德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赐监修国史、宰臣王旦等宴于修史院,以始事也”。[12]礼四五,1750可见,此为宋代首次举行修书宴。元丰五年七月,神宗“因《两朝国史》修成,宴于垂拱殿”。[6]卷113《礼志十六》,2693哲宗绍圣三年十一月,“以进《神宗皇帝实录》毕,曲宴,宰臣、执政、文臣试侍郎、武臣观察使以上并修国史官赴坐”。[6]卷113《礼志十六》,2694
其二,讲书宴。古代自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御前讲席,至宋代始称经筵,设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这是古代帝王接受儒家教育的主要方式。史载,宋真宗在听政之闲暇,命邢昺讲《左氏传》。“咸平五年正月二十日,宴宗室、侍读、侍讲学士、王府官于崇政殿,赐邢昺及侍讲夏侯峤等器帛,昺加袭衣、金带。”[12]礼四五,1750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经筵讲《论语》完毕后,“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帝亲书唐人诗赐之”。[6]卷113《礼志十六》,2693又绍兴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经筵讲《尚书》完毕。次日,高宗“赐宰执、侍讲、侍读、修注官于秘书省”。[12]礼四五,1751由此可见,南宋时期讲书宴依然奉行。
其三,观书宴。此处“书”不仅指帝王和名臣所撰文集,还包括书画、书帖等。史载,北宋“龙图阁四壁设五经图,阁上藏有太宗书帖三千七百五十卷”。[12]礼四五,1751咸平四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御龙图阁曲宴,诏近臣观太宗草、行、飞白、篆、籀、八分书及画”。[6]卷113《礼志十六》,2692此外,北宋国子监、翔鸾阁、天章阁、宝文阁等都藏有皇帝御书,因此北宋观书宴时常在上述馆阁举行[注]宋代观书宴在文献中记载截止到北宋仁宗时期嘉祐七年,估计是文献缺载所致。参见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礼四五,第1751—1753页。。
综上,宋代曲宴在设宴场合及设宴目的均有不同,但其主要特点是设宴并无常制,唯以皇帝决断而定,而且参与宴会者多为皇帝近臣或辽国使者。因此,其规模无法与宋代大宴相比拟。
三、宋代曲宴的仪制
宋代曲宴有多种类型,其仪制理应有所差异。然宋代文献对不同曲宴之仪制未有详尽记载,唯有徽宗朝大观三年,议礼局进上垂拱殿曲宴仪。其仪式依先后次序分列如下:
(一)皇帝降座入殿后阁
皇帝视事完毕,东上閤门呈上座次图。皇帝降座后,鸣鞭,皇帝入殿后阁。
(二)皇帝御殿,群臣贺拜、进酒
诸吏安排妥当,群臣班列齐备,皇帝出后阁升坐,鸣鞭。群臣分东西入殿庭,立定。班首上奏“圣躬万福”,就坐,再拜。群臣从东西阶升殿,至席前相向站立。閤门至御座前,奏班首姓名以下臣僚进酒。舍人引导殿上臣僚再拜,班首向皇帝进酒,奏乐,皇帝饮酒完毕。皇帝赐酒,群臣再拜。
(三)行酒、宣示盏、宣劝
初次行酒,先宰相后百官,均奏乐。由尚食典御和尚食奉御[注]尚食局,始于北齐,北宋初空存其名,元丰新制欲复其职,崇宁二年二月始建置,供御膳馐及品尝事,靖康元年罢。其官额有管勾官一人,典御二人,奉御六人,监门二人。参见龚延明编《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4页。进上食物。酒五行之后,如果宣示盏,閤门揖手称“宣示盏”,弯身唱赞就坐。如果宣劝[注]宣示盏大概是指饮酒过程中,宣明官员须站立出示酒杯,以示饮酒完毕;宣劝即为指皇帝赐酒劝饮。,百官则立于席后弯身饮酒。
(四)百官退出、皇帝降座
舍人引导百官走下台阶横向排列,分班退出。皇帝降座,鸣鞭。[注]此仪参考《政和五礼新仪》之记载,参见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卷201《拱垂殿曲宴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54—856页;此外,《宋史》也有相关记载,但远比《政和五礼新仪》记载简略。参见脱脱等撰《宋史》卷113《礼志十六》,第2694页。
以上诸仪式中,皇帝有先降座入殿后阁,然后又从后阁出、升坐的仪式,在此期间官员须班列整备。凡皇帝升坐或降座,均须鸣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观三年议礼局进上垂拱殿曲宴仪中并未记载赐花仪式,这是否为文献漏载,尚不得而知。但文献明确记载,宋代赐贡士宴有“赐花有差”“戴花毕”“谢花再拜”[6]卷114《礼志十七》,2712等仪式。
宴飨是古代一种行于朝廷的宫廷礼仪活动,其并不涉及僚臣、士人之间以及普通百姓的宴饮。从宴飨设置的场所及参与者身份、规模来看,古代宴飨主要分为大宴和曲宴,此外还有时节赐宴等。与大宴相比,曲宴不仅规模较小,其设置亦无定制,参与者多为皇帝与近臣或外国使者。在中国古代,宋代为曲宴之盛行时期。宋代曲宴多设置于宫廷内苑、垂拱殿及其他内殿,如皇帝到苑池游玩或观稼、狩猎时在所到之处所设之宴,包括赏花钓鱼宴;宋代在将相或外国使臣见辞时所举行的宴会,均属于曲宴。现存文献中详细记载宋代曲宴仪制的是北宋徽宗大观三年议礼局制订的垂拱殿曲宴仪,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君臣举行曲宴时的前后仪节以及尊君卑臣的内在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