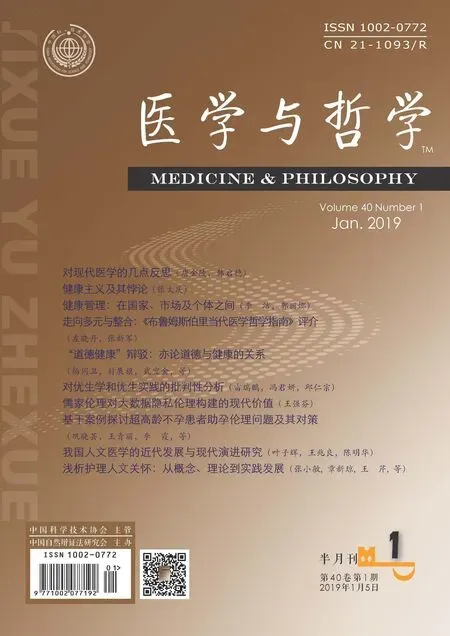我国人文医学的近代发展与现代演进研究*
叶子辉 王兆良 陈明华
医学的现代发展展现出科技进步对人类健康维护的强大现实支撑。特别是生物技术、基因技术、手术机器人的临床应用,推动医学实现对人类健康全过程、全周期的维护,却也存在着医患关系紧张、缺乏人文关怀、扭曲生命价值等伦理问题。人文医学的兴起发展是从最初的理念、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的新兴学科[1]。人文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先后经历先天不足、中西医的交互影响和回归本质发展的阶段,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现阶段人文医学发展的脚步,研究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探索人文医学的发展路径。现代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在最初的预冷、后期的火爆,其中也穿插着与本土中医的市场、政策支持、社会话语权的争夺,既有过废除中医的政治风波,也出现过西学中、以服务人民为背景的社会运动。
1 人文医学,现代医学传播中的先天不足
人文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存有先天不足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现代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并非是通过内生型社会科技发展促进现代医学诞生,而是外源性技术通过技术输入式的形式在我国传播发展,我国在清末民初时期并未形成或建立与之相配套的现代科学体系和社会环境。现代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存有“输入式”和“引进式”两种传播形式。输入式即外籍医生在国内执业行医,同时兼以传授知识和技术[2];引进式即中国学生前往国外学习现代医学技术后回国执业行医并传播[3]。无论是“输入式”还是“引进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技术与社会认知脱节的情况,即社会对现代医学的认知和社会意识的形象表达并非如西方现代医学发源地一般[4],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认知存在很好的良性互动,即医学中缺乏人文属性,这一阶段自现代医学传播以来为伊始到建国前。
现代医学在我国的发展是以技术为传播先导,作为现代科学体系的传入晚于医学技术应用在国内的开展,最初作为“奇淫秘技”的现代医学产生了颠覆传统认知的社会性恐慌[5]。相比较于我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有着治疗效果更佳等优势,但在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社会认知中,是以一种“技”的形式存在。在“技”的认知社会背景下,现代医学的发展传播也仅以技术传播的形式展开,在其传播伊始便存在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理论支持系统,特别是缺乏西方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伴随之发展的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哲学,即扎在现代医学头上的“紧箍咒”。兼具传教士身份的医生和医学教育者们在进行技术传授的过程中,难以在东西方文化背景差异的情况下有效地将医学本身的人文精神内核进行传授。同期中国的留学生在西方学习现代医学的过程中同样存在重技术轻人文的潜意识。
现代医学的外在规范和社会共识规范形成是在一个长期的科学与愚昧的互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这种外在的人文性、社会性规范是针对医学科学技术可能存在的恶而产生的[6]。医学的传播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规范话语体系,因现代医学相较于传统医学有更为明显的治疗效果,进而医学在身体控制和疾病治疗方面形成了绝对的话语体系[7]。
20世纪初的现代医学,在传入我国的伊始已经是几乎接近成熟的科学技术,能够有效维护人类群体健康、延长群体生命、保护人类免受传染病的袭扰。早期的医学教育培训并未有与之相适应的人文理念进行传授,国内最初的现代医学高等教育的发轫多是以教会医院为基础的师徒传承制的形式展开的。“医学救国”的口号更是将技术作为核心理念深入留学生的内心。“医学救国”是近代以来对医学的社会意识,认为可以通过对机体的技术性帮助实现国人强健和国家富强。同时现代医学的发展传播过程中存在以否定中医的形式推动现代医学走进社会和为民众所接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医存废之争”亦是一种重技术轻人文侧面的反映[8]。
在存有先天不足的情况下,人文医学的早期起步与发展,从最早的协和中文部诞生开启人文医学与医学人文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作为现代医学人文反思的开端[9]。医学法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史等医学人文课程和研究在医学院校的引入,开始推动人文医学在我国的发展。对医学的认识初步从技术的单一狭窄视角转换到相对更为全面、带有人文属性的视角后,医学科技的发展表现出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人文医学在经历民国时期的发轫后,遭遇了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战争、动乱都给医学人文前进的脚步带来新的坎坷。
从历史的轨迹来看,医学的发展传播、推广呈现出的是不可逆的历史时代潮流,这种潮流下却也存在有社会的盲目认同和不分主次的接受。医学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专业化的精进,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性规范脱节。
2 政治推动下的人文医学发展
建国以后,人文医学的传播与发展主要体现在“西学中” 和“医学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等政治运动中,同时因为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对医学全过程的参与,进一步推动了人文医学的发展。
初期在全国卫生政策的道路选择上存在对中医有失偏颇的方向,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同志做出西医应当向中医学习的指示,“西学中”运动,客观上推动了人文医学的发展和医学人文理论的提升,其关键在于通过“掺沙子”运动安排中西医工作者一同工作学习,实现将中医的人文精神和思想带入到西医中去。这弥补了现代医学在我国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先天不足。
建国后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依旧存在重要的问题,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便是体现,即医疗卫生资源发展的分布不均和城乡差别较大,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并未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维护,这显然与党和国家的人民群众路线相违背。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并为人民群众服务,医疗卫生发展亦是如此。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在医疗卫生体系内开展“医学应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政治运动,这客观上也进一步推动了人文医学发展和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本土化。
在院校教育中,马列主义教研室实现在国内医学院校全覆盖,党、团、工会等政治组织也以不同形式进入到各类医疗机构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入到医学临床实践中,人文的脚步以另一种形式进入到医学教育体系和临床服务中。现代医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中人文的脚步以别样的形式重新进入了医学的视野,相比较于西方医学人文发展中的生命伦理学、叙事医学等学科的兴起和发展,以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将医学的科研和技术运用落在“实用主义”的范畴,即以中国现有技术实现对所面临问题的最大限度解决。同时,以政治视野看待中国医疗问题,实现以为人民群众服务、“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医疗服务精神在医疗行业的传播,实现政治通过医学对人实施关怀,实现政治人文关怀和医学人文关怀的结合,推动人文医学的实践发展。
与同期西方国家的人文医学发展相比,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在学科交叉与社会思潮的影响下,人文医学发展在20世纪中叶实现了“从静水流深到涟漪漾起”的转变[10]。
3 回归应有之路的人文医学与多元化发展
人文医学在我国近代现代医学的传播发展伊始所存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回归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应有之路。医学有着自身固有的边界,医学应当在求“真”的同时更应该求“善”,这其中的“善”便是医学的人文[11]。新时代人文医学的发展进步与医疗卫生政策的推进,医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在逐渐增大,已经由“治病救人”拓展到“健康中国”的更广阔的天地,人文医学的发展也应抓住人文的本质顺应时代的潮流实现多元化拓展。
3.1 回归应有之路
改革开放后,中断数十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再次开始,在医学科技发展和临床技术应用等方面中国再次认识到东西方的差距,要注重技术的引进和人员的交流。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逐渐走向深入,西方的第二波医学人文研究成果也逐渐被翻译到国内,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思路的引入,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医学的人文属性和人文医学的发展影响现代医学的发展和社会接受。我国学者也在认清差距后积极加入到第二次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浪潮中,1979年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以及《医学与哲学》杂志的创办,呈现出内生型发展与外源性输入并存共荣的局面。
人文医学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为其带来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医学人文课程在医学院校的增加,人文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在几所高校做了尝试,人文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为人文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也将人文医学的研究学者逐渐凝聚起来,形成学术合力推动人文医学的理论发展。与此同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中增加了人文执业理论考核内容,近年来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也要求将人文执业和医学人文的内容融入培训的全过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医学为人服务。
课程的增加、考试内容的增加、培训过程的重视,这一切都是外在的形态变化,在逐本溯源的过程中推动人文医学的发展。逆专科化的临床学科设置让患者的就医过程不再只是单纯的“治病”,转而是以人的机体康复为重要目的,将人放在临床治疗中的首要位置,实现医疗全过程服务于人的健康。
人文医学的发展推动医学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建设,其中最关键的依旧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对医学最迫切的要求才是真正关怀人的医学。人文医学的理论发展与中国的医学发展实践相结合,同时也受我国卫生政策发展所影响。人文医学的理论发展回归学科发展的规律,却也面临着医药卫生体制变化的不确定性,呈现出发展的艰难性。
人文医学发展中理论的宏大叙事与现实的执行无力彰显出人文医学的发展过于注重理论,进而忽视理论应与实践相结合。纵观理论研究,从一线临床护士到高校理论教师都在谈人文医学与医学人文,却未将人文如何走进医学、走进临床,如何推动医学服务模式的改变作为问题。如同近年来临床实践所面临的“博士不会看病”的尴尬境遇一样,人文医学也面临着“空谈”的问题。人文医学的发展更多地需要推动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能够理解医学的人文性,将人文医学的发展融入到临床实践中。人文医学的发展只是医学人文性展现的外因,关键在于将外因传导作用于实践医学的个体中,并改变现有的医疗服务模式,真正做到以人为中心。
3.2 人文医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向
医疗行为从传统医学的熟人社会和家庭医疗方式逐步转变为具有统一标准的工业化社会形态,流水线作业式的医疗模式逐渐呈现出将人的个体独立性融入到社会化生产的群众中。
人文医学发展最直接的目的即是人的健康,延伸的发展就是机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并存,同时以“治未病”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文医学是融入在医学中的人文价值,是在具体实践中从医务工作者的个体劳动中呈现出的群体效应,即医学为人的健康存在服务发展。人文医学理念的提出呈现的以人类社会在面临医学所支配的话语体系中要求医学的发展应当更尊重人,其发展更是以话语体系展现关于文化和价值的思考。健康中国事业的推进与人文医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交织发展形态,在医学深度参与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人文医学的发展应更好地推动医学在融入社会日常的过程中保持决策的被动性,即保持人的主体自觉性。
人文医学的发展同时,国民经济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社会大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从基本机体健康转变为对生命质量的追求。伴随医学快速发展的还有不断扩大的疾病谱系和复杂疾病的发病率,受医疗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水平发展不充分,居民在某些程度上获得的医疗照护并未呈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提升。在现有条件下医疗服务资源将被最大化地利用,实现对人民健康的最优服务,人文医学发展的道路依旧漫长且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