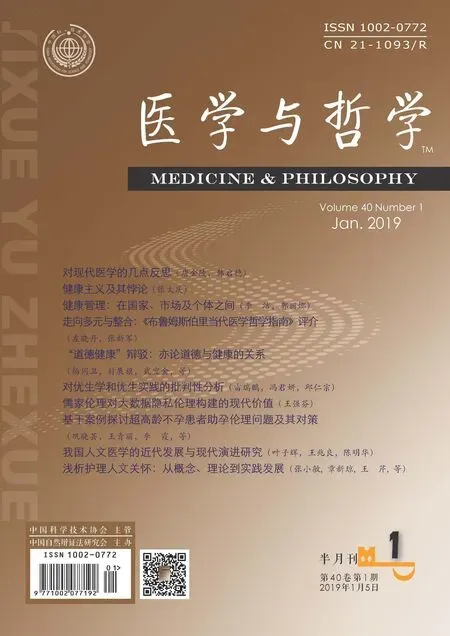无创产前DNA检测中“滴血验子”现象的伦理思考
肖葛根
无创产前DNA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技术是直接抽取孕妇外周血,提取胎儿游离DNA,通过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评估胎儿相关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的风险。目前该技术广泛应用于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可筛查胎儿罹患21-三体、18-三体、13-三体风险。同时NIPT技术可检测性染色体X和Y的数目,因此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违法进行“滴血验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易忽略伦理相关问题[1],另一方面“滴血验子”的确会引发一些伦理问题,因此本文从伦理学角度做如下思考。
1 NIPT技术应用现状
全球出生缺陷发病率约4%~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近800万[2],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约90万例[3]。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的重要环节是产前筛查和诊断,在NIPT技术应用之前,临床上一直采用血清学、生物化学检测方法和超声影像方法来进行产前筛查,导致部分高风险孕妇做不必要的侵入性诊断,绒毛穿刺或羊水穿刺诊断是有创性的、有流产风险,且多数孕妇心理上抵触这些侵入性诊断。而NIPT技术的出现使侵入性产前诊断的孕妇数量大大下降,减轻了有创性产前诊断的压力。
NIPT技术曾被认为是没有“准生证”的产前检测技术,由于高敏感性、高特异性,从而具备准确性较高、无创、高通量等优点,有极大的市场诱惑。1997年,香港中文大学卢煜明在孕妇外周血的血浆中发现了胎儿游离DNA片段,自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寻找诊断唐氏综合征等遗传病的新方法[2]。2008年,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孕妇血浆游离DNA测序和定量分析,提示可检测胎儿唐氏综合征。2011年之后,全世界陆续开展NIPT技术,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能够提供此项服务。2015年初,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了一批产前诊断试点单位开展NIPT技术;2016年10月,为推动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满足广大孕妇对产前筛查与诊断分子遗传学新技术服务的需求,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文废止了此前的试点机构相关规定;规定开展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产前筛查与诊断采血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当为有资质的产前筛查或产前诊断机构,收紧了此前没有产前筛查或诊断资质机构的样本采集,具备产前筛查资质的机构将成为唯一的收采样渠道。
NIPT技术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大幅提高了21-三体、18-三体、13-三体综合征的检出率,降低了染色体异常缺陷患儿的出生。在有效避免出生缺陷发生的同时,降低了有创性产前诊断带来的风险,提高了出生人口素质。在降低出生缺陷的同时,NIPT技术应用也为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近两年,“滴血验子”新闻受到各大媒体关注,一些农村家庭并没有违反婚育政策,结婚怀孕生子都在常理之中,但不少人在怀孕后选择了堕胎,在当地看来非常反常。究其原因是这些人都收到一份快递,检验结果是血液中未检出Y染色体DNA物质。从警方公布数据可见:“滴血验子”现象涉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5万多人次,涉及金额达2亿元,涉及人员近100人[4],这些非法中介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地下产业链。
近些年,通过严厉打击,非法黑B超情况越来越少见,而“滴血验子”现象又使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有所抬头,这是典型的NIPT技术滥用的结果,通过抽取孕妇少量外周血,检测是否存在Y染色体,鉴定胎儿性别,是违法的。这种现象的直接后果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增高、妊娠堕胎率增加等。由于我国明令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中介为了经济利益,便采取“曲线”策略,介绍孕妇抽血运送到境外鉴定胎儿性别。对于那些存有重男轻女观念的夫妇,不惜花重金进行检测,一旦收到未检测到Y染色体的报告,就选择堕胎。
总之,目前NIPT技术在产前临床的推广应用已经显示出其优越性,但如果监督与管理滞后,则可能引起更多的伦理问题。
2 NIPT技术检测中“滴血验子”现象的原因分析
2.1 重男轻女观念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一种社会事实只能用另一种社会事实来解释。”[5]“滴血验子”现象之所以存在,体现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存在,甚至在很多人观念里还是根深蒂固。因此,想生男孩的夫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在孕早期利用非法B超鉴别,现在就直接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NIPT技术去做胎儿性别鉴定,这也给非法开展胎儿性别鉴定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重男轻女是传统的男权思想在作祟以及当前社会现实的映照,男女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生育、教育、社会与家庭地位、婚姻等多方面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主要影响因素有传统社会生产、历史文化传统、家族人口等社会客观条件等。特别在农村,重男轻女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其背后隐藏的还有养老问题。俗话说:养儿防老,这种思想也许在现代的年轻人中可能有所淡化,但是在农村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几千年传下来的思想仍根深蒂固,生育儿子仍然是家庭育龄夫妇的第一追求。要消除重男轻女的思想,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问题,特别是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让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适宜的养老保障,才能逐渐消除独生子女和双女户家庭的后顾之忧[5]。如果养老得到保障,或女儿也可养老,社会多方面支持,使老年人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们逐渐会认可生男生女都一样。除养老外,在对女孩教育、就业等方面寻求性别上的公平,才能改变现状,使老百姓真正认为:生男生女都一样。
我们要看到重男轻女的现实和文化土壤,传统与现实相互依存,如果现实没有改变和革新,文化上的偏见只会越来越深。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光从文化思想上做工作,还要让人们看到生男生女的确一样的现实。让男女平等不只是成为口号,更应成为每个公民从心底里认可并且遵从的社会准则,让“滴血验子”现象终结。
2.2 利益驱使的诱惑造成了违法的真相
国家一直明令禁止胎儿性别鉴定,通过严厉打击,非法黑B超的情况越来越少见。而随着NIPT技术的出现,为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高额利益的诱惑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利用“滴血验子”,获得高额回报,甚至形成了一条黑色产业链。
NIPT技术开发以来,初期只是在科研水平,而不用于临床筛查与诊断。国家对该技术的监督与管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空档,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干违法的事。因国家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因此这些不法分子就辗转将样本送到境外进行检测,利用当前的网络、物流快递业务来实现远程检测与报告发放,当然这些也是违法行为。杜绝“滴血验子”现象,需要严厉打击进行此类检测服务的黑中介,斩断黑色产业链。
2.3 监督管理的滞后导致了客观的现实
医疗新技术是医学科学发展的产物,其临床应用有利用于提高人们防治疾病的能力,但在新技术应用之初,可能存在医学技术的监督与管理滞后[6]。事实上,新技术的出现,行业约束没有规则,可能出现监管空白或不知道如何监管的问题,最终造成很多乱象。“滴血验子”现象一部分原因就是NIPT新技术发展之初,监督管理滞后导致的客观现实。
“滴血验子”现象还体现了卫生监督不到位。有研究提示农村卫生安全形势严峻,卫生监督存在着体系不健全、投入不足和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7]。我国实行的是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县级卫生监督机构的组织建设、人员配备、资金投入等方面都较为薄弱,而乡镇级和村级卫生监督机构的模式并不健全,很多乡镇没有独立的卫生监督机构,卫生监督不受重视,导致乡镇的农村卫生监督只能流于表面。为了彻底将“滴血验子”等现象杜绝,除加强执法人员的监督外,发动群众相互监督、举报、奖励等机制,加强乡镇与农村卫生监督,将减少这些违法行为,为规范开展NIPT技术提供更好的环境。
自2011年NIPT技术在临床应用,到2016年10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规范》经历了五年时间。NIPT技术由于其优越性,加上部分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在临床上快速发展,成为没有“准生证”的产前检测技术。2012年原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对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临床应用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包括配套设备注册问题、临床应用准入问题、临床应用监管问题等。2014年又开展了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试点。2016年10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发文对开展无创产前筛查和诊断的医疗机构和人员做出了新的规定。在这5年中,部分医疗机构存在夸大宣传、滥收标本、未取得相应资质违规开展检测等,甚至存在非法性别鉴定“滴血验子”等现象。
针对NIPT技术,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文件明确指出属于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范畴,按照国家《母婴保健法》《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中的分子遗传项目进行监督与管理;明确归属于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监管,要求切实履行职责,保证NIPT技术在临床的规范应用。对非医疗机构和非医务人员开展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采血或检测的,按照非法行医进行查处;对不具备资质开展该技术采血或检测的,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近期,各省(市、区)逐步转发国家文件,出台相关通知,规范各地区NIPT技术的应用。加强管理,规范NIPT技术在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的应用;增加普法宣传,打击违法行为,同时更要斩断产业链背后的重男轻女观念。对此,不仅需要加强宣传教育,还可采取对生育女孩的家庭予以奖励、鼓励孩子随母姓等措施[4],标本兼治,不能让落后观念得以在高科技的助力下“高效”地阻碍时代发展,坑害我们的时代与未来。
2.4 网络渠道的扩展加速了信息的传播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化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刘少杰[8]认为网络空间的无边界性、信息流动的迅捷性和网民参与的便利性,都使网络空间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参与具有更广泛的辐射性和深入性。一旦某事件在网络中引起关注,数以万计甚至数以百万计不同身份的网民,超越位置和环境的限制,迅速形成网络关注兴奋点,甚至结成网络共同体,通过信息交流和观念沟通,进而引发实际社会行动,证明了网络空间的广泛传递效应和对实际行动的强大动员能力。
“滴血验子”的新闻被曝光后,调查人员发现很多孕妇在怀孕8周~9周就做了人流,这种趋势发展得非常快。分析其中原因,“互联网+”加速了相关信息的传播。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招募相关业务人员,按样本量提成,而自己躲在幕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分成。希望生育男孩的夫妇,通过网络、微信朋友圈能够快速传播,只要有一个人实现了“滴血验子”,很快就能在朋友圈传出去,相关的夫妇就会是下一个“滴血验子”者。
3 “滴血验子”现象的伦理学思考
3.1 干扰自然出生人口性别比
出生人口性别比关系到婚姻家庭、社会经济发展、卫生决策等问题。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必将使婚姻年龄段男女人口比例失调,直接影响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人口性别比偏高形势仍严峻,虽然从2010年的117.94到2015年的113.51,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稳步下降[9],但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一定程度后,继续下降的难度加大,同时由于 “滴血验子”等新情况的出现,非法性别鉴定更加隐蔽,查处监管更难。
NIPT技术能够对部分染色体异常遗传病进行筛查,使侵入性产前诊断孕妇数量大大下降,同时依据该技术的“滴血验子”现象也给想生男孩的夫妇提供了更新、更准的技术,越来越多的夫妇加入这个行列中,在收到未检测到Y染色体信号报告后,直接引产,直到生育男孩为止。这种DNA检测技术,使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极大提高,遍布城乡的服务网点和低经济成本,使性别选择具备了高技术可行性和易获得性,使一些家庭将男孩偏好付诸行动,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0]。因此,社会各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杜绝“滴血验子”现象的继续。
3.2 妊娠堕胎率增加
“滴血验子”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妊娠堕胎率增加,这也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堕胎涉及胎儿生命权也是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国内外对胎儿生命权有更多的争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生命的权利始于出生,因此胎儿不享有生命权。人工流产作为一种辅助的节育措施,对我国严格施行的计划生育来说,的确是有效的办法。而事实上,人类胚胎已经是一个活生生、可辨别的有机体。
现实“滴血验子”夫妇只想着生育男孩,后续的及对社会的影响往往被忽略,例如,堕胎可能直接导致不孕不育。流产可能直接改变女性子宫、内分泌、免疫等生理状态,使女性再次怀孕失败或不能怀孕的几率大大增高。而事实上,NIPT技术并非100%准确,无创产前检测与染色体核型结果并非完全一致[11]。NIPT检测孕妇血浆中胎儿游离DNA片段主要来源于胎盘,并非胎儿本身;NIPT检测的结果还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有假阳性或假阴性的可能。也就是说“滴血验子”报告显示未见Y染色体信号,而引产的可能是男孩,这样的结果对育龄夫妇打击更大。因此,加大宣传力度,使育龄夫妇认清该技术的局限性和准确用途,通过正规渠道合理利用NIPT技术。
3.3 患者的知情同意选择
真正的知情同意取决于患者对技术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掌握更多的、可靠的、准确的信息,了解对自身的影响及检测后的处理方案等。而NIPT技术的应用对真正的知情同意选择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首先,NIPT技术在全球临床实践的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人们对NIPT技术的理解和掌握,甚至有部分医生也仅仅知道其对21-三体检出率较高,更不用说患者能真正的知情。曾经有专家认为,将NIPT技术的应用归结为高风险害怕产前诊断的孕妇,或血清学筛查临界风险的孕妇等相关指征,而临床实践中则应用到更多的患者,包括低风险患者。另外,从NIPT技术的最初应用有假阳性的可能,到后来发现该技术受孕妇自身等多种条件影响,可能会出现假阴性的可能,这个过程经历大量样本的验证。因此,向所有患者知情交待全部可靠的和准确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12]。
其次,对NIPT技术真正知情同意选择的另一个挑战是检测者(包括商业操作的公司或医疗机构)没有向患者提供相关的宣教材料,而是直接向患者提供知情同意书签字而已。有文献报道,多数孕妇在行NIPT技术检测前没有接受过关于唐氏综合征等相关信息准确材料和最新技术信息,只有29%的受访者在接受相关检查前,由产科医生提供了相关宣教材料;且接受的宣教材料很容易阅读,包括相关的图像和故事,能够指导其决定是否继续妊娠[12]。部分接受NIPT技术检测的孕妇,对相关知识不甚了解,对检测后的高风险或低风险怎么处理也不清楚[13]。而事实上,临床上的临时交待很难让患者做出自身最佳的选择。因此,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患者都需要对NIPT技术进行相关的教育,了解其可能的结果和局限性,以促进患者真正的知情同意选择。
再次,规范的遗传咨询对患者知情同意选择非常重要。一方面虽然NIPT技术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目前价格仍较高。而在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可选择的技术还有产前血清学筛查、羊水染色体产前诊断等。而这些技术都有一定的适应证,不同孕妇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应该知情选择。事实上孕妇对这些技术知情选择的前提是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才能做出自己意愿的选择。另一方面,遗传咨询医生对遗传病的严重程度及相关准确的信息,能减轻孕妇对孩子将来是否有残疾的担忧,并能正确选择是否终止妊娠。例如,性染色体非整倍体通常比其他染色体的非整倍体表型较轻,也比较常见;而医生在给患者提供孩子出生后信息时,可能有致病性的、发育迟缓或孩子正常表型的,就会使孕妇选择不同的结局。曾有病例报道:一个产科医生给怀超雌(47,XXX)胎儿的孕妇说“不是唐氏综合征,是另一种染色体异常”,这对夫妇没有再咨询遗传学专家,而是2天后终止了妊娠[12]。事实上,携带超雌染色体的女性表型正常、能正常生育,与正常人基本一样,孩子是可以出生的。针对这些遗传病的遗传咨询,多数产科医生可能不熟悉这些相关的遗传病咨询的指南,应该加大培训力度,或加强遗传咨询师职业的推广。
3.4 商业化问题
NIPT技术应用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的商业化问题。从前期技术发展上看,由于NIPT技术由个别公司掌握,公司以商业化模式运作,推动NIPT技术的临床应用,且在产前临床领域竞争尤其激烈。首先,商业化问题是直接追求经济利益。由于NIPT技术产前领域市场极大,越来越多的商业公司出现,深入全国各大小医院,宣传推广,导致NIPT技术应用混乱,使地下“滴血验子”事件很难避免。其次,商业化操作直接挑战患者真正的知情同意选择。关于NIPT技术的优缺点,最准确的信息掌握在相关公司手里。与相关公司相比,产科医生不可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检索和学习文献报道相关的NIPT技术的进展、优势、局限性等。部分公司推广NIPT技术,夸大技术优势,避免提及不利因素,加剧了患者真正的知情同意选择的挑战。
因此,学术组织或第三方机构应该积极开发公正、客观的相关宣教材料,使医生和患者真正了解NIPT技术的优势和局限性等各个方面,这样才能实现患者真正的知情同意选择。规范NIPT技术市场,加强管理与监督,避免商业化操作,实现NIPT技术更好地临床应用。
3.5 过度检测与追求“完美婴儿”
“滴血验子”利用的技术是NIPT技术,这个技术中涉及分子遗传学的基因检测技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子遗传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遗传病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可能导致人们对“完美婴儿”的追求热度增加。
在目前遗传诊断技术的基础上,个别夫妇为了追求“完美婴儿”,可能行多种遗传技术手段进行过度检测,只要遗传上不正常,就直接引产。事实上每个人在基因水平上都存在遗传变异的可能,最多达300多个缺陷基因,而携带缺陷基因并非都表现出有什么异常,可以正常生活生育等。例如,前面提到的超雌染色体异常的携带者,是可以正常生育的;还有部分染色体平衡易位携带者,临床表型也正常,这样的孩子是可以出生的。
因此,“滴血验子”现象提示,新技术应用的监督与管理应该加强或要有前瞻性预期,更多更新的基因编辑技术提示的追求“完美婴儿”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避免后续的管理滞后等情况。
3.6 未来儿童基因信息隐私
“滴血验子”现象还有一个可能的远期影响,即未来儿童基因信息的隐私问题。由于“滴血验子”采集孕妇外周血,提取外周血中胎儿游离DNA,来评估胎儿性别。而事实上,这个胎儿游离DNA包括这个孩子的基因信息。而孕妇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血被送到哪里,如果将来孩子出生,儿童基因信息基本没有隐私可言,有可能被一些公司利用。希望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既保证国家的遗传资源不流失,又能保证儿童相关信息的隐私。
总之,“滴血验子”现象是NIPT技术滥用的结果,而NIPT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表现出与伦理、社会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关系到临床合理地应用、关系到患者真正的知情同意选择等,通过政府、社会、临床医生、患者自身对NIPT技术的了解和掌握,避免技术滥用和商业化操作,实现NIPT技术在产前临床领域更好更快的应用,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