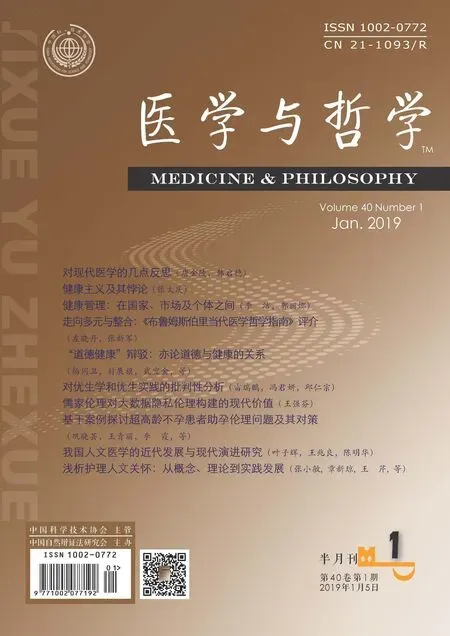基于案例探讨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伦理问题及其对策*
巩晓芸 王青丽 李 霞 腊晓琳 万晓慧 闫娟娟 艾海权
辅助生殖技术发展至今已经整整40年,随着这一技术的成熟应用与普及,越来越多的45岁以上超高龄不孕妇女来到生殖医学中心寻求医学帮助以期达到生育目的。然而45岁以上超高龄妇女要求助孕可能有多种原因,如各种原因导致适孕年龄错失良机、想生二胎已高龄等,但更多的可能来自失独、重组家庭,因此这一人群的自身特点以及辅助生殖技术的局限,使得超高龄不孕妇女助孕过程中易引发伦理问题,本文结合笔者所在单位生殖中心的两个典型案例,探讨超高龄不孕妇女助孕的伦理问题,并寻求相应的伦理对策。
1 案例资料
案例1:患者张某某,46岁,无固定职业,初婚顺产一女(21岁,已订婚),再婚未孕7年,要求再生育。首诊见患者面容憔悴,头发已经全部花白,询问病史,患者诉再婚丈夫无子女,因再婚后未避孕至今未孕,夫妻感情不和,面临再次离婚;患者母亲为挽救女儿婚姻,将自己积攒多年的全部积蓄5万元交由患者让其来医院行试管婴儿助孕治疗;患者就诊后评估卵巢储备极差,双侧卵巢内未见明确窦卵泡,且自身患有高血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宫腔粘连;告知患者用自身的卵助孕成功率极低,建议放弃助孕治疗,但患者生育愿望极其迫切,要求接受供卵助孕治疗,已等待半年余仍然未找到合适的卵源。
案例2:患者张某某,49岁,某高中优秀教师,结婚20余年,独女去世后要求再生育,患者自诉女儿在大学毕业后保送至国外一所名校读研期间因抑郁症跳楼自杀,丧女后5个月放弃工作来医院就诊要求助孕治疗。就诊过程中明显的抑郁、焦虑状态,经检查卵巢储备功能差,双侧卵巢内仅见1枚~2枚窦卵泡,子宫多发小肌瘤,甲状腺功能异常,提示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建议放弃助孕治疗或者考虑供卵助孕,但患者坚决要求自卵助孕治疗。第一次助孕治疗获卵1枚,异常受精取消周期;第二次助孕再次获卵1枚未形成可移植胚胎再次取消周期,并向患者夫妇沟通建议终止助孕治疗,患者丈夫表示同意终止,但患者仍然拒绝,为此夫妻不睦。
2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现状
我国产科定义高龄孕产妇年龄为≥35岁,而≥45岁则为超高龄孕产妇;美国生殖医学会也规定,>45岁的女性在胚胎移植前必须进行全面彻底的医学评估[1];故本文中将超高龄不孕妇女的年龄暂定为≥45岁。目前超高龄不孕妇女助孕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2.1 迫切的生育愿望及负性心理导致助孕期望过高
寻求助孕的超高龄不孕妇女大多来自于失独或者重组家庭,在经历家庭变故后,出现明显的紧张、焦虑、抑郁甚至绝望的负性心理反应,她们一旦决定行助孕治疗,则生育愿望极其迫切,对助孕的期望值极高,但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不确定性又是造成女性心理压力的重要因素[2]。案例1中超高龄不孕妇女来自重组家庭,婚姻已经出现破裂征象,夫妻不睦已经影响到患者的身心健康,为了助孕,全家动员,不惜举债甚至花掉父母养老金,将助孕治疗作为挽救家庭、婚姻的救命稻草;而案例2中妇女深陷丧女之痛无法自拔,也将助孕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甚至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丈夫反目。这些均是严重的负性心理及过高的助孕期望值所致。
2.2 卵巢储备功能极差
卵巢储备功能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卵泡数量的减少:超高龄不孕妇女由于年龄及盆腔手术史的增加,卵泡池内的卵泡闭锁加剧。文献报道青春期时卵泡池内卵泡约为30万个~50万个,37岁时仅约为2.5万个,而到绝经时不足1 000个[3]。本文案例1卵巢已衰竭未见明显窦卵泡,而案例2也提示窦卵泡极少。(2)卵母细胞质量的下降:随着年龄增加,卵母细胞代谢异常,氧自由基等代谢产物积聚,细胞内纺锤体、线粒体老化加剧,线粒体内DNA发生突变或缺失几率明显增加,出现非整倍体几率明显增加,从而导致卵母细胞质量下降[4-5]。案例2中虽两次取出卵母细胞但均不能得到有效的胚胎。
2.3 身体机能及卵巢储备的下降使得助孕的风险和不良结局均明显增加
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极易引发各种疾病,研究表明高龄女性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子宫器质性病变风险增加。本文两个案例均存在子宫器质性病变及甲状腺功能异常,同时案例1中患者还患有高血压,这些生理机能的下降在助孕过程中不但增加助孕风险也可能导致胚胎种植失败,从而增加助孕不良结局。另一方面,由于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及卵母细胞质量下降,助孕过程中高周期取消率、低妊娠率、高流产率等不良结局明显增加。案例2中两次助孕均取消周期, Tsafria等[6]研究发现45岁时助孕妊娠率仅2.8%,而国内马翠娥等[7]发现43岁以上患者助孕活产率为0。
3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易出现的伦理困惑
3.1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需求和助孕现状的矛盾
生育权是女性的基本权利之一,女性可以自由决定何时生育,而且我国《婚姻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没有规定高龄妇女禁止生育。因此,超高龄不孕患者的助孕需求是合理合法的。但目前针对超高龄助孕的现状是由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及患者本人身体机能的下降,她们助孕治疗妊娠率低而流产率高,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以及更大的经济投入。而依据目前的医疗技术,即使大量的投入也无法达到满意的结局,案例2患者辞掉工作,两次助孕治疗前后历经数月,花费数万元,仍然连胚胎移植机会都没有,因此强烈的需求、过高的期望与助孕现状存在明显的矛盾。
3.2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对母代身心健康的影响
45岁以上超高龄不孕患者身体机能的下降,行助孕治疗时大剂量药物、激素等的刺激,加之手术和精神情绪的应激,使得助孕的风险明显增加,同时由于目前医学技术的局限,绝大部分患者最终仍然难免不良助孕的结局,大大增加了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如案例2中,两次助孕失败,不但未将该患者从丧女之痛中解脱,反而两次的挫折使患者的负性情绪进一步恶化,甚至有些偏执,无视医生建议,仍然要求无谓的继续;另一方面该患者群行助孕治疗即使成功,也属于超高龄孕产妇,孕产期易于出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等并发症。因此超高龄不孕助孕可能对母代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
3.3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对家庭及子代身心健康的影响
目前在我国,所有助孕治疗费用没有医疗保险,属于完全自行支付,加上超高龄患者卵巢低反应、低妊娠结局可能需要反复治疗,且治疗周期长影响工作,所以每一位超高龄不孕妇女助孕的背后都需要有强大的家庭和经济的支持。案例1中,虽多次建议助孕夫妇放弃治疗,但其仍然拒绝,甚至要求动用父母养老金行助孕也令医生面临尴尬。同时随着年龄增加,超高龄患者助孕成功后的子代先天畸形的概率明显增加,即使正常生育的后代由于亲代年龄因素导致的体力下降,从而出现个人生活自理能力、基本劳动能力等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可能不能很好地养育,因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也易于出现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及自闭症等精神疾病[8]。
3.4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后亲子关系对人伦和社会公益性的冲击
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成功后亲代均属于中老年得子(女),亲代子代巨大年龄反差的亲子关系有别于我们通常情况下的亲子关系,这种异于常情的亲子关系在日后抚养孩子及孩子成长求学过程中都会冲击正常的社会人伦关系。同时对于已有成年子女的超高龄助孕家庭,如案例1女儿已21岁,即将结婚生子,一旦助孕成功,亲代生育的子代和其成年子女子代的关系辈份等也会对于当下人伦关系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目前法律规定60岁退休以后属于社会赡养者,45岁以上超高龄助孕的子代在亲代满60岁时仍然未满15岁,仍然属于未成年人,他们也随着亲代的退休被推向社会赡养,增加社会负担,因此对当今的社会公益造成冲击。
3.5 超高龄不孕供卵助孕卵源的供需不平衡的矛盾
我国目前由于卵巢早衰以及高龄助孕的不断增加,要求接受供卵助孕治疗的妇女越来越多,就笔者所在单位生殖中心登记在册等待受卵的人就有近200名,有人已经等待数年,案例1也已等待半年余,可见卵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为避免卵子的商业化倾向,2003年我国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指出供卵助孕的卵源必须来自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周期中妇女的无偿捐赠,捐卵者年龄须≤35岁,其助孕治疗周期中需获得20枚及以上的成熟卵母细胞,同时保留至少15枚自用的前提下方可捐赠,因此各大生殖中心达到捐卵条件同时愿意无偿捐赠的人越来越少,而且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卵子库,所以卵源极度供需不平衡,这种卵源供需不平衡极其容易滋生供卵商业化,从而有违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伦理原则。
4 针对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的伦理对策
4.1 尊重超高龄不孕患者的生育权和助孕选择权
超高龄不孕患者的生育权受法律保护,她们的助孕需求合理合法,任何个人及医疗单位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为其实施助孕治疗;同时由于目前医学技术仍然无法克服的助孕治疗现状,对于超高龄助孕患者,在尊重她们生育权的基础上,必须如实告知助孕治疗的局限及不同助孕方法的利弊,充分尊重她们的助孕选择权。
4.2 加强对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过程的知情同意
由于目前超高龄不孕助孕的风险及不良结局明显增加,对于有助孕需求的不孕患者是否应该行助孕治疗,目前业内尚无统一意见;同时国内没有明确的助孕治疗的女性年龄的上限值,这无疑增加了临床医师诊疗难度,临床医师在患者助孕需求和预期的不良助孕结局之间矛盾徘徊。因此,作为医生必须在助孕过程中权衡各方利弊后加强知情同意,适时劝告患者及时终止助孕治疗或选择接受供卵助孕。
4.3 重视对超高龄不孕患者的心理疏导
本文两个案例均提示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前后的抑郁、焦虑及紧张等负性心理反应较强,她们对于助孕的期望值极高,有的甚至将助孕治疗作为挽救婚姻家庭的救命稻草,负性心理反应和助孕不良结局之间相互影响,而且形成恶性循环,对这一部分患者如不及时进行心理疏导,易于引发医患纠纷,将会给患者本人及社会造成影响。因此,在超高龄不孕患者诊治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4.4 完善针对超高龄不孕患者助孕的相关法规
超高龄不孕患者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助孕过程中易引发许多的伦理问题,因此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如超高龄患者助孕是否应该有年龄限制问题,法国规定43岁及以上患者不能在该国申请供卵助孕治疗[7],我国学者也建议50岁及以上患者不推荐行助孕治疗,包括供卵助孕治疗[1],目前针对这一问题仅有国内外的建议,业内尚无统一法规。另外,对于超高龄不孕助孕的供卵卵源供需不平衡问题也亟待相关法律规章及伦理法规监督。
总之,由于其自身特点及目前医疗局限,超高龄不孕助孕患者属于辅助生殖临床诊疗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易于引发诸多伦理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制定相应的伦理对策,进一步规范超高龄不孕的伦理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