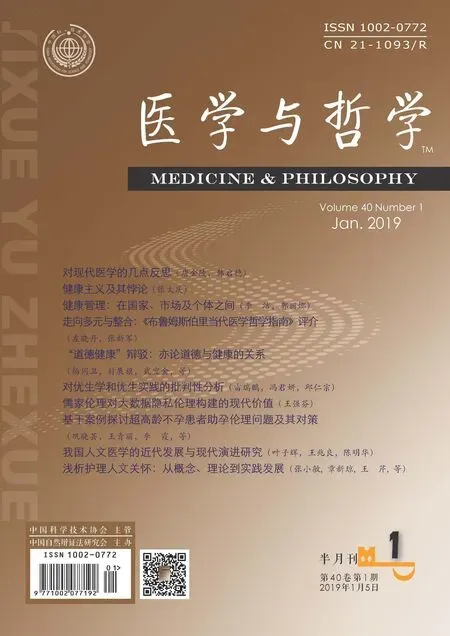走向多元与整合:《布鲁姆斯伯里当代医学哲学指南》评介*
左晓丹 张新军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是英国一家享有很高声望的学术出版机构,近年出版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系列指南,以其学术性和权威性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对学科知识的普及与推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布鲁姆斯伯里当代医学哲学指南》(TheBloomsburyCompaniontoContemporaryPhilosophyofMedicine)(以下简称《指南》)自2017年出版以来,在欧美医学哲学研究及教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部书的主编詹姆斯·马库姆(James Marcum)是哲学和生理学双博士,现任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生物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哲学、科学史和医学史,著有《医学哲学概论:将现代医学人性化》(AnIntroductoryPhilosophyofMedicine:HumanizingModernMedicine)和《大医精诚:美德在医学中的作用》(TheVirtuousPhysician:TheRoleofVirtueinMedicine)。
医学哲学是一个充满活力、争议不断、与时俱进的学科。《指南》概述了医学哲学的前沿问题、研究方法以及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收录的文章均由该领域的顶尖学者撰写,阐述了当今医学哲学面临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挑战,如循证医学和以人为中心的医学(person-centered medicine)、医学人文、性别医学之间的争议,乃至疾病、健康、临床推理和临床决策等经典论题。该书兼具实用性和前瞻性:不仅附有研究资源的详细指南、关键术语的简要解释、核心文献的注解说明,而且还概述了各种研究方法,讨论了现代医学发展所产生的新的研究方向。《指南》围绕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医学问题,阐述了医学为哲学发展所提供的学科资源以及哲学为医学争端所提供的思辨视角。
1 内容简介
《指南》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编为“导论:医学哲学、研究问题与方法”;第二编为“当下研究与未来方向”,第三编为“研究资源”。
第一编导论部分由两篇文章组成。马库姆(Marcum)“导论:当代医学哲学”介绍了当代医学哲学的学科背景和本书的框架。马库姆[1]开篇即表明:“现代医学就其本质与实践而言是多元主义的,《指南》旨在反映这种多元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医学本质的逻辑理性解释与人文叙述,在医学实践上则有循证医学与以患者为中心医疗,反映了不同的哲学视角。20世纪医学中的科学与艺术之对立演化成了循证医学和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之对立,此外,还产生了分子医学与基因组医学、流行病学、进化医学。为克服医学对科技的沉迷,医学人文倡导患者作为人、医生作为人的观念转型。文章还简述了书中没有包含的一些领域:整合医学(integrative medicine)、分析医学、叙事医学等。迈克尔·洛林等所撰“医学哲学中的研究问题与方法”考察了为认识医学多元主义而采取的哲学方法(如逻辑分析、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现象学等),分析了这些方法背后的形而上预设及本体论承诺,讨论了过去几十年中旨在改变“通常做法”的几种尝试,如循证医学、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基于价值观的实践等。文章认为当代医学哲学的目标是能否让关于医学多元主义的持续讨论变得茅塞顿开、富有成效。
第二编是《指南》的主体部分,共13章,按内容可以分成三个模块:医学作为科学(4章)、医学作为人文(5章)、专题研究(3章),最后一章描述了医学哲学中的新方向。
“医学作为科学”部分有4篇文章。玛丽安·博恩林克“基因组医学和分子医学时代的疾病”综述了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遗传学的思想变迁,讨论了这些变化对疾病概念的影响。经典遗传学认为特定疾病与基因的关系是确定性的和单一因果式的。这些假设后来引起争议,人们开始聚焦基因发挥功能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基因组医学),认识基因和临床效果之间的关系(分子医学)。这是源于疾病从本体论概念到疾病作为过程的观念转变,作为过程的疾病可通过生物标志物进行量化,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同健康区别开来。表观遗传学和系统生物学的进展深化了对社会和环境影响基因表达的认识。
亚历克斯·布劳德本特“流行病学哲学”介绍了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总结了所提出的主要哲学问题。第一,流行病学在对抗疾病的单一因果理论方面发挥了历史作用。流行病学涉及到许多疾病的多因素性质问题,总体上完善了医学中的因果主张。第二个问题是对各种流行病学测量(measure)进行因果阐释,如“归因风险”通常是凭直觉做因果解释,但可能会导致非直觉的荒诞结果——如肺癌导致吸烟。第三个问题是流行病学结果(如果有的话)何时能够证明因果推论的合理性。
杰里米·豪威克“为循证医学认识论辩护”综述了与循证医学相关的认识论问题,认为循证医学背后的认识论是合理的,提出了三个方面的主张:比较试验总体上优于观察证据、病理生理推理和临床经验。循证医学的认识论合理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随机试验优于观察性试验,主要是消除各种偏见;其二,夸大了机制证据在建立因果关系、将结果应用于个体患者、产生假设方面的作用。
迈克尔·鲁斯“进化医学的哲学层面”提出进化论可以与医学实践相关联,如对身体过程或症状的进化解释可能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如发烧之类的症状,进而影响对治疗是否恰当的判断。然后,鲁斯提出了进化医学的两个主要哲学问题:自然选择有多大的解释力,应该如何在群体或个人层面理解自然选择。
“医学的艺术或人文方面”有5篇文章。阿尔弗雷德·陶伯“医学人文:哲学与历史基础”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了医学作为科学事业和作为人文事业的分离,考察了医学的科学观和人文观何以通过一系列重大文化和知识变迁而分道扬镳,如科学因专业化而变得与哲学泾渭分明。
莉迪·菲奥罗娜“医学人文:二十世纪的启示”考察20世纪日渐充斥人们生活的医疗干预和监控,导致了患者的客体化、非个性化、碎片化。医学技术的进步强化了医学的权力,新的医疗体制程序改变了医学的本质。技术的发展没有把患者看作遭受痛苦的主体、忽视了医学实践的内在伦理性质。菲奥罗娜讨论了抵制这种趋势的哲学资源,尤其是通过现象学把人理解为具身的(embodied)、社会嵌入的、时间性的存在,可以在痛苦中寻求意义、在他人的痛苦中寻求伦理需求。
弗雷德里克·斯韦劳“现象学与医学”进一步证实了医疗实践需要承认和回应患者作为整体的人的痛苦,而不仅仅是作为疾病的载体或需要治愈的风险状态。他援引萨特、梅洛·庞特和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道,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看,疼痛和疾病的产生不是孤立的体验,而是体验本身的性质转变。疾病可能阻碍并因此改变人的具身体验,扰乱生活目标和计划,最终改变个人身份。现象学思路提供了多种方式来理解疾病的意义以及生活中的意义产生过程。从现象学的角度看,理解疾病如何改变患者的生活世界以及如何在其处于不自在状态下帮助他们是医学的必要组成部分。
塔尼亚·葛格尔“性别医学与现象学具身性”总结了性别成见在诊断和治疗中的各种作用方式:特定疾病有时被刻板地认为更可能发生于某个性别,这可能与诊断率、诊断时的疾病阶段和治疗决定有关,女性的身体疾病更容易被误诊为精神疾病。有些问题可能与研究中缺乏女性参与者有关,这背后是因为男性身体构造被视为基本标准,女性生命阶段的医学化是一种把女性健康主要视为生殖健康的观念。现象学资源尤其是具身性理论,为思考身体与伤害、质疑规范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马库姆“以患者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中心能维系吗”首先评述了以人为中心和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批判其轻视医生作用的倾向以及破绽百出的自主性概念,考察了其定义以及所隐含的本体论和伦理主张。马库姆认为,尽管这种方法很有价值,但还没有提出对“人”这一中心概念的恰当理解,而“人”这个概念足以证明以人为中心的医学是合理的,并可用于实践。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马库姆借鉴医疗人格主义(personalism),将人视为关系性的、具身性的和社会性的,这样才有助于减轻痛苦和恢复临床中的尊严。
“专题研究”部分有3篇文章。蕾切尔·库珀“健康与疾病”梳理了围绕健康和疾病概念的广泛争议。紧扣功能概念解释了自然主义观点,盘点这些观点在参考类和异常概念方面存在的问题;清理了规范主义的一些变体,指出其对伤害的不同理解,以及除伤害之外对疾病所必需的其他标准的不同立场。然后讨论了试图重构概念或重设争议的一系列新兴观点,以及与第一人称体验、风险因子医学、医学化等作用相关的新问题。还探讨了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区分问题。
布兰登·克拉克和费德丽卡·拉索“医学中的因果”介绍了问题背景,通过案例说明了因果关系的不同方面和相关哲学问题,广泛涉及以人口层面的研究证据来治疗个人的因果假设、忽视逆向推理的因果关系、病因的社会决定因素、多因素疾病的因果关系。作者推崇对因果关系的多元解释,亦即依据相关目标(如预测、控制、解释或推断),在医学哲学中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因果理论的各个方面。
希勒尔·布劳德“临床推理与认知”首先描述了显性分析推理和隐性推理之间的区别、如何以及何时使用隐性知识和推理。然后讨论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中认知偏见的证据,说明临床推理是如何被隐性地引入歧途。探讨如何使用元认知(反思和改变自己的认知)来揭示偏见以消除偏见。虽然以这种方式使用元认知可能行之有效,但试图在临床推理中简单地去除隐性知识的作用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可取的。最后,布劳德将实践智慧看作临床推理的模型,认为它整合了多种不同的认知(包括元认知)以及主体间过程和道德需求。
最后一章是雅各布·斯泰根加等撰写的“医学哲学的新方向”,围绕过去20年在医学哲学领域发生的认识论转向,指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四个方向:(1)对不同类型证据的使用进行更精细的研究,如评估随机对照试验的具体细节,而不是讨论随机化的优点,采用证据等级制度以及在设计试验时考虑临床实践的复杂性。(2)诊断研究,如诊断检验评估,首先需要评估诊断检验的准确性,但即便诊断检验相对准确,仍然存在其是否有价值的问题。因此,确定诊断医疗价值的过程需要认知和伦理成分。(3)与医学哲学相关的精神病学哲学的新发展部分概述了与精神病学分类系统有关的科学和伦理问题,并根据一般心理/生物系统中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来理解心理健康和疾病的性质。(4)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的客观性思想,尤其是要结合社会认识论的新进展。医学研究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有助于构成医学研究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威胁着这种客观性,只有从过程中消除有害的主观性和与之相关的偏见,才能实现客观性,从而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第三编研究资源包括核心术语、研究指南、注释书目。术语列表对核心术语进行简短的解释,并提供了相关学者和文献来源。研究指南提供了医学哲学的辞典与百科全书、网络文章、概论性著作、文集、丛书、期刊、网络数据库、专业学会、研究机构等。注释书目列出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代表性书籍,并附内容简介。对于有心涉猎医学哲学的人士来说,这一部分的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 简评
《指南》既探讨医学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展望未来发展,又反思经典问题、纵论各种争议,体现了包容、开放的特点。本书紧扣医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广泛阐述了各种方法和立场,倡导一种多元主义的思路,力图实现这些方法立场的有效整合。这是为了应对医学哲学学科的客观现实,即当代医学充满了各种争议与对立。我国学者杜治政[2]在《医学在走向何处》一书中提出了现代医学的六组二元矛盾,并论述了整合思路,崇尚整体思维,倡导医学整合。马库姆[3]在其《医学哲学概论》中将医学哲学界定为“对医学知识与医学实践的不同模式进行形而上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价值论与伦理学的分析”。他认为当代医学过度依赖生物医学模式,导致了医疗品质危机,破坏了医患关系,援引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理性)、爱索斯(品性)、帕索斯(情感)之区分,提出解决方案,医学当根植于帕索斯,将技术理性转变成智慧,将医疗品性转换成爱心。
医学哲学学科本身也充满了争议。例如,著名哲学家卡普兰(Arthur L. Caplan)[4]就认为医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尚不存在。他提出判断学科地位有三个标准:与同源学科的完美整合、经典论著、一系列独特的问题,认为医学哲学尚不符合这些标准。当然,有更多的学者承认医学哲学的学科身份,认为完全符合卡普兰的三个标准。第一,同源学科问题:医学哲学明显有两大学科即哲学和医学,争议是把它看成哲学下的还是医学下的亚学科。第二,经典问题:医学哲学属新兴研究领域,核心的理论、著作、教科书尚有待时间沉淀。其实可以换个视角,从学术体制看问题,医学哲学已经创设了各种学术期刊、学会、研究机构,进入医学院课程体系,就不用说各种丛书了。第三,研究主题:医学哲学对限定学科的基本问题已有共识,如疾病与健康、医学科研的方法论、临床推理、治疗的哲学逻辑等。
至于医学哲学的学科视角,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佩莱格里诺(Edmund D. Pellegrino)[5]是狭义视角的代表,将医学问题的哲学探讨划分成四种情况:(1)哲学与医学(philosophy and medicine),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保留各自的身份,考虑共同关心的问题并进行自主性对话,如身心问题,意识、感知、语言等的意义问题。(2)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medicine),将哲学的具体分支如逻辑学、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美学应用于医学问题,此即医学哲学的广义视角。(3)医学的哲学(medical philosophy),医生对医学实践的非正式思考,包括行医风格、临床智慧,典型如威廉·奥斯勒。(4)医学哲学(philosophy of medicine),对医学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如医学所特有的内容、方法、概念、预设,正是这些问题使得医学成为医学。医学哲学追问医学是什么、医学何以不同于其他学科。“医学哲学关注的是人类遭逢健康、病痛、疾患、死亡、预防与伤愈欲望时的那些独特现象。”
恩格尔哈特(H. Tristram Engelhardt)[6]是广义视角的代表,在其《生命伦理学基础》中提出了医学哲学的四个分析框架:(1)哪种机能、疼痛、畸形被视为常态的评价性假设;(2)疾病描述与分类背后的预设;(3)因果解释的各种模式;(4)对特定疾病的社会预期。斯坦普西(William E. Stempsey)[7]也推崇广义视角,认为我们对生命、死亡、疾病的形而上看法,对医学知识的认识论主张,对人体的审美观点,限定了什么是医学问题,进而塑造了我们的医学实践,这必然需要一种广义的医学哲学。因此,斯坦普西展望医学哲学的新愿景,认为这将是医学的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社会研究的大融合,甚至仿效科学元勘,建议将之命名为“医学元勘”(medicine studies)。
两种学科视角各有千秋。狭义视角可以明确限定医学哲学的学科界限,凸显学科特色,这对学科诞生之初确立合法性尤为重要。但是,广义视角是学科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还是有些囿于西方医学,是否还应该补充跨文化视角?例如,2004年中国医学哲学专业委员会推出了《医学哲学研究纲要》[8],就纳入了中医等东方医学,但未涉及美国文化所重视的性别、种族问题。
医学哲学归根结底是对医学的哲学反思,也就是如何看待医学的一个问题,这中间总是充满了各种张力,既有现代医学与替代医学(或称另类医学)这种宏大对立,又有医学中科学与人文的经典争辩,乃至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的新近对峙。在国内,也曾出现过樊代明与方舟子关于循证医学的争论、崔永元与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食物的争论,可惜这些良好的机遇都不曾演化成规范的学术辩论。在我们看来,不断的争议与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问题重构与理论修正,恰恰是学科活力和学术产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