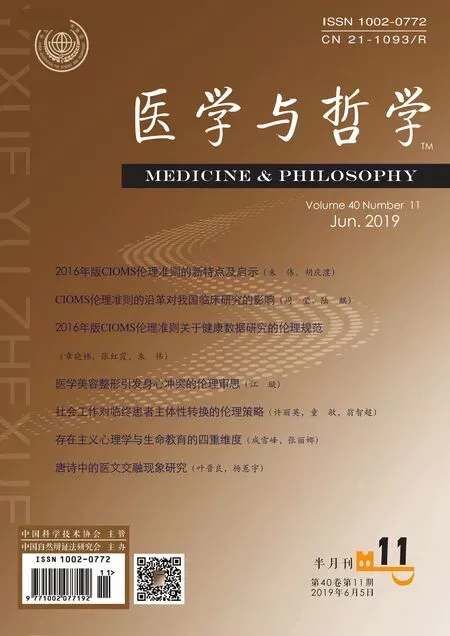法哲学视域下的活体器官悔捐问题研究*
王树华 王 薇
器官移植,21世纪的医学之巅,挽救了大量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病人的生命。但据卫生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可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主要原因是器官捐献率极低,捐献率只有每百万人0.03[1]。尤其自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移植器官唯一合法来源[2],器官短缺的问题愈加严重。
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我国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第八条规定“公民捐献其人体器官应当有书面形式的捐献意愿,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 即器官捐献者有任意悔捐的权利。然而,毫无限制地自由放任主义已经造成诸多弊端,任意悔捐已经严重伤害万般美好的器官移植,对计划受捐者的伤害尤其沉重。如吴某某被诊断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与中华骨髓库内天津和广东各1名捐献者配型成功,天津的捐献者同意捐献后,吴父汇款供血采集费3万元,吴某某接受了手术前的预处理(即用化疗手段摧毁自身免疫系统),天津的捐献者突然反悔,而广东的也不同意捐献,但此时由于已做预处理,吴某某的免疫力和造血功能正在一步步丧失,如果此时不进行手术,很快就会因感染出现并发症并导致死亡[3]。同时,任意悔捐也不是个别现象,据报道,我国仅配型成功后的反悔率就高达20%[4]。因此,任意悔捐已经成为正在发生、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可否借鉴国际经验,解决国内问题?但据美国国家骨髓捐献者资料库一再申明,骨髓捐献永远是自愿的,志愿者应该被告知在实施骨髓移植手术前的最后一分钟都可以撤销同意,拒捐率高达50%[5];亚洲骨髓配对组织也仅建议捐献者“如果拒捐一定要尽早告诉有关人员”,志愿者有60%最终拒绝捐献[6]。由此可见,对于悔捐问题,既无国外经验可供借鉴,也不能拘泥于“实定法”,而需从法哲学的视域思考、分析活体器官捐献者能否任意悔捐?如何规范活体器官捐献?
1 活体器官具有人身属性,自由决定是否捐献
活体器官移植是指在不影响供体生命安全和不造成其健康损害的前提下,由健康的成人个体自愿提供生理及技术上可以切取的部分器官移植给他人,而决不是以牺牲一个健康的生命来换取另一个生命或健康[7]。由此,表面看来,活体器官移植增加了社会利益,提升了移植器官受体生命质量,甚至是挽救了其生命,但深入分析,会发现这些“受益”,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非移植器官的供体。作为供体,在器官移植中,所得到的除了手术创伤、手术并发症外,还有器官代偿功能的丧失,疾病防御能力的降低,甚至是导致相应器官衰竭。
人体具有特殊的属性,是人格的载体,不能将其视为物;因而,活体器官在没有与人体分离之前,与人格相联,不能成为“物”[8]。因此,是否实行器官与自身分离,应当由人体器官所在的自然人本人决定。这种决定权是一种绝对权,其权利主体是器官所在的自然人本身,而义务主体则是除其本身之外的任何人,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不得妨害的义务。因此,若非本人在真实、自愿的基础上作出同意决定,任何人(包括但不限于近亲属、医师等)都无权使器官与本人分离。
为实现捐献决定的真实、自愿,应保证器官供体的知情权和决定的真正自由。知情的内容包括捐献的目的;器官摘除术的风险(死亡和并发症);摘除器官后对健康的可能损害、对就业能力、对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受体可供选择的治疗手段;受体移植手术可能的预后情况(良好的和不顺利的)和受体的特殊情况。这些知情的内容尽管冗长繁杂,但都是必须的。但知情未必能够保证自由,只有最初既排除了可能迫使其不得不捐献的非自愿因素(如道德压力、经济诱惑等),又已考虑了日后可能致使其拒捐的因素(如亲友的阻拦),并已赋予了其前期即可体面不捐的理由,方能实现最初是否捐献的决定的真正自由。也许这些告知和对捐献自由的保证会致使部分供体放弃捐献承诺,但总胜于前期以隐瞒手段获得捐献承诺,后期却因明白风险而悔捐。
脱离人体之器官,其最初所有权,属于分离以前所属之人,他人无权处分该器官。器官脱离人体之后,成为人身之一部分,然部分已非人身,所以,脱离人体之器官得以成为外界之物,法律上之物,即权利的标的。同时,现代社会,自然人均为独立的个体,任何人不从属于他人,因此,脱离人体之器官的最初所有权,属于分离以前所属之人,他享有最完整、最充分的权利,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都属于器官分离以前所在之人。所以,即使是脱离人体的器官成为“物”后,其最初所有权仍是特定的,他人无权处分,更无权强迫所有者必须无偿捐献。
2 器官捐献应信守承诺,不对他人造成伤害
尽管活体器官分离之前属于人体组成部分,分离之后归其所有,但器官移植受体因器官捐献的意思表示做出一定的行为时,此器官捐献的意思表示便不再仅仅涉及欲捐者(有捐献意思表示的人)本人,而是定会影响他人从而产生人际关系,如欲捐者与预受者(已准备接受移植器官的人)之间的关系。活体器官捐献虽不同于一般的捐赠关系,但也应遵守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则,而不该任由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因为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9]。
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 是罗马法以来各国法律所共认的观念。时至今日,该原则已被奉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 有“帝王条款”、“超级调整规范”之称[10]。该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务之注意对待他人事务,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11]。诚实信用原则,不仅为学者所推崇,也为各国法律所明确规定。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12];瑞士民法典第二条“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13];日本民法典总则编第一条二款“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时,应当恪守信义,诚实实行”[1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我国大陆《民法总则》第七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信赖保护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私法原则,旨在强调将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纳入私法规范的构造之中,以维护民商事交往中的信赖投入并确保交易的可期待性[15]。该原则适用的条件是,如果原告基于被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那么就应该赔偿原告因信赖被告的允诺而遭受的损害[16],其目的是为了使信赖他方允诺的一方处于允诺作出之前其所处的地位[15]。
活体器官悔捐行为是对诚实信用和信赖保护两项原则的明显违背,违背了欲捐者的前期承诺,又伤害了预受体的信赖利益。活体器官捐献,捐献者将自己血肉之躯的一部分,无偿奉献给他人是人世间最美的画面。但,这只有付诸实际行动,才会动人,如若仅是空许诺,不践行,则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甚至会让人形成骗子的印象。需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长期忍受病痛的煎熬,当得知有人为自己捐献器官,必定待其如圣贤乃至神灵一般,无比敬仰、满怀期待,并为接受器官移植做诸多准备,甚至是使自己处于比原发疾病更危险的境况,但是,到头来,结局却是“我不捐了”,这是对其信赖利益的严重伤害。
3 “悔捐”应区分情况,适当追责
从上述分析可知,活体器官具有人身属性,不得强制捐献,但承诺捐献后,便应诚实守信,遵从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底线,如此一来,任意悔捐就缺乏了正当性基础,合理区分造成的人身损害和悔捐的原因,适当追责,便有了正义性。
首先,悔捐没有造成预受体人身损害时,无论悔捐者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应被追责。损害,是指受到的损失和伤害,本应包括对人身的、对财产的、对精神的损失和伤害,但由于活体器官捐献的是自己的身体组成部分,而实体的人身权的法律位阶高于财产权和无形的精神权利,所以悔捐只要没有造成预受体人身损害,即使造成了财产和精神损害,也不应被认为存在损害事实。不存在损害事实,即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必考虑悔捐的原因,均不应被追责。
其次,悔捐造成预受体人身损害,悔捐的原因可被理解时,可免于追责。生命原本脆弱,易受伤害,这在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身上更易体现,因此悔捐往往会造成预受体的人身损害。伤害往往难以避免,但追责不一定必然发生,因为活体器官捐献者的初心是无私奉献,是一种应当鼓励的善举,只是毁于捐献的过程中。所以,当悔捐的原因能被公众尤其是预受体理解时,法律不应对善举要求过于苛刻,可免于追责,以免打击善心者的捐献积极性。
最后,悔捐造成预受体严重人身损害,且悔捐的原因不可原谅时,应当追责,但应除外强制履行。当悔捐造成严重人身损害时,意味着欲捐者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了预受体的信赖利益,进而伤害预受体的人身利益。当悔捐造成的伤害大于原发疾病时,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减损,具有追责的正当性。爱心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慎重的承诺,践行承诺不仅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当因自己悔捐造成他人严重伤害时,应当担责。只是如前所述,活体器官具有人身属性,不应被强制履行,但可以通过形式性经济赔偿、赔礼道歉等方式承担责任,用以填补预受体的部分损失,维护爱心互助的社会风尚。
如何区分以上所述悔捐原因是否可被理解与原谅? 首先,应考虑预受体的意见。若预受体不追究欲捐者的悔捐行为时,不论悔捐是何原因,外界均无须干涉。其次,当预受体不理解、不原谅欲捐者的悔捐行为,将纠纷诉至法院时,法官则应以社会利益的损益为标准衡量悔捐行为。若悔捐获得的社会利益显著大于捐献可获得的社会利益,悔捐者不应被追责;反之,则应承担责任。如悔捐的原因是欲捐者健康突发变更,捐献会对捐献者身体造成严重损害,此时,悔捐不应被追责;又如捐献不会损害捐献者健康,悔捐仅是因为主观意愿改变(或只是因为不想捐献),悔捐应担责。
综上,活体器官捐献是最能体现人类互帮互助的善举,其精神应得到赞赏,其行为应得到提倡,但是否捐献应由个体自由决定,而做出捐献承诺后应诚实守信,对悔捐行为,应区分情况,适当追责。如此,活体器官捐献方能实现三大法律原则:意思自治、诚实守信、信赖保护,器官移植才能走得更远,人类社会才能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