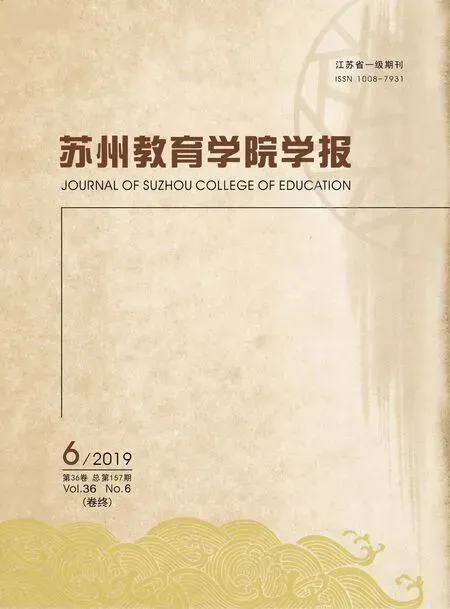试论《清平山堂话本》的口头传统和程式叙事
范沁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明人洪楩刊《清平山堂话本》,源出《六十家小说》,原有《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现存《雨窗》《欹枕》二集12篇,佚名作品15篇,残文2篇,共计29篇。一般认为《清平山堂话本》所收的篇目涵括宋元明(截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三代,而章培恒先生在《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一文中考察《述古堂藏书目》与《也是园书目》著录的收入《清平山堂话本》的“宋人词话”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宋人话本,至少不是宋人话本的原貌”,已经过元、明人的改编[1]。
对《清平山堂话本》的研究,历来多以古代文学中“小说”一门的解读方式进行。但若还原语境,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古代民间口头文学的文本集。本文的分析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话本更接近说书人的“录本”,而非“底本”。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话本是说话人的底本:“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是为‘话本’。”[2]对此观点,后来的研究者有持认同态度的,也有从另一方面对“话本”的口头属性给予关注的。胡莲玉回顾了学界关于“话本”定义的争论,辨析底本问题,认为现所见宋元话本并非说话人的底本,而是由说话人讲说的故事整理而成,“体制和艺术上均带有明显的口传文学的特征”[3]。宋常立通过分析宋元明文献中的“话本”一词并无“说话人底本”之意,提出“话本”之“本”不是指用文字写成的“底本”,而是指说话艺人代代相传的“口传之本”,在一次次的表演中“也许会融进提纲式的‘文字之本’以助记忆,但这种提纲式的‘文字之本’是附属于‘口传之本’的,师徒间传承与表演的完成时态是‘口传文本’”。[4]这种“口承性”正是民间文学的特质。
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与阿尔伯特·洛德共同创立的“帕里-洛德理论”(Parry-Lord theory),又称“口头程式理论”,将口头传统研究成果运用到书面文本分析中,自提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美国华裔学者王靖献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程式概念研究《诗经》中的套语,还有冯文开的《口承与书写视域下的〈诗经〉研究》,及其与其他研究者合作的《宋代歌妓唱词的演述:一种口头话语方式》《敦煌写本〈汉将王陵变〉的口承性及其文本属性》,刘家民的《口承—书面视域下〈聊斋〉的故事书写——以〈阿绣〉为例》、李斯颖的《口承与书写的二重奏鸣—兼论中国史诗传统中的文字》,等等。洛德提出口头传统与书面文本的二元划分,认为二者不可能并存。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后来的研究者们发现这个标准的二元框架过于简单化。“口头传统于书面文学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一种过渡的文本,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研究《诗经》这样的书面文本,探求其口头传统特质。”[5]122
《清平山堂话本》与《诗经》《聊斋志异》都是以书面文本呈现非活态口头传统。由于话本是说书人的录本,保留着口头表演的痕迹,《清平山堂话本》又具有自身的特色。“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可以概括为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它们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6]下文对《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程式和典型场景试作分析。
一、《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程式化表达——以女性人物为例
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提出:“程式,我指的是‘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这是帕里下的定义。”[7]5程式是口头传统词语的一个最小单位,最初是运用于诗歌的。《清平山堂话本》虽非诗体,但话本这种体裁,与变文、弹词等说唱文学一样,属于口头传统,穿插韵语和长短句甚多,而且有些长短诗句的程式化十分明显。帕里提出作用于修辞之上的步格制造了程式句法,而这一过程及其结果正可以通过分析“名词—特性形容词”的程式得到说明。“通过集中关注‘名词—特性形容词’的片语,帕里得以精确地说明,这些相对而言是大量的和不变的要素,是怎样经由传统而系统化,进而成为荷马及其同道们可资利用的特定传统习语(special traditional idiom)的一部分。”[8]55帕里以描写神祇英雄们的“名词—特性形容词”程式为切入点,对荷马史特文本的传统特征进行验证。《清平山堂话本》的传统和口头特质亦可由此法进行验证,唯因语法差异,话本中程式的格式一般表现为“特性形容词—名词”。
(一)老年女性描述程式
在《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程式》《洛阳三怪记》中,老年女性出场时,都辅以程式化诗句:
眉分两道雪,髻挽一窝丝。眼昏一似秋水微浑,发白不若楚山云淡。[9]14(《简帖和尚》骗子婆婆)
鸡肤满体,鹤发如银。眼昏如秋水微浑,发白似楚山云淡。形如三月尽头花,命似九秋霜后菊。[9]26(《西湖三塔记》獭精)
鸡皮满体,鹤发盈头。眼昏似秋水微浑,体弱如九秋霜后菊。浑如三月尽头花,好似五更风里烛。[9]69(《洛阳三怪记》鸡精)
由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在对老年女性进行描述时,用到了“鸡肤/皮”“鹤发”“三月尽头花”“九秋霜后菊”等一类常用的程式单元,大多呈现为“形容词—名词”的形式,并在文本中多次出现。也有一些“名词—形容词”形式,如“秋水微浑”“楚山云淡”等。这些程式排列组合成段,构成一个程式系统,这个系统中各个程式单元的内涵相近,并形成一种可以替换的模式。这一类老年妇女的描述程式具有指向性,大多用于“恶婆婆”类型。无论是《简帖和尚》中替和尚骗小娘子的老婆婆,《西湖三塔记》中的獭婆婆,还是《洛阳三怪记》中的鸡婆子,皆非善类。由于“当歌手运用了一个程式的时候,该程式中所隐含的意义往往多于我们从词典中所能得到的涵义。……所有这些附加的涵义也包含在‘传统’之中”[8]30,说书人与观众处于共同的传统中,在话本表演时,当说书人使用听众熟悉的程式描述某位人物时,听众便会对其所代表的角色性质隐有感知。所以,同为老妇,《花灯轿莲女成佛》中的虔诚念诵《妙法莲华经》的婆婆,便不在这类程式系统适用范围内:“只见一个婆婆,双目不明,年纪七旬之上,头如堆雪,朗朗之声,背诵念一部莲经,如瓶注水。”[9]194“头如堆雪”的形容隐有穆然之气,诵经的“朗朗之声”“如瓶注水”,又强调了老婆婆的庄重与虔诚。这类描述脱于程式之外,便是特为不同类型的人物而设。然而,《清平山堂话本》中程式与人物性质之间对应关系有时并不严格,从青年女性程式中可见一斑。
(二)青年女性描述程式
梳理《清平山堂话本》中描述青年女性外貌的程式化诗句:
云鬓轻梳蝉翼,娥眉巧画春山。朱唇注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花生媚脸,冰剪明眸;意态妖娆,精神艳冶。岂特余杭之绝色,尤胜都下之名花。[9]3(《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周月仙)
云鬓轻梳蝉远,翠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花生丹脸,水剪双眸,意态自然,精神更好。[9]182(《杨温拦路虎传》冷氏)
绿云堆发,白雪凝肤。眼横秋水之波,眉插春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玉指露纤纤春笋。[9]27(《西湖三塔记》白蛇精)
绿云堆鬓,白雪凝肤。眼描秋月之明,眉拂青山之黛。桃萼淡妆红脸,樱珠轻点绛唇。步鞋衬小小金莲,十指露尖尖春笋。若非洛浦神仙女,必是蓬莱阆苑人。[9]72(《洛阳三怪记》白猫精)
由上可知,青年女性程式系统中常见的程式片语有“云鬓轻梳”“绿云堆发(鬓)”“白雪凝肤”“眉拂春(青)山之黛”“皓齿排两行碎玉”“玉指(十指)露纤纤(尖尖)春笋”等,由于汉语的特殊性,这些词语能以精练的形式构成“特性形容词+名词+动词+宾语”的程式单元。相较于老年女性程式系统的单元固定、虚词变化,青年女性程式系统的句式模式很清晰。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与《杨温拦路虎传》按“六—七—四”言句式,以“鬓—眉—唇—齿—脸—眸”推进,总结以“意态—精神”;《西湖三塔记》与《洛阳三怪记》按“四—六—七”言句式,以“发—肤—眼—眉—脸—唇—足—手”敷演。一一描绘五官体态的顺序,与其说按直观,不如说来源于一代代说书人的师徒承继中形成的传统。
还有一些程式化诗句文言气息较浓,所用程式单元也各出新意。其主要意义在于佐证了这样一种句法模式的存在:在一段诗末以类比句式收尾(点睛)。
眉如翠羽,肌如白雪。振绣衣,被桂裳。秾不短,纤不长。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临溪双洛浦,对月两嫦娥。[9]41(《风月瑞仙亭》卓文君)
精神潇洒,容颜方二八之期;体态妖娆,娇艳有十分之美。凤鞋稳步,行苔径,衬双足金莲;玉腕轻抬,分花阴,露十枝春笋。胜如仙子下凡间,不若嫦娥离月殿。[9]200(《花灯轿莲女成佛记》莲女)
“岂特余杭之绝色,尤胜都下之名花”“若非洛浦神仙女,必是蓬莱阆苑人”“胜如仙子下凡间,不若嫦娥离月殿”“临溪双洛浦,对月两嫦娥”等句标明了两点。其一,在此类“若非……必是……”“胜如……不若……”句式中,程式的“替换”特征更加明显,更接近《诗经》的程式化。这种自由填充的框架结构可灵活运用于各种场合,而且汉语丰富的语料库给这个句式中的关联词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其二,本来为了方便记忆,“若非……必是……”这一类关联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但在每一个故事中,现存文本都采取了不同的模板,避免了简单重复,这或许是受到了书面文学求新而规避单调重复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关联词的重复并不能提供有效理解故事的深刻印象,重复的重点还在实词或有实在意义的词组,所以在关联词上说书人就凭个人习惯自由发挥。
二、《清平山堂话本》之“主题”程式举例
《清平山堂话本》的口头传统特质不仅体现在人物描写的程式化表达上,还体现在各类景物描写的主题中。洛德将“主题”定义为:“诗中重复出现的事件、描述性的段落。”[7]5
如《西湖三塔记》和《洛阳三怪记》中对妖怪变幻出的住处的描写:
奚宣赞在门楼下,看见:
金钉珠户,碧瓦盈檐。四边红粉泥墙,两下雕栏玉砌。即如神仙洞府,王者之宫。[9]26(《西湖三塔记》)
青衣女童上下手一挩,挩住小员外,即时撮将去,到一个去处。只见:
金丁朱户,碧瓦盈檐。四边红粉泥墙,两下雕栏玉砌。宛若神仙之府,有如王者之宫。[9]72(《洛阳三怪记》)
高度相似的描述使这个段落成为一个典型的“住所”主题。诸如此类的主题散见于《清平山堂话本》中,此处举春、风、晨、昏为例。这些主题由相似的构件组成,并体现出传统的指向性。
(一)“春”主题
“春”主题坐定故事的发生背景,尤其是在灵怪类故事中:
乍雨乍晴天气,不寒不暖风光。盈盈嫩绿,有如剪就薄薄轻罗;袅袅轻红,不若裁成鲜鲜丽锦。弄舌黄莺啼别院,寻香粉蝶绕雕栏。[9]25(《西湖三塔记》)
乍雨乍晴天气,不寒不暖风和。盈盈嫩绿,有如剪就薄薄香罗;袅袅轻红,不若裁成鲜鲜蜀锦。弄舌黄鹂穿透奔,寻香粉蝶绕雕栏。[9]69(《洛阳三怪记》)
《清平山堂话本》中,故事多发生在春季。如《风月瑞仙亭》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初次花园会面在三月十五,《风月相思》中冯琛、云琼最初以诗传情也发生在春天。春为一年之始,有种万事出新的开端感和新鲜感。话本中常用套语“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说明春这个季节与情事的不解之缘。《西湖三塔记》与《洛阳三怪记》更用大段程式化语言描写了清明时的春,“乍雨乍晴”适宜营造缥缈诡幻的氛围,“不寒不暖”的春日,又比热烈的夏日、肃杀的秋冬更能使听众放松心情,进入故事情境。
(二)“风”主题
“风”则多用于道士作法之时,形容其法术效力:
天色将晚,点起灯烛,烧起香来,念念有词,书道符灯上烧了。只见起一阵风。怎见得?
风荡荡,翠飘红。忽南北。忽西东。春开杨柳,秋卸梧桐。凉入朱门户,寒穿陋巷中。
嫦娥急把蟾宫闭,列子登仙叫救人。[9]31(《西湖三塔记》)
口中念念有词,把符一烧。烧过了,吹将起来,移时之间,就坛前起一阵大风。怎见得?那风:
风来穿陋巷、透玉宫。喜则吹花、谢柳,怒则折木、摧松。春来解冻,秋谢梧桐。睢河逃汉主,赤壁走曹公。解得南华天意满,何劳宋玉辨雌雄![9]75(《洛阳三怪记》
这里的“风”不再是春景里“不寒不暖”的和风,而是具有穿透力、扫荡力、威慑力的存在,不仅草木伏之(吹花谢柳、折木摧松),世间惧之(凉入朱门户,寒穿陋巷中),英雄人主奈之若何(睢河逃汉主,赤壁走曹公),连仙人也畏之(嫦娥急把蟾宫闭,列子登仙叫救人)。并且,此“风”因作法而起,便具有了宗教属性(解得南华天意满),而非为了文学美感(何劳宋玉辩雌雄)。同时,这一类型的风往往为召唤神将而出,并不为收妖。
在收妖时起的是另一类风:
四员神将领了法旨,去不多时,就花园内起一阵风。但见:
无形无影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
就地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9]77(《洛阳三怪记》)
真君乃于香案前,口中不知说了几句言语,只见就方丈里起一阵风,但见:
无形无影透人怀,二月桃花被绰开。
就地撮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9]133(《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可以想见在话本讲演时,当说书人说到此种“风”的典型场景,观众就会知道,即将成功收妖,故事就要结束了。《西湖三塔记》与《洛阳三怪记》中两段对风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基本要素是相似的。《洛阳三怪记》与《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两段则高度趋同,它们出现的情境和代表的意义是各自内部一致的,这再一次表明了传统赋予并规定了程式代表的意义以及在故事中适宜出现的场合。
(三)“晨”“昏”主题
“晨”一般表示脱困或出发,用于积极的场景:
北斗斜倾,东方渐白。邻鸡三唱,唤美人傅粉施妆;宝马频嘶,催人争赴利名场。几片晓霞连碧汉,一轮红日上扶桑。[9]28(《西湖三塔记》)
薄雾朦胧四野,残云掩映荒郊。江天晚色微分,海角残星尚照。牧牛儿未起,采桑女由眠。小寺内钟鼓初敲,高荫外猿声怎息。正是:大海波中红日出,世间吹起利名心。[9]74(《洛阳三怪记》)
晓雾装成野外,残霞染就荒郊。耕夫陇上,朦胧月色时沉;织女机边,晃荡金乌欲出。牧牛儿尚睡,养蚕女犹眠。樵舍外犬吠,岭边山寺犹未起。[9]116(《阴骘积善记》)
残灯半灭,海水初潮,窗外曙色才分,人间仪容可辨。[9]181(《杨温拦路虎传》)
《西湖三塔记》中这一段描述的是奚宣赞与潘松从妖精之处脱身后所见,当妖异可怖的黑夜过去,从封闭的场所中逃出来,这一段列举了人间种种可亲景象,使听众得以放松紧绷的神经;《阴骘积善记》中这一段则出现在主人公林善甫和杨温晨起出发之时。组成“晨”的典型单元有大海与红日,还有雾野、荒郊、寺钟等,但这一典型场景与故事本身有时并不十分贴合:奚宣赞甫脱妖窟,如何能兴起“宝马频嘶,催人争赴利名场”之感慨;《洛阳三怪记》中以“大海波中红日出,世间吹起利名心”作结的一段“晨”主题也似乎更适合游子故事。至于故事主人公所在之地能否看到“海上日出”或“海水初潮”,更是无从也不必深究了。
有学者研究《西游记》时指出,太上老君常自称“当时过函关,化胡为佛”,可能是《化胡经》流行之时说老子故事时的套语。但“老子化胡”的传说意指佛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暗含佛、道一争高下之意。《西游记》第六回,太上老君与观世音菩萨对话时,仍自道当年化胡为佛之事,既不合时宜也不衬场合。“该文本或套语被百回本《西游记》所吸收,此时的‘作者’已不能确知其含义,故亦不曾加以修改,莫名其妙地保存下来,成了一块‘化石’,很不和谐地夹在文本之中。”[10]同理,话本中保留下来的与故事本身有距离的、突兀的主题插入,在口头讲述时只是作为过场,起渲染烘托气氛的作用,听众与说书人一般不会较真。而当它们以书面形式定型时,便成了文本中的一块块“化石”。
话本中的“昏”场景与“晨”相似,这些编织好的小片段由归家的渔父、骑犊的牧童(如“渔父负鱼归竹径,牧童同犊返孤村”[9]76、“遥观鱼翁收缯罢钓归家”[9]170、“牧童骑犊转庄门”[9]171)等单元构件组成,以便随时取用。它们同样与故事整体氛围甚至情感逻辑的贴合并不紧密,既无宗教意义,也不大体现出传统。至于对路上风景、客店的描述亦是如此。后人将这类大同小异的描写称为“陈套”,郑振铎指出,宋人话本中若干例“形容形貌景色的歌词”,其特色之一是“往多抄袭雷同之句;他们仿佛有一套谱子在,咏少妇用什么,咏老太婆用什么,咏婚夕用什么,似乎都有规定的格式”[11]。夏志清亦指出:“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语言已经装载着许许多多采自名家的诗、词、赋、骈文的陈套语句,以至于他们(元明)的说书人亦然,用起现成的文言套语来,远比自己创造一种能精确描写风景、人物面貌的白话散文得心应手。”[12]当口头表演的程式化语言被文字记录下来,袭用于章回小说等体裁的文本创作中并被反复使用,便陈陈相因,成为审美视角下、阅读过程中的赘疣。但仅就《清平山堂话本》来说,将其置于口头传统背景下考察,“程式”本身就不为体现艺术美感而存在,而是故事创编与演述的需要。
三、《清平山堂话本》之口头传统特质
(一)程式化的表达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程式包括韵文诗句和散文片语两种形式,韵文诗句如前文所举诸例,散文片语则是穿插在文中出现的“朱唇皓齿”等程式。在《杨温拦路虎传》《董永遇仙传》《戒指儿》中,女性角色出场开口说话时都先铺垫以“启(一点)朱唇,露(两行)皓齿/碎玉”等语。这些程式化的表达在《清平山堂话本》内部经过反复运用,又被后世多处征引(如在“三言”中也大量出现),的确不太能带给人陌生化的美感。但正因此,它们为《清平山堂话本》的口头传统特质作了明示。只有在口头经过不断敷演、流布、传承,才会形成甚至连眉眼描摹顺序都一致的传统。只有事先用预制单元组成一个个小构件,说书人才能在表演过程中根据听众的现场情况把握故事的进行节奏、篇幅长短。当听众不大感兴趣时,可以削减无关场景的描述,也可以插入一段人物的形容描摹,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程式不仅作用在描述性段落中,“在口头传统中,程式几乎无处不在,程式的主题,程式的故事形式和故事线,程式的动作和场景,程式的诗法和句法等”[5]112。在《清平山堂话本》中,诸如《张子房慕道记》《快嘴李翠莲记》这类几乎靠对话串联的故事,虽会被视为单调松散无情节,却可能是最典型的一类程式化的口头故事范本。以《张子房慕道记》为例,张良请求入山慕道,经历了高祖、众官、老夫人三场劝说,每场劝说分为二至四个回合不等,每一回合劝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张良的回答也一再围绕着王失政事、无常之苦、荣利之虚与慕道之乐展开,反复渲染,颇有《诗经》重章叠句一唱三叹之风,但它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一个“故事”,一篇“小说”。但书面文学中正式写“小说”时,这种写法却一般不被采用。“诉诸于听觉和诉诸于视觉的艺术,其规则是不同的,这不简单是接收器官的转移,实际上规则转移了”[13],这种写法只适用于口头。这种由程式化的形式和线索结构而成的故事,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说书人讲唱的主要范式之一。
(二)主题的连结
程式之外,各类“主题”则为口头故事的不断新生与创编提供了随取随用的灵活小单元,说书人由这些主题牵引来编织故事。如《西湖三塔记》和《洛阳三怪记》,二者皆由“春光”“出游”“宴饮”“出逃”“捉妖”等多个相似的情节链连成,可视作披上不同外衣的同一个故事,在洛阳讲是“三怪记”,在西湖讲就是“三塔记”,可以想见当初或许还有其他同类型的故事在不同地域的说书人中流传,诸如“开封三怪”“苏州三塔”之类,只是没有被文本记录下来就散佚了。有时,故事中的某一个主题会游离于故事主线之外,看似毫无必要,实则“闲笔”不“闲”。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故事按“陈巡检携妻上任—陈巡检梅岭失妻—紫阳真君收妖—陈巡检夫妻重聚”线索展开,关目紧凑,却忽于陈巡检上任后插入一段收捕南林村镇山虎的情节。这段“剿匪”主题,虽体现陈巡检武艺高强,却与故事主线的推进无关。但正是这类在书面文学中看似附赘的“主题”,在口头表演中自有其作用,因武打情节精彩好听,于说书场上颇能吸引听众,也能在故事进行近半时再度集中听众注意力,消除倦怠。后来的古典小说评点中有“宕开一笔”“闲笔”之说,口头文学在这些关节处的处理虽然生硬,是否也曾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提供了经验与借鉴呢?
(三)基于口语的思维表达痕迹
除了反复出现的程式化表达和主题外,《清平山堂话本》中还保留了一些基于口语的思维表达痕迹。沃尔特·翁将“尚未触及文字的文化”定义为“原生口语文化”(primary oral cultures),而“在口语文化里,语词受语音约束,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表达方式,而且决定了人们的思维过程”,这就形成了基于口语的思维和表达的特征。[14]25中国古代的“说话”伎艺在宋元时大盛,直到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亦记载:“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15]既以“话本”为说书人的录本,则可知从最初的职业化说书人到西湖边讲唱的男女瞽者,其说话伎艺通常口口相传,虽与沃尔特·翁所指的“原生口语文化的民族”已有距离,但不通过文字而通过口语来表达,并在“说话”过程中形成基于口语的思维和表达特征,却是共通的,其中一点便是“聚合性”:“口语文化的民族,喜欢说的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勇敢的士兵,不是一般的公主而是美丽的公主,不是一般的橡木而是坚韧的橡木,在正式的话语里尤其有这样的偏好。如此,口语表达承载着大量的称号和其他的套语,反之,高度发达的书面文化则排斥这样不太灵巧、冗余过多的语言习惯,因为聚合结构显得过于笨重。”[14]29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如《简帖和尚》一篇,杨氏见丈夫要休了她,无处安身,便“上天汉州桥,看着金水银堤汴河,恰待要跳将下去”[9]14。诸如“金水银堤”的描写,无益于故事氛围的渲染,但如同不会问为什么橡木一定是“坚韧的”,公主一定是“美丽的”,听众也不会去问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汴河是“金水银堤”的,因为“金水银堤”这个修饰语在这里同“坚韧的”“美丽的”一样,只用来确保聚合结构的完整,是说书人的惯用表达习惯。这一类表达在书面文学中已几近消失,正因此,《清平山堂话本》中保留的痕迹是珍贵的,也再一次标示出它有别于书面文学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集的口头传统特质。
当口头的故事落在纸面上成为写定的版本,后人的增删改编重重叠叠地覆盖了其原型,《清平山堂话本》呈现出驳杂的面貌。其中既有情节简单、语言朴拙的篇目,也有构思完整、行文成熟的篇目;既有口头表演气息浓郁的故事,也有与文言短篇小说几无二致的故事。而在改编较少、保留较多原貌的部分篇目中,也呈现出一个口头传统与书面文学“过渡”的面目。民间故事的底色加上文人的笔触加以勾勒,书面文学的形式难掩口头传统的闪光,人们曾用古典文学的阅读规则来解读它,也在民俗学目光的观照下发现它的别样奇景,这正是《清平山堂话本》的复杂与迷人之处。
——兼议古代平山堂由大明寺代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