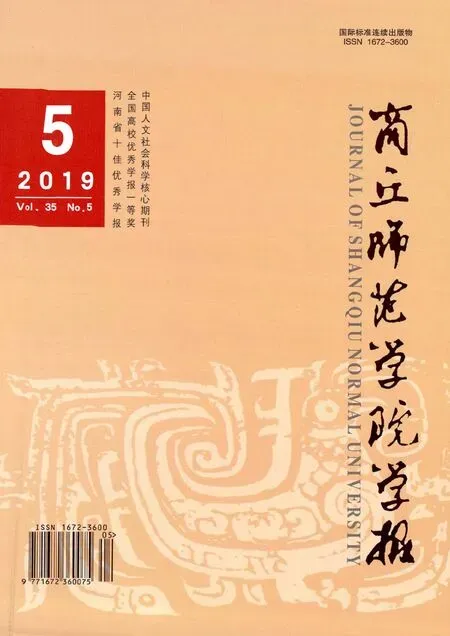试论明末史学的务实精神
——以蒋之翘《删补晋书》为例
王 传 奇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蒋之翘,字楚墀,明末浙江秀水人,《嘉兴府志》《明诗综》等书对其生平略作记载,但皆极为简略。《嘉兴府志》称“秀水蒋之翘,字楚墀,少工诗,采禾中先正诸咏为镌李诗乘。家贫,好藏书。明末避盗村居,收罗名人遗集数十种,选有《甲申前后集》,又尝重纂《晋书》,校注《昌黎》《河东集》”[1]3。《明诗综·小传》仅称其为“秀水布衣,甲申后隐于市”。
《删补晋书》,又名《晋书别本》,全书130卷,其中帝纪10卷、志20卷、传70卷、载记30卷,其体例及各卷内容、人物排比大多依照《晋书》原本,但根据作者对晋史的不同见解又有所调整,其表现主要有二:一是考证纠误,“节原文者十之四,全删者十之二,正其舛误者十之三”;二是在调整原文的基础上,通过史评将晋史与明朝当代史相联系,发挥历史经世致用的作用。这两种做法与明朝中后期史学尤其是私史的“好奇”、粗鄙特点形成强烈对比,表现出明显的务实精神。
一、注重史料精准、简略
《晋书》史料来源众多,除因唐太宗《修晋书诏》曾提到而广为众知的何法盛、习凿齿、臧荣绪等18家晋书外,据《明代书目题跋丛刊》所言,还有李轨所作的晋泰始、咸宁、泰康、元康、建武、大兴、永昌、咸和、咸康、建元、永和、升平、太元等历朝起居录共193卷,刘道荟《晋起居注》320卷,徐勉《流别起居注》660卷,何始真《晋起居注钞》50卷等。此外,如《世说新语》《语林》《搜神记》《幽明录》等小说,亦在取材范围之内,因晋人“尚玄”、喜“清谈”,故上述材料中存在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而唐朝纂修《晋书》诸公又“皆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2]卷7,5,以70卷列传为例,《晋书》采用《世说新语》材料极多。据统计,《诸臣列传》采用104人209条,《忠义列传》采用6人8条,《艺术列传》采用1人1条,《宗室列传》采用1人1条,《良吏列传》采用1人2条,《文苑列传》采用6人18条,《外戚列传》采用6人8条,《隐逸列传》采用1人1条,《列女列传》采用4人10条,《叛逆列传》采用4人14条,共计130人307条[3]260。这些原因共同造成《晋书》纪、传部分取材多比较琐碎,且谬误较多,故自成书之日起,就不断有史家表示不满,如刘知几即讥刺其“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宋代学者欧阳修、胡应麟也有类似言论。
蒋之翘对《晋书》这个不足也极为不满。在《删补晋书序》中,蒋之翘将原史不足总结为6条,头两条即为材料问题,即“其文不能典而美,其语不能博而奥”、“征材于王隐诸家以及《世说》《语林》等书,能比较于司马迁、贾逵、刘歆之手笔乎?”随后他又说《晋书》“机祥浪谑,璅屑备存,研覆未遑,进退失体,已不无绮靡之辞,冗杂之调”[4]删补晋书序,2。认为原史在立国、拓境、偏安、民情风趣、治乱兴衰等方面对后世都有其特殊意义,但正是由于取材芜杂,影响了其效果发挥,故有修改的必要。
蒋之翘对《晋书》材料缺陷的批评也集中在原书大量引用《世说新语》方面,称其“最新《世说》”。他认为,《世说新语》作为小说体裁,虽然或有其事,但或为琐事碎言,或是遗文逸事,皆为“谈客伎俩”,不足纳入正史。为纠正这个不足,蒋之翘提出两个修改意见:
一是根据《十六国春秋》《华阳国志》《通鉴考异》等书做法,将原书中存在疑问之处以小字或眉批形式纠正或存疑。如卷36《卫玠传》就卫玠卒处进行考证,指出“诸书皆谓卫玠卒于豫章,原史独云在卞都,此乃《世说》误引,今正之”[4]15。又如卷35《陈骞传》指出,原书虽然已对可疑材料进行调整,但仍保留了大量荒诞不经的内容,“丰城剑气事绝用小说氏文,其怪妄者虽已汰之,然终归可删”[4]8。此类材料在《晋书》中极多,蒋之翘都一一指出并予以删略。
二是大量删减不必要的内容。蒋之翘认为,史书撰写当尚“简”,如此才能突出经世致用的作用。他指出,荀悦删“迂阔寡要”之《汉书》而成《汉纪》,李延寿不满“芜秽”之宋、魏等史而成南、北《史》,文减事概,但“皆为历代所珍,有逾原本”[4]删补晋书序,4,遂主张史书材料当概括而不烦冗,简略而不遗漏,因此对原史许多诗赋都仅录其名,如张华《鹪鹩赋》、刘实《崇让论》、皇甫谧《释劝论》《笃终论》、挚虞《思游赋》、潘尼《释奠颂》等都是如此,删减了原书大量篇幅。
二、以晋史针砭当朝
《删补晋书》表现出强烈的以史鉴今的倾向。明自万历中期以降,随着国势日益颓靡,朝野众多文人尤其是史家一改之前喜谈野闻轶事、好发奇谈怪论的“好奇”学风,转而追求学术的经世致用,为此甚至不惜走上另一个极端,借助天人报应之说来警惕当代,蒋之翘亦是如此。《删补晋书》全书评论达两千余处,除引用唐、宋、元、明各代史学家之论外,另有近乎一半的数量为蒋之翘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主要集中在忠贞观、朋党论、天道论三个方面,表面上看是讨论晋史,实则表现出非常明显的针砭时弊的倾向。
(一)忠贞观
蒋之翘幼年接受了严格的正统经学教育,在《删补晋书·自序》中称:“予鬓方覆额,即耽□史,先人以为《左史》、前后《汉》而外,无裨经生家言,禁弗读。”[4]自序,1受理学影响极深,故其成年后极为强调“士君子立身行道,出处之际不可不审”[4]卷49,1,要求个人行为必须严格符合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而明末士气沦丧的现实也促使蒋之翘《删补晋书》的评论大量集中在这个方面。
为借古讽今,蒋之翘在评论晋人之际,发出大量与前人截然不同的深刻观点。
首先,因为建国名义不正,蒋之翘对西晋的开国帝王均采取极度贬斥的态度。
出于遵循原书体例考虑,《删补晋书》虽然仍然承认晋室的正统地位,但在评价晋代帝王时却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司马氏夺取政权手段不义,“晋承其(曹魏)末,与世污隆,宣皇创基,功弘而道屈”[4]卷31,1,故在议论之际频繁以“贼”“老贼”“奸种”来称呼司马懿、司马昭、司马师父子三人。如魏明帝景初三年(239)托齐王于司马懿、曹爽,评价道:“死乃复可忍二句痛绝慰绝,竟劳对贼而作,□话史称明帝明敏,抑所明何事耶?”又正始九年(248)司马懿诈称中风麻痹曹爽以避杀身之祸,后者中计反为司马氏所制,道:“老贼作为风□之状,亦写得出纤细如戏。”[4]卷1,14评价司马师、司马昭行事不同,称:“师、昭均奸种,处事不同乃尔。无他,习闻与不习闻也。”[4]卷2,1此外,在《后妃传》中又称穆后为“老物”“老奸”[4]卷31,2,等等。《删补晋书》中类似之处很多,此处不一一列举,但从上述几个例子就可看出,虽然蒋之翘表面上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实际上对晋朝的建立手段极度鄙视。
其次,与前人讨论,重新展开忠贞之辨。
蒋之翘强调历史人物是否忠贞,不能仅看其是否忠于本朝,更重要的是要看其是否站在大义的立场上。出于这种见解,蒋之翘重新对诸葛诞、文钦、毋丘俭、司马孚孰忠孰奸展开独到的讨论。
诸葛诞、毋丘俭、文钦三人因起兵反叛司马氏政权,在唐修《晋书》中被列入叛逆传,蒋之翘提出了不同见解,他提出:“诸葛诞事虽无成,不失忠义,亦人杰也。”[4]卷2,5“毋丘俭、文钦之讨师,诸葛诞之讨昭,《春秋》诛乱贼共义不□,独伤其志大而才小,□□而功丧也。”[4]卷2,4认为诸葛诞三人举兵,虽然从晋室的角度看来是叛逆,但考虑到他们曾是曹魏臣子的身份以及晋室建立手段的不义,其行为符合《春秋》诸侯“诛乱贼”的大义,则不能不说他们是魏朝的忠臣,因此主张将三人列入《忠臣传》中。
与此相反,蒋之翘认为,《晋书》中被称为“纯臣”的安平王司马孚需要重新评价。
司马孚,司马懿次弟,在曹魏官至司空,后代王凌为太尉,转太傅。西晋代魏,司马孚始终以“魏之纯臣”自居,临终命诸子以素棺单椁薄敛,且自为墓志铭曰:“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4]卷37,6明初方孝孺曾对其大加赞赏,将之列为“二千年间有生于逆乱而不为所变者”三人之一(另外两人是武攸绪、朱全昱)。但蒋之翘表示出相反意见,他认为,司马孚虽然能知“篡逆之非”,但却接受晋室封爵而不辞,远不及武攸绪“避位辞去”之举,实在有负“魏贞士”三字。为作出对比,蒋之翘对司马子思大加赞赏,后者因叹武帝受禅事“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由是被废徙武威,“然终身守志不移而卒”。蒋氏对比二人道:“子思才是有□贞士,安平王孚奚其厚颜?”[4]卷37,8
通过上述两个事例可以看出,蒋之翘史学思想中有着严格的忠贞之辨,并以之指导评价历史人物,任何与之不符的行为都受到他严厉批评,但其潜在目的,还是借此警戒当朝官员,倡导忠君思想,这也是他最初“删补”《晋书》的根本动因之一。
(二)天道论
古代史家对社会变乱、王朝鼎革,多归因于“天”或“天道”。但“天”的含义至迟于南宋就已经发生变化,不再被看成是有独立人格意识的主体,而是一抽象的具有至高权利的存在。如程颐回答弟子唐棣“天道如何”之问,即解释为:“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5]卷15,6但在部分明末学者笔下,开始重新强调“上天”的独立意识和赏罚权利。蒋之翘即是这些学者之一。
在《删补晋书》中,蒋之翘将晋的旋兴旋灭(蒋之翘认为,晋朝至武帝后期就已灭亡,东晋不过是“守典午之祀者”)归结于天命予夺,虽然与武帝后期政治混乱、贾后专政有一定关系,但根本原因还是司马懿父子以伪《九锡文》灭汉代魏,从而导致天罚。他说:“此非武帝罪也。盖南风煽祸,不起于夕阳私语时,而先酿于挥戈南阙,高贵乡公刃出其背之际矣。……贾充亡魏,充女亡晋,此天人之微也,非武帝罪也。”[4]卷3,1将乱臣贼子弑君篡权与上天责罚直接联系起来。
对于皇位传承问题,蒋之翘也用天道思想进行解释,认为此非人力争夺可成。他引用怀、愍二帝继位之易与七王相争而不得相比较,认为怀、愍二帝以旁系身份,未尝觊觎大权却“终居皇位”,宗室诸王起兵相争,最终身败名裂而“终无所得”,“夫为之易者如此,其难得之者如此,其不意宜天之有意于二帝乎?”[4]卷5,6认为之所以成败不同,是因为怀、愍二帝行为符合理法,得到天道认可;七王谋位不合理法,失去天意支持。
此外,蒋之翘不仅通过天道观来警戒乱臣贼子,还希望史书能够影响得之于“正”的君主,使之从善纳谏,而不得罪于天地社稷。他比较秦、隋、晋三朝兴亡的原因和特征,说:“秦始一传而胡亥,晋武一传而惠帝,隋文一传而炀帝,三君颠覆其国家,事极相肖。但秦隋一亡不复,而晋之东犹能在江表百有余年,虽曰牛马异类,亦终为守典午之祀者。此秦隋以暴虐亡,天实诛之。晋则强藩称兵,贼后乱政□然,一帝是为虚寄,非已得罪于民社者。”[4]卷4,2认为虽然秦、晋、隋都是二世而亡,但秦、隋“一亡不复”,而晋朝仍能保有东南半壁江山百余年,宗庙不失祭典。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秦、隋二朝帝王暴虐不仁,失命于天,最终“天实诛之”,而晋朝虽然政治混乱,但暴虐之政都起于强藩、贼后,而非惠帝之过,故上天惩罚较轻。
但要注意的是,以蒋之翘《删补晋书》为代表的此类认识,在实质上并非是重新回到宋以前的观点,而是面对明末社会士气堕落、政治腐败的现实,无计可施,不得不求助于上天,希望通过提倡“天道赏罚”来警惕当朝以达到重振国势的目的。正如他所言:“不惟天道有以明操,实有以教之乎!”自有其本身的意义所在。
(三)朋党论
朋党是封建政权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汉、唐、宋三代,皆有党争,并与国运相始终。晋朝亦有朋党问题。但平心而论,晋朝的朋党问题并不像上述三者那么明显,影响也没有那么严重,而在《删补晋书》中,蒋之翘仍频繁地提出这个问题。如卷45《刘毅传附任恺传》提到任恺与庾纯、温颙、向秀、和峤等相善,而贾充与杨珧、王恂、华廙等亲近,眉批道“于是朋党纷然”;又卷75《王湛传》卷首即批曰“太原派”;卷76《王舒传》卷首批曰“琅玡派”;等等。蒋之翘评论道:“昔人论立朝□欲必无党,不爱官、必无欲,是天下事未有不坏于朋党者,但小人之党最浅露,故其祸近而党亦易破。有一种阳君子而实行小人事者,其党尤牙盘根据,固不可拔,当中者能弗忧之欤?”[4]卷45,12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坏于朋党者”,但他重点强调的是小人之党与“君子”之党作出区别,认为前者危害近而浅,而所谓的“君子”之党则“固不可拔”,于国家的危害最深。很明显,蒋之翘这里提出党争尤其是“君子党”问题正是影射明朝后期的阉党与东林党之争,而正是“君子党”之间的“急富贵而相妒压”[6]卷2,19,“精神智虑,俱用之相倾相轧,而国事遂不暇照顾”[6]卷2,12,造成明末的危难局势。蒋之翘生活于这种社会环境中,深刻体会到党争对政治的破坏,自然不难理解其借晋史发出“今用人者非□姻娅,则门生故吏耳,恶能辨别贤不肖,为天下国家计哉”[4]卷66,1的感慨。
至于如何彻底解决朋党问题,蒋之翘在重申前人立朝“无欲”的前提下,提出了“纯臣”概念。他以刘弘为例,说:“刘弘,晋纯臣也。览其遗事,卓似羊叔子,纯无一点纵横习气,全以安天下、尊王室为心。如刘乔与范阳构乱,弘各遣书和解可知。已至督荆州军事,不欲其婿为襄阳,何其公也。谮陶侃者日至,而独以讨陈敏任之,抑何明也。”[4]卷66,1
蒋之翘认为,要消除党争,需先树立“纯臣”标准,其有三:“安天下、尊王室”的“忠”心、任人唯贤的“公”心、不听信谮毁之言的“明”心。朝廷官僚做到这些,自然会政治清明,朋党消弭。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蒋之翘所提出的纯臣标准,恰好是明朝后期诸臣于节有亏之处,从此也可以看出蒋之翘此处的实际用心所在。
《删补晋书》是明末诸多研究《晋书》著作中内容最全面的一部,蒋之翘对该书的修改和书中评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末史学风气和关怀内容的变化,虽然某些评论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借晋史讥刺本朝的做法,无疑反映出明末史学极强的务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