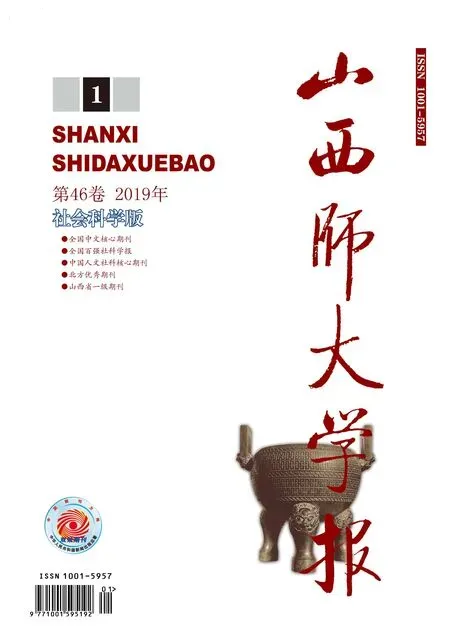宋初晚唐体研究中的谬误及辩正
----在学术史的视角下考察
宋 皓 琨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类有关晚唐体论著在晚唐体诗人师法对象、人员构成、主体风貌等方面形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似乎已没有可讨论的空间。然而近年来,人们开始突破原有的认知,如李定广《论“晚唐体”》指出晚唐体师法对象不止于贾、姚,还有张籍、王建、司空图等人,[1]张立荣《宋初“晚唐体”新论》则认为晚唐体研究不应局限于五律,并从五律与七律两种视角对晚唐体进行了新的定义。[2]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均未能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更为彻底的检视,且囿于传统之见,论述本身普遍存在偏颇之处,凸显了长期以来有关晚唐体认知的强大惯性。对此,本文将从学术史视野出发,对晚唐体研究中的诸多谬误进行辩正,以澄清人们的相关误解。
一、概念的运用
众所周知,元人方回首次提出了“三体”概念,但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产生大的影响。戴表元对方回是熟悉的,曾为方回《桐江诗集》作序,但他在《洪潜甫诗序》中论述到白体与西昆体,而没有提及晚唐体。[3]第1194册,115袁桷《书汤西楼诗后》则只提到宋初有西昆体。[4]第1203册,631直到明清时期,方回“三体”说才有了些许回响,如明徐伯龄《蟫精隽》卷十五说:“宋诗变而为数体,有九僧体,学晚唐,即晚唐体也。九僧乃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古九人也。又有香山体,学白乐天。又有西昆体,祖李义山,自杨文公亿首与刘筠变宋初诗格,缌织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5]第867册,176但徐氏把方回描述的创作群体缩小至“九僧”,指出“九僧体”即“晚唐体”,与方回并不完全一致。再如《四库总目提要·南阳集》也引用了方回的说法,云:“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晚唐一体,九僧最迫真。寇莱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祖凡数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6]2035所不同的是,《总目》去掉了方回提出的鲁三交,同时把晚唐体诗人由“数十家”改为“数家”,规模大为缩小。总的看来,“三体”说及“晚唐体”的提出并没有得到清及清以前学者的普遍关注。
进入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大量出现,方回关于宋初诗坛的表述才为文学史家所普遍接受,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三体”格局的接受;二是对方回所提代表作家的接受。如1916年朱希祖所撰《中国文学史要略》云:“宋初之诗,尚沿袭唐人,魏野、潘阆学晚唐,王禹偁学白居易,而杨亿、刘筠等十七人学李商隐为西昆体,其流最盛。”[7]2911917年吴梅所撰《中国文学史》云:“宋初诗脱去五季余习,而一意宗唐者有三派:为王禹偁初学少陵,后学长庆,是曰白体;寇准、林逋、魏野、潘阆辈则学晚唐,是曰晚唐体;杨亿、刘筠等十七人宗法李义山,是曰西昆体。”[7]470这都反映出对方回“三体”说的接受,只是在代表作家上有所裁减。1918年发行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说:“宋初如徐铉诗,犹有唐音。当时九僧亦有名……九僧以后,遂有杨大年辈之西昆体。”[8]9—10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所谓“三体”,但将徐铉、九僧、杨亿分别叙述,实际包含了“三体”的概念。然而人们对晚唐体代表作家的认定则有很大分歧,这主要表现在九僧与晚唐体成员的关系上。许啸天《中国文学史解题》、李维《中国诗史》等论及晚唐体时,并未谈及九僧,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及陈去病的《诗学概论》则相反,唯以九僧代表晚唐体。吕思勉《宋代文学》则是将九僧与林逋、寇准等人分为两个群体,云:“九僧而后,风靡一时者为西昆体……此外徐铉诗学元白;寇准,林逋,魏野,潘阆学晚唐,皆出于西昆之外者。”[9]49—50并未指出九僧与林逋、魏野等人的一致性。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也说:“在‘西昆体’流行的前后,未入杨、刘们之网罗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较早的时候,有九僧。……他们尝相酬和,别具一体。归心禅门之人,其所写的诗篇,总要带些寒酸之色……又有寇准、王禹偁、林逋、魏野、潘阆、陈尧佐、赵湘、钱易诸人,皆以诗名,而俱清真平淡,不为靡艳之音。”[10]490—491同样未指出九僧与林逋、魏野的一致性。其他如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分别谈到宋初有徐铉、潘阆、寇准、王禹偁、林逋、魏野、九僧等人,惟于潘阆下曰“尚有晚唐作者之遗”[11]第91册,89,在寇准下曰“有晚唐之致”[11]第91册,90,不惟未指出同九僧与其他晚唐体成员的一致性,似乎也没有将魏野等人归入同一群体之意。
可知民国时期对晚唐体的接受并未达成一致。其中1938年发现的梁昆《宋诗派别论》还拈出了晚唐体的师法对象、创作领袖、群体成员、创作风貌等要素[12]第20册,29—30,用流派的逻辑将方回提出的代表诗人组合在一起,开了后世用流派模式描述和论述晚唐体的先河,然而这在当时远非学界共识(具体论述请见下文)。1957年,教育部颁布《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游国恩等学者和中科院文研所据此编写的两部重量级《中国文学史》仍只论及西昆体,并未提及晚唐体。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梁昆《宋诗派别论》才开始受到重视,受其影响,人们在晚唐体师法对象、人员构成、创作风貌上得出了与梁昆几乎一致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晚唐体的诸多认识都与梁论密切相关。
二、贾、姚作为“师法对象”的形成历程及梁昆的误读
一般认为,晚唐体师法贾岛、姚合,且人们多举北宋蔡宽夫的话为例。然而蔡宽夫说:“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13]410明确指出时间是“唐末五代”,无法证明宋初“以诗自名者”也“大抵”学习贾岛。到元代,方回,说:“有宋国初,未远唐也。凡此九人(九僧)诗,皆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14]第1366册,529他只是说九僧学贾岛,并没有把贾岛与整个宋初晚唐体联系起来。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九僧诗)几于升贾岛之堂,入周贺之室,佳句甚多。”[15]杂编卷五,303这显然是接受了方回的影响,同时他又说:“魏野、林逋亦姚合流亚也。”[15]外编卷五,201这两段话出自不同的卷页,且他只谈到了魏野、林逋,而“流亚”也并不意味着师承。到清初,贺裳《载酒园诗话》则将二者合一,云:“宋初多学贾岛、姚合”[16]第一册,401,并指出“九僧诗皆宗贾岛、姚合”[16]第一册,230。也就是说,到贺裳这里形成了晚唐体师法贾、姚论的雏形,但他仍未明确将晚唐体代表诗人与贾岛、姚合对应起来,“多”字使他在表达上留有一定的余地。然而,梁昆在《宋诗派别论》中明确说:“取学白乐天者谓之香山体,取宋初学姚贾者谓之晚唐体,……取以李商隐诗为准者谓之西昆派”[12]第20册,6,把贾岛、姚合推为晚唐体的集体师法对象,这就不免武断和简单化,以至于引起人们的长期误解。
应该说,把贾岛作为宋初晚唐体的师法对象之一,这本身并没有错,从贾岛在宋初的影响及宋祁所说“大抵近世之诗,多师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萧散于摩诘,则肖貌乐天,祖长江而摹许昌也”[17]第24册,321便可知。然而,梁昆把贾岛塑造成林逋、魏野、潘阆、寇准、九僧等人的集体师法对象则有问题,他的论断存在诸多纰漏,如他说:“潘阆《忆阆仙诗》:‘风雅道何玄,高吟忆阆仙。人虽终百岁,君合寿千年。骨已埋西蜀,魂应北入燕。不知天地内,谁为读遗编。’推崇贾岛,可谓备至!则阆诗必宗贾岛。《载酒园诗话》:‘九僧诗俱宗阆仙。’则九僧诗亦宗贾岛。《瀛奎律髓》:‘莱公诗学晚唐,与九僧体相似’,则寇准亦宗贾岛。《四库提要》:‘赵湘诗源出姚合’,然武功诗本效贾岛,则赵湘亦宗贾岛。《瀛奎律髓》:‘林和靖诗,予评之在姚合之上’,则林逋亦宗贾岛。故晚唐派皆宗贾岛无疑。”[12]第20册,21其中关于寇准、赵湘、林逋宗贾岛的论述颇为牵强和武断,稍辨自明。尤其好笑的是,他依据方回“林和靖诗,予评之在姚合之上”,推导出林逋“亦宗贾岛”的结论,其间并无严密的逻辑性可言,显然他在贺裳的基础上,以“派”字挂帅,生拉硬拽,进一步将师法贾、姚的诗人具体化为寇准等人,以此形成了他的判断。
从现有材料看,自五代到宋初人们对贾岛都有着客观的评价和冷静的观察。如孙光宪说:“进士李洞慕贾岛,欲铸而顶戴,尝念‘贾岛佛’,而其诗体又僻于贾。”[18]59指出贾岛诗“僻”的特点。对于贾岛的身世际遇,孙光宪说:“贾岛,以其僻涩之才,无所采用。”[18]51这里的“僻”包含着明显的贬抑色彩。《太平广记》也载:“贾岛字浪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艳,虽行坐寝食,吟咏不辍。”[19]第4册,1124虽然是表彰贾岛以“僻”矫“艳”的成就,但对其诗歌很难说是赞赏。只有孙僅在《读杜工部诗集序》中指出“公(杜甫)之诗,支而为六家……贾岛得其奇僻”[17]第13册,307,才有了一些赞赏的意味。可以说,“僻”是五代至宋初人们对贾岛及其诗歌风貌的共识,但没有表现出多少赞赏与推崇之意,相反,却时有贬抑之嫌。事实上,晚唐司空图对贾岛诗的认识已经很客观了。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说:“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20]193指出贾岛只有在“蹇涩”方面才能写出好诗,并明确指出这是贾岛的不足。宋初《文苑英华》《唐文粹》都选有这篇《与李生论诗书》,因此宋初人对贾岛之“僻”应是很熟悉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贾岛诗可以是部分的接受,但大概不会像李洞那样顶礼膜拜。除了贾岛,姚合的诗闲适平淡,应比贾岛诗更适合宋人的口味,但他在宋初的影响远不及贾岛,对他的评价也基本见不到。姚合在诗学话语中频繁出现,始于宋末晚唐体形成时期,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也频繁地指出宋末晚唐体学贾岛、姚合,同时也批评宋末颇受欢迎的许浑等晚唐诗人的创作不足,如“细碎以求新”“小巧而近乎弱”“多先锻炼景联、颔联,乃成首尾以足之”“装点纤巧”“体格太卑,对偶太切”等,这些本是评价宋末晚唐体以及晚唐作家的论述都构成了梁昆论述宋初晚唐体的理论前提,因此梁昆“晚唐体”概念的提出,是他综合前人对晚唐体的论述,并将胡子眉毛一把抓的结果。
把贾、姚作为宋初晚唐体的集体师法对象,这在民国时期并非学界共识。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种,谭正璧《文学概论讲话》持杜牧说,认为:“林逋、魏野、潘阆等学杜牧诗,号为‘晚唐体’。”[11]第59册,61第二种,柳村任《中国文学史发凡》持大历十才子说,认为“九僧……的作风多半和大历十子相像”[11]第91册,325,延续着清初王士禛“大抵九僧诗规模大历十子”[21]第869册,843的看法。第三种,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持杜牧与姚合两分说,认为:“大约宋初诗人,西昆而外,寇准、赵湘为一类,以温丽为恻怆,杜牧之遗音也。潘阆、种放、魏野、林逋为一类,以瘦炼出清新,姚合之嗣响也。”[22]494第四种,即梁昆《宋诗派别论》的贾、姚说。贾、姚说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写作与晚唐体研究影响甚巨,然而这在当时只是一家之言,梁氏所论无非是合并此前诸家说法,却是对前人的误读与“粗暴”总结,这既偏离了古人的认知,也找不到实实在在的材料依据。
至于人们为何认同宋初晚唐体师法贾、姚,或许是按照相似性原则,由于宋末晚唐体师法贾、姚,而且方回又说过“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送罗寿可诗序》)[23]第1193册,662,于是将宋初与宋末晚唐体混为一谈,主观地认为宋初晚唐体也师法贾、姚,亦或根据九僧学贾岛,简单地以偏概全,将贾岛扩大为整个宋初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李定广《论“晚唐体”》说:“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误认为宋初晚唐体师法姚、贾说源自方回。然而真正误导后人的实乃梁昆,这在李定广先生可谓百密一疏。
三、叙述逻辑
在方回的概念里,他只是指出了宋初有晚唐体存在,并提出了一些代表人物,换句话说,他只是客观地叙述了宋初有哪些人在创作晚唐体作品。从元明以至民国人们大都如此认识。但梁昆《宋诗派别论》不但提出晚唐体师法贾、姚,而且提出以寇准为“盟主”,成员包括林逋、魏野、潘阆、寇准、九僧等人,并总结其诗具有“重五律轻七律”“重腹联轻首尾”“重景联轻意联”“炼句不炼意”等特征。[12]第20册,14—22当然,他所使用的“派别”观念未必等同于西方传入的“流派”,但他用流派逻辑描述宋初晚唐体则是不争的事实。受此影响,人们至今仍难以摆脱这套叙述逻辑的影响和束缚,如张立荣认为应从五律与七律的视角分别认识晚唐体,他说:“就五律而言,宋初‘晚唐体’的代表诗人为九僧、寇准、赵湘、潘阆等,而以九僧为主,取法对象为贾岛、姚合,其诗多写幽仄之景,清苦之情……对于七律而言,‘晚唐体’的取法对象为许浑、郑谷,代表诗人当为寇准、赵湘;潘阆七律类白体。”姑且不论其论述允当与否,就其论述逻辑而言,依然是在师法对象、创作成员、作品风貌的框架下进行的,这显然是受到了梁昆流派逻辑的潜在影响。再如最新出版的袁世硕、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仍有类似的问题,其中虽然指出“当时所谓的晚唐体诗人的诗派意识并不明显,缺乏比较统一的诗派主张和组织形式等”,但又指出晚唐体“推崇晚唐贾岛、姚合诗风,诗歌创作也模仿贾、姚”,而且指出寇准“事实上成了晚唐体诗派的盟主”[24]220—221。显然未脱《宋诗派别论》以来的影响,仍以流派逻辑来构建对晚唐体的描述,可见其影响之深。
近年来人们已逐渐认识到晚唐体概念中存在的纰漏和不足,其中风貌上的差异是人们质疑晚唐体的主要之处,但实际上,风貌上的差异与创作成员之间缺乏紧密的诗学联系有关。寇准、魏野、潘阆、林逋、九僧等人虽然生活年代较为接近,但活动地点迥异,实际上难得一见,常有学者在宋初晚唐“派”成立的预设前提下,考察晚唐体诗人间的交游情况。然而我们经过仔细梳理,会发现晚唐体诗人间的交游有一个特点,即多为单向的拜访或拜谒,如魏野作有《喜怀古上人见访》《送怀古上人游钱塘》《送文兆上人南归》,再如林逋作有《酬昼师西湖春望》,潘阆《赠林逋处士》等,其中有三个热点人物即魏野、林逋与寇准,前两位是著名的隐士,是当时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僧侣文士争相交游的对象,寇准是风雅的宰相,也是人们尊崇的权贵,与其交往或许难免有攀附的成分。[25]76—82在这些晚唐体诗人中,多是四处云游的九僧及潘阆与居所相对稳定的林逋、魏野、寇准的交往,且多是单向的人际走动,如魏野的活动地点多是在陕州附近,而林逋曾二十年足不出钱塘,只有寇准与魏野在一段时间内互动较为频繁。魏野作为著名的隐士,寇准在陕州任职期间曾多次前往拜访,魏野也一度成为其座上宾,这些都与当时社会对隐士人格的仰慕一致。而且我们要看到,寇准拜访魏野是权贵的一种风雅,魏野到寇准府上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士的自我标榜?因此他们的诗学交流在人际交往中恐怕只能占次要地位。而且在晚唐体诗人之间,他们的酬赠也和他们与晚唐体以外诗人间的唱酬无明显不同,加之见面次数有限,其中有些人恐怕终身都难得一见,他们的见面不过是对隐士的推崇或对权贵的攀附,很难说会有密切的诗学意义上的交流和创作联系。常有学者因林逋、魏野诗风与贾、姚有异,而对其是否属于晚唐体进行质疑。事实上如前所述,晚唐体并不以贾、姚为集体师法对象,其创作风貌的多样性恰恰符合不以某个晚唐人为集体师法对象的特点。因此林逋、魏野作为晚唐体诗人,其风貌与贾岛、姚合不一致,无可厚非,而这种质疑说到底仍是自梁昆以来将晚唐体风貌“定型化”以后,其中的流派逻辑发生潜在影响的结果。
梁昆关于晚唐体流派化的叙述在民国时期并未取得共识,也未产生大的反响。《宋诗派别论》出版后,1939年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也出版了,但钱氏并没有把晚唐体成员放在一个有共同师法对象的群体当中。1946年蒋伯潜、蒋祖怡出版了《诗》,其论曰:“当时除西昆体以外尚有冲淡一派的诗人,如王禹偁、寇准、林逋、范仲淹等。”[12]第7册,96也没有用派别的叙述方式对晚唐体进行归纳,可见梁昆的论述在当时只是一家之言,故我们须谨慎对待和接受。
四、关于“三体”并列问题
对宋初诗坛,北宋人就已开始关注了,但对晚唐体的认知却姗姗来迟。欧阳修《六一诗话》仅提到“白乐天体”的浅近、“昆体”的雕琢,却没有提及有所谓“晚唐体”存在。蔡宽夫则较系统地回顾宋初诗坛的批评家,他说:“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26]144—145也没提到有所谓“晚唐体”。其他如司马光等人评论过九僧、林逋、魏野,但都没有指出宋初有所谓“晚唐体”。从现存资料看,整个北宋都没有“晚唐体”的提法及相关评论,表明北宋人缺乏对宋初诗坛“晚唐体”这一概念的认知。[27]447—451然而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虽没有提出有所谓“晚唐体”,却多次提到过“九僧”,同时宋初还编有《九僧诗集》,可知在当时和稍后,“九僧”与白体、西昆体一样,已经作为宋初诗坛突出的创作现象被人们注意到了,他们以集体面目出现,而且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
我们若以白体、西昆体的树立标准观照宋初诗坛,那么“九僧”相互唱和,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与创作风貌,其诗歌可当仁不让地与白体、西昆体相提并论,构成宋初“三体”。实际上,方回已隐约有这种提法,如他说:“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有西昆体者,祖李义山。”[14]第1366册,7再如他说:“元祐诗人诗,既不为杨刘昆体,亦不为九僧晚唐体,又不为白乐天体,各以才力雄于诗。”[14]第1366册,275明人徐伯龄《蟫精隽》亦云:“宋诗变而为数体,有九僧体,学晚唐,即晚唐体也。……又有香山体,学白乐天。又有西昆体,祖李义山。”[5]第867册,176民国时期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陈去病的《诗学概论》等也有这种表达方式,如陈去病云:“宋兴,有九僧者,咸袭晚唐。厥后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又宗法义山……白乐天派,若王禹偁之徒。”[28]1416—1417可知“九僧体”这个称谓及其与白体、西昆体并列的叙述格局由来已久,如前所述,北宋欧阳修等人的诗学批评也足以支持这一诗坛架构。
因此宋初晚唐体的构成相对复杂,一方面有群体性鲜明的“九僧”存在,另一方面在整体人员构成上却不成体系,如同散落在夜空中的繁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晚唐体呢?
立足于宋初创作实际,我们会发现晚唐体是当时最切于日用的创作思潮。白体表达闲适、乐意及旷达的情怀,创作主体是生活优裕的官员,或是洒脱的方外之士以及少数有着闲适情怀的文人,可以想见这不会是宋初诗坛上的多数群体。西昆体的华丽繁缛虽成为一时风气,但本质上只对应台阁文人这一特殊群体,它是学习李商隐华辞丽藻的产物。相比之下,晚唐体的内涵相对宽泛,表达的情感和旨趣可以是闲适、平淡,也可以是感伤、深沉,它反映的是宋初人在现实中的真性情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其创作态度可以是苦吟,也可以是平易,创作主体可以是官员,也可以是落第才士及平民普通人,乃至方外之士等,不一而足。相比于白体和西昆体,晚唐体才是多数宋初人身边的诗,它的存在符合人们的现实创作需求,从这一点说它是宋初最普遍的创作思潮。
从北宋诗歌发展来看,宋人从晚唐体中受益良多,如对字句的锤炼,格律的重视,甚至苦吟的态度,等等,梅尧臣、欧阳修等人的诗都有明显的晚唐体痕迹。然而如此重要的创作思潮为何没有像白体、西昆体那样被人们着意强调呢?这似乎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深入宋初创作背景,这一现象解释起来或许非常简单:白体在宋初拥有前代无可比拟的鼎盛局面,不但有皇帝亲自领导和组织,而且众多达官显宦参与其中,使白体在宋初有着重要的影响;西昆体则在平庸、琐屑的宋初诗坛异军突起,以其鲜丽繁缛的美学特征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赢得了人们的追捧。而晚唐体就存在于人们身边,显得那么平淡无奇,以至于司空见惯,不为时人所瞩目,欧阳修等人虽从晚唐体中受益良多,甚至“儿时犹诵之”(欧阳修《六一诗话》)[29]265,但在晚年回顾宋初诗坛时却没有形成对“晚唐体”这一概念的认知,可以想见晚唐体对人们来说或许就像每天要吃饭一样平常,无需刻意强调,算不上特别的诗学现象。相比之下,白体与西昆体兴盛是宋初诗坛上的突出现象,“九僧”也以其特殊的身份和鲜明的风貌引起了人们的集体关注,因此需要着意说明和记录一番,故欧阳修等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评论。这也从侧面说明晚唐体在整体上并没有特定的师法对象,也没有特定的创作群体及相关群体特征,故没有给人以突出而深刻的整体印象,否则不会被宋人集体忽视。
然而作为一种创作体式,晚唐体在宋初是切实存在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三体”并列问题上对晚唐体与九僧体进行融通呢?鉴于“九僧体”在宋初的独特性以及人们对它的突出强调,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晚唐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特指“九僧体”,从一致的师法对象(方回认为学贾岛、周贺)、创作风貌等来观照,“九僧体”可当仁不让地与白体、西昆体构成宋初“三体”;广义上晚唐体代表诗人则包括九僧及各具风貌的潘阆、魏野、林逋、寇准等人,他们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宋初晚唐体的多重面貌。对于“三体”并列而言,则应从特定的诗风的角度来分辨,李定广《论“晚唐体”》认为:“五代诗歌”是晚唐诗歌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从具体创作来看,宋初晚唐体主要就倾向于这种“轻快有味”或“轻清细微”一路。
五、结语
宋初晚唐体虽是人们熟知的“常识”,但其中仍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体认和考察,这涉及如何认识晚唐体的性质,如何表述其特性和内涵,因此仍有予以重视的必要。同时,从作家、作品的角度去研究晚唐体,常常陷入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境地。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去梳理晚唐体概念的形成过程,则很多疑问可迎刃而解,如师法对象、体派属性以及林逋等人的诗是否属于晚唐体等。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虽然学术后出转精,但不排除在某一阶段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一些问题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宽泛和模糊,而去掉这重时间带来的“翳障”,进而求“是”,正是学术研究的责任和乐趣所在。
——“绿筑迹 ——台达绿色建筑展”台达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