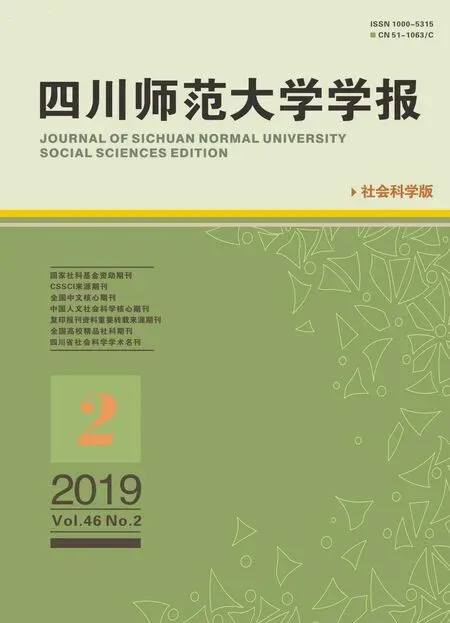清前期边界观念与《尼布楚条约》再探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人类最初的区域界限意识,大概可以追溯到动物本能的领地行为。随着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演进,作为国家界限的边界也得以产生[1]235。在中国历史上,清前期的边界问题,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其时清朝拓展疆域的成就极其突出,也因为在1689年中国首次以条约的形式划定了近代意义的国界。目前,关于《尼布楚条约》与清前期边界问题的研究已极丰富,惟总体来看,相关论著多集中于边界沿革和界务交涉方面,而对边界观念的探讨仍较薄弱①。与此相关的是,尽管过去不少学者强调《尼布楚条约》对清朝边界观念影响匪浅,但实际上,此中若干关键问题至今仅停留于模糊认知层面,或尚未为学界充分注意,以致前人观点有失简单和偏颇。例如,清朝究竟何时、因何产生边界意识?《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是否与清朝自身固有认识有关?该约对清朝边界意识影响程度到底如何?清前期中西边界观念有何异同、差异根源何在?等等问题,过去均缺乏清晰的论证。本文将追根溯源,较为细致地考察入关前清廷边界意识的生成,进而揭示其对《尼布楚条约》签订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天下主义对其发展形成的制约,以期对上述问题有更加客观和深入的认识。
一 辽东局势与后金入关前边界意识之生成
关于清朝边界意识的产生问题,学界尚无专门研究,但有一些论著简要指出,17世纪后半期,沙俄入侵和中俄订约对清朝边界观念起到了重要刺激作用[2]47。从《满文老档》《清实录》《朝鲜实录》等文献来看,其实早在入关以前,清政权已逐渐形成较为明确的边界意识。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整个清朝前期边界观念的基础。
清政权早期的边界意识,萌芽于努尔哈赤时期,亦即满族从部落向国家过渡的阶段。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1587年和1603年,努尔哈赤先后兴建费阿拉城和赫图阿拉城作为女真部落的统治中心。1605年,他开始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随着努尔哈赤自立政权的意识日益明确,其边界意识也开始萌芽。
1608年7月,努尔哈赤与明朝辽东官员,“刑白马,以血、肉、土、酒各一碗,销骨而盟誓”,约定:“帝之边界,凡汉人、诸申,无论何人偷越,见即杀之。见而不杀,则殃及不杀之人。明若渝盟,则明帝之广宁都堂、总兵官、辽东道、副将、开原道、参将等六大衙门之官员,均受其殃。”随后,双方“勒碑立于沿边诸地”[3]2。此时,努尔哈赤在名义上尚臣属于明朝,故其与辽东官员所约定的“帝之边界”,并非国家之间的边界。不过,这一边界盟誓仪式郑重、充满敌意,非一般地方官商定彼此行政界线的行为可比。可以说,这是努尔哈赤边界意识开始萌芽的重要标志。努尔哈赤对于1608年的誓约及其规定的边界极为重视,在日后谴责明朝时再三提及,甚至视之为反明的重要依据。
1616年正月,努尔哈赤正式称汗,建立后金。数月之后,努尔哈赤因明人越境,谴责对方曰:“每岁越境掘银采参……为禁其扰乱,曾立石碑、刑白马盟誓。然负前约,每岁逾越帝界,我即戮之,亦不为过也。”[3]15遂将越境的五十余明人杀之。努尔哈赤选择此时严格执行1608年的誓约,处死越境之人,显然与后金政权的正式建立有关。这说明,敌对政权的公开建立,以及国家意识的萌生,进一步激发了努尔哈赤的边界意识。
1618年5月,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七大恨”中,有“两恨”与明朝违反1608年的边界盟誓密切相关:“曾勒碑盟誓……然明军渝誓出边,援助叶赫驻守,其恨二也。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边境,侵扰劫掠诸申地方。我遵前盟,杀其越界之人者实。然明置前盟于不顾,责我擅杀,执我前往广宁叩谒之刚古里、方吉纳,并缚以铁索,逼我献十人解至边界杀之,其恨三也。”[3]19可见,在努尔哈赤看来,国家之间对边界的侵犯,足以构成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
后金建立之初,便处于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之中,因此它必须妥善地处理与蒙古和朝鲜的关系,才不致多面受敌。事实上,后金颇为重视对蒙古和朝鲜的笼络,同时注意利用边界防范对方。1621年5月,努尔哈赤致喀尔喀五部诸贝勒曰:“河东汉人皆已剃发归降,五部诸贝勒当各晓谕部众,严密固守,不得越界行乱,招致衅端,小事亦可酿大祸也。若谕而不从,仍自越界滋扰,致我二大国开启战端,沮坏两国和好之大业,惜哉,有何益处。”[3]50对于与朝鲜的边界,后金则派兵戍守。1623年3月,努尔哈赤令:“每旗出小旗长一人,率每牛录白巴牙喇一人,前往朝鲜边界一带驻守。”按此规定,同年4月,“副将巴都虎、副将康喀赖、副将塔音珠、参将阿什达尔汉,率每牛录甲兵二人前往戍守朝鲜边界”;5月,“副将冷格里率白巴牙喇四百人戍守于朝鲜边界”[3]159。努尔哈赤对驻守边界的将士要求严厉,唯恐其有所疏忽,如在该年4月谕曰:“尔等驻守边界之人,切勿玩忽,谨慎防守。”[3]167类似的言论,努尔哈赤在日后多次重申[3]168-169。
皇太极时期(1626—1643),是清政权早期边界意识生成的关键阶段。后金在与明朝的战争中,最初屡屡取胜,但进攻辽西一再受挫。在此情况下,皇太极遂以议和为缓兵之策。1627年5月,皇太极致书明朝守将袁崇焕:“两国诚欲和好,先划分地界,从何处为明地,从何处为诸申地,各治其地。”[4]460接着,他致书明廷:“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某地属尔,某地属我,各居疆土,以安生业。”[4]468上述议和建议虽未实行,但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很值得重视。皇太极一再提出“划分地界”、“议定疆界”的议和主张,表明他已清晰意识到共定边界对于邻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共定边界之外,皇太极时期较为显著的疆界意识还有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后者的形成,多得益于后金与朝鲜的交往。这是因为,1627年后金对朝鲜发动“丁卯之役”之后,与之约为兄弟之国,两国的边界交涉最为频繁。
(一)各守封疆。1627年“丁卯之役”结束不久,后金与朝鲜举行盟誓,誓曰:“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各遵约誓,各守封疆,毋争竞细故,非理征求。”[5]3322誓词中的“各守封疆”一语很值得注意,在当时金朝两国交往的文书中屡屡出现[5]3314。作为战败方的朝鲜要求“各守封疆”,显有防范后金之意;而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后金,也一再强调“各守封疆”,则体现出其对互不侵越边界的认同。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对朝鲜发起“丙子之役”。尽管朝鲜由此成为清朝的臣属之国,但双方对疆界始终看重。1641年,朝鲜因清方军民越境索粮咨云:“小邦之与大朝,虽义同一家,而彼此疆场,自有界限。”清方虽认为责任在朝,但表示将“遣人严行禁止”,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6]722-723。此时,清廷难免具有上国心态,但对“各守封疆”的信条依然是遵守的。从1627年要求“各守封疆”,到1641年强调“彼此疆场,自有界限”,皆体现了朝鲜对清朝的提防之心以及较为强烈的疆界意识,这无疑会对清廷边界意识起到强化作用。
(二)互遣逃人。1627年8月,朝鲜遣使后金,书曰:“自今两国之民越境逋逃者,各相察还,毋得容隐。”[6]51同年年底,后金致书朝鲜:“至于我国逃人,当两国盟誓时,原议自盟之后,尔国即行送还……今我撤兵之后,已细察逃往人数。其外藩逃人,俟再察出以告。”[6]55此处的逃人,系指本国出逃至境外的罪人。金、朝规定由对方遣返越境逃人,反映了双方对疆界的尊重和对“各守封疆”的遵守。
(三)严禁私越。其时,在中朝边界方面最为棘手的问题是朝民不断越境猎兽采参,而后金始终强调严禁私越。1628年,后金致书朝鲜,“谕以两国人民,有私自越境捕猎者,宜严察禁止,毋使恣意乱行,以滋衅端”[6]60。尽管如此,朝民越境盗参的现象依然存在,后金因此反复与朝鲜交涉。1633年,后金遣使朝鲜互市,携所获朝鲜盗参二人同往,书曰:“贵国既言人参无用,乃每年出尔边界,入我疆土。不顾罪戾,采此无用之参,何为乎?……贵国违弃前盟,潜入我境,猎兽采参。如贵国地方多有虎豹,我国何曾有一越境猎取者乎?”[6]207后金言辞如此激愤,不独有政治、军事方面的考虑,亦有经济利益的考量。盖对后金而言,与朝互市,可换取所需物质,从而保障战斗力[7]252;而朝民越境采参,会导致人参减价,影响互市效果。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入关以前,清政权已逐渐形成了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的意识。上述意识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金建立以来国家意识的生长以及长期身处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的刺激。
清朝入关初期,基本延续了上述边界意识。惟从中朝界务来看,此前的边界理念有进一步制度化的趋向。其重要表现之一,便是清廷将地方官对边界管理的责任予以明文规定。《大清会典》载:“(康熙)十二年题准:外国人私行进口,该地方官不察报者,降一级调用;该管上司,罚俸一年。又题准:凡外国人,不论蓄发与否,均不许擅进边口,违者守边官弁皆从重治罪。”[8]卷六二八与此同时,清廷对于较为严重的朝民越界案,往往派遣专使与朝方共同审讯,以加强约束[9]39。不过,应当看到的是,清朝此时对边界的认识仍缺乏清晰性。例如,入关前,清朝已与朝鲜确定以鸭绿江和图门江为界,但实际上两江上游和江源多有模糊之处。长期以来,清朝对此未予充分注意。直到1670年代,清廷开始重视两国边境模糊地带的调查[10]189。然因朝方不予配合,查界计划一再搁浅。
那么,同一时期西方的边界观念,与清朝有何异同呢?在17世纪之前,欧洲主要国家,尚无明确划定固定边界的意识[11]264。17世纪中期起,欧洲国家中已经出现要求严格划定精确边界的思想。1637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在《方法论》和《几何学》中阐述了可测量的、地图上可标识的、严格划定界线的、可控制的空间观,“奠定了近代政治意义上而非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国界概念”[12]291。不过,这一时期中西仍存在“国际边界不明确,疆域概念模糊”的相似之处[13]4。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约》签订以后,由于欧洲主权国家原则得到确立,中西边界观念的差异才逐渐显现。如1648年,30年战争结束之时,瑞典和勃兰登堡首次以界石的形式作为国界的标志[14]133-134;1659年,比利牛斯条约签订过程中,西班牙和法国设置了专门的勘界委员会,被认为“开启了近代意义上的正式边界”[15]33。总之,在清朝入关以后,西方才逐渐形成以条约的形式划定精确且固定的国界的观念,从而与中国边界意识的差异日益显著。
二 清朝固有边界意识对《尼布楚条约》之推动
对《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与过程,学界已有颇具分量的研究②,此处无须赘述。不过,由于前人对入关前清政权早期边界意识缺乏深入考察,故未能注意清朝固有的边界意识对此约签订产生的影响。下文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康熙亲政之后,对黑龙江地区俄患颇为留意。最初,他尝试采取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未能奏效,遂决定使用武力方式。1685年4月,在已做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康熙仍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乃致书俄皇称:“向者,尔国居于尔界,未曾侵扰我界,边民咸宁。后尔罗刹人侵我境,骚扰地方,抢掠百姓妇孺,滋事不止……倘尔怜悯边民,使之免遭涂炭流离之苦,不至兴起兵革之事,即当迅速撤回雅克萨之罗刹,以雅库等某地为界,于该处居住捕貂纳税,勿入我界滋事。”[16]51此时,康熙虽未明言与俄国划分疆界的问题,但谴责俄国侵越疆土、冀望各守封疆之意已明。
清军击退雅克萨俄军之后,康熙于1686年正月向大臣表达了欲以尼布楚为中俄边界的想法:“日者,大兵往征鄂罗斯、破雅克萨城,释鄂罗斯不诛,赦之使生还。其时不并取尼布潮地者,盖以尼布潮地画为疆索,使鄂罗斯不得越尼布潮界,界外听其捕牲也。”[17]313这种划分中俄疆界的考虑,在同年9月康熙通过荷兰使臣致俄国的国书中有更为明确的体现:“当以屡谕情节,备悉作书用部印,付荷兰国使臣转发俄罗斯察罕汗,令其收回雅克萨、尼布楚诸地罗刹,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逾越。”[16]57随此国书送往俄国的,还有兵部咨文。该咨文不仅同样表达了划界的主张,而且论及了遣返逃人与越境处置的问题:“若不遣返我逃人,不撤回其雅克萨等地之俄罗斯人,则凡遇窜入我境者,即行擒杀,不留一人,悉加歼除。”[16]59
值得指出的是,在1686年以前,虽然俄国曾数次遣使来华,但其训令均未提及划界问题[18]21-60;康熙也曾致书俄皇,却一直未有回复。正因如此,康熙才让与俄国有联系的“荷兰贡使”代为转呈国书。关于此前未有复文的原因,俄皇在1686年11月底复康熙称:“前我之所以未予复文,皆因我周围国家动乱不安,道路不通。”[16]72对此,魏源在《圣武记》中也指出:“顺治十二年、十七年,俄罗斯两附贸易商人至京,奏书绝不及边界事。康熙十五年,贸易商人尼果赉等至,圣祖召见之,贻察罕汗书,令约束罗刹毋寇边,久之未答也。”[19]249这表明,1686年的清朝国书和兵部咨文中所提出的划分中俄疆界和严惩越境之人的主张,实出于清廷自身。
那么,此时清廷得以提出划分中俄疆界之主张的原因何在?蒋廷黻先生在民国时期已指出,俄国入侵和蒙古动乱,是促使清朝与俄国订约划界的重要因素[20]24。盖对清朝而言,与俄国划定疆界、避免冲突,从而稳定喀尔喀蒙古、孤立准噶尔,实为迫切和必要。本文要强调的则是,从观念层面来看,清廷这一主动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固有的边界意识。清朝的边界意识并非因俄国入侵或《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而产生,而是早已有之。从前文来看,自皇太极时期起,清政权已逐渐形成了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的理念,这些边界理念曾被后金用来处理与朝鲜以及明朝的关系。可以说,在当时统治者的认识中,与相邻的国家,特别是敌对的邻邦,形成双方认可的边界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在应对中俄边境冲突时,清廷能够利用固有的思想资源,主动提出划分疆界以弥后患。
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1642年松锦之战后皇太极致明廷的议和倡议书:“若我国满洲、蒙古、汉人及朝鲜人等,有逃叛至贵国者,当遣还我国。贵国人有逃叛至我国者,亦遣还贵国。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两国俱于此互市。自宁远双树堡土岭界北,至宁远北台,直抵山海关长城一带,若我国人有越入,及贵国人有越出者,俱加稽察,按律处死。或两国人,有乘船捕鱼,海中往来者。尔国自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我国于黄城岛以东为界。若两国有越境妄行者,亦俱察出处死。”[6]829若将此书与上述1686年清朝致俄方的国书和咨文对比,不难发现,二者对于划界、逃人、私越等问题的主张存在诸多明显相似之处。
在此,有必要略加申论的是,清廷之所以能对明朝和沙俄主动提出共定边界的建议,不仅与固有边界意识的延续有关,也与其自身心态不无关系。因为清廷是兴起于东北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入关前曾长期处于敌国环逼的局势之中;而至17世纪80年代仍入关未久,被“汉化”的程度也相对有限。故其所具有的传统思想包袱,自然较汉族中央王朝要轻,在定界问题上,亦无须突破极为严重的思想障碍。
俄皇彼得收到清朝国书之后,于1686年11月底回复:“若即撤兵,则互相可停止兵革。尔属下人应勿过境骚扰寻衅,滋生事端,并希放还战俘;双方共派使臣,并令尔所派使臣,凡事秉公妥善办理。杀人者治罪;各定原来疆界,退还尔新取之地;为首寻衅者,亦当治罪。”[16]72在这一封正式打开中俄划界谈判序幕的关键性国书中,俄皇提出了撤兵议和、归还战俘、议定边界、禁止越境等要求。这些要求,可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当时俄国的边界理念。自17世纪中叶起,俄国受到欧洲国际法和国界理念的影响,开始与土耳其帝国等以条约的形式正式确立线状的防御性边界[11]264。我们若将上文所引俄皇国书中的要求与清廷的主张相比,不难发现,在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严禁私越、互遣逃人等方面,二者的边界理念存在不少类似的地方。这表明,在17世纪末期,中俄边界观念,尽管渊源有别、旨趣各异[12]18,但在某些原则上却不无相通之处。
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其分界方面的内容大体为清廷之前所重点关注的有几个方面:一、划定疆界,“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二、禁止越境,“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三、互遣逃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击遣还”[21]1-2。就这些内容及其所贯彻的原则来看,既有对传统理念的继承,也有某些突破。其中,以条约这一近代西方国际交往的法律形式明确划定两国疆界始于此时,而各守封疆、严禁私越和互遣逃人在此前应对中朝疆界问题时早已实行。清朝过去在边界问题上所采用的一些原则,最终能体现到《尼布楚条约》之中,固与中俄两国的妥协以及耶稣会士的周旋密不可分,但上文所指出的中俄所具有的边界观念共识也至关重要。
三 边界观念发展之限度与天下主义之制约
对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朝边界观念发展的一些表现,如加强东北边防、设立中俄界碑、绘制实测舆图等,前人已有不少论述③。其中,不乏给予高度评价者,甚至认为清朝的边界观念达到了西方近代国界观念的水平④。揆诸史实,《尼布楚条约》的订立,对清朝相关认识的发展确有促进,但这种观念的转变程度实际较为有限。
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在1689年之后所表现出的较为强烈的边界意识,并非皆因中俄订约划界的刺激而产生,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其入关以前业已形成的观念。例如,树立界碑的意识,在1608年已有类似的雏形,当年努尔哈赤与明朝边将举行盟誓,约定疆界,“勒碑立于沿边诸地”[3]2。又如,驻守边境的意识,在后金时期已经产生。如前所述,1623年努尔哈赤便“着每旗出小旗长一人,率每牛录白巴牙喇一人,前往朝鲜边界一带驻守”,并要求“谨慎防守”[3]159。再如,对于划分疆界的意义,努尔哈赤在1627年已有清晰的认识,他致书明廷说:“两国和好,宜先议定疆界,某地属尔,某地属我,各居疆土,以安生业。”[4]468若不充分考虑清朝固有的边界观念,便极易夸大《尼布楚条约》的影响。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晚清以前中国远未形成近代国界观念。按照西方近代的国界理念,国家应以条约的形式清晰地划定线状的边界,并对边境内侧实行积极严密的防御和管辖⑤。而在《尼布楚条约》订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清廷的认识与此有显著差异,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未形成以订约划界为通则的意识。1689年以后,清朝仅于1727年与俄国正式划定了蒙古段边界,而无意与俄国继续确定西北边界。在宗藩边界方面,长期只存在一些较为含混的传统边界习惯。1712年,穆克登赴中朝边境查边之举,颇引学者注目。不过,康熙谕令穆克登查边,“特为查我边境,与彼国无涉”[22]495,即只是将疆界查明而已。期间,清朝的态度颇为草率,在并没有对边境进行清晰了解的情况下,便派遣穆克登去查界;查界之后,将树立界栅之事委之朝鲜,也未会巡边界[23]202。显然,清廷并无将之前中俄订约划界的新规则运用到中朝边界的意图。
第二,对边界的认识具有相当模糊性。尽管清前期曾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绘制了《皇舆全览图》等实测舆图,但长期藏之内府,未必能代表时人认识。当时官方运用较多的是政书和方志上的地图,其中以《大清会典》和《大清一统志》上所附舆图较为权威。这些舆图,基本沿袭着传统疆域示意图的绘制方式,明显存在表示粗略的问题。如在嘉庆会典的《科布多图》上,西北处标识了“俄罗斯界”和“哈萨克界”的字样[24]卷三一二,20,但其边界具体的位置和长度依然很不清晰,难免使人感到困惑。尤为严重的问题是,界、卡认识混乱。乾隆平定西域后,在西北边境设置卡伦。因卡距界较远,而巡边沿卡而行,久之二者便模糊不清。1813年,嘉庆下谕,“卡伦以外各夷部落自相争论之事,天朝断不值代为剖判”,惟当“谨守边界”,不应“越界管理”[25]660。在此,俨然已以卡为“界”。
第三,对边界的防卫态度亦较为消极。在边防相对严密的东北边疆,清朝所设卡伦多离边界甚远。当地巡边,理论上是一年一小巡、三年一大巡,其实际效果自较有限[20]31。至于西北边疆,清廷允许中俄两属的哈萨克在缴纳赋税后于界内住牧,真正意义的边界防御更难实现。在中越边境,自乾隆朝起虽设有“三关”、“百隘”以及一百二十余卡,但“正口关隘外,其余并无范例,出入无从阻拦”,实际“久无中外之防”[26]354-355。当然,清朝疆域辽阔,在生产力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要对漫长复杂甚至环境恶劣的边界地区采取严密有效的防御措施,无疑存在极大困难。不过,清朝边界防御普遍较为粗疏的情形背后,亦可反映出以“守在四夷”为核心的传统边防理念的深刻制约。
那么,清廷在与俄国划定具有近代意义的国界之后,何以迟迟未能形成近代国界观念?笔者认为,天下主义是此中一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清朝的边界观念,并非孤立存在的认识,而是根植于传统天下主义的一种意识。而清朝所依据的天下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颇强的包容特性。因此,即使天下主义受到一定的冲击,仍可为传统边界观念的继续运行提供理论支撑。下文将对《尼布楚条约》后的天下主义演变及其对边界观念的制约略作分析。
新知的接受,是思想变迁的常见动因。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是清朝接触西方国际法的一个早期契机。尽管有研究者指出,康熙在中俄谈判之前,极可能会向其所器重的耶稣会士徐日昇和张诚咨询有关西方交往规则的情况[27]114-116;但张诚日记中的一个细节从侧面体现出康熙对国际法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的钦差大臣们曾经得到皇帝的明白谕旨,应当以基督教徒的上帝名义为和平宣誓。他们有理由相信,没有比以真主名义宣誓,更能影响俄国人,使他们坚定不移地信守和平的了。”[28]45正因康熙对西方条约效力背后的国际法理论缺乏了解,才会分外看重以“真主”名义来宣誓。而康熙之所以认为俄国会信守宣誓后的条约,与耶稣会士的信仰虔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关[29]26。至于清朝谈判代表们的相关认知,张诚更是直言他们“对于国际公法完全陌生”[28]31。显然,这种新知的接触,是难以产生对天下主义的反思的。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也未对天下主义形成有力冲击。清朝前期,中国周边仅有北方俄国能对边疆构成较大威胁。康熙与雍正时期,俄患与准乱交织,为了化解危机,清朝主动与俄国采用条约的形式明确划定边界,但并未动摇天下主义。《尼布楚条约》订立之初,议政王大臣等奏称:“鄂罗斯国人,始感戴覆载洪恩,倾心归化,悉遵往议大臣指示,定其边界。此皆我皇上睿虑周详,德威遐播之所致也。”[17]578完全将中俄平等的划界订约修饰成清朝对俄国的一种恩惠。虽然康熙、雍正曾将俄国视为“敌体之国”,与之对等谈判划界,但按天下主义,这并不意味中俄两国处于平等的关系[13]引言,xvi。随着中俄部分国界的划定以及西域的平定,清朝不再像过去一样可能面临沙俄和准噶尔联盟的危险。而当时俄国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入侵,“遵循一些渐进步骤和慎重态度,不去惊扰中国人”[30]161。况且,该地与俄国之间还有哈萨克等藩属作为“屏障”。故对清朝来说,在西北地区并无划定中俄边界的迫切需要。在此形势下,清廷对俄国的定位也开始变化。如乾隆征服准噶尔后,便要求沙皇对其臣服[18]351;并否认过去视俄国为“敌体之国”的事实,对俄政策重回“朝贡礼”路线,从而将其纳入天下秩序之中[31]80。
由此可见,天下主义非但未因中俄订约划界而动摇,甚至自乾隆中期起还有强化的趋势。天下主义的稳固与强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中国近代国界观念的形成。其一,天下主义拒绝平等的国际关系,乾隆更是不再承认有“敌体之国”。在此情形下,礼仪问题便会成为对等谈判的严重障碍,遑论缔约划界。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和1805年俄国戈洛夫金使团的来华遭遇[32]103,便可表明这一点。其二,“天下”理想的膨胀,会造成边界的淡化。成书于乾隆后期的《清朝通典》有谓:“东瀛西蒙,环集幅辏,固已无边之可言,而亦岂列代防御之术可比论哉!”[33]2729即是追求“无边”的天下一统的表达。其三,天下主义还会抑制边防意识的发展。雍正与乾隆时期,清朝为加强中朝边防曾两度欲沿鸭绿江近岸设汛和开垦边外荒地,但均因朝鲜反对而作罢。乾隆感慨地说:“此因怀柔小邦之意,但屡以难行之事,俯准所请,辄为停止,于国家体制,亦为不合,转为轻视,曷若不举行之为愈也。”[23]99显然,较之加强宗藩边防,怀柔属邦在乾隆心中更为重要。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天下主义对边界观念的制约,我们可以西方的情形稍作对比。17世纪后半期起,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在欧洲国家之间逐步形成[11]264。这种国界观念,产生于欧洲诸国平等的国际秩序之中,以国际法为基本规则,以主权国家理念为思想基石⑥。正是基于这种主权国家理念,西方国家才处于一种平等而竞争的关系之中,才形成一种明确的“自我”与“他者”的意识,才具有确立清晰的、固定的边界,并对领土进行绝对的、排他的管辖的要求[35]6。相比之下,中国长期处于以自身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之中。这一秩序以天下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据,讲究尊卑有序,拒绝多元平等。与主权国家理念下的平等、竞争的关系不同,中国的天下主义终极目标是天下一统、世界大同。而这种追求与目标,恰与订约划界的取向相抵牾。由此可见,中国边界观念与西方近代国界观念形成差异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前者秉持的是天下主义理念,而后者依托的是主权国家理念。
四 结语
过去的相关论著多强调《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对清朝边界观念产生的刺激作用,但就历史实际而言,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或许更加显著。如本文所揭示,早在入关以前,长期身处敌国环逼的辽东局势之中的清廷,已形成共定边界、各守封疆、互遣逃人、严禁私越的明确意识。这种意识,为康熙主动提议划定中俄边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尼布楚条约》的订立。同时,渊源有异的中俄边界观念,存在一定相通之处,亦有利于此约的顺利缔结。
1689年以后,清朝固有的边界意识,虽因中俄订约划界而有所发展,但在晚清以前这种转变较为有限,远未形成近代意义的国界观念。其深层原因在于,清朝的边界观念是基于中国传统天下主义而存在的。而清朝的天下主义,非但未因沙俄入侵和中俄缔约的冲击而动摇,反而在乾隆平定西域以后有所强化,严重制约了清朝边界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相比之下,17世纪后半期,西方近代国界观念的产生,得益于欧洲多元平等的国际秩序的孕育与主权国家思想的激发。故就根本而言,清朝前期边界观念与西方近代国界观念的差异,不在于“界”的意识,而在于“国”的理念。
正因如此,对清朝而言,在意识上真正接纳近代国界观念,须以对天下主义这一自身根本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变革为前提,这无异于一场思想上的脱胎换骨。晚清以降,随着疆土频遭割让、藩属接踵丧失,天下主义也日益动摇,中国适应近代国界理念的漫长而痛苦的脱胎换骨之路方真正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