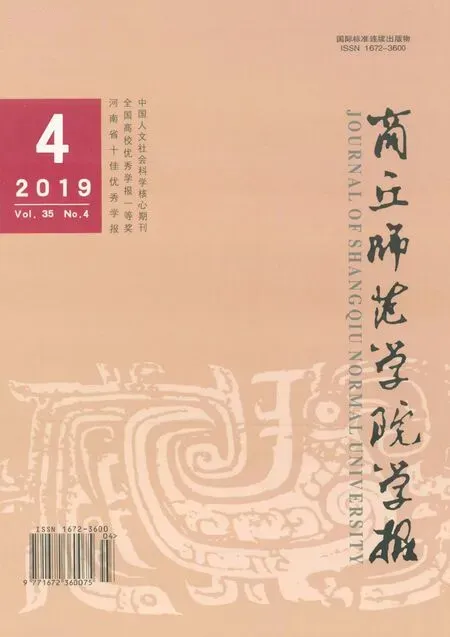法律规避误区的澄清
张 新
(华东政法大学 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法律规避通常系指当事人事实上意欲从事某种法律上禁止之行为,却通过为法律之文义未包含之法律行为架构方式,最终实现了相同的经济上结果[注]①法律规避亦系国际私法中的一个固定概念,指当事人借助冲突法规则中可变连结因素,故意避开本应适用之强行法而使利己法律得以适用之行为。参见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规则和原理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1页。但本文均在国内法意义上使用法律规避概念。[1][2]。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1款第7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3项均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行为无效。学理上多认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系避法行为(或脱法行为)[3][4][5]。司法实务中,当涉及法律规避时,法院亦多援引该规定径直判定行为无效[注]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4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1054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766号民事判决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规避”一词的使用颇为丰富,如规避风险、规避执行[注]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法〔2011〕195号)。、规避损失、规避制裁、规避准据法[注]④法律规避本就是国际私法的一个概念,指回避原本应当适用的准据法,而使他国或地区准据法得以适用的行为。、避税、规避法律等。那么究竟何者属于我们讨论的私法中的法律规避?法律规避与规避行为、法律行为、违法行为以及无效行为关系为何?对于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尚缺乏清晰的认识,且不乏理解上的误区,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法律规避与规避行为
法律规避行为概念于罗马法后期始逐渐形成,又称为“对法律的欺诈行为(in fraudemlegisagere)”。我国学者通常采用“法律规避”[3]“规避法律”[5]“避法行为”[2]等称谓,在台湾地区民法上又称之为“脱法行为”[6]333[7]224[8]210,德国法上对应的称谓为“Gesetzesumgehung”[9][10][11]731[12][13]181-182。在学理或实务上,人们为了使用上的简便,通常以规避行为指代法律规避行为。但必须明辨的是,二者并非完全等同之概念。规避行为其实系法律规避行为的上位概念。以规避之客体为分类标准,不仅包括法律规范,还包含约定之负担。换言之,规避行为除法律规避行为类型外,还涵盖规避约定内容之行为。
兹举一例加以说明,甲项目公司有一块地A,系甲公司之唯一或主要资产,甲未确定是否出卖,乙十分想购买,于是主动找到甲,约定了一个优先购买权,支付给甲10万元。后来丙公司欲购买该地,亦找到甲,由于甲、丙公司之间关系较好,此时甲欲出卖A地于丙,但碍于乙之优先购买权,于是甲、丙决定由丙公司吸收合并甲公司,从而实现取得该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目的。甲、丙之吸收合并行为,即实现了规避甲、乙之间约定负担之目的。因为自客观经济效果而言,丙公司取得了该地块的所有权,而乙公司约定之优先购买权落空。
法律规避与合同规避(Vertragsumgehung)系规避的两种类型,尽管我们在日常使用中,多指代前者,但不妨碍后者之客观存在。正如学者弗卢梅精准地定义,规避行为,系当事人通过法律行为之架构方式规避某一法定或意定规则[14]350。在处理路径上,前者关涉对相关法律规范之解释,后者涉及对意思表示之解释,具体而言,系补充性契约解释。
补充性合同解释是对存在漏洞的契约所作的补充。首先,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确认合同成立后,才可能对合同进行补充性解释。此时,可能发现合同中未就某一事项作出约定。该结果可能出于当事人双方故意之不作为,因为他们认为非为必要,也可能系无意之不作为,因为忽视了特定问题或者不可能考虑到该问题。补充性解释的前提是,法律行为中存在漏洞,法官通过漏洞填补进行补充[15]。而是否存在漏洞,系通过对法律行为进行解释来查明。只是该解释不应只停留在对效果意思之查明,还应对引起效果意思之动机及其他情况进行分析。须填补的漏洞在以下情况中存在:缔结法律行为之当事人没有或者以非正确的方式对特定情况加以考虑。无论是当事人在法律行为缔结时忽视了既存之情况(原生漏洞),抑或该情况嗣后发生(次生漏洞),对解释不生影响。
如果在法律行为中发现了需要加以规范的漏洞,那么法官必须对其进行填补。法官须查明,假如当事人考虑到了未想到的情况并且注意到了诚实信用原则及交易习惯,那么其所欲为何。鉴此,其决定性作用的系假设之意思,而非当事人之真实想法。对假设之意思的查明,必须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评价出发,并提出以下问题:在知道该漏洞的情况下当事人会如何合理地进行约定。在填补漏洞时,应当以当事人的评价作为基础。尽管补充的契约解释以假定的当事人意思为依据,但却通过假设当事人原本就对实质上正确的东西有所意愿,从而致使那种假定之意思向客观转向。如德国帝国法院指出,被表示出来的东西,也包括从合同条款的整体关联中推出的不言自明的结论;并以此为出发点,当事人基于合同目的及交易观念,愿意作出此种(补充之解释)安排,且依照由双方确立之原则也已作出了该种安排[16]96。有鉴于此,补充之解释不仅仅因为当事人想到了,就会作出如此之约定,还应将其视为由整体行为之关联性所附带之内容。
补充性解释是一种使个案实现正义的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16]99。法官在填补漏洞时如何考虑当事人之评价取决于个案中的情况。因此,必须考虑案件中的所有情况,如动机、目的、交易习惯、利益状况等。通常而言,探明当事人所追求之目的起决定性作用。例如,乙将某书店转卖给甲,一个月后,乙又在隔壁重新开了一家书店。甲认为,乙不应当与自己竞争。乙反驳说,并不存在此类竞业禁止,因为他们并未在合同中对此进行约定。该案中,乙之行为会对合同造成广泛的损害,结合契约目的、诚信原则,如果当事人考虑到该情况,将会就特定期间内的重新开店禁止作出约定,如此,漏洞即得到相应补充。
概言之,补充性合同解释以假定的当事人意思为依据,而假设的当事人意思之探寻,以当事人于契约上所作的价值判断(契约目的)作为出发点,基于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而为认定[7]327。而合同规避系当事人通过为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之内容,实现逃避合同负担之结果,致使合同之目的落空。因此,面临合同规避问题,法官需要从事的,系判断是否存在契约漏洞,是否进行补充性契约解释,以及作出何种补充解释。倘当事人所为之行为恰巧系补充之解释内容,则约定之负担依然发生。有鉴于此,合同规避问题的本质系补充性合同解释问题。
在法律后果上,合同规避与法律规避存在区别,前者非涉及法律行为效力问题,而仅关涉约定之负担是否发生的问题。以前文所涉案件为例,查明假定之当事人意思,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约定之优先权合同”的目的在于当项目公司甲欲出售地块时,自己享有优先购买之权利。尽管双方未对甲能否被其他公司吸收合并在合同中作出约定,但考虑到甲公司系项目公司,该地块系其唯一资产,其被他公司吸收合并与其直接出卖该地块并无二致,因此,根据契约目的、诚实信用原则,对甲公司之被吸收合并行为之禁止,构成了优先权合同之不言自明的组成部分。如此,契约漏洞即得到相应补充。而甲公司违反该内容,则约定之负担发生,乙可基于约定向甲主张该优先购买权,即使甲不存在,乙亦可向丙行使该权利。
除此之外,笔者发现,实践中法律规避之外,还存在一种类于合同规避,但又不完全相同之规避行为,当事人规避的既不是法律,又非合同上约定之负担,而系附条件要约或承诺之“条件限制”。例如,在吕培从与福建省南安市华洲石业有限公司股票权利确认纠纷案中,原告吕培从与被告华洲公司签订《委托代购合同》,约定吕培从委托华洲公司代购南安农村合作银行股权400万股,股本金额由吕培从承担,华洲公司出面购买。股份虽在公司名下,但实际为吕培从资产而由公司代为持有。根据2010年6月22日所发布的《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公告》,明确规定不募集新自然人股东。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吕培从与被告华洲公司签订《委托代购合同》,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增资扩股公告》虽然规定不募集新自然人股东,原告吕培从存在规避该公告的行为,但该行为的目的在于购买福建南安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并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法院此项认定是否妥当,暂不具论,其须强调者,系本案法律行为所规避之客体,并为规避行为类型上的重要问题。
依笔者所见,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公告系“附条件之要约”,而案涉委托代购合同正是为了规避该“条件限制”,从而实现订立合同之目的。从性质上而言,该“条件”非为法律,亦非合同之负担,因为合同还未成立,充其量可以称之为“承诺之负担”。鉴此,规避之客体为要约之条件限制。类似情形还可能发生于房屋买卖情形。例如,房产商甲为回馈家乡,开发了一栋房屋,以市价的一半出售,但明确表示只售卖给自己所在村的村民。现不符条件的乙与未有资金的村民丙签订《委托代购合同》,约定由丙出面购买房屋并代为持有,但房屋实质系乙所有。
综上,法律规避仅系规避行为之一种,尽管属于最为典型的类型。除法律规避外,规避行为还包括合同规避,以及规避要约之“条件限制”。
二、法律规避与法律行为
法律规避行为系国内私法中的概念,其前提系以法律行为之架构方式来规避法律。同时,只有规避行为属于法律行为,才有私法上研究之意义,因为只有法律行为才有效力瑕疵的问题,才可被施以法律上的价值评价。
司法实务中,诸多“规避”与本文所论述之规避行为、法律规避或法律规避行为无涉,只因其全程中并无任何一个法律行为存在。
例如,“故意提高诉讼标的额规避级别管辖”类案件,法院指出:“为了避免当事人故意规避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应对起诉进行形式审查,并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表面证据所指向的数额确定诉讼标的额,进而作出判断。”[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辖终326号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初14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裁定书。其实,关于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专门有一个批复,指出:“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诉讼请求从而加大诉讼标的额,致使诉讼标的额超过受诉法院级别管辖权限的,一般不再予以变动。但是当事人故意规避有关级别管辖等规定的除外。”[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第2条。
又如,“单纯隐藏财产规避执行”类案件,当事人通过单纯将金钱、财物隐藏于他处方式,以规避法院执行[注]参见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宁02执异13号裁定书。。
前述案件中,尽管法院在认定上均使用“规避”一词,但应明辨,法院充其量只是在“主观目的”层面使用该词,客观实际上,其与法律规避行为无涉,因为从中压根无法找出一个为了规避目的而为的法律行为。
因此,法律规避行为首先系法律行为,私法中对法律规避之研究的最终落脚点,系对法律规避行为之法效果判定上。
三、法律规避与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顾名思义,当事人之行为直接违反了法律规定。换言之,当事人之行为符合了法律规范之构成要件,被涵摄在法律规范的射程之内。例如,当事人之间签订贩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玳瑁”之契约,直接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七条第1款、《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之规定,系直接违法行为。又如,当事人之间签订买卖人体器官“肝脏”之契约,依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系直接违法行为。
法律规避的一个关键特征,系不违反法律规定之文义(Wortlaut)。易言之,规避行为并不符合法律规范之构成要件,不能直接被法律规范所涵摄。比如,当事人为了规避器官买卖禁令,将器官买卖合同拆分为器官捐赠合同以及器官赠予合同。由于法律不禁止器官捐赠,故不构成直接违法,但实现了相同的经济上结果。
法律规避与直接违法之间存在两个维度的问题:其一,通过意思表示解释认定的法律事实直接落入既有规范之射程范围,系直接违法,或者将本属规避之行为,强行进行法律行为解释,认定为直接违法,实践中最为典型的例证系“名为……实为……”类案件;其二,通过法律解释,更具体而言,系目的论扩张解释,从而将案涉情形涵摄于内,亦系直接违法(或失败的规避)。下文分别详述之。
(一)法律规避与“名实不符”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一类案件,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名为……实为……”,并据此作出判决。有学者认为,这属于“虚伪行为”之一种[17];亦有认为,其构成法律规避[注]在“长春中振发展有限公司与长春电影制片厂房地产开发公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纠纷上诉案”中,一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即认为,长影厂房地产公司与中振公司签订的《关于联合建房协议书》是名为联营,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双方以联建为名,规避法律、行政法规,以达到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之目的,故双方所签联建协议无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经终字第225号判决书。。笔者对这两种观点皆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名为……实为……”类案件,当事人可能存在避法目的,可能涉及隐藏真意目的,但其本质是意思表示或法律行为解释问题,处理上是拨开字面上的“云雾”,探究当事人真意的过程。其既非虚伪行为规范规制之领域,亦非规避制度辐射之范围。同时不同于“阴阳合同”,后者客观上存在“一真一假”两个法律行为,而前者仅是对“同一事物”认识上的不同而已,一般仅存在一个法律行为。例一,甲、乙之间从事毒品交易行为,为掩人耳目,称之为奶粉买卖合同。例二,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件投资纠纷案中指出,案涉投资合作关系,实质是投资人仅提供资金,但是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无论企业盈亏,投资人均享受每月固定回报。这种合作模式违反了合作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属于“名为合作,实为借贷”[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例三,最高人民法院在李建国与孟凡生、长春圣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中指出:“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范围为《资质证书》中规定的工业与民用建筑承包范围,也就是说,究其合同约定之实质,该合同‘名为内部承包,实为建设工程施工企业资质租赁或者有偿使用’。李建国在庭审中亦自认其经营建和分公司,主要是利用圣祥公司的资质方便其对外承揽建筑程。换言之,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之实质并非承包法律关系。建筑施工企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不仅要求此类企业要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注册资本,而且要具有与所从事的建筑施工活动相适应的专业资质。实践中,一些建筑施工企业中所谓承包或者租赁经营的实质,是不具备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以承包或者租赁形式,掩盖其借用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进行施工的目的,由于借用资质进行施工是法律及司法解释所禁止的行为,故与之相关的承包或者租赁经营合同以及施工转分包合同亦为法律所不容。”[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49号民事判决书。上述案例中只存在一个法律行为,且法院也只是根据掌握的证据,对当事人的意思作出实质认定而已,故不同于一真一假形式的“阴阳合同”,且一般按照实质内容认定后,行为即自动落入法律规范之涵摄范围,构成直接违法行为,从而与规避无涉。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诸多名实不符之认定不免存在僭越之嫌,似超越法律行为解释之一般规则。例一,在一则涉及采矿权纠纷的案件中,当事人通过投资方式入股煤矿项目,并约定其投资主要用于采矿权价款等费用支付,法院认定该协议是“名为双方合作经营,实为采矿权购买及权益分配”,而其行为未经依法批准,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5项、《矿产资源法》第六条之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注]参见“林为曾、陈永河合伙协议纠纷再审案件”,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28号民事判决书。。例二,在朱岳海与海南万宁大花角海洋文化城有限公司、赵守仁股权纠纷案中,大花角公司的股东将其100%股权全部转让给新股东,公司资产中包括海南省万宁市港北镇某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一审法院即认定名为股权转让,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由于该宗土地目前既没有形成工业用地或其他建设用地条件,转让不符合法定条件,故双方之转让行为系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行为[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二终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早在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已有相关答复[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练志伟与被上诉人陈如明及原审被告林惠贞、郑秀英及原审第三人福州市常青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6]民四他字第22号)。案情简化如下:福州常青公司原股东练长清、林惠贞(甲方)以股东代表练长清的名义与陈如明(乙方)签订了一份《企业股份转让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权属常青公司的工厂包括厂区内的建筑物、水、电设施等及凡属常青公司的财产100%转让给陈如明;甲方办妥市计委立项手续后,乙方应无条件支付甲方股份转让金人民币265万元。甲、乙双方即办理企业法定地址以及法人代表变更。合议庭多数人认为,讼争合同的性质,应从合同的名称、内容去审查认定,同时还应考察签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本案合同的名称、合同订立的主体、内容及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分析认定,本案讼争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正像其所表述的那样,应定性为股权转让合同。但少数人认为,本案合同形式上是股权转让合同,但内容上明确约定所转让标的,仅系常青公司拥有的工厂厂房、设施及土地使用权,既未包括公司拥有的其他财产,也未接管职工,实质上转让的是划拨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故应定性为财产转让合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本案合同定性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答复,赞同多数说意见,理由主要有三点:其一,合同名称本身为“股权转让合同”;其二,合同甲方当事人为股东,而非常青公司,故无法实现公司财产之转让;其三,从合同诸多条款之文义、体系解释来看,转让之标的物确系公司股权,此为双方当事人之真意,否则亦无须约定法定代表人变更等事宜。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案涉合同为股权转让合同。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强调,本案常青公司拥有之土地使用权财产系划拨用地,因此公司股东通过股权全部转让方式,是否实质在移转土地使用权,应予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的认定殊值赞同。依照其认定思路及精神,上文例一、例二之法院行为定性存在问题皆不言自明。“名为……实为……”系法律行为解释及定性问题,因此法官不能超越法律行为解释之一般规则,应以双方当事人的真意为据,超越当事人意思之行为定性系事实认定错误。倘问法院为何如此青睐该种处理方式,究因如此为之,案涉行为自动落入法律规范之涵摄范围,构成直接违法,法官之朴素的法感情得以“抒发”,且按照此种案件处理方式,不可能再存在法律规避,所有的法律规避行为都将落入直接违法行为的“口袋”。但该种做法,破坏性极强,一旦流于形式,会严重戕害意思自治,将所有法律行为置于无效风险之下,绝不足采。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名实不符”之行为认定应持一种极为谨慎之态度。
(二)法律规避与扩张解释
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之界分,理论上以言,甚为明晰,但实践中不无疑义。在法学方法论上,“可能之文义”系划定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之界限,实在不能发现其他的界分标准,此种界分也受到学界及实务界的普遍承认,具体指依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之语言用法,该用语能够指称之意义[18]202-203。但可能之文义未必始终能精确界定,因此在某些事例,究竟是在作扩张解释,抑或通过类推适用在作漏洞填补,有时不无疑问。折射到规避领域,如果通过扩张解释可以涵盖案涉情形,则仍系直接违法,又被学者称为“失败之规避”。易言之,规避必须逾越语言上可能之文义范围,依法律可能之文义,作最广义的解释,尚不能使之涵摄于案件事实时方可。例如,德国法上规定,禁止养老院的老人通过遗嘱将护理人员列为继承人,现某老人将其财产遗赠给其护工的配偶。无论将“护理人员”如何作扩大解释,亦无法包含非从事护理工作的护工的配偶,故不满足规范要件,不构成规定之直接违反,但德国法院认定其构成法律规避,进而判决遗赠行为无效[19]。
但是,由于可能之文义范围之非得准确界定性,所以于规避情形,可能出现扩大解释与法律续造之争议问题。兹举一例加以说明,近期影响较大的“福建伟杰投资有限公司与福州天策实业有限公司以及第三人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业信托纠纷案”中[20][21][22],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签订《信托持股协议》约定,鉴于委托人天策公司拥有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亿股的股份(占20%)的实益权利,现通过信托的方式委托受托人伟杰公司持股。受托人伟杰公司同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明显违反了《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中,笔者认为,要作出准确的结论,必须首先辨别 “委托持股” 与 “信托持股”的关系,易言之,前者在文义上能否通过平义解释甚至是扩大解释的方式包含后者,不无疑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为直接违法;反之,至多可通过进一步的立法目的探寻,判断可否类推适用之。
此外,根据原则上的一致意见,法律规避有别于法律避免(Gesetzesvermeidung),后者不违反规范意旨。而法律规避的特殊性在于,虽不违反规范文义(Wortlaut),但违反规范的内容(Inhalt)。类似的表述,如果通过滥用他种法律行为型构方式,致使强行性规定的规范目的落空,则系属法律规避[23]91。规避之存在,导致强行法的目的被破坏,其他的法律上的手段可能性被滥用。法律规避被看作是对规范意旨之违反,该意旨是通过目的性解释查明的。因此,学者Teichmann批评该定义,其会导致人们将法律规避与法律解释相提并论或同质化,但按照主流观点,法律规避仅存在于被规避规范之解释界限被逾越时。鉴此,法律规避与违法行为存在共性,即行为经济上结果相同,且都违反了规范意旨。所以对于法律规避行为(狭义),为了贯彻规范目的,不致使立法目的落空,在德国法上,通常采用类推适用相关法律规定手段进行漏洞填补。
综上所述,法律规避与直接违法行为区别在于,法律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之构成要件。共性在于,行为之经济上结果相同或类似,且违反规范意旨。
四、法律规避行为与无效行为
法律规避行为与无效行为关系,具体体现为二者是否必然存在包含关系。如果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3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指的就是法律规避,由于其法定效果仅系无效一种,所以可能结论很简单,即法律规避行为是无效行为之一种。但该规定本身广受诟病,无论是其构成要件上之模糊性,还是其法律效果上之单一性。有鉴于此,学界、司法界皆提出了修正之方案[17]。笔者无意在此展开论述,仅欲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即违反禁止性规定,法律行为是否一律无效?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之但书内容,答案不言自明,否则该但书规定毫无意义。既然直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法律行为非一定无效,易言之,行为或有效,或效力待定。那么当事人采用更弱之迂回方式,行为反而一律绝对无效,遭受更严苛之负面法律评价,无论按照“举重以明轻”方法,哪怕依据“同等对待原则”,结论都无法让人信服。鉴此,至少可初步作一结论,法律规避行为非一定系无效行为,可能有效可能存在效力瑕疵。
从本质上讲,法律规避仅系对一种客观现象的描述,仅具描述性功能(deskriptiveFunktion)[24]11,伴随着此种现象,法律适用者必须审查既有规范之意旨是否得到贯彻,存在法律漏洞与否,应否进行法律续造,具体而言,系可否类推适用相关规范于案涉法律规避行为。所以法律规避行为的后果非为直接无效,而是得否类推适用被规避规范,最终法律效果如何,取决于该规定之规范性质和立法目的。如果该规范系单纯强行规定,则行为一定发生效力瑕疵;如果其性质系禁止性规定,则须援引《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管道条款),并结合规范意旨,经由比例原则手段进行法律行为效力判定,方能得出妥适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