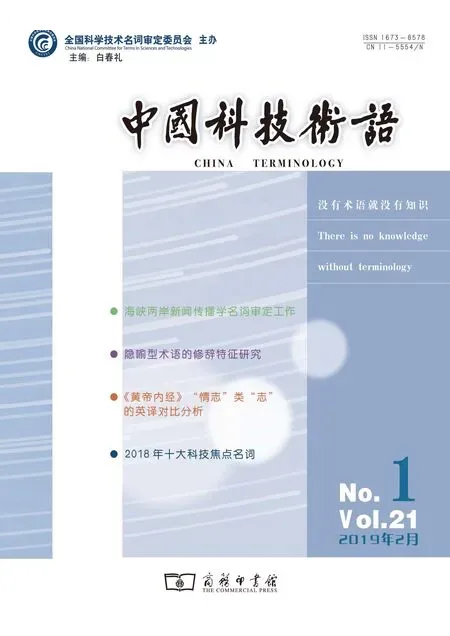哈萨克医学术语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
古力沙吾利·塔里甫 木合亚提·尼亚孜别克
(1.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2.新疆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引 言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腾飞,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医学的一个分支,哈萨克医药学(以下简称“哈医”)教育也得到了国家的扶持,由过去的中专教育提升到了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作为一个跨境民族,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北疆和哈萨克斯坦的中亚丝绸之路上,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兼收并蓄了多种文化思想,形成了融汇多种医学思想的传统医学[1]。其中既体现有中医的天人合一的医学思想,如讲究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和时辰对个体体质、脏腑的影响,在治则方药中要求根据时辰、环境和个体的RAY特性等来确定个体化的保健或治疗方案,还在长期畜牧生活中大量解剖牛马羊的实践中推测出各器官、系统的功能活动,形成了特有的24脏器学说、循环学说、六元学说和十种平衡学说等独具特色的医学观。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作为传统医学的一个分支,哈医古籍的现代哈语翻译和汉语翻译取得了长足进步,相应地催生出大量的哈医新术语。
一 哈医教材中术语的现状
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哈医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新疆北疆多地建立了哈医医院或哈医科,对哈医的需求量也在逐步增加,同时,哈医古籍的现代哈语翻译版本也不断涌现。其中的术语翻译有音译、直译和意译的,五花八门、各持己见。但哈语术语丰富,例如,即便是具有最常见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气管炎”词义的名词就有很多种说法,图1按出现频次高低排列。

图1 同一语义不同表达的名称举例
试想一下,若将哈医中高频使用的、具有同一语义的这些疾病名称的词音译成汉语,其中引用的个别汉字再稍有所不同,在目前信息电子化的时代,应用计算机软件检索时,就可能被当成新词,这无疑会对后续哈医数据的整理和医学知识的交流形成不必要的障碍。
1. 术语意译与音译共存
虽然哈医本科教材的整理出版是属零的突破,具有很大的意义,但目前教材中术语的翻译既有以原文为导向的直译或音译,也有以读者为导向的意译或兼用的混杂现象。如哈医最基本的哲学思想为万物均具有“六元”属性,且认为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六元”,对事物的掌握才会全面。故“六元”为其最核心的术语之一,而“六元”的翻译在《哈萨克医学基础理论》(以下简称《哈基》)中以意译为主,分别翻译为“天元”“地元”“明元”“暗元”“寒元”和“热元”。而在《哈萨克医诊断学》(以下简称《哈诊》)中,大多名词术语的翻译却采用了音译,如“六元”被翻译成“阿勒特突固尔”,其中的“寒元”用“苏吾克突固尔”指称,“热元”用“俄斯特克突固尔”等指称。而在《哈萨克医内科学》(以下简称《哈内》)教材中,“寒元”与“热元”的音译词中的一个或两个汉字又变成了其他的同音异形字。
哈医在强调事物都具有“六元”属性之外,还强调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所处的外环境及所构成体系或整体的各组分间存在着关联性,故要求对事物的分析除了其所具有的“六元”属性外,还应分析其与内外环境的关联性。而内外环境中的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就是“RAY”。因此“RAY”一词在哈医中使用的频率也极高,此词有翻译成“气候”,也有翻译成“热阿依”。构成“RAY”的四大突显成分在《哈基》中按意译为“寒”“热”“风”“湿”,而在《哈诊》和《哈内》的教材中“风”又被音译为“恰勒达玛”,“寒”被音译为“俄孜合玛”,“湿”被音译为“斯孜那”,“热”被音译为“胡孜那”,等等。且在《哈诊》和《哈内》教材的不同章节中音译词中的汉字还有所差异。
以下仅列举归纳第一版教材中对哈医核心名词“六元”和“气候”的翻译版本,见图2、图3。
2. 术语音译泛化
哈医本科教材中很多名词的词义已很明确,翻译时完全可以直接意译,却大量地采用音译,尤其是在《哈诊》教材中。比如:在《哈诊》中词义为“生命状况”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江斯尔格”,而词义为“详细状况”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曼斯尔格”;词义为“全面诊断”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昂尕热木达玛”,词义为“现正诊断”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纳合达玛”;词义为“自汗”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哈斯康格铁热”,词义为“盗汗”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加斯康格铁热”,词义为“大汗淋漓”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阿斯塔尔勒铁热”。哈医在描述不同“脉”的术语中,根据脉搏跳动的速率、节律、脉中体液含量、脉中体液黏稠度、脉管壁紧张度等的差异及不同的排列组合把脉分成了很多种,原本可以就按词义翻译,简洁明了,可教材中也采用了音译。如词义明显为“细脉”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和勒达玛脉”,而词义明显为“数脉”的词采用了音译形式的“孜尔合玛脉”等。这种仅为了凸显特色就将词义已经很明确的词采用音译的做法,暂不说对学术和教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也增加了与其他医学同行间交流的难度,会成为约束自身发展的巨大障碍,实不可取。

图2 哈语“六元”相关术语的汉语翻译举例

图3 哈语“RAY”相关术语的汉语翻译举例
3. 疾病术语的意译
大量的音译不可取,但意译不当弊端也不小。哈医临床课程的教材中对疾病名称的翻译借用了中医疾病的名称。如在《哈内》中将24个脏系之一的肾系中常见的尿液异常表现的疾病群名称意译为“淋证”,将肾系中常见的排尿困难类疾病群名称意译为“癃闭”;又将24个脏系中腺系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名称意译为“瘿病”,将肺系中常见的由外感病虫感染所致的疾病名称意译为“肺痈”“肺痨”等,这比起音译是极大的进步,但为了走捷径,这种直接照搬的译法也有其不足。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的交流活动,不仅是单纯的语言转换。众所周知,中医学理论体系独特,是几千年来的文化结晶,是一门独立的完整的科学学科,既有自己的独特的语言特色和风格,又有很深的古代哲学背景。许多中医用语词义深奥,对没有中医基础理论知识的人而言是较难懂的。哈医相对而言只有数百年的历史,理论体系与中医有相似性,但差异也不小,哈医为了走捷径在疾病名称的翻译上只借用中医的术语名称而缺乏相应的理论底蕴,对民语言招生的哈医专业学生而言,正确理解的程度有限。而如果哈医学生按哈医理论理解的“淋证”“癃闭”等与实际中医语义中的“淋证”“癃闭”存在差异的话,将对中医术语正确翻译成哈语造成人为障碍,也将对真正中医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各国的传播造成不小的负面影响。
二 哈医术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在科学领域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中为避免产生歧义,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很重要。术语“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2],术语和客观事物之间是一种标记关系,即用一个语词符号标记一种客观事物包含的概念。即概念将所感知的事物的本质特征与属性抽象出来,而术语则用词或短语等语言形式反映概念体系。这种标记化过程表面看是术语对事物的称谓,只是一个符号,实际上术语的语义与事物之间既有约定俗成又有一定理据性的联系,应该是统一和规范的。术语的规范和统一不仅对学科的传承、发展和学术交流影响很大,而且对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随着习总书记倡议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以来,我国仅新疆由哈国前来就医的病患年均远过万人次[3-5],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但患者出院诊断时的病名被翻译成的哈医术语却很不规范,甚至有歧义。如“肾虚”翻译成了“бүирек дарменсздкы”和“еркектктың алсыреуы”,即直译的“肾脏功能减弱”和自以为意译的“男性性功能减弱”,这不仅不符合科技术语的要求,而且“肾虚”的医学范畴也明显狭义化了,其他“脾虚”“血虚”等中医名词的翻译也多停留在字面上的直译,不仅译语太长,而且它们本身具有的医学含义也在不同程度上被狭义或局限化了。这种不规范,甚至错误的术语不仅会影响中医在哈萨克斯坦等国的正确传播,也不利于中国文化在中亚各国的传播。
三 建立哈医术语规范化研究团队的必要性
术语是专业领域中概念的语言指称,是集中体现和负载一个学科领域的核心知识。术语是定义明确的专业名词,是领域专家用来刻画、描写领域知识的基本信息承载单元[6-8],是信息检索和信息提取的重要单元。我国政府一贯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早在1950年就成立了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术语的翻译历来是翻译中的难题。要保证译文的正确,不但取决于对原文的理解,而且还取决于对译文语言的修养。张培基认为:“翻译的过程是正确理解原文和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为理解、表达和校核三个阶段。”[9-11]“创造性地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原文”可理解为,译者把自己从源语所理解的内容创造性地用目的语新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这需要由专业人员构成合作团队共同研究达成共识,体现出原文内涵的“形、神、意”,而不应是每个个体的各持己见的音译或意译。
研究建立规范化的哈医术语团队,不仅对于正确学习和传承哈医具有重要意义,也可为挖掘哈医的精髓,光大祖国传统医学添砖加瓦,为后继哈医药学研究、机器翻译、语料库建设等民生工程建设研究建立基础,并且对底蕴深厚的中国文化在中亚各国的推广具有现实意义。哈萨克斯坦地居中亚,哈萨克语与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塔尔语等语言词根相近,相互交流频繁。因此,哈医术语的规范化翻译不仅对哈医学科本身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各国间的医学交流和促进中医文化的传播都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 结 语
新事物在发展初期除了存在很多不足之外,也会产生出各类新术语,需管理层尽早加以监督和引导。哈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大家族中的新成员,得到了政府大力扶持和挖掘。哈医术语作为哈医学术概念的载体,质量的好坏不仅会影响哈医学术传承和交流的效果,还会影响哈语民众医学知识的普及和与周边国家间进行医学交流的效果,也会影响我国民族语言信息化建设和检索的工作。哈医术语规范化的工作应该尽早得到重视和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