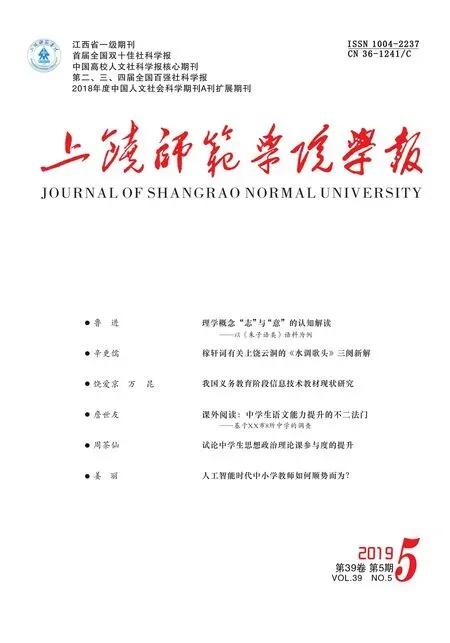论王国维“忧生忧世”思想及其在“人间词”中的体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全才,早年兼攻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诗词创作,中年以后又转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研究王国维一门的学问,尤其是其早年的学术研究,若只局限于此一门学科之中,必然会有管窥之嫌。因为一个人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和文学观是相互渗透、不可割裂的。而在王国维的哲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创作上,确实存在一条可以一以贯之的线索。这条线索就是王国维的“忧生忧世”思想。
一、“忧生忧世”的文化传统
“忧生忧世”之说见于王国维所著《人间词话》第二十五则,其文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1]353王国维在这则词话中通过举例,提出“忧生忧世”思想乃是优秀诗、词作品中所共有的,这实际上也是在表明“忧生忧世”乃是一种跨越各文体之上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特征。那么这种思想特征的涵义到底为何呢?由于王国维并没有直接对“忧生”和“忧世”二词下直接的定义,我们只能从王国维所举的例子中去一探究竟。
王国维所谓的代表了忧生之意的“我瞻”二句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的第七章“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2]441对于这章诗义的理解主要有两大派:第一派以郑玄为代表,《毛诗笺》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驾,今但养大其领,不肯为用,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蹙蹙,缩小之貌。我视四方土地,日见侵削于夷狄,蹙蹙然虽欲驰骋,无所之也。”[2]441按此意,“我瞻”二句则为忧世之意;第二派观点则针对《郑笺》提出反对意见,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说:“刘向《新序》引《诗》‘驾彼四牡,四牡项领’而释之曰:‘夫久驾而长不得行,项领不亦宜乎?《易》曰:‘臀无肤,其行趦趄。’此之谓也。’其意盖谓久驾而不行,则马颈将有肿大之病,其说当本《韩诗》,与《笺》言‘养大其领’异义。”[3]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转引前人观点,亦与马瑞辰相同,更进一步的阐释了其象征含义:“《潜夫论·三式篇》:‘人情莫不以己为贤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诗》云:‘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汪继培注:‘此引诗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则以四牡项领而不得骋,喻贤者有才而不得试。’《中论·爵禄篇》:‘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时世之不遇。’《诗》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伤道之不遇也。”[4]王氏所举诸说虽立足于贤者、君子之忧生,但仍然强调了时世的昏暗是诗人忧生的客观原因。方玉润论此则更为详细:“尹氏为政,失在委任小人,且多姻亚;而又‘弗躬弗亲’,政出私门。故多不平,以致召乱。天人交怒,灾异迭兴,流言四起,而犹不知自惩。偶有规而正之者,反以为怨。此家父之深以为忧也……既知其无救正,‘乱靡有定’,顾瞻四方,不知逝将焉往。”[5]由以上两派观点来看,“我瞻”二句兼有忧生和忧世两种内涵。而对于晏殊之词“昨夜”三句的意境,王国维曾解释为“即所谓世无明王,棲棲皇皇”[6]。盖个体之“棲棲皇皇”是因为“世无明王”,王国维以此举例,更加说明了其“忧生”思想中亦兼有“忧世”思想,“忧生”是在举世皆无出路的情况下对于个人命运的深沉思考。
王国维所谓的代表了忧世之意的“终日”二句出自陶潜诗《饮酒》第二十首。上句化用阮籍之典,《晋书·阮籍传》谓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7]阮籍曾心怀兼济之心,逢魏晋易代,天下名士减半之时,只得托醉避祸;下句化用《论语·微子》中孔子使子路问津于“辟世之士”长沮、桀溺之典[2]2529。把二句结合起来看,则有于乱世中独善其身之意,兼有“忧世”“忧生”两种内涵。王国维以此举例,则说明其“忧世”思想中亦兼有“忧生”思想,忧世是在个人理想(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往往即是平天下)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对于整个天下的命运产生的深切忧虑。
综上所述,则在王国维的语境中,“忧生”与“忧世”互为前提,实不可分。“忧生忧世”思想将个人命运与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主体欲望(企图对命运的掌控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与现实世界的残酷限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是“忧”之真正原因所在。由于主体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每个人的忧虑体现在一人一事上总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往往会把目光投放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主体与世界的这种普遍性矛盾也会被具体的人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所掩盖。这种掩盖若发生在具体的文本当中,那么作者的忧生忧世便可能不会得到大多数读者的认同,从而也无法唤起大多数读者的审美体验。而丧失了普遍性审美体验的文学作品显然不是王国维认可的优秀之作。
那么什么才是王国维真正认可的“忧生忧世”的文学作品呢?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1]45这一番说法正可以看成是王国维“忧生忧世”思想的注脚。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其它两则当中,对其最为推崇的词人李煜之感慨、忧戚作出的深刻阐释也正好符合了上述王国维所论“真正之大诗人”的特点。
《人间词话》第十五则云:“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1]352第十八则云:“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小大固不同矣。”[1]353李煜身负亡国之恸和南冠之耻,以己一人之悲起兴作词,却往往在最后结句处升华至千万人之悲。如“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人生永远之悲哀遗憾与自然之无情相衬托;如“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写出人所贪恋追求之一切美好事物终将消散,而人却对此无能为力。所谓的“眼界始大”乃是李煜能超越自身的亡国之哀痛,来抒发全体人类自亘古以来就有的悲痛——即是主体追求理想的欲望与残酷世界之矛盾,因而这种忧愁和感慨才是他人远远不及之“深”。
由此可见,王国维所推崇的诗人词人的“忧生忧世”乃是超越了一时、一人、一事、一物的忧愁。在“通古今而观之”的“诗人之眼”内[1]380,这种忧愁扩大至忧全人类之生和忧千载万载之世。从这个高度来看,忧生与忧世的内容与对象达到了完完全全的重合,忧全人类之生即是忧千古之世,忧千古之世即是忧全人类之生。
王国维的忧生忧世思想在其自己的词创作当中亦有体现。举几个例子,如王国维感慨七年的漂泊生活而作词《采桑子》,在下片写道:“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8]8从个人羁旅之思写到全人类之漂泊无依的命运;再如苏州吊古之词作《青玉案》:“算是人生赢得处。千秋诗料,一抔黄土,十里寒螀语”[8]33,从对江山美人烟消云散的一人一事的感慨最后上升到对于每个存在主体都将必然走向消亡的哀叹;再如《浣溪沙》一词:“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宵欢宴胜平时。”[8]27从描写人类捕食孤飞大雁这一情节入手,运用象征和对比的手法,将人世间的“吃人”罪恶本质委婉道出,与多年后鲁迅所作《狂人日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再如《浣溪沙》:“曾识卢家玳瑁梁。觅巢新燕屡回翔。不堪重问郁金堂。 今雨相看非旧雨,故乡罕乐况他乡。人间何地着疏狂。”[8]46由燕子回巢这一生活中的小事生发了对整个人类归属与世事变迁的忧虑。王国维的作品中,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而他的词集中大量的出现“人间”“人生”也正是因为他忧虑全人类之生、永恒之世的缘故。
二、叔本华悲观哲学对“忧生忧世”思想的影响
王国维青年时代接触西方哲学,对康德、叔本华之学说颇有涉猎。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极其崇拜,曾作《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极尽褒扬之语,而此二公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对王国维的世界观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在思考宇宙人生之宏观问题时,受到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影响,王国维认为意志(欲望)是世界的本质,而生存意志(欲望)是造成一切痛苦的最终源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写道:“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1]2在王国维的语境中,个人欲望与世界残酷现实之限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若想超越这一矛盾,使自己乃至全人类进入彻底解脱之域,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使个人欲望完全寂灭,第二条路则是摆脱客观世界的束缚,此束缚即王国维所谓的“身扃乎七尺之内,因果之法则与空间时间之形式束缚其知力于外,无限之动机与民族之道德压迫其意志于内”[1]71。而由于王国维本人信奉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认为意志(欲望)是世界的本质,实际上这两条路也就是一条路,即拒绝生存意志(欲望)。
为了彻底解决主体欲望与客观限制这一矛盾,从而使全人类进入无痛苦的解脱之域,王国维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主义的泥沼。他认为全人类乃至整个世界都应该拒绝生存意志,走向灭绝,从而实现涅槃——即叔本华所谓的“灭不终灭、寂不终寂”[1]72。其论之曰:“然则举世界之人类,而尽入于解脱之域,则所谓宇宙者,不诚无物也欤?然有无之说,盖难言之矣。夫以人生之无常,而知识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谓有非所谓真有者乎?则自其反而言之,又安知吾人之所谓无非所谓真无者乎?即真无矣,而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肩之所,不犹愈於世之所谓有者乎!”[1]15
不过,从逻辑上来讲,欲使主体欲望寂灭本身就是一种欲望,而凭借怀有一欲望进而能够拒绝所有欲望则是一种悖论。王国维也发现了叔本华拒绝意志说有矛盾之处,其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论之曰:“然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解之疑问也。尼采亦以意志为人之本质,而独疑叔氏伦理学之寂灭说,谓欲寂灭此意志者,亦一意志也”[1]60,进而“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9]。王国维在奔向解脱理想之路上开始怀疑一切理论和事物,其填有一阙《鹧鸪天》,可证其心迹一二:“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8]59在其所写诗《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中亦叹道:“欲求大道况多歧”“知识增时只益疑”[1]273。
如果拒绝意志(欲望)仅仅是一种主观臆想的话,王国维意识到,人类可能永远也无法进入解脱之域。不但如此,无休止的生存意志(欲望)会使得人类未来的现实生活也走向逼仄和黑暗。王国维说:“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1]19王国维甚至认为,无休止的生存意志(欲望)迟早会毁灭现实世界。胡适曾在日记里记录王国维在与他之间的一次谈话中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10]由此可见,王国维认为主体欲望不可能真的彻底拒绝,解脱之理想也许亦属空谈,而他对充满欲望的现实世界更是报以无限忧虑和绝望。王国维发现自己对现实的欲望世界深恶痛绝,却又受困于此,无法摆脱;对无欲的解脱世界充满向往,却又无法到达。对于解脱理想之幻灭的悲慨和对红尘的忧虑绝望则又构成了王国维“忧生忧世”的新层次内容。而这新内容实际上与他人的“忧生忧世”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仍然是属于个人欲望与世界残酷现实之限制的矛盾。王国维依靠叔本华哲学绕了一大圈,最终又回到了原点。
这一痛苦寻觅与失败的过程在王国维的词里经常被反映出来。王国维常常把解脱之域喻以梦境、仙境或者是其他理想之域,而在词结尾处,又总是以梦境之幻灭或仙境之可望不可即而告终,剩自己一人在充满苦痛的现实人间中徒增哀叹。例如《点绛唇》:“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 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8]98;《如梦令》:“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无据。无据。斜汉垂垂欲曙”[8]1;《点绛唇》:“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8]20;《点绛唇》:“岭上金光,岭下苍烟冱。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8]21;《浣溪沙》:“金焦在眼苦难攀”[8]55;《减字木兰花》:“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依旧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8]58;《蝶恋花》:“窣地重帘围画省。帘外红墙,高与银河并。开尽隔墙桃与杏。人间望眼何由骋”[8]62等等。甚至在点评他人作品时,王国维也对同样意境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1]356秦观的这首《踏莎行·彬州旅舍》全词兹录于下:“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11]王国维认为这首词只有前三句是“凄婉”的佳句,是因为秦观在前三句中描绘了一个被重重夜雾包裹起来的梦幻之境,此境通向象征最高理想的桃花源,可是理想之域却可望而不可即。秦观词此处意境和上述王国维词的意境别无二致,故而为其所激赏。至于该词的其它部分,则流于普通的离恨之词,故而为王氏所讥。
三、“忧生忧世”主体的膨胀与幻灭
上文提到,王国维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领悟到欲望与苦痛乃是现实世界的本质,于是一心想要找到从现实的欲望世界到达解脱之域的路径。由是,王国维自认为已经站在了“忧生忧世”的最高点,即思考全人类的终极解脱问题。虽然身处于欲望世界,受到欲望世界的种种限制,但是王国维认为“忧生忧世”者由于勘破了现实世界的本质,其境界要远高于蒙昧无知的普通人。王国维曰:“若夫天才,彼之所缺陷者与人同,而独能洞见其缺陷之处。彼与蚩蚩者俱生,而独疑其所以生。一言以蔽之:彼之生活也与人同,而其以生活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之生于世界也与人同,而其以世界为一问题也与人异……彼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欲人之所不敢欲,然其被束缚压迫也与人同。”[1]71王国维所谓的“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欲人之所不敢欲”即常人习惯于认为现实世界是合理的(或者寄希望于有神论),而“天才”则知道被欲望支配的现实世界是荒诞的、痛苦的;常人在现实世界中寻找理想,而“天才”却敢于超越现实世界去寻求永远解脱之域。虽然这番话是针对叔本华与尼采说的,但是年少成名,才兼文史,学贯中西,且亦忧虑全人类之解脱问题的王国维在字里行间未尝不自许为叔本华、尼采的同道。对欲望世界永恒痛苦的洞察与对人类解脱方向的思索既给王国维带来痛苦和惶惑,又让他自许为“天才”之列。
王国维认为,叔本华、尼采这类的具有伟大知力和强烈意志,敢于欲求无欲境界之欲的“天才”乃是傲视天地的大写的人,其曰:“叔本华与尼采,所谓旷世之天才非欤?二人者,知力之伟大相似,意志之强烈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其高掌远跖于精神界,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九万里之地球与六千年之文化,举不足以厌其无疆之欲。”[1]71-72信奉“天才论”的“忧生忧世”主体相信,由于自己勘破了欲望世界的本质并敢于去寻找超越主体欲望与现实世界限制的矛盾的解脱之域,自己便是凌驾于蚩蚩众生之上的“天才”。极度膨胀的自我让王国维也同样的“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自负有解脱自己乃至全人类的使命。
不过,就像上节所提到的那样,王国维后来对叔本华的解脱之径——拒绝意志产生了莫大的怀疑,那么“天才”解脱之可能与否也成了莫大疑问,王国维甚至对人类究竟是否可以解脱也产生了怀疑。王国维写道:“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於昔也……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1]18“天才”若只与普通人一样,永远也无法触及解脱之域,永远被欲望世界所禁锢,那么“天才”作为特定的主体而言就丧失了其特殊性,而“忧生忧世”主体对于自我的定位与期待注定会落空。从这个角度来说,“忧生忧世”主体所自许的那个自我彻底幻灭了。
“忧生忧世”主体的膨胀与幻灭在王国维的词中亦有体现。一方面,由于能够认识现实欲望世界的本质,自许为“天才”的“忧生忧世”主体既有几分常人无法理解的寂寞,又有几分卓尔不群的孤傲之心,如《蝶恋花》:“如此高寒真欲绝。眼底千山,一半溶溶白。”[8]119《点绛唇》:“严城锁。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8]30《临江仙》:“红墙隔雾未分明。依依残照,独拥最高层。”[8]3《蝶恋花》:“又是廉纤春雨暗。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已恨平芜随雁远,暝烟更界平芜断。”[8]48站在瞻望全人类命运的高峰上,王国维既为重压感觉到惶恐,感到高处不胜寒,又体会着很少人理解的寂寞,更对眼底无边无际的、黑暗的欲望世界感到烦闷与无奈,但毕竟还是作为俯视世界与人类的观察者,一个高高在上悯世者而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自己也无法得到解脱,“忧生忧世”主体虽然是觉醒者,但却也和蒙昧的昏睡者面临着同样痛苦的命运,因而不得不对主体本身也进行了价值否定。如《蝶恋花》:“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8]117楼上之人俯瞰红尘之中的芸芸众生,却和陌上之人一样在欲望世界中陷入无尽的痛苦;再如《浣溪沙》:“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8]23所谓“天眼”即叔本华所说的“世界的永恒的眼睛”,“忧生忧世”者用此眼即可窥破世界之本质是意志(欲望),然而发现了欲望世界本质的主体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欲望世界中的一员,和其他没有发现这一本质的普通人一样,无法解脱。而且,普通人并不了解这一切,他们的痛苦只限于无法满足对一人一事的欲望,而“忧生忧世”者的痛苦则是立足于全人类、全世界无法解脱的永恒痛苦,世上无其它痛苦更甚于此。
作为“忧生忧世”者的王国维是痛苦的,受西方悲观主义哲学以及黑暗时代的影响,他看不到这个世界和人类解脱的出路。王国维在否定了“忧生忧世”者在解脱问题上的特殊性后,放弃了哲学、美学研究,转攻史学、古文字学和考古学。也许在他看来,只要“忧生忧世”者依然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就避免不了要受到欲望的驱使,永远也无法研究出一条解脱之路。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无上知力与强烈意志的“天才”与普通人的命运是一样的。不过,王国维在《水龙吟》一词中写道:“一样飘零,宁为尘土,勿随流水。”[8]16也许,在王国维看来,就算是注定一样的痛苦命运,他也有自己的选择。
四、结论
王国维的“忧生忧世”说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在融合了西方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后,对他本人的文学批评和词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国维的“忧生忧世”词可谓是忧虑全人类命运的哲人词,极大地开拓了词境。而且,王国维也是第一个以西方哲学思想入词的古典词人。王国维对于词学有着革命性意义,理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