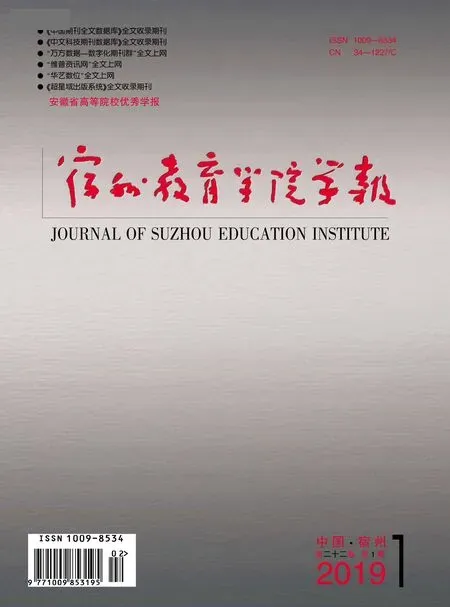叙事学视域下张洁小说《无字》的悲剧书写
苏 曼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阜阳 236000)
悲剧是众多文学样式中特殊的一种,在悲剧结构、叙事方法等叙事方面有其独特之处,所以在叙事学视域下探讨悲剧艺术的审美特征自有其价值所在。学界对叙事理论的研究早已有之,20世纪60年代“叙事学”基本形成。至20世纪末,叙事学在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流派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使文学艺术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张洁小说的创作风格是多样的,这与她不断变化的叙事风格密不可分。把《无字》放在叙事学视域下来分析作品的悲剧书写,可以更好的理解作家对人类悲剧性现实的正确把握和对人灵魂深处悲剧意识的展现。
一、开放式叙事结构书写人生命运双重悲剧
悲剧作品都是按照一定的悲剧结构组织而形成的。西方学界从悲剧作品的情节、性格、矛盾冲突等角度探讨了悲剧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密不可分的关系。形式的独特安排是和内容相契合的,是为了内容更好的表达。悲剧作品的结构形式主要有“封闭式”结构和“开放式”结构,采用开放式结构的悲剧作品叙事方法多样,常用倒叙、插叙、追叙等叙事方法,文本结构比较复杂。《无字》采用的正是开放式结构,书写了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的百年际遇,可以说是一部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同时也是历史中人物的命运史。作品将吴为家族的几位女性放在20世纪中国的巨大语境下进行描写,人物命运的转折巧妙的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契合,个体命运的悲剧得以展现。这些都归功于作者对小说的复杂叙事时空结构的驾驭能力。
(一)倒叙与插叙的交错运用
“倒叙”和“插叙”是指叙事作品的文本时间和自然时间序列不一致的叙述方式。《无字》交错运用了这两种叙述方式,成功地展示出了人物一生的追求、遭遇以及他们不甘沉沦的生命历程。《无字》共三部,第一部故事的整体框架基本形成,二、三部分别以叶莲子和吴为的生命线索为主轴,对第一部的故事情节进行补充和深入。从整部作品结构来看,采用了“倒叙”的手法,文本开始就交代了女主人公吴为的现状:她疯了。然后以“她疯了”为故事的当前时间,讲述她发疯之前的故事。通过吴为发疯前接到的两个质疑电话以及她“擦洗刀叉”的细节,引出了吴为生命中三个最重要的人:母亲叶莲子和丈夫胡秉承以及“情敌”白帆。通过这三个人物的出场,将吴为的童年、及成年后婚姻生活中的苦难遭遇表现出来,并且多角度、立体地展示出吴为的“性格悲剧”以及她面对苦难所怀有的抗争精神与生命激情。在追溯过去的生活时,作者采用“开放式”结构,充满跳跃性,层层倒叙,用吴为的思维方式回忆出来,现实与回忆交织,过去与现在对比,吴为一生的遭遇贯穿故事始终,悲剧命运清晰可见。在整体倒叙之前,就突兀地将吴为的发疯交代出来,再逐步将发疯的原因一一掲示,这对作者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折磨!但同时这也是作者对人生和命运最真切的诠释。让读者见证了吴为发疯的悲剧,除了引发读者的思考之外,更会带来同情和灵魂的震撼。
《无字》在整体倒叙中,也交叉运用插叙来表现人物完整的生命历程。比如在第一部的第三章,作者用第一人称来写主人公吴为发疯之前重回故里的回忆和感悟。正是这些回忆和联想展示出了吴为一生的追寻:和母亲的互相守护及女人的最终归宿。可最终这两者她都没有做到!在无为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从生命的起源地试图找寻生命的意义和精神归属,这同样也是作家对生命的思考。的确,人类正是有了苦难,才会激起人们心中战胜困苦的激情与勇气。吴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追求,不断遭遇苦难中度过的,这就是她的生命历程。而在第三部所有的故事已讲述完后,故事即将画上句号的时候,叙述者让故事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交代了吴为对生命的最终抉择——死亡。小说的开头以“吴为疯了”起,以倒叙的手法让故事回到开始,以插叙的方式展示了吴为的生命历程,叙事又回到开始的节点,再水到渠成的交代故事的结局,小说终。在此过程中,人物形象得以丰满,主人公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和对命运的追问获得了读者的巨大同情和思考,人物的悲剧命运更是撼动读者的心魄,悲剧的崇高意境得以升华。
(二)预叙的反复使用
预叙,就是在故事发展中对将来要发生的事预先描述出来的叙述活动。中国文学中预叙很常见,在显示人物智慧,精炼文本方面都有重要作用,这与中国人的宿命论观念有一定联系。预叙是“宿命论”观念反映在叙事手段上的一种体现,而“宿命论”和悲剧精神又是密不可分的。《无字》在叙事方法上另一技巧就是频繁运用预叙,叙事者将人物“未来”要发生的事和结果预先告知读者。如,“她更没想到,为这段短暂的婚外情,会负上如此深重的罪恶感,没有一时不在考虑如何从这罪恶中逃出,而且明白必得采取一种决绝的办法,方能斩草除根。可她也将随着她的坦诚下地狱,《红字》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遭受的一切,她一分一毫都不会差地受下去,直到离开人世,而她刚刚二十几岁。”[1]这样的“剧透”将吴为一生的精神历程呈现出来,预示着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及她一生所承担的精神苦痛——为了爱情,她一生背负着罪恶感。这种负罪感始终折磨着吴为,直到死亡。吴为没有顺从,也不愿意承担灵魂的折磨,她选择了坦白,然而同时也陷入了另一种悲剧境地,遭受了各种来自伦理道德控制下力量的攻击。人类面对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罪”,所能做的只是“充满压抑感的顺从或是进行灵魂的自我折磨”,[2]这既是人存在于世的宿命悲剧,也是社会历史带给人的现实悲剧。
吴为家族几代女性的共同之处是对生活过于认真,她们的命运和她们的性格是分不开的。然而,吴为的遭遇又像命中注定一样。这和叙事者跳出故事,插入一些评论性的话语有关,这也是一种预叙的处理。在文中有很多,比如:“如果那天吴为不回头,是否就不会有后半生的那场大戏?”[3]“换而言之,那本来就有的自杀凶纹,也可能自行消失?命运是可以改变还是不可以改变的?也许改变也是命中注定。”[4]这些预言的话将人物命运无常的宿命感表现的淋漓尽致,也揭示出人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虽然命运和死亡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注定会面临的选择,但主人公选择不向命运低头,“向死而生”也是一种抗争。叶莲子对生命的执着以及对命运的预言也是一种预叙处理,“这些暗示性的预叙成了为命运伴奏的沉重音符——命运历程与人生结局相交织,产生出别样的动人心魄的预言诗般的效果,其审美张力也就显现出来了。”[5]
二、个人化叙事伦理书写历史中的个体悲剧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发现历史题材频频出现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历史小说很受作家们的青睐,这都反映出历史叙事在当代小说中日益受到关注。张洁的小说创作,其叙事伦理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无字》的历史叙事则有质疑历史、重构历史的特征,在历史书写的外表下,有鲜明的个体叙事的特性,表现的是历史时代大背景下个体的记忆和悲剧。作品把一百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当作背景,着力叙述墨荷、叶莲子、吴为、禅月几位女性以及顾秋水、胡秉宸等男性在历史裹挟下的个体悲剧命运。
(一)个体命运:历史书写的目的
张洁在《无字》中抛弃了“宏大叙事”,用她敏锐的观察去关注着身处历史情境中那些最普通的个体,书写他们随重大历史变迁而沉浮的命运。人生与社会历史总是在不断碰撞中前进,作家更关注人类历史中那些偶然和意外的事件,以及由历史偶然性造成的个人悲剧命运,呈现出个体的欲望与社会历史的规则相冲突导致的人性异化的悲剧。
首先,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不是按照“必然性”规律进行的,而是选取一些偶然性和意外来贯穿人物命运。历史是繁复的,生活和人也是复杂的,文学对生活的反映也是能动的,并非镜子一般的反射。历史事件的发展从宏观上来说具有必然性,而个体的命运是如何与历史有涉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无字》中的历史叙事也多关注那些偶然性与意外,正是一些偶然性因素造成个体悲剧性的命运。顾秋水投身入伍完全出于一件偶然事件,走投无路选择了参军,他这一步不仅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也注定了叶莲子以及吴为的命运。赵大锤出乎意料的惨死,让人不禁感慨命运无常,生死难料,他的死亡给人一种难以逃脱生命中偶然的悲凉感。作者以入伍不久的顾秋水的视角来叙述郭松龄夫妇的死,不仅写出了郭松龄夫妇像普通平民一样悲惨而无常的命运,也暗示了顾秋水不平的人生之路。
其次,社会历史是个体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在不以个体的意愿为改变的前提下向前发展,个体在历史力量的裹挟下踉跄前进,渐渐失去自我。《无字》中体现出了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人性不断异化的轨迹。其一,这种人性的异化表现在人的情感的扭曲。顾秋水因为历史的数次变迁,不得已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他对叶莲子的感情也随之淡漠,甚至是变异的折磨,他当着吴为母女的面与情人的亲热,给吴为留下了终身的阴影和创伤,以至于吴为在成年以后对感情的追求也是扭曲的,不能平等、理性的对待自己的情感,得到的是异化的情感。其二,人性的异化也体现在人的精神的异化。《无字》更多关注人在历史变革中的精神历程,顾秋水、胡秉宸在现实生活中历经各种政治风云,最终变得温顺起来。延安的经历在文中被反复提及,这一事件对胡秉宸的性格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不自觉地学会了顺服和伪装,历史的力量在他身上完成了由人到奴的异化过程。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在历史的洪流中只能被动改变,只能说是人性在追寻尊严的过程是曲折的,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一定是人性战胜异化。
(二)质疑与追问:历史叙事的个人化立场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叙述的主体是历史,呈现出的是群体记忆。而在《无字》中,张洁从个人化的立场来书写历史,重构历史,历史事件成为背景,文本着力书写的是人们的世俗生活以及生存状态,所以她写历史的真正目的是关注人的命运以及透视人性的复杂性。《无字》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扉页上写着“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张洁的母亲便是小说中叶莲子的原型。所以,《无字》对吴为、叶莲子等女性悲剧命运的揭示是深刻而真实的,甚至对顾秋水、胡秉宸等男性也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以悲悯情怀来观照他们的命运,将他们放在历史大环境中来书写。张洁始终坚持的叙事伦理是通过文学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而非是用现实和人伦的规则。顾秋水、胡秉宸的人生选择会受到社会道德人伦的谴责,但他们的精神悲剧也是社会历史造成的。张洁没有对男性进行犀利尖刻的批判,而是以历史的眼光来反思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真正原因,表现出她对社会、历史、自我的质疑与追问。
首先,《无字》从个体生命历程出发刻画的三位母亲吴为、叶莲子和墨荷都对生活有执念。墨荷毫无怨言的承担叶家“篮筐”的角色,忍受着一个封建大家庭所有人的折磨直到难产死去;叶莲子在漫长的岁月中饱受着各种折磨,依然信守从一而终;吴为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但骨子里还是有着较真的个性。从社会道德角度说,吴为是个不守妇道的人,私生子是她人生的污点。虽然社会容不下她的污点,但她仍然选择承认并面对一切,这无疑是对传统男权社会的质疑与抗争。她怀着对理想爱情的期望,一次次的祈求代表权威的男人们的谅解,但结果是“爱到无字”。
其次,作家书写了吴为等女性的爱情悲剧宿命,理想爱情遭到解构和否定,表达的是对爱的质问与怀疑。吴为选择了死亡,她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获得了一份超然的同时满怀着对历史社会的质疑离开了。吴为的反省寄托着作家的反思,也是女性的自我反思。在人类社会还是以男性为权威的时代,女性把理想的爱情看作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她们面临的只能是悲剧。
结 语
综上所述,《无字》作为张洁本人最欣赏的作品,不管是小说的主题内容还是文本独特的呈现形式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蕴。把《无字》放在叙事学的视阈下观照,研究小说的悲剧精神,是笔者力求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相结合,拓宽小说研究的广度,挖掘作品深度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