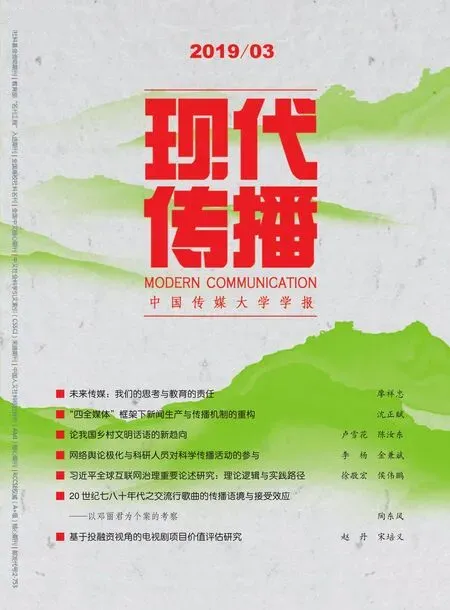赛博空间与人的存在转向:“比特视域”的提出、议题与反思
■ 郭子淳
阿格尼斯·赫勒在《现代性理论》中认为,早期现代世界是与空间感和空间概念之间的革命一同诞生的。①空间问题的探讨,既表现在认识论层面,也表现在技术层面。历史上,自哥白尼的空间革命以来,关于“空间和视域”理论的探索不胜枚举,从笛卡尔的“物质说”到洛克的“意识说”,从胡塞尔的“现象说”到海德格尔的“时间说”等,历史上对于“空间和视域”的理论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然而,这些理论建构的空间质料都是建立在以原子②所构建的空间基础上。事实上,在当今数字化进程中,比特作为一种新的质料形式在不断融合和迭代着原子作为质料③的空间样式。数字空间下的存在关系,正在从多个维度解构着人们传统意义上对空间和视域的认知。如果说,原子空间所构建的“视域论”来自非数字技术时代下的空间认知层,那么,当下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探索与空间应用,也必然意味着传统的“视域”机制,开始了比特化的历史进程,即呈现出从以原子物质构成的“表象空间观”、以纯粹意识构成的“心理经验空间观”到以数字技术比特重塑的“赛博空间”的迁移。近十年,VR、AR、MR等虚拟技术加速了“比特”与“观看视域”之间的联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看方式。基于此,笔者认为理论界亟须提出一种全新的、基于比特质料的空间范式来考究视域的全新形态。“比特视域”关注虚拟空间概念、知识构成与心理状态中所存在的沉浸性趋势,笔者力求从“空间认识论”的历史回溯和视域机制出发,对“比特视域”加以研究并获得理论支持。
一、“空间认识论”的两条路径:“物质表象”与“心智经验”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空间视知觉的讨论早就进入了人们的哲学视野。早期的“空间”理论主要从宗教角度出发,直到17世纪“空间”理念才开始了现代性和科学意义上的探索,并开始逐渐划分为两条路径。
一条是在笛卡尔解析几何的影响下,以广延的方式将空间的结构与构成从物质角度进行诠释,即物质说。一方面,笛卡尔认为空间是物质外延的结果,空间存在与主体意识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物质性隔绝了空间与意识的关联,笔者称其为“物质表象的空间观”。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对广延进行了系统性的描述,认为“广延(extension)由三向量构成。不过,我们所谓广延即不是一种扩展行为,也不是某种不同于量的东西。”④物质的长宽高,必然占据空间,这就是广延。这就是物质的基本属性,即物质的空间属性。另一方面,笛卡尔主客二分的机械论理念也加深了这一看法。笛卡尔主义者从“彻底几何化”的机械论观点出发验证了“空间无非是指物质实体的广延本身。空间不是实体,而是属性;即除了作为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的广延,没有任何其他空间。”⑤主客之间的关系各自独立,且遵循着特定的逻辑关系,即一种机械化的运作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空间的构建和显现也遵循着自身物质之间延伸与外延的因果逻辑,与主体的意向活动没有直接关系。
另一条路径,是以洛克为代表的纯粹精神路径。他认为空间并非由物质的广延而来,而是通过对于心理运动的绵延(duration)而来。空间观念的形成是来自主体精神和以往经验对客体绵延与连续后的心理映射,即空间的运动与感知完全来自经验和心理作用而非作用于物质的广延。一个人在观看一个真正运动的物体时,如果那种运动不能产生出心理运动的绵延,那么他亦完全直觉不到运动的存在。譬如,一个人在海上,四无陆地,天气晴朗,水波不兴,则他虽在整个一小时内观察那个日、那个海或那个船,他亦完全看不到哪一样有了运动”⑥这种通过经验和精神外延的空间观念,笔者称之为“心智经验空间观”。
精神路径否认了物质与空间的联系。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认为空间与物质之间不能等同其一,空间观念与主体的视觉和感知息息相关,认为空间的观念实质上是关于“心理场”的延伸,即“场的延伸与延展,正如时间之于绵延”⑦。洛克认为,人们对于距离或长度所产生的观念不是由长存的空间构成,而是由飘忽消逝的连续(succession)的各部分空间构成而来的。这种距离就叫做绵延(duration)。⑧同样,除了主体视觉的感知以外,主体还会根据自身的连续经验进行内在“意识场”的建立,从而辅助视觉感知来建构主体对于空间的理解和感知。由于连续(succession)的经验观念,来自我们观察了自身心中的现象(回忆和经验),因而有了绵延的观念,在没有物体存在的地方,我们只要通“意识场”就能建构出绵延的过程,从而完成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绵延,最终确定长度和距离的观念。比如,一个人如果有过穿越草原的经验,那么当主体再次看到一个草原视域时,即使只是一张图片,主体也会感知到草原空间的存在性,并通过意识场的绵延建立出草原的空间距离和长度。同样,当人类没有真正经历过宇宙外太空的经验和精神观念,人们是无法对于外太空的空间观进行建立的。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亦认为“这些观念之所以暗示在我们的思想中,正是由于视觉而引发的一些可见的观念和感觉,这些感觉或观念就其本性而论并不与距离或远隔的事物有任何相似之处,或有任何关系。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向我们暗示出距离和远隔的空间,只是因为过去的经验来告知我们。”⑨
笛卡尔主义者将空间归属于物质性的实体,贝克莱和莱布尼茨则将空间归属于精神性的实体。⑩如此看来,无论是笛卡尔所代表的“表象论”,还是以洛克和贝克洛所代表的“经验感知论”无不是将主体感知和外在物质进行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分裂。前者仅仅强调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而放弃了主观意象机制的能动性,后者则过分地强调空间意识仅仅出自精神的意识化,从而摈弃了三维空间的物质原理和客观性。毋庸讳言,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无法真正解释出人们在视域方面理解“空间”的核心。
二、“空间视知觉”的核心:视域
生物学家普遍认为人类对空间的视觉感知,首先是来自视网膜上“二维图像”的提取,随后再经过视网膜神经进行一种判别和分析,即在一定的视域内所建立的空间认知。“视域” 这个概念,最先由现象学家胡塞尔作为哲学概念提出,并将“物质外延”和“精神外延”两者结合起来,认为物质和精神共同作用于空间感知,打破了笛卡尔和洛克等人的单一论,完善了人们对于“空间视知觉”的认识。
胡塞尔在《事物与空间》一书中认为,事物的空间显现离不开两个因素的融合:其一是幻相(Phantom),即在视觉机制的引导下三维空间直接呈现出来的二维事物躯体,是一种来自物质空间对于视网膜投影后的精神处理。相对于洛克等人的纯粹主观精神论而言,幻相乃是一种综合化的显现。克莱斯格斯将幻相称为“因此我能遍历所有的面,以至于我最终拥有一个在诸多侧面建立起一个表象流形成一种为封闭的表面形构,即幻相。”
由于视网膜的视觉映射,只是引发了“二维”的图像空间。对于三维的空间感知,还需要建立一个景深维度的介入。那么如何让这种幻相,从二维空间感知转向三维空间感知呢?这就需要加入另一个重要要素:时间流。
人眼的运动系统,除了对二维画面的水平扩展以外,还进行了时间流下的意识干预。这种时间流作为一种心理运动机制,将二维的幻相进行了延伸,完成了Z轴纵向空间的建构。如果说,幻相的显现流是来自对多个侧面的建构和延伸,那么这种显现流的根本动力就是时间流的连续性。因而,时间意识的连续性导致了从“二维空间”转化为“三维空间”。胡塞尔认为“幻相既是又不是对象;它有别于对象,并能够自行隐没以便让对象呈现;它是它与对象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这两者的同一”比如当我们去观察一把椅子时,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角度的呈现,每一个角度之间的幻相都具有差异性,只有我们花费时间对这把椅子的每一个幻相都进行观察,我们才能对椅子的空间认知进行同一化。进一步而言,这个幻相的综合的过程必然离不开时间因素(时间流)的介入。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即只要主体可以在视网膜上二维呈现画面的基础上,加入时间流的意识转化,我们就会感知到一个三维的空间。关于这一点,胡塞尔在1907年的“事物”讲座中,将其称之为“被时间流构造对象之同一的、纯粹眼睛运动的面。”事实上,历史上有不少魔术师和矛盾空间艺术家都是利用“幻相”和“时间流”这两个视域要素去完成“空间”的骗局。荷兰著名艺术家埃舍尔就曾经在作品《纪念碑谷》中应用了错位的透视来欺骗观众;一方面,通过碑谷上方的“水流”来产生“时间流”,作为幻相的动力机制引导观众的空间延伸;另一方面又通过楼梯和站立的人物来暗示该建筑物的空间关系是符合逻辑的。最终,呈现出一个局部透视似乎合理但是又无法构建出来的空间。很显然,在这里,笛卡尔的坐标空间理论被打破,透视与空间之间的逻辑性被撕碎,取而代之的是来自时间流下的意识干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于空间认识的结构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解读:即空间视觉感知是来自“幻相”与“时间流”的共同干预,这种机制的有机结合便是“空间认识论”的核心,我们称其这种机制为“视域”机制。视域作为空间显现的视觉前提,是视知觉和心理感知共同的结果。正如斯奥里乌斯·格内乌萨森(Saulius Geniusas)所认为的那样:“视域作为显现的必然条件,绝不应仅仅限于视觉现象,也不能限于感知现象。”对于“视域”的准确把握,亦成为了解空间感知的重点。因此,对“视域”这一概念的延伸,将成为笔者对于探讨赛博空间中,视觉感知变化的重点,即“比特视域”的提出。
三、何为比特视域
列菲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认为,视域不仅仅是空间中主体心质关系演变的“容器”和“平台”,也是面对着空间构建中质料不断更替和渗透下的外延。换言之,有什么样的质料构造,就势必会产生相应的视域感知。从这一点上来看,空间质料的差异化亦会导致主体视域的差异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计算机技术和控制论的影响下,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在《神经漫游者》中首次提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一词,认为在计算机和互联网语境下,比特(计算和数字通信的基本信息单位,也是最小单位,这些状态值被表示为0和1的组合)作为质料所承载的数字空间不同于现实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存在,不是由原子物质所建构而成,它可以是一种无限的空间延伸,亦可以是一种非实体的存在。哲学领域,德勒兹作为当代西方对电子媒介研究领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和加塔利合作的名著《千高原》(1980)被称为赛博空间的“哲学圣经”。在书中,德勒兹重点以差异哲学和游牧美学来解读赛博空间,所提出的诸如千高原、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多元符号论等为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哲学角度,认为相比原子空间,赛博空间语境下所延伸的哲学探讨和理论维度将远远高于前者。吉布森的结构论与德勒兹的哲学观无疑成为了探索赛博空间理论的基石。一方面,赛博空间的理论在吉布森的诠释下,从主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上,开启了一种人与计算机、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存在关系;另一方面,在主体的视域接受上,亦呈现出技术媒介与视觉感知的比特化迁移,传统的原子空间中的“视域”呈现也开始转向为一个全新的数字空间。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笛卡尔所代表的物质空间观是一种“表象视域”,洛克等人所代表的主观空间观是一种“经验视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以数字网络技术所创造的赛博空间中,会存在一种“比特视域”的可能性?笔者认为,“比特视域”中数字比特(0/1)代替了传统视域的原子质料,是以所构成的赛博空间或区域中所呈现的视点和周围点作为研究对象。其内在机制,是以“比特幻相”和“比特时间流”两者作为建构比特视域的重要因素。相比原子空间而言,在对空间的超越和显现中,作为空间物质质料的第一性从原子转向为比特,时间流和幻相将呈现出更多的维度,不存在地平线和地形这种实在的固化方式。由于,建构视域的两个重要元素分别是“幻相”和“时间流”。因此,我们可以从两者比特化的进程中对“比特视域”的内在特质进行解读和分析。
(一)比特幻相
一方面,梅洛-庞蒂认为“视域就是在探索对象的过程中能够保证对象的同一性的东西”。其中,被知觉对象的同一性就是一种“视域综合”的结果。那么,对于传统原子空间的幻相而言,由于幻相只能呈现事物的一个侧显,即二维的呈现。那么,只有做到“幻相综合”,我们才可以塑造出三维的空间感。
在赛博空间中,事物的空间质料不再是原子。比特介质可以打破原子空间的三维方式,同时以多样化的维度方式而存在。比如,一个人在原子空间中,是无法同一时间看到一把椅子的正面、侧面和背面的,这是由于原子空间事物的凝性(Solidity——洛克语)所导致;然而,在赛博空间中,比特可以将椅子的所有面(无穷)同时呈现在一个幻相之中。因而,这种空间的呈现方式,可以给沉浸其中的主体带来多个维度的幻相融合,呈现出从一维性到多维性的空间流型。德国本土艺术家格列格·施耐德(Gregor Schneider)的新媒体作品《N.Schmidt,Pferdegasse 19,48143 Müster,Deutschland》就通过数字技术,在赛博空间中建构了无数维度的事物,如一维的雪花、二维的植物和动物乃至四维的时间屋,观众可以通过虚拟装置进入时间屋来控制时间的走向。在这个赛博空间中,三维幻相不再是唯一,多种维度的幻相共同融入其中。可以说,“多维幻相融合”从本质上完成了构造模块化空间的任意组合,其赋有的动感意识和动感材料,也就不再局限于笛卡尔式的空间坐标和位置因素等。因此,“比特幻相”相比“幻相”来说,具有多维性的特质,不必再符合和遵循着物理世界之中的逻辑关系。
另一方面,由于“比特”自如的显现生成方式可以摹仿或超越任何先在的原子空间样式,并根据主体的意愿来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肌理。在赛博空间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创建任意想象中的事物,且不必考虑其外在的合理性。因此,事物显现的样式呈现多样化的并存,笔者称其为显现融合。前不久上映的《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2018)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影片中的“绿洲”是由游戏公司创始人去世前所创造的一个赛博空间,这个虚拟空间完全独立于外在的社会空间,外在的法律和伦理不再适用其中,所有进入这个“空间”的玩家,都要遵循着创始人的游戏模式和空间认知。同样,当玩家如果找到了那把象征着权威的钥匙时,这个创始人所搭建的赛博空间将会被格式化,获胜者可以重新搭建一个自己意志的空间。
一言蔽之,“比特幻相”是指在以数字化虚拟生成的赛博空间内,结合主体的意象活动与比特事物共同作用下的显现综合,其特质呈现为“维度融合”和“显现融合”。
(二)比特时间流
我们知道,胡塞尔给出了现象学空间构造的系统勾勒,从眼睛到头部的动感系统和身体运动的位移是产生时间流的根本前提。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原子空间的认知,来自时间流对眼球瞳孔上二维画面以及肢体运动后的延伸。那么,比特化的时间流,会呈现哪些其它的特质呢?
由于0和1是比特的最小单位,作为赛博空间中的质料,我们可以无限延伸0和1的组合,数字组合的任意性大大超于了原子组合的可能性。这就导致时间流在比特视域中将会呈现出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事物有限延伸背后的时间干预;另一种是对事物无限或零度的时间干预。前者的有限延伸,同物理世界之间一致,呈现出时间的连绵性和线性化,即时间流的恒定性与方向性;后者的零度延伸和无限延伸,则不存在与物理的现实世界之中,呈现出一种对时间的组合性和非线性。
从本质上来看,原子空间的时间性如同河流般一直向前,以不可逆性的形态呈现出时间的线性化和方向性。根据能量守恒的定律来看,原子世界中的物质每一刻都在经历着从诞生到衰亡的变化。在我们生存的原子空间中,每一个事物都无法逃脱时间绵延向前的干预。
然而,在赛博空间中,能量守恒等一切定律都可以被解构,其空间存在的事物既可以弥足常新,亦可以加速或减速事物从诞生到衰变的过程,时间的连续性在这里被打破。在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一位女科学家常年被监禁在一个实验室之中,她的工作就是不断地用数字技术去创建一个又一个赛博空间。影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表现她用数字技术创建鲜花的时候,鲜花的成长速度、光泽、外形等这些受时间影响的因子,都是通过她手中的控制仪扭动完成,时间流向在赛博空间中成为了一种任人把持的介质。可以这样认为,比特化的时间流,打破了物理世界的唯一性,将时间速度、方向等维度进行解构,建构出一种全新的时间观。因而,我们可以给“比特时间流”一个初步的概念诠释,即在以数字化虚拟生成的赛博空间基础上,对客体显现进行无限和有限的时间干预。
笔者认为,数字视觉时代的到来,将人类视域显现的空间划分为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数字技术出现前的原子世界,所有视域的呈现方式都是直接和第一性的,人们与视域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原子空间之中,即原子视域;另一个维度,则是与原子视域相对的比特视域,其视域不存在于真实的物理空间之中,而是通过数字介质重塑的一种虚拟的视域空间,呈现方式是间接和第二性的,由于其最小的质料单位是由0和1的比特化建构,其比特视域中的时间流和幻相两个因素也因而呈现出多维性、非线性、融合性等特质。
四、 反思与议题
(一)本体:“视域综合”的消逝
梅洛·庞蒂认为视域由“内视域”和“外视域”共同构成,即视域综合。视域综合是指人们无法孤立得只看一个物体(内视域),而忽略物体所处环境和场域(外视域)的存在。由于,现实世界中每一个物体都与其环境和场域一同存在。因此,在现实世界中“内视域”和“外视域”是共同交织而成。正如梅洛·庞蒂所说:“看一个对象,就是栖居于对象,并从那里出发,再根据其它所有物体朝向它的那一面去把握这些物体……因此,每一个对象都是其它对象的镜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视域综合在原子空间中呈现出对象的内视域与外视域的“交互蕴涵”(implication reciproque)关系。
然而,在赛博空间中,这种“内外视域”共存的本体论将会被解构,并表现在“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一方面,比特视域的非线性和跨维度性,这导致空间维度和事物维度的多样性和并存性,这不同于原子空间中事物(内视域)和事物所处环境(外视域)都并存于三维空间的绝对性,打破了空间三维性中“视域综合”的唯一性。因此,对于个体而言,进入赛博空间后,将呈现出内视域与外视域皆不存在、内视域外视域共存、内视域与外视域各存四种方式,笔者称其为“四域化”。譬如,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中,主角尼奥通过计算机第一次进入赛博空间时,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初始化状态,内视域和外视域皆不存在,内视域和外视域的个体显现和并存方式都由尼奥的意向性所支配,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影片尾声,尼奥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精神意志力在赛博空间中成为超人(现实中尼奥只是一个凡人)。
另一方面,德勒兹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认为赛博空间如同一种“平滑”(lisse)空间。“平滑”是指打破现实空间中固化的客观规律和制约,任何的事物和场域处于赛博空间中都可以进行“平滑”般的过渡。因此,赛博空间中的每一个事物(内视域)和场域(外视域)都各自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自由度,一种星群般的交融和异化。进一步说,如果说群体(多个个体)共同进入到赛博空间后,由于每个个体的视域组合都不相同,因而会产生出两种结果:一种是群体的合一化,有如“星群”般的交融,即每个个体都将各自的视域呈现给彼此,实现“平滑”过渡;另一种则是群体的“层化”性,即虽然每一个个体都存在于一个赛博空间中,但各自做看到的事物(内视域)和环境(外视域)都不一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现实空间(物理空间)中“视域综合”的同一性和唯一性规,并不适用于赛博空间之中,内外视域的个体组合和群体组合也分别呈现出“四域化”的个体化、“星群”的平滑性和“层化”的多异性。
(二)观看:比特视域下的沉浸之蔼
数字技术与人机网络结合应运而生的赛博空间,使得比特视域下的视觉假象和心理机制在虚实交融中不断向前推演,呈现出一种观看机制的沉浸之蔼。
在原子空间中,看的方式和层级决定着人们对空间认知的程度。其中,“凝视”作为一种观看心理是从低端视觉认知到高端视觉的桥梁。借用中国宋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提出参禅的三重境界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是一种机械的“再现之看”;“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则是一种“想象的凝视”;而“禅中彻悟,看山仍然山,看水仍然是水”则是一种在经历了想象的凝视后所达到的“意象之看”。
数字显现技术的指数级增长,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穿梭在原子视域和比特视域之间;主体的观看机制和心理感知在原子视域与比特视域交织的视觉语境中,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在比特视域中,主体对视域所呈现的“沉浸性”将更加敏感,沉浸性所带来的真实感要远远高于通过想象凝视所带来的真实。正如艾柯所说的那样:“当人们试图暗示真实时,事实必须看似真实。‘完全真实’被认定为‘完全伪装’,绝对不现实也成为一种真实存在。”比特视域中的“完全伪装”转向为一种“完全真实”。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曾指出了数字显示技术在后现代社会中的魔性力量,通过沉浸性的“视觉奇观”来代替传统的观看方式并使主体的意识奴役化。电影《黑客帝国》中,生活在未来的人们从出生那一刻就被沉浸在一个由比特建构的赛博空间之中并被奴役化,真实与虚幻的隔阂被打破。正如“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认为的那样,数字计算机的显示能力,让人们有机会获得那些在真实世界中无法直观感受的熟悉概念。
未来,比特视域和原子视域不再是并存,而是嵌入和融合。这种嵌入所带来的“身临其境”首先来自对于主体观看方式和心理映射的改变,人们的观看方式从原子视域中“想象的凝视”开始转向为观看的“沉浸性”。
(三)审美:比特视域的意境化
图灵在20世纪初期,从计算机的数字化的角度论证了数字化世界的出现,解构了传统艺术虚拟性的物质性和原子性。
相比数字化所建构的虚拟影像,原子虚拟影像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从这一点上来看,传统原子胶片所带来的文本意象依旧是来自现实之中。比如,在电影《芙蓉镇》中,芙蓉镇虽然是一个虚幻的世界,但导演可以通过假定性的文本和画外音方式来引导观众对于这个世界真实性的认同,从中来感受江南小城的意象之美。然而,当电影中的故事背景转向为一个有别于人类生活的外化想象空间时,我们就不得不寻求一种搭景和模型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方式大多用在早期的科幻电影之中。如在早期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的摄制中,导演梅里埃就通过美术置景对月球王国进行了最大维度的再现。但其观众而言,这种原子置景的方式,最终导致了画面的不真实性,观众很难沉浸其中,大大影响了观众的审美意境。
但是,如果将影像语境设置为赛博空间之中,比特的虚拟性就可以无限地延续文本意境的可能性,最大可能的放大了意境世界的表现性和再现性。正如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所认为:任何纯粹的空间都是相对的,“在严密地考察之后,我们或者会看到,我们甚至不能构成一个离开一切物体的纯粹空间概念……因为它是一个最抽象的观念”下面,我们通过分析《阿凡达》影片当中潘多拉星球的塑造来阐释比特意境的生产过程;
首先,创作者从中国张家界风景区的云中山峰提取灵感,碎片化和解构化山峰的原子意象,提炼出潘多拉星球的主峰外貌;其次,设计师们将各自脑海中的虚拟意象汇聚到原子意象之中,创造出一个虚拟而不失真实的意象;最后,将来自真实世界中的原子碎片化的介质和来自想象空间中的碎片化介质共同嵌入和转化为比特介质,外化成一个杂糅着原子介质和比特介质的意象世界。
比特化的意象世界不断诱使观众进入一个笛卡尔式的无实体状态空间,在比特意象中,一切都是全新的意象,主体通过图像世界中视觉与精神的临场共鸣,融合实现一个超越原子世界的意象空间。同时,相比原子世界再现的意象性和沉浸性,比特虚拟性影响观看者的时间越长,观看者的情感和精神认知就会被无限的代入其中,精神模型和现实模型都能得到三维的虚拟体现,并通过全身心的沉浸与交互在其中。意象的比特化,体现出了虚拟性所带来的体验于情景的裂变。海德格尔的体验观认为,体验是依托自我的意识来对世界进行解读,纯粹体验是一个在情景之间所生成的实践中得出,在虚拟比特世界中,情景的外延在包含了传统原子世界虚拟性的特质基础上,再一次得到裂变。
(四)身份:“化身”与“拼图”
尼格罗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认为,人类生存的语境变迁,正从现实地域转入赛博地域之中,数字化的民主化不断削弱现实群体部落中的文化潜能,种族意识在数字地域中被重新构建。赛博空间下的终极形态将会是对于主体神经编码的形态化和映射化,人的大脑和身份被比特化,身体和维度将被再次赋予新的“化身”,真实与虚拟将交融与共生。
在虚拟世界中,仿真比特的存在哲学基础,恰恰是因为它昭示了一股时代的潜流,原本的道德彼岸和理性彼岸,已经失去了一种权威性。在当下异常火爆的游戏《绝地求生》中,美感的体验已经被“化身意识”所代替,快感代替美感,杀戮代替快感;游戏中,玩家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荒芜化的世界中抢夺有限的资源生存下去,玩家在其中抛弃道德和理性这些现实中的准则,可以不择手段地为了生存而战。
不难看出,现实个体意识中的潜意识,诸如暴力、欲望等一旦被碎片化汇聚到虚拟空间中后,立刻被比特化进行放大,重新建构出一种形态,即主体身份的拼图化。在这个拼图中,巴赫金的狂欢成为了玩家一种本能的体现,文明与冲突逐渐成为虚拟意识空中的本体。在这个空间中,每一个玩家善与恶的碎片化意识都被重建为一个部落化的化身群体,玩家可以建立自己的权利所在,民主所在,一切的意识都在经历了比特化后重新构建出一种拼图化的彼岸。并进一步划分为两种拼图化的群体意识,一种则是相比现实的世界显得更加美好而和谐;另外一种,就如同在《绝地求生》中,无政府主义的生存化所呈现出的混乱。因此,现实中玩家个体潜意识中虚拟的碎片化被无限的解构为黑白两元,每一个玩家的“自主情结”在比特世界中转化为一种虚拟“个人意识”,即本能的看待数字世界的审美认知。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在《无意识心理学》中着重论述了有关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的理论。他说:“个人潜意识是紧靠意识门槛之下的相对稀薄的一层,和它相对照,集体潜意识在正常情况下没有显现出成为意识的倾向,并且用任何分析的技术也不能恢复它的记忆,因为它从来没有被压抑或遗忘过”个人的意识可以常常在文学和作品中本能的显示出来,一些无数次的欢乐和忧伤的残留都在群体的召唤下塑造为一个全新的有机整体。
可以明晰的是比特世界对于人潜意识的碎片化后的重组,包含着两个可能性:无序性和有序性。在社会学意义上,社会意识的碎片化往往包孕这削弱这向心力的危险,这是一种后现代做成现的反抗精神,而比特世界中缺乏权利的监管,这种重组后的部落意识,可能会影响到现实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诸如对暴力美学的误导和滥用。数字技术得不断进步,导致了人们数字化生存方式的可能性,虚拟世界中的生存现实被得以实现,最终导致了现实世界中的情感缺失,这未尝不是一种亟需人们深思的残酷现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亦又潜藏着审美民主和自由发展的机遇,开辟了全新的天地。
五、结语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认为,“一切知觉都发生在某个视域之中,最终说来发生在‘世界’之中;两者都以实践性的方式(partiquement)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由我们明确认识并设定的”。知觉从本质上来讲,呈现出从“对象-视域”(object-horizon)的结构,是对视角性特征的肯定性刻画即呈现出一种“对象-视域-世界”(object-horizon-monde)的拓展关系。因此,对于“视域”的本体思辨与现实转向,无论是对主体知觉还是对世界的感知与存在都产生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技术进一步扩大了空间与视域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到主体知觉的变化。正如电影《头号玩家》中,玩家的知觉在赛博空间中被重新定义,由数字比特所建构的对象,打破了原子视域的局限性,重构出全新的世界观与空间观,梅洛·庞蒂的“对象-视域-世界”的结构关系被比特化。比特视域的出现和转型成为整个未来虚拟世界中生存的重要介质,原子视域所给予人类了解世界的方式在发生着融合与跨界。真实与假象、存在与虚无、我与化身等问题,在比特视域中完成了时间的非线性和幻相的多维融合。齐泽克曾在《无身体的器官》中认为“赛博空间的幻相皆为真相”主体身份的解构和重塑,势必影响到未来人们对于本体论的考究,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哲学跨界后,再次回归到了奇点。
比特视域的时间流与幻相特质所持有的多维性、非线性使其将“看”的心理机制把持在完整性和模糊性的融合之中,凝视与想象被沉浸性所融合。这种数字文本空间的文化生态和存在方式也亦加速和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和思维。一切传统关于本质的感受都被重新定义,就像尼采所认为的本质并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寻求某种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环境中再次显现自己,显现自己隐性的环境亦使本质自身。比特化的视域环境,将原子视域的显现回归了一种原点。比特视域中人类社会的生态变化,不再被时间和维度所束缚,所有的空间存在都会被分类出无数个个体的空间,就像电影《黑客帝国》中那些沉浸在美好幻相的人们一样,本体与存在自身本身消除了界限。
注释:
① [匈]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6页。
② 注:原子论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一种重要思想,按希腊语:“原子”一词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文艺复兴之后以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提出了原子论的思想,认为物理世界的真实和存在都是通过“原子”作为单位而构成。随着物理学的发展,人们已经发现原子并非是最小的单位。但为了区别于数字空间的最小单位“比特”,笔者拟以“原子”作为现实物理世界的最小单位。
③ 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其中“质料因”是构建事物结构的最小单位。
④ [荷]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王荫庭、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9页。
⑤ Descartes,ThePhilosophicalWritingsofDescartes,Vol.I,Trans.by J.Cottinghamet a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227-228.
⑩ Patocka,“L’espaceetsaproblematique”,in Qu’est-ce que la phenomenologie?Traduitpar E.Abrams,Paris:J.Millon,1988,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