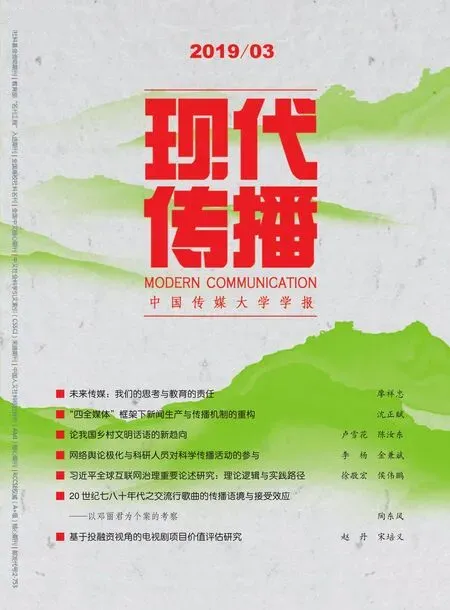以破碎的整体感重构产业美学:移动音频生产的本土经验
■ 战 迪
伴随着数字互动网络技术的高速迭代,信息传播和交易的成本大幅降低,从而催生了包括喜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企鹅FM、凤凰FM、木耳FM等在内的一大批新型移动音频App产品。作为独立于中国传统意义上国有媒体的“公用媒介”(public use media),移动音频产品以人人均享的信息发布、传播、分享、接受的模式创造着前所未有的声音信息资源形态,实现了以社会资本为主体,国家权力管控,市场调节的对自由资源的整合营销机制。如果说在我国20世纪30年代因电波资源稀缺、私人电台盛行而一度造成了产业秩序的混乱,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电台收归国有后秩序井然,1986年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所缔造的“珠江模式”、1992年上海电台和东方电台所创造的“广播活动+品牌主持人”的“东广模式”,以及此后不久北京电台推出的“音乐/交通台模式”再造了商业广播的传奇,那么,在新世纪伊始,随着电视业的蓬勃发展、新媒体的推陈出新,受众接受习惯的改变令传统广播业再次陷入低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移动音频产品应运而生。2013年3月喜马拉雅App正式上线,时隔不久类似的音频软件纷纷亮相抢滩市场份额。而2013年也无疑因此成为了中国移动音频产业元年。QM数据平台显示,2017年移动音频电台产品日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1400万人,每日使用共1.2亿次,日均累计使用时长达到4.3亿分钟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媒体副总裁李向荣声言,“当前出现了网络视听产品用户规模和使用率进一步提升、网络自制内容全面进入精品化、用户付费意识养成,用户需求更加细分化等趋势。”②据易观千帆数据统计,截至2017年末,国内移动音频用户呈爆炸式增长,移动音频用户一线城市居多,占比43.4%;中高消费者占比46.25%;用户年龄集中于36—40岁,占比35.27%。面对着如此优质的消费群体,传统广播拥抱新媒体的信心倍增,为迎接新一轮的技术挑战蓄势待发。
一般认为,美学是以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审美创造和审美鉴赏等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学科。相应的,产业美学作为美学研究与产业研究的交叉学科,是以现代化产业活动中审美生产与接受为研究对象的新兴领域。作为新媒体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音频生产集文化、审美、市场于一体,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应用性特征。它建基于后现代产业系统,生产流程的现代性和媒介产品的后现代性同在,并融合和适应于生态美学、技术美学、审美经济学、审美应用学和审美经济学等学科基础。特别是作为传媒艺术的试验田,其前沿的媒介性、大众参与性、科技性特征与传统艺术形态对举,别开生面。对移动音频产品的本土经验进行深入探索,不仅延展了传统广播产业的理论与实践范畴,更为产业美学的创新实践提供了绝佳的现实蓝本。
产业美学就是打破文化工业的创作惯性,以美学思维重构文化产业。在工业时代,这种理念仅仅是一种构想,但在后工业时代,特别是技术赋权和审美日常化的综合语境中,产业美学获得了全新的生成空间。而大音频产业的勃兴就是明证。在这种生产时空中,碎片化的音频片段被整合为一副整体性的审美印象。特别是根据具体用户的喜好,大数据,算法革命更是将一个个分散的音频信息编织成一幅幅宏大的百衲衣,具有整体性的美学图景。
一、从PGC、UGC到PUGC:深度参与的接受美学机制
当下国内移动音频产业的版图基本由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两部分构成,前者以喜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三大巨头为代表,吸纳了国内超过8000万的用户资源;后者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发的中国广播、HITFM,以及地方电台相继开发的听听FM(北京电台)、阿基米德(上海东方广播)、大蓝鲸(江苏电台)等为代表,这些App产品以移动电台的新模式创新了传统广播的传播方式。
客观而言,相较于民营移动音频产品,传统广播电台出品的移动产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短板和劣势:由于传统广播电台商业化运营模式的保守性、大数据使用和社交互动性等方面的不足,使得其运营能力偏弱;对传统广播内容模式的依赖性较强,难于形成互联网化的创新内容体系,因此原创能力不足;同时,由于对传统电台广播内容版权保护能力有限,导致盗版内容泛滥成灾,直接影响了移动电台的收益。不难想见,在疾风骤雨的新媒体传播环境中,传统电台的移动化进程并不顺利。反观民营移动音频产业,其高度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却具有超强的自我调节和自适应能力,由此在互联网商业的浪潮中激流勇进。举例为证,喜马拉雅FM以粉丝经济和社群经济为着眼点,不仅依靠传统广告收益,还推陈出新,开发了“音频淘宝”、主播工作台等应用程序,便于受众检索声音信息和发布个性化声音信息,以此来吸引会员。同时,与运营商合作分成、针对地方有声文化地标产品服务收益、对受众内容付费习惯的培养等,都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扩大了收益渠道,创新了商业模式。同样作为民营移动音频产品的荔枝FM,竭力打造社群电商模式,与运营商合作建立阅读基地,用“打赏+会员制”的方式开通虚拟物品商业路径。再以企业人力资源和对资本市场的融入为切入口,调研发现,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喜马拉雅500人左右的员工队伍涵盖了技术研发、智能硬件、大数据分析、产品运营、派驻海外等多个工种,其集约、高效程度均远超传统媒体。加之C轮融资亿元以上,创造了200亿人民币的企业估值。市场占有率居第二、三位蜻蜓FM和荔枝FM的员工也仅有400人和200人,经融资后市场估值分别达到25亿和30亿。可以说,民营移动音频产品尽管没有强大的政府资金支持,却借助船小易掉头的优势,以小博大,先发制人,及时跟进市场,创新产品。
不同于传统媒体,互联网行业音视频内容的发展经历了从用户原创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专业生产内容PGC(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和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三个明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以早期人人网、优酷视频、土豆视频为代表的UGC生产方式伴随着Web2.0概念的提出而倡导上传与下载并重的个性化体验,将个人内容共享推向主流,以重组后的优酷土豆网率先创办《逻辑思维》《暴走漫画》《飞碟说》等合伙人原创视听品牌节目为代表,PGC产品用专业化的内容生产强化了多元视角、民主传播和虚拟社会关系,那么,喜马拉雅FM倡导并率先推出的PUGC产品则打通了上下游的区隔,增强了深度参与的用户体验,重构了互联网音频的生态链。
值得强调的是,移动音频App内容生产以“UGC+PGC+独家版权”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以UGC表现形态的内容,却产生出接近于PGC的专业化效果。但PUGC产品却很大程度上克服了UGC产品内容粗粝,PGC产品因生态闭环而缺乏受众参与等方面的不足。在上游运营机制方面兼具个性化色彩,用户深度参与和专业化水准的同时,也为草根主播提供了系统性的孵化通道;中游联通了手机、车联网等技术平台,充分借助大数据技术支持为主流用户“画像”,靶向式定位目标受众,从而以算法推送的方式为用户智能推荐;而下游则采取移动终端用户、智能硬件、公共交通工具等多线布局。
一般而言,与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包括私营与国营在内的移动音频产品努力打破传统媒体线性传播的束缚,创造各种环形通路来实现点对点的互动式传播效果,进而激发用户的深度参与热情。特别是在其内容序列中,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报道、述评已经不是主流。相反,生产方另辟蹊径,将延伸自传统广播文艺的诸多内容形式反复打磨,形塑为带有强烈个性化色彩的付费内容。基于用户在使用移动音频App产品时对有声小说、人文讲座、情感故事、经典相声和时尚脱口秀等语言类产品的青睐,明星与素人相辉映的整合营销方式被广泛采纳。艾宝良播讲的“盗墓”系列小说、高晓松主讲的《晓说》、青音的心理谈话节目、郭德纲的《品俗文化史》、点击量超过3000万的素人脱口秀《然哥脱口秀》等一大批风格迥异的音频内容相继亮相,在满足目标用户复杂的口味的同时,也利用评论、点赞、打赏、订阅、收藏等种种途径构建起传受双方的深度对话机制。
媒介化生存背景下,艺术与审美的疆界大大泛化,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艺理论的创新互为表里。曾几何时,发端于18世纪的现代美学极力将艺术与工艺、艺术与非艺术在其核心概念中加以厘清。20世纪中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领袖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激烈批判成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精神记忆,以古典主义文学艺术来救赎社会的呼号犹在耳畔。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然过半,艺术显然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专利。泛媒介时代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普罗大众在技术赋权的背景下将18世纪贵族把玩的艺术,19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收藏的艺术,20世纪大资本家垄断的艺术收归己用,并通过充分改造,形成服务于现代社会需求的文明系统。杜威就曾在其《艺术即经验》中曾声言,要建设一种崭新的美学样态,“这种美学要寻找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艺术与工艺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像以前的许多美学家所做的那样,致力于区分。”③今天,我们讴歌包括移动音频产品在内的一切文化创意产业,正是从一个侧面为艺术的人民性正名,同时,也是对既往孤芳自赏的古典主义美学态度的一种反驳。找寻文化创意产业与艺术理念的连续性问题,可以作为一条通路,探索后工业文明生态中产业美学的共性与个性。显然,传媒艺术的大众参与性是这其中不容规避的一个重要现象和规律。
在传媒艺术的时代谱系中,作为深度参与者的新媒体用户,其规模之巨大、卷入程度之深入、对技术美学之熟稔是前所未有的。用户的审美习惯和欣赏趣味逼催着创作主体以时不我待的激情积极投身创意创新的洪流。作为一种创造美的技术,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媒介社会中,艺术的表达途径和作用范畴空前放大。大众参与的技术支持与权力增殖不仅彰显了审美领域中的民主意识,更为接受美学的实践提供了绝佳的注脚。如果说传统视听媒介研究领域对受众意识的关注还停留在阐释学的视角,强调受众期待视界与审美距离的辩证关系的话,后工业文明语境中的接受美学方案则打破了传者中心与受者中心的博弈,以某种反中心话语的张力勾连起传受双方求同存异、平等对话的机制。而巴赫金所倡导的对话未完成性也在人人共享的文化广场中最终得以印证。亦如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伊瑟尔所提出的“召唤结构”,文本中埋藏着诸多“空白”,“一种寻求缺失的连接的无言邀请”④。
高晓松在《晓说》这样一个纯粹的听觉文本中,常常被听众戏称为“坑王”,他时而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社会文化热点纵谈某一话题,听取用户的建议调整节目方案,补充、添加故事信息,时而会在“种草”后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取消预定主题,任性地选取自己崭新的话题。这样的案例在《小沈龙脱口秀》《李诞脱口秀》等素人音频节目中时有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晓说》等移动音频节目并非完整而自足的文本阐释链,而是一种碎片化的启发性结构,留给听众更多的“空白”,邀约他们自行阅读、填充、完型。从这个意义上讲,移动音频产品从UGC、PGC向PUGC演变的历程正是技术迭代导引下受众深度参与的接受美学机制的形成过程。
二、从工业噪音到声音风景:听觉文化的复兴与推广
20世纪60年代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初兴引发了学界关于视觉文化的思考,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米歇尔正式提出“图像转向”的概念,则标志着“读图时代”业已得到全面确认。当代高度发达的视听传媒技术在助推 “媒介化生存”的现实图景的同时,也不断佐证着“视觉中心主义”的话语地位。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一直信奉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思维理念,并笃信视觉文化的力量远超听觉。即便1997年学者韦尔斯在其专著《重构美学》中大胆地提出了大众文化声音转向的观点,也并没有引发过多的学术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韦尔斯声言:“听觉文化的兴起可以说是电子传媒一路畅行之后的必然结果,它更具有一种后现代气质,固然它没有视觉文化的延续性和同质性,但是它具有电子世界的共时性和流动性。”⑤然而,在唱响电视、唱衰广播的21世纪前后,这种观点因得不到实践的支撑,显然不能获得广泛的认同。
令人诧异的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移动音频产品的异军突起,在“视觉霸权”的大众文化领地中另辟蹊径,获得惊人的产业奇迹,不能不说,现代人内心深处深藏的听觉基因被全面激活。曾经从大众传播、分众传播到今天垂直传播的理论构想已经成为现实,移动音频产品的自我订阅和基于算法推送的内容共同建立起用户专属的“声音List”,麦克卢汉所言的“重新部落化”构想在声音产品的粉丝社群中被搭建成型。自此,以小博大,挑战视觉文化的听觉文化也重又浮出水面。对此,有学者不无夸张地预言:“人类和我们星球的继续存在,只有当我们的文化将来以听觉为基本模式,方有希望。因为在技术化的现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堕落还是得救,灾难还是拯救这就是不同选择的图景,人们正试图以它来搭救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⑥
在西方学界,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声音文化(Sound Culture)一般被认为是“研究对音乐、声音和噪音以及相关科技的物质生产及消费,以及上述这些是怎样在历史和不同的社会里变迁的”⑦。将这一概念接榫到国内实践语境中,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移动音频产品的横空出世不仅验证了声音文化相关理论推演的合法性,更为相关产业美学的勃兴带来了现实启发。如果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演说作为一种声音政治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兴盛,那么,近年来南开大学文学院周志强教授所反复批判的“唯美主义的耳朵”则直指后现代工业文明下流行音乐生产领域中的“工业噪音”。诚然,在后工业时代,泛娱乐化、戏仿、机械复制等生产机制一定程度上异化了声音美学,导致“灵韵的消逝”,但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在移动音频产业所搭建的文化艺术舞台中,精英话语有的放矢、平民话语异军突起,二者同台竞技,形成了彼此制衡又平等对话的良性氛围。借用西方学者雷蒙德·默里·谢弗的提法,“声音景观”(Soundscape)的价值正日益凸显。
声音文化的重装出场并非历史的巧合,作为视觉文化的补充,它填充了现代人视觉依赖的种种不足。作为一种哲学和美学的实践,移动音频产业具有着先天的认知优势。首先,从生理状态出发,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可以“闭目”,但无法做到“塞听”,于是,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倾听主体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特别是在移动音频产品的收听方面,用户本能地基于一种内敛的主体性体验来接受信息,兼听则明,这无形中抑制了主体性的张扬与泛滥;其次,相较诉诸于感性的视觉文化,听觉文化的深度性较强,“倾听主体不是要像现代视觉文化中视觉主体表现出的欲望贪婪和止于图像表层,也不是要鼓噪饶舌地制造无尽的噪音污染,而是要通过倾听他者的声音,进入事物本质的深层,真正达到对世界存在的本真理解并在这种理解过程中实现对自我生存意义的高度升华”⑧;最后尤为重要的是,移动音频产品本身并不负载过高的技术含量,更多诉诸于声音形式的美感和声音内核的理性法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为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视觉文化生产中过度张扬的技术理性起到纠偏的作用。
在大音频产业系统中,借助新媒体平台发轫并广泛释放的声音能量,不再仅仅局限于诉诸听觉的物理性传播情态,而是通过技术与审美、物理与心理、社会与文化的综合叠加形塑为丰富的意义系统。西方学者早前曾指出:“声音直接引起激动,作为有机体本身的震动。听觉与视觉常常被列为两种‘理智的’感官。实际上,尽管听觉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理智范围,耳朵在本性上却是情感的感官。”⑨一如视觉风景,当声音图谱被打磨、加工、复制、扩散为声音景观时,声音文明与社会变迁的相关性必然越发紧密,它既是一种对自然界的超越,也是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领域的全面拥抱。听者当然可以用审美的耳朵聆听伊甸园般的“声音花园”,也可以用社会学的耳朵倾听多元的批判话语,更可以用政治学的耳朵体悟社会变迁的精神动力。总之,移动音频产品的高超之处恰恰在于以某种生活审美化的方式打造出用户专享的私人领地,而“解读声音景观问题的总钥匙,不在于声音自身,而在于选择性聆听、塑造声音变迁的听觉性感知与思维”⑩。
如果说早前的广播可以被视为监听公共空间的听觉背景,那么,新媒体语境下的音频产品则是耳机深处的“私密事件”。可以说,在以耳机为媒介的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声音世界里,无论是流行歌曲、经典小说、文化讲坛、心理访谈,还是作为声音杂耍的脱口秀,都将听者与真实世界暂时隔离,在健身房、私家车、安睡前的床头塑造出一个自足的聆听时空,极大地满足了人们便携、自由诉求的同时,也扮演着后现代流浪者的角色,亦如“自给自足的城市旅行者,为了应付各种天气和各种情况并在一个自我包围、自我设置的声音气泡中穿过城市所必需的装备”。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移动音频不仅成功地将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听觉产业化运作和推广,更在听觉主体性的建构中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语境化的动力系统,从而实现“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
三、破碎的整体感:技术驱遣下的“品位共同体”建构
关于后现代文化中“碎片化”阅听体验的相关论述已屡见不鲜。当然,从技术决定论的立场出发,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技术文明对审美文化领域的僭越已是不争的事实。现代传媒技术的高速迭代发展丰富了传媒艺术的表现手段,扩大了审美接受和体验的范围,特别是通过产业手段强化了信息传播与分享的民主化进程,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技术赋权的驱动下,碎片化的垃圾信息泛滥成灾,非个性与伪个性的媒介内容以商业性取代了审美性,直接导致了阅听者审美感受力的钝化和惰性。既往学者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技术理性对表现理性的伤害,并直陈消费民主性不等同于文化民主性,认为前者以市场交换为基本逻辑遮蔽了商品背后的世俗性和功利性,后者尽管在形式上被区分为若干圈层和层级,却在本质上相互渗透、融通。
作为创意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移动音频产品具有显著的大众消费属性,在垂直付费的引导下,被细分为无数复杂的枝系,碎片化特征十分明显。特别是草根话语的崛起似乎抹平了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再次脱去了古典艺术神秘而不可见的外衣。随着多元话语在新媒体平台的泛滥,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所言的“意义的通货膨胀”显而易见。“审美文化在符号的生产规模方面和能力上,早已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意义的生产上,却和这样的规模正好形成鲜明的反比关系。产品越多,意义却越平庸越浅薄。”当然,这种“意义贬值”的现象在传媒艺术产业化进程中是一个难以逾越的特殊阶段。特别是UGC、PUGC互联网视频生产的崛起,更以喜剧性为主导性审美范式消解了“宏大”与“崇高”的美学传统,助长了理想型文化向世俗型文化的转变。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相较于传统视频产品和当下流行的短视频产品,移动音频产品依托声音传播本身开放性、深度性、理智性的认知特质,并借助垂直性付费模式的支持,在私密化的信息接受氛围中重构了用户的审美趣味与阅听习惯,进而形成了不同类型、层级的声音文化彼此平行、交叉传播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在移动音频产品中,审美文化领域中的古典文化、现代文化与后现代文化并非各自铁板一块,拥有着彼此绝缘的专属领地。相反,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回归传统与倡导和谐的古典文化在有声读物的历史、人文板块被娓娓道来,并在文化名家散文化的讲述方式中被赋予了现代性启示;相应地,在《晓说》《领读者》《逻辑思维》中曾经被认为与大众文化格格不入,“拒绝交流”与“拒绝阐释”的现代主义文化在保留了其思想自主性、趣味对抗性和文化严肃性的前提下,也俯下身躯,以道德关怀和审美坚守的名义反思社会现实,希图起到批判与重建的应有之义;特别是一度被认为击碎“元叙事”,打通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文化与非审美文化之间的区隔,并“生活在碎片之中”的后现代文化,努力寻求各不同社会、自然层级领域受众之间的可通约性。喜马拉雅点击量过4000万的《然哥脱口秀》《上班脱口秀》等产品亦为典型代表。
从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出发,当代文化产业中存在着“有限生产场”(The de-limited field of 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The large-scale field of production)两类场域。如果说前者指称艺术生产和消费的群体同为文化界圈内人士,而后者则将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相剥离。实际上一直以来前者都是通过“命名权”对后者行使宰制性权威的。然而在移动音频生产领域,两个场域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生产者和消费者彼此交合,在错综复杂的传受链条中,碎片化的声音信息被缝合成一张色彩斑斓的百衲衣,呈现为不同个性人群的“品位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群落既不是以古典、现代、后现代三大审美文化形态和结构来进行划分,也不是基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进行划分,而是在复杂的分化和整合机制中被一种“破碎的整体感”所笼罩。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尽管宏大叙事依旧失语,“中心情结”荡然无存,畸形审美仍然存在,但庆幸的是,边界的消弭和类型的重组令严肃艺术不再绝缘,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得以复现,草根达人在纵情狂欢之余也会在产业美学的发展脉络中找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最终,在移动音频生产领域,“品位共同体”渐次被搭建成型。
总之,移动音频产业所构造的产业美学是以技术理性为先导,大众深度参与为表征,现代化工业化流程为手段,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体验”与“品位”为内核的后现代媒介文明。诚如杰姆逊对审美文化的现实构想,纪念碑式的作品已然不复存在,“而是对以前存在的文本碎片的无穷重组:一种拆除其他书以装配自己的元书,一种核捡其他文本碎片的元文本”。
注释:
①② 《共商媒体融合大计 首届“广播新声音大会”在杭州开幕》,中国新闻网,http://www.zj.chinanews.com.cn/news/2017/1222/9051.html,2017年12月22日。
③ 高建平:《文化创意是产业时代的艺术追求》,《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④ [德]伊瑟尔:《本文与作者的交互作用》,《上海文论》,1987年第3期。
⑤ [德]沃尔夫冈·韦尔斯:《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⑥ 陆涛:《文化传播中的听觉转向与听觉文化研究》,《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⑦ Trevor Pinch and Karin Bijsterveld.Introductionto“SoundStudies:NewTechnologiesandMusic”.Special Issu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4(5),2004:636.
⑧ 肖建华:《当代审美教育:听觉文化的转向》,《中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⑨ John Dewey.ArtasExperience.New York:Perigee Book,1980:264.
⑩ 王敦:《“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学术研究》,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