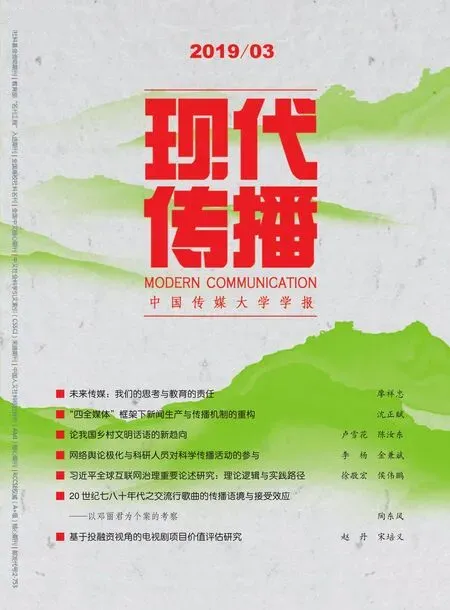本体·泛化·滥觞:论改革开放40年本土类型电影的嬗变*
■ 徐兆寿 林 恒
一、中国本土类型电影问题概说
“类型电影”是美国电影制片厂制度完善后的工业化产物,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将不同的题材、人物、情节、技巧进行模式化归类,按照不同的类型要求进行制作,以满足观众“期待视野”的商业电影。早期中国电影从艺术片到商业片的“陡然转向”,发生在美国好莱坞电影、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民族文艺审美取向的共同作用之下。在这种由电影经营公司和知识分子主导的生产结构中,虽说可以看出中国电影的类型化端倪,但却很快被其他创作潮流所替代。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国电影创作始终带着政治的镣铐舞蹈,无法充分满足中国观众的诉求,同时也扼杀了电影创作者的个人才能。而1978年“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的重视,直接引发了此后40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化、商业化的不懈探索和持续深化,类型电影在客观上越来越被大众熟知、接受和认可。如今本土类型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市场的中坚力量,不仅在电影创作中形成核心主导,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并且正以独特的本土艺术性,持续改写着世界类型电影的创作走向。
纵观中外电影史,电影的艺术特性虽然自有其性,但只有在广泛的传播中才能被大家所认知。在国家行政手段严格管控的时代,电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电影的传播是宣传工作的内容之一,所以那时候的放映员可以到偏远的山区,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是传播至每一个人。而市场经济建立以来,国家行政手段减弱,市场的力量崛起,电影不也是简单的宣传内容,而是要付费的消费品,此时,电影的商业价值才被确立起来。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40年都走过的道路。今天,讨论电影的价值多偏于市场经济以来的商业价值,很少再去讨论电影的宣传教育功能,这也是时代特征所决定的。而中国电影在数量上繁荣、产业上创汇、国际传播力方面的提升恰恰是在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激活了电影消费与创作的潜在能力,当然。这也与中国的开放政策分不开。世界电影的涌入为中国电影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的影响是从内到外的一次革新。
顺着这一路径,来考察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电影,可以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一是1980年代第四、第五代导演对电影本体表达的探索,这一时期的电影仍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内容,市场由国家管控,导演的任务就是拍好电影,而电影传播的任务则另有广大而严格的国家渠道,也无需导演来操心。二是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探索期,逐渐形成主旋律电影、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创作格局。这是中国社会的阵痛期,也是电影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阵痛期。其前期仍然是沿续着1980年代的艺术之路在行进,但因为思想的进一步开放使电影的创作有了更为宽广的精神之路,所以在早期出现过一些经典电影。1990年代中期,大众文化滥觞,思想进一步解放,市场也进一步松绑、解放,市场经济的雏形已有,电影也出现了商业电影。三是21世纪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电影开始与世界电影争锋,再加上网络信息媒介的催发,终使中国电影业迎来了大发展,形成贺岁大片的类型电影滥觞、多元泛化的类型片发展。而“类型片的成熟与发达,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电影产业兴盛的基础”。①它不仅显示出中国电影强大的内部驱动力,而且也显示出中国电影的立体形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发展,才使中国成为世界电影第一大国,但要走向世界电影强国,还要在电影艺术方面再上台阶,也需要在电影技术领先于世界。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总结中国类型电影的得与失,将有助于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
二、观念转变:中国本土类型电影创作意识
《易》云:“否极泰来”。否卦的上卦是天,下卦是地,指天越来越高,而地越来越低,天与地离得越来越远。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意识形态在后期走向了人心的反面,这就必然会导致人民的反对,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追求“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了中国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强大,这便是泰卦的意思,上卦为地,下卦为天,意思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百姓为天。否卦意味着否定,而泰卦意味着安定团结,这就是1980年代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
此时,电影业从体制改革入手,重整电影放映事业,“十七年”电影得以解禁,市场状况一片大好。与此同时,为摆脱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影响,第四、第五代导演纷纷奉行欧洲“作者电影”,追求个人思想的表达,以美国好莱坞为首的“类型电影”则被贴上“艺术模式化”的标签而遭到质疑和批评。这种电影创作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电影产业在文革之后快速恢复,但是这种由精英主导的反叛性现代话语与中国观众的传统审美经验却发生了巨大的悖离,从而压抑了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再加上电视的逐渐普及,使电影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急速缩水,“1984年比1979年全国城市电影观众下降了30亿人次,平均每年下降率约为6%,1985年更是出现了极具下降的趋势,主要城市下降率高达20%—40%”②。为了解决当时的观众危机和票房危机,中国电影界逐渐将目光转向繁荣发达的好莱坞电影,其成熟的产业化、娱乐化、类型化开始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学者邵牧君认为,商业电影和类型电影的本质是相同的,类型电影支持电影的商业规律,同时也促进了电影的再生产。树立正确的类型电影观念,不仅是创作者对电影特性和观众诉求的尊重,同时也是探索本民族独特的类型范式,实现中国电影本土化的必由之路。于是,为了扭转1980年代中期急速下滑的电影市场,中国第五代导演开始积极寻找商业化与雅文化的交叉点,以1987年张艺谋导演创作的《红高粱》为起点,中国电影单纯追求艺术性创作的观念开始逐渐发生嬗变。影片改编自莫言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抗战时期山东高密农民的普通生活,以及经营高粱酒坊的男女主人公抗击日军的曲折经历。导演一方面注重选材的故事性和真实性,力求贴近普通观众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想象;另一方面又不拘一格地使用色彩和光线,以“黄色”的土地表示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以“古铜色”的皮肤代表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性格,以“红色”的高粱表达人们对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的向往。可以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创作中,完美结合了电影的商业性与艺术性,并将个性化的导演风格融入到综合化的类型题材中,将民族话语融入世界话语体系,从而开启了以反映“中国老百姓的常态生活”为基础,力求“电影语言的国际性”的中国类型电影探索之路。当然,必须看到,商业性和类型化是我们从今天的视角进行观察的结果,事实上,在1980年代中期,商业化思想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掀起,它不仅是政府主导的国家意志,同时也是百姓渴望富起来的个体意识,但它仍然是作为一种强烈的冲动和意识而出现,还未曾真正落实到行动中。
所以,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就成熟的就好莱坞类型电影而言,中国对类型电影观念的接受明显是滞后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故事片大多集中在对当代文学小说的改编,例如颜学恕执导的《野山》(1986),改编自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通过讲述小山村里的两对夫妻,探讨改革开放精神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谢飞执导的《本命年》(1990),改编自刘恒的《黑的雪》,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反映巨大时代变革中的年轻一代迷茫、焦虑的心理状况;黄建新指导的《背靠背,脸对脸》(1994),改编自刘醒龙的《秋风醉了》,借由主人公滑稽的政治生涯,反映中国人传统意义上与政治的关系;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改编自王朔的《动物凶猛》,通过讲述文革时期北京部队大院里的青春故事,探讨阳光与红旗之下年轻人的成长问题。这些带有现实主义创作倾向的电影,虽然仍具有典型的精英知识分子批判色彩,但就电影本体的视听表达而言,创作思路已经逐渐从过去意向化的造型语言中跳脱出来,转而朝向对商业电影叙事特征的不懈探索。与其将这些故事片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进入商品社会的产物,不如说它是改革开放时代下,中国电影不断朝向商业类型化迈进的“探索片”。
实际上,类型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单纯由电影界创造出来,或者简单地归结为资本经济的发展产物,中国电影走向商业类型化市场也不是一簇而就。类型电影所表现的模式化、规范化特征,其实也深刻地表露出一个民族深层的审美文化心理。1980年后期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促使相当一部分导演进行类型电影的尝试,例如滕文骥执导的爱情片《大明星》(1985)、剧情片《飓风行动》(1986);黄蜀琴执导的惊悚片《超国界行动》(1986);周晓文执导的犯罪片《最后的疯狂》(1987)、《疯狂的代价》(1988);田壮壮的剧情片《摇滚青年》(1988);张艺谋执导的动作片《代号美洲豹》(1989)等。但这些完全西方化的类型电影并没有受到重视,甚至在票房上也接连失利,反而那些改编文学小说的“探索片”占据了主流,这也从另一方面揭示了中国观众长久以来的观影经验与审美特征趋向于精神文化主导的方向,当然,这也与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有关,人们最为看重的是思想之新。这也就很容易理解在那个时代为什么文学的位置远远高于其它艺术,而电影也只能是文学之后的艺术品,而且那时人们对电影的理解就是文学的影像化。这样一种电影的观念直接影响着电影的类型化和商业化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商业化与大众化、娱乐化是一体的,而类型化与思想的多元格局是一体的,但1980年代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主张多元格局,但总体上是反对大众化和娱乐化的,因此,从今天来看,那个时代的电影思想是处于矛盾中的。
三、自觉探索:中国本土类型电影创作实践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和21世纪初的兴旺发达,改革开放便也只能是空谈。反过来说,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是形而上的探讨,而1990年代便是形而下的探索,但真正摸清路径大发展则到了21世纪。这就不难理解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意义,它标志着我国进入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这是改革开放40年的第一个分水岭。第二个分水岭则是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
在1980年代电影探索的惯性下,1990年代的电影便开始迫不及待地向着市场行进,但此时的一切都仍然在阵痛中,从政府控管到市场的自主建立这一转型还仍然在摸索中,因此虽前路茫茫,但信心百倍。当然,也免不了最初的尴尬命运。据资料显示,中国电影在1995前后遭遇了巨大的冲击。“1994年全国电影观众人次从1979年的293亿下降到3亿,1995年进口的7部进口大片占据了中国电影票房的80%”,1997年的电影产量比90年代的电影年平均产量降低30%”③。进口大片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打破了20世纪80年代电影人对于“类型电影”的简单想象,在这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中国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行业,都不得不从经济的角度思考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此时电影界讨论的已经不再是“类型电影”涉及的娱乐性、商业性,或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世界电影竞争格局中,积极应对商业化带来的挑战,努力拍好中国本土类型电影以及建设市场机制的雏形。
尽管当时电影界已经意识到类型电影创作与特定民族和特定时期的普遍社会文化心理密切相关,但培养稳定、统一的观众群体却是发展类型电影的票房前提和市场保证。在培养特性的类型电影观众方面,冯小刚于1997年开始,连续四年的“贺岁片”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甲方乙方》(1998)、《不见不散》(1999)、《没完没了》(2000)、《大腕》(2001)等,都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积极迎合了中国转型期市民的大众趣味,以滑稽、调侃的叙事技法刻画平凡的生活素材,摆脱了过去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目标和审美理想,将单调、平庸、重复的生存现实,转化成银幕上充满诱惑的奇闻异事,通过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娱乐精神,将生活中啼笑皆非的日常琐事,改造成普通人的现代性神话,不仅消解了传统中国电影的批判标准和道德立场,并且给予现代都市市民情趣的合法性定位和足够的精神支持。这些具有典型“中国式”喜剧特色的“贺岁片”,在消受层面上极为符合当时中国观众的审美趣味,其在票房上获得的巨大成功,不仅挽回了国产电影低迷的国内电影市场,并且成为中国本土类型电影中一个醒目的标志,这是大众文化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泛起的大众文化热潮,精英文化开始退守于一隅,而大众文化甚嚣尘上。精英们处于一片焦虑之中,但网络文学、娱乐文化、电视的商业化、电影的娱乐化发展处于一片兴旺之中。一阴一阳之谓道,过去是大众文化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文化只有单一的国家意志,民间文化没有兴作,现在,国家意志的精英文化稍稍退守,民间文化便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全球化和商业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为了与进口大片抢夺国内电影市场,中国第五代导演积极突破“艺术片”观念的桎梏,开始陆续投入到商业电影的制作,从而寻求自我创作的转型。以张艺谋拍摄的《英雄》(2002)为起点,中国电影正式开启商业大片时代。这部耗资3000万美元,聘请内地、香港众多华语电影明星,集结世界范围内优秀电影工作者拍摄的武侠巨制,最终以全球票房1.77亿美元,国内票房2.5亿元人民币获得2002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此后,以注重明星效应、追求叙事规模、营造视觉奇观为主要特征,以满足满足票房为首要目标的商业大片,开始迅速成为中国电影界创作的主流。例如张艺谋相继执导的《十面埋伏》(2004)、《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陈凯歌执导的《无极》(2005)、张之亮执导的《墨攻》(2006)、冯小刚执导的《夜宴》等,都将创作题材对准古装、武侠类型片,借助耀眼的明星和绚丽的视觉特效,迎合中国观众长久以来对“武侠形象”的集体崇拜和对“传统江湖”的无意识想象。然而,商业武侠大片作为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中国类型电影,虽然在票房上获得了惊人的成绩,但在形式风格和文化内涵方面,却招致一片质疑和诟病。对明星、特效、场面、票房的盲目追求,使得中国导演忽略了对经典文化“探本求源”的影像剖析,用“假、大、空”的叙事方式勾勒出整部电影,使得影片在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上显得苍白无力。因此,虽然这些武侠大片适时满足了中国观众对于本土类型片的迫切需求,但最终由于文化内涵缺失导致观众审美疲劳,期待受挫,因而其逐渐在2006年之后走向衰落。
此外,在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类型电影创作过程中,香港导演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2003年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签定后,香港电影不再受到进口配额的限制,香港电影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北上浪潮,如徐克、陈可辛、陈嘉上、刘伟强等知名香港导演都陆续到内地开办工作室或与大陆合作拍片。于是由内地制片方投资出钱,香港导演出力的“合拍片”生产模式,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电影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色。香港导演的加入一方面扩大了中国类型电影题材的创作范畴;另一方面,他们丰富的创作经验也使中国本土类型电影更具市场号召力。像陈可辛执导的爱情片《如果·爱》(2005)、古装片《投名状》(2007)、徐克执导的武侠片《七剑》(2005)、尔冬升执导的犯罪片《门徒》(2007)、陈嘉上执导的魔幻片《画皮》(2008)等,均获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然而,两地“合拍片”的初期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许多北上导演由于不了解内地观众的文化心理和电影生态,因此通常放弃自己所擅长的当代类型电影题材,转而跟风拍摄一些相对容易过审的古装、喜剧类型片。拍出的电影同中国式大片一样,只流于皮相而缺少内涵,导致“叫座容易叫好难”,同样引来观众不少的负面评价。因而面对复杂、激烈的市场局势,一味追求“商业价值”并不能成为电影创作的先决条件,中国本土类型电影创作有待进一步深化。
四、多元泛化:中国本土类型电影格局
其实,类型电影并不是一个区别艺术与商业的机械式的概念,而是一种建立在“作者”和“观众”的共同认同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惯例系统和创作范式,“如同一条连接电影工业所想和电影观众所需的可靠纽带”④。如果简单把创作定义为电影思想性的集中体现,票房作为一种电影商业性的集中代表,则会割裂作者与观众、艺术与商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类型电影创作也“不应被视为一个在形态学意义的完全封闭的系统”,它的变迁既受电影工业发展的影响,又随着时代变迁和观众喜好而不断演变,所以应将其看作是“一种在标准化运作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开放性系统”⑤。于中国电影发展而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多元文化语境、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电影观众复杂的心理结构,无疑加大了类型电影本土化创新的难度,这也是多年来类型电影在曲折探索的根本原因。2008年以后,随着观众市场进一步分化,中国式商业大片的浮华逐渐退去,类型电影的制作愈发注重质量,其创作格局开始逐渐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在以“娱乐性”为指向的商业电影创作中,喜剧片凭借其本身的电影特性,迅速成为中国类型电影创作的重点。以宁浩执导的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2006)为代表,中国本土喜剧片开始显示出独有的本土风格和内涵。影片讲述了重庆某工厂保安、本地小偷、国际大盗三方人为争夺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所引发的一连串笑料百出的故事。片中的场景、人物、台词极具重庆本土特色,故事结构逻辑严谨且富有张力。影片以工厂保安的无知胜利作为结尾,不仅积极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而且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重新解释了利益面前的善与恶,可以说较好地将艺术性与商业性融合在了一起,颠覆了国产商业片长期以来重明星、重特效、重票房的浮夸倾向。此后,中国喜剧类型片开始逐渐抛弃表面的喧哗,转而朝向对内涵和深度的挖掘,例如《长江七号》(2008)、《疯狂的赛车》(2009)、《人在囧途》(2010)、《无人区》(2012)、《夏洛特烦恼》(2012)、《重返20岁》(2014)、《美人鱼》(2016)、《驴得水》(2016)、《一出好戏》(2018)等票房较为成功的喜剧电影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对人生价值的判断和人性善恶的考量,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影片采用救助白血病患者的真实故事原型,将喜剧元素灌入电影叙事,在笑与泪之中完成对人性的拯救,不仅受到观众和业界的广泛赞誉,并且影片中所涉及探讨的医疗问题,还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堪称中国喜剧类型片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以现代都市背景的类型电影创作中,由于“爱情”本身具有的普遍性和关注度,因而也迅速成为当下中国本土类型电影的重要创作母题。一是以《失恋三十三天》(2011)、《北京爱上西雅图》(2013)、《一夜惊喜》(2013)、《等风来》(2013)、《小时代》(1—4)、《前任》(1—3)等为代表的小妞电影,通过描述现代都市白领女性寻觅自我和内心成长,最终获得爱情的理解和人生意义。这一新类型电影题材,由于其本身具有丰富的现实土壤和庞大的女性观众群体,因而成为中国本土类型片发展中,以“小成本投资”和“明星效应”抢占高票房的突出代表。虽然中国小妞电影在票房上的成绩值得肯定,但其短时间内的井喷式发展,则间接导致了影片同质化、山寨化的情况出现,故而近年来中国小妞电影也总体陷入了叙事空洞、趣味偏低的尴尬处境。
二是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匆匆那年》(2014)、《左耳》(2015)、《七月与安生》、(2016)、《无问西东》(2018)为代表的青春爱情片,通过展现青春的懵懂和伤痛,将美好的青春神话进行颠覆和重构,重新唤醒观众对于青春的期待和追忆,弥补了中国电影长期以来强烈的政治意识造成的观众个人心理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青春片创作的严肃和呆板。但不足的是,当下有不少青春爱情片,为了追求票房的最大化,以“明星”“粉丝”“初恋”等为话题进行炒作,内容上生硬地拼凑中国社会变革造成的青春断层,过分突出青春的坎坷、迷茫、惆怅,从而忽视了电影的艺术性和青春的真实内涵。
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以“合拍片”为代表的动作类型片,经过两岸三地电影人多年的探索与磨合,逐渐成为中国电影由“本土”转向“全球”的主要创作阵地。其一是武侠片的创作逐渐走向多元化,以《苏乞儿》(2010)、《龙门飞甲》(2011)、《黄飞鸿之英雄有梦》(2014)、《狄仁杰》(1—3)为代表的影片主要专注于视觉场景、动作特效方面的突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武林的猎奇和想象,创造了银幕上特有的中国奇观;以《剑雨》(2010)、《绣春刀》(1—2)、《刺客聂影娘》(2015)为代表的古装片主要将当代人的意识、观念倾注于武侠题材,借以叙事的内化完成对人性的思考;以《黄元甲》(2006)、《十月围城》(2009)、《一代宗师》(2013)、《叶问》(1—3)、《止杀令》(2013)为代表的影片多注重中国传统武学特有的精神内涵,将“止戈为武”与“民族大义”联系起来,突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侠义精神和民族气节。
其二是警匪片的创新不断走向泛化,以《西风烈》(2010)、《毒战》(2013)、《解救吾先生》(2015)、《烈日灼心》(2015)、《心迷宫》(2015)、《暴裂无声》(2018)等为代表的本土警匪片,在结合当下中国的实际现状与社会秩序,满足观众暴力欲望宣泄的同时,力求深入探讨人性、道德与工业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兼具艺术性和商业性。以《反贪风暴》(2014)、《非凡任务》(2017)、《湄公河大案》(2017)、《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等为代表的主旋律动作片,在宣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套路中,有机地融入了暴力、犯罪、警匪等类型元素,使故事剧情愈发显得生动和饱满,克服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严肃、呆板的政治说教,近年来大受海内外观众的喜爱。
从这些琳琅满目国产电影中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本土类型电影经过不断地探索与演变,基本形成了以喜剧片、爱情片、动作片为主的创作格局,其亚类型片逐渐朝着多元泛化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在类型电影的创作中,对不同类型元素进行组合与重塑,都会演变成一种新的泛类型样式。对于成熟类型题材电影的把握,对类型元素的创造性使用,如今愈发成为衡量一个导演创造力的标准,因而类型电影创作也不应作为一种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它实际要求在创作者在立足中国本土现实,了解观众审美心理,尊重电影创作规律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导演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找艺术表达的新方法,这不仅是类型电影创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导演表达个人艺术理想,寻求自我突破的有效路径。
五、机遇与挑战:当下中国类型电影困境与对策
古人云,欲速则不达。中国在电影的快速发展中已经成为电影大国,在电影票房、电影制作量等方面均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要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世界强国则还有很大的距离。从这个高度来看中国类型电影的发展,则存在很多问题。
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电影的发展,是在国家宏观市场体制改革主导下,由观念转变不断迈向实践转型的动态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电影放映,平衡制片、发行、放映三方利润,到20世纪90年代完善电影制片厂,建立院线制经营,促进产业化建设,乃至新世纪后,深化电影市场机制改革,吸引各类资本进入,实施加快主动开放策略。中国电影创作在宽松的政策和开放的环境下,逐渐摆脱了过去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几代电影人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为原始动力,在融合西方艺术思潮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和社会发展,不断修正、吸收好莱坞电影的类型模式,以剔除呆板观念、拒绝生搬硬套、谋求本土生存为基本思路,创作出有别于西方类型标准,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类型电影,逐步建立起开放、成熟的电影观念,推动了电影工业体系的生态建设。
然而,就世界类型电影发展而言,我国在对商业电影的实践探索方面因为时间较短,走得过快,而社会政治、经济等大环境本身存在很多问题,再加上电影机制与市场的不完善,便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首先,存在重市场、无调控和重形式、不重质量以及有高原、无高峰的问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电影创作环境中,中国类型电影大多以追求票房为首要目标,对电影的质量、思想和艺术性方面的追求就显得力不从心。虽然电影的产量和票房都位于世界前列,但没有令世界赞叹的高质量的作品,就像习总书记所讲的那样,有高原却没有高峰。究其原因,还在于电影工作者放弃了精英立场,在形式和内容上过分倚重大众心理,类型题材的选择多以爱情、喜剧、动作为主,创作格局较为狭窄单一,作品层次较低。部分创作者为了突出电影的“娱乐性”,不惜以夸张搞怪的人物定位、怪诞离奇的情节构思,颠覆观众对现实清规戒律的传统认知。不仅使电影丧失掉应有的艺术性,无法成为国家理想的叙述者,并且产生严重的媚俗化倾向,导致影片丧失底线,引发价值观的混乱。李安导演2013年接受采访时曾说道:“内地还没有很好的电影,观众品味需要培养。”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平衡是事物发展的最终目的。电影的发展也一样,既要有精英意识引导,也要允许广大的民间的大众文化的兴作,两者要不断地协调,才能产能好的文化和艺术作品;既要有政府的调控,要有体现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的大片、好片,也要允许市场自洽的大众娱乐文化的繁荣。现在的问题在于精英意识在当前的电影市场没有多少立足之地,政府的调控力也有所失当,不能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去认识何为中国精神,哪些故事是中国故事,导致电影创作方面存在视野狭窄、思想认识不清、站位不高的种种情况。若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国家电影的管理者做好顶层设计,但这种顶层设计不能简单地照搬政治的教条,而要从党和国家制订的宏观视野中去寻找更大的空间,要扶持精英立场的电影走向市场,同时,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只有这样,类型电影才能上质量、上层次,也才能够有高峰。
其次,存在一味地摹仿西方电影的倾向,缺乏中国风格的类型电影。中国本土类型电影发展较迟,后来的发展又较为迅猛,一味地摹仿好莱坞的大片,但这种模仿又多是在技术层面上,而在剧本创作、人物表演和形象塑造、故事情节以及影片的立意方面驻足,导致学习的只是皮毛。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中国的类型电影存在过分的娱乐化倾向、浓重的商业趣味和技术的粗糙化问题,还存在重明星、重颜值的拜金主义倾向,导致电影市场畸形发展,社会效益极低,这也是第五代导演的商业大片多年来备受诟病的关键原因。
中国类型电影若要摆脱上述困境,就要在“本土”二字和“中国精神”“中国故事”这些关键词上下功夫。国家电影管理部门在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方面,要更大倾斜地扶持带有精英立场的电影,要求电影工作者既要学习好莱坞电影精湛的技术,又要学习好莱坞电影弘扬美国主旋律的这一精神特征,要倡导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学以致用,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特别要扶持那些能把中国文化融入电影中的大片,鼓励这些影片走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与世界对抗,而是强调要立足中国,胸怀世界,面向未来。只有这样的胸怀才真正能够表达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不是对抗性的一元论文化,中国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它强调整体性,在文化交流中很容易体现出它的包容特征,而这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精神。要坚信中国文化一定能够为人类的未来贡献其巨大的精神营养。
最后,是电影艺术本身的问题,存在艺术追求上的无名状态。如果说1980年代的导演和演员都是认真地创作、表演,在力图表达一种清晰的艺术精神的话,那么,1990年代以来的电影就出现了认识上的模糊,到了21世纪以来就出现了非常混乱的局面。电影到底是艺术,还是产业?在1980年代电影人的眼里,电影自然是艺术,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很多电影人那些,电影就是产业。一些有影响的电影研究者也持这样的态度,他们最为关心的是电影的票房,正如戴锦华所说的那样,学者们成了电影票房的背书者。对艺术特征的放弃或模糊恐怕是新世纪以来电影界最大的问题之一。诚然,电影艺术是集体创作,需要资本的投入,所以电影也可以说是一门商业艺术,但无论是什么样的商业艺术,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艺术,商业只是其伴随物。正如一个人一样,是精神与肉体的结合体,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肉体的欲望需要,那是低层次的,当然是基本需要,但在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时,更多地讲的还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体,此时,其肉体的存在只是隐性地存在。电影也一样,当一部电影呈现出来后,它就是艺术,商业是伴随者,是隐性存在的。所以,电影市场不能简单地被资本控制,不能让投资人和制片人随意指挥,要尊重导演的独创精神。反过来讲,投资人和制片人要想获得丰厚的商业利益,就要尊重导演的艺术精神,把电影当成艺术,这样,电影才能拍得好,才能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
当然,这里要强调一下导演现在的问题。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以前,导演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精神还是传统的,所以,那时的导演多选择从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它至少有一个成功的底本,但现在的导演大多直接写剧本或找一些商业性很浓的无名作者写剧本,这虽然与当下文学不会讲故事的特征有关,而更多的还是在于电影想独立于文学门类之外的念想,这样面临轻视剧本的问题。剧本是电影的核心,轻视剧本就等于在根本上轻视艺术。
在表演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因为市场的畸形发展,导致制片方和导演多用人气高的演员,且为了使市场的号召力强,不惜放弃艺术本身的规律,一个大片中往往有几个主角,且平均分配时间,这样一来,电影就不再重视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演员们也是浮光掠影地出镜,根本深入不到角色的灵魂里,一场电影看的时候热闹非常,但看完后就觉得毫无意义,一个形象也记不住。而在运用新技术方面存在技术大于表演、技术大于人物的特点。
还有一个艺术环节是缺失的,即电影评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评论是电影上映后精英们与大众交流的方式之一,也是电影的传播中非常重要的引导方式。电影评论既有赞美的,也有批评的,目的在于促进传播的同时,指出电影的优缺点,维护电影的艺术精神。但21世纪以来,电影评论在一段时间是缺位的,或者成了电影生产者的合谋者,没有独立的精神。新媒体产生以后,大众评论泛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电影评论缺失的问题,但是仍然缺乏真正有见识、有思想精神、有艺术高度的评论者。
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些艺术创作本身的问题,就要从电影市场的机制、导演的定位、演员的投入以及评论者的培养等诸多方面去解决。虽然与欧美国家发达地区的类型片创作相比,我国的本土类型片还不成熟,但是凭借着电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华语电影人的不懈探索,中国本土类型电影已经逐渐开始在世界电影市场中崭露头角。面对其在当下巨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作为创作主导中国导演,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坚持 “本土化”的基础上,把电影放在宏观的体制背景下,以坦诚、客观的态度深入社会现实,在与观众达成情感共鸣的基础上,揭示更为深刻的社会现实和人性思考;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导的电影观众,也应该积极的提高自身的观影品味,回归经典艺术作品,回归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培养和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对当下中国本土类型电影创作提供积极的反馈。此外,中国电影的权力机构,也应当在履行电影“把关人”的职责基础上,以更加包容和尊重的态度对待电影艺术,以开放和进取的精神制定相关政策,努力引导中国电影进一步走向世界,以此促进中国电影工业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 沈国芳:《观念与范式——类型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② 饶曙光:《中国类型电影:理论与实践》,《电影艺术》,2003年第9期。
③ 杨世真:《美国类型电影观念中国化接受中的变异问题》,《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④ 郝建:《类型电影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⑤ 沈国芳:《构建类型电影的新观念》,《当代电影》,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