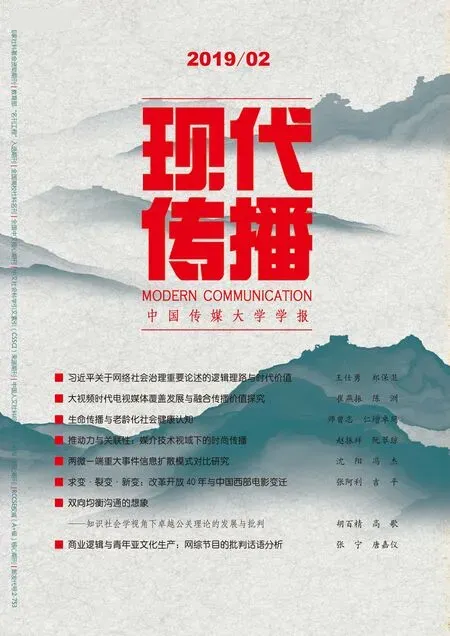仪式、压缩、断裂与永恒:农民工的媒介时间特征研究
■ 李红艳 牛 畅
一、提出问题
时间不仅是社会形态的一个指标,而且是社会规则变化的一个标识。从农业社会的自然时间到工业社会的机械时间,时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时钟设置的机械时间观念对劳动管制产生了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使用时钟时间来管理和组织工人,并使之内化为新的工作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任务导向的工作替代了之前以自然节奏为基础的工作时间,定时劳动意味着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进行明确的划分①。严格的时间控制和场所规范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官僚化规范的重要规则。同时,生物学家研究指出,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时间的质的经验、时间基础上的独特性,甚至是对美的渴望,都是整个生物界的特征,而非仅仅是人类社会生活所独有的②。因此,可以从信息视角来理解人类时间,既然“信息交换是生物秩序的一种现实”③,那么,“信息时间”(information time)的属性便是将人类世界、自然界与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需求关联起来了。卡斯特把信息与传播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引入了永恒的时间(timeless time)这一概念,他指出在网络社会中,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不清,导致个体的生命时间节奏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生活在一个似乎没有时间限制的场景之中。基于工作和技术之间关系的调整,人们一生的工作时间被缩短了,这将会导致社会凝聚的制度,导致年龄战争。④因此,卡斯特提出了关于网络社会新的假设,“网络社会的特征是生物与社会之节奏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周期观念的破灭。”⑤人的生命历程由此发生了改变,技术把死亡从人类的生命中抹除,死亡“总是他人的死亡,而我们自己的死亡则是意外惊奇中的遭遇。通过将死亡与生命分离,并且创造技术的系统来使得这种信念得以长存,我们在生命范围内建构了永恒。因此除了我们被圣光笼罩的那短暂一刻,我们都已成为永恒。”⑥换言之,当死亡从生命被“消除”的时候,信息成为一种“永恒的此在”,替代了人们的生命节奏,也置换了人类的生命时间。同时,即时传播将全球的信息集合在一起,信息便不再向人类提供历史背景,而是在与历史分离的或者撕裂的状态下进行传播,这便导致网络时代的人们被放置在无时间、无历史的精神世界中,引发了“一种永恒的即时性、一种连续性和自发性的缺乏。”⑦安东尼·吉登斯用时空距离来表明人类社会时空维度的不断变迁过程⑧。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进入非嵌入化(dis-embedded)状态,这种非嵌入式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不再受到一些固定的,或者说嵌入的传统社区如村庄,或者说是自然如季节、土壤和地貌等的控制,人们可以选择如何进行生活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扩散与普及,时间的规制和空间的设定在21世纪并没有消失,反而细致入微地渗透到社会的每个环节中了⑩。“时间的障碍被风俗习惯的扩展所打破,信息被存储起来以便随后使用,或者传给未来的一代人。”
在论述技术与世界的关系时,沃尔夫冈·希佛尔布施指出:“我们一旦认可了每一项技术都是一种尝试,要让自然服从于它的规则,达成这个目的的物质手段就是机器。而造成的新现实不过是一种阴谋诡计,是一个分身,或者自然的一个化名,那么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事每次发生,世界都成为了一部世界机器。”在“世界成为世界机器”的时代,我们也已从工业主义的发展模式进入到一种新的社会技术范式(socio-technical paradigm),出现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尽管如此,在这个时代中,进步依然是关键,过去是不可重复的,现在是短暂的,而未来则是无限的和可开发的,时间是同质的、客观的、可测量和无限可分的。当媒介时间替代社会时间成为计时工具时,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也在重新塑造着人们对时间的认知,从以自然节奏为主导的时间感知、到机器时间的时间感知再到信息时代的时间感知,媒介时间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大众生活的工具和标杆。“在以土地利用为主要生计方式的传承中,乡村的时间意义通过‘集体记忆’表现出来。‘集体记忆’即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加强,其中对社会结构影响较大的当属农民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农民工城市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移”,即从在日常生活中从农业时间的体验转变为工业时间的生活,从农村居住空间搬迁到城市居住空间,这种位移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自我陌生化农村、继续自我社会化的过程。它涉及农民工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转变过程。就时间意识而言,在乡村社会中,农民的时间是按照自然节奏来规制的,这里的自然节奏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外在的自然节奏,即季节的循环流动;第二层含义是指身体的生物时间,“我们的作息与地球的光明和黑暗循环相关,我们的生命遵循着成长和衰退的自然周期。”而当机器时间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不得不适应机器时间来调节个体的生活和工作时间,同时,金钱的价值观念取得了统治的地位,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生态性的,即,非个人的、匿名的,以及在不断进行计算的事情。”换言之,四季的轮回在传统农业劳动中,扮演着既日常化又神圣化的角色,而在城市的社会时间中,四季的轮回对工作时间几乎不会带来任何影响,某些行业的市场与四季的变化关联性较强,但是其工作时间的固定化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在这种夹缝的生活状态中,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在适应城市时间节奏的同时,利用媒介形成了作为农民工独特的媒介时间属性。
本文借用卡斯特“永恒时间”的概念,将其与媒介接触行为结合起来,使用媒介时间这一概念,从不同视角论述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城乡之间流动中,个体在信息时代是如何获得不同群体的时间属性的?这种时间属性与社会秩序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媒介时间,并非是从媒介技术角度而言,也不是从媒介管理视角而言,而是指农民工在媒介使用中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特征、以及这种时间特征与其在城市中日常生活的关系。
本文所采取的研究工具为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资料主要来自于笔者自2011-2018年之间在北京地区对郊区农民的调查,以及自2005-2017年对北京市农民工群体进行的调查。
二、文献回顾
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种时间立场,媒介技术通过对时间的压缩来实现瞬时性、无序性和零散化等特征。媒介时间的即时思维影响了人们的认知、记忆与行动,造成了当代文化纵深感的消逝。媒介时间安排社会事件发生的时间,媒体以对时间的操纵权将生活的逻辑完全颠覆。时间和空间在媒体的表达中,处于被动和安排的角色,媒体成为时间框架的制造者和运营者。媒介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显现出人类不同的时间感受,而技术的不同形态,则与人类的时间意识结构有一定的对应性,电视数字化进程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人类深层心理中试图把握与控制时间的欲望。媒介时间在未来的电子世界中会成为新的时间参考标准。而后工业社会的媒体意味着时间量度的媒介化、时间分配的媒介化。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电视被认为是所有大众传播类型中最合适充当增进城市认同的互动中介。农民工在城市生活实践和工作积累中,利用媒体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提升了他们对媒介本身的基本使用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媒体普及率已经超过传统媒体。他们使用新媒体主要以人际交往、休闲娱乐功能为主,集中于对QQ和百度的使用,他们对新媒体的评价也要显著高于传统媒体。新媒介技术的出现,在当下中国的数字化城市发展过程中,使得(介于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信息缺乏者人群凸显,信息缺乏者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使用ICT技术模式的改变,则可能会促进一种新的集体认同的形成,并形成新的文化表达。
现有研究或者从媒介时间本身出发,研究媒介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或者从农民或者农民工媒介接触的行为进行考察,或者从信息占有与群体分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上述研究没有侧重考量媒介时间在农民工群体属性形成中的影响力。本文从永恒时间这一概念出发,考察农民工的媒介时间观念的特征,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上述研究无疑是一种补充和发展。本文认为,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有四个特征:仪式性、压缩性、断裂性与永恒性。下文将按照这四个特征分别论证,最后对信息自由权和所有权问题、私人与公共信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三、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一:仪式性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失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网络之后,尽管依然保持着农业时间的观念,但身体却已经被搁置在另一个“时间场景”中了。在这一“时间场景”中,随着对自我的身体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不断调适,他们在逐渐学会利用新的技术来调适自我,以便应对这种不适应的“时间意识”,而可以提供多元化信息的媒介技术,成为他们调适时间的主要载体。因此,在对城市生活的适应中,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的第一个特征——仪式性,逐渐凸显出来,仪式性特征主要有两个表现形式:乡愁性和可逆性。
乡愁作为农民工时间观念核心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影响了农民工在媒介使用时的习惯与态度。“乡愁”则是在媒介使用中他们提到最多的一种表达,同时乡愁在媒介时间中的凸显,也成为他们利用媒介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具体而言,乡愁体现在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建构所建构的媒介关系中,大部分被访者认为,在城市中他们无论是工作的空闲还是休息时间,主要是把媒介看成是主要消遣工具,无论是阅读还是看电影或者是唱歌游戏,都依靠媒介来实现。而那些实现了整个家庭在城市中定居者,其乡愁意识并未由此消失。
“我爸妈以前在老家种地,但他们不喜欢种地,就出来做小生意了,岁数大了,现在就给别人打工。我们全家现在都在北京啦,每个月有四天的休息时间,全家会一起爬爬山、或者去公园溜达溜达。但是,还是觉得城市里的生活少点什么。”
“还是在家乡好,想玩的时候找得到朋友一起玩,可以一起去娱乐场所,或者单纯吃吃饭喝喝酒。在北京,闲下来了也没什么朋友一起玩,最多的时候就是看看电视。现在除了手机上网看电影,聊天之外,其他好像也没什么玩的了。”
乡愁在媒介时间中不仅体现一种潜在的情感依恋,而且体现为生活中与城市生活空间的“疏离”状态,这种“疏离”也是在心理空间上与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疏离。随着农民工群体对城市生活适应程度的加深,乡愁性渐渐从显性的意识表达转为隐性的行为表达,由此过渡到仪式性特征的第二个表现:可逆性。
列维·施特劳斯指出,仪式本身不仅可以将过去与现在关联起来,克服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对立,同时仪式还可以克服历时性和共时性内部的可逆时间和不可逆时间的对立,无论是纪念性的仪式还是悼念性的仪式都假定,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过渡在两种意义上都是可能的,举行仪式这一事实意味着将过去变成现在。春节时间,是农民工家庭在打工之余一年一度可以让工业时间“终止”、可以令农业时间“循环”的一种可以“人为操作”的“永恒时间”。对他们来说,无论是长久的城乡分离,还是短暂的城市分离,其最终目的都要指向年终的春节时间。而春节时间,是中国农历的时间,也是中国传统时间的一种仪式化延续,相对于阳历时间而言,阴历时间总是处于变化中的,因此每年的春节时间也不是固定的,人们总要通过阳历的时间进行“计算”。尽管如此,春节,依然被视作一种“弹性化”的和“可循环”的时间。春节团聚,意味着人们要“放弃”工业时间、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回到曾经熟悉也一再被记忆反复加强的“传统时间”的感知中。
仪式性的感知体现在媒介时间中,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媒介产品中乡村时间的缅怀,这种缅怀是通过一种刻意将农业时间节奏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
对于年长一代的农民工而言,通过网络所获得的与乡村生活之间的虚拟联系,是一种被强制的时间感知,他们在这种跨越地理距离的时间感知中,将现在的时间投射到过去,又将过去的时间投射到现在,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转换,使得他们的媒介时间出现了一种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同时又以现实时间的意识,影响着他们在现实中的意愿与选择。
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而言,通过网络所获得与乡村生活之间的联系,则更多地是基于同学之间、同伴之间的联系,随着生活场景和社会经历的差异,这种联系渐渐稀少了,在城市生活中,他们的媒介时间便呈现出飘忽不定的特征。一方面,无法像父辈一般缅怀乡村的农业时间节奏,在当下的社会时间中又觉得没有根基,“返回乡村去”成为他们在媒介时间里形成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以承受当下的时间观念为前提的。
当“生活时间”只剩下“工作时间”的时候,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媒介时间便成为他们与世界对接的一种“时间接口”。这个“时间接口”通常对接的一方面是乡愁意识,另一方面对接的是返回乡村的潜在诉求。因此,乡愁性和可逆性构成了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中仪式性特征的核心内容。
四、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二:压缩性
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勒提出了工作时间的定额劳动研究,目的是为了从工人手中取得工作的控制权。亨利·福特将该原理运用在大规模的流水线作业中,打卡上下班成为遵守时间的一种描述。在后来著名的霍桑实验及人际关系学派的主张中,对工作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均没有在这一点上受到质疑。这种工厂制度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控制模式,目的是对工人体力的控制,逐渐延展到办公室工作中,严格的时间控制和场所规范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中职业官僚化规范的重要规则。任务取向与时间取向的转换,起初这种“新的时间规制是从外部强加的,即通过把时间与劳动力沟通的制度,以及强迫在工作日连续工作来实现的,之后它们连续内化为劳动者的日常劳动时间观念,并且在可靠的机械时钟得到普及的同时,这种时间观念也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1973年,丹尼尔·贝尔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更是将其替换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他的核心理念是,过去存在的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 system)已经失范了。在这种变迁中社会结构与政治是根本分离的。服务业社会便是后工业社会。因为在前工业社会中,农业劳动是最普遍存在的工作,而在后工业社会中,工厂工作成为典范,到了后工业社会社会服务型工作则占据了支配地位。
从乡村社会的共同体进入城市社会中之后,农民工“暂时”失去了共同规范的约束,但受制于工业时间的规制,同时他们的行为又被正在兴起的信息社会的时间意识所规范,因为位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中心的是信息劳动力,这些信息劳动力处于中心的原因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以及他们继承的财富所造就的某些有利条件。对于服务业的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不仅仅是任务取向的,也是时间取向的,两者合二为一的时候,时间便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被压缩的特征。而在媒介时间的观念中,被压缩则意味着需要在“剩余”的时间里,“实现”被消耗的工作时间里所积累的愿望。而这些愿望只能由作为工具和作为伙伴的媒介来承担了。媒介因此被挤压、被收缩,也被收编、被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媒介时间的收缩性特征,首先是通过在媒介中寻找“认同时间”的形式实现的;其次是通过在媒介中“浪费时间”来呈现的。
服务业工作的农民工,在城乡社会变迁中,从媒介时间的压缩性中力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寻找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在此过程中,也凸显了农民工个体化的自发性努力。对青年一代的农民工而言,服务业、物流业的工作由于其工作时间的“漫长”,在这些行业工作的农民工,其媒介时间中渴望寻求认同的感觉尤为强烈。每天睡觉6个小时,工作14-16个小时,其余的时间便是他们的媒介时间。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身体在城市之中,但是心灵却飘荡在乡村与城市之间。而在媒介时间里,他们的身心可以全方位地感知着城市,在被压缩的媒介时间中,城市景观甚至是全球化景观、乡村景观被融合了,因此,压缩性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身心与媒介的时间在这一刻,成为一体。换言之,媒介时间中农民工的客体和主体在压缩性的过程中,既使自己成为主体,也生产了作为主体的客体和作为客体的主体。
其次,压缩性特征也体现在将个体时间“免费销售”给媒介时间的过程中。在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无论选择何种职业,或者不断调换何种职业,职业时间之外的个体时间,通常被媒体时间所置换。这一点在老中青三代农民工身上表现得都很突出。“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月薪4000多元,一个月能休息3天。看电视直播、上网购物、喝咖啡和打游戏,看直播一般看偏游戏的比较多。上网的话最喜欢跟人聊天,偶尔去购物。”个体时间的有限性,在媒介时间的压缩性中被延伸了,在这种全方位感知的延伸中,个体在新一轮的循环中更加自觉地不仅仅将个体时间“免费出售”给媒体时间,而是将个体时间“直接等同”于媒介时间了。
简单而言,媒介时间的压缩性特征意味着农民工在媒介时间中,寻求着一种“脱离乡村”后的共同感,也在媒介时间中,感知着身心在城乡之间的“合一性”。但遗憾的是,这种“合一性”仅仅是技术时间中“虚拟”出来的。
五、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三:断裂性
卡斯特认为,真实虚拟的文化伴随了电子整合的多媒体系统,以两种不同的形式促成了当代社会里时间的转化,亦即同时性(simutaneity)与永恒性(timelessness)。一方面瞬间对于全球信息的流转,为社会事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即时性;另一方面,随着媒介中信息在全方位的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互动,在媒介中各种时间混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无始无终的时间拼接画面,这种多媒体时代的无时间性或者时间的永恒性,也是媒体时代文化的一种特色。换言之,媒介缩短了时间和空间差异,产生了即时性文化,“即时性文化在媒介时间的规范中是短暂的,也是快速的……”这种短暂与迅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断裂。同时,当下社会正在从大众社会向网络社会过渡,其主要的社会关系特征之一在于铰链式关系,即“关系本身以牺牲它们在相关的单元或成员为代价变得越发重要”。基于上述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特点,城乡之间不断游荡的农民工,其媒介的时间与乡村社会的时间、城市社会时间之间所呈现出的断裂性特征,首先体现在全方位感知中的媒介时间鸿沟中,其次体现在城乡信息在媒介时间中的断层过程中。
首先,全方位感知中的媒介时间鸿沟,是指在压缩性的媒介时间感知中,当农民工的个体时间被媒介时间完全侵袭后,他们的感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感体现在个体的心理失调中。地理位置的转移、身体位置的移动、职业时间的转换,在媒介时间中,呈现为不同程度的裂痕,即笔者所说的媒介时间鸿沟,这种媒介时间的鸿沟,在逐渐从乡村到城市定居的群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笔者用一个案例来说明:
我从农村到县城打工,在农村时,先是用卖两头肥猪的钱购置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价格为340元)。1990年,又用两头肥猪钱换回了当时很流行的录像机,1995年一家人搬去城里打工,攒钱购置了彩色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当时,21英寸的长虹彩电花了2700元,容声牌冰箱花了2800元,小天鹅牌洗衣机花了880元。彩电和洗衣机至今还能正常运转,只是由于买了更新的款式,被替换了,闲置在一旁,但也没舍得扔掉。
案例主人公成年时期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从乡村社会中对媒介的购置、到城市定居中媒介类型的更换,在她眼里,媒介更像是一种“新家具”一样,也像是“未来”生活的符号一样,需要不断更换。她虽然居住在县城,但是家里并没有网络,只有当两个外出读书的孩子寒暑假回家时,家里才开通网络。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在她的眼里,更多是一种媒介形式的差异和媒介使用的差异,媒介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蕴含了乡村社会时间与城市社会时间的巨大鸿沟。
其次,媒介时间断裂性特征的表现在于城乡信息在媒介时间中的断层过程中。信息对于曾经居住在乡村继而迁徙到城市、同时又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定期移动的农民工的身体而言,是一种物质的运动和位移过程,在这种类似于物质的运动中,他们不断对自我的身体进行着规训,同时也进行着身体主导性的自我培育。在这种信息的物质运动层面,身体也抵达了另一种状态,即弹性状态。正如韦伯斯特所说:“随着后福特主义从以生产为导向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系统转变,社会不仅减少了产业工人的数量,而且生产了更强大的个人主义和以消费为中心的个人,信息在个人生活中必然承担了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消费者必须找到什么是可以用来消费的;其次拥有个性的个人渴望通过消费来表现自己”,人们在信息中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不同信息结构,这些信息结构反过来促成了个体的弹性时间与弹性身体,这些弹性特征也意味着信息本身的分层特征,弹性身体则意味着“身体”不再是物质性的身体,而成为信息世界的“身体”,“身体”在信息的弹性中不断被赋形。在媒介时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个体一方面在媒介时间中寻找信息的潜在交往性,另一方面在媒介时间中寻找信息与城乡社会之间的潜在对接点,这两个层面的过程加剧了媒介时间中压缩性中信息的分层状态。而信息的分层状态反过来也加剧了媒介时间在城乡之间的诸多鸿沟。
六、农民工媒介时间的特征之四:永恒性
在古希腊,时间是一种特殊的现成存在者,它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而运动则是理解时间的条件,因此,时间是一种物理时间:它是一种引起万物展现与消失的特殊的物理存在者,即一种自在的物理之流。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对时间的循环性做了颠覆性的修正,他认为人类事件具有周期性的时间,是虚假的一种循环,他强调了时间的直线性发展特征,由此可逆性的时间观念开始取代永恒轮回的时间观念,并最终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线性时间观的霸权地位得以巩固。“你的年岁终无穷尽,你的年岁永远是现在:我们和我们祖先的多少岁月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了,过去的岁月从你的今天得到了久暂的尺度,将来的岁月也将随此前规而去。……明天和将来的一切,所有和过去的一起,为你是今天将做,今天已做。”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时间,是作为实在的时间,它与被造物及其运动变化等空间意象联系在一起,与永恒的时间形成鲜明的对比。换言之,“在现代神学中,线性时间以对永恒的承诺为结论,但是在世俗的、现世的工业主义活动中,时间单位是有限的,时间是一种资源。”这种时间资源在新的媒介技术视野中,则转换为一种“永恒的现在”或者“永恒的当下”。因此,农民工的媒介时间中永恒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运动与流动中。运动旨在说明媒介时间中的动态与压缩性,而流动则旨在从线性的视角说明“永恒性”的固态性与扩张性。
就流动而言,乌苏拉·胡斯在论述新技术与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关系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节省劳动”的设备没有节省劳动?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工作程序的提高和服务行业工作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消费工作”不断增长,把负担增加在消费者身上;其次是服务的集中将时间、精力和交通成本转移给了使用者;再次是意识形态的压力;最后是有偿劳动的发展,割裂了公共劳动和家中私人劳动的关系。笔者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农民工的弹性时间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呢?原因在于媒介时间在媒介产品生产和消费中的“永恒流动性”,这种“永恒流动性”意味着个体在媒介时间中处于“无始无终”的状态,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差异、个体感官的不适感、甚至是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差异,都在这种状态中消弭了,人们在这种状态,获取的不再是信息,也不再是情感,更不是共同感,而仅仅是一种流动感。
流动中的身体,也是移动中的身体。信息与身体在“流动”中“相遇”,又不断在“分离”中进行“迁徙运动”,在信息流动中这种生生不息的“迁徙感”,呈现的是无休止的状态,我们无从确定其开端,也无法确定其终点。制度化的壁垒在这种无休止的信息运动中,甚至无法找到时间的节奏。
运动与流动密切关联,基于媒介在时间的无节奏中被不断分割、不断融合,媒介时间逐渐替代时间成为运动本身,农民工群体在媒介时间的运动中,被不断抛离轨道,又不断被抛回地面,一切都像是一种“技术游戏”,手机是他们参与这种时间运动的主要武器,也是有“永恒性”诉求的载体。
与其他群体相比,在教育和资源方面的困乏,使得他们在城市社会中获得的职业资本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在媒介时间的观念中,他们又处于城乡社会序列中的“前台”,“永恒性”因此在这一群体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七、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认为,从信息视角对时间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工群体的变迁特征,而将信息与传播结合起来,定位为媒介时间这一立场,可以通过对农民工媒介时间特征地分析,折射出农民工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迁中的角色与地位。通过上述描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仪式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乡愁性与可逆性。乡愁性是指媒介时间中呈现出来对乡村生活的潜在时间意识,而可逆性则是指媒介时间中呈现出来的农业时间、节假日等所关联的流动时间与流动行为。
第二,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压缩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认同时间”与“浪费时间”两个特征,“认同时间”是指从媒介中获得时间认知,进而获得对日常生活的认同感;“浪费时间”则是指农民工群体在缺乏社会关系网络中,如何通过媒介“消耗时间”的。
第三,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断裂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全方位感知中的媒介时间鸿沟和城乡信息在媒介时间中的断层过程中。其中媒介时间鸿沟是指农民工群体在城乡流动中对媒介时间的一种总体感知,而媒介时间的断层则是在信息接触中所“遭遇”到的陌生化状态,也可以说是信息上的“区隔”状态。
第四,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时间呈现出“永恒性”特征,主要体现在运动和流动两个属性中。运动是指媒介时间中的动态特征,而流动则从线性的视角说明“永恒性”的固态性与扩张性。
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农民工的媒介时间呢?即影响农民工媒介时间的主要因素有什么?笔者调查显示,影响农民工媒介时间观念的主要因素是职业时间与家庭时间。就职业时间而言,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时间,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媒介时间。鉴于他们的职业以服务业、物流业为主,因此职业时间往往不是固定的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通常的休息时间是按照每个月有几天来计算的。这种漫长的职业时间,导致他们的时间主要为职业时间所主宰。一定程度上,媒介时间被职业时间所覆盖。就家庭时间而言,调查显示,与家庭居住在一起的农民工,家庭时间与媒介时间会部分交融,而与家庭分开居住的农民工,其媒介时间在“永恒性”上比较突出。此外,还包括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这些因素如何对农民工的媒介时间观念及特征产生影响,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