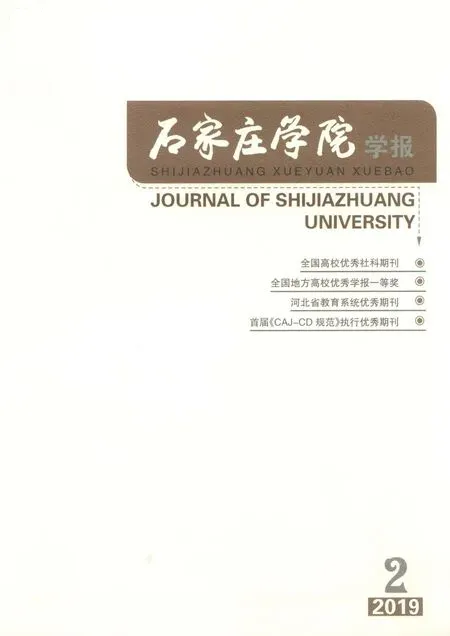汉文化生成模式的若干问题
王 健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本文研讨的汉文化,是指两汉时期形成的、以汉族为核心载体的断代文化形态。与拥有2 000多年历史的汉民族文化(即广义的汉文化)相比,它是一种狭义的汉文化概念。自新史学问世以来,传统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逐渐会通,为重建汉文化带来全新的视域融合。①1925年,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提出其“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的文献与考古资料互证的“二重论证法”,迄今史学界奉为圭臬。当代海内外时贤对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之关系多有高论,笔者赞成杜正胜先生的广义历史学方法论:“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这是新史学的历史概念。新史学植基于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取得则是来自于二十世纪田野考古。田野考古者与狭义的史学家只有分工之不同,其追求历史重建的终极目的则无异,而且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他们的学问就是广义的历史学……如果能从考古资料发现普遍意义的课题,推衍而成为普世性理论,这是才称得上中国学派吧。”见氏著《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张忠培、俞伟超主编《考古、文明与历史》,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版,第110页,第145页。其跨世纪成果结晶为断代文化史、文化通史的两汉文化卷和汉代考古发掘的大型报告,而各类专著、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跨学科研究成为重建断代汉文化的学术前沿。②新时期以来,大陆学术界的代表性著述有熊铁基著《秦汉文化史》、冯天瑜著《中华文化史》秦汉章、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华文明史》秦汉卷、郑师渠主编《中国文化通史》秦汉卷、龚书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秦汉卷等。专著和专题论文甚多,不予枚举。新时期考古学汉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代大中型墓葬、城市遗址、丝路交通、简牍资料等专题的发掘整理报告,如《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地下长安》等,以及大量的专著和专题论文。
反思当前的断代汉文化研究,虽然在重建古史的目标上取得重大进步,但尚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薄弱环节——即在上述大量的成果之中,真正将汉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文化生成的维度展开专题探索,研讨其生成的历史机制和发展模式的话题却较少受到关注,一些学术名家从宏观角度论述了秦汉文明或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特征和规律,③在新时期史学中,涉及到解读汉文化生成规律的开创性、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林剑鸣先生的《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结束语中提出“主旋律与变调、中外文明的碰撞、挑战与进步”三大规律性总结;熊铁基先生的《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对秦汉以来文化发展轨迹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判断,即连续性中的波浪式发展、统一性中的不平衡发展和承传性中的老翻新。在考古学领域,俞伟超先生的经典论文《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就探索汉文化生成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观点,为跨学科探索提供了学术指南。但鲜见系统探索和不同观点的争鸣。同时,对于汉文化生成的认知误区也缺乏理性反省。这种局面倘不改观,将加剧汉文化研究的碎片化趋势,也妨碍人们体认汉文化形成、演变的运行规律,这与汉文化研究的显学地位是不相匹配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现象的个体描述,而应当关注总体历史。”[1]1因此,激活汉文化生成的问题意识,叩问汉文化生成的历史机制,还原汉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风貌,是当下治汉史者亟待突破的研究瓶颈之一。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文献研究与考古新资料、新成果融合会通,追溯汉文化远承和近承的渊源关系,分析汉代历史主体的选择性继承机制,探索汉文化生成的创新机制,揭示其生成、演化历程所蕴含的动态模式及历史特征,辨析积非成是的认识误区,力求真切地把握汉文化生成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真相,并求教于方家。
一、汉文化对周秦文化的选择性继承
汉代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是探讨汉文化生成的基本问题。这种渊源关系,可以从远承和近承两个层次来分别考察。
先看汉文化远承关系。三代文化是我国进入文明时代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开创了中国道路的农耕文化、宗法文化、礼制建构和道德精神的基本模式,构成汉文化的历史源头。特别是汉文化对周文化的选择性继承更有突出的表现,留下了大量有迹可循的历史线索。
首先,农耕文化形成于夏商时期,至周代进一步完善,形成农居聚落、农业技术、农政思想、农神祭祀和农事诗篇等系列形态,对于汉代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承接周制的籍田仪式为例,是来源于原始公社时代的古老习俗,《甲骨文合集》所收材料留下商代籍田记录,西周时期的籍田亲蚕之礼已充分制度化,《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言论,反映了周天子亲率农事的古礼。西汉初年,汉文帝效法古制,在汉代首开籍田之礼。《史记·孝文本纪》载二年诏书:“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2]417西汉的景帝、武帝、昭帝和东汉的明帝、顺帝、献帝都曾亲耕藉田。籍田仪式的制度功能承载有“致敬鬼神”“率劝农功”和“亲民和民”等多重意义,成为汉代塑造农政仪典、倡导重农主义政策的文化象征。[3]
其次,宗法文化是上古血缘社会的产物,周朝宗法的原则为“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和按宗族血缘来“受民受疆土”的分封制。周朝的封邦建国分为同姓封国与异姓封国两种,目的是为王朝设置蕃屏。汉代封国制度就来自于西周分封传统,正如王夫之所指出:“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余波也。”[4]56周朝封侯有册命之辞,要在祖庙举行册命典礼。西汉初期封国建侯也循周制在宗庙举行,汉高帝曾“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毕以为王”[5]2260,“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5]527即是册命之辞。研究者指出,武帝分封三王的诰文就颇近似于西周封国建侯礼与锡命礼。[6]256正是在继承西周分封传统的基础上,汉代创建了郡国并行体制和相关的政治文化。
其三,礼制是三代国家的典章制度,西周初年周公制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7]1736,囊括了从国家体制到贵族生活规范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响久远的礼治传统。两汉文化中传承了很多周代礼制规范,以汉代婚俗为例,其纳采、请期、亲迎等“六礼”均来自《仪礼·士昏礼》。西汉末,王莽当权复古改制时重申亲迎之礼:“(元始三年)诏光禄大夫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倂马。”[5]355朝廷虽新定亲迎之制,但仍是遵“六礼”精神行事。再如汉代葬俗中的“正藏”与“外藏椁”制度,约发端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至少已成为好几个诸侯国的王陵制度,此即“周制”。汉代诸侯王和列侯的墓葬沿用了这种传统,其表现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被称为“汉制”。但后者却是由前者演化而来,其基本制度即模拟的内容是一致的。①详见俞伟超《汉代诸侯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辅阶段性》,出自《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其四,西周在政治文化领域最重要的遗产就是首倡“以德治国”,开创伦理规范政治的先河。周人倡导的德,“不仅是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功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8]336。汉代思想家“斟酌道德之渊源,肴核仁义之林薮”[9]1385,承续西周贵族政治的伦理传统,以儒家伦理为核心,融摄道、法等多元伦理精神,建构了中古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石。西汉形成的伦理政治结构包含有两大机制,一方面,汉廷用纲常伦理控制臣民;另一方面,士大夫用伦理政治原则制衡皇权。这种政治生态对于调节专制弊端、维系中古政治与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0]以上对于周文化的远承关系,被史家概括为“承周立汉”。
再来看汉文化的近承关系。近承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前朝文化,秦朝政治制度为汉制度文化提供了主体构架,《后汉书》称之为“汉承秦制”②《班彪列传》中有:“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后汉书》卷四十上,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 323页。[9]1323。楚汉相争期间,刘邦集团曾力图恢复楚制,但开国后很快转向对秦制的全盘继承,当然也有很多创造性的改良。《汉书·百官公卿表》将大量汉朝职官都注明“秦官”,反映了秦制在汉职官制度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专家指出:“汉初全国的官制、郡县制、二十等爵制、钱币和度量衡制度皆承自秦制,这加强着文化的统一性。”①详见俞伟超的《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出自《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但文中所列第三条,建筑用瓦的秦式卷云纹图案;第五条,秦文化中独有的茧形壶、蒜头壶、鍪、陶仓囷等模型明器,并指明为“随葬之俗”。将这两条现象列为继承秦制的表现,似有将习俗等同于制度的嫌疑。[11]183这种继承现象,反映了汉代制度建设的高度指向性和自觉性。②以郡县制为例,目前借助于秦简资料,对秦郡县级政区已能复原近千个县级区划,这些区划被西汉初期政区所继承。证明汉承秦制不光是郡县制的体制性继承,而是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秦县区划。这个历史侧面丰富了我们对汉承秦制的细部认知。
为何秦制度在列国制度中脱颖而出,并得到汉统治集团的青睐?战国数百年间,积淀有丰厚的列国制度资源。经过长期的制度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实践检验,秦制的历史优势脱颖而出。这种制度优势可以概括为变革性、创新性和高效性,是秦人政治发展中追求制度创新的雄厚成果。如陈直先生所论:“秦自商鞅变法之后……采六国之所长,创秦国之定式。始皇并天下以后,更加就损益……成为一套完整的政权体制。”[12]322这笔遗产为西汉开国集团所认同,田余庆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承秦立汉”[13]。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历史内在的脉络并没有发生断裂。秦制中许多积极的东西,通过汉初百年的继承和消化,而永远地留存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之中。”[14]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二世而亡,秦朝的大一统文化形态处于一种未完成时态。与借助武力征伐完成的政权递嬗相比,分立文化的整合是一个更为长期的渐进过程。一方面,秦始皇虽然抱有一统天下文化的雄心,用行政力量推行秦文化来整合关东文化,但秦与关东六国之间仍存在着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上的隔阂、对立,造成很大的阻力,统一进程举步维艰。睡虎地秦简《语书》透露,在秦人统治楚故地南郡半个世纪之后,南郡百姓“私好、乡俗之心不变”③《语书》是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南郡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一篇文告。此时秦在南郡地方已统治半个世纪,但当地楚人势力还有很大的影响。详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15]14,仍在抵制秦朝法令和“匡饬异俗”的政策。另一方面,秦统一后的行政制度,“总的来说,是以秦人对关东地区的征服、压迫和奴役为前提的”,“承担帝国繁重徭役的却主要是关东六国人”。[16]345秦地域政策引发的尖锐矛盾和冲突,成为导致秦亡的重要因素。
当秦代的短命统治结束和楚汉相争尘埃落定时,刘邦集团完成了政治上的朝代递嬗。新皇朝面对双重的文化遗产——既有秦朝遗留下来的一种远未完成整合的朝代文化形态,也有东周数百年诸侯分立形成的多元文化系统。对汉文化近承的历史资源要作具体解析,这是把握和分析汉文化生成问题的特殊前提。
还要指出,文化分合是一个动态的辩证过程。在指出秦代文化欠整合、区域冲突严峻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东周期间出现的文化融合现象。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市场的拓展以及各大文化圈之间空前频繁交往等多种因素的推动,在各个部族之间、各大文化圈之间出现相互吸纳、逐渐融合的文化趋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的扩张浪潮,使后者不断吸收、接纳中原礼仪规范、器用制度和文化习惯,两大流域在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所呈现的一致性,使得南北地区在文化上跨越政治和地域的阻隔而深度交流,并加快了文化认同,逐渐走向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统一体。[17]720从民族结构来看,经过东周以来长期的民族融合,华夏民族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文化分立格局也在逐渐消解之中。事实上,这种华夏文化的发展趋势为汉朝大一统的汉文化生成创造了条件。
以上表明,汉初文化的继承并非单纯地借鉴前朝文化遗产,而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周各大文化圈传统的选择性继承关系。下面就汉文化结构性成分的继承脉络作进一步的分疏。④为避免重复,上文谈及的制度继承不再列出。
在意识形态上,是对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的重点吸收。在汉代文化建构中,先后有几个融合高潮:西汉初年形成新道家,西汉中叶的儒家独尊和新儒学,西汉中后期的谶纬思潮。其中以楚文化为主体背景的道家文化,以齐鲁文化为背景的儒家体系,先后主导了汉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西汉前期,来自于战国楚地、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黄老学说,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治国思想。道家文化的源流可以追溯到楚国本土创造及发展,熊铁基先生的新道家研究,充分揭示出道家思想所折射的楚地域环境及其融入汉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⑤详见熊铁基著《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刘邦开国集团主要来自于西楚,该地域盛行的道家黄老思潮对统治者的抉择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8]
至西汉中叶,主流意识形态面临一场新的变革,朝廷政治文化酝酿着重大转向,在武帝时代推向演变的高潮。武帝发起的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政策,是对百家争鸣时代各种思想遗产的再选择。汉廷推行了一系列儒家制度化举措,使之取代黄老道家,成为汉朝的官方统治思想和主流的社会信仰。孟祥才先生的齐鲁文化史研究,充分解析这种文化趋势,齐鲁故地是两汉时期输送儒家精英和贡献经学典籍最多的区域,对汉文化精英思想的生成、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①参见孟祥才等《齐鲁思想文化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还需指出,以三晋文化为源头的法家文化、以燕齐滨海文化为背景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谶纬思潮,这些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精神文化,在汉代正统的意识形态结构中都扮演了不同角色,成为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汉代尊儒的表象之下,深层结构则是外儒内法的,其中渊源于三晋文化的法家思想充当了维护皇权、控制臣民的思想工具。
在文学艺术上,是对楚文学艺术浪漫主义传统和楚辞文体的重点继承。汉代文学成就显赫,被公认为中古文化史上的文学高峰之一。无论是汉赋还是乐府诗歌的艺术特征,在其历史渊源与继承关系的谱系之中,楚文化的传统都占据了显著的主干地位。刘跃进先生的汉代文学地理研究,发掘出汉文学的空间分布和流派特征,揭示了汉赋艺术特色中蕴含的楚文化基因。②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还有研究者指出,“汉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精神上的。司马迁则更加肯定‘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的合理性”[19];其次是艺术表现上的接受,汉赋的许多作品在艺术形式方面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楚辞的影响,再转化为汉赋“铺彩摛文,体物写志”的结构形式。如《七发》即是如此。汉代辞赋还直接承受“《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20],在文学上就是用物之美去象征、衬托、彰明人格及人品之美。汉赋对楚辞的这种象征手法的接受还表现在隐喻君臣关系的抒情模式中。在句式上汉赋对楚辞也有较多的接受,如枚乘的《七发》就有明显的楚骚句式。此外,楚辞对汉乐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代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形成也受益于楚辞。[21]306
在风俗文化上,以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大政治中心地域,即两汉的司隶州部,在整合七国风俗传统、生成典型的汉文化风俗过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在东周数百年间,七大文化圈的风俗模式有很大差异,形成关东与关西、北方与南方的空间分野。在居住、婚姻、丧葬、祭祀和衣食住行等各个生活层面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在西汉建立后,不同文化区的风俗形态中凝聚的文化共性因素愈来愈趋于突出,而各个区域本土文化传统却在共性因素的生长融合中趋于弱化。
以葬俗文化为例,考古研究揭示出关东地区以本土文化传统为基础,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扬弃了旧传统,逐渐变革而生成新的文化形态。黄晓芬教授的汉墓研究,揭示出汉墓形成过程中存在传统与革新的诸因素,汉墓的变革“来自传统的槨墓形制自身的阶段性发展变化,进而转变为新兴室墓”。东汉以后,“以穹隆顶为特点的砖、石室墓在帝国上下都呈现出一元化普及现象”[22]2,标志着考古汉文化在墓葬形制上的彻底确立。具体而言,室墓的生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槨内开通、向外界开通和祭祀空间的确立,“中轴线配置型的前堂后室式室墓,就是代表室墓走向完全成熟后的构造形制”[22]92,换言之,墓室层面典型的汉文化至此彻底确立了。
汉文化新生因素的出现,并非完全颠覆传统的全新文化,而是新的思潮与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以汉墓陪葬品之习俗为例,一方面,关中地域秦文化习俗对汉文化形成,贡献了富有发展前景的习俗性基因——生活化明器。研究者发现,秦葬俗率先摆脱周礼制的羁绊,对汉文化葬俗的生成具有先导性影响:“随葬囷和车的模型始于秦国,反映秦国社会形态和风俗习惯开始发生变革,旧的礼制正在被破坏,开启了汉代随葬囷、灶、井、车、家禽、家畜的先河。”[23]“从新器物来说,秦墓新出现的器物,常常以某种日用器物取代另一种日用器物,或用以实用器物取代陶礼器,最后陶礼器日趋消亡。如战国中、晚期出现的茧形壶、蒜头壶、缶、瓮等,即先后取代了陶礼器。”[24]亦有研究者指出:“战国晚期随着秦国征服六国的战争,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秦文化,文化面貌已经开始了走向统一的趋势。”[25]这种传播和涵化过程,体现了秦文化具有较强的传播优势。
另一方面,出现关东文化与秦文化互动融合的现象。以秦文化葬俗中屈肢葬蜕变为直肢葬的进程为例,研究者注意到,秦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地向东传播。其间,也可能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融合。例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一批秦统一前后到汉初的秦人士兵墓葬,“随葬器物具有明显的秦文化传统,但人骨葬式均为直肢葬。这些情况表明,从战国末年到汉初随着秦人与关东地区的交往,秦人墓葬的人骨葬式也受到了关东地区的影响,由秦式屈肢葬向直肢葬转化”[25]。这些现象说明,不同地域文化接触、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改变并非单向度的,而是互有取舍。
汉风俗文化对楚文化也有重要的承传表现。湖北睡虎地M77出土汉代简牍,其中《葬律》简为首次发现。[26]简文对西汉彻侯葬制的绞衾、祭奠、棺饰、棺椁、墓坑、墓地、墓园诸制度均有规定,所及葬俗与先秦时期的楚制非常一致,说明汉初葬制是承传了先秦楚制。①参见高崇文《从楚文化看楚汉文脉关系》,出自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再以西汉漆器为例,学者对扬州地区西汉墓葬出土漆器的研究表明,该区漆器种类、胎质、工艺及纹饰等均受楚文化强势影响,延续时间较长,西汉晚期仍可见楚文化的印迹。但该区漆器又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所以,它是动态继承楚文化,而非一成不变、故步自封的,即继承中有所创新与发展。这个案例表明,西汉先民在吸收楚文化精粹的同时,渐进性地加入自身的文化因素并融入汉文化。[27]216
再以汉代东方诸侯王的墓葬文化为例,其“斩山为廓,穿石为藏”的营建方式、前庭后寝的墓室结构、金缕玉衣的使用制度、配套的陵园和寝园制度,这一整套墓葬文化虽然容纳了战国王陵形制的一些元素,但其所呈现的文化共性因素便是典型的汉文化,恰好与汉文化生成的历史进程配合默契,是观察旧的文化壁垒被消除、汉文化逐渐生成的重要侧面。
还要指出,汉代风俗区域的融合是一个相对的过程,要用多样、统一的辩证关系来看待习俗融合的历史进程。《汉书·地理志》中的20多个风俗区,在大一统的文化进程中仍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地方传统,并不是简单无条件的文化统一。这种地域之间的文化个性差异,贯穿了两汉乃至中国通史。[28]270
以上考察显示,汉文化在文化源继承的客观选择上是多源并取,并没有狭隘地拘泥于某种文化形态作自我复制,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采博取的策略来吸收华夏文化圈内不同区系的精华成分,为自身生成和发展服务。这种生成机制,给汉文化带来源头多元、内涵丰富、高度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进步属性。
二、汉文化生成的创新表现
汉文化的生成过程,显示了汉文化具有选择性继承的能动机制和强大的创新机制。上文已重点论述了继承机制,此处拟就汉文化的创新机制作概略论析。
人才资源是文化创新的基础。繁荣的社会经济、发达的教育设施、广泛的文化传播渠道、功业建树的人生追求成为汉代文化人才成长的有利条件。文化精英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两汉时期各类文化人才的涌现及其个人创造力的迸发,将汉文化创新推向高潮时段。班固曾有一段话,对西汉中叶人才辈出格局给出了经典表述: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5]2634众多的治理人才,只是汉帝国文化人才辈出格局的一个侧面。两汉文化人才星空璀璨,从西汉的司马迁、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杨雄、李延年、张骞到东汉的班固、张衡、王充、王符、蔡邕、蔡伦等,成为两汉文化繁盛局面的人才支撑。由于历史的局限,两汉文化的民间人才很难知名见纪,但在汉画像艺术、古诗十九首乃至汉代器物遗存的工艺成就层面上都可以展现民间的文化创造,杰出的民间文化人也是汉文化创造的历史主体。
汉文化创新的历史表现,首先体现为制度创新。在政治制度领域,形成了皇帝制度、廷议制度、刺史制度、察举制度和太学制度等系列化的体制性制度,而在中观和微观制度层次上,出现了诏书传布乡里的扁书制、鸠杖尊老制、公车上书制等新制新规。②参见刘岱主编《制度篇:制度的宏规》,出自《中国文化新论》,联经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在汉朝问世的新制度中,如察举制的发明,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制度创造,它使职位不再世袭,“草野之士可以凭自己的才能获取官职。使先秦时期任职制度中任人唯亲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克服”[29]22。后来又逐渐演变为科举制,“在中国的文明模式中,这是惟一的可供选择的文官制度。而且在前工业时代,它还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政治形态”[30]233。
还有大量来源于前朝但有显著改良的新制,如弥补、调节汉代君主专制制度缺失的廷议制度:“廷议在秦汉尤其是在西汉,基本是有政必议,朝臣参议者范围比较开放。通过廷议剖析治国课题,集思广益,阐明利害,不同的方案在辩论中比较出它们的利弊长短,在此基础上为国家政务的决策提供了比较合理和切买可行的处理方案”,“两汉以廷议意见为断的情况居多数,这就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把君主决断限制在众议可行的方案范围内,使最终决策有可能建立在集思广益和正确判断础之上,对加强封建统治有重要作用”。[31]再如汉代盐铁官营体制的创新性:“这项政策有效地节制了资本,裁抑了兼并,剥夺了私家操纵盐铁的专利”,“由于冶铁作坊的官营适应于批量的铁器制造,极大地促进了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高。”[32]该体制渊源于春秋战国的齐国,但汉武帝时代创制做了显著的改革,属于改良型的制度创新。
其次,思想文化的创新。在社会思潮领域,先后涌现出新道家、新儒家和谶纬思潮;在学术领域,尊儒政策造就了先秦所未见的经学体系。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家,是在继承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和谶纬观念,进而提出具有时代标识意义的“谴告论”“天人感应论”,而倡导的富有改革精神的“更化论”,是一个在更高阶段上融合各家思想的更加发展了的思想体系。[33]209再如对传世《孝经》的经学解读、《忠经》的问世,将忠孝思想升华为中古特色的伦理体系。①详见陈少峰的《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些纲常伦理等社会观念不仅载入传世文献,还渗透到画像石、墓葬壁画、碑刻和简牍等物态文化载体中,对于整合“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9]2589的儒家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再如文学领域出现的汉赋体、前所未见的五言诗和七言诗,东汉宗教领域形成的原始道教信仰,中外文化交流带来的佛教传播局面等。
第三,社会风俗的更新。以婚礼丧服之制为例,先秦传统为“昏礼不贺”,到西汉中叶,汉宣帝颁发诏书予以解禁。周寿昌曰:“前汉承周制,故郡国二千石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至此特诏弛禁也。”[34]卷四社会各阶层婚嫁的贺婚、喜宴和饮酒等新习俗出现,婚俗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礼制。依周制,“天子七月而葬”,但西汉皇帝的葬期较之周制有很大改革,最短的文帝葬期为七日,最长的哀帝葬期一百零五天,无一与周制相合,可知西汉葬期迄无定制。[35]78-258在丧服制方面,周制为父为君为天子服丧三年,文帝对此也有重要改革,定制为三十六日。颜师古注:“此丧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创而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也。”又曰:“汉制,自文帝遗诏之后,国家遵以为常。”②《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4页。沈文倬先生认为:“皇帝公卿不实行三年之丧,中下级官吏以至民间是实行三年之丧的。”陈戍国解释道:“文帝遗诏定约礼之制,在皇帝诸侯王列侯至公卿少数人中间实行,而中下级官吏及民间则一如先秦周制,实行三年之丧。”见前揭《秦汉礼制研究》,第153-154页。[5]134再如葬俗方面,最突出的是家族茔地的兴起。这是土地私有制的实行后的一种新现象。如洛阳烧沟汉墓群中郭姓、吴姓、尹姓等系列家族墓地,与周代墓地大异其趣,是为“汉文化的新特点之一”[11]186。汉葬俗文化另一个突出特色是礼制传统的衰落和陪葬明器日趋生活化,模型明器的发达成为汉文化迥异于两周礼俗的新形态。③详见武玮的《黄河中下游汉至西晋模型明器研究》,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
第四,技术的创新。汉代是中古史上技术创新的辉煌时期,坦普尔(Robert K.G.Temple)教授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列举了中国首创发明和发现的100项科技成就,有多达38项注明是发明或发现于汉朝的。汉代的科技创造发明,其中包括铁犁、旋转式风车、曲柄摇把的发明、生铁炼钢、龙骨车、耧车、生铁炼钢、水排鼓风箱、造纸、瓷器、地动仪等,对农业、手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以农技的创新为例,史念海先生指出,汉代农业技术的改革“以赵过的代田法和泛胜之的区种法最为重要”。直到西汉末年,“区种法仅试行于三辅,代田法则三辅而外,曾在西北边地推广,山东似尚未沾其余泽”[36]181。新农具如三脚耧车、水排、石磨等逐渐问世,推动了农业耕作效率和粮食消费习惯的变迁。以耧车为例,在汉代又叫耧犁,崔寔《政论》中说“其法三牛共一犁,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37]180-181,这不仅有利于抗旱保墒,还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一直使用至近代。
第五,物态文化创新。如城市新规制下的汉长安城、洛阳城;社会消费领域涌现出熏香习俗和焚香专用的博山炉等④汉初为豆形,由于神仙思想流行起来之后,人们将熏香之器与海上有神洲之说结合起来,将熏炉做成想象中的神仙仙山状,多为山峦重叠,异兽奔腾。详见俞伟超的《秦汉青铜器概论》,出自《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葬俗领域出现的墓葬画像石和祠堂祭祀画像石,这种新事物几乎与汉朝相始终,成为断代汉文化的独特艺术事象;皇室、诸侯王葬俗领域出现的黄肠题凑、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等,以及其墓葬中生活明器如銗镂、盆形樽、鋞、魁、灯等,大多是先秦物态文化所未见的。仅以汉代灯具为例,就有高灯(豆式)、雁足灯(柄部作雁足形)、行灯(有柄似熨斗式,便于手持行走)、辘轳灯(卧羊式或椭盒式)、巵灯(巵形深腹)等,再现了社会上层考究的生活场景,品类令人目不暇接。[11]211
上述带有原创和创新意味的各类文化事象,大都是先秦和秦代文化中所未见的新事物,均是在旧质基地上渐变或突变而产生的新质事物。作为文化生成的结果,一种崭新的、充满生机和朝气的汉文化降临人间。大融合带来文化大更新,文化旧貌变新颜。从思想层面看,新儒家不再是原始儒家,新道家也不再是原始道家;从制度层面看,皇帝制度不再是东周列国的国君制度,墓葬格局也不再是七雄时期各行其是的纷乱制度。新内涵、新形式、新景观在涌现,旧文化很多形态及元素也在黯然退场。比如,制度名物领域中大量东方列国的官职名称、葬俗领域的屈肢葬等均成为历史陈迹。文化形态的新旧演替,充分展现了汉文化除旧布新的强盛创造力。
三、汉文化生成机制的几个特点
汉文化生成模式充满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它对周秦文化和七大文化圈遗产的选择性继承,既表现出中古时期断代文化形成的普遍特征,也带有两汉时期独特的历史烙印。
首先,在汉文化的生成过程中自觉性和自发性两种机制共驱并存。这个历史进程,既是汉朝统治集团致力于文化建构的自觉进程,也是文化自我更新、自发融合和自发选择的自在进程。汉朝君主及其官僚集团在实施文化统治方面具有较强的选择态度和设计意识,通过定向的文化选择和整合举措来推进文化的不断完善。在承周立汉的过程中,西周确立的伦理政治传统和宗法礼制传统,被汉代选择性地继承;汉代诸子的思想成就,都是建立在继承东周百家之学基础上并有所扬弃的再创造;在承秦立汉方面,秦制度体系被汉代统治集团主动采用,反映了一种自觉继承的生成机制。
汉文化生成中的所谓自发过程,其实是遵循着文化适应性的进化规律。七大文化圈各自的本土文化成分,除了政策选择的结果之外,更多的是文化适应性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汉代历史条件下社会具有自发选择机制,哪种文化因素更能契合汉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该因素就能够适者生存,自发地融入汉文化结构中得以延续和发展;反之,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文化成分便蹈入自然淘汰的命运。
其次,创新机制是新元素的增益和改变,才得以在继承基础上产生新质事象。文化创新未曾割断与渊源文化形态的联系,正如国外学者对文化创新原理的分析:“新事物指向未来,但它不是从未来中产生,而是从过去中成长起来。”[38]88以上述汉赋的创新为例,如果仅仅是继承和接受,还不能使汉赋成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除了直接继承楚辞的有关元素外,当今研究者将创新机制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多种句式交错运用,二是对楚辞对话体结构的改造,三是对楚辞中自然描写的超越。[39]上述新因素的融入带来了成功创新,才使汉赋在璀璨的汉文化宝库中占据一席之地。文化生成的结果使得汉赋这种新的文学形态降临人间,质朴雄浑、超迈往古,焕发着两汉闳阔进取的时代朝气。
第三,汉文化生成是原有各大区域文化整体性变革的结果,是七大文化圈基因的重组和更新。汉文化不是先验地存在的某种文化范型,而是在汉帝国建立后的广袤空间中,由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相互吸收、相互整合的新事物,是整合过程的最终结果。这是由不同地域文化贡献公共因子、不同文化圈基因交互重组的历史过程,也是各个区域文化产生自我变革为背景的整体转化过程,不是某种先验的既有文化对不同区域文化的置换,而是各个区域文化既有所革除又有所增益的变迁进程。
随着时间推移,不同区域文化体出现历时性的文化转变,汉文化风俗形态①这里指风俗文化的第一层次。率先在两京文化圈的所谓文化中心区形成,出现一种自两京向外推进的模式,率先辐射外围各大文化圈,然后逐渐向皇朝疆域的边缘文化区推展,各个文化区域共同走进新时代。
由于汉代广袤的疆域和众多文化圈的存在,就带来了共性文化因素的成长及其对旧文化的改良、取代这样一个漫长过程。以往将新旧文化更替的时间节点笼统地定在汉武帝时期。如同研究者所指出:“取代秦文化的汉文化,要经过六七十年至汉武帝时才形成完整形态;汉初期原有的秦文化和东方六国文化正处在重新组合的状态下。”[11]203按照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将汉文化确立的时间节点定在建汉之后大半个世纪左右。
需要指出,这种看法只是就汉文化整体形态的一般发展所给出的大概估计。而根据目前的深入考察,由于各个文化区本土文化传统的强弱不同、距离文化核心区的远近不同、传播渠道的通畅程度不同,所以汉文化形成的进度在空间上并不是平衡的。《汉书》中终军“六合同风,九州共贯”[5]2816的说法,其实是反映汉代人追求的文化理想。目前学术界对典型区域的实证性研究表明,实际上很多区域的汉文化形态确立、旧传统退场的时间坐标要晚到两汉之际甚至东汉中、晚期。可见汉文化基调的酝酿到成熟,在汉朝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范围内,决不是一刀切或一风吹而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从六七十年到200多年、跨越了众多世代才完成新旧交替的,所以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四,汉文化生成过程中的一体多元性。一体是指文化大一统进程中形成统一的文化价值、政治认同、伦理信仰等民族共同体的同一性内涵。如20世纪70年代曾在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先后出土的西汉帛画,虽然两地遥距千里,但南北两地帛画从内容到风格却极为接近,表明了楚文化的广远影响和汉统一后的文化融合趋势。但一体化并没有完全消解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历史个性。这是大一统文化模式下的多元性,秦文化区、齐鲁文化区、吴越文化区乃至楚文化区仍旧保留了鲜明的自身个性。例如,西汉杨雄的著作《方言》便是这种区域性的生动例证。文化区域性特点的流风所及,直至现代社会仍旧得以延续。汉代各个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交流、融合的互动过程,其中汉民族为主体民族,①吕思勉道:“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汉。”出自《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但“汉族”一词,近代方出现。是汉文化的优势载体和传播主体,其他周边民族在大多仍保持民族自身文化基因的同时,也大量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因素,形成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景观。
第五,文化生成是“内源”与“外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考察文化生成,既要追究本土根源,又要观照外来影响。林剑鸣先生曾将秦汉时期中外文明之间的互动,称之为“大规模吸收和远距离传播”[39]537,凸显了中外交流对于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巨大意义。两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十分辉煌。如同杨联陛所比喻的那样:“整个帝国的网络系统类似于一个巨大的酒瓶,尽管这个酒瓶里大多数时候都装着旧酒,但它能够不时地容纳一些新酒。”[40]3外来文明输入的新事物种类极为丰富,研究者曾将其分解为九个大类、近百种形态,认为它们的存在“丰富和充实了中国思想学术和汉代文化社会生活”[41]612。上述看法就目前中外交流史研究界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笔者认为,从汉文化生成的角度来考察,新事物输入的意义决不止于所谓的“丰富和充实”作用。汉朝这种开放地拥抱外来文明的姿态,固然体现了汉文化的包容性;但更重要的是,某些外来文明因素已开始把与汉文化的互动涵化过程转化为汉文化结构中的有机元素。最典型的莫过于佛教传入中国,在丰富了国人宗教信仰的同时,又给予本土宗教信仰重要的启示和影响。[43]印度佛教的一些思想观念、宗教仪轨乃至教团等形式要素,最终与汉朝本土的原始信仰相结合,促进了东汉道教的形成。上述过程中还涉及到文化互动双方的深义文化受容问题,有待进一步研讨。②详见王健《汉唐中外文化交流断想》,载《中华文史论丛》2004年第73辑。由此可见,文化交流决非单向文化移植,而是一种互相涵化的过程,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均发生变迁,从中产生出具备双方要素的新的文化组合。
四、汉文化发祥地说法的认识误区
在汉文化生成的背景中,是否存在某些研究者提出的汉文化发源地或发祥地?在汉文化生成过程中,有没有某种先验的特定文化源或来自外界的某种文化类型被用来置换、替代秦朝文化形态?
如所周知,大凡历史上任何类型的文化渊源,都是依赖于文化创造人群即早期民族为主体的。中国古史上的皇朝系列,按照该朝代开创主体的背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民族征服途径所建立的皇朝,通常称之为“征服朝代”,如夏商周、辽、金、元、清等;另一种则是由华夏族或汉族内部的各种势力集团通过武力角逐或政变方式所建朝代,如汉、唐、宋、明等。据此,可以分为征服朝代的文化和非征服朝代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的文化源头、形成模式有很大的差异。
先看具有征服民族主体的朝代文化。例如,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均具有早期民族征服的历史背景。崛起于晋南的夏族所创建的夏朝,其文化的发源地便是晋南豫西;商朝是由崛起于东夷背景的商族征服而建立,商朝文化的发源地是东夷地区;周朝则是由崛起于周原的周族征服而建立,伴随统治民族的更替,周部族取代商部族成为统治民族,周原文化便成为新兴周王朝的文化之源,“岐山是西周王朝肇基之地,是古老璀璨的周文化的发祥地”[43]。
中古时期的征服朝代中,征服民族的文化一般来说就成为该朝代文化的一支重要源头,如契丹文化、蒙古文化和满清文化,都具有朝代文化来源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或渗透到朝代文化建构之中。所以,元文化蕴含有蒙古文化的源头成分,清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女真族文化之源。例如,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曾是世界历史上最大帝国元王朝的首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它被认为是中国“大元王朝及蒙元文化的发祥地”,忽必烈在此登基建立了元朝;人们通常也将白山黑水之地视为清朝文化的发源地或发祥地,便是这个道理。而征服民族文化来到中原之后,经过与汉文化的长期交融,最终也整合融入了新的朝代文化。
另一种是基于同一民族内部的不同势力角逐而建立的朝代文化。汉朝文化就属于这一类型,同类型的还有隋唐两朝、两宋和明朝。这种类型所包含的朝代文化,无疑是中古历代文化的主导型。早在战国中后期,古代民族格局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楚、秦部族逐渐高度华夏化,中原地区的夷狄民族被融汇到华夏族体之中。秦朝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深度融合进入了新的统一进程。昔日七雄的划分,只能看作是政治实体的分立和文化区域的分野。因此,在汉朝对秦朝的鼎革过程中,刘邦集团取代秦朝和西楚政权,并不存在统治民族的更替,不具有民族征服的性质。刘邦虽然喜欢以“楚人”标榜,但这种身份认同只是视为楚地域文化的归属心态而已。汉初关东集团治理国家,体现了政治权力的更替;汉朝定都长安,是对关中战略优势地位的认同。汉文化形成的具体事实足以证明,关中文化并没有垄断汉文化生成的来源。因此,在中国古代史上伴随王朝鼎革带来的文化递嬗,不可一概而论。
汉文化是在秦朝文化的母基上,通过各大文化圈的再整合,并且与周边四夷文化互动融合的复杂进程中生成的新文化。所谓朝代文化发祥地,应包容了该朝代文化的制度、思想和风俗乃至物态文化的基础性发源之地。但在客观上,作为汉文化的整体,其继承层面的系列要素分别来自周秦时期的七大文化圈,是七雄列国区域文化精华的整合与荟萃。比如就制度渊源而言,秦文化是汉制度文化的重要源头;就儒家思想渊源论,齐鲁文化是汉意识形态的基本源头;长安和洛阳两京文化圈则酝酿了汉主流风俗文化。如此说来,汉文化就其渊源而言是多元的。易言之,汉文化的每一种组成要素各有其历史渊源;我们可以说齐鲁地域是汉文化意识形态的发祥地,但不能说齐鲁地域是整个汉文化的发祥地。这使我们只能就汉文化的某一种结构性要素或局部的事象,来探讨其文化源头或文化发祥地。
作为汉代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关中土著文化对汉文化形成的资源贡献度比较高,但不能说关中为发源地;同理,丰沛集团成为汉帝国的缔造者,其政治上起家的丰沛之地可视为西汉政权的发祥地;但无论丰沛地域亦或汉中地域,均非汉文化的发源地,只是对汉文化生成的资源贡献度较高的区域而已。因此,汉文化作为一种整体文化形态,并不存在特定的文化发源地。综上可见,所谓汉文化发源地的观点,不仅违背了中国历史上朝代文化生成的基本规律,也不符合汉代文化的历史真实。